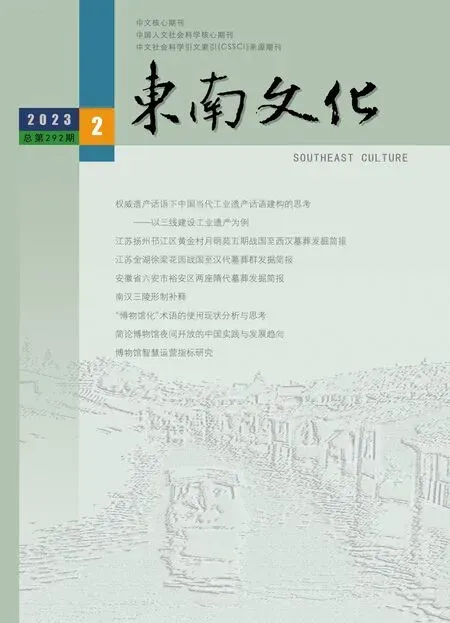博物馆展览中的观众参与:内涵、方式、困境与对策
常丹婧
(浙江大学考古与文博系 浙江杭州 310028)
内容提要:近年来随着博物馆对观众的重视和研究,促进观众的参与成为很多展览策划的目标之一。展览中的观众参与转向表现为观众的观展方式从单一的视觉观察到身体、情感、思维的参与,认知方式从被动的信息接受到主动的探索和思考,观展效果从浅层的学习和观赏到深度的学习和对话。博物馆展览中主要有以传播知识和促进理解、以激发对话和建构意义、以鼓励表达和分享观点为目的的观众参与方式。针对当前展览中存在的观众参与困境,博物馆可通过注重以促进观众参与为目的的阐释、观众主体和博物馆引导相结合、发展批判性反思与多视角解读、注重知识性与警惕娱乐化等四方面对策,促使观众参与在展览中的有效实现。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中后期以来,在新博物馆学的影响下,学界反思传统博物馆的转型以及当代博物馆面临的挑战和责任,很多问题都绕不开“观众中心”的理念,博物馆满足观众新的需求和期待、展览立足观众视角并促进观众的参与已成为学界共识。在此背景下,“观众参与”是近年来学界经常提及的概念。国外学界有不少博物馆学著作讨论了“观众参与”的相关内容,比如《吸引人的博物馆:发展观众参与的博物馆》(The Engaging Mu⁃seum:Developing Museums for Visitor Involve⁃ment)、《参与式博物馆》(The Participatory Museum)、《培养积极的长期参与》(Fostering Active Pro⁃longed Engagement)[1]等。国内学界也不乏观众参与的相关研究:甄朔南先生曾提到,新博物馆学与传统博物馆学一个明显不同的特点就是“尽可能让观众参与”[2];周婧景认为,区分“阐释性展览”和“非阐释性展览”的根本标准在于“能否促使观众参与”[3]。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Royal Ontario Museum,ROM)研究员沈辰总结了博物馆运营的六个方面,其中之一便是参与(engage⁃ment),并强调这是关乎公众的一个理念[4]。此外国内还有一些基于具体博物馆实践的研究,包括提升博物馆参与性、教育活动中的观众参与、对国外参与型博物馆的借鉴[5]等。
虽然“参与”在博物馆界已不是新兴概念,但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层面,“观众参与”的研究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和较多值得探讨的问题。由于在当前的博物馆研究中,“参与”一词包含了不同参与主体、不同参与阶段以及不同参与目的下多种类型的参与,所以为了避免概念混淆,本文主要讨论展览中的观众参与。那么如何理解展览中观众参与的内涵?在不同的展览目的下观众参与的方式及其特征是什么?此外,即便当下的博物馆展览已有不少提升观众参与性的实践,但不容忽视的是,实践中还存在一些阻碍观众参与以及由观众参与引发的问题。围绕以上问题,本文旨在辨析展览中观众参与的内涵,分析展览促进观众参与的方式,探讨展览实践中阻碍观众参与的因素并提出解决策略,以期为提升观众在展览中的参与提供一些思路。
二、展览中观众参与的内涵辨析
(一)观展方式:从单一的视觉观察到身体、情感、思维的参与
公共博物馆诞生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博物馆对藏品的关注多集中在审美价值和物质属性上,与此观念相适应的是器物本位的展览,其展示目的主要是满足观众的好奇心和欣赏的愿望,观众主要通过对器物的视觉观察来完成参观。而随着收藏观念的转变和博物馆功能的多样化,博物馆出现了越来越多信息本位和现象再现的展览,这类展览通过提供语境化阐释和多感官体验等方式来促进观众的理解和建构,让观众超越单一的视觉观察,进入身体、思维、情感的深度参与。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观众参与只局限于多感官体验或具有操作互动属性的某些固定参与模式,观众参与理念强调的是通过多维度参与以促进展览与观众建立连接,使观众更积极地融入展览并有所收获。
(二)认知方式:从被动的信息接受到主动的探索和思考
传统博物馆常常将观众视为被动的信息接受者,博物馆作为知识权威向观众“灌输”说教信息,这种传播方式反映了行为主义的教育模式,即教育的目标在于传递客观世界知识,学习者在传递过程中得到教育者希望达到的理解,但教育者无视传递过程中学习者的理解及心理过程。而以促进观众参与为目标的展览将观众视为主动的学习者、探索者,反映了建构主义的教育理念。建构主义强调“头脑在活动过程中的参与意识,认为学习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被动接收的过程,相反它是一个学习者应主动参与对知识进行归纳总结后再吸收的过程”[6]。参与的观展方式使观众在展览中通过自主的探索和思考来获取知识,将自身原有的认知系统与新的知识信息融合和重构并形成个人化意义。
(三)观展效果:从浅层的学习和观赏到深度的学习和对话
观众在以视觉观察为主的展览中主要通过欣赏器物和浏览事实性信息来观展,这种观展方式容易使观众停留在一种浅层的学习,即被动、机械式的学习方式,这容易使观众将信息作为孤立的、不相关的事实来被动接受。观众缺少自主思考和归纳的过程,以至于没有相关知识储备和足够兴趣的观众很容易走马观花式地参观展览,展览信息很容易被过滤和遗忘。而观众参与的展览指向一种深度的学习,即理解性的学习、批判性的高阶思维、主动的知识建构、有效的知识迁移及真实问题的解决。在既定知识的理解和获取之外,观众还可以进行有意义的互动和对话,产生个性化、多视角的解读。展览更容易对观众的认知乃至态度、行为产生影响。
三、展览中观众参与的方式
(一)以传播知识、促进理解为目的的参与
知识传播是大多数博物馆展览的主要目的之一。在知识传播的目的下,为了激发观众的兴趣和主动性,使观众更好地理解展览内容、获取知识,博物馆会通过一些体验式、操作式、提问式等设计激发观众参与,将展览从静态的展示空间转变为互动性学习空间。有的展览通过提供感应装置和多感官具身参与带来的沉浸式、真实性的体验,使观众获得难以言传的知识。例如中国丝绸博物馆“万物生灵:丝绸之路上的动物与植物”特展展示了通过丝绸之路传播的食物、香料等,观众可以通过触觉、嗅觉体验了解丝绸之路对生活的影响;展览还增设了“气味电影”,观众可在观看电影的同时感受各种食物的气味,感官的刺激可以增进观众的深层认知并加深记忆[7]。有的展览通过提供观众参与的操作系统,引导观众在动手操作中了解蕴含其中的原理。这在科学类博物馆展览中尤其常见,一般操作系统包含物件、变量和未知的结果,观众通过操作引入变量,观察因果关系的变化,从而领悟科学规律。还有的展览通过提出问题引导观众主动思考、寻找答案。一般情况下,问题常出现在知识获得的首尾:在知识获得之前,问题的引入可以激发观众的学习和探索;在知识获得之后,问题可以深化观众的进一步理解和思考。在知识传播的过程中,观众通过自主地探索、发现和思考获取知识,而不是被直接告知答案,这也是参与和非参与的区别之一。
以传播知识、促进理解为目的的参与方式的理想结果便是观众理解了展览传达的内容、完成了自身知识体系的构建。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虽然知识的获取是由观众主动参与实现的,但实际上知识的传播往往在展览预设的框架之内。也就是说,观众通过参与理解知识这一认知过程是由展览方定义并控制的,观众参与性的发挥也局限在展览的设计范围内。
(二)以激发对话、建构意义为目的的参与
加拿大博物馆学者邓肯·卡梅伦(Duncan Cameron)曾提出博物馆是神庙(temple)还是论坛(forum)的问题[8],引发了学界对博物馆身份的反思。虽然这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问题,但提醒学界观众可以一种更平等的身份参与展览,这种参与打破了传统博物馆作为知识权威、观众作为被教育者的界限,使观众和博物馆共同参与意义的生产。有的展览或展览的部分内容没有固定的答案和意义,比如一些历史类展览由于时间跨度长、资料证据不足等问题,不能给观众呈现一个绝对的逻辑结果;一些科学类展览涉及争议性话题而没有明确立场;一些艺术类展览没有确定的或标准的答案等。在这些展览中,馆方可能是问题的提出者、材料的提供者、内容的阐释者,都不是以权威的声音固定展览交流的内容,而是提出问题供观众反思和对话,提供材料供观众解读,通过阐释为观众的意义建构搭建桥梁,展览对意义的协商持开放的态度。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的“永远有多远”展览不同于传统展览传递知识的教育模式,运用建构性展览叙事理念,以人类的生命观为主题,将文物藏品与当代艺术作品并置在同一空间内,为观众提供多种视角与维度,以此营造一个反思与探讨的展览语境。策展人旨在“构建一个存在于主观与客观世界之间的‘异托邦’,在那里主体经验有着充分的自由得以伸展与投射,并能够生成属于各自不同的意义”[9]。与前述参与方式不同,此类展览没有预设知识传播的框架,展览的目的是激发观众参与思考和意义建构,而不是向观众传递某个知识点,这种观众参与的方式更倾向于一种双向沟通。
相比之下,这种对话式的参与方式给予观众更广阔的参与空间和更深入的参与机会,但同时也可能带来参与门槛高、参与群体小、沟通效率低等问题。一般来说,一方面,很多观众对于博物馆的预期是通过参观展览获取知识和增进认知,但没有标准答案和固定意义的展览可能会造成观众理解的障碍和意义的混乱。另一方面,由于展览本身没有标准答案和固定意义,需要观众的参与才能建构意义,这意味着需要观众发挥更多的能动性,而观众的参与取决于自身的认知结构、既有经验和兴趣等因素,因此真正参与展览的观众可能只有少部分爱好者和有一定认知基础的观众。
(三)以鼓励表达、分享观点为目的的参与
展览中以鼓励表达、分享观点为目的的参与有多种形式,有的展览通过向观众提问与展览内容相关的问题以获取观众的评论和反馈,不仅可以让观众就展览内容作进一步讨论,也是观众了解展览信息传播情况的工具。比如,美国宪法号博物馆(USS Constitution Museum)在播放了1812年的一场战争短片后,向观众提问“这个短片如何改变你对海上战争的看法”,展览评论板收到了多种类型的观众评论,包括爱国类、反战类、支持战争类、共情类、对于博物馆的评价类以及无关类[10]。在展览最后收集观众的评论反馈是博物馆的常见做法,但需要注意的是,有具体导向的问题会更有可能收到有价值的观众反馈,将反馈和评论在展览空间内可视化更能激发观众的参与。
还有展览邀请观众参与争议性社会问题的讨论和决策,观众通过展览提供的资讯、知识,结合个人的情感、经验、价值观等,对争议性问题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立场。比如,法国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Muséum d´Histoire Naturelle of Paris)2007年举办的“苍蝇”(Mouches)展览通过文本、视频和纪录片、真实的苍蝇和艺术装置等,向观众提供关于苍蝇的信息和知识。展览的最后一部分以圆桌讨论的形式邀请观众参与投票,观众可以根据他们在展览中了解的信息决定苍蝇被捕获或被释放[11]。知识传播是博物馆的重要使命,但博物馆并不止于传播知识。这一展览不仅利用各种阐释手段使观众了解关于苍蝇的知识,还引导观众进一步反思和讨论,并赋予观众权力参与投票和决策,让观众的想法和决定影响展览的结果。
此外,有的展览激发观众在展览主题下分享他们的感悟和故事,使其构成展览的一部分。比如,美国明尼苏达州科学博物馆(Science Museum of Minnesota)2018年举办的“心理健康:心理问题”(Mental Health: Mind Matters)展览的一面墙展示了个人对心理健康状况的分享,旁边设置了“让我们谈谈吧”(let’s talk about it)环节,邀请观众在纸上写下他们愿意分享的有关心理健康经历的故事,这些故事也会被印刷出来供其他观众观看[12]。这种参与方式让观众更深入地融入展览之中,观众不仅是观看者、学习者,也是分享者、贡献者。
(四)思考与总结
上述三种展览的观众参与方式各有特点,参与方式的设定主要受到展览主题、展览目的等影响,观众参与程度的高低不是评判参与方式的标准。对于公众认知度低的展览内容,以传播知识、促进理解为目的的参与方式可以提高展览与观众的沟通效率,增进观众的认知效益;对触及个人的情感和价值观、无固定答案和意义、与个体相关的涉及社会问题的展览,以激发对话、建构意义为目的的参与方式可以使观众更平等、更深度地参与展览;以鼓励表达、分享观点为目的的参与方式可以根据展览特点,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将观众的声音融入展览。三种观众参与方式也不是互斥的和独立的,而是互相补充,有时在同一个展览中可以存在不同的参与方式。
总的来说,上述三种观众参与方式是区别于向观众灌输说教信息的展览方式,笔者认为观众参与的展览可以总结为两个要点——“展览的留白”和“观众的建构”。“展览的留白”意味着展览不是把事实信息、知识结果、问题答案全部呈现给观众,而是在阐释基础上给观众留出探索、思考、对话的空间;“观众的建构”包括知识的理解、思维的对话、观点的分享。有效的观众参与需要合理把握“展览留白”和“观众建构”,这涉及展览方的作用和观众能动性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而展览实践中依旧存在阻碍观众参与的困境,我们应进一步关注和反思。
四、阻碍观众参与的展览困境与应对之策
(一)阻碍观众参与的展览困境
1.展览阐释不足导致的观众难以参与
展览中的观众参与主要以阐释性展览为讨论范畴,“阐释性展览”是指以展览要素为沟通媒介,向观众传递藏品及其相关信息以促使观众参与的展览;“非阐释性展览”是指以展览要素为沟通媒介,向观众传递说教信息,仅用作物件识别或欣赏的展览[13]。可见阐释性展览的目标即为促使观众参与。随着博物馆的发展,与物件本体的内涵相比,物件背后的文化和故事以及与人的关系成为博物馆揭示的重点,也因此阐释性展览越来越成为博物馆的主流展览类型。然而,当下有不少展览虽然定位为阐释性展览,但依旧保留着非阐释性展览的特点,观众在此类展览中仍处于被动参观模式,难以实现主动参与。造成此现象的因素有很多,其中重要的一点可能在于博物馆对展览“阐释”的理解不够到位,主要表现为展览内容以描述性、说明性的事实信息为主,这样的展览方式对观众的吸引力和认知影响都比较有限,观众作为信息的被动接受者,难以参与展览。
2.无认知收获或认知偏差导致的观众无效参与
在有知识传播目标的展览中,观众的认知收获是衡量展览传播有效性的重要标准之一。为了吸引观众、提升观众的学习体验,参与性互动装置成为很多博物馆推崇的设计。“参与”被认为是与学习有很大相关性的概念,然而不是只要有参与性的互动、动手,就意味着学习的发生。观众在观展中有时会遇到虽然参与了却没有认知收获的情况,有的观众参与只停留在机械性的身体行为互动,但这种参与本身并没有给观众带来认知的收获,有时是因为设计本身的局限性,有时是因为观众没有理解互动背后的意义;有的参与性设计由于没有充分考虑目标观众的认知范围,使观众在参与过程中出现认知困难的迷惑状况;还有观众在参与之后产生错误的理解和判断,这些情况都导致了观众认知不理想的无效参与。虽然很多展览重视发挥观众主观能动性,给予观众探索和发现的空间,但如果没有配合馆方科学有效的引导,很有可能导致盲目或无效的观众参与。
3.思想体系灌输导致的观众被动参与
有的展览在思想体系上具有线性的宏大叙事特点,将多线性的历史简化为单一的过程,用统一性的框架替代了差异与多元。这种展示策略一方面容易形成“一言堂”的话语模式,影响了意义的协商;另一方面容易陷入片面的狭义视角,而忽视了问题的复杂性、历史的多样性等。这样的展览即便在形式上为观众建立了互动性的参与方式,实质上却导致了一种思想体系灌输下观众被动参与的局面。澳大利亚博物馆学者安德里亚·维特科姆(Andrea Witcomb)在探讨美国洛杉矶宽容博物馆(Museum of Tolerance)时,认为其采用个人主义的思想体系叙事,限制了对不宽容的社会基础进行更复杂理解的可能性。博物馆的设计理念基于时间顺序的线性设计,其策展意图是实现对观众的全面情感控制。观众参观宽容博物馆的过程是在高度管理下被告知如何思考和做什么,展览语言既有道德性又有说教性[14]。即便展览为观众提供了沉浸式的互动体验,但思想体系灌输式的展览在一定程度上容易导致封闭思想体系下的观众被动参与。
4.为博眼球而内容中空导致的观众假象/表象参与
当下部分博物馆过度迎合大众、吸引关注度而打造出博眼球的“网红展览”,看似引来一批公众的参与和产生一时的热度,但这种“热闹”的参与由于其内容中空、深度缺乏,可能只是一种假象或表象参与。往往这类展览没有长期深入的研究支撑,依靠花哨的技术和观点作为噱头来吸引观众,展览带给观众的更多是视觉和情感的冲击,观众沉浸其中获得短暂的快感,但缺乏深入的思考和感悟。一方面,这会导致观众的参与方式变得被动,即便观众可以在互动和参与中获得愉悦感,但实际上观众只能被动接受外部环境带来的感官冲击,使观众的参与流于表面而失去深度思考的机会;另一方面,展览注重观赏性而忽视知识的构建和传达,导致展览质量水准的下降和博物馆教育方向的偏离,使博物馆与其他休闲娱乐场所的界限变得模糊。
(二)观众参与困境的展览应对之策
1.阐释以促进观众参与为目的
如何理解阐释及其与观众参与的关系?在观众参与被广泛提出之前,关于阐释的讨论就蕴含了参与的意味。美国学者弗里曼·蒂尔登(Freeman Tilden)认为,阐释是一种通过使用原始物件、第一手资料和说明性媒体来揭示意义和关系的教育活动,而不仅仅是交流事实信息[15]。美国学者山姆·哈姆(Sam H. Ham)进一步强调揭示意义和关系的并不是阐释者,而是观众在头脑中的自我揭示[16]。英国学者格雷厄姆·布莱克(Graham Black)以促进观众参与为目标总结了阐释的原则[17]。由此看出,可以把观众自主揭示意义和关系的过程理解为观众的参与,这也是阐释的目的。进一步说,展览的阐释性工作应该引导观众在主动的思考和对话中形成具有个人意义的认知,而不只是作为信息的旁观者,以此才能更深度地参与展览。近年来,国内许多博物馆意识到阐释对于展览建设和博物馆教育的重要性,在展览实践中可以发现促进观众参与的阐释理念。江苏吴文化博物馆馆长陈曾路强调,博物馆教育首先应该聚焦阐释,阐释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最终展览呈现的效果以及观众利用展览环境进行学习和探索的程度[18]。良渚博物院第一展厅“水乡泽国”展览在介绍良渚文化时,不是直接告诉观众良渚文化距今多少年,而是先向观众提出“良渚文化多久远”的问题,并呈现一个包括良渚王国、夏朝、秦朝、宋朝的时间刻度尺,问题的提出和时间刻度尺的设计使观众主动地联系既有认知并进行比较,以此对良渚文化的时间建立更形象深刻的认识[19]。
2.观众主体和博物馆引导相结合
随着传统博物馆的转型,博物馆认识到观众在博物馆学习中是具有自主选择权、主动探索意识和独立思考能力的认知主体,因此很多博物馆在展览设计上强调发挥观众的主观能动性。不过博物馆在强调以观众为中心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博物馆的引导作用,否则将走向另一个极端。博物馆的引导可以帮助观众提升认知效益,减少无效的参与,比如细致的操作步骤讲解可以确保观众操作的有效性,启发性的问题可以激发观众深入的思考,教育人员在参观中的指导可以给观众个性化体验等。因此在博物馆学习中,既要突出观众的主体地位,即观众作为认知主体主动地获取知识、建构意义,又要充分发挥博物馆的支持引导作用。比如,山东孔子博物馆的“拜师孔子”互动展项通过细致具体的引导和拜师氛围的营造,使观众无障碍地自主体验拜师仪式、学习中国传统礼仪文化。互动展项主要有学礼、行礼、献礼、合影等环节,每个环节都有明确的示范动画和语音步骤提示,还有古琴背景音乐营造拜师情境[20]。又如巴西卡塔文托博物馆(Catavento Museum)的“预防青少年怀孕”(Preventing Youth Pregnancy)展览,有性教育者(同时也是心理学家)和博物馆教育工作者引导观众观看投影,在纸上记录,根据问题作出选择,根据选择进行不同的体验,分享故事和解决疑问[21]。博物馆教育者的指导确保了观众有效利用展览提供的资源,让观众进行个性化的选择和体验。
3.发展批判性反思与多视角解读
“博物馆源自于现代主义的思维,是启蒙时期的产物,强调的是科学证据、理性思维、分类秩序”[22]。但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博物馆不可避免地受其影响并产生新的变化。与代表权威、崇尚分类秩序的现代主义博物馆相比,后现代博物馆重视个人的经验与价值,鼓励个人意义建构。虽然并非所有博物馆都需作出改变,但这反映了博物馆更具包容性和批判性、更具反思力和行动力的发展趋向。在这样的背景下,博物馆不再只是呈现不可动摇的真理事实,而应积极介入社会议题、呼应当代社会的需求。争议性主题的展览由此出现,它们往往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因此也更强调观众的参与性,观众不再只是信息和知识的接受者和旁观者,而是积极参与社会问题的反思、讨论和解决。展览应避免狭义的预设和绝对化的表达,呈现多元的声音和多视角的解读,重点在于激发观众参与对话和发展批判性的反思。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史实展不是采用单一声音的叙述视角,而是呈现中方、日方以及世界不同身份的多种声音和视角。展览虽然有对大屠杀场景氛围的营造和对遇难同胞的哀悼,但显然不只是为了让观众沉浸于悲痛和愤恨的情绪中,而是通过大量物件、图片、影片等媒介客观叙述史实,引发观众在感性之外对战争、家国、世界等问题的进一步反思[23]。2010年德国历史博物馆(Deutsches Historisches Museum)“希特勒与德国:国家与罪行”(Hitler and the Germans:Nation and Crime)展览重新利用纳粹宣传机器生产的物件和图像来讲述不同的故事。策展人西蒙尼·埃尔佩尔(Simone Erpel)表示,这是一个通过各种展示策略避免创造“虔诚的”或“妖魔化”物件的问题。有学者对此评价,德国这一展览的独特之处在于其能够反思、摆脱和(或)批判传统的国家类别。创新性的展览和博物馆不只是对历史作出明确的解释,而是将其呈现为复杂的和多视角的面貌[24]。
4.注重知识性,警惕娱乐化
参与性设计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弥补传统博物馆静态呈现、被动欣赏的不足,增加展览的趣味性以优化观众的学习体验。许多展览的参与性设计也带有较强的娱乐属性,其本身并没有问题,因为“娱乐”也是博物馆的功能之一,这在博物馆的定义中便有体现[25]。但是需要警惕的是博物馆娱乐的本质和特征及其与其他休闲娱乐场所的区别,避免博物馆走入娱乐化的误区。美国纽约现代美术馆(The Museum of Modern Art)馆长格伦·劳瑞(Glenn Lowry)曾提道:“‘娱乐’这个词带有一种负面的含义或价值,它来源于法语词entretenir,意思是‘吸引某人注意力’或‘取悦’。自我发现或理解同娱乐没有半点联系,却与‘愉悦’相关。‘愉悦’一词也来源于法语,但其原始含义是‘自我反思’。”[26]劳瑞馆长的阐释可以为理解博物馆的娱乐带来启发,博物馆娱乐不能通过分散或控制观众的注意力,使他们被动卷入一种短暂的快感而丧失自主思考的机会,博物馆作为与知识、理性、思考相关的公共学习空间,应该为观众提供“理智的愉悦”[27]。上海科技馆“能源新天地”展厅的“能源挑战之旅”以游戏化的方式融入能源知识,让参与游戏的观众在有限时间里尽可能获得最多的能源分数,并产生最少的环境污染[28]。此展项不仅具有吸引力和趣味性,还促进观众对知识的获取和对环境意识的培养,并且赋予观众制定策略的自主性,使观众在游戏的过程中不断思考能源与环境的关系。
五、结语
如本文开头所述,“观众参与”是近年来学界经常提及的概念,促进观众的参与也是大多展览的共识。然而,博物馆对观众参与的理解不应局限于身体参与、互动操作类的参与方式,而应从更广义的视角看待观众参与的问题,同时考虑观众的认知特点、展览传播的有效性以及博物馆在当下的角色和使命等。笔者从观展方式、认知方式和观展效果三个方面分析观众参与的内涵,讨论以传播知识和促进理解、以激发对话和建构意义、以鼓励表达和分享观点三种展览目的下观众参与方式的特点,针对当前展览中存在的阐释不足导致观众难以参与、无认知收获或认知偏差导致观众无效参与、思想体系灌输导致观众被动参与、为博眼球而内容中空导致观众假象/表象参与等四个方面的困境,提出阐释以促进观众参与为目的、观众主体和博物馆引导相结合、发展批判性反思与多视角解读、注重知识性与警惕娱乐化的应对之策,希望对提升观众在展览中的参与有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