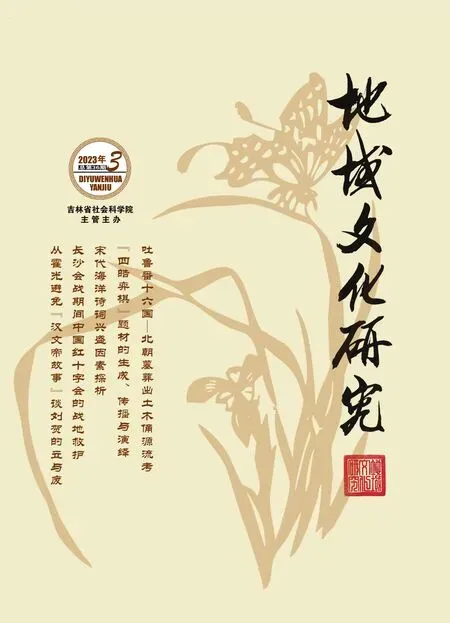宋代海洋诗词兴盛因素探析
康丹芸
海洋诗词是指以海洋景观、海洋物产为描写或叙述对象,或直接想象海洋世界,或描述航海行为以及通过描写滨海生活、海洋政事等来反映海洋、人类自身及人类与海洋之间关系的诗词作品。在长期以来的内陆文化环境中,宋前的许多中国古代文人因种种原因而无法进入海洋空间,海洋及与海洋相关的事物不能成为其常态可见的审美对象,“他们和海不发生积极的关系。”①[德]黑格尔:《历史哲学》,北京:三联书店,1956年,第146页。然而,宋人与海洋的接触却相当频繁,这使他们改变了前人与海洋较为疏离的空间状态,为文学与海洋的联结创造了条件,而这与宋代特定的内外环境有相当大的关联。
一、避籍与轮职
宋代自开国之初,统治者就定下“偃武修文”②(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1,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370页。的政策,形成了以文取士、文人主政的局面,③贾海涛:《北宋“儒术治国”政治研究》,济南:齐鲁出版社,2006年,第9页。仅仁宗在位期间就录取进士近万人,约为终唐一朝总数的2倍多,④刘海峰、李兵:《中国科举史》,北京: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04年,第162页。如此数量巨大的文人陆续进入官场,员多阙少,造成了宋代“天下有定官无限员”(宋祁《上三冗三费疏》)等严重超编的现象;又宋代统治者为“鉴五代藩镇之弊,遂尽夺藩镇之权”,⑤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070页。通过推行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使“上下相维,轻重相制,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①(宋)范祖禹:《范太史集》,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00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69页。。在以上因素的推动下,赵宋一代在官员任职上施行地区回避制度和定期轮职制度。地区回避制度“主要限制官员在本州、本县或邻县任官”②苗书梅:《宋代官员选任和管理制度》,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20页。,“应见任文武官,悉具乡贯、历职、年纪,著籍以闻。或贡举之日,解荐于别州,即须兼叙本坐乡贯,或不实者,许令纠告,当置其罪。自今入官者皆如是,委有司阅视。内在西蜀、岭表、荆湖、江浙之人,不得为本道知州、通判、转运使及诸事任。”③(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31页。曾巩在《送江任序》中所说“或中州之人,用于荒边侧境、山区海聚之间、蛮夷异域之处,或燕荆越蜀、海外万里之人,用于中州,以至四遐之乡,相易而往”即为这种避籍状况。而定期轮职制度则使文士的流动更为频繁,“中外任官,移替频速”的现象非常普遍,以致当时官员任职的时间普遍不足三年。④梅新林:《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欧阳修就在《自勉》诗中说,“引水浇花不厌勤,便须已有镇阳春。官居处处如邮传,谁得三年作主人。”而且,从北宋到南宋,地方官员的任期越来越短,南宋时期任期平均上已基本不足二年。⑤苗书梅:《宋代官员选任和管理制度》,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59-262页。
如此深度的避籍与频繁地换任制度使宋代地方官员的流动较其他时代更广、更快,宋代文人自进入官场之日起就要辗转于各地,这为他们与海洋接触创造了一定程度的条件,有宋一代有相当数量的文士有机会轮职至滨海地区担职。如梅尧臣,宣州宣城人,曾知建德、监湖州盐税;欧阳修,江西庐陵人,曾知青州;王安石,江西临川人,曾任鄞县知县;苏轼,四川眉州人,历仕于杭州、湖州、密州、登州;陶弼,湖南永州人,历任邕州、钦州知州;杨万里,江西吉州人,曾知漳州、除广东刑狱,等等。每个地区都有其独特的自然景观与人文风貌,而滨海的仕宦经历让宋人有了更多的机会去接触那些前人很少能触及的海洋风物,他们又有着强烈的史录自觉意识,这使他们对这些滨海风物给予格外的关注。如《予求守江阴未得酬昌叔忆阴见及之作》中“黄田港北水如天,万里风樯看贾船。海外珠犀常入市,人间鱼蟹不论钱”是王安石对江阴黄田港最深刻的印象;苏轼连作多首观潮诗词展示壮阔的钱塘海潮,并表达对当地农民及弄潮儿的关怀;刘弇知莆田,有“傍海千塍稻,由来䆉稏蟠。异时更虐飓,中夕舞惊澜”句,书写了当地海洋农业与飓风灾害(《莆田杂诗》);杨万里过广州,有《疍户》“天公分付水生涯,从小教他蹈浪花。煮蟹当粮那识米,缉蕉为布不须纱”诗展示海上疍民的日常生活;虞俦《食墨鱼有感》记载在滨海食用海洋水产的感受,等等。这些在传统文化以及文人们在内陆时少见的风物令他们充满好奇,于是纷纷进入文人载录。
此外,《庆元条法事类》记载的宋代地方官员考课内容有,“1.生齿之最:民籍增益,进丁入老,批注收落,不失其实;……3.劝课之最:农桑垦殖,水利兴修。4.养葬之最:屏除奸盗,人获安居,振恤困穷,不致流移,虽有流移而能招诱复业,城野遗骸无不掩葬。”⑥(宋)谢深甫:《庆元条法事类》,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9页。宋代文士游宦滨海,必然会接触和办理当地所倚靠的海洋事务,这是其政绩要求之所在,除为考课而记录自己对滨海事务的关注和努力外,他们也会“对新的所见、所闻、所感,做出自己的理解、判断或者反应,并把这一切表现在自己的作品当中。”①曾大兴:《文学地理学的几个理论问题》,《中国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研讨会论文集》,2011年,第48页。如柳永在任昌国州晓峰盐场的盐监时,作《鬻海歌》记录当地盐民的深重苦难;蔡襄在出知泉州时不仅在减轻民众负担、加强海洋军事防务以抗击海寇等方面颇有成就,而且他还在洛阳江下游出海口处兴建了被誉为“福建桥梁的状元”的中国历史上第一座海港大石桥万安桥,解决了当地一有海洋气象灾害就“沉舟被溺,死者无算”的民生问题,并在此期创作诸如“怪得寺南多语笑,疍船争送早鱼回”(《宿海边寺》)、“纳纳春潮草际生,商船鸣橹趁潮行”(《春潮》)等诗歌作品,陈偁后来知泉州时修护万安桥时亦作《题泉州万安桥》,以“缣图已幸天颜照,应得元丰史笔褒”句赞誉海桥建成之功;又如,由于受台风等天气影响,滨海地区经常发生海溢、海潮冲决海堤等海洋自然灾害,如淳熙四年(1177)九月“大风雨驾海涛……余姚县溺死四十余人,败隄二千五百六十余丈……定海县败隄二千五百余丈;鄞县败隄五千一百余丈”②(元)脱脱:《宋史》卷61,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332页。等,不仅造成民房的大量损坏,还造成人员的惨重伤亡,为缓解海患,被誉为“吴越四贤”之一的谢景初在浙江余姚任知县时就发动民众修筑海堤,作《余姚董役海堤有作》诗,表达自己对滨海民生的关切;赵师侠在莆田任职时作《诉衷情·莆中酌献白湖灵惠妃三首》记录当地民康俗阜、雨润风滋的繁荣景象。
观察以上所举宋代海洋诗词,可以发现其中除了与宋前类似的海洋景观书写外,更以记录当地风俗物产为盛,这表明宋人对海洋的接触与开拓已达到前代所不及的深度,他们眼中的海洋不再仅仅局限于景观物色,而更与社会文化紧密相关。
二、党争与贬谪
促使宋代文士任期缩短、流动加快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党争。有宋一代,从庆历改革、熙丰变法、元祐更化到崇宁党禁、和战之争、理学之争等,党争长期延续,士大夫们各自形成阵营,被卷入者不知凡几,党派之间水火难容、党同伐异,一方得胜,另一方的文士即遭贬谪,“党与既植,同门者互相借誉,异己者力肆排摈。”③(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003页。且受谪次数频繁、谪居时间久长④尚永亮、钱建状:《贬谪文化在北宋的演进及其文学影响》,《中华文史论丛》2010年第3期。,如寇准、丁谓、范仲淹、欧阳修、苏轼、苏辙、秦观、黄庭坚、邹浩、张耒、李纲、李光、胡铨、朱熹、刘克庄、范晞文、谢枋得,等等,其中不乏一贬再贬者。至于贬谪地,相比唐代贬地大多为西南诸道及岭南西部等内陆地区,宋代文士贬谪地更多在今两广与海南一带。⑤梅新林:《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
据宋徽宗在崇宁四年(1105)九月己亥的诏书中所言“应岭南移荆湖,荆湖移江淮,江淮移近地,唯不得至四辅几甸”⑥(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卷89,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2287页。,贬地分为四等,其中岭南为距京师最远、地理条件最恶劣者。南宋王朝与金人划淮而治之后丧失了大片领土,但岭南依然保留于版图之内,并依旧作为国土南端之极限被充作贬所。据金强统计,两宋被贬岭海的士大夫有超500人之多,且不同于唐代仅有少数如沈佺期、宋之问、韩愈等人贬谪滨海的情况,宋代文士大量贬往滨海,如卢多逊流崖州,寇准贬雷州司户参军,丁谓贬崖州司户参军,苏轼“责授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且诏轼合叙复日未得与叙复”①(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3891页。,又贬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苏辙贬雷州,秦观流雷州,胡季昭流钦州,赵鼎贬兴化军、又徙吉阳军,胡铨编管吉阳军,李纲贬万安军安置,李光、范晞文贬琼州,仅被贬往海南者就有近百人之多。②金强:《宋代岭南谪宦》,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9-428页。
而在这一过程中,谪宦们往往会经历一个从痛苦到平和、由无奈接受或排斥到融入与主动发掘、由忧惧到旷达的转变过程,这与他们对当地海洋自然环境、人文风物等的观照有很大的关系。首先,当谪宦初到僻陋滨海之地时,心态上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愤懑不平,海南带来的生命威胁更使谪宦们充满了对当地的忧惧与排斥,而地理上的偏远和生存环境的恶劣与文人心理文化层面上的“天涯”概念相印证,再加上远离中心、被主流文化所抛弃的情感,使谪宦们不得不产生虽生离而实死别的凄凉、绝望心理,如苏轼在被贬海南前在《与王敏仲书》中就痛苦地坦言:“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贻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当作墓。乃留手疏与诸子,死则葬海外。”其次,远贬海外势必要跨海而去,而海洋的凶险渺茫往往使谪宦们在短时间内经历巨大的生命两极变化和生存落差,“琼崖块隔巨浸,汹涌涛吼”,③(明)欧阳保等:《雷州府志》卷20,明万历四十二年刻本。苏轼在《伏波将军庙碑》中说:“适珠崖南望,连山若有若无,杳如一发耳。舣舟将渡,股慄魄丧”,李光感叹“迁流万里,落天一涯,孤帆涨海,寄此一身”(《祭马伏波文》),谪琼文士们对跨海之行充满极度的不安与恐慌;复次是在恶劣的自然环境影响下,海南岛文化废弛,其风土人情与中原文明格格不入,当地黎民往往巢居野服,“梗悍不驯”④(宋)宋祁,欧阳修:《新唐书》卷112,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3311页。“黎僚犷悍”⑤(清)萧应植修,陈景埙纂:《乾隆琼州府志》卷8,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年,第844页。,又文化水平低下,这种愚昧落后的行为与情感意识与中原截然不同,带给谪宦们强烈的陌生感与飘零感。
同时,尽管“减秩居官,前代通则,贬职在迁,往朝继轨”(沈约《立左降诏》),“三古以来,放逐之臣,黄馘牖下之士,不知其凡几。”(纪昀《月山诗集序》)这对于奸邪小人的流贬自是罪有应得,然而,从历代的贬谪情况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在当权者“凭尊恃势……宰割天下,以奉其私”(嵇康《太师箴》)的背景下,有大量正直刚贞、疾恶如仇的有志之士遭到贬谪的不公待遇,于是其表现出极大的愤慨与不甘,如秦观因为苏轼辩诬而成为新党党同伐异的牺牲品,这使他在被贬时产生强烈的冤屈感,在《冬蚊》中发出“蚤虿蜂虻罪一伦,未如蚊子重堪嗔”的愤慨;又如李纲忠心为国,却因主战而被主和派打击报复,一贬再贬,至于万安军安置,愤慨长叹“慨王室之艰危,悯生灵之涂炭,悼前策之不从,恨奸回之误国”(《伏读三月六日内禅诏》)。
上述这些因素无限压缩了谪宦们的生存空间,扼杀了其生命自由,“因正道直行横遭贬黜独处遐荒无可表白的屈辱感和愤怒感,一种因社会地位骤降为人歧视前途迷茫进退维谷的自卑感和孤独感,一种被整个社会和所属文化抛弃的恐惧感和失落感”,⑥尚永亮:《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以中唐元和五大诗人之贬及其创作为中心》,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页。给贬谪岭海尤其远贬海南的文士们带来了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与巨大威胁,极其剧烈的身心打击使他们往往像刘禹锡所言“悲斯叹,叹斯愤,愤必有泄,故见乎词”,以创作抒发其恨。自屈原以来,贬谪文学常表现出强烈的消沉与悲哀,或表现出“倦鸟得茂树,涸鱼反清源。舍此欲焉往,人间多险艰”(白居易《香炉峰下新置草堂即事咏怀题于石上》)这样一种基于恐惧心理的对人生忧患的逃避。①尚永亮:《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以中唐元和五大诗人之贬及其创作为中心》,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页。谪宦们在面对贬地风景时是无法激发出内心的审美冲动的,而往往将其作为宣泄内心情绪的对象。而宋代谪琼文士则更多出一份理性,可以对种种恶劣环境进行乐观的思辨,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逐渐适应自身身份的变化,心态也随之改变,其中,对于海洋的观照使他们逐渐消解贬谪的苦闷,反而多了分厚重的旷达自适与随遇而安。
以苏轼为例,在绍圣四年(1097)贬往海南途中他内心充满“首当作棺,次当作墓”的绝望,这从他在由惠州前往儋州的两个多月内数量既少、情感又低落的诗文中可以探知,即使乐观如他,在《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闻其尚在藤也,旦夕当追及,作此诗示之》一诗中也有“天其以我为箕子,要使此意留要荒。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之语,这种豁达更多是王水照先生所说的故作旷达。而在抵达海南后,苏轼在对海洋的审美观照与哲理思辨中领悟了先贤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并逐渐消解了远离“中心”的执念,在精神上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又在海南优美的自然环境与和谐平静的人文环境中慢慢适应与融入其中,谪琼三年后所云“我本海南人”(《别海南黎民表》)、“余生欲老海南村”(《澄迈驿通潮阁二首·其二》)、“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等即是这一由惶惑惊惧到平静旷达转变过程的见证。应该说,苏轼的这种旷达离不开他对海洋的接触与观照,离不开当地自然与人文社会环境的浸染,海洋带给苏轼以“最高层次的生命体验”,使其由饱含执着的悲剧精神走向自适的超越意识,最终“身处逆境,却能不为所累,超然物外,与世无争,在精神上达到一种无所挂碍的境界。”②尚永亮:《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以中唐元和五大诗人之贬及其创作为中心》,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页。
而南宋谪琼文士们更是通过对苏轼旷达精神的学习以及对海洋的审美观照,达到了对个人穷通畅达地放下与对生命自由自适的感悟。比如李纲,在得到贬谪诏命后,也不免心生悲凉,认为海南“皆骚人放逐之乡,与魑魅荒绝,非人所居之地。”③(宋)李纲:《李纲全集》,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第213页。贬谪海南、势必有性命之虞,于是“震惧之余,斐然有作”(《见报以言者论六事》)诗,表达强烈的悲愤之情与深刻的忧生之嗟。这种忧虑不安的情绪,在李纲进入海南前的最后一站雷州时达到了顶点,在岸边望见茫茫不见涯涘的大海时,对自己即将渡海时可能发生的灾难充满了哀情、无奈,但是他通过对苏轼等先贤的学习,并且在海洋的审美观照下领悟了人生意义,作《乘桴浮于海赋》,曰“虽七旱而何伤”,“虽万死而何悔”。海洋的宽大广阔、深沉渊博也让诗人的心灵更加开阔。“自哂井蛙真见小,望洋向若一卢胡”一语双关,不仅是说海洋气象让原本宛如井蛙的自己见识到了真正的广博,另一方面也暗含李纲对黑暗现实的嘲讽:之前受到的苦难何其渺小、政敌的迫害何其有限,如果自己的心胸如同海洋般广阔,这些苦难又有何惧!李光更是直接以“可是胸中未豪壮,更来沧海看鲸波”(《渡海·其三》)揭示其通过观照海洋感悟生命从而超脱旷达之“理”,由此亦可见海洋对于贬谪文士心态转变的影响与作用。
总的说来,党争与贬谪推动了宋代海洋诗词创作的发展。在“本朝文治之盛,前朝所不能及也”①(宋)曹彦约:《经幄管见》卷3,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第460页。的盛景背后,是“重文”国策下数量众多的文臣的宦海浮沉,由于两宋在政治上反复拉锯,各成阵营,党同伐异,常常一派主政,一派失势,占下风者被贬至岭海之地者不知凡几,其中不少官员被贬至广南西路的海南岛,元祐年间便有诏令曰:“沙门岛已溢额,移配琼州、万安军、昌化军、朱崖军。”②(元)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019页。这里四面环海,交通闭塞,远离中心。对这些人生被禁锢于海滨贬所的文人来说,他们在这一过程中有了相当丰富的海洋生活经历,这些不仅是诗作中宝贵的素材,更是人生中难以忘怀的深刻体验。他们以诗词来记录航海经历、海洋生活,这些又反过来激荡起他们生命的情怀——海洋是谪居岭海文士们观照世界、调节心理的重要媒介,他们常常通过海洋来安顿心灵,而海洋也深刻影响着他们的诗词创作。
三、通使与战争
宋代文士出使海外及与其他政权之间的战争也是使人才向滨海流动的重要原因,同时也为宋代海洋诗词的创作提供了特定的历史环境。首先是宋与高丽、日本以及其他南海诸国之间的交往。建隆三年(962)宋太祖即遣人出使高丽,与之建立了正式的通使关系,并在宋太宗即位之初达到两国奉使往来的第一个高潮,左司御副率于延超、司农寺垂徐昭文等人陆续出使高丽。由于辽阻隔陆路,两国使者皆以登州、密州海路为通道来往,为此,宋人在送行两国使臣时创作了若干海洋诗词作品,如王禹偁《送迤郎中使高丽》、李沆《贡院锁宿闻吕员外使高丽赠徐骑省》等,透露出“海水无波分岛屿,扶桑见日认藩垣。东夷休请萧夫子,好把诗书问状元”、“圣化今无外,片途莫惮赊。扬帆萁子国,驻节管宁家”的上邦优越感。太平兴国四年(979)命太子中允直舍人张泊、著作佐郎直吏馆勾中正“使高丽告以北伐”,雍熙三年(986)宋太宗再度发兵分三路北征契丹,以高丽国“接契丹境,常为所侵”,遣监察御史韩国华资诏谕高丽王出兵击契丹,发兵西会。然而宋军北征全线败退,高丽国虽然勉强承诺发兵,但并无实际行动。宋淳化四年,高丽文彭王王诏十二年(993),契丹大举入侵高丽。次年,高丽国遣使元郁向宋乞师救援,“朝廷以北鄙甫宁,不可轻动干戈,为国生事,但赐诏慰抚,厚礼其使遣还。”③(元)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8621页。
自此,高丽受制于契丹,始行契丹年号,与宋朝贡关系一度中绝40余年,与之相关的海洋诗词创作也随之停止。直至宋神宗即位,以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实行变法,宋王朝国内局面出现转机,出现了两国奉使往来的第二个高潮,与此同时,有关宋丽使臣往来的海洋诗歌又重新繁荣起来,如赵抃的《次前人赠奉使高丽安焘密学》、曾巩的《厚卿子中使高丽》、刘攽的《送高丽使》、苏辙的《送林子中安厚卿二学士奉使高丽二首》、刘挚的《送安厚卿二人使高丽》等等,这一期间的海洋通使诗仍然保有宋人大国上邦的自豪感,如“大明照海阳乌近,黑雾迎潮水怪腥。北貊左肩输策略,西垣右掖付仪刑”(刘攽《钱穆甫杨康功使高丽还为中书舍人书此为寄》)、“并使时推出众材,异方迎拜六城开”(曾巩《厚卿子中使高丽》)中以“怪”“貊”“异”“迎拜”等字眼记录对域外“他者”的超越,然而,宋丽之间并不像汉唐时期那样以华夏绝对的优势来往,“澶渊之盟”等屈辱令宋人在与高丽的来往中不得不放低姿态,诗歌中多了分“鱼龙定亦知忠信,象译何劳较齿牙”(苏辙《送林子中安厚卿二学士奉使高丽二首·其一》)的冷静。
不过,一方面,为了表示重视,宋廷对于高丽使臣提高接待规格,在物质待遇上“费悉官给”,使“待之寝厚,其使来者亦多”。高丽每次来华的使节团人数都相当多,而且逗留时间也较长,如在天禧五年(1021),高丽礼部侍郎韩祚率领179人来宋,居宋朝近一年,①(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40页。而在此期间宋廷却要花费巨大的财力、人力来接待使团,“所得贡献皆是玩好无用之物,而所费皆是帑廪之实”“所至差借人马、什物,修饰亭馆,暗丧民力”,给国家带来了很大的经济损失,这些负担又被转嫁给百姓,“高丽靡敝国家五十年,政和以来人使岁至,淮、浙之间苦之”。②周彦文:《宋代以来中国书籍的外传与禁令》,《韩国学论文集》,北京:北京大学韩国研究中心,1994年。故以苏轼为代表的宋朝官员提出“止绝高丽朝贡,只许就两浙互市”的建议,“熙宁以来,高丽人屡入朝贡,至元丰之末,十六七年间,馆待赐予之费,不可胜数。两浙、淮南、京东三路筑城造船,建立亭馆,调发农工,侵渔商贾,所在骚然,公私告病。朝廷无丝毫之益,而夷虏获不赀之利。……自二圣嗣位,高丽数年不至,淮、浙、京东吏民有息肩之喜。”(《论高丽进奉状》)另一方面,一些文士担心高丽使团中可能隐藏辽国间谍打探宋廷机密,给宋带来安全隐患,“高丽名为慕义来朝,其实为利,图其本心为契丹用。”③(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49,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0798页。“高丽之人,所至游观,伺察虚实,图写形胜,阴为契丹耳目。或言契丹常遣亲信隐于高丽三节之中,高丽密分赐予,归为契丹几半之奉。朝廷劳费不訾,而所获如此,深可惜也。”(苏辙《乞裁损待高丽事件札子》)鉴于以上因素,苏轼创作《元丰七年,有诏京东、淮南筑高丽亭馆,密、海二州,骚然有逃亡者》《顷年杨康功使高丽,还,奏乞立海神庙于板桥。仆嫌其地湫隘,移书》等诗词,表达不满,如“檐楹飞舞垣墙外,桑柘萧条斤斧余。尽赐昆邪作奴婢,不知偿得此人无”。在苏轼等人的强烈反对下,宋丽海上往来再次陷入僵局。
宋徽宗时期,北宋朝廷面对金政权的严重威胁,风雨飘摇。徽宗即位初试图调和熙丰与元祐党争,旋以“绍述”神宗为国策,虽造成宋与高丽间奉使的第三个高潮,然而做的是“壮朝廷之威灵、耸外夷之观听”的花架子文章,于国家之强盛无补。这一期间的海洋往来诗词有程俱《送傅舍人国华使高丽二首》、刘一止《望明河·赠路侍郎使高丽》等,其除以“鲸波霁云千叠,望仙驭缥缈,神山明灭”“长啸溟波又一游,眼中壶峤接沧洲。紫薇垣近三台象,银汉槎浮八月秋”这样华彩摛文的辞藻描写海洋景象外,更多的是“膏泽东南四十州”“看飞棹,归侍宸游,宴赏太平风月”之类自我麻醉、粉饰太平的成分。
到了南宋,宋丽官方关系完全终止,主要以民间贸易为沟通,与之相关的宋丽官方海洋往来诗歌创作也不再出现。不过,从大中祥符五年(1012)到祥兴元年(1278)的这两百余年间,宋丽之间进行了相当繁盛的民间贸易往来,甚至海商一度充当“官方”使者维系着双方关系,贸易的舰队就多达一百三十余批,人数近五千人。①杨渭生:《宋丽关系史研究》,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69-279页。宋日之间的海上往来也有类似之处,北宋时期由于日本“锁国”,宋日无政府层面的往来,直到大中祥符六年(1013)两国才正式开始官方交往。宋日交往主要由僧侣与商人推动,官方之间基本没有往来,于是两国间的海洋通交文学多以中日僧人的赠别送行诗的形式出现,如释文珦《送僧归日本》曰,“远人仍远别,把手话江皋。积水一韩路,古风八月涛。海门山似粒,洋屿树如毛。他日难通信,想思梦寐劳。”又《送禅上人归日本》曰,“今日送君归日东,便成永别恨难穷。海邦万里波涛隔,不似青山有路通。”不饰文典而充分运用白描的平铺直叙,海景刻画细腻、寄寓之情深刻,表现出清寂与平和冲淡的风格,富有“诗不离禅,禅不离诗”之韵。②(元)释英:《白云集》(原序),《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665页。而大多数宋日僧人的海洋赠别诗则多“波斯”“法空”“祸胎”“佛眼”“口鼻”等之类的佛教用语,与赞、偈类似,文学性不强。
此外,宋廷与东南亚诸海国之间的关系也非常密切。根据《宋史》《宋会要辑稿》《诸藩志》《岭外代答》等文献资料记载,与宋存在往来关系的海外政权或地区有占城、真腊、邈黎、三佛齐、阇婆、丹眉流、苏吉丹、单马令、凌牙斯加、佛罗安、婆罗门、罗越,甚至于勿斯里国(今埃及)、默伽猎国(今摩洛哥)、三兰国(今坦桑尼亚或索马里一带)等,宋政府大力促进这些海外地区使者往来中国,如太宗尝“遣内侍八人赍敕书金帛分四纲,各往南海诸番国,勾招进奉,博买香药、犀牙、珍珠、龙脑。每纲赍空名诏书三道,于所至各处赐之。……海舶久不至,使招来之。明年,至者倍其初,珍货大集。”③(元)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8916页。不过,与以上地区之间的往来更多是宋廷为获市舶之利而大力支持的,在丰厚的利润下,宋朝与海外频繁交往,形成了一条繁忙的海上丝绸之路,同时也为宋人带去了无数海洋物产、海外珍奇,这些都成为宋人笔下书写海洋的素材。
北宋在燕云十六州丧于辽后一直心有不甘,但一直没有能力收复,直到北宋末年,宋徽宗认为与金联合灭辽将可趁机收复燕云,于是在宋金“海上之盟”后,两国联军于宣和七年(1125)灭辽,然不久后便招致金人的大举南侵,高宗赵构南逃临安,与金朝划淮水—大散关为界,建立南宋。此后的九十余年间,南宋与金一直处于或战或和的状态。这一期间,宋廷多次派人使金,或以营救二帝为幌子议和,或在和议称臣后每年各种节日派使臣出使金国。在此情况下,南宋派往金国的使臣在出使途中创作了不少使金文学作品,其中,由海道出使或经过沿海地区时使臣们多有临海怀古之思的书写,如曹勋于绍兴十一年(1141)宋金和议后充报谢副使出使金国,劝金人归还徽宗灵柩,十四年、二十九年又两次使金,在使金途中在海路经碣石创作《临碣石三首》,其一曰:“肃我严驾,登彼绝阪。目极天渊,曾不知远。曜灵舒光,乐彼鲦鰋。”在思故魏武神功、表达“前迹可究,兴亡可悟”之幽思的同时,也抒发了诗人对隐逸海上、自由生活的向往之情;又李璧于开禧初年奉旨出使金国的海行途中亦作《使金诗》,“天连海岱压中州,暖翠浮岚夜不收。如此山河落人手,西风残照懒回头”,借壮阔美丽的山海景观表达对故国家园的热爱与山海沉沦的愤慨;再如周麟之在出使金朝看到金人强迫留北的宋遗民给军队造海舰、以备南下攻宋之用而“驱民忍作鱼龙食”,作《造海船》诗,对金人妄图以海道攻宋的行为表达强烈不满与讽刺,同时也对沦陷区水深火热的宋民报以深切的同情。
不过,正如曹勋《黄湾书事》中所说的“海边鼓角动星辰”,黄海、淮海区域从原来的腹地变成了宋金战争最前线,南宋的立国形势也变得相当严峻,时人章如愚即云:“江淮,手足也;海口,咽喉也;京畿,心腹也。钱塘面瞰浙江,去淮有千里之遥,涉海无半日之顷。江淮故要津,守御既备,仓促有警,未足为腹心之忧。巨海梯航,快风顺水,自海而入京畿,不信宿而直捣吾腹心。江淮之师虽列百万,各坚守御,岂能应缓急之援?”①(宋)章如愚:《群书考索》别集卷24,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429页。果然,建炎三年(1129)底,金人轻而易举突破南宋江淮防线,将高宗逼至海上,并开始“搜山检海”以捕高宗的行动,而次年春,“金人陷明州,夜,大雨震电,乘胜破定海,以舟师来袭御舟,张公裕以大舶击退之。”②(元)脱脱等:《宋史》卷26,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475页。随后又遭到浙西制置使韩世忠部“以海舰进泊金山下”“以海舟扼于江中”的截击,最终金军被逼进黄天荡,被困二十余日后方狼狈逃出。③(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23-624页。此番海河大战,不仅重挫金军锐气,还鼓舞了宋军士气,吕本中的《海上篇》即对南宋海军军威进行了深入描写,“天风万里起,海水高十寻。中有都人士,拔剑拯陆沉。素甲三十里,朱縢万千垒。誓身殉家国,援抱常切齿。东连海上兵,天挺三世英。艨艟山岳高,军储沧海倾。纵横长江动,军威千里空。”可惜,“拊手功可立”的大好抗金复国形势终因主和派“岛上复卖国”的退让而白白浪费,吕本中只能愤慨地望洋空叹“海外多君子,至今长恨水。”不过,宋廷在这次海战之后也认识到了海防的重要性,积极加强海洋军事力量,刘子翚的《巡寨偶书》一诗便对此“倚兹形势险,寇至常迁延”而“吾邦备宜先”的状况有所说明。
除了与金朝之间的海上交锋,宋元战争也多向海上转移。宋蒙承宋金旧事,于绍定五年(1232)两国结盟,端平元年(1234)联合灭金。然而,不久南宋便又招致蒙古的大举南下入侵,景定二年(1261)刘整投降蒙古,随后为蒙古建设了一支强悍的水军,宋蒙之间在此后进行了数次海上战争,其中亡宋的崖山之战就在广东新会的海域发生。在这样的环境下,催生出许多书写海洋战争的诗歌,比如辗转海上抗元而亲身参与和见闻了一系列海战的文天祥就创作了大量类似“诗史”的海战诗,如《二月六日,海上大战,国事不济,孤臣天祥,坐北舟中,向南恸哭,为之诗曰》《祥兴第三十三》《祥兴第三十五》,等等,对参与海战的人物和海战过程进行了深入细致的书写,而且“每篇之首,悉有标目次第,而题下叙次时事,于国家沦丧之由,生平阅历之境,及忠臣义士之周旋患难者,一一评志其实,颠末粲然,不愧诗史之目。”④(清)永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64,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408页。使崖山海战等战役的始末有了更完整清晰的呈现。
此外,南宋各沿海地区还屡屡遭受海寇侵扰。早在动荡不安的两宋之际,就有大量起义造反的农民和盗贼流窜南下,加入东南沿海地区的海盗集团,给社会治安带来非常严重的威胁,而到了南宋,随着“今日财赋,鬻海之利居其半”⑤(元)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454页。的海外贸易的兴盛,在客观上诱发了更多海盗活动的发生,东南沿海一带海盗日益猖獗,朝廷同地方政府与海寇之间的冲突贯穿整个南宋。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南宋频频发生海上抗击海寇的事件,有不少文人或领兵出征,或入幕参谋,在海上与滨海地区往来御寇,创作出不少与之相关的海洋诗词,如曾觌的《喜迁莺·福唐平荡海寇宴犒将士席上作》就是对宋军在福建福州一带“殄群丑,看一鼓雷奔,沧溟波静”后获得镇压海寇胜利的讴歌,类似的还有王亦世的《海寇赵某伏诛》、乐雷发的《桂林送人之琼州招捕海寇》等诗作。
海洋战争也引发了陆域民众向更远、更偏僻的海滨地区的逃亡,许多文人亦在其中,他们辗转滨海、飘零岛隅,在饱受兵燹之祸、流离失所的逃难过程中,创作了不少记录这一悲惨境况的诗歌作品,如林景熙的《避寇海滨》、《归自越避寇海滨寒食不得祭扫》等诗,深刻讲述了自己在宋元战争中冒着“腥浪”“水弱”之苦而不知“何处避”的惨烈状况,而仇远的《元夜叹》则描写了在流亡途中所见沿海民众所受的深重负担与灾难,表达“天险之防,以人心为本,而先使百姓憔悴,根本摇动”①(宋)梅应发:《开庆四明续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5991页。的愤慨。
四、转徙与迁居
除了以上原因的经行海域,宋代海洋诗词创作者中还有大量士大夫阶层之外的平民,如李清照、武衍、姚宽、赵蕃、姜夔、戴复古等人,亦有士大夫在入仕之前或致仕之后生活于滨海者,在这些人中,有许多本非设籍滨海,却由于战争、政治、经济等原因自本人起或因祖辈迁徙定居滨海。冰心在谈论文学创作时曾指出,“文学家的作品,和他生长的地方,有密切的关系。”②谢婉莹:《文学家的造就》,《冰心研究资料》,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第156页。创作者会根据其对所生长、生活地域生活的体验与理解,从大量身边可接触到的事物中遴选、提炼的创作素材。宋代文人向沿海地区的辐辏骈集使其与海洋接触的机会大大提高。
首先,宋代自立国起就一直处于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复杂的民族关系及长期不断的战争中,致使原本生活在临近西北、北部战场的居民纷纷向远离战火的南方迁徙,“民去本业,十室而九空,其不种之田千里而望,流移之人心已弃决,非朝夕可还也。”③(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074页。其中靖康之乱引发的迁徙是文人南迁中规模最大、人数最多者,所谓“高宗南渡,民之从者如归市”④(元)脱脱:《宋史·食货志》,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4340页。,数百万北方民众移聚南方,相应地,向以北方内陆为主要“根据地”的文人群体也大率迁徙南地。葛剑雄先生在其《中国移民史》一书中对1391 位靖康南渡的北方文人进行迁入地考察后得到这样的结果:这些北人中只有27%迁入江南西路、荆湖路、川西四路等南方内陆地区,而其余73%的大部则迁入两浙路、福建路、两广路及淮南东路等南方沿海州路。⑤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4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93页。继续考察其迁入的府州后发现,迁徙至临安府、台州、明州、越州府、湖州、温州等两浙地区的沿海府州的北方文人数量高于非沿海府州,尤其临安,“自累兵火之后,户口所在,裁十二三,而西北人以驻跸之地,辐辏骈集,数倍土著。”⑥(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73,钦定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而福州、兴化军、泉州等东南沿海地区也聚集了大量来自内陆地区的文学移民,这与中国古代历史上“永嘉之乱”与“安史之乱”的两次南迁中文人主要迁入地集中于今江苏、安徽、湖北、四川等地,且以建康为中心向周边的寿阳、镇江、江陵、襄阳、荆州、豫章、东阳等长江中游段地区辐射,但始终未向海洋转徙的情况有了巨大的差异。①李克建:《再论魏晋南北朝的民族迁徙》,《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年第6期。宋代南迁文人的分布整体上呈现出“环东南沿海向南推进”②梅新林:《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的形势,滨海地区成为宋代文人迁徙的重要选择目标,以越州为例,陆游就曾说,“予少时犹及见赵、魏、秦、晋、齐、鲁士大夫之渡江者,家法多可观。”(《杨夫人墓志铭》)
导致宋代中原文人大规模向南且主要向东南沿海方向迁徙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在战乱中文学家以保障生存与安全为迁徙目的,多选择远离战场前沿且环山通水利于逃亡之地迁居,两浙沿海地区则凭借其西南有崇山峻岭之阻、北有长江天险之拒、东南有轻舟重舰浮海之便的地理优势,成为宋代文士迁徙和定居之首选,如陈思恭因宋夏战争携族由熙州狄道(今甘肃临洮)迁入临安(今浙江杭州),韩肖胄因宋金战争携族由相州(今河南安阳)迁入越州(今浙江越州),以及赵鼎(河东解州)、李清照(济州历城)、陈与义(河南洛阳)等大量文人及其家族从中原地区迁入并定居,使沿海地区迅速代替中原关洛地区而成为新的文学中心。
其次,宋代文士起家主要依靠的是科举,但他们如果没有一定产业的话,仅依靠俸禄很难维持整个大家族的生计,而且为保障致仕之后免于饥寒,拥有可以不仰于禄而富足的田产就成为宋代文士必须考量的问题,由此使宋人多怀“里有地,乡有田,而子有禄,可以休矣”(苏颂《少府监致仕王公墓志铭》)的“求田问舍”心态,在宋代“不立田制”的政治制度下,他们以极大的热情参与土地买卖,③[日]周藤吉之:《宋代的官僚制和大土地占有》,《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79页。以致士大夫们“宦游而归,鲜不买田”(袁燮《叔父承议郎通判常德府行状》)而物产富饶、鱼米飘香的东南沿海地区很符合他们对沃土平原的需求,因而成为其买田置舍的首要选择,不少内陆文士陆续向沿海地区迁居,如曹勋由原籍开封迁入浙江天台,曾几由河南府(今洛阳)迁入越州山阴(今浙江越州),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文士们为了迁居沿海富饶之地甚至不惜以“贫而不能归葬”为借口来逃避当时社会对于士大夫迁居的批评。④魏峰:《宋代迁徙官僚家族研究》,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同时,宋代海洋商贸非常发达,且以杭州、明州(今浙江宁波)、泉州最为发达,并且以这些城市为中心,很快辐射到秀州、越州、台州、温州、福州等整个东南沿海地区,为这些地区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与条件,使除了杭州这一大都会以外其他原本偏于一隅、落后荒僻的沿海地区迅速纷纷跻身到“一线城市”行列,如明州“实越之东部,观舆地图,则僻在一隅,虽非都会,乃海道辐辏之地。故南则闽广,东则倭人,北则高丽,商舶往来,物货丰衍……亦东南之要会也。”⑤(宋)张津等:《乾道四明图经》,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4877页。舒亶也说这里“梯航纷绝徼,冠盖错中州”⑥(宋)张津等:《乾道四明图经》,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4918页。。又如奉化鲒埼镇,之前是一个离县城五六十里的偏僻渔村,却因当地人民“开团出海”“强招客贩”“商舶往来”,十余年这里就迅速繁盛起来,“聚而成市”“邑人比之临安,谓之小江下”。⑦(宋)罗濬:《宝庆四明志》,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5180页。沿海城市经济发达、商业繁荣、生活便捷,因此吸引着大量内陆文人迁来此处居住,比如本籍广德(在今安徽)的何大圭为久居福州不惜“避籍换官”,原籍浦城(今福建南平)的詹体仁,在提举浙西常平后,也寓居湖州不再离开,再如临川(今江西)的王安石,羡慕于江阴沿海黄田港外贸发达、经济繁荣、物产丰足、人民富庶的海港社会生活,为此乞奏出知江阴,为以后定居当地早早做打算,未得偿所愿后甚至发出“强乞一官终未得,只君同病肯相怜”(《予求守江阴未得酬昌叔忆阴见及之作》)的无奈感慨。
此外,宋代文人也因滨海地区具有文化发展与政治网络关系的优势而迁居于此,进而与海洋发生关联。宋代义理学发达的地区除了分别作为两宋政治文化中心的汴梁与临安外,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一带也往往是教育业兴盛、义理学大家云集的地区,如海陵人胡瑗在苏湖一带设教二十余年,期间“天下之士不远万里来师就之”,又如“永嘉学派”创始人王开祖身边有从各地求学而来的从学者数百人,福州“滨海四先生”陈襄、郑穆、陈烈、周希孟开创“古灵学派”后,山区人林仰苦于当地教育文化落后,迁居至福州跟随四先生学习。自始迁者起,为了使家族子弟能获得更好的文化环境和教育,这些求学者的家族也随之迁居东南沿海一带,尤其浙闽沿海一带。而且,东南沿海一带也是众多士大夫群体的聚集荟萃之地,许多内陆文士正看中了这里政治上方便与这些耆旧名臣结交的环境优势而迁居于此,如徽州人俞灏之父在湖州娶妻并定居于此;金华人潘畤在中举后游宦各地,因娶上虞大族李光之女,遂迁居,在此地依靠姻亲力量以图发展。
由此可见,宋代文人向东南沿海地区迁居的这一现象相当普遍,而滨海的地理条件为宋代文人创作海洋诗词提供了必要条件,是其创作海洋诗词的基础所在。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不少南迁文士接触到了从未见过的海洋,海洋于是成为新的“诗料”而出现在其诗词创作中,如李清照在南渡过程中乘舟渡海,创作了重要的海洋词《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而海洋壮阔的特性还使这首词充满了豪放风格;①康丹芸:《海洋地理与宋词浅谈》,《地域文化研究》2021年第6期。陈与义在迁往滨海后临海观望,创作《登海山楼》一诗,“我来自中州,登临眩冲融。白波动南极,苍鬓承东风”,借海洋抒发归隐之情;李正民在随高宗辗转海上时创作《扈从航海》诗,表达希望国家“蛟蜃伏藏舟楫稳”的情感,等等。而随着宋人南渡,南宋生长和生活于东南沿海地区的文人数量较北宋更多,海洋诗词也在南宋发展到顶峰,数量和质量上都较北宋有了长足的突破与发展。
总的来说,避籍与轮职、党争与贬谪、通使与战争等因素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宋代海洋诗词创作的发展。在文人们向海洋区域经行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使海洋事物成为他们的审美对象而予以观照,并常常以之安顿心灵、抒发情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