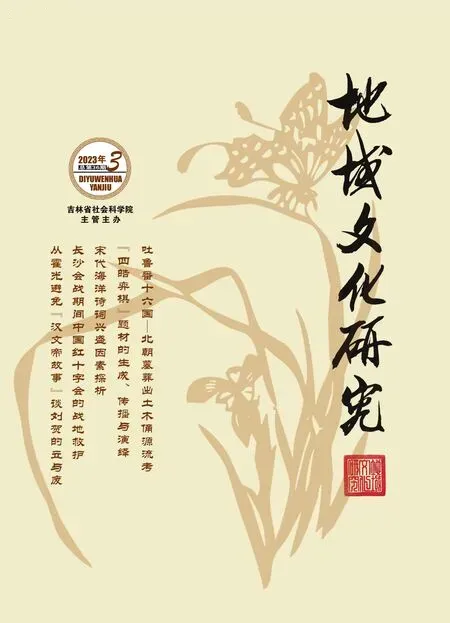人物·文献·制度
——地域儒学研究路径及其传承机制
马 琛
地域儒学指以六经及其衍生文本为研究对象,以研究、阐释和传承儒家思想为目的,经有特定的士人群体在某一特定地域范围内传播,带有一定地域学术特色的儒学。孔子以六经教授,门弟子各得其一隅。众弟子学成后,又将其学说带至各地传衍,如号为十哲的子夏被列为“文学”之科的代表,曾为魏文侯师,在三晋之地弘学;澹台子羽将孔子的学问传至“南蛮鴂舌之地”的楚国,让荆楚神秘而浪漫的巫鬼文化更增一层庄重和理性的色彩。今出土楚系简帛如“郭店楚简”“上博简”“清华简”“安大简”中均有儒家文献①郭店楚简中《缁衣》《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性自命出》《成之闻之》《尊德义》《六德》均为儒家学派的著作。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中《易经》《性情论》《缁衣》《子羔》《孔子闲居》《乐礼》《子路》《曾子立孝》《颜渊》《乐书》等,均为儒家学派著作。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中有大量《尚书》典籍。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中《诗经》内容极多。,足资印证。凡此种种,皆可称为地域儒学之滥觞。
孔子在世时,门弟子能够就其所学、所思、所悟质证于师;孔子殁后,散居各地的弟子及其后学在研读、阐释、传授儒家经典的过程中,逐渐因治学路径的差异和对文本理解的分歧渐行渐远。加之秦火后书缺简脱,造成汉代学者各守师(家)法、各据所本的局面。《史记·儒林列传》载:“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①(汉)司马迁:《史记》卷121《儒林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118页。这些学说的传播囿于一地,有些径以地域名称命名,可谓地域儒学的正式形成。
从西汉的黄龙十二博士,到东汉的十四博士,各地传播的师法各异、家法不同的儒学流派先后立于学官,被整合进整个国家层面的儒学体系,供全国学子研学。自此,依据不同文本和师说的先秦两汉地域儒学逐渐式微,具有新内涵的地域儒学——即与国家层面儒学相对的地域儒学在各地蓬勃发展。
此后在中国古代历史中,儒学所处的文化核心地位始终没有动摇,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无一例外都与汉文化进行融合。虽然各民族文化丰富了儒学的内涵,但从未改变其基色。余英时所说:“现代有些人提出中国史上有所谓‘超稳定系统’,并且想从经济政治结构方面来加以解释。其实专以政治、经济结构而言,中国史乱多于治,至少治乱各半,不能说是‘稳定’。如果真有什么‘超稳定系统’,那也当归之于‘文化’,不在政治或经济。换句话说,文化的超越力量才使中国有一个延续不断的大传统。”②余英时:《论文化超越》,载氏著《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509页。由儒学统摄形成的大传统观念是中国维持大一统局面的根本原因,而“地域儒学”作为“中国儒学”这一“总体”中的“局部”,始终作为维系汉文化大传统的重要力量绵延不息。
时至今日,在地域文化研究日益勃兴的形势下,作为文化核心的地域儒学研究也应提上日程。由于学界对地域儒学研究尚未形成方法论,因此本文拟探究地域儒学发展传承路径,以为地域儒学研究提供理论支持。
一、地域儒学研究路径
地域儒学研究不同于一般的地域文化研究。就地域文化研究来说,“‘地域’作为一个区域性的概念,它必须具有相对明确而稳定的空间形态”,在此基础上形成“具有相对明确而稳定的文化形态”,才具备地域文化研究的基本条件。而形成“明确而稳定的文化形态”的前提是具备“传统”,“如果没有传统,就不可能有相对明确而稳定的形态。”③参见王祥《试论地域、地域文化与文学》,《社会科学辑刊》2004年第4期。但对地域儒学研究来说,区分地域来寻找这种“传统”似乎存在困难,因为儒学本身具有极强的普遍性。正如陈来教授在《儒学的普遍性与地域性》中所述,首先,孔子创立的以继承周文化为使命的儒家在文化意识上是超地域的。其次,孔子周游列国,弟子广布天下,其往来学传的传播方式也是超地域性的。再次,秦汉以后,“统一的郡县制国家的建立,全国使用相同的书写文字,国家确定通行的儒家经典崇拜,这些都为确保儒学话语的普遍性进一步提供了条件和保证”。④陈来:《儒学的普遍性与地域性》,《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概言之,儒学本身具有的内涵及传播方式都具有普遍性,国家制度更对这种普遍性增加了保障。
在儒学普遍性特征的支配下,儒学发展一定程度上来说是一个求同的过程,必然会在发展过程中消磨地域带来的特殊性。因此,用儒学史的一般研究要素来研究地域儒学,往往会得出相似的结论,这正是地域儒学研究的困惑所在。为解决这种困惑,在研究地域儒学史时,首先应正视其与一般儒学史研究所面临的共性。作为大的儒学史的一部分,自然要将一般儒学史研究的基本要素作为地域儒学最主要的研究方法,这是学理的共通性使然,可以称之为大儒学史统摄下的“主流”。然后才是“地域性”的儒学史,将地域儒学视作拥有自我意识的相对独立主体,考察特定地域范围内的儒学流变问题,可以称之为儒学的地域“流变”。此种以“主流—流变”统领全局的视野,或许能更好地认识地域儒学。
就“主流”视野来看,一般儒学史研究的基本视角为人物、文献、制度,由此决定了地域儒学研究也应由此三个视角入手,回顾以往学人的相关研究,也的确如此。
其一,儒学人物角度。人作为一切文化活动的主体,是推动儒学发展的主动力。儒学史研究最重要的领域正是以人物为核心的思想学术史研究。
早在唐代,《北史·儒林传》著者李延寿便意识到南学、北学不同的学术风格,云:“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①(唐)李延寿撰:《北史》卷81,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709页。近代学者梁启超通过一系列论文对地理环境、历史文化及学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全面论述。②如《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地理与文明》《地理与文明之关系》《中国地理大势论》《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等。其中,梁启超发表于《清华学报》1924年第一卷第一期的《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首次明确研究地理与学术之间的关系,该文以十八行政区划分节,细述各个政区明清以降学术之特点。③梁启超:《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饮冰室合集》第14册,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4046页。“学风”一词,梁启超虽未在序言中明确解释,但显然是基于各个地区学术风格不同的考虑。沿此思路,近年来有研究儒家政道思想的学者关注到:儒学分流之初,“春秋时期鲁国的地缘造就了儒学的道统,而战国时期齐国的地缘造就了儒学的政统。”④徐庆文:《儒家传承中的道统与政统——兼论儒学形成的地域性特征》,《东岳丛刊》2011年第11期。鲁国“壤地褊小,风俗谨严”,齐国“临海富庶,气象发皇”。⑤梁启超:《儒家哲学》,《饮冰室诸子论集》,南京: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0年,第27页。孟子带有鲁儒色彩,走向“内圣”的道统路径;荀子带有齐儒色彩,开辟“外王”的政统路径。
如果说“学风”是对地域学术的大致判断,清人全祖望《宋元学案》提出的“学统”则是基于地域学派的明确分类。北宋庆历时期,齐鲁、关洛、巴蜀、江浙、湖湘、福建等地,陆续形成具有地域性质的学派,即清人全祖望《宋元学案》中所说“庆历之际,学统四起”。近年来,研究湘学的代表学者朱汉民使用“学统”概念,并指出:“地域学派的形成有两个基本条件:第一,形成自己自成体系、独具特色的学术思想;第二,形成一个学统上有传承、学术上较一致的学者群体。”⑥朱汉民:《张载的义理经学及关学学统》,《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罗检秋则为之定义说:“简言之,学术落实于授受、传衍,彰显其旨趣和统绪,便是学统。”⑦罗检秋:《学统观念与清初经学的转向》,《清史研究》2020年第2期。杨念群的思考则指出:“儒学的地域化过程所导致的思维范式的多元化,会形成绵延久长的传统,它统摄着不同地域知识分子群体对文化人格结构、思维取向和行为模式的选择。”⑧杨念群:《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20页。此为各地域不同学术风格、不同学统形成的原因。
具体来说,人物角度的研究路径是思想史、学术史研究,主要研究地域人物的生平、师承、重要思想、学术影响及各地学术流派、士人群体等,以反映地方儒学的学派特色、学术旨趣等。基于此角度,从明清时期便产生了《伊洛渊源录》《关学编》《浙学宗传》《皖学编》《洛学编》《蜀学编》等地域学术史文献。但这些汇编类文献,囿于体例,仅在编排时对一些个案进行简单梳理,或在序中作浅显交代,并未形成系统成体系的研究。近代以来,胡昭曦、刘学智、朱汉民、刘复生、彭华等学者著作①胡昭曦等:《宋代蜀学研究》,成都:巴蜀书社,1997年;刘学智:《关学思想史》,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朱汉民:《湘学通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刘复生等:《近代蜀学的兴起与演变》,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7年;彭华:《民国巴蜀学术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21年。均是基于学术史研究角度,使各地域学术体系化。目前学界还热衷引入社会史角度,加大对士人交游、士人互动、家族学术、移民与士人流徙等研究,为研究地方儒学提供了更加生动的视角。
其二,文献角度。文献之于儒学的关系,如谢维扬所说:“儒学为古代文献传统的最终形成整理出最重要的一些文献文本,而以这些文献文本为核心,儒学贡献了支撑古代文献传统发生作用的完整的、有力的记述和论述基础。”②谢维扬:《儒学对中国古代文献传统形成的贡献》,《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孔子修订“六经”,使春秋时期流传的杂乱无章的文献得到整理,形成中国早期最具影响力的古书。孔子修订的经学文本主要用于教学,先秦地域儒学虽然存在“真伪纷争,诸子之言纷然殽乱”③(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30《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01页。的现象,但从现有的史料来看,仅指文献解读上的偏差、学术观点上的歧异、学问思想上的醇疵,还未涉及经典文本在篇目、文字上的差异及基于此种差异而诱发的一系列纷争。汉惠帝除挟书令,儒家经典再次大规模传播。然此时已书缺简脱,造成了儒家经典在文本上的差异,各家学者可以据自己所掌握的文本著书立说,彼此攻犴,甚至可以贿赂兰台令史,削改内府秘藏的漆书以就己本。对经学文本接受的不同造成了地域儒学的不同,申培公传鲁诗,专讲训诂;辕固生传齐诗、韩太傅传韩诗,“便取《春秋》、采杂说,都讲五际、六情”。④蒙文通:《儒学甄微·鲁学》,载《蒙文通文集》第1册,成都:巴蜀书社,2015年,第203页。正如徐庆文论述:“经学的出现使儒家经典分化越来越细,儒学的传承分支越来越多”,汉代经学确立后,《诗》分齐、鲁、韩三家,《书》分欧阳、大夏侯、小夏侯三家,《易》分施、孟、梁丘、京氏四家,《春秋公羊》分严、颜二家。“经学的细化是儒学地域特色越来越浓的原因”⑤徐庆文:《略论山东儒学的地域性特征》,《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魏晋以降,学者更多据已经定型的儒家经典结合时代的需要进行阐释,或者根据已得到广泛认同的经典文本对在传抄、刊刻过程中产生谬误的文献进行校勘之类的工作。前者即义理之学,后者即考据之学。无论如何,文献始终是学术进行的凭借,朱汉民在解释宋学学派的地域性时说:“每一个精神面向吸收的学术资源不同,‘道’既可以是《周易》《中庸》《孟子》等不同的儒家经典资源,还可以是佛、道的学术资源;同样‘政’的经典资源既有‘五经’与‘四书’的明显差异,更包括对管、商、申、韩思想的吸收。”⑥朱汉民:《宋学的多元思想与地域学统》,《天津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所谓学术资源不同,即是对文献吸收的不同。各地学者有意识或无意识接受文献的不同,造成了地域学术思想的差异。
因此,一定程度上来说,儒学史是对经典接收、阐释的历史,任何地域传承儒学都离不开儒学文献的传入和传播,任何地域儒学的发展也离不开地域学者对儒学文献阐释的精进。在大儒学主流观念的统摄下,接受儒家文献的程度区分出地域儒学发展步伐的快慢,也一定程度上成为评判该地文化兴盛与落后的标准。所谓地域儒学特色,必然会反映在当地儒学文献的发展演变上。所以,从文献学角度研究地域儒学文献的数量分布、时代分布、代表学者及代表著述等,可以直观反映地方儒学的兴盛程度及其学术特色。巴蜀历史上的学者如杨慎编《全蜀艺文志》、李调元修《函海》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近年各省学界纷纷加强对当地文献的整理,如浙江省《浙江文丛》《浙学未刊稿丛编》、江苏省《江苏文库》、湖南省《湖湘文库》、陕西省《关学文库》《陕西古代文献集成》、安徽省《安徽古籍丛书》、四川省《巴蜀全书》、重庆市《巴渝文库》、贵州省《贵州文库》、宁夏回族自治区《朔方文库》等等。在这些地域学术成果合集中,可以直观了解各地传世儒学文献。但文献合集仅仅是研究工作的起步,普遍来看,目前的整理工作仅仅是对地域儒学成果的简单堆砌,更深层的挖掘还有待深入。
其三,制度角度。从汉武帝“表彰六经”开始,儒学研究中始终存在一条儒学成为国家主导意识形态的线索,在国家意识形态主导下,各个时期的中央政权都通过学校、科举制度培养、网罗人才,影响着地方儒学的发展。
从中央角度来看,地方儒学似乎只是中央儒学的分支,如有学者认为:“中央在地方发展儒学,加强官学、科举的普及,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避免地方完全‘地方化’。”①杨民:《西汉蜀地政风与“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载《川大史学·文化史卷》,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672页。承此观念,似乎中央制度的贯彻对地域性有所削减。在进行地域儒学概念阐释时也可以发现,两汉以地域命名的各家学说立为官学后,为全国学子所学习,便削弱了学说的地域性。由此,魏晋以降的新的地方儒学,即是与国家层面相对的概念。此层面地域儒学的具体差异表现在各地贯彻儒学政策的程度不同,或者说接受儒学的方式的不同。有些地域自下而上的影响中央儒学,有些地域接受中央儒学自上而下的灌输,而在大多地域,往往能看到这两种方式的良性互动。在良性互动的作用下,民间在贯彻中央儒学政策的实践中,也逐渐形成自身的制度,如书院、义塾的设立,乡约、乡规的制定等,充分体现出地域差异。典型如书院,各地书院在办学宗旨、讲学模式、人才培养标准等方面各有特色。朱汉民在其研究中即指出书院如何强化地域儒学:“在学统四起的两宋之时,那些希望在体制外振兴儒学、重建儒学的新儒家学者们,纷纷创建、主持书院、书堂、精舍等民间性的学术教育机构。这些学术教育机构成为各个地域的学术中心与教育中心,进一步强化了地域性的学派的形成和发展。”②朱汉民:《从学统四起到理学独尊》,《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第2期。
从制度层面出发,要求基于政治史、文化史的角度,研究中央儒学政策在地方的贯彻程度,如地方学校建设情况、人才选拔制度等,研究结果可以论证地方儒学兴衰及儒学传统维系的原因。如巴蜀儒学制度方面,有熊明安、徐仲林、李定开、胡昭曦、涂文涛、魏红翎、刘秀峰等学者的相关著作问世③熊明安、徐仲林、李定开:《四川教育史稿》,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3年;胡昭曦:《四川书院史》,成都:巴蜀书社,2000年;涂文涛:《四川教育史》,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7年;魏红翎:《四川国学院史》,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刘秀峰:《书院的复活:民国四川书院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
二、地域儒学传承机制
以上论述说明,儒学的普遍性使得地域儒学研究不可避免的统摄在大儒学下,其概念阐释、研究路径均无法脱离“主流”儒学的研究范式,即人物、文献、制度角度的研究。地域儒学之“流变”正发生于三者的传承过程及作用方式——即传承机制中。儒学之所以能长时期在中华各地传衍不息,形成深远的儒学传统,固然依赖于各地学者对“同”的追求。但追究其实现路径,则要追溯地方儒学稳定的传承机制,在此机制的维系下,地域儒学不因地域偏远、政治战乱发生明显间断,这也是地域儒学较之一般地域文化的不同之处。
(一)儒学人物传承机制
历代儒学人物的产生及维系是地域儒学传承的关键因素。金人元好问云:“士之有所立,必借国家教养、父兄渊源、师友讲习,三者备而后可。……故作新人才,言教育也;独学无友,言讲习也;生长见闻,言父兄也。”①(金)元好问编,萧和陶点校:《中州集》癸集第10《溪南诗老辛愿传》,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613页。这段文字指出,儒学人物的产生与国家教养、师友讲习、家学渊源密不可分。国家教养层面将在制度一节专门谈论,此处主要讨论后两点。
自孔子打破官方对学术的垄断,推行民间教育,广收门徒。师徒相授成为学术传承的主要方式。有识之士多诣师习经,后归乡教授,形成延绵不绝的传承脉络。汉代私家师徒相授在不少地区的民间都已形成风气,举凡大经学家,门下弟子蔚为大观,皮锡瑞《经学历史》概括当时师徒相授盛况云:“大师众至千余人,前汉末已称盛;而《后汉书》所载张兴著录且万人,牟长著录前后万人,蔡玄著录万六千人,楼望诸生著录九千余人,宋登教授数千人, 魏应、丁恭弟子著录数千人,姜肱就学者三千余人,曹曾门徒三千人,杨伦、杜抚、张玄皆千余人,比前汉为尤盛。”②(清)皮锡瑞撰,吴仰湘编:《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42页。
与师徒相授相伴兴起的是以同乡、学侣、姻亲、同年等形成的广泛的士人之间的学术交流活动。以学术鼎盛的宋代巴蜀为例,据邹重华研究,“整个两宋时期,四川地区都存在着士人学术交游圈子,尤其是以成都府为中心,连接周围诸多州县的士人群体,形成庞大的西川士人学术圈”。北宋早期,士人学术圈规模尚且狭小,中期以华阳范氏、眉山苏氏、梓州文同、成都吕陶为核心,学术圈急剧扩大。北宋末东川也形成了以谯定为首的东川士人学术交友圈,也即“涪陵学派”。南宋前期则以资州李石、隆州虞氏、华阳范氏、眉州李氏(焘)、隆州李氏(心传)、汉州绵竹张氏、卭州魏高氏、潼川杨子谟、简州刘光祖等为主,主要集中在经学、史学领域,中期以后,学术交流以理学为主,“二江九先生”③“二江九先生”指虞刚简、华阳四范(范仲黼、范荪、范子长、范子该)、薛绂、程遇孙、宋德之、邓谏从。见《宋元学案》卷50《南轩学案》、卷72《二江诸儒学案》。及魏了翁最为著名。④参见邹重华《士人学术交友圈:一个学术史研究的另类视角(以宋代四川为例)》,载邹重华、粟品孝主编《宋代四川家族与学术论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93-456页。学术圈的形成,不仅促成儒学在当地的发展,也使得当地儒学出现群体性特征,也即朱汉民先生定义的“学统”。
比师友讲习稍晚兴起的传承路径是家学传承。西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以经学起家成为晋升官僚的主要途径,东汉时逐渐形成累世公卿的局面,经学传家也成为维持家族特权的一种方式,不少学术名家学问承自家族,如东汉经学家贾逵学自父亲贾徽,名儒郑兴传学问于子郑众,等等。至魏晋南北朝,尤其在九品中正制推动下,士族更加注重家族经学教育,经学世家更繁,三国时魏国经学家王肃之学深受父亲王朗影响,吴国学者虞翻家族五世传《孟氏易》。魏晋玄学家王弼家族中,曾外祖父刘表、族祖王粲均为知名《易》家。越到后期,学术家族的规模越大,传承的辈分越久。
人才机制的运行还表现在与外界的交流,对地理位置偏远、地缘封闭的地域来说尤其如此。这种交流具有双向性:一是外来迁入,陈寅恪在论魏晋时期河陇区域学术文化时说:“河陇一隅所以经历东汉末、西晋、北朝长久之乱而能保存汉代中原之学术者,不外前文所言家世与地域两点,……河西一隅自前凉张氏以后尚称治安,故其本土世家之学术即可保存,外来避乱之儒英亦得就之传授,历时既久,其学术文化逐渐具地域性质。”①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3页。本土学术世家与外来避乱儒英共同促成河陇地域学术文化的形成。如巴蜀儒学中,外来刺激因素也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从秦朝巴蜀作为流放地开始,巴蜀不断接受外来士人的迁入,形成“自古诗人例入蜀”的文化现象。三国初,尹默与李仁等蜀中学子外出学习古文经学,又返回蜀中,促使东汉盛行的古文经学在巴蜀有所发展。安史之乱爆发后,大量士人家族迁居巴蜀,唐末五代,四川社会较为安定,统治者兴文重教,吸引大量外界士人入蜀。唐代这批入蜀士人后来成为宋代发达的文化家族的主力军。宋代世家大族如丹棱李氏、眉山史氏、华阳范氏、成都宇文氏、仁寿虞氏、绵竹张氏、阳安刘氏、安岳冯氏等,先祖均为唐时期入蜀。二是地方士人通过游学、游宦、干谒等方式主动与外界沟通。通常来说,靠近都城的地域、交通极为便利的江浙平原地带等,除战乱特殊时期,能够一直保持与外界的频繁交流,因此儒学往往具有前沿性。巴蜀地缘偏远,交通不畅,乱世之中往往形成独立政权,导致儒学发展出现一定的滞后性。但巴蜀自战国时期纳入秦朝管辖范围,始终是中原政权辐射地,因此在和平时期与外界的交流亦十分频繁。从秦汉时期开始,不少士人游学、游宦中原地区。汉代司马相如曾三次前往长安,以辞赋干谒。文翁化蜀时,派遣蜀中学子前往长安学习儒家经典。此后王褒、扬雄、落下闳等名士皆有前往京师求官经历。唐代科举确立以后,地方士人和中央的联系更加紧密,不少儒学名士都具有在京为官经历。在与外界联系过程中,巴蜀儒学虽然时有脱节滞后,但始终是全国儒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互通有无,共同发展。
(二)儒学文献传承机制
宋人郑樵云:“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有专门之学,则有世守之能。人守其学,学守其书,书守其类,人有存没而学不息,世有变故而书不亡。”②(宋)郑樵撰,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804页。儒学文献是保存儒学文本、传承儒家思想的重要载体。比起以人物为载体的活态传承,文献的传承更为可靠和持久。谢维扬更认为,儒学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是具有“文献主义”,“它致力于推出一组支撑其学说的文献,并使这组文献成为对全社会和国家有重大影响的一种力量”③谢维扬:《儒学对中国古代文献传统形成的贡献》,《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儒家自孔子改造古代文献为儒家经典,后世学者不断更新文献,以支持儒家学说发展,由此产生两条儒家文献的传承路径,一是文献衍生路径,即学者的著述、校勘、汇编等;二是文献传世路径,即收藏与刊刻。
首先,儒学的传承依赖儒学文献的衍生。孔子删《诗》《书》,定《礼》《乐》,序《易》,作《春秋》,是为儒家最原始的典籍——六经,孔子诸弟子及再传弟子在传授儒家经典的过程中而形成的新文本,如《春秋》之《公羊传》《穀梁传》等,也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并著录于《汉书·艺文志》中,和六经一起,共同构成了儒家的核心文献。东汉末年,儒学核心文献在文本上的差异,因《熹平石经》的刊刻而基本得到解决;今古文学的纷争,亦因东汉末大儒郑玄整合今古文师法、遍注六经而得以平息。至唐代孔颖达修《五经正义》,选取权威注本,自此,地域儒学因中央儒学有了相对较为准确的文本和较为固定的学说体系而发生了概念转变,即从以文本之争为主转变为以学理之争为主。此后,学者更多据已经定型的儒家核心文献结合时代需要进行订正、阐释,于唐宋形成义理之学,于清代形成考据之学。丰富的著述类、考证类文献承载着地域儒学“自成体系、独具特色的学术思想”①朱汉民:《张载的义理经学及关学学统》,《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而汇编类文献更代表一方儒学传播的集体成就。
其次,收藏儒学文献是地域儒学传承的前提与保障。张之洞云“士不通经,不足以言学,然目不睹全经之文,遽与之言贾马许郑,是躗言也。”②(清)张之洞:《覆刊万氏十一经读本叙》,清光绪二年四川学院衙门重雕本。足以说明经典文本之于学者的重要性。在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前,文献传播主要依靠镌刻和抄写。汉兴以来,惠帝除“挟书令”,儒家经典文本出现了今文经与古文经两个不同的版本系统。在今文学家与古文学家的学术与政治斗争中,甚至有学者行贿兰台,改中密书,以迁就己本。故有熹平石经立于中央学官,吸引全国学者前去订正底本,然后带回各地传播。新朝王莽时期《武威汉简》中《仪礼》、敦煌文献中儒学抄本的存在,均证明了儒学在偏远地域的传播,学者研读经典,并手抄经学文本,形成传世文献。唐代雕版印刷术发明后,极大加速了儒学文献的传播,见诸史籍的藏书家增多,藏书也成为士人家族的标志性行为。
再次,刊刻儒学文献是地域儒学传承的动力。许多学术交流活动都是伴随新文献的刊刻而进行的。宋承平时期,士人家族喜好刻书、藏书的传统达到高峰。元人袁桷描述宋代士人刻书风气时说:“于时国家承平,四方无兵革之虞,多用文儒为牧守,公私间暇,击鲜享醴,会寮属,以校雠刻书为美续。至于细民,亦皆转相模锓,以取衣食。而闽之建、蜀之益,其最著者也。”③(元)袁桷撰、杨亮校注:《袁桷集校注》卷22《袁氏旧书目序》,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019页。宋代全国三大刻书中心四川、福建、杭州,均是兴盛之地。图书刊刻也促成地方文献的整理,汇编大型地方文献丛书以传播乡贤文化成为士人热衷的事业。
通过收藏、刊刻儒学文献,历代学者既有对文本的学习,也有对其中传达的儒家精神的领悟,而精神往往活化在文本中,代代传承,成为维持地方儒学传统的不竭动力。
(三)儒学制度传承机制
儒学的流播,首先是学派形式的学术传播,孔子门生虽然广布各地,但私学师传的影响力毕竟有限。经董仲舒改造后的儒学为汉武帝采纳,成为具有正统地位的学说,在全国大力推行。儒学制度的传承也有两条路径,一为国家层面的制度推广,二为民间制度的维护。
从国家层面来说。首先,学校制度保证了儒学在全国的推行。汉景帝时,文翁在成都创办文翁石室,以七经教学,开创地方官学先河。不久蜀地学风卓荦,人才辈出。公元前124 年,汉武帝下令全国效仿文翁兴办学校。儒学成为官学后,各地学校成为传播儒学的阵地。官学之于儒学传播的重要性,如杨民所说:“官学是国家政权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个宣教性工具,国家对知识的垄断权和解释权的控制始终存在,官方提倡的观念和学说成为民众必须接受和认同的东西,对整个社会意识起到定向、规范和塑造作用。”①杨民:《西汉蜀地政风与“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载《川大史学·文化史卷》,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672页。正是在学校的宣讲下,具有普世价值的儒家思想渗透各地文化之中,儒家倡导的生活方式也为各地百姓接受,中央辐射之地尽成儒化之地。在官学之外,经由地方乡贤的积极提倡,形成了书院、私塾等教学体系,这些民间教学制度在元代以后也逐渐纳入官学体系。其次,科举选拔制度激励儒学的传承。学校设立的目标是培养人才,因此也涉及人才的选拔。文翁在成都创立的石室,即“在汉初以来以军功、察举孝廉、恩荫和纳赀等方式选士之外,首开文化知识入仕的途径”,实现了儒家“学而优则仕”的理想,“为后来汉武帝实施开太学,置博士弟子员,按课试成绩以选人才,探索和积累了经验,在一定意义上开启了人类政治制度上文官制度的先河”②舒大刚、胡游杭:《“蜀学”的特征与贡献》,《中国哲学史》2017年第4期。。国家制度的激励机制一旦调动,便会极大激活地方的传承兴趣。唐代确立的科举制度更加强化了这种读经入仕的传统。“科举制度是制度化儒家的核心和枢纽,维系着儒家的文化价值和传统的制度体系之间的平衡”③干松春:《科举制的衰落与制度化儒家的解体》,《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它使中央王朝网罗人才的标准得以确定,而这个标准正是来自儒学,这就诱使怀有投门报国思想的文人学士苦读儒家经典,因此从社会心理上稳定了儒学的地位,使儒学成为全民自觉维护的圭臬。
从民间层面来说,民间儒学制度的形成体现全民维护儒学传承的自觉意识,家法及一方乡俗、乡约,以教育子弟恪守儒家传统为理念,家塾、义塾的兴办,以鼓励家族子弟读经入仕为目的。这些民间约定俗成的制度不仅保障了家族子弟的读书路径,更是儒家教化思想的强化,尤其在中央政权势弱、战乱年代发挥了重要作用。民间儒学制度还是对中央儒学制度的重要补充,如宋明理学的产生和发展壮大,更多是以民间讲学、民间书院为依托。此外,尽管儒学在地方的普及削弱了地方本土文化的生命力,但儒学仍有迎合地方本土文化的一面,如各地民间信仰对象的不同、丧葬礼仪上的不同等。因此民间儒学制度的传承,更能体现地域儒学特色,不容忽视。
综上可以认为,人物、文献、制度三个层面既是主流大儒学史研究的基本路径,同时也是构成地域儒学发展的内在机制。地域儒学传承正是此三个层面相互作用的结果。通过对某一地域历史上各个阶段儒学史的考察,可以发现只要三个层面其中之一存在,该地该历史时期的儒学传统就不会间断。通常认为的儒学高峰期,无非是国家制度完备、儒学文献丰富、儒学大家辈出的时期。而处于儒学低谷期时,往往文献凋落、人物不显、制度断层。此三层面决定着地域儒学传承脉络,也构成了地域儒学研究的三个维度。
——由刖者三逃季羔论儒家的仁与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