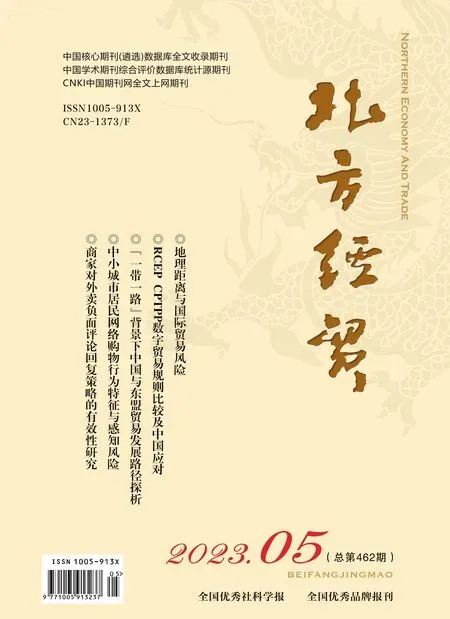数字普惠金融的最新研究:一个文献综述
曲晓东,李苹绣
(广东东软学院,广东佛山 528225)
一、引言
2016 年9 月G20 杭州峰会上,“数字普惠金融”(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的概念被正式提出。数字普惠金融的前身是“普惠金融”(inclusive finance),由联合国在2005 年的国际小额信贷年上首次提出,倡导金融服务的公平性和包容性,所以普惠金融又被称为“包容性金融”。普惠金融的宗旨是以可负担的成本,持续地为社会经济体中那些被排斥在传统金融服务以外的贫困人口、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服务,满足他们的资金需求,体现金融服务广泛的包容性和公平性。
中国积极倡导普惠金融,党中央和国务院在多次重要会议上强调要推进普惠金融体系建设。然而,普惠金融体系的建设却受到较高金融服务成本的制约,在现实中难以快速实施。在此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应运而生。数字普惠金融是科技赋能金融、金融的数字化创新,是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在普惠金融领域的应用。借助这些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降低金融服务的成本,扩大金融服务的覆盖范围,提供更高的交易便利性,有效缓解金融排斥问题。
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趋势。根据郭峰等(2020)[1]与蚂蚁集团研究人员合作编制的“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2011 年,各省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中位值为33.6,到2020 年增长到334.8,指数值平均每年增长29.1%。数字普惠金融的快速发展对人民群众生活和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数字普惠金融与居民消费
(一)数字普惠金融对消费的影响
易行健等(2018)[2]依据2012 年、2014 年和2016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和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数据集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可以显著促进居民消费。异质性分析表明,促进作用在经济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即收入较低的农村家庭更为明显,在东部地区却不显著。郭继辉等(2022)[3]的研究也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家庭消费水平的影响在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家庭表现更为突出,在东部地区则不显著。但与上述两篇论文的观点不同,王刚贞等(2022)[4]的研究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消费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最强,中部地区居中,西部地区最弱。李建伟等(2022)[5]的研究却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西部地区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不显著,对中、东部地区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显著。
孙玉环和张汀昱等(2021)[6]采用大连市居民的消费调查数据集,结合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居民消费,促进作用与住户居住区域和收入水平有关,存在异质性。不仅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居民消费,而且其三个维度——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支持服务程度均能促进居民消费(沈慧翠和朱洋洋,2022)。[7]
也有学者将研究视角转向了消费市场活跃度。张冰倩等(2022)[8]的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促进消费市场活跃度的提升,在东部、中部地区促进作用显著,而在西部地区不显著。马晓旭等(2022)[9]将研究视角转向了农村消费不平等,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可以缩小农村家庭收入不平等,进而缩小农村家庭消费不平等,作用效果东部大于西部,对中部无影响。
研究方法方面,不同于上述学者常采用的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任爱华等(2022)[10]采用时间序列VEC 模型,研究了河北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当地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研究显示与城镇居民相比,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冲击影响更大,程度稳定在20%左右。
(二)数字普惠金融影响消费的渠道
易行健等(2018)[2]研究认为,便利支付和缓解流动性约束是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居民消费的两个渠道。何宗樾等(2020)[11]也认为,由于数字金融增强了居民支付的便利性,进而刺激了消费增长。但江红莉等(2020)[12]则认为,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和产业结构优化才是数字普惠金融影响消费的中介变量。沈慧翠等(2022)[7]也认为,“收入差距”是这一促进作用的中介变量,李建伟等(2022)[5]的研究也支持这一观点。孙玉环等(2021)[6]则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了居民消费依赖于“保险使用”这一中介变量,直观含义是居民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降低,居民的消费支出将会增加。
以上学者关注的都是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居民消费的中介变量,也有学者重点研究了这一影响的调节变量。刘琳等(2022)[13]的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消费升级在互联网普及率和居民金融素养高的地区更为明显。
综上,学者采用不同的数据集、不同的计量模型就数字普惠金融对消费的影响开展了广泛的研究,虽然样本数据、研究视角、研究方法上有所区别,但基本都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对消费有促进作用,并且具有异质性。但在异质性特征方面,不同学者持有的观点不同,有的学者认为是东部地区不显著,中西部地区较为显著;有的学者认为是西部地区不显著,中东部地区显著;有的学者认为东部、中部、西部都显著,只是强弱程度有区别。除了异质性,学者关于数字普惠金融影响消费的渠道也存在分歧,各自持有不同的观点。
三、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减贫
(一)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减贫的影响
McKinnon(1973)[14]和Shaw(1973)[15]的研究认为,金融抑制现象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是这些国家难以摆脱贫困的一个重要因素。发展普惠金融可以缓解金融抑制现象,在“数字普惠金融”的概念提出之前,学者围绕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进行研究;后续随着“数字普惠金融”概念的提出,研究对象才转向数字普惠金融。
卢盼盼等(2017)[16]研究了发展普惠金融对减缓贫困的影响,依据选取我国31 个省、自治区2005-2014 年面板数据,采用SYS-GMM估计方法证实了发展普惠金融确实能够促进减贫。从普惠金融的细分维度看,贷款密度的减贫效应比银行网点密度和银行从业人员密度的减贫效应更大。马彧菲等(2017)[17]也进行了类似的研究,不过研究所设计的衡量普惠金融发展程度的指标体系与前者不同。其设计的普惠金融指数涵盖“宏观”“银行”和“保险”三个维度、“金融机构存款余额/GDP”等11 个三级指标,采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方法进行降维合成中国各省份2005—2013 年的普惠金融指数,随后实证检验了发展普惠金融对减缓贫困的积极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是普惠金融的数字科技化,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也能起到显著的减贫作用(Wang,2018[18];Mushtaq 和Bruneau,2019[19])。黄倩等(2019)[20]基于2011—2015 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LSDV、2SLS 和IV—GMM的估计方法,验证了数字普惠金融具有显著的减贫作用;相较于富裕群体,减贫作用在贫困群体上更为显著。刘锦怡等(2020)[21]利用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也证实了数字普惠金融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其他学者采用不同时间跨度的省级面板数据,建立不同的计量模型,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刘鹏举和张一童等,2022[22];张前程和宋俊秀等,2022[23])。
也有学者利用更为微观的数据进行了细致分析。石玲玲等(2022)[24]利用中国市级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及其三个维度(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有利于居民收入的提高;与城镇居民、高收入群体相比,其对农村居民、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提高作用更大。蔡皎洁(2022)[25]基于湖北省孝感市的县级数据进行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促进县域农民增收减贫,二者之间具有“U”型门槛效应关系。鹿光耀等(2022)[26]基于江西省“百村千户”的调研数据,运用Probit 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证实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可以促进农户创业,丰富农户收入多样性。
(二)数字普惠金融影响乡村减贫的渠道
黄倩等(2019)[20]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对减缓贫困的显著作用是通过促进收入增长和促进收入分配改善两种机制来实现的;蔡皎洁(2022)[25]的研究结论与之类似,认为减贫是通过经济发展和城乡收入分配两个渠道来实现的;石玲玲等(2022)[24]的研究也认为,减贫是通过促进收入增长来实现的。与上述学者的观点不同,刘锦怡等(2020)[21]的研究认为,减贫是通过促进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提高乡村的金融可得性来实现的;而鹿光耀等(2022)[26]的研究则认为减贫的渠道是促进农户创业。
除了关注中介变量外,也有学者关注了减贫效应的调节变量。张前程等(2022)[23]认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经济的益贫式增长,作用效果受到调节变量“金融发展水平”的影响。
综上,无论是普惠金融还是数字普惠金融,学者们都一致认为它们有助于乡村减贫,减贫效果在贫困及低收入群体中更为显著;学者们的分歧在于减贫效果的渠道机制上,不同学者研究视角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
四、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
(一)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部分学者采用省级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任经辉(2022)[27]通过建立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黄河流域九个省、自治区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能减小城乡收入差距,但数字化程度的深化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杨彩林等(2022)[28]运用不同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模型也印证了这一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也得到周利等(2020)[29]、宋晓玲(2017)[30]研究的支持,他们基于不同时间跨度的面板数据,分别采用分位数回归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结论与之相符。
另外,一些学者采用地级市或县城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略有不同。李容德(2017)[31]把普惠金融分解为金融服务覆盖率、金融服务使用性和金融服务质量三个层面;随后对江西省75 个县城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三个层面的发展都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曹晓旭(2022)[32]基于辽宁省14 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也证实了数字普惠金融的三个维度均能显著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而采用省级面板数据进行研究的学者普遍认为数字化程度的深化会加大城乡收入差距。
至于数字普惠金融和城乡收入差距的数学关系,任经辉(2022)[27]的研究认为,二者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存在以经济发展水平为门限的双重门槛效应。王小刚等(2022)[33]的研究也认为,二者之间的数学关系是非线性的,存在三个不同的拐点。张贺等(2018)[34]的研究认为,城镇化率是这一非线性关系的门槛变量。
(二)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渠道
周利等(2020)[29]认为,数字普惠金融主要是通过增加金融可得性和放宽信贷门槛的方式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杨彩林等(2022)[28]的研究认为,农户信贷供给是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中介变量。邓金钱等(2022)[35]的研究显示,数字普惠金融的便利性和低成本对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作用要大于对城镇居民收入的提高作用,因而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总体来看,虽然学者们采用的数据集不同,计量模型也略有区别,但是研究得到的结论基本一致: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具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但对作用的渠道机制,学者们存在分歧。
五、数字普惠金融与创新创业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2014 年9 月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由时任国家总理李克强提出的,旨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创新创业的浪潮,通过“双创”实现经济增长的创新驱动。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双创”进行了广泛的研究,累积了丰富的文献资源。
(一)数字普惠金融对创新创业的影响
依据经济学常识,研究者会很自然地认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促进创新创业,但是也有学者认为是创新创业促进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杨立生和龚家,2022)。[36]他们认为政府为鼓励民众创新创业,会与银行等金融机构协调引导信贷资源流向长尾群体,因而促进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当然,大多数学者还是认为数字普惠金融是因,创新创业是果。
1.数字普惠金融对创新的影响
梁榜等(2019)[37]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及其三个维度均对城市和企业的技术创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种影响作用在中西部城市和金融可得性较低的城市以及中小民营企业更为突出。万佳彧等(2020)[38]依据不同的样本数据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段鑫等(2022)[39]的研究也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家创新、创业精神具有积极的影响,并且这种积极影响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影响程度在东部和中部城市高于西部和东北城市。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促进技术创新,进而推动产业升级,技术创新是中介变量(翟金德和朱兴洲,2022)。[40]但也有学者持有不同的观点,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产业升级并不是依赖于技术创新,而是通过缓解资本要素错配和劳动力要素错配来实现的(沈洋和郭孝阳等,2022)。[41]
2.数字普惠金融对创业的影响
谢绚丽和沈艳等(2018)[42]的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及其三个维度都对创业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中小微企业上,对大型企业的创业并无显著影响。曾之明和伍剑超(2022)[43]将研究视角由企业转到家庭,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创业决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影响作用在东部地区和农村地区更为显著。
(二)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创新创业的渠道
关于影响渠道方面,不同学者持有的观点不同,但也有相似之处。万佳彧等(2020)[38]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创新的渠道是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梁榜等(2019)[37]持有同样的观点,不过他们认为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也是一个影响渠道。与以上学者的观点不同,段鑫等(2022)[39]则认为弱化要素错配才是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创新的真正渠道。
关于影响创业的渠道,谢绚丽等(2018)[42]认为,是扩大金融服务覆盖度和降低金融服务成本。和两位学者的观点有所不同,曾之明(2022)[43]认为除了降低金融服务成本渠道外,提升信贷可得性和促进居民收入增长同样是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创业的渠道。
综观以上研究,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可以促进创新创业这一点上,学者们并无分歧。分歧之处在于,这种促进作用究竟是在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哪个区域更为显著?促进作用产生效果的渠道机制究竟是什么?是否同时存在多个中介变量发挥作用?这些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
六、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增长
(一)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张勋等(2019)[44]研究认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提高了经济落后地区的居民收入,缓解了区域发展不平衡,有利于实现经济的包容性增长。钱海章等(2020)[45]运用双重差分等多种计量方法进行回归分析,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可以显著促进经济增长,促进作用在城镇化率低和物质资本高的省份中更大,存在空间异质性。后续多个学者(李建军和彭俞超等2020;[46]李映彤和赵健,2021;[47]薛秋童和封思贤,2022;[48]李梦雨,2022[49])的研究也证实了促进作用异质性影响的存在。
(二)数字普惠金融影响经济增长的渠道
关于数字普惠金融影响经济增长的渠道,学者们持有的观点有所不同。张勋等(2019)[44]认为,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促进农村家庭创业来影响经济增长。钱海章等(2020)[45]认为,除了家庭创业外,技术创新的渠道也不可忽视。李建军等(2020)[46]的研究则认为,其影响渠道是减轻信息不对称和优化资源配置。也有学者认为中介变量是产业结构升级(李映彤和赵健,2021[47]),是居民消费(薛秋童和封思贤,2022[48])。还有学者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促进创新发展与共享发展的途径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李梦雨,2022[49])。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学术界已经达成共识。但由于经济增长是一个非常复杂和宏大的问题,影响因素繁多,学者们对数字普惠金融影响经济增长的渠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需要进一步辨析。
七、数字普惠金融体系建设
数字普惠金融体系的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诸多方面,学者们依据自己的研究从不同的视角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首先,薛秋童等(2022)[48]认为,建设数字普惠金融体系的重点是加强行业监管,约束金融服务提供商合法合规经营,保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其次,要加强城乡金融知识普及和消费者风险教育,引导城乡居民正确认识数字普惠金融的便利和潜在风险(董玉峰和赵晓明,2018;[50]胡芸,2022[51]);再次,要深度挖掘涉农数据信息,加快数字征信体系建设,给予城乡居民精准化金融服务(胡芸,2022;[51]高巍和林梦瑶,2022[52]);然后,要加大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推动互联网金融发展,实现数字普惠金融全面覆盖(高巍和林梦瑶,2022;[52]罗春玲和王定祥,2022[53]);最后,由于数字普惠金融体系的建设涉及多个主体,不同主体在不同时期发挥的作用有所不同。乡村数字普惠金融体系的建设应该以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助力乡村振兴为出发点,发挥政府、金融机构、需求主体和数字技术中介“四元主体”的协同作用(文宗川和杜益欣,2022[54])。
八、数字普惠金融的风险
金融创新也必然蕴藏着金融风险,数字普惠金融也不例外。黄益平(2017)[55]认为,相比于传统普惠金融,数字普惠金融的风险在于由于监管措施不到位,部分金融服务机构(如P2P 平台)以普惠金融为名,行金融套利之实,挪用储户资金现象频繁发生。何敏等(2022)[56]利用中国裁判文书网的数据,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居民债务风险的关系,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刺激了居民债务风险的上升。易行健等(2018)[2]的研究也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会刺激居民消费,导致家庭债务杠杆上升,增大了居民的债务风险。
九、结论与展望
(一)结论
从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围绕数字普惠金融做了非常丰富的研究,这些研究的共同点基本都是以数字普惠金融为解释变量X,探讨它对不同的被解释变量Y 的影响。但根据研究目的需要,学者们分别采用了不同的计量模型(如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面板数据随机效应模型、二元选择Probit 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门限回归模型等),不同的估计方法(如,OLS、GMM、QR 和DID 等)研究了X 是否对Y 有显著影响,得出了基本一致的结论。学者们之间的分歧在于X 是通过什么渠道来影响Y 的?X 对Y 影响的空间异质性是什么?学者们各执己见,这些问题还有待未来继续深入研究探讨。
(二)展望
正如上面所描述,学者们的研究基本都是以数字普惠金融为解释变量X,探讨它对不同的被解释变量Y 的影响。但既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具有促进消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助力乡村减贫、刺激创新创业等诸多有益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那么如何更好、更快、更有成效地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呢?如何因地制宜制定可执行、能落地、针对性强的差别化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政策呢?是哪些因素影响数字普惠金融的健康发展呢?现有研究在以数字普惠金融为被解释变量Y,研究其背后的影响因素X 方面还存在巨大空白,这是非常值得深入研究的。
数字普惠金融是科技赋能金融、金融的数字化创新,改变了传统金融业的生态格局,正在对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金融创新必然伴随着金融风险,存在风险就必须监管。现有关于数字普惠金融风险的研究集中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债务风险的影响,尚未对数字普惠金融的信用风险、操作风险和流动性风险进行深入研究;也未针对如何建立监管框架防范这些风险进行系统研究。此外,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会产生“金融脱媒”的问题,会对货币政策的传导路径造成冲击,给央行进行货币流动性监测、掌握货币流动性的真实情况带来风险挑战,增加央行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难度,诸如此类问题亟待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