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乐的伦理精神
内容提要 原初时期礼乐一体,以敬神娱神的方式,发挥了维持群体秩序、巩固共同体团结的伦理功能。殷周之际将礼乐制度化,其最大变革在于制礼作乐合于德,并以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的伦理原则作为礼乐的规定性。春秋时期,孔子以仁作为礼乐的内在依据,并重视乐化育人心的独特价值。其后,《荀子·乐论》《礼记·乐记》都发扬了礼乐根源于人心的观念。而《乐记》更提出了“礼者天地之序”“乐者天地之和”的理念,礼乐以仪节、仪式与乐歌、乐舞形式来追求“序”“和”这样深远的伦理目标,实现了礼乐伦理精神的历史建构。可以说,礼乐的伦理精神超越时代而绵延不断,其所追求的化解冲突后的自由(“和”)且秩序井然(“序”),是中国传统伦理对于世界文明的重要贡献。
关键词 礼 乐仁 和 伦理精神
徐嘉,东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如何书写中国伦理的起源或早期形态是一个难题。自蔡元培先生1910年完成现代中国第一部《中国伦理学史》开始,迄今已有二十余部系统研究中国伦理思想史的著作面世。概括而言,对先秦诸子之前的伦理思想的研究,大体上有三种方式:一是将殷周之际作为道德理性意识觉醒的时代,认为从殷人尊神到周人尊礼的变化过程中产生了中国早期的伦理道德思想的萌芽[1];二是归纳和总结出西周以来的“孝”“德”“礼”等具有道德意味的观念的产生[2];三是挖掘中国伦理的形上依据“天”“命”的意义,诠释“修德配命”“敬德配天”“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等命题的伦理价值[3]。应该说,这些研究所得出的中国早期伦理思想的观念、范畴、命题已经比较清晰地呈现了前春秋时期的伦理思想的一般性特点,可以作为解释中国伦理发展源流的依据。但是,由于传世的甲骨文、金文和早期文献本身的局限性,这些研究和描述不可避免地带有孤立、零碎和空泛的特征。因此,本研究认为,西周的礼乐制度是一个整体性的文化模式,或者说是一整套建构国家体制、维持社会秩序的理念与指导民众行为方式的准则与规范,对中国伦理特别是儒家伦理产生了奠基性的、持久性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儒家伦理的原初形态,而且深刻影响了其伦理精神的形成与发展——此言伦理精神,是指伦理规范体系中核心的、本质性的价值目标,是一种自觉的意义追求和精神指向。
因此,本研究从礼乐的维度,探寻商周时期礼乐的伦理内涵,以溯源儒家伦理的原初形态与演化路径。虽然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礼乐之治渐失生命力,但是在经历了西周、东周数百年的理论化、系统化的发展之后,礼乐凤凰涅槃,最终升华为一种道德理想与伦理信念,从《论语》到《荀子·乐论》《礼记·乐记》,对礼和乐的新诠释,使其具有更深刻而永恒的伦理精神。
一、原始礼乐的伦理意义
广义的“伦理”,是人类社会的行为准则和内在秩序,是人伦关系的客观结构与规范要求,即个体性的“人”与实体性的“伦”(伦理实体)的关系。对于早期人类而言,伦理的意义在于维持一个共同体(族群、氏族或部落)有序的社会生活,而礼乐则代表着人类早期社会生活中的伦理秩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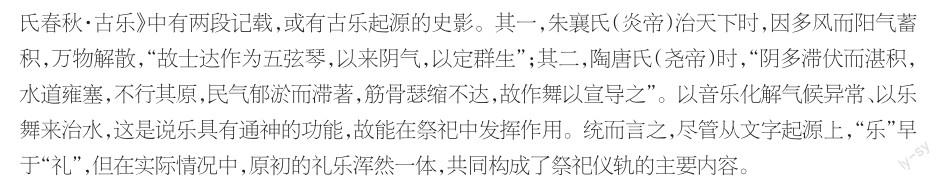
礼乐所代表的上古敬神祈福仪式,主要包括对图腾、祖先神与神灵的各种祭祀,这种活动的伦理意义十分明确。对图腾的祭祀是期望通过信仰与本族有亲缘关系的动物、植物或自然物的灵魂载体,而对族群有保护作用;对祖先神的祭祀,则是人们希望自己祖先的灵魂能够庇佑本氏族的成员;在殷商卜辞中,对神灵的祭祀包括日、月、风、云、山、河、东、南、西、北之神等等,其中,“帝”是最高的众神之神,管理人间事物,决定收成的丰歉,左右战争的胜负,对自然神、“天帝”的祭祀皆以祈福、祛灾为目的。对此,余英时先生认为,礼乐的主要功能在于沟通天人。这种礼乐具有宗教的特征或性格,中国古代的宗教即托身于礼乐之中[1]。礼乐具有原始宗教的意味,就仪式而言,在事神祈福仪式中,礼与乐在献祭、颂神、祈福的仪式规范都按照一定的规程进行,因为要沟通神灵,所以烦琐而复杂、神圣而严肃,由此而有严格的规范要求。就目的而言,礼与乐是为了整个群体的利益,而非个体的精神需要。比如巫觋的求雨祭仪,对于农耕社会来说,对整个族群的生存、繁衍都意义重大。族群是一个血缘共同体,亦是一个天然的伦理实体,无论是祖先崇拜还是图腾崇拜,周而复始的祭祀客观上都在强化全体成员对族群(以及以后的宗族)的归属与认同,使之认识到个体与团体的鱼水关系,因此既巩固了个体对共同体的皈依,又促进了共同体的凝聚与稳定。所以,礼乐的直接意义都是强化团结、凝聚对共同体的意识、不断强化伦理实体的神圣性。可以说,礼与乐是中国伦理最初的表现方式。李泽厚先生认为,以礼乐为特征的巫术礼仪的主观目的是“沟通天人,和合祖先,降福氏族”,而客观上达到的效果则是“保持秩序,巩固群体,维系生存”[2]。此论十分精辟。礼乐的客观效果,正是伦理的真正意义与功能,这很好地诠释了原初礼乐的伦理性与价值所在。
二、“制礼作乐”的伦理基石
西周初期,“周公制周礼”(《左传·文公十八年》),礼乐从殷商时期的祭祀仪式转变为一整套“政治-伦理”制度,其确立的礼与乐的伦理内涵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儒家伦理的原初形态,并影响了其伦理精神的形成与发展。概要而言,礼乐制度的伦理基石有三层内容:一是“制礼作乐以合德”,“德”是“敬德保民”的行为和良善的品性;二是礼乐制度以宗法家族伦理为支撑;三是“乐以养德”。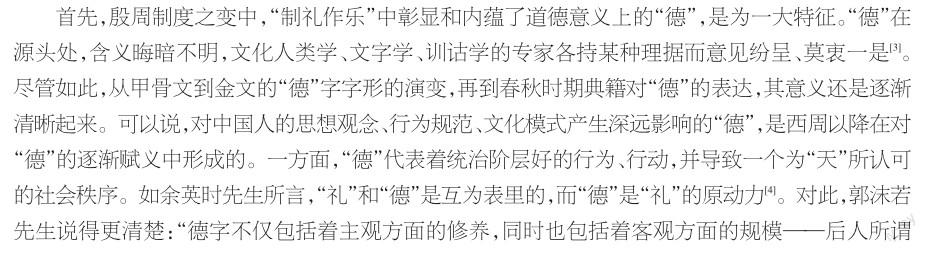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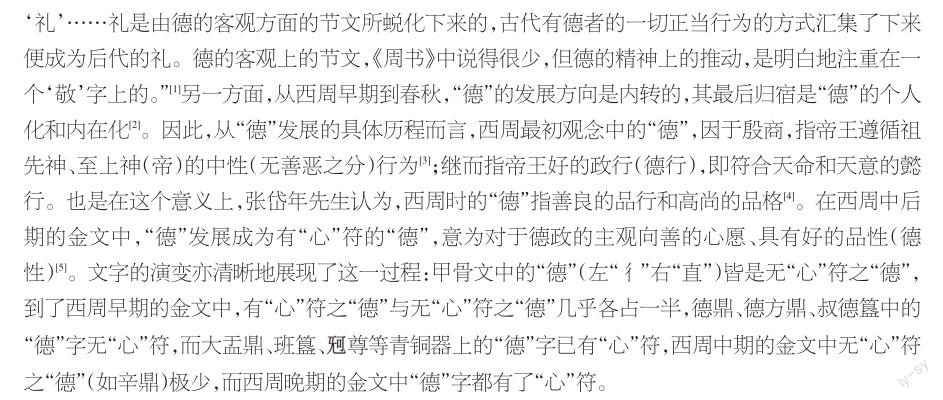
可以確定,在反映西周思想的文献中,把“德”作为道德意义上的“好的行为”“好的品性”是周人对“德”注入的新内涵。小邦周取代大国殷,在周人看来是“以德配天”的结果。《召诰》云:“(夏殷)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尚书·蔡仲之命》云:“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康诰》云:“丕则敏德,用康乃心,顾乃德,远乃猷,裕乃以;民宁,不汝瑕殄。”这是周公追述文王“克明德慎罚”是德政的典范,并告诫康叔以德治民的道理。所以,王国维《殷周制度论》中说:“殷周之兴亡,乃有德无德之兴亡。”而表现方式,则是通过西周时期的治礼作乐来彰显“德”:
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先君周公制《周礼》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左传·文公十八年》)
“则”是法则、规范,即具体的礼乐制度——礼乐既确定了相应的身份、地位、享受等级,亦确定了责任和义务,而这些责任和义务兼具政治要求与伦理要求。在履行禮乐的规范中,观察人的德行、德性,以好的德行处理事情衡量功劳,这是享用俸禄的依据。所以,建立一套有效的政治、文化制度,要求“制礼作乐”合于“德”。“敬德保民”“德惟善政,政在养民”的观念意味着,“德”不但是周王应然的善行,亦是向善的品性,以此保民,即是保周之天命。
其次,西周设立的礼乐制度遵循明确的宗法伦理,并以此作为有力的支撑。李学勤先生在《邲其三卣与有关问题》一文中对比殷墟二祀邲其卣铭文与周初的保尊、保卣铭文,指出商周祀制类同,因多于革[6]。对此,陈来认为,虞夏商周四代礼制存在差异,但四代礼制具有相同的结构,对祭祀场所、祭祀对象、祭祀器物的种种规定,只有细节的差异,而无结构的不同[7]。刘雨先生的研究最具说服力,他指出,西周的祭祖礼共二十种,“除翟、禋、尝三种次要祭礼外,其余十七种祭祖礼都是殷周同名”[8]。其实,商周礼之仪节、仪式大同小异,而内在之礼制、礼义已发生根本性变,“礼”已成为一种具有伦理性的政治制度——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礼”,才是西周区别于殷商的地方。王国维先生《殷周制度论》所言之“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亦是指此。这种变革,核心在于“永保厥命”的政治要求,却以宗法伦理加以实现与强化。具体而言:“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此数者,皆周之所以纲纪天下。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1]
①殷商时代,王位继承制度既有父死子继,亦有兄终弟及。殷代中丁死后,因诸弟争位而有九世之乱,殷之衰亡与此有莫大的关系。鉴于殷人之失,王位继统法上的周代礼制变革为“立子立嫡之制”。由此又衍生出了宗法制,即嫡庶之别、大宗小宗之分。不但天子、诸侯遵循“立子以贵不以长,立嫡以长不以贤”的原则,而且贯彻于大夫以下。而为了严分嫡庶,又衍生出居丧期间的丧服之制。《仪礼·丧服》规定的丧服由重至轻,分为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之“五服”。这一规定因居丧者与死者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不同而有服丧时间长短、丧服规制的轻重之别。静安先生以“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为“丧服”之制的原则,其实这亦是整个西周礼乐之制的原则。②《礼记·王制》中规定“庙数之制”:“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祭于寝。”殷、周皆以庙供祀祖宗,殷代“亲亲”之统并不严格,而周代规制进然,即天子七庙,诸侯、大夫、士的庙数依次递减。这既是等级制度,又强化了宗法家族的组织结构,其依托的是以“亲亲”“尊尊”为核心的宗法家族伦理。③“同姓不婚之制”,是通过同姓不婚而对异姓之国等非宗法所能统摄的各种势力进行联姻的方式,“以婚媾、甥舅之谊通之,于是天下之国,大都王之兄弟、甥舅,而诸国之间,亦皆有兄弟、甥舅之亲。周人一统之策,实存于是”[2]。即把需要团结的力量,通过联姻的方式,以伦理的方式有机地联系。这形成了“家国同构”,即“以尊尊之义经亲亲之义而立嫡庶之制,又以亲亲之义经尊尊之义而立庙制”——政治结构采用了凝聚家族的伦理机制,从而一统天下。
综合而言,以上“立子立嫡之制”“庙数之制”“同姓不婚之制”皆以伦理道德为秩序原则,王国维说:“周之制度典礼,乃道德之器械,而尊尊、亲亲、贤贤、男女有别四者之结体也,此之谓民彝。”[3]民彝者,人与人之间相处的伦理道德准则。进而言之,“由是制度,乃生典礼”,此言典礼即礼乐仪式,是“此其所以为文也”,这种“文”的方式是以高度仪式化的礼乐仪式来给予制度以正当性与合理性。“制度、典礼者,道德之器也,周人为政之精髓,实存于此。”[4]礼有礼器、礼制、礼义、礼仪等形态,而西周建立的制度层面的礼是最重要的,支撑礼制的宗法家族伦理亦成为礼的核心内容。
最后,周代的礼乐制度中,乐的伦理价值在于“乐(教)以养德”。西周的礼乐制度虽然以礼为主,但亦有乐政、乐治等内容。如《礼记·王制》载:“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汉书·艺文制》载:“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得失,自考正也。”特别是《周礼·春官·大司乐》中说:“以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安宾客,以说远人,以作动物。”即乐可以招致鬼、神、祇而祭祀,以使得各邦国亲睦、和谐民众、安定宾客,使边远的少数民族悦服归附。乐治的意义可见一斑。当然,在礼乐制度中是乐制配合礼制,乐仪配合礼仪。“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代表着秩序井然,制礼、作乐、征伐等国家大事都是王的专有权力。此外,乐的享用等级遵守礼的要求。王国维先生在《释乐次》中详细说明了天子、诸侯、卿、大夫在典礼过程中如何用乐的等级要求。而除乐政、乐治之外,乐的一大功能在于“乐教”。《周礼·春官·大司乐》载:
(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祭于瞽宗。
(大司乐)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祇、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夏》《大濩》《大武》。
乐教包含乐德、乐语与乐舞,以乐涵养而成德,郑玄注《大司乐》说:“中犹忠也。和,刚柔适也。祇,敬。庸,有常也。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友。”不仅如此,《云门》《大卷》颂黄帝之德,《大咸》赞唐尧无所不施之德,《大夏》誉夏禹平治水土之德,《大濩》言汤能救民之急之德,《大武》表武王伐纣救民于水之德。乐舞的内涵中自始就有丰富的伦理教化内容。
所以,殷周之际从尊神事鬼到尊礼尚施的历史性跨越所展现的礼乐文明,很大程度上是伦理意义上的进步。虽然周礼与事鬼敬神等祭祀活动并不是彻底一刀两断,但是,这至多是一种神道设教,周礼所展现的礼器的分别,服制的区分,冠婚丧祭相见的仪节,男女之别、长幼之序的规定,都是一种更理性而文明的社会形态。其以严肃、神圣的礼乐仪式展现出来的政治制度、伦理要求、道德规范,都昭示着古代思想世界中的非理性、神秘性色彩开始淡去,伦理道德色彩开始凸显。西周礼乐制度所依赖的伦理观念,是一个以人的理智和人性的自觉来实现社会进步的学说。
三、释礼归仁与乐以成人
春秋时期,随着周王室力量逐渐衰微,礼乐制度走向衰落,但这一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对礼乐的依据、本质的思考,却促进了礼乐走向伦理层面的理论建构。
西周的礼乐制度的表现方式无疑具有强烈的仪式感,玉帛荐献、进退揖让、黄钟大吕、干戚羽旄等等,充满了“郁郁乎文哉”的艺术之美。但是,礼乐仪节严格的动作规范与程式,都象征着秩序。比如《仪礼》中所记载的诸侯见天子的“觐礼”,从“至于郊”“天子赐舍”“诸侯前朝”到“诸侯觐于天子”“祭天”,一言一行、一问一答、一举一动、服饰、车马皆有规定,体现了觐见诸侯的尊卑等级、血缘远近[1]等复杂的“政治-伦理”关系。而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不仅表现为“八佾舞于庭”这种对礼乐制度的直接僭越,而且礼乐仪式与实质内容的分离、脱节更是当时司空见惯的事情。那么,礼乐作为仪式,其本质是什么?其实,这一问题在当时已有诸多讨论,即礼仪与礼义的区别。有两个有名的历史事件:其一,鲁昭公出使晋国,“自郊劳至于赠贿,无失礼”。但晋大夫女叔齐却认为,鲁昭公的行为“是仪也,不可谓礼”。因为“礼之本”在于“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民者也”,即政治上的权力合法性的根据,而鲁国的政令出于卿大夫,有人才不能任用,人民心中没有国君,可以说已失去了礼的根本[2]。其二,赵简子向子太叔请教揖让周旋之礼,子太叔亦回答说,“是仪也,非礼也”。真正的礼是“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又说“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礼者,谓之成人”[3]。可以看出,《左传》中严格区分了“礼”和“仪”的不同,这种区分既指政治上的“礼之本”与“礼之末”之分,亦是伦理上的礼义和礼仪之别。
正是在这个方向上,孔子面对礼乐的形式化、表面化问题,在追究礼乐的源头与本质时,创造性地将礼和乐建立在“仁”的基础上,赋予礼乐以深刻的伦理依据。孔子曰:
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
礼,与其奢,宁俭。丧,与其易,宁戚。(《论语·八佾》)
仁而不仁,如礼何?仁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
礼乐不在玉帛、钟鼓等形式,其本质是人内心的仁,没有仁的礼乐,徒然有其仪节和礼乐之器罢了。《论语·阳货》载,孔子的学生宰我认为,三年之丧太久,而孔子认为,三年之丧,才能表达内心对父母的情感,才能心安。宰我对礼乐的看法是只是形式上的,没有发自内心的情感,这样的礼乐是无根的。可以说,孔子对礼乐最大的发展在于赋予礼乐以内心的根据——“仁”。孔子对“仁”最一般意义的解释是“仁者,爱人”。这种“爱人”,始于“孝悌也者,仁之本与”(《论语·学而》),“本”是基础、起点之意,即孝、悌这种血缘之爱,朴素而自然的情感是心中的初始之“仁”。然后,这种爱亲之情扩大,“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或者“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即可以通过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的方式将血缘亲情扩展成为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普遍的感情,最后成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伦理金规则——一种道德标准(忠恕之道)由此建立起来。可以说,礼乐的仪节、仪式建立在人的“仁性”基础上,才是社会秩序的根本保障。在孔子的思想中,礼乐依然神圣,不是因为礼是“本于天,肴于地,列于鬼神”的权威,而是因为礼乐根植于人人皆具的血缘亲情之中。
“仁”不只是为礼乐注入的崭新的合理性依据,亦丰富了礼乐的伦理道德层面上的内涵。如果说《左传》中对礼仪与礼义的区分,看重的是“礼”的治国层面的典章制度是否合于“德”,那么,孔子一方面持有同样的态度,“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另一方面,孔子为礼乐注入的“仁”,在礼乐制度功能弱化的时代更凸现了“礼教”“乐教”的意义: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
“興于诗”者,《诗经》是抒发情感的,语言朴素,“而吟咏之间,抑扬反复,其感人又易入”;而“立于礼”,意为礼的规范使人立足于社会。孔子认同作为制度的周礼,但更扩展了“礼”的伦理道德内容。比如《论语·泰伯》载:“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这里的“礼”不是具体的行为规范,而是引申为行为的“规则、尺度”。所以朱熹《四书集注》注曰:“礼以恭敬辞逊为本,而有节文度数之详。”这一解释非常精当,不是礼制之“礼”,而是道德意义上的礼教之“礼”。对于“乐”亦是如此。孔子既维护作为制度的“乐”的严肃性,强调“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季氏》),又首倡“成于乐”,即乐对于人格之完成的意义。朱熹《四书集注》注曰:“古人之乐,声音所以养其耳,采色所以养其目,歌咏所以养性情,舞蹈所以养其血脉。”一言以蔽之,这是乐以成性。《礼记·仲尼燕居》中记载了孔子与学生的一段对话,更细致地解释了“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不能《诗》,于礼缪。不能乐,于礼素。薄于德,于礼虚。……达于礼而不达于乐谓之素,达于乐而不达于礼谓之偏。”无乐,礼教的形式就过于寡淡;无内在之德,礼的仪节就显得虚伪。通晓礼而不懂乐,就质朴无文;通晓乐而不通晓礼,就会造成更大的缺失。
简言之,孔子对于礼乐制度是完全赞同的,但是,在“礼崩乐坏”无可挽回的发展趋势下,孔子以“仁”作为礼和乐的内心依据,发展了礼和乐在伦理道德层面的价值,将礼作为道德行为的规范、尺度,将乐作为成就理想人格的方式。特别是孔子认识到了乐的特殊表现方式而肯定了乐的独特价值——乐的特征即引人入胜的旋律、节奏、舞蹈、黄钟大吕等,能够使人在精神愉悦、情感共鸣中完成内在品性的升华。西周的乐治方式中隐约有此义,而孔子更加明确而强化了乐的这一功能。可以说,孔子对乐的这一观念成为后世持续认同的一个重要方向。
四、“天地之序”与“天地之和”的伦理精神
孔子之后,礼乐渐成儒家坚守的一种理念,不同于制度形态的礼乐,也非仪节上的仪节、乐歌、乐舞,而是将礼乐转化为一套理论化的具有强烈伦理价值意味的思想观念。这出色地体现在《荀子·乐论》《礼记·乐记》等儒家经典中。对于礼之起源,《荀子》说:
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而分之。(《荀子·礼论》)
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是养天下之本也。《书》曰“维齐非齐。”此之谓也。(《荀子·王制》)
这不是真实的“礼”的起源,而是在言“礼”的社会功能。人人生而有无限的欲望,必然导致纷争,为此,先王制礼以使不同的人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别,有智、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各司其事、各有其位,即“礼”是人类社会的群体生活的保障。更重要的是,农、贾、百工、士大夫各尽其能、各居其分,富有天下而不自以为多,抱关击柝不自以为寡——“礼”就是“斩而齐,枉而顺,不同而一”的人伦秩序,即“礼”使社会成员以不齐为大齐,“维齐非齐”却是“至平”。之所以能做到职分不同却和谐一致,是因为“礼”的要求可以通过“乐”的“导志”来实现。“志”者,人之天然之情,人有好、恶、喜、怒、哀、乐之“六志”(《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导志”是“乐”的意义与功能,因为“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乐”是人的快乐情感的自然表达,并且具有“入人也深”“化人也速”“可以善民心”等特点。《荀子·乐论》说:
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乡里族长之中,长少同听之,则莫不和顺。
君子以钟鼓道志,以琴瑟乐心;……故乐者,所以道(导)乐[lè]也,金石丝竹,所以道(导)德也。乐行而民乡方矣。
先王制《雅》《颂》之乐,“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为諰,使其曲直、繁省、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雅》是周天子直辖地区庙堂祭祀时所用的“正声雅乐”,《颂》是宗庙祭祀之乐(如《周颂》《鲁颂》)庄重肃穆。先王制《雅》《颂》之乐,表达快乐而不过度,内容清晰而纯正,韵律、旋律、节奏能够激发人的善良之心。简言之,“乐”以其特有的使人愉悦的、感动人心的方式,引导人们的情感表达,使社会以“礼”区分的等级秩序而合理起来。故《荀子·乐论》说:“故乐者,天下之大齐也,中和之纪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是先王立乐之术也。”
将乐作为通向天下“大齐”“至平”的方式,荀子大大提升了乐的伦理功能,而在先秦论乐的典籍中,《礼记》中的《乐论》篇无疑将这一思想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是先秦儒家乐论的里程碑。《乐记》辑录编纂于汉代,遍采《荀子》《左传》《易传》《吕氏春秋》《孔子家语》等典籍中论礼乐的片段,而采自《荀子》最多。《乐记》论乐,非常出色地看到了乐的表达方式的根本特征,以此对乐的功能进行溯源。《乐记》曰: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
人心之于外物有所感动而自然吟唱出来的曲调是“声”,“声”辅以旋律变化,成为“音”,“音”再配以乐器演奏、持以舞具跳舞,而成为“乐”。简言之,乐之起源,本于“人心之感于物也”,此论极有见地,而由“声”而“音”而“乐”亦符合西周时期的“采风”传统。人心感应于外物时,发出的声音是不同的:哀心有所感时,发出的声音“噍以杀”;乐心有所感时,发出的声音“啴以缓”;喜心有所感时,发出的声音“和以柔”;怒心有所感时,发出的声音是“粗以厉”;等等。所以,圣贤的帝王“慎所以感之者”——对于能触动人的情感的事情十分慎重,因为不同的“声”“音”表现了不同的社会状况。《乐记》曰:“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1《]乐记》在解释乐治原理的基础上亦开拓了“乐”在伦理层面的功能:“先王慎其所感之者。故礼以道(导)其志,乐以和其声……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音”是自然而生、自发而成的民众的心声,“乐”则是在辨别不同“音”之后的有意识、有目的的创造。礼义的作用是引导、规范人们的心志,而乐是以其特有的方式来“和其声”,即和同人民的声音来统一民心而使社会安定、天下大治,这也是所谓圣王作乐以为教。《乐记》更进一步说:
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
律小大之称,比终始之序,以象事行,使亲疏、贵贱、长幼、男女之理皆形见于乐。
因为“乐”能够影响人的内在德性,所以是“通伦理”的。规范音律使其高低适度,排列乐章使其前后和顺,如同各种伦理关系,使亲疏、贵贱、长幼、男女的区别都由乐表现出来。所以,先王作乐不是率性而为,而是“本之情性,稽之度数”,根据人天生的情与心性,审慎地制定音律,使其发挥教化民风的作用。《乐記》中说:“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圣人喜乐,是因为乐能够使民心向善,可以感人至深,可以移风易俗,起到乐教的作用。
如果说“审乐以知政”是西周来的某种共识,那么“乐者通伦理”则是《乐记》的贡献。当然,《乐记》最大的理论意义在于继承和发扬了《荀子·乐论》中“乐合同”的思想[1],由此提出了礼乐的伦理精神。伦理的本质是共同体的行为规范,而伦理精神则是伦理规范体系的价值目标与精神指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乐记》将礼乐的内涵升华到了伦理精神的层面,《乐记》曰:
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
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
乐,象征天地的和谐;礼,象征天地的秩序。乐的精神是“和谐”,礼的精神是“秩序”。这不仅仅是给予礼乐以神圣的形上依据,更重要的是赋予礼乐一种深远的、具有文明气象的伦理精神,同时也指向了理想的文化模式和美好的社会形态。“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乐记》)一个理想的社会,须礼乐相辅相成:一方面,礼的规制井然有序而使人不能争;另一方面,乐使个体精神安宁、群体和谐安定,此乃更高的追求。毋庸讳言,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有着严格等级次序的社会,维持这种秩序不仅要靠外在的规范,而且需要每个社会成员内心的认同——“序”要求行为一丝不苟,“和”既是对个人内心的一种修养要求,也是整个社会所追求的一种群体的状态。《乐记》曰:“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乐是为了和合情感,礼是为区别差异。情感相和就能彼此亲近,相互区别才能有所尊敬。乐过度就会失去敬重而无尊卑,礼过度就会疏离失和而对立。所以礼乐不可偏于一端,礼追求秩序,却非冰冷的有序,而是有温情的、和谐的秩序,也即是说,乐是在等级差异中求和谐,礼是在混乱中定秩序。“序”的极致不是铁的秩序,而是和谐的“礼之用,和为贵”。
更进一步说,礼乐是身心相应、内外统一的。内心的情感是伦理之源,乐者通伦理也;而外在的规范则是情感的共鸣,礼之至必达于乐。《乐记》说:“衰麻哭泣,所以节丧纪也;钟鼓干戚,所以和安乐也。”前者是礼发自内心之情,后者是乐以音律舞蹈之美合和人心。《乐记》中说:“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合乎情然后才能应乎礼。朱光潜先生说:“内不和而外敬,其敬为乡愿(按:伪善);内不合乎情而外求当于理,其理为残酷寡恩;内无乐而外守礼,其礼必为拘板的仪式,枯渴而无生命。礼不可以无乐,犹如人体躯壳不可无灵魂。”[1]
可以说,“礼者天地之序”“乐者天地之和”是礼乐文明独特的价值追求。在《礼记·孔子闲居》里,孔子提出了无形式的“无声之乐”“无体之礼”;《乐记》中也强调“大乐必易,大礼必简”,即最隆重的礼献祭的是最简单的东西,最隆重的乐是最朴素的、使民合爱无怨的德音。这背后的深刻内涵在于,礼乐是仪节仪式和乐歌乐舞,更是在追求一种内在价值——“序”与“和”的统一,这是儒家伦理的一种深层结构和独具特色的伦理精神。这种精神因“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的人文气象而成其盛,因“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的道德理想而成其久,已成为中国伦理的一种信念,这无疑具有超越时代的意义。
五、余论
虽然从《论语》《左传》到《乐记》都强调礼的仪节和乐的形式表达都是“末节”,但这只是针对当时涣散的礼乐制度缺乏内在精神而言的。其实,礼的规定仪节、乐歌乐舞的表现形式都有重要意义。礼,在一举一动中养成了秩序的习惯。乐使人在美的享受过程中,在抒发、宣泄情感中,以融善入美的方式感动人心、陶冶心灵。《荀子·乐论》中曾颇有深意地详细描绘了“乡饮酒礼”的整个过程,朴素的乐与细致的礼规水乳交融,细节中所蕴含的是深层伦理秩序。与礼相比,乐最直接的作用是同化感情、引发共鸣。无论什么等级的人,或长或幼,或尊或卑,于悲伤之乐中一哀俱哀,于欢娱之乐中一喜俱喜,于肃穆之乐中皆是庄重之情,这是乐化除差别的功用,即《乐记》中所谓“合同而化,而乐兴焉”之意。把礼的規则通过乐的感与化,使人在审美体验中成人成德,这是儒家伦理的优胜之处。
百年来,一批具有世界眼光的中国现代学者尤其重视礼乐的伦理价值。金岳霖《说礼》曰:“夫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礼也者,体也。体不备,其他美德无由而生。……欧风东渐,厌旧喜新,夷狄诸夏,此其时矣!救末世而挽颓风,端在君子悦礼乐而敦诗书者,其有意于斯乎?”[2]贺麟先生则看重“乐”的意义:“儒家特别注重诗教乐教,确具深识卓见。惟凡百艺术皆所以表示本体界之意蕴,皆精神生活洋溢之具体的表现。”[3]而对于礼乐作为一种普遍意义上的伦理精神,朱光潜先生的论述最为精辟,他说:“从来欧洲人谈人生幸福,多偏重‘自由一个观念;其实与其说自由,不如说和谐,因为彼此自由可互相冲突,而和谐是化除冲突后的自由。和谐是个人修养的胜境。”[4]综合以上诸论,可以说,礼和乐的伦理精神是相互关联的,“序”与“和”的相辅相成、对立统一,体现了礼乐伦理精神的真谛,也是中国传统伦理对于世界文明的贡献。唐君毅先生说:“中国后来之学者之无不向慕三代,向慕文王周公之德教,亦即向慕此内涵的精神。而中国以后数千年之文化,皆本此原始精神,而经种种挑战,再加同应,以次第发展至今而未尝断绝。”[5]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礼乐的制度形态已经渐失其生命力,而唐君毅先生所说的礼乐之德教所蕴含的伦理精神,却一直绵延不绝,历久弥新。
〔责任编辑:洪峰〕
本文为江苏省道德发展智库、江苏省公民道德与社会风尚协同创新中心项目“中国传统礼乐文化的伦理机制研究”(2242018S10016)、“商周伦理探源研究”、国家社科基金“先秦儒家伦理的情感逻辑研究”(19ZXB115)的研究成果。
[1]参见陈瑛、温克勤、唐凯麟等:《中国伦理思想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罗国杰主编:《中国伦理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参见张岱年:《中国伦理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沈善洪、王凤贤:《中国伦理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张锡勤:《中国伦理道德变迁史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3]参见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朱贻庭:《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1][5][7]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3页、第368页,第466页,第357页。
[2]王国维:《释礼》,《观堂集林》上册,中华书局出版社2004年版,第291页。
[3]郭沫若:《十批判书·孔墨的批判》,《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6页。
[4]裘锡圭:《甲骨文中的几种乐器名称——释“庸”“丰”“鼗”》,《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00—201页。
[6]罗振玉:《殷虚书契考释·三种》下册,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463页。
[1][4]余英时:《论天人之际》,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81—82页,第83—84页。
[2]李泽厚:《由巫到礼释礼归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11页。
[3]参见巴新生:《试论先秦“德”的起源与流变》,《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李建德:《“德”之初义研究综述》,《武陵学刊》2019年第1期。
[1]《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36页。
[2]余英时:《论天人之际》,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212—223页。
[3]王德培:《〈书〉传求是札记(上)》,《天津师大学报》1983年第4期。
[4]张岱年:《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54页。
[5]参见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1页;王德培:《〈书〉传求是札记(上)》,《天津师大学报》1983年第4期。
[6]李学勤:《中国古代文明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7页。
[7]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27—238页。
[8]刘雨:《西周金文中的祭祖礼》,《考古学报》1989年第4期。
[1][2][3][4]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下册,中华书局出版社2004年版,第451—454页、第474页,第477页、第475页。
[1]《仪礼·觐礼》载:“(天子称呼诸侯)同姓大国,则曰‘伯夫;其异性,则曰‘伯舅。同性小國,则曰‘叔父;其异性小邦,则曰‘叔舅。”(杨天宇撰:《仪礼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93页)同姓大国、异姓大国、同姓小邦、异性小邦的称谓不同,意味着血缘亲疏与政治秩序中的地位。
[2][3]左丘明:《左传》,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650页,第1967页。
[1]值得一提的是,《史记·吴太伯世家》中对季札论乐的精彩描述,以《乐记》的理论确实可以得到合理的说明。
[1]荀子特别关注礼乐配合对于社会秩序的意义。《乐记》继承这一观点:“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者也,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故先王之制礼乐,人为之节。”人心在外物的影响下会产生各种欲求,若内心不能节制,即被物化,就会泯灭天理而追求无尽的人欲,所以圣王制礼作乐都是为了节制人心。《乐记》说:“衰麻哭泣,所以节丧纪也;钟鼓干戚,所以和安乐也。”这一“礼节民心,乐和同声”的思想源自《荀子·乐论》的“乐合同,礼别异,礼乐之统,管乎人心”。
[1][4]朱光潜:《乐的精神与礼的精神》,《思想与时代》1942年第7期。
[2]金岳霖:《说礼》,清华学校编:《赠言》,清华学校1914年印。转引自郑建成、许晨:《金岳霖〈说礼〉》,《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3月30日。
[3]贺麟:《儒家思想的新开展》,《思想与时代》1941年第1期。
[5]唐君毅:《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0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