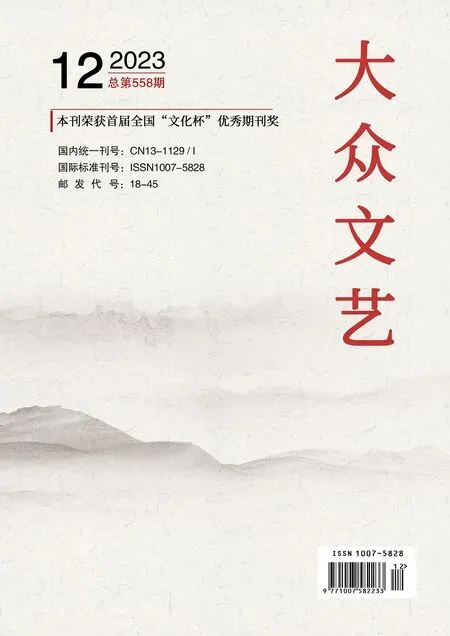理性如何实现正义?
——《米歇尔•科尔哈斯》中对理性的思考
席田越
(南开大学,天津 300071)
《米歇尔•科尔哈斯》这部小说描述了写科尔哈斯追求正义的经历。从表层来看,小说在探讨如何实现正义这一问题,甚或是,当法律不能实现正义,应如何实现正义?科尔哈斯首先诉诸法律手段,一旦法律难以维护正义之时,他便走向了法律的对立面,一为从外部打破法律制度,建立“私人化的法”的暴力手段,另一为从法律内部,挑战法律理论架构的神学力量。然从更深一层去看,小说是在探讨理性是否能实现正义。法律本应是群体理性的代表,用以维护群体中每个人的权益,但是在实际运用中,无论是从立法权还是解释权,法律作为统治者的工具,不能顾全普通人的权利。故科尔哈斯借以个体理性来反对集权理性,暴力便是科尔哈斯实现其个人的理性的途径,即以“‘暴力秩序’剥夺法律的‘文字秩序’”[1]。他通过暴力来撼动象征群体理性的法律,建立起个人法律,即“法的私人化”,以彰显个人理性。然而,无论是集权理性还是个体理性,当其膨胀之时,都会以牺牲他人权利作为其建立的代价,那么二者均不是实现正义的恰当途径。故事中,真正使科尔哈斯获得正义的是一张偶然获得的“神秘纸条”,它以认知理性彻底打败了法律的集权理性,触发法律自身的自反性,从而消解了法律的理性意义,令法律走向理性的另一端。认知理性获取正义的高明之处在于它是从内部推倒了法律架构之中的第一个多米诺骨牌,然而这一偶然机制,却触发整个法律体制的崩塌。
下面,结合文本,对这三种方式进行一一分析。
一、法律——集权理性
齐泽克曾说:“这个故事讲述了一个不了解确定法律运用的不成文法则的‘固守法则的人’过分追求正义,最终以犯罪结束。”[2]他认为,科尔哈斯不了解法律运用的不成文法则,即“虽然没有人明确地陈述过这些规则,但是,不遵循这些规则的话,便会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2]马克思解释这种“不成文的法则”为“现实抽象”力量,是社会中约定俗成的具有服从意味的共识,其目的是维护统治特权。意识形态存在的作用之一便是遮蔽社会现实中盛行的“现实抽象”。在《米歇尔•科尔哈斯》中,“不成文的法则”是法律的天平自觉地倾向集权统治者,无论是马丁路德、律师还是司令官,对此心知肚明,然科尔哈斯对这一“现实抽象”力量发出挑战。
首先,科尔哈斯认为任何人必须按照法律行事。容克私设关卡,收取过路费敛财;擅自规定“没有国君的许可证,任何人不得带着马匹越过边境。”[3],限制通行;又非法扣留私人财产,并虐待科尔哈斯的两匹黑马,留下来照看马匹的马夫赫尔塞也伤痕累累。这便“从一开始的扣留马匹,升级为对私人财产的损害以及对马夫赫尔塞的人身伤害。”[4]这是容克对科尔哈斯所行的三件不法之事。科尔哈斯“熟悉国君有关他这个行业的一切法规”,故他深知容克违背法律规定,便要求容克赔偿他的所有损失。事实上,科尔哈斯忽视了容克享有的法律特权,所谓“不成文的法则”便是容克可以滥用私权。法律固然没有表明容克有权利用路障敛财,但是作为统治阶层的一员,容克可以违反法度,或者篡改法度,因为立法权及法律的解释权掌握在集权统治者手中。
其次,科尔哈斯坚信统治者可以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他将希望寄托于执政者:“国君本人,我知道的是公正的;只要我能过他周围臣仆的关,向他面呈此事,那我毫不怀疑正义会得以伸张。”所以,面对不公,他不断求助于地位更高的执法者。一开始,当堡长要求出示“国君的特许证”,克尔哈斯主动要求面见容克,可还是留下黑马抵押;之后科尔哈斯向德雷斯顿法院提出诉讼,最终被撤诉;之后他托人将申诉书呈送到萨克森选帝侯手中,但处理此事的首相置之不理;最后他的妻子以身犯险将申诉书送到柏林国君手中,却惨遭杀害。容克、法院、选帝侯……科尔哈斯寄希望于更公正的执法者,实际上,没有容克的默许与纵容,堡长不敢提出非分的要求并虐待黑马与马夫;因为容克与上层亲近的人际关系,科尔哈斯才被剥夺诉讼权;为了国君安全,平白牺牲了妻子的生命。背后的种种原因都在证明,统治者非但无法维护科尔哈斯的正义,而且不断侵犯着科尔哈斯的合法权利甚至伤及无辜。科尔哈斯没有意识到的是,整个司法体系出了问题,法律的实施过程中缺乏制度的维护,“他认为公正的执法者是实现正义的保证,没有认识到执法者作为个人,需要有制度来约束他的弱点,从而保证其不徇私情、不偏不倚。”[4]
从西方律法的传统看,法律本应是“理性的宣言”[8],作者克莱斯特“察觉到了个体意志与法律形式的冲突,并开始质疑法律的有效性。”[1]需要明确的是,造成法律失效,并非“成文法本身的不公正”[5],而是“当权者忽视法律这一事实”[5]。所以,批判的出发点其实是法律背后的运行机制。而这完全是集权统治的机制,其正当性反应于集权理性。所以作为被统治阶级,科尔哈斯利用象征集权理性的法律来为自我正义张本,从根本上是不可能实现的。甚或是,在集权统治运行的机制下,法律不能实现真正的正义。
二、暴力——个体理性
“面对纵横交错的人性的弱点和欲望时,对于一个绝对的、由国家保障的公平的假设分崩离析”[6]科尔哈斯并非一直蒙蔽在法律的幻境中,妻子的死亡让他明白:合法途径不能使他实现正义。他便走到了法的对立面,用暴力来捍卫公平与正义。
科尔哈斯的暴力反抗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且主要来自他对法律的失望。首先,转向暴力反抗的原因是因为法律手段的失败。“速到特龙肯堡将马匹领回,不得上诉,否则便予以监禁,以示儆戒”。选帝侯的批复使科尔哈斯对法律制度彻底失望。其次,他的遭遇在许多民众中具有代表性,如“这几个人平素都对容克不满,对战利品也有觊觎之心,很想投到他的麾下效命”所以在广泛的群众基础之上,他建立武装军队,开始暴力反抗。还有,如小说开篇介绍“他乐善好施,仗义执言”,而且他富有责任感,他为同胞们所受的欺辱感到愤恨。无论是他自身超乎常人的美德,还是为广大民众打抱不平,还是对现有制度的失望,都促使科尔哈斯走上了暴力反抗之路。
然而,科尔哈斯的暴力更是一种非理性的行为。无论是为自己还是为他人,他对正义的理想化追求使得他个人理性极度膨胀,“在他的价值体系中只存在着清晰的非此即彼,在他的思维中善与恶截然对立”[6],这种绝对化、单一化的思维方式,令他逐渐偏离了理性的轨道。
当个人的理性膨胀,便会走向非理性的极端,科尔哈斯选择暴力手段维护自我理性,即把自己当作视为世界的中心,以自我为目的,以他人为手段。在小说中,科尔哈斯将自己从现存的社会关系中剥离,并宣称自己是一位“仅服从于上帝的帝国及其边界的自由民”他骄傲地将自己的驻扎地称为“世界临时世俗政府所在地”他号召百姓加入自己,“为了建立更好的秩序”,并且将自己打造为复仇天使米歇尔的地方执行官,以上帝之命进行惩罚。他无限抬高自己的身份,为了建立自己的秩序,那就需要打破原有的体制,既然要成为“父”,那就要替代原有的“父”。如此,“科尔哈斯由一个正义的寻求者变成了独断专行的正义的制定者,他体现出具有超凡魅力的合法革命者之态,威胁着要剥夺传统意义上合法统治者的生存基础”[5]
科尔哈斯曾经作为集权体制的牺牲品而被剥夺自身的主体性,他现在以剥夺他人主体性的方式来建立自我的主体性,这一逻辑和集权统治的逻辑并无二致。他的初衷是维护自我与他人的正义,为民除害,但是在实行中,他通过纵火行为制造群体恐慌,借此将个人仇恨上升为社会仇恨,他敕令道:“如不将容克交出,将玉石俱焚,使城池化为一片废墟,使我无须隔墙便能将容克擒拿归案。”对于民众来说,纵火威胁着他们的人身安全,只有将容克赶出城外,才能重新获得稳定与安全,所以他们将容克视为“吸血鬼、害群之马”。这种强化意识认同,驯化思想,建立统治的模式与集权统治的运行机制极度类似。
科尔哈斯的暴力维权看似走到了集权法律的对立面,究其根本,科尔哈斯的暴力来源于他对法律的过分认同。齐泽克分析说:“一旦他(科尔哈斯)开始相信现存的法律结构的腐败,无法遵守其自己的法则,他便朝着一个几乎偏执狂的方向送出象征性信号,宣称他打算建立一个‘新的政府’”[2]法律作为一种“文字秩序”,通过制定明确的规则与惩罚来制约人的行为,科尔哈斯通过暴力,形成对人的恐吓与威胁,进而通过压迫来使人顺从,他用“暴力秩序”取代法律的“文字秩序”,完成“法的私人化”。科尔哈斯的行为也就从一个“有法律保护的暴力”变成了“制定法律的暴力”[2]。本质上,科尔哈斯建立一种新的集权统治,这种集权与他曾经背弃的政治形式如出一辙,而最初所追求的正义也在暴力的行为中失去了其应有的价值。
利德尔对科尔哈斯评价道:“科尔哈斯通过部分革命的方式追求一种非革命的状态。他头脑中也没有那种法国大革命期间与广泛自由理想相联系的对全新开始的狂热情绪。科尔哈斯将赋予暴力以拯救和纯洁功能的千禧年革命的观念给世俗化了。对义人的拯救应该通过建立一个新的耶路撒冷来实现;对社会的纯洁应该通过清除杂草来实现。”[7]由此可以得知,科尔哈斯自身保守性导致他选择暴力反抗的方式就是错误的,他的暴力行为无疑是失败的。如上文分析到,他的暴力是自我理性膨胀情况下,以自我意志对对社会秩序的再构,这一定会危害到群众的利益,既然如此,他一开始想要守卫的正义也无处谈起。所以,个人的暴行和集权的法律一样,都不能维护正义,甚至会损害正义。
三、神秘的纸条——认知理性
小说的张力在于,如果科尔哈斯因其在讨伐容克过程中所做的暴行而被判处国家安全罪,那么“法律无法实现其正义”这一事实便是他犯罪的诱因,这便变相地承认了国家的过失,显然不合适,然而,如果科尔哈斯没有因为其暴力受到惩罚,那么国家就没有履行对其他在这场暴乱中无辜受害者的保护义务,那么如何处理科尔哈斯,科尔哈斯的正义又该如何实现,是矛盾的症结所在。
因此,作者引入具有神学色彩的“神秘纸条”改变了故事的走向。吉卜赛女王交给科尔哈斯记载着选帝侯命运的纸条。自此,萨克森选帝侯陷入了深深的不安当中。他企图撤回对科尔哈斯的诉讼,故先后致函给德意志皇帝和勃兰登选帝侯,希望科尔哈斯免于死刑。最终,萨克森选帝侯利用法律手段来延缓科尔哈斯刑期的努力均以失败告终。在临刑前,科尔哈斯径直吞下“神秘纸条”,萨克森选帝侯永远无法得知预示的真相,身心受到极大打击。对于选帝侯而言,“神秘纸条”完全超出其认知秩序。这张神秘的纸条使萨克森选帝侯彻底沦为现代的坦塔罗斯。在“神秘纸条”的作用下,萨克森选帝侯和科尔哈斯在法律领域和认知领域中建立起附属与支配地位完全不同的对立关系。在法律秩序中,萨克森选帝侯以法的命运剥夺了科尔哈斯的生命与自由,在认知领域中,科尔哈斯凭借神秘纸条获得了选帝侯精神世界的绝对控制权。无法获得的预言秘密就像是永远得不到的食物与悬在空中头顶的巨石,使他无时无刻不在受着精神的折磨,为了从认知领域的困境中解脱,萨克森选帝侯不得不在法律领域中推翻对科尔哈斯的处决,保留科尔哈斯的生命以保证“预言”的存在。这时的神秘纸条已经不仅仅是预示意义的能指,更是一种特权意义的能指。“神秘纸条”的对法律的颠覆性在于选帝侯通过法律手段惩罚科尔哈斯转向利用法律手段来拯救科尔哈斯,然而,科尔哈斯通过法律手段的无效性达到了折磨选帝侯的目的,最终真正实现正义。
“科尔哈斯以‘神秘纸条’的认知权利完成对选帝侯法律权利的支配与奴役……象征着法律秩序中的选帝侯最终沉浮于认知秩序中的至权者(科尔哈斯)。”[1]也就是说,科尔哈斯通过认知领域中的理性颠覆了法律秩序,达到了真正的正义。需要明确的是,认知理性并非个人理性,而是一种理性标准,它凭借精神力量对抗法律代表的集权理性。对抗的方式便是激发法律的自反性,即利用法律内部规则使法律制定者深陷困境,从而消解法律自身的权威性,将其推向非理性的边缘,背后则是对法律制定者和集权理性的一种不满与质疑。
小结
本文探究在实现正义的途径背后所反映的理性问题。那么为何要谈这部作品对理性的阐释,这与作者克莱斯特本人不无关系。
作者设置“神秘纸条”来干预法律机器的运行,用一种带有神秘性的因素颠覆了理性的法律机制,透露作者出对理性的质疑与思考。这与作者克莱斯特思想上出现的“康德危机”有关。他曾不止一次在其书信中说过在思想上遭遇了“康德危机”。康德提出人是有限的理性存在。而且理性的膨胀导致人偏离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而沦向工具理性与物质理性。对于在“求真观念中包含一种非此即彼的偏执”[1]的克莱斯特,这一观点改变了他对人理性的认知,并开始反思人过度依赖理性的后果。“理性的自我控制以及对主体的重视导致了主体的绝对化,而且带来了这样的后果:纯粹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认知模式处于转变状态,然后解体。”[9]他意识到理性导致主体绝对化,即人夸大自己的作用与地位,以自我为目的而将他者当作手段,不仅认为本身有突破自身界限的能力,而且还企图利用知识获得支配外在世界的能力。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何在《米歇尔•科尔哈斯》中探讨理性与正义的关系问题了。换句话说,不仅仅是理性能否实现正义的问题,更值得反思的是,滥用理性才是引起非正义事件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