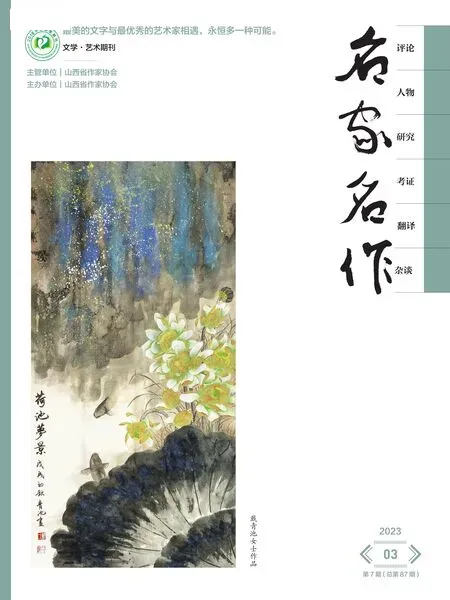从《看虹录》第三节看沈从文的自我抒写
曾钰雯
《看虹录》是沈从文20世纪40年代创作的短篇小说,从一发表的备受争议,到之后的重见天日得以发掘其中的价值,作家和作品的命运同样起伏波折。至今,对《看虹录》的研读相较于沈从文的其他代表作品算不上数量丰富,但已经较为多样,不过仍有一些东西被遗漏了。小说《看虹录》共三节,以往的讨论研究中重点大都集中在篇幅较长的第二节,对第三节没有给予充分的关注,通过对《看虹录》第三节内容的分析,可以进一步走近沈从文,了解这位中国作家哲学层面的所感所思,也能更加理解沈从文在20 世纪40 年代的个体生命情感。
一
叙事本来应该是小说的主体,但在《看虹录》中抒情是绝对的主题。小说取名为《看虹录》,根据字面意思,就是对看“虹”的记录,第二节“看虹”的过程理应是小说的重点,但沈从文却没能停笔,在第二节记录主客之间的故事之后,又以第一人称继续写下了第三节中那些意识流式的自我情绪抒写。有研究者认为这篇小说“第二部分是叙事的诗化,第一、三部分是抒情的故事化;前者通过隐喻手法暗示抽象本质,后者则以对时间的明确标志达到叙事化”[1],可以看出评论者已然发现抒情是《看虹录》的“重头戏”,但只将最是抒情的第三节看作表明时间的叙事部分。在我们看来,《看虹录》作为一篇抒情小说,叙事只不过是小说必要的形式,抒情才是这篇小说真正的题旨。
《看虹录》中,第二节记录了主客之间的对话,第三节则以第一人称在抒情,也就是“我”在直接抒发感怀,这篇小说中的“我”很带有沈从文本人的影子。我们来看一下小说第三节中的描述:“试游目四瞩,这里那里只是书,两千年前人写的,一万里外人写的,自己写的,不相识同时人写的”;“在桌上稿本内,已写成了五千字。我知道这小东西寄到另外一处去,别人便把它当成‘小说’,从故事中推究真伪。对于我呢,生命的残余,梦的残余而已”[2]。这些片段和特征,让我们感受到作家沈从文与小说中的“我”的某种重合。我们说《看虹录》是沈从文抒写自我生命情感的一篇抒情小说,我们应当从中进一步走近沈从文、理解沈从文。正如钱理群教授在《沈从文〈看虹录〉研读》中讲评时提出的:“文学研究是干什么的?不就是研究‘人’(研究作家其人,又通过作家的作品,研究社会、历史上的人)吗?不理解,又算得了什么研究呢?而且,我们要研究的是这样特殊的人:他(她)们的思想、感情、心理,都更复杂,更敏感,也更脆弱,更需要小心地,细心地去体察,理解”[1]。
我们说《看虹录》是一篇抒情小说,其中以第一人称叙事的第三小节,就是沈从文在直接抒情,在自我关照,通过对第三节的再读,我们更加贴近了作家20 世纪40年代在昆明时期的心灵状态。其实,《看虹录》是沈从文整个四十年代创作的一类型作品中的一个,这一类作品的共性是对生命的思考、对神性的抒写以及对生命的焦虑、对文化的焦虑。“四十年代对于沈从文是有着特殊意义的年代,丰富的人生经历和独特的生命体验,使沈从文的文学创作无论从思想性还是艺术性上都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境界”[3]。20 世纪30 年代,由于抗日战争爆发,沈从文随西南联大来到云南,在昆明郊区生活了8 年。正如有评论者所说:“20 世纪40 年代可以说是沈从文的彷徨期。随着以湘西生命形式为根基的生命理想的失落,沈从文的生命焦虑与文化焦虑日益加剧,这时期他思考的问题都是围绕生命而展开的”[4]。
二
《看虹录》第三节篇幅短小,但内涵与意义比第二节更为丰富。第三节结尾处有一个词——“自苦”,很能概括沈从文那个时期的心境,因自我的尘扰生出苦涩、苦恼、烦闷,他在“看虹”之后回到现实中来,他写他感受到“我似乎很累,然而却依然活在一种有继续性的荒唐境界里”。从第三节情绪化的文字里,我们还可以挑出这些关键词——“空虚”“消失”“失去”“生命残余”,我们能够察觉到沈从文在抒发对生命的虚无感、易逝感。这种状态,其实是20 世纪40 年代沈从文整个的一种写作状态,我们可以从他当时所写的一系列散文中看到,小说《看虹录》与散文《长庚》《水云》《绿魇》等,其实都是在表达同一种思考、同一种焦虑,就像沈从文在《长庚》中写到的:“由于外来现象的束缚,与一己信心的固持,我无一时不在战争中,无一时不在抽象与实际的战争中,推挽撑拒,总不休息”[5]。
抽象与实际,正如《看虹录》中第二节与第三节的关系。“看虹”的故事从何而起?沈从文在开头写道:“忽闻嗅到梅花清香,引我向‘空虚’凝眸。慢慢地走向那个‘空虚’,于是我便进到了一个小小的庭院,一间素朴的房子中……”随后小说展开第二节中客人对“虹”之美的欣赏和记录,而在第二节结束时作者又专门点明“……这一切又只像是一个抽象”。“虹”在自然界中本身就是一种海市蜃楼般的虚空存在,彩虹作为自然界的神奇造物,是人类抬头仰望之物,它自然、美好、绚烂、短暂、易逝,也就是第二节中客人“我”对女主人身体欣赏的感受。关于《看虹录》中的身体写作,正如《论沈从文〈看虹录〉的身体叙事》一文中所说:“该小说长期淹没在历史中。1992 年小说被整理发掘出来,随即引起学界极大的兴趣。研究者不再将其简单地视作一部关于‘性’的文本,而是力图从审美、意象、结构等角度挖掘其中丰富的内涵,探讨小说的‘本来意图’。一方面,我们无法否认《看虹录》确是以身体为书写重心,女主人公仅仅表现为身体存在,身体不仅是人物的表现形式,也是人物的本质;另一方面,小说中的身体显然又不同于实在的‘肉体’,而是表现出浓厚的抽象色彩。”[6]是的,小说第二节中的身体描述,不能简单地看作是情色,而是沈从文自我深感且崇拜伟大造物的神秘与神奇,他是处在一种西方哲学的纯粹理性中完成的欣赏。美是不朽的,但世俗还在,他不可能长久地待在纯粹中,所以思想的困顿来了,人生中的实际永远追随着每一个人,不同的是每一个个体如何面对实际。
沈从文回到实际人生中,就委顿、烦闷了。在作为结尾的第三节中,他叙述说“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离开了那个‘房间’,重新站到这个老式牌楼下”“我已经回到了住处”,这些描述都是在提示我们,他从“一个人二十四点钟内生命的一种形式”回归了现实,所以他遭遇了虚无。他心中的矛盾和冲突,来自他也想“回到生命的本体中去”,如徐志摩一样,想“与生命的本体同绵延”,但是他与他的朋友一样,这一理想并没有得到更多的理解,抽象与实际的战争在沈从文内心往来不息。
三
还是回归到第三节中沈从文的自我抒写。对于“看虹”的记录,他说:“我面对着这个记载,热爱那个‘抽象’,向虚空凝眸来耗费这个时间。”他表达得清楚,他向往着超脱于实际生活之上的那种纯粹的精神空间和状态,他的生命精力也愿投入其间。可是,沈从文不能摆脱世俗人生的束缚,真我被压抑,只能自苦,他在第三节里抒发“我似乎在用抽象虐待自己肉体和灵魂,虽痛苦同时也是享受”“我完全活在一种观念中,并非活在实际世界中”。《看虹录》之所以在当时备受批判和指责,是因为沈从文的追求和思考偏离了中国社会文化所规定的行为模式。沈从文著名的宣言——“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这庙供奉的是人性”以及《看虹录》第三节中的感叹“唉,上帝……”,是的,沈从文思想中有西方哲学,有研究者指出“沈从文与西方现代哲学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沈从文既受到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西方现代心理学、存在主义等非理性人本主义哲学的影响,又受到西方现代理性主义哲学的影响。当沈从文站在生命——人性立场上时,非理性人本主义哲学思想占据主导地位,而当他站在历史发展进步的立场上时,西方现代理性哲学思想便表现得比较明显。唯物与唯心、理性与非理性、科学与玄学等同时参与建构沈从文的哲学思想,它们相互交织、相互激荡,形成一种悖论逆反的关系,构成沈从文哲学思想复杂性与‘复调性’。”[7]《看虹录》中对身体的纯粹欣赏与描述,也正是发端于西方超越感性现实的纯粹理性,正如西方以雕塑或绘画表现裸体,但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无法理解这样的沈从文。
通过对小说《看虹录》第三节中“我”的内心独白的探讨,我们可以去理解一个内心充满冲突、自苦、斗争、思考生命意义的沈从文。德裔美国心理学家、新弗洛伊德主义的代表人物卡伦·霍妮在其著作《我们内心的冲突》一书中指出,由于深受生活环境的影响,我们总是与我们想成为的人背道而驰,于是产生了这些足以主宰我们人生的内心冲突。卡伦·霍妮是社会心理学的最早倡导者之一,她认为,人类的精神冲突与社会环境联系密切,她相信用社会心理学说明人格的发展比弗洛伊德的性概念更适当。卡伦·霍妮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她认为是文化因素引发了心理病症。《看虹录》的第三节就是沈从文在尝试着描述自己内心的冲突,这一冲突很大程度上来自社会和文化。沈从文曾说:“自己过去习作中的一部分,见出与社会现实的脱节。由情感幻异的以佛经故事改造的故事,发展成《七色魇》的病态格局,以及《看虹录》《摘星录》中夸侈荒诞的恋爱小说。……究其原因,除了读书范围杂,以尼采式的孤立、佛经的虚无主义和文选诸子学,以及弗洛伊德、乔依斯造成的思想杂糅混合,全起源于个人与现实政治游离产生的孤立。”[8]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一书中,卡伦·霍妮列举了社会文化中引起不可消解的神经症冲突的三种主要矛盾:一是价值标准混乱所导致的矛盾;二是各种享受需要与无法满足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三是个人自由和实际所受到的一切局限之间的矛盾。[9]沈从文通过《看虹录》表达了头脑中不可消解的冲突和矛盾。
四
沈从文在《抽象的抒情》中说: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其实他的《看虹录》就是在进行抽象的抒情。自苦的思索者沈从文通过《看虹录》表达了他的思想:生命的存在就应当活跃、流动、蓬勃,生命本就饱满壮实,生命待赠与、待扩张,不然就会枯萎,这是“神”创造生命的意志。他通过小说中对母鹿和女主人美丽精致的身体的描述,完成和实现了他自己的一次生命意义的追求,悦乐疯狂,但选择写出来公之于众是很冒险的。作为那个抽象故事中的客人,沈从文借客人之口,说出了他对现实的忧虑和恐惧,小说里写到“你知道,大凡一种和习惯不大相合的思想行为,有时还被人看成十分危险,会出乱子的!”内心敏感的沈从文已经感知到这个故事会带来危险,那为什么还要写出来呢?他渴望得到理解,被理解才能在虚无中捕捉生命的意义。这一点在小说中也有体现:客人说自己正在写一篇小说,只有小孩子能真正欣赏这个故事,当女主人评价说故事不真实的时候,客人(作者)严厉地说“请你看下去!看完后再批评”,客人(作者)希望读者能理解这个故事。故事中的故事,那头母鹿对于“我”却是不惊、不惧,“似乎完全知道我对于它的善意”。沈从文已然告诉读者,《看虹录》的故事绝非邪淫,而是单纯素净,是道德的极致,他写到那头母鹿居然“为了理解爱而叹息”,理解爱——这可能是作家沈从文写作《看虹录》的其中一个意图吧。第三节结尾处,作者说他在写《聊斋》中的青凤要她在自己笔下复活,青凤作为狐魅生灵,有人的感情但无人之束缚,这是一个有着人情味的自然生命,充分体现着沈从文认可的“人性”。沈从文在《看虹录》中思考的不是他这一个体,而是“人”这一群体,不只思考一般而是求索普遍价值,沈从文在其中的思考带有中国式经验,他不会通过理性的论述形式来展现他的思考,而是通过感性的抒情呓语来传达价值,他在小说中重复写到“神在我们生命里”,这是一种庄严的情感。
我们说沈从文的抒情小说《看虹录》,记录的是他基于庄严道德的情感而进行的生命之美的欣赏和赞叹,传达的是他对于生命存在应当充分绽放燃烧的思考,但他深感得不到理解,于是在小说第三节抒发了自我内心的冲突和无解。小说的三个部分是一个整体,从第三节切入分析更易发现和明确小说的本来意图和作家的内心抒写而不至于误解第二节中的内容为不洁。作家沈从文一直以来都渴望得到理解,但斯人已逝,希望《看虹录》一类的作品不再被简单否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