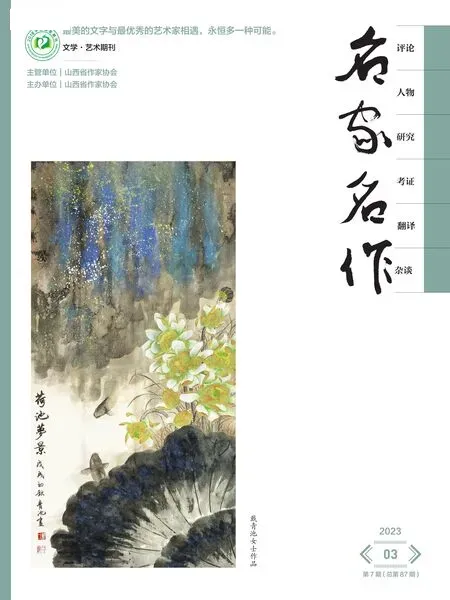人:神圣礼仪的现实存在
——评芬格莱特《孔子:即凡而圣》
陈孟婕
中国在世界学术研究视野中一直未曾缺席[1],但直到20 世纪才开始蓬勃发展。芬格莱特创作于20 世纪70 年代的《孔子:即凡而圣》具有转折性的意义,此前的西方学者多用西方理论价值体系评判儒学思想:20 世纪10 年代,韦伯将儒教置于宗教界中,认为其更关注人的现世生活,“没有超世的上帝的律令与现世之间的对峙”[2],具有明显的“现世性”与“人文主义”倾向,是“一种现世伦理,缺乏超越的神圣的精神向度”[3]。20 世纪30 年代,顾立雅出版《孔子其人及其神话》,以西方“民主改革家”[4]的称号概括孔子的政治思想。在精神向度的问题上,此前海外学者普遍认同韦伯,顾立雅认为孔子将“天”视为一种非人格性的道德之神[5],即韦伯所说的“神圣的精神向度”。20 世纪70 年代,一批学者认为“天”是孔子儒学中超越的精神向度,是现世秩序与道德价值的源头,而孔子之后的儒家思想家都“没有切断人间价值的超越性的源泉——天”[6]。这种说法在后来被西方汉学研究学者普遍接受,并开展了对孔子思想中精神向度存在与否、本体为何的新讨论。
一、西方视域下的汉学研究
1972 年,芬格莱特出版《孔子:即凡而圣》,在此书中,对于孔子思想的超越向度问题,他提出了新观点:“尽管孔子确实说到了天,但它的作用不太清楚,也没有得到详尽的阐释。……对于形上学的思辩和‘神学’的可能性,孔子缺乏感受”[7],认为孔子并未将“神圣性”放在“天”上。芬格莱特试图摆脱西方世界价值导向与思想体系的影响以还原孔子,其以相对中学的客观角度阐述了孔子的人性范畴观点,力求忠诚于孔子作为东方大思想家理念的“独特性”[7]。
在芬格莱特之前,孔子是中学研究的薄弱环节,很难再找出一个顾立雅之外的孔子研究者,先秦文学难以在宋明理学主导的学术空间里占有一席之地。但是在芬格莱特之后,西方史学者对传统儒学的研究几乎都不能脱离孔子礼学框架,“礼”成了英语世界研究孔子的基本平台。
本书共五章,内容环环相扣,形成文本闭合。首章中芬格莱特指出,无所不包的神圣礼仪完成了对人类生活的整合,个体的生命在礼仪和谐中趋于“止境”,表现为“一种广阔的、自发的和神圣的礼仪:人类社群”[8]。第二章指出,儒家提供的是一条没有十字路口的大道,不走就是歧路,没有道德两难。人可能因为“智”的缺乏而犹豫或是背离道,因此感到“耻”与忏悔,“耻”指向外在社会荣誉与地位的丧失;忏悔指向过去对道德秩序的侵犯,而非西方的“罪感”[9],指向对未来的威慑。第三章中芬格莱特尝试从非心理学的角度解释仁,认为仁和礼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仁是内在和外在的统一,个体按照礼仪形式做事,能够达到自发的和谐,这是因为礼仪行为与行为者个体的“临在”融合统一。第四章与第五章则离开了对孔子所提核心概念的阐明,将关注点放到孔子思想的社会性与时代性上,讨论了孔子所面对的“习俗和价值的种种冲突”[10],关注个人在参与礼仪行为本身的“神圣性”[11],从而探讨了孔子的学说是否符合时代的要求,以反驳西方世界以自身时代视角评判其缺乏真理性的普遍观点,厘清孔子心中的“君子”:他是一个“完满圆成之人”[12]。
五章内容共同搭建起了孔子的思想框架,在这种一体性的阐述之中芬格莱特摒弃了英语世界原有汉学研究的西方视角,忠于文本地阐释孔子思想的“原本”,完成了对礼与仁的多角度论述。
二、礼:外在行为形式
孔子认为,人是生活在社群中的,具备社会性,在日常社会生活中有一个至高的、神圣的精神向度引导着集体无意识完成“礼”的概念实践。孔子的“神圣性”不同于西方神学思想的至高体,信仰彼岸也不是来世的幸福安宁,而是“现世的”“务实的”[13],“子不语怪力乱神”就是反对依靠鬼神保佑或是某种外在力量成就人类的道德与精神;这种“神奇魅力的力量”[14]不在于某种无所不能的精神实体,而在于通过对礼仪行为的忠诚信任自然无为地实现他的意志(“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就是说圣王只要遵循礼仪行为,自然能达到“天下归仁”的目的,圣王舜治天下的措施就只是“恭己正南面”而已;“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以德”就是在践行“礼”,自然能得到诸侯拥护,天下和谐;“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按照礼的要求慎重操办后事,自然能达到教化民众的作用,是礼的对外辐射)。
身在社群当中的个人永远地“与他人同行”,与他人交往的过程就是“向礼”的过程,但这不等于人云亦云,而是自有“礼”的指引,一直坚定地朝着“礼”的方向走去,而不会因为周围礼义缺失者的指指点点就丧失自身的价值判断(子曰:“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孔子按事君之礼对待君王,时人不知,反以为谄。孔子这里所要表达的是礼之应当,这个标准在孔子的心里,并不会因为他人的指责误会就轻易改变。在孔子看来这才是在保持对“礼”的忠诚,真正地在践行“礼”)。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见贤思齐焉,见不贤乃内自省也”,正是此意,通过社群生活中的“思”,个体走向理想境界,这是一种“健动”的精神。
人的道德是在社群生活的具体礼仪行为中实现的,孔子所说的“克己”,是克服自身的动物性,继而在社会生活中践行“礼”,使个体走向完满。礼是实践行为的共同模式,是“人际性”[15]的表达,是一套行为规则,是“公开的动作模式”[16],但是这个行为的核心在于心,反映出中国传统价值观 :中国人倾向于把语言放得很低,放在行动后面,行动又在心灵忠诚后面。如果只是表面学习或是按照礼仪的表面行为“要求”来做而不走心,没有精通礼义,就好比没有精通乐谱只是机械地演奏音符(《论语·八佾》中,子曰:“无不与祭,如不祭。”强调的就是“心”之“在场”,范式注《论语》:“诚为实,礼为虚也。”)。行为本身不是礼仪,只有当行为者内心具备了尊重和信任,符合礼仪要求的行为才能真正成为礼仪行为,否则将“空有形式,缺乏生命”,并且“毫无意义”[17]。礼仪的践行者在具体情境中做出调整,言行举止有机完整,个人礼的行为朝外散发出仁的力量,最终影响其他社群成员,个体间相互配合,共同演奏礼乐,达到一种“自发的协调性”[15],从而影响更多个体,使本不在礼仪行列中的人跟从,遵循原有礼仪姿态,最终达成社群的整体和谐。
三、“仁”的内核讨论
史华慈支持芬格莱特将孔子思想从心理学领域摘出去[18],但他也指出“孔子主要关注的是那些品质、身份以及内在的心理倾向”[19],这一点恰好与芬格莱特所认为的孔子强调个人因社会性行为的完全社会存在性相反。芬格莱特认为“仁”的反面是“忧”[20],指向客观外界“某种不安、忧虑境地并对之回应的状况”,仁者在客观中塑造自我,从“忧”的状况中解脱出来。史华慈认为仁自身“包括了所有外向德性和灵魂的气质倾向”,是“对人们直接控制的世上事务的幸运或不幸态度漠然”[21]。“仁者不忧”并不是外在的秩序井然,而是仁能够使人内心有一种处之泰然的力量,使其在各种逆境之中保持平和的心态,支撑儒者“不知老之将至云尔”[22]。同时,史华慈受到雅斯贝尔斯“轴心期”的影响,要求看到“孔子思想作为‘通见’所向我们敞开的种种可能性(既包括了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又包括了中西文化的‘共通性’)”[23],尝试将孔子思想拉入西方认识论框架。
杜维明表示,“仁对于礼的第一性和礼对于仁的不可分性正是……我的论点”,仁是“一个内在力量和自我认识的问题”[24],这与史华慈的理解不同。田立克认为史华慈实际上受到了基督教的影响,他的观点“是一种没有提到罪性的道德二元论”[25]。葛瑞汉试图将孔子抽离出二分法框架,认为孔子以中国方式回避了西方人惯有的事实与价值的二分对立,“行为的价值”本身就来源于“智慧的价值”[26],在思考之前,个体行为本身已经被牵引到上文所说的“大道”。仁不是一个程度问题,而更像是“无须努力便可正当行事的方向”,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几乎无人能够把握的动态平衡”[27]。
芬格莱特同时强调孔子学说的外向化、社会性维度与“排除内在的心理所指”[28],认为仁是内心的状态,外化到行为中以“礼”的形式辐射到社群,史华慈等人的批驳实际上是基于西方框架对芬格莱特的误读。郝大维与安乐哲纠正了这一点:“西方文化的两大基本预设与中国的孔子思想格格不入:西方常常喜欢讨论‘超越’,但孔子则有一种强烈的内在论的先决设定,即不存在任何超越的存在或原则。”[18]学习、礼仪行为本身既是对外界的接受又是能动的改造,既面向外在秩序又面向于主体内心,它超越了西方二分法的对立关系,这是典型中国对立统一“大同”式的精神内核。冯友兰的立场类似,认为仁是“一切德性的总和”[29]。
在对至高主体“圣人”的评定上,孔子表现出了极端的谨慎。圣人是因然不是使然,无可无不可,神圣礼仪已经深深根植于他的内心并外化到行为,与他融为一体,所以“从心所欲,不逾矩”。坚定的“仁者”绝对稀有,即使是孔子自己,也从未说过自己已达于仁,因为儒学所向的终点不是一个实际的境地,而是一种理想状态,“所止”“所安”并没有实际的衡量标准,所以大道永无止境。宋明儒学强调“知其不可而为之”,即使一辈子学习都无法得其精髓,也优越于放大某种才能并凭其立足于世。
尽管孔子思想是现世的、务实的,他的“神圣的东西并非源于外在的精神领域”[23],呈现出了独特的理性主义倾向,但中国人并不是纯理性主义的,孔子也表现出了天真的理想主义:圣人因然的境界本身就是空想,孔子的理想世界必须在所有社会群体都忠诚的情况下才能实现,但是在复杂的客观现实因素之前,这种要求违背人性,从根本上是不可能的。
芬格莱特之后,儒家思想以一种非宗教性的、独立于西方话语体系的形式进入英语世界的学术讨论中。英美学者一边借孔子思想反思西方价值体系的陷阱,一边用西方视角赋予传统儒学新的内涵与价值,这些讨论共同丰富了英美世界研究孔子的视角。在海外孔子研究已经硕果累累的情况下,国内学者如何以新姿态继续研究传统儒学,就成为亟待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