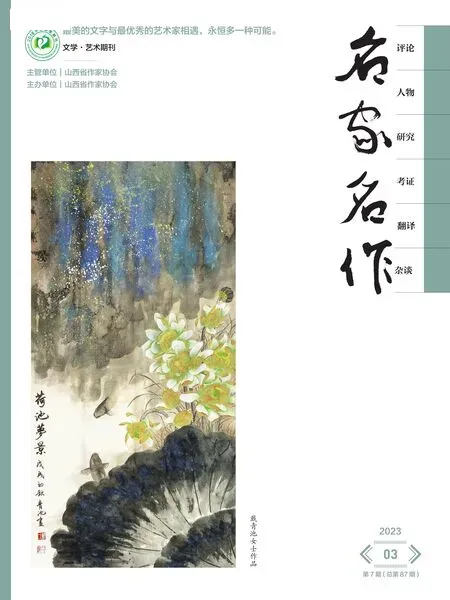《美丽新世界》:并不美丽的新世界
刘鹏超 田孟儿
英国作家奥尔德斯·赫胥黎一生创作了50 多部著作,但真正让他为世人所熟悉的是他在1931 年创作的小说《美丽新世界》。赫胥黎借用《暴风雨》中米兰达的赞美之词“人类多么美丽!啊,新奇的世界,有这么出色的人物”[1]作为小说的名字来讽刺小说中所展现的未来世界,其讽刺意味犹显深刻。
作为现代文明发源地的欧洲,自工业革命兴起之日起就有学者表达了对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现代性焦虑,即使在社会转型完成之后,仍有大量学者投身于对工业文明的反思之中。赫胥黎也继承了这一传统,在《美丽新世界》中浸透了其对现代社会的极具前瞻性的思考。
一、工业制度:破碎的人与完整的人
《美丽新世界》中社会所采用的福特纪元以亨利·福特命名,而福特元年是以福特生产线诞生为标志。福特生产线使得传统的全能技工被处于传送带特定位置的特定技工代替,它的运作模式被无数产业采用,成为工业生产制度的代名词,在提高工业生产力的同时,问题也随之而来。
福特生产线技术所带来的分工使原本完整的人变成破碎的人,“不是劳动得到了分化,而是人本身被分化了——被分化为片片断断,人变得支离破碎,生命成为碎屑”[2]。在工业分工制度下,你无法成为一名有生命感的人,而被迫沦为机器的工具,成为机械的人。
《美丽新世界》中的生产制度完美继承并超越了现实中的福特流水线技术,福特流水线技术针对的仅是机器的生产,而在赫胥黎笔下,这一技术被运用到人的创造中。在福特流水线机制下诞生的大部分人的生理机能(阿尔法人除外)都是破碎的,存在天生的功能不完善的症状。而在培育婴儿成长的过程中,经过特殊的教育,如书本与噪声、鲜花与电击相联系的教育,大部分人的心灵也是破碎的,人与自然的天生亲密关系惨遭割裂,因为热爱自然会使工厂开工不足。对于书本的厌恶使得人们放弃了思考的可能,下层阶级的人被完全固化在他们的岗位上,如机器一般进行重复劳作。这样自然的、完满的人成为机械的、碎片化的人,意外进入印第安聚集区的琳达便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琳达原本是在新世界受精室中工作的次等贝塔,在与男友来印第安聚集区旅游时出现意外,在被印第安人救下后留在印第安聚集区生活。但她并不能适应在印第安聚集区的生活,“我在受精室里工作,从来没有人教过我这些事情。这不是我应该做的事情”[3]118。在琳达的潜意识里,补衣服不是她应该要学会做的事情。当她尝试主动走出第一步,去帮助印第安妇女织毛毯时,又因为不会织布而被排斥。琳达这一经历反映出工业制度下的人返归自然的希望的渺茫性。
针对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所带来的问题,柯尔律治、卡莱尔、阿诺德均提出组建一个具有完满人性的特殊阶层,这个阶层“为社会定下最高价值目标,并将这些目标传递给社会大众”[2]139,来提高群众文化教养,以对抗工业制度带来的人的异化,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赫胥黎笔下的主宰者群体和柯尔律治的“知识阶层”、卡莱尔的“精神贵族”、阿诺德的“残余分子”异曲同工,不同的是,上述后三者属正面阶层,被赋予更多积极想象,而赫胥黎的主宰者群体虽然实现了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但却是通过施加负面影响来实现。主宰者是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完满的人,但他们并没有将精力用于提高大众的认知,而是为了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忽视个体的发展,将大众洗脑为思想统一的人。究其根本,还是因为工业制度的确立使得机械论“根植于人们信念的最深处,由此在整个生活和活动中生发出无数噬人的枝杈、浸毒的果实”[2]245。这体现了赫胥黎对三位前辈关于特殊阶层构想的否定。
唯一完整的“人”是成长于印第安聚集区的约翰,但他作为一个受印第安聚集区生殖崇拜与苦行宗教氛围影响的人不太可能会做出理性的价值评判,他更多的是作为赫胥黎的代言人。这个原始人进入新世界后便使得工厂主任下岗,当读者以为他要做一番消解新世界秩序的伟大事业时,赫胥黎笔锋一转,写了他在新世界的各种碰壁,外部的环境不允许他做一个革命者,在处处碰壁之后迎接他的只有死亡。
赫胥黎借此书发出预言:在工业制度下,人性的破碎将成为常态,即使存在少数较为完整的人也不足以汇聚为掀起革命的力量,技术、机械将成为未来的统治力量。
二、科学技术:神话的消解与再造
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最大改变表现在人们的物质生活模式上,而启蒙运动则在更早之前培养了人们对科学“迷恋”的思想态度。启蒙运动究其根源起始于17 世纪的科学革命,而且相比于思想革命,科学革命也是对世人直接影响最大的。正因为如此,启蒙运动使得人们对于科学的痴迷远胜于伏尔泰等人领导的思想启蒙。对于18 世纪的欧洲人来说,他们的启蒙导师是牛顿、笛卡尔、帕斯卡、洛克、蒙田等人[4],这也就为后来的“科学神话”埋下了祸根。随着人文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分裂,启蒙理性逐渐与工具理性画上等号,科学技术成为启蒙的代名词。
神话产生于对自然的恐惧,由于对自然的恐惧,先民们根据有限的认知将自然万物拟人化为自己的同类,并以对待自身的最高规格的仪式去尊崇神。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发现自然万物都可利用自身掌握的自然科学知识加以把握,他们之前所崇敬的神并不存在,自拥有自主意识之日起就压在他们身上的来自神的压力消失了,人类借助科学技术的进步夺回了命运的掌握权,自然的神秘面纱被科学撕得支离破碎。对自然的恐惧转变为对科学技术的信赖与依靠,人们运用自己掌握的自然科学知识去再造自然,靠神答疑解惑、寻求力量的时代过去了,科学代替神话为人类答疑解惑,给予人力量,科学“比神话更加无法抗拒,更具有绝对权威性”[5]408。
所以我们看到,在赫胥黎笔下厄洛斯与阿佛洛狄忒消失了,新世界里的人们关于男女爱情的概念也消失了;上帝关于夏娃受制于其丈夫的训诫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随意交合的男女关系;对于天堂、地狱的崇敬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死者作为产生磷元素的原料被扔到熔炉之中。更荒唐的是,当人类由神灵创造的谎言被攻破之后,取而代之的不是人类自由结合来诞生后代,而是靠科学技术创造理想的人类。
中世纪时,拥有虔诚信仰的人会寻求神的帮助解决自己的烦恼,而在新世界,人们会使用新型药品苏摩忘却烦恼。苏摩“拥有基督教和酒精的所有好处,却没有它们的任何缺点”[3]61,使用它可以随时摆脱现实,远离苦恼。过去人们想要依靠神灵获得的一切馈赠如今都可通过科学技术实现。
既接受了印第安聚集区文化熏陶,又在母亲影响下对新世界文明心生向往的约翰,处在两种文明的撕裂之间,被赫胥黎塑造成一位“武士”(brave 含有“印第安武士”的意思),是神话信仰的代表。面对科学技术创造的世界,他也曾发出赞叹:“啊,美丽的新世界,有这么出色的人物!那我们赶快出发吧。”[3]135但在真正接触新世界后,他所面临的是来自科学神话的冲击。带他来到新世界的琳达在进入新世界后便一头扎进苏摩的怀抱中,沉醉于虚拟世界直至死亡;他喜欢的莱妮娜像极了“人尽可夫的娼妇”[3]185。他本可以隐居活下去,但当自己信仰的鞭笞苦刑成为众人高姿态观看的对象时,当他在人群里还能发现莱妮娜作为看客在另一个男人身旁时,自杀对他来说才是最好的解脱。
三、大众文化与消费:扼杀希望的温柔乡
赫胥黎在给奥威尔的信中写道:“我个人认为统治寡头一定会想办法寻找更加简单易行的统治手段来满足他们对权力的欲望,这些手段与我在《美丽新世界》中描述的那些东西非常相似。”[6]“换言之,我觉得《一九八四》中的噩梦最终会变成和我在《美丽新世界》里预言的世界更为相近的噩梦。这种变化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统治者感到他们需要更为有效的方法。”[6]赫胥黎认为,统治者与其使用高压政策统治人民,不如制造一个奶头乐的世界来驯服他们。在新世界里,即使存在思想觉醒的异类,如伯纳德、赫姆霍兹之流,他们虽然不满,但都没有推翻新世界秩序的想法。究其根源,除了在成长过程中给予洗脑教育外,新世界统治者更是借助大众文化,或者说文化工业与消费给人民编织了一张如蜂蜜般甜蜜又黏人的大网。
《美丽新世界》中所表现出的大众文化,更贴切地说是一种文化工业。阿多诺认为,文化工业为大众消费制作的产品(娱乐性报刊、电影等)“是在标准化、格式化、通用化的运作过程中弥平了个性的,而经济、技术、行政的力量则是其背后的推手”[7]。新世界的人们喜欢的感官电影,即一种通过将香薰机器、音乐、体感体验机器、画面结合在一起的新的电影形式,可以让观众获得与电影中人物同样的体验。统治者利用这一新的电影体验形式让人们沉浸于低俗下流的电影,沉浸于轻易就可获得的感官快感,使其深陷其中无法自拔。阿多诺认为这样的娱乐“带来的快乐是一种逃避,但是这种逃避不是逃避残酷的现实社会,而是逃避大众心中最后的反抗观念”[8]。无疑,新世界的主宰们做到了。
育儿所里的儿童自小被教育“旧衣服丑死了”“补丁越多越是穷光蛋”[3]56,消费观念打小被植入内心。赫胥黎在书中提及人物的衣着时,也总是在刻意标明衣服的材料,如醋酸丝纤维、粘胶纤维、仿摩洛哥皮革等人造制品,这一刻意仿佛是在以第三者的眼光对文本中人物进行打量,且对衣着重点打量,并在无形之中给予读者一种暗示——衣着材料不仅是材料,更是一种身份符号。当琳达在多年后第一次见到新世界来的人时激动地表示:“还有文明人的衣服。我还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一件真正的醋酸丝绸缎衣服了。”[3]116在她的意识里,文明人的标志之一就是穿着人工材料的衣服,这样文明就与人工制成的面料画上了等号。以赛亚·伯林评价赫胥黎是真正的预言家,的确,当我们将目光投向我们的现实世界,会发现生活中有不少消费品已被打上符号的标签,钻石与爱情对等,品牌服装与某种阶层、某种生活态度相联结,人们早已习惯于通过商品之间的价格差别来区分自己与他人的社会地位和等级。鲍德里亚认为20 世纪60 年代以来的西方社会进入了消费社会,但赫胥黎通过《美丽新世界》早在30 年前就预言了消费社会的到来。
总的来说,奥尔德斯·赫胥黎不仅是一位出色的作家,更是一位关心人类命运的人道主义者与思考者,这不仅表现在他在哲学思辨的高度进行《美丽新世界》的创作,预见性地指出人类社会未来可能出现的危机,更体现在其并没有被《美丽新世界》获得的成功冲昏头脑,而是继续为人类未来思索。赫胥黎在1958 年的论著《重返美丽新世界》中,比较了现代社会与他在《美丽新世界》中所构想的寓言式图景的方方面面,认为他早年的悲观预言正在成为现实。我们不能因为赫胥黎没有明确指出解决问题的方法而对他的积极思考给予否定,相反,我们应将赫胥黎视为对人类社会发展发出预警的敲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