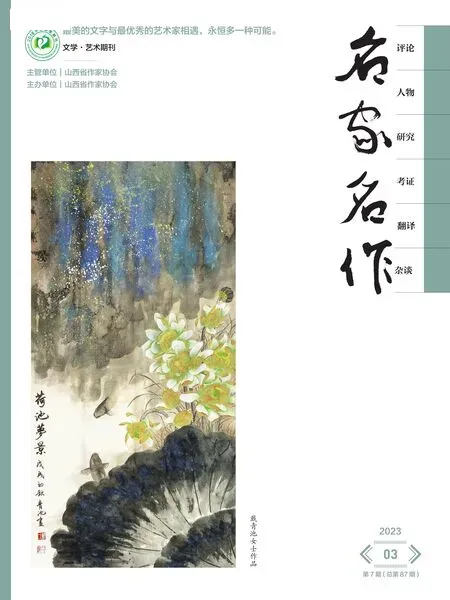《花束般的恋爱》:爱情电影中的叙事策略与细节表达
岳书婷
《花束般的恋爱》于2021 年初在日本公映,由执导经验丰富的土井裕泰、编剧经验丰富的坂元裕二联手创作。上映期间,其曾一度拿下了日本2021 年上半年真人电影票房第二名,在我国豆瓣网电影平台的评分更是高达8.6 分,是豆瓣网2021 年度评分最高的爱情电影,可谓是近年来成绩最亮眼的爱情电影之一。
一、开始,是结束的开始:镜像世界拉近心理距离
《花束般的恋爱》讲述的是一对男女从相识相爱到热恋、到爱情逐渐归于平淡、再到成为陌路人的故事,正如影片名称所提示的,这是一个有“花期”的爱情故事。花束从剪下的瞬间就开始枯萎,因为它没有根、远离土壤,所以无论其曾经多么光鲜亮丽,最终都终将归于凋零、化为尘埃。影片正是通过这个概念揭示了爱情具有时效性的问题。
朱光潜在其对“心理距离说”的阐述中提到,审美体验作为一种精神活动,必然会因创作者和接受者个人的因素而产生不同的体验。作品创作越是与接受者接近,越是能引起其相应的共鸣,从而产生美感。[1]影片的叙事结构并不复杂,一定程度上属于传统的线性叙事,影片在开场前插入了男女主人公分手后的情节作为“楔子”,营造悬念感。而这个“楔子”在影片结尾又有接续的体现,形成了一种首尾呼应。《花束般的恋爱》叙事的高明之处在于,它的主线叙事虽然采用了平铺直叙的方式,但这种平淡的方式本身就很贴近观众的日常生活。其建构了一个影像化的镜像世界,更加拉近了观众与影片的心理距离。可以说,影片的叙事方式在多个层面都闪烁着现实主义的光辉,对现实世界的镜像反映渗透着一层现实底色。
(一)有始有终——叙事结构上的首尾呼应
《花束般的恋爱》是一部首尾呼应、运用线性叙事的影片。其中,首尾呼应不仅仅体现在前文提到的影片开场前的“楔子”与影片结尾两人背对挥手作别的情节,更体现在许多小的细节之中。这些小细节不仅推动了影片的叙事,更是将情感氛围推向了高潮。
其中,影片男女主人公在恋爱前与分手前心里的想法十分相似——“末班车来之前就表白”“婚宴结束后就分手”。而两人在分手前去的 KTV 正是两人恋爱前去过的 KTV,分手前去的餐厅正是他们互相表白时所在的餐厅,甚至两人在餐厅里遇到了“年轻版的自己”。从红绿灯下的第一次接吻到分手告别时红绿灯下的拥抱,从给同居的爱巢装上窗帘到分手后将其取下,这部影片没有一处不在告知观众:天下无不散的筵席。这些情节和细节更加增添了影片的现实色彩。
(二)镜像建构——叙事细节拉近心理距离
一般而言,从镜像理论出发,对电影进行深度解读与分析主要有以下两大维度:其一是影像世界中的情境与现实世界之间的相似、相通之处;其二是影片中的人物主体在主我与客我之间的交流与碰撞,最终形成带有社会性质与个体特殊性质的主体。[2]
影片通过设计一些小的细节和情节,通过将现实界(Real)、想象界(Immaginary) 、象征界(Symbolic)三层界域有机统一[3],成功建构起一个镜像世界,即一个现实世界的缩影。可以说,《花束般的恋爱》并不是仅聚焦于主人公的感情故事本身,而是在讲好故事的基础上穿插描绘了现实的日本社会,丰富立体地表现了当代日本年轻人的社会困境:固化的阶级、严苛的上下级观念、压得人喘不过气的高压工作制度等。
现实界中,男女主的生活条件并不优渥。二人所生活的日本第一大城市东京无疑是日本年轻人生活压力最大的地方。二人在工作上的不顺心,无疑是影片对受日本沉重压抑的社会氛围压迫的日本年轻人的困境进行的精确、立体的镜像化描绘。
想象界中,二人受到了来自他者的固化认知的压制。二人的父母对其职业选择、个人意志都表达了不支持、不鼓励的态度:八谷娟的父母是东京本地的广告商,虽然不愁吃喝,但处世圆滑,是影片中标准的成年人形象;山音麦的父亲则是一家烟花厂的老板,希望山音麦不要再漂泊在东京,应该回家继承家业。而山音麦在公司里被代表社会的固化认知的上司所规训。
象征界中,二人在恋爱的五年成长过程中,都有着其作为主体本身的感知,感受着外界对其自身的凝视。比如,影片后期山音麦在公司加班时,借由一段指代别人的谈话,感知到了同事的凝视,产生了愤怒的情绪。八谷娟在辞去工作入职密室逃脱的工作室时,也感知到了山音麦的凝视,而山音麦同样感知到了八谷娟的反馈凝视,二人的对话段落看似平静,实则波涛汹涌。
影片中对社会及主体镜像的建构塑造了一个现实社会的缩影,透过这些状似现实的艺术真实创作,使观众感受到了日常生活的缩影,产生了共鸣,从而达到了拉近其心理距离的效果。
(三)审美主体——叙事细节烘托情感
贯穿《花束般的恋爱》这部影片的是数不尽的细节。其中八谷娟作为一个文艺青年,喜欢的事物都比较小众。影片中提到,在男女主热恋时,八谷娟喜欢的一位情感博主“恋爱生存率”自杀,海边的这场戏居于影片整体时长的三分之一处,从这一场戏之后,剧情开始从男女主人公恋爱的甜蜜转向两人感情归于平淡。这个情节不仅暗示了后续的剧情发展,更体现了八谷娟作为审美主体的情感依托的消逝。而八谷娟作为影片外的审美客体,其遭遇与经历更是引发了有相似经历观众的深深共鸣。
影片中,“恋爱生存率”博客中的每一篇文章都使用了《开始,是结束的开始》作为标题,而后八谷娟对“恋爱生存率”博客进行了如下描述:“‘相遇总是伴随着离别……我们的派对,现在正在高潮部分。”
由此得知,女主人公对自身恋爱的生存率虽然持肯定态度,但字里行间充斥着对这段感情的不信任,为后续二人感情归于平淡、相忘于俗世间埋下了伏笔。作品的审美主体形象框架需要承载审美主体的情感依托,需要建立起第三视角下的情感联系。八谷娟作为“恋爱生存率”的一个关注者,这无疑是她作为审美主体的情感寄托;而影片外的观众作为影片的接受者,其作为审美主体,无疑会将八谷娟的情感遭遇作为自己的情感寄托。与此同时,“恋爱生存率”博主自杀只是一个很小的情节,但这个情节之中的细节,如山音麦去买沙丁鱼盖饭途中突然消失,八谷娟说“你不要突然消失”,不仅是暗示,更推动了剧情向后发展,助力了八谷娟的情感态度转变。
二、成长与反成长叙事:反衬式人物塑造
在塑造女主人公八谷娟与男主人公山音麦时,创作者使用了成长叙事与反成长叙事相结合的手段,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反衬的作用。
(一)独白塑造人物形象
《花束般的恋爱》中大量使用了男女主人公的画外音内心独白,这种独白不仅起到了交代情节的作用,更为人物塑造做出了贡献。影片开头男女主人公各自进行了大段的内心独白,从而简明扼要地让观众了解了男女主人公的人物设定,从而对两人有了如同朋友一般的了解,开启了“上帝视角”,拉近了观众与两位主人公之间的心理距离,从而更加期待男女主人公两人的相遇,期待两人碰撞出火花。
(二)成长与反成长叙事
在这部影片之中,创作者运用一定的反衬手法,同时使用了成长叙事与反成长叙事。成长叙事的基本范式可以简要概括为:由“少年”过渡为“成人”阶段的年轻人,反复遭遇种种挫折,继而努力习得了种种规则、博弈与妥协的策略,最终融入社会,成为游刃有余的成年人。[4]而反成长叙事,顾名思义,是与成长叙事相反的叙事手段。
影片中,山音麦的人物形象变化无疑是常规的成长叙事,即从开始到结尾,他一直在按照线性的时间“成长”,其人物形象被按照传统的成长叙事情节塑造着。从影片开始的青涩大学生形象到影片后期成长为社会中摸爬滚打的成年人,其内心在潜移默化之中被社会所同化,深刻体现了八谷娟母亲所说的“进社会就像泡澡”。影片开始时他为成为职业插画家而努力,而后遭遇挫折后选择找工作,认为自己可以在工作之余画插画。但他在忙碌的工作中被磨平了棱角——他成为满口工作的成年人,说出了八谷娟父亲曾经说过的话:“生活就是责任。 ”八谷娟的父母作为影片中少数出现的成年人,代表的其实就是这个社会的规则,其每一句台词都在之后有所体现。
而八谷娟的人物形象则恰恰相反,虽然她也在生活的重压之下进入了社会,但她为自己的内心留存了一片净土,是一种成长中的反成长叙事模式——八谷娟的成长体现在内心,她变得更坚强,更有勇气和能力去守护自己热爱的事物,并没有被社会所同化。她考了会计资格证,工作一段时间后毅然决然地辞去工作,找了一个被认为是不务正业的工作,她变得更坚韧,做到了在成长的过程中“反成长”。
八谷娟与山音麦随着时间变化的对比更加反衬出山音麦的“成长”。譬如,八谷娟一直没有放弃在工作之余给自己喘息的空间,保留了每天在闲暇时间看书、玩游戏的习惯,而山音麦则每天都坐在书桌前加班工作,追过的漫画最后甚至忘记了情节。在八谷娟辞去工作时,山音麦称其不务正业,本质上是在玩乐。影片重复出现的一段对话情节非常有趣:在八谷娟找工作失败时,山音麦问面试官是谁,八谷娟说是一个很厉害的人。山音麦说:“他如果看了今村夏子的《野餐》,肯定毫无感觉 。”而在影片后期,当山音麦遭遇挫折时,八谷娟用同样的话安慰他,他却回应道:“我可能也没感觉了。”
三、球鞋、耳机与面包店:细节表达悲剧意象
在《花束般的恋爱》中,细节的设计不仅助力了前文所述的叙事结构建构、人物塑造,更为情感的传达和气氛的营造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正如鲁迅先生所言:“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影片中许多细节的表现,更多体现的是一种美好,对于接受者而言,可以说是一种审美主体的情感寄托。而这些细节却被通过反衬的手段毁灭给人看,更加烘托了影片作为一部爱情电影若有似无的悲剧气氛。
在影片的开场,男女主人公作为独特的个体,拥有许多相似的爱好,这些爱好在一般人看来可谓小众,但从他们的言谈透露的细节之中,二人惊奇地发现了彼此的契合:他们都因为一些无聊的琐事错过了天竺鼠展览,笑称天竺鼠展览的门票是“两人相遇的门票”;两人都喜欢用电影票根做书签;两人穿着相同的白色球鞋;两人的耳机线都会打结;两人喜欢的作家高度重合,如石井慎二、今村夏子等。
然而,这些美好的细节在影片后期却逐个被消解:山音麦不再愿意跟八谷娟去看展览和话剧,觉得这并非“正事”,放弃了自己曾经的兴趣爱好;两人从穿着相同的白色球鞋到变成了不同的黑色皮鞋;八谷娟发现山音麦在看有趣的电影时会流露出无聊的神情;而电影票根做书签本身就象征了他们之间的爱情终将如电影票根上的字一样消亡;两人逛书店时,山音麦不再看小说,而是看起了“成功学”书籍《人生的胜算》……
而耳机作为贯穿影片的细节元素,在这一点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首先是两人的耳机线都经常打结;而后是在两人确定关系的夜晚,为烘托气氛,两人共戴一副耳机听一首情歌,结果被一位职业录音师教育耳机分有左右声道;两人恋爱后不约而同地送了对方无线耳机,而使用无线耳机之后,两人的感情逐渐归于平淡,甚至各自听各自的音乐,谁都不理谁;影片最后两人决定分手时,坐在曾约会的餐厅里,看到一对酷似曾经自己的男女共戴一副耳机。在影片中,耳机不再仅仅是一个细节元素,而是一种意象,所指代的正是男女主之间的情感距离,从尝试靠近,到共通,到疏远,最后成为陌路人。
面包店则体现了两人破裂最终的“和解”。两人刚同居时发现楼下的面包非常好吃;而山音麦“成长”之后,对于面包店关门的态度却变成了“车站前买面包”;时间来到两人分手很久之后,某天山音麦突然发现在街景地图上和八谷娟一起买面包回家的场景。尽管在恋爱后期两人的感情从分裂走向平淡,最后相逢不相识,但在山音麦“人生第二次奇迹”发生的时刻,两人的关系在无形中走向了和解。
从白色球鞋到耳机,再到面包店,这些贯穿全片的细节无一不昭示着两人感情的变化过程,体现了再美好的爱情也会有花期,从感情开始的一瞬间就开始了枯萎,这无疑是对美好事物的解构,是一种悲剧的体现。
四、结语
爱情电影一直以来都是商业电影所青睐的类型之一,而《花束般的恋爱》不仅在商业上取得了成功,更在艺术性和商业性上做到了很好的结合,从其极具现实底色的叙事方式、成长叙事和反成长叙事的有机结合、反衬手法的有效运用和贯穿始终的细节与意象呈现可以看出创作者之匠心独具。与之相比,我国的爱情电影更多喜欢通过情节中激烈的戏剧冲突来体现轰轰烈烈的爱情,这两种模式并无优劣之分,但这种较为平淡、贴近现实的叙事模式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为我国影视工作者提供新角度、新方法,在两种方式之间取得一种微妙的平衡,从而给国内对固定模式已审美疲劳的观众带来全新体验。不过,这种方式仍需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进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