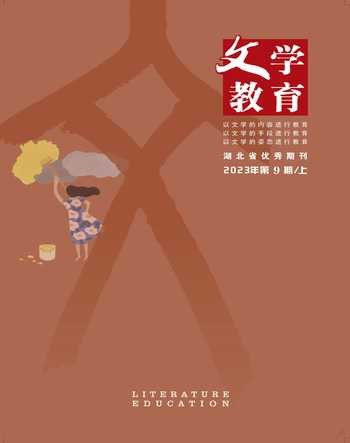虚与实的并置融合:《山上的小屋》的空间叙事
王美银
内容摘要:《山上的小屋》是一部颇具实验性的作品,其凭借丰富多元的空间类型、复杂多变的空间组合方式,形成了独特而新奇的空间叙事模式,同时展现出残雪对于当时人的绝望的生活状态和冷漠人性的深刻思考。本文从空间叙事理论出发,聚焦文本中地志空间、梦境空间、空间的并置交融三个层面,通过对作品中各个空间所呈现出的丰富变化和微妙关系进行分析,为读者展示一个虚实交互的病态而荒诞的世界。
关键词:《山上的小屋》 空间叙事 梦境空间 地志空间 空间并置
龙迪勇曾指出:“叙事学研究既存在一个时间维度,也存在一个空间维度”。张世君也认为:“空间叙事在叙事文本中广泛存在,但东西方学者未对其给予高程度的重视,并且未对它进行深入而全面的探索和研究。而今的叙事学理论多关注文本中的时间因素,强调时间流中的叙事结构构建,忽视文本中空间因素对叙事的影响”。诚然,在过去的很长时间中,叙事学的重点都在“时间”,而非“空間”之上。但20世纪后期,这种“厚此薄彼”的研究倾向出现极大的转变,在“空间转向”理论热潮的影响之下,叙事中的空间元素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叙事空间理论也因此发展勃兴了起来。诸如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加布里尔的《走向叙事空间理论》和福柯的《论他者空间》,这些批评家的论著使叙事空间理论更为成熟,同时也推动了叙事空间理论与当代文本的结合。
空间叙事理论,由美国比较文学教授约瑟夫·弗兰克在《现代文学中的空间形式》中首先提出,其基本论点为:现代文学在形态上是“空间性的”,即现代小说具有打破时间与因果顺序的空间特征。他的论著对后来诸多批评家的叙事空间理论产生了影响,如安·达吉斯坦利和约翰逊提出了开放与封闭空间的概念;罗侬区分了“框架的空间”和“架构的空间”;查特曼区分了“故事空间”与“话语空间”等。这些理论的提出与发展为文学文本的解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点。
如果说弗兰克是空间叙事理论的开创者,那加布里尔·佐伦《走向叙事空间理论》则进一步深化和完善了叙事文本中对空间结构的讨论。他指出了叙事文本中三个层次的空间结构:即作为静态实体的地形层空间结构,作为符号文本的文本空间结构和作为事件或行动的基础的时空空间结构。加布里尔进一步扩充了空间叙事理论的意义涵指,使空间叙事理论与文本的结合更紧密。
残雪的《山上的小屋》是一部颇具实验性的作品,与传统小说叙事不同,《山上的小屋》故事主线简单,主要描写了发生在一个家庭中的怪诞事情。在小说中残雪打破传统小说惯常的线性表达方式而创造性地采用了类似梦境般无逻辑、碎片化的表达,使得“我”在两个主要空间—小屋和家中不断穿梭进出,其他人物和事件也在两个空间中出现不同程度的交叉和融合。与此同时,文本中反复出现的一些意象起到了构建、融合叙事空间的效果,使文本呈现出独特的空间叙事特色。本文将以弗兰克、加布里尔和列斐伏尔的空间叙事理论为依托,从梦境空间、地志空间以及二者的并置融合三个方面来解析残雪小说虚与实交互并置的空间叙事特色。
一.实:地志空间
地志空间是一种基本的空间,是故事发展所必须的场所。加布里尔在《走向叙事空间理论》一书中阐述了何为地志空间,他认为地志空间是文本中既独立存在又依托于其他叙事学因素的空间层,其是叙事结构中最为基础又最为高层次的存在,其参与叙事时间结构的构建和文本顺序的安排。小说往往通过最为直接的方式来书写和建立地志空间。叙事文本中的诸多其他因素,如叙述视角、叙述声音、色彩都会对地志空间的形成产生影响”。
也就是说,地志空间是小说空间建构的支点,是故事发展不可脱离的空间基础,其设置往往与主题阐发息息相关。在《山上的小屋》中,残雪以“家”和“山上的小屋”作为人物存在和故事发生的主要地志空间,她将地志空间进行异化、并置和融合,以此来表现两个地志空间的差距,凸显二者不同的象征意义。
(一)地志空间的异化
《山上的小屋》中,无论是“我”和父亲、母亲、妹妹一同生活的家,还是只有“我”一人可见的“山上的小屋”都是与常见空间不同被刻意异化过的空间。首先,在“家”这一空间中,处处透露着不同寻常的怪诞气息:“我”将死蛾子、死蜻蜓视作喜爱之物放在抽屉里珍藏;母亲会因为我开关抽屉的声音而发狂;父亲执着地想打捞那把掉下去的剪刀;凡是在“家”里的人睡着了脚心都出冷汗,种种奇异的行为使文本中的“家”区别于传统的家,呈现出独特而怪异的空间特征。其次,在“家”空间中,传统的以“和谐美好,人人相亲”为特点的亲情被异化,家中鲜少有温暖感人的亲情,反而充斥着各种冷漠畸形的家庭关系:母亲“一直在打主意要弄断我的胳膊”,妹妹用“直勾勾的目光刺得我脖子上长出红色的小疹子来”,而父亲则像狼一样异常冷漠。在“家”这一空间中充满了虐待欲、窥探欲和极端的冷漠,传统“家”空间中的那些温馨、和睦的明亮元素被刻意隐去,突出呈现的反而是迫害以及恐怖,一个丑陋、异化的“家”空间跃然纸上。
在小说中除了充满虐待畸形家庭关系的“我家”以外,残雪在小说中也构建了“一个人的家”——山上的小屋,它是故事中另一个被异化的空间。小屋的异化首先体现在其所处的自然环境上,小屋所处的荒山是一个诡异莫测的地方,山上的自然环境都是由一点一点碎片化的意象组合构成:“许多大老鼠在风中狂奔”,“到处都是白色在晃动”,“每一块石子都闪动着白色的小火苗”,它们的呈现方式表现出一种变形性和怪异性。其次,小屋的异化还体现在对疯狂的“屋内人”的塑造上。小屋中有一个“暴怒地撞着木板门,声音一直持续到天亮”的毫无身份特征的人,他的这种持续性的撞门行为是没有指向性的,是疯狂的,魔怔的,他的存在也让山上的小屋与传统的小屋不同,表现出一种非理性的空间异化特征。
通过对家和小屋两个地志空间的异化,小说呈现出了不同寻常的意趣,使文本的怪诞风格更为突出,人物性格特征更鲜明,同时也使作品中的世界与现实世界产生疏离,因此产生了文本的空间化审美效果。
(二)地志空间的并置、融合
空间并置是弗兰克在《现代小说的空间形式》中提出的一个概念,它是相对于传统叙事文本中的时间书写而言的,其强调打破叙述中常见的线性时间流,并列地释放那些或大或小的意义单位,使文本的统一性存在于空间关系中。空间并置在文本空间设置上表现为空间的并列,即二者的相互独立。在小说中,“家”和“小屋”虽然都是被异化的空间,但二者不存在主次之分,相反二者是相对独立的,即“家”中的怪异与冷漠,客观而言是不会对“小屋”产生影响的,而小屋中那个疯狂的“屋内人”也未曾对家中的父亲、母亲与妹妹造成伤害。同时,两个地志空间独立承担着各自的象征意义:“家”象征着十年浩劫中人们被迫互相撕咬的冷漠社会;“小屋”则象征的是一种对肮脏卑琐现实的超越和净化,是对“家”的逃离。从上述两方面而言,“小屋”和“家”是并置的两个地志空间。
弗兰克的空间并置理论在强调“并列”的同时,也指出文本的统一性即空间的融合,《山上的小屋》中两个地志空间通过“我”这个空间中介体进行了巧妙的融合,从而使文本的主题呈现出整体性。是“我”坐在家中的围椅里,听见北风在凶猛地抽打小屋;也是“我”吃饭的时候对家人诉说山上的小屋;更是“我”最后发现“没有小屋”,我试图将小屋带入家空间,也试图挣脱家的束缚,去探索小屋的真实样子,正是因为“我”的一系列行为使得读者在“家”空间和“小屋”的空间之间闪回、穿梭,因为感觉的延缓两个空间因此发生局部重叠和融合,两个空间的绝对独立性被消减,从而使文本表现出空间的统一性和主题的整体性。
二.虚:梦境空间
梦是人类一生中极为常见的精神现象,其往往与被隐藏、压抑的意识和欲望有关,正因如此,在文学世界中,作家们纷纷把笔下人物的梦境绘制于纸上,借此向读者展示人物的深层精神世界。残雪《山上的小屋》中的梦境空间是“意识深处发动的起义”,它与一般梦境的详尽、梦幻、迷离不同,其是简略、恐怖、病态的。
(一)简略、恐怖的梦境空间
传统小说中的梦境描写往往通过详细叙述梦境内容来表现梦境特征和做梦者的内心欲望,如《水浒传》中“宋江还道村梦受天书”用洋洋数千言,详细描写了仙境美景及宋江受天书的经过,全方位表现了宋江替天行道、全忠仗义、辅国安民的内心愿望。与此不同的是,残雪在《山上的小屋》中,并未详尽书写家中每个人的梦,相反,她以人物做梦后的反应来间接、简略地说明他们梦境空间的特征。首先,“我”说母亲在睡梦中表现的十分害怕,她的脚心直出冷汗,而家中的每个人睡着了脚心都会出冷汗,被子的潮湿程度也恰恰证实了这一点。这里并不直接叙述家人们梦境内容的奇异与恐怖,只是转而用“我”的话语来略说他们在睡梦中害怕的直出冷汗以及被子的湿潮,通过家人们的反应间接展现梦境空间的可怕。同时,在写母亲的梦时,残雪采用了更为简略的语言:“母亲从门边伸进来墨绿色的小脸,嗡嗡地说话:我做了一个很下流的梦,到现在背上还流冷汗。”她用一句话,将母亲梦境空间的可怖展现给读者,在简短的语言背后是其留给读者的广阔想象空间,这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加深了小说的空间色彩,文本可读性也得以增强。
(二)执拗、病态的梦境空间
除了简略、恐怖以外,小说中的梦境空间还表现出明显的病态特征,《山上的小屋》中的父亲是病态梦境空间的集中体现者,其梦境的病态呈现是极为强烈的。在父亲梦境空间中,井里有他掉下的一把剪刀,他也决计要将其打捞上来,但“一醒来,我总发现自己搞错了,原来并不曾掉下什么剪刀”,按常理而言,在梦中梦到的并不可信,在现实中,父亲理应放弃打捞剪刀,但他却不死心,下一次又记起打捞剪刀一事,并为此事苦恼了几十年,这样极端的执拗使梦境空间带有了一定的病态色彩。同时,在后文中进一步表现了父亲梦境空间的病态、离奇特征:“我打开隔壁的房门,看见父亲正在昏睡,一只爆出青筋的手难受地抠紧了床沿,在梦中发出惨烈的呻吟”。母亲也指出父亲在梦中“梦见被咬的是他自己”。父亲在危险,恐怖的梦境空间中不断挣扎,用呻吟来表现自己的痛苦,其梦境空间的病态也在苦痛的呻吟和极端的执着中得以凸显。
三.虚与实的并置交融
在残雪的小说中,实实在在的地志空间即实境空间与迷离怪诞的梦境空间即虚境空间之间的并置交融常常是她完成小说构建的一种重要创作手法,《山上的小屋》也正是通过对地志空间:“家”空间和虚幻空间:父亲梦境空间的并置交融,来实现小说空间的统一性。
(一)虚幻空间和实在空间的交融共生
在小说中,实在的地志空间和虚幻的梦境空间是并置的,二者互相印证,且以“井”為并置空间的意象中介。父亲梦境空间的建构,是建立在实在的“家”空间的基础上的,没有实在的家存在,其梦中的掉剪刀和打捞剪刀行为将无场所依傍。同时,他梦中的井是实在的“家”空间的组成部分,他病态的打捞行为也是在家的空间中进行的,正是因为有地志空间“家”的存在,父亲的梦境空间才有生成的参照系统,其梦中的奇特行为才有存在的可能,也就是说,虚幻空间的存在需要实在空间提供前提性的支撑。更为重要的是,虚幻空间和实在空间是交互存在的,即“家”空间与梦境空间又是交融共生的。父亲在梦中梦见“那井底,有我掉下的一把剪刀”,于是他在夜晚““反复不停地将吊桶放下去”企图将梦中的剪刀在现实的井里打捞起来。父亲打捞剪刀的行为,实际上代表着他在虚幻的梦境空间与实在的地志空间之间穿梭进出,残雪也正是通过对这一行为的书写,实现实与虚两个空间的交融并置。
(二)空间并置交融的作用
残雪小说的空间在其文本叙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空间不再只是作为小说中宏观的的背景或环境,其参与文本微观层面的呈现,空间的并置交融也在三个方面展现了其对文本建构的独特作用。首先,空间并置交融能推动叙事进程,如《山上的小屋》中通过小屋和家、家和梦境的空间并置与空间转换来实现叙事视点与叙事内容的变化,从而推动故事发展。其次,空间并置交融能表现文本中不确定的时间,将不可感的时间具体化为空间中的某一物体的改变或某一人物的行动,在《山上的小屋》中空间的时间性作用尤为突出。小说中通过人物在“家”空间中的不同行为的相继出现,如吃饭、清理抽屉、打捞剪刀、睡觉来表现时间的流动;小屋和家、家和梦境的空间交融使时间碎片化,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时间的可感性,但梦境空间的多次出现又使时间在叙事进程中被不断提及,梦境空间的每一次出现都代表着时间的流逝与变化,从此而言,时间的可感性又得到了增强。最后,空间的并置交融使小说形成了不同于传统叙事文本的空间结构——散文式结构。读者阅读《山上的小屋》就像是在浏览一本画册,各式各样的奇异、怪诞画面一一呈现在面前,小屋、家、梦境三个空间的不断变化,空间中人物的行为也随之不断的变化,甚至在同一个空间中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梦境空间,各自独立的梦境被并置融合在共同的家空间中,就像画册中各自独立,风格各异的画面被并置在一起,而并置在一起的画面又共同诉说一个主题,像是散文一般形散而神不散。
在《山上的小屋》中,以“家”和小屋为代表的异化地志空间与以父亲梦境为代表的病态梦境空间共同构建起了一个虚空,压抑的荒诞世界。而残雪进一步地将实际的地志空间与虚幻的梦境空间进行并置融合,在并置融合的空间中,她以“我”——一个精神变异者的眼光对空间中的人的生活状态和人性进行了深刻思考。总之,空间在残雪的小说叙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山上的小屋》中虚实空间的并置融合也给予了文本独特的空间特色。
参考文献
[1]龙迪勇.叙事学研究的空间转向[J].江西社会科学,2006(10):61-72..
[2]张世君.《红楼梦》空间叙事的分节[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99(06):36-44.
[3].Towards a Theory of Space in Narrative[J].Poetics Today,1984,5(2).
[4]刘思佳.残雪小说空间叙事研究[D].哈尔滨师范大学,2022.
[5]薛晓倩.寻找迷宫的出口[D].华中科技大学,2021.
[6]龙迪勇.空间叙事本质上是一种跨媒介叙事[J].河北学刊,2016,36(06):86-92.
[7]董晓烨.文学空间与空间叙事理论[J].外国文学,2012(02):117-123+159-16
0.
[8]龙迪勇.试论作为空间叙事的主题-并置叙事[J].江西社会科学,2010(07):24-40.
[9]程锡麟.论《了不起的盖茨比》的空间叙事[J].江西社会科学,2009(11):28-32.
[10]龙迪勇.论现代小说的空间叙事[J].江西社会科学,2003(10):15-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