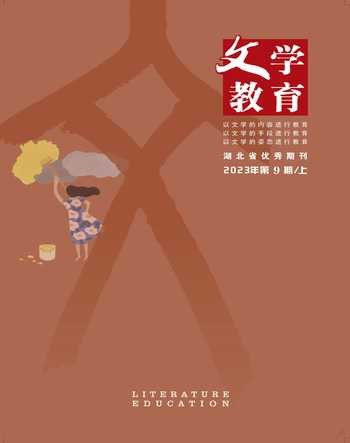本雅明视角下白先勇《孽子》的都市书写
叶晓茜
内容摘要:本雅明在其拱廊计划中以漫游者的形象分析了波德莱尔及其作品,这个走入现代化工业进程的形象,在都市中四处游走,以一种悲观绝望的姿态反抗飞速运转的现代社会。这个形象横跨一个世纪,出现在白先勇的《孽子》中,小说中塑造的人物也如同漫游者一样,在台北这座城市寻找自己的落脚点,并试图构建自己的家园。通过分析《孽子》中的空间结构,以及故事中的漫游者形象,探讨都市空间与人物之间相互构成的可能。
关键词:白先勇 《孽子》 漫游者 本雅明 空间
本雅明在拱廊计划中,以巴黎为研究中心,通过拱廊街这个具有辩证性的意象,一方面反映的是十九世纪资本主义兴起后文化发展的图景,另一方面,作为消费场所的拱廊街,吸引众多人前往并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后现代都市景观。而在拱廊街中,除了琳琅满目的商品之外,游手好闲、到处闲逛的漫游者也成为了其中独特的风景。现代化进程使得都市看起来如梦似幻,而漫游者走入人群中,化身为“人群中的人”,他们不肯独处,而是寻找人群,躲进人群中。“对于闲逛者来说,人群是一层面纱,熟悉的城市在它的遮掩下化为一种幻境。城市时而幻化成风景,时而幻化成房屋。”[1]在这种梦幻的景象中,他们获得了一种“震惊”式的体验,这是对城市空间最大的现代性体验之一。“震惊”来自于人对城市生活多重意象获得的异化体验,不仅是城市给人群带来的害怕与恐惧,更多的也包含着现代化工业进程的劳动体验。在《孽子》中,白先勇刻画了一个迷离华丽的台北城,以及在城市边缘四处逃散的一群少年。都市空间是开放且流动的,但是他们身处于都市之中,却又不被都市接纳。故事从阿青被逐出家门开始,从新公园到安乐乡,而阿青与那些同他一样流离的朋友,无论是他们曾经听闻的故事,还是自己身上发生的故事,都如同土壤下盘根交错的树枝缠绕在一起,最终指向爱欲与生死的命题。这群都市中的青少年与本雅明笔下的漫游者形象有一定的相似性,故本文试以本雅明的视角切入分析故事的空间向度,以及处在流动空间中的同志主体。
一.流动的空间——《孽子》的空间流转
“我們没有政府、没有宪法、不被承认、不受尊重,我们有的只是一群乌合之众的国民。”在《孽子》中,这群青春鸟在台北这座城市逃亡般的游荡。根据小说叙述的结构,可以看出《孽子》的空间流转首先是由家开始,度过到学校。在经过“放逐”后,游荡到新公园即“我们的王国里”,而“安乐乡”便是其中最重要的精神领地,最后,这群少年如青春鸟一般,四散各地。故事先创造一个私人空间,再转向公共空间的流动塑造,由此,白先勇笔下的台北城便逐步立体起来。
《孽子》中的叙述者“我”,李青,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家住在龙江街破败的眷村里:
这条死巷巷底,那栋最破、最旧、最阴暗的矮屋,便是我们的家。……我们的房子特别矮,阳光射不进来,屋内的水泥地分外潮湿,好像径湿漉漉在出汗一样,整栋屋子终年都在静静的,默默的,发着霉。绿的、黄的、黑的,一块块霉斑,从墙脚下,毛茸茸的往上爬,一直爬到天花板上。我们的衣服,老是带着一股辛辣呛鼻的霉味,怎么洗也洗不掉。[2](P36)
母亲住的那栋房子就在克难街底的一个贫民窟里。那是一栋十分奇特的建筑物,一所日据时代残留下来两层楼的一座水泥房子,墙壁坚厚,墙上没有窗户,只有一个个小黑洞,整座房子灰秃秃,像是一座残破的碉堡,据说是日本人驻军用的。我进到房子里,一道螺旋形的水泥楼梯,蜿蜒上升,伸到那看不清的幽暗里去。[2](P46)
巴什拉在《空间诗学》中说到“家宅是一种‘灵魂的状态”,同时,“大城市的家宅缺乏宇宙空间性。这些家宅不在于自然之中。居所和空间之间的关联成了人为的。在这种关联中一切都是机械的,内心生活从那里完全消失了。”[3](P27)在巴什拉看来,家宅对人们来说代表着对身体与灵魂的庇佑,也同时反映出了内心领地的幸福感。但是在《孽子》中,白先勇极力刻画了家宅的破败之感,李青父子居住的房子常年阴暗潮湿,还带着挥之不去的霉味。而李青母亲出走后所处的居所,也是残破幽暗的,对李青来说,母亲的出走也代表家的不复存在。居所的狭窄且固定,使得房屋纵深感消失了,如同没有了“根”。李青的父亲经历了战乱,革去了军籍,曾经的风光换来现在的落寞,以及眼前这个本不属于自己的房子。而李青更是因为在躁动的年纪发现自己与他人的不同,而在家宅这个本该得到庇护的地方却充斥着父亲的规训,家宅也不再具有完整性,而是充满绝对权力的空间,这也与李青自我放逐有着一定的必然性。
紧接着便是这群青春鸟们最重要的精神栖息地安乐乡,从桃源春到安乐乡,这些场所都是为这群青春鸟打造的一个的乐园,从外部空间看安乐乡是隐蔽、狭小的,但一旦进入地下空间,安乐乡就变得敞亮,既阻挡了外部空间的挤压,又能为同性恋群体提供一个实体的隐秘空间:
在这浮面的繁华喧嚣下,我们的新窝巢安乐乡却掩藏得非常隐密,不是我们的同路人,很容易便被隐瞒过去。因为安乐乡的外面,没有招牌,大门紧挨着金天使的左侧,狭窄的一条门缝,仅仅能容得一人通过,接着便是一条陡直的楼梯一级级伸引下去,楼梯口只悬着一盏淡黄的小灯,光线昏暗,走下去,得扶着栏杆,摸索下降,直到下面,一转右,两扇玻璃门便唰地一声,自动张开,里面赫然别有洞天,进入了安乐乡中。
安乐乡的地下室酒馆有六十坪大。东西两壁镶满了水银镜子,灯光人影互相反射又反射,照出重重叠叠的幻象来。灯光一律是琥珀色的,映得整间酒馆浴在濛濛夕雾中一般。[2](P208-209)
另外,台北中心商业区域西门町,是一个旧历史与新潮流碰撞的地方,也代表着现代城市的消费橱窗。台湾这座城市拥有着复杂且多元的文化意蕴,经历了都市改造的计划后仍旧包含着许多社会边缘性特质,在这里混杂着多种各异的元素,而孽子们也投入这个空间中,进行了探索与体验。
我们窜逃到南阳街,一窝蜂钻进新南阳里,在那散着尿臊的冷气中,我们伸出八爪鱼似的手爪,在电影院的后排,去捕捉那些面目模糊的人体。我们躲过西门町霓虹灯网的射杀,溜进中华商场上中下各层那些闷臭的公厕中。我们用眼神,用手势,用脚步,发出各种神秘的暗号,来联络我们的同路人。我们在万华,我们在圆环,我们在三水街,我们在中山北路——我们鬼祟的穿进一条条潮湿的死巷,闪入一间间黝暗腐朽据时代残留下来的客栈里。[2](P30)
空隆——空隆——空隆——中华商场外面铁路上,有火车急驶过来,穿过西门町的心脏。车声愈来愈近,愈响,就在窗下,陡然间,整座中华商场的大楼都震撼了起来。我企望着窗外那些闪烁的灯光,突然兴起一股奔逃的念头,往那扇窗户外面,飞跃出去。可是我并没有马上离开,我将一团温湿不知数目的钞票塞进裤袋里,又扭开了水龙头,哗啦哗啦,在黑暗中,一直让凉水冲洗我那双汗污的手。[2](P61-62)
他们离开家,走向都市,穿过人群,又流窜到一条条街道暗巷中。白先勇不描写城市繁华的样貌,却在此刻画了位于繁华市中心的公共厕所黑暗、逼仄的环境,这样的“脏”与窗外闪烁的霓虹灯形成强烈的对立感,在看似繁华的地方,黑暗与肮脏也一直伴随其中,通过借繁华的西门町显露出城市中心仍旧存在的被边缘化的景象,也正是有了这种景观的存在,孽子的存在也得到合理化的解答。
二.游荡的身体——《孽子》中的都市漫游者
漫游者,“游手好闲的懒骨头,一个不知道该去哪里消磨他的无聊和困扰的人。”后来本雅明将漫游者这个文学形象运用分析到波德莱尔身上,他认为波德莱尔是最富有典型意义的漫游者代表,波德莱尔在其诗作中揭开巴黎梦幻神秘的面纱,也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命运,人群的面孔瞬息万变,而波德莱尔融入其中,在城市的震惊体验中隐匿自我。本雅明认为对大城市的揭露性呈现出自那些穿行于城市之中却心不在焉、或沉思默想、或忧心忡忡的人。漫游者与看热闹的人不同,“单纯的闲逛者总是保留着全部个性,而看热闹的人身上没有个性。他的个性被外部世界吸收掉了……外部世界令他如醉如痴,以至他忘却了自己。”[1](P140)这些漫游者看起来融入人群中,但却依然保留着自己的全部个性,既不属于资产阶级,也不会融入都市的人群中。游荡的行为体现出生存状态的脆弱性,一种“无根”的虚空感。虽然他们是不被主流社会所接受的,仍处于边缘地带,但是他们依旧渴望在这座城市获得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在《孽子》中,李青、小玉、老鼠、吴敏等人都如同本雅明笔下的漫游者一样,在都市里懒散闲晃,游荡辗转于旅馆、酒吧、新公园、安乐乡里,因为自身身份的特殊,使得他们的漫游显得不那么自在,更多了一些悲剧性,他们被巨大的社会体制所压制着,处在一种被社会抛弃和抵制而又无处可逃的困境中。
故事的主角李青因為被学校抓住发生了淫猥行为而被记过并被勒令退学,而其父得知后便将其逐出家门。被放逐后便开始了他带有流亡性质的漫游。离开家后,李青游荡到新公园,在这里他完成了生命意义的建构,在家被规训的身体到了新公园后摆脱了权力的束缚。可是虽然离开了家,阿青也仍无法安定下来,先是陆陆续续遇见像自己弟娃一样的小弟,却又在短暂地相处和照顾后与他们分离,甚至当面对那些愿意给予他爱的人时,他也主动逃离,辗转于王夔龙、俞先生、严经理等人的身边,最后再悄然离去。像是宿命般地,他选择继续漫游于都市之中。除了阿青之外,故事里还有许多像他一样因为“异类”而被放逐的鸟儿们,小玉十四岁就因为不同的性向被继父发现因此离家出走,他也一直惦记着自己的亲生父亲,并在安乐乡关闭后去往东京寻找父亲,在东京他四处奔波:“东京叫人兴奋,叫人着迷,叫人心惊胆跳!昨天我去逛银座,看见那么多车子,人,高楼大厦,我恨不得跳起来大叫。……东京的街道门牌号码乱得可怕,我在新宿那些大街小巷里横冲直撞,像在迷宫里打转。……找完了新宿的中岛正雄,就找浅草、涩谷、上野,一直找下去。”阿玉渴望找到自己的生父,但最后也只是像阿青调侃小玉常常做的一场樱花梦一样,梦醒后仍然继续被放逐。因为爱上阿凤,被父驱赶到美国的王夔龙,在其父亲死后都无法见他最后一面。而王夔龙到了美国后,仍然过着一种醉生梦死的生活:“我去当酒保,一来想赚几个零用钱,二来我也喜欢躲在那个极深极深的地窖里,跟那群流浪汉混在一起……”回到台北后他旧地重游,来到新公园遇到遇见与当年的阿凤一般年纪的阿青,并与他敞开心扉,讲述了自己的过往。无论是在纽约还是台北,他始终找不到自己的根。
再回到“孽子”之名,无论是自我放逐的阿青、寻父的小玉还是杀了爱人的龙子,他们都在寻找“接下来该去哪里”之路,他们渴望得到救赎,但或许孽子身上本就流淌着颠沛流离的血液,他们也因此聚集在一起,即使家境、年龄、阶级各不相同,却因“同志”身份聚合在一起,试图构筑起属于这个群体的新家园。
三.寻家之旅与身份认同
《孽子》中的空间建构与每个角色主体进行互认,空间影响并反映出人物不同的生动形象,而人物也反过来对空间塑形起到一定的作用。孽子们被家驱逐,有家却回不去,这个家不仅仅指代着实际的住所,更是一个由父亲主导的充满权力话语的家。“大多数的同性恋者心灵上总有一种无家可归的漂泊感,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她们都是被父母放逐的子女。”[4]这种破碎的宿命感是通过父子伦理关系反映出来的,手握绝对权力的异性恋父亲试图塑造完美的父权空间,而因为先于主体存在的父系空间侵蚀了自己的主体性,受到权力规训的同性恋儿子同时也选择了自我放逐。
对于孽子们来说,新公园、安乐乡已非一个同类聚集的场地,更多的是充满集体想象的精神地标,这些地标体现出空间想象的流动性。而在空间的流动中,孽子们去寻找安放自己情欲的地方和身份认同的可能性。但是在故事结尾,安乐乡被记者的窥视和检举,精神教父傅老爷子因病去世从而导致这些青春鸟们再次失去与世界的连接,被家庭放逐、被社会唾弃的孽子们,仍然在台北城或是异国漂泊漫游。除了家庭外,媒体、学校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也构成了隐形的权力建构,这些标榜着自己是社会中正常的人以一种他者、非我的目光来审视孽子们,导致他们一再被边缘化,从而本该是正常的身份不断被异化,在这些非暴力、隐形的霸权侵袭下,孽子们的“家”无处可寻。
即使如此,当再次想要找到栖息之地时,当那些和自己一样处在身份认同困境中的同类们,在放逐中还有对彼此的支持,他们依然可以另寻乐园。正如小玉来信时写道“东京据说有上百家的‘安乐乡……东京的青春鸟可厉害着哪,满街乱飞……新宿也有一个新公园,叫御苑,比咱们的新公园可要大十倍哩。”也像阿青和吴敏在街头奔跑时开的玩笑一样,这些青春鸟就像游牧民一样,不会总生活在同一个地方,而是不受约束毫无方向地漫游。
孽子们在都市里漫游共同塑造了属于那个群体的集体记忆,在空间轨迹的流变里,他们表现了对爱的渴望、对生命的思考。这是一个在一次次奔赴爱的路上成长的故事,也是在这个时代,被边缘的、性少数群体彼此取得救赎的故事。那些孤独彷徨、无所依归的孩子们,最终也许会汇聚到一起,重塑自己真正的家园。
参考文献
[1](德)本雅明著,刘北成译.巴黎,十九世纪的首都[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2]白先勇.孽子[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
[3](法)加斯东·巴什拉著,张逸婧译.空间的诗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4]白先勇.白先勇文集第四卷:第六只手[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