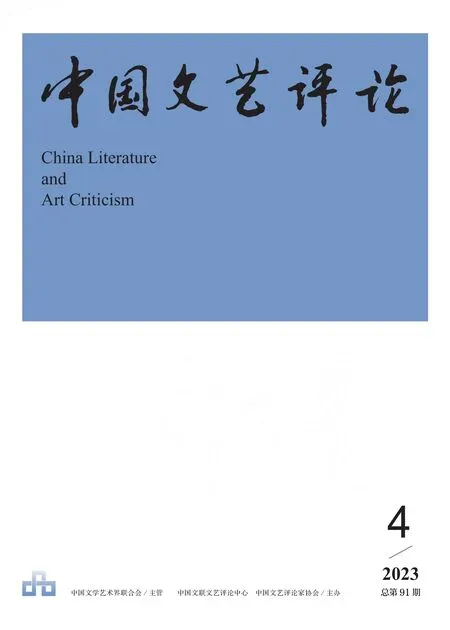“尽是人间第一流”
——《本事诗》的人物风雅与中国古典文评景观
■ 廉水杰
诗话是古典文艺批评品藻诗人风采及其诗歌关涉逸事的独特存在。宋代文人许顗《彦周诗话》云:“诗话者,辨句法,备古今,纪盛德,录异事,正讹误也。”[1][清]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78页。诗话中选取的诗歌都是便于传唱的“雅言”,正是这种雅言的传播复活了历代文人、美人的风雅风采。晚唐文人孟启[2]“孟启”的名字,《历代诗话》本作“孟棨”,有学者据新出土墓志铭认定为“孟启”。据此,本文作“孟启”。参见胡可先等:《〈本事诗〉新考》,《中国典籍与文化》2004年第1期,第79页。的《本事诗》在诗话发展史上有着经典意义,不仅品藻了我们熟知的李白、杜甫等大诗人,近人丁福宝辑录《历代诗话续编》亦以其为首。然而,以往的研究基本侧重于《本事诗》的诗学观念及文体辨析。[3]参见吴怀东:《〈本事诗〉“诗史”说与中晚唐学术脉动》,《文史哲》2018年第4期,第140-151页。孟启曾在《唐孟氏家妇陇西李夫人墓志铭(并叙)》中自云“常以理乱兴亡为己任”,并对天下事“默知心得”[4]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八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年,第215页。,其对世事沧桑非同一般的识鉴体现在所编撰的《本事诗》中。《本事诗》作为诗话“本事批评”的经典之作,别出心裁地以诗歌所涉故事为本原,对诗人、美人以及王侯将相、僧人道士进行品论,很有必要作进一步研究。因此,本文重在对孟启《本事诗》诗话视域下诗人、美人的风雅流韵作以品鉴,从而呈现古典人物的性情风雅及中国古典文评景观,希望为当下文艺批评提供借鉴。
一、“嘲戏”:文人的“幽默”风雅
我国古典文化一向有“幽默”的传统,不仅《庄子》里有大量的幽默风趣之言,司马迁的《史记》也专列“滑稽列传”,而“嘲戏”作为“幽默”的一种表现方式,在孟启《本事诗》的诗话视域下,有抒怀、讽刺的功用。文人的“幽默”风雅源于“雅言”的绝妙运用,《本事诗序目》言:“抒怀佳作,讽刺雅言,著于群书”[1]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页。。《本事诗·嘲戏第七》载:
宋武帝尝吟谢庄《月赋》,称叹良久,谓颜延之曰:“希逸此作,可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昔陈王何足尚邪!”延之对曰:“诚如圣旨。然其曰‘美人迈兮音信阔,隔千里兮共明月’,知之不亦晚乎?”帝深以为然。及见希逸,希逸对曰:“延之诗云:‘生为长相思,殁为长不归。’岂不更加于臣邪?”帝拊掌竟日。[2]同上,第20页。
总览《本事诗》,除了颜延之嘲戏谢庄这则雅事及南朝陈乐昌公主与其夫徐德言的故事属于六朝时期,其他均为唐代文人逸事。颜延之作为六朝晋宋时期的文化风雅大家,以性情傲岸、言语博雅著称。“嘲戏”有调笑戏谑的意味,三国时期魏文帝曹丕《典论·论文》云:“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词,至乎杂以嘲戏。”[3]郁沅、张明高编选:《魏晋南北朝文论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13页。曹丕说孔融在文章中穿插“嘲戏”之言,是因其不善于写理论文章。言外之意,“嘲戏”的语言有助于主体性情的抒发而不利于发议论讲道理。孟启在“嘲戏”类首则故事中引用颜延之事,显然在于推崇颜延之与谢庄的富有才性之美的诗歌互答。关于此事,早于《本事诗》的初唐编撰的《南史》“谢庄传”亦有记载,而《南史》记载的文字更为简略,没有宋孝武帝刘骏“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称赏及对《月赋》中借陈思王曹植之口的评点。对比之下,《本事诗》的记述更有意味,也更能突出颜延之的风雅性情。颜延之戏谑谢庄知道“美人”“明月”相隔太远的常识太晚;而谢庄亦借用颜延之《秋胡行》的诗句嘲笑其知道“生”“死”比他还晚。两人的机锋之言让宋武帝开心多日。颜延之才思敏捷,连大诗人谢灵运也比之不及,《韵语阳秋》记载:“颜延之、谢灵运各被旨拟《北士篇》,延之受诏即成,灵运久而方就。”[4]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99页。孟启选取此事,不仅表现了颜延之才思迅捷,也呈现出了君臣嬉戏的平等氛围,这在晚唐明争暗斗的高压政治之下,别有时代意蕴。
以《本事诗》的“嘲戏”视域来看梁代评论家钟嵘《诗品》对颜延之的记述,可以看出诗话编撰者选取此类事例的匠心。颜延之作为与山水诗人谢灵运齐名的大家,其五言诗“错彩镂金”的诗风却一直备受诟病。钟嵘《诗品》载:“汤惠休曰:‘谢诗芙蓉出水,颜诗错彩镂金。’颜终身病之。”[1][梁]钟嵘著、曹旭集注:《诗品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351页。关于颜延之的“终身病之”,曹旭注解为:“谓颜延之对此评价,终生怀恨在心。”[2]同上,第358页。站在“嘲戏”视域来看,若把“颜终身病之”解释为“颜延之终生怀恨在心”,作为风雅大家的颜延之“小肚鸡肠”的形象呼之欲出,与古典文学史上颜延之能相交其时名微的陶渊明,并能面对君王出“嘲戏”之言的磊落潇洒亦相悖。
这就引申出一个问题,同样作为诗话大家,钟嵘是否与孟启一样有“嘲戏”视域呢?综合考察钟嵘的《诗品》,亦不乏“嘲戏”之言,如在《诗品》的“中品”评价西晋著名文人张华的诗歌时用了“儿女情多,风云气少”[3]同上,第275页。。张华诗歌情思缱绻,语言妍丽,缺少慷慨之气,其代表作《情诗》更是如此,这也是历代诗论者的共识。然而,钟嵘一句“儿女情多,风云气少”,用戏谑之言生动形象地阐释了张华诗歌的审美特征。再如在“下品”评价齐代文人袁嘏时,引用其言:“我诗有生气,须人捉着。不尔,便飞去。”[4][梁]钟嵘著、曹旭集注:《诗品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616页。袁嘏诗才一般,却总是爱吹嘘自己,钟嵘引用其对当时权贵徐孝嗣说的话,让人莞尔。以诗话的“嘲戏”视域来看,钟嵘一句“颜终身病之”,明显是借用汤惠休之言来调侃名盛文坛的颜延之,其意蕴的传递远远超出了“颜延之终生怀恨在心”的阐释,颇有黑色“幽默”的味道。因此,“嘲戏”视域的背后是对人性本真和创作主体本然性情的认可,建立在评论主体对诗歌创作规律的切实认知之上,幽默轻松的背后体现出诗话评论家的人文素养和审美识鉴。
孟启撰《本事诗》“嘲戏”类共有七则,除了第五则写诗人张祜和著名文人白居易的对答逸事外,其余六则全部写的是诗人与皇亲贵戚之间的戏谑事,即使与张祜嬉戏的白居易,其时也在苏州刺史的任上。诗话中的此类记述,反映了诗人与位尊者的平等交往,没有高下之别,如《本事诗·嘲戏七》载:
则天朝,左司郎中张元一滑稽善谑。时西戎犯边,则天欲诸武立功,因行封爵,命武懿宗统兵以御之。寇未入塞,懿宗始逾邠郊,畏懦而遁。懿宗短陋,元一嘲之曰:“长弓短度箭,蜀马临高蹁。去贼七百里,隅墙独自战。忽然逢着贼,骑猪向南窜。”则天闻之,初未悟,曰:“懿宗无马邪?何故骑猪?”元一解之曰:“骑猪者,是夹豕走也。”则天乃大笑。懿宗怒曰:“元一夙搆,贵欲辱臣。”则天命赋诗与之,懿宗请赋“菶”字。元一立嘲曰:“裹头极草草,掠鬓不菶菶。未见桃花面皮,先作杏子眼孔。”则天大欢,故懿宗不能侵伤。[1]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0-21页。
武则天时期的文人张元一用白描漫画式的诗歌,对外戚武懿宗御敌时的胆怯无能进行了生动传神的刻画,“长弓短度箭,蜀马临高蹁。去贼七百里,隅墙独自战。忽然逢着贼,骑猪向南窜。”笔法入微,寥寥几笔就把武懿宗的逃跑丑化为“猪”乱窜的丑陋之态。武则天为了巩固皇权,罔顾宗族子弟的实际才干,重用武懿宗去领兵抗击侵犯边境的西戎,而武懿宗离敌甚远就准备遁身而逃。身为左司郎中的张元一用诗歌对武懿宗这种御敌逃脱的丑态进行了嘲讽。面对武懿宗进一步的刁难,其又用诗歌进行了“嘲戏”,“杏子眼孔”对比“桃花面皮”,更是让人忍俊不禁。张元一不慌不忙戏谑武懿宗的同时又对自己的危险境遇进行了机智化解,最后在武则天的大笑中避过武懿宗的刁难。比之武懿宗,张元一虽官微却胆大智慧,称得上是有勇有谋。此外,《本事诗》“嘲戏”类最后一则故事记载了唐中宗李显畏怕老婆韦皇后的逸事,孟启借助于伶人所唱《回波词》对中宗进行了幽默的“嘲戏”,让韦皇后“意色自得”,并以“束帛赐之”。
《本事诗》“嘲戏”类中诗人们以机智的反应、言语的机锋,幽默地传播了权贵们的可笑事迹。钱锺书先生在谈及司马迁《史记·滑稽列传》的“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时,说“言廷臣所不敢,谲谏匡正”[2]钱锺书:《管锥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第602页。,也肯定了幽默之言的庙堂作用。得体的“嘲戏”他者,不仅需要渊博的学识,更需要对雅言高超的驾驭技巧,也最能反映诗话编撰者的批判精神。“嘲戏”的“幽默”背后,是诗人们不卑不亢的文人气度与审美意识。袁济喜在论述民国学人林语堂对“幽默”的态度时,就明确指出“幽默”能“使人们从专制社会与日常生活的沉重压迫下解脱出来”[3]袁济喜:《“谁是诗中疏凿手”——古代文艺批评的角色探讨》,《中国文艺评论》2022年第10期,第31页。。“嘲戏”作为“幽默”的一种形式,在诗歌的雅言传播中,不仅能突出诗人们的本真性情,更能烘托出故事氛围,成为表现人物风雅的重要方式。
二、“拙俗鄙俚,亦所不取”:美人“超出俗流”的风采
孟启的《本事诗序目》叙述了其取录标准,不仅强调以情感为本位的“触事兴咏,尤所钟情”,还进一步言“拙俗鄙俚,亦所不取”[4]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页。。此准则在《本事诗》“情感”类体现得尤为突出,特别是对众美人的逸事选录。《本事诗》“情感”类共有12则故事,其中众美人超出俗流的风采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有“真性情”风骨的美人。《本事诗》“情感”类开篇是有名的“破镜重圆”的故事,这则故事充分表现出了人性之美,有乱世中有谋略的乐昌公主之夫徐德言,有“成人之美”的位高权重的隋朝权臣杨素,更有不慕奢华并“才情卓然”的乐昌公主。乐昌公主已在杨素家被“宠嬖殊厚”[1]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页。,面对久别重逢的夫君徐德言,她的一首“今日何迁次,新官对旧官。笑啼俱不敢,方验作人难”[2]同上。,在自嘲的同时,又不失作为亡国公主的风骨。乐昌公主“涕泣不食”的真情最终感动了杨素,令其“怆然改容”,这才有了“破镜重圆”的夫妇传奇。“情感”类第二则故事是和乐昌公主同样有着“美人风骨”的窈娘,《本事诗·情感第一》载:
唐武后时,左司郎中乔知之有婢名窈娘,艺色为当时第一。知之宠爱,为之不婚。武延嗣闻之,求一见,势不可抑。既见即留,无复还理。知之愤痛成疾,因为诗,写以缣素,厚赂阍守以达。窈娘得诗悲惋,结于裙带,赴井而死。延嗣见诗,遣酷吏诬陷知之,破其家。诗曰:“石家金谷重新声,明珠十斛买娉婷。昔日可怜君自许,此时歌舞得人情。君家闺阁不曾难,好将歌舞借人看。富贵雄豪非分理,骄奢势力横相干。别君去君终不忍,徒劳掩袂伤红粉。百年离别在高楼,一旦红颜为君尽。”时载初元年三月也。四月下狱,八月死。[3]同上,第5页。
武则天时期,左司郎中乔知之有姿容、才艺堪比西晋权贵石崇歌婢绿珠的美人窈娘,被权贵武承嗣所夺,知之作诗密送之,窈娘感怀其情投井而死,于是武承嗣大恨,动权把知之下狱,最终致其殒命。关于绿珠的命运,《红楼梦》中林黛玉作《五美吟·绿珠》,其云:“瓦砾明珠一例抛,何曾石尉重娇娆。都缘顽福前生造,更有同归慰寂寥。”[4][清]曹雪芹著、[清]无名氏续:《红楼梦》中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第896页。林黛玉谴责了权贵石崇,认为石崇的锦衣玉食之宠,并不是真正地看重她,不值得她以死相报。与绿珠不同的是,窈娘是乔知之钟情所爱,“知之宠爱,为之不婚”,虽仅有八字,却有惊天地泣鬼神之感。在男性可以纳众多侍妾的唐代,乔知之只钟情一人并为所爱不婚娶,此举远超俗流。乔知之不被礼教束缚,可见其情深意重,所以无法脱离虎口的窈娘在得到乔知之的诗后,毅然决然赴死。“人不可以无情”,千载之后,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塑造的“至情至性”的“尤三姐”与窈娘的“刚烈”何其类似,这是古典文学作品中独特的女性形象。可以说,“窈娘之死”在古典女性形象传播史上,其经典意义不低于“绿珠之死”。“美人以死报恩遇”,窈娘形象风骨凛然,让人唏嘘不已。乐昌公主、窈娘这类女性形象是中国古典文评史上一道亮丽的人文景观。
第二类,有别致心曲、积极追求爱情的题诗宫女。“宫怨诗”是古典文学比较常见的题材,一般以书写宫女幽居深宫、自怨自艾为主,如汉代班婕妤的《怨诗》,一句“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5]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17页。,将无可奈何的幽怨跃然纸上。钟嵘在《诗品》中曾把班婕妤这类诗列为“上品”,并评之“辞旨清捷,怨深文绮”[1][梁]钟嵘著、曹旭集注:《诗品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13页。。孟启《本事诗》“情感”类12组故事中有两篇与宫女相关的故事,表现了宫女对爱情的积极追求。《本事诗·情感第一》载:
开元中,颁赐边军纩衣,制于宫中。有兵士于短袍中得诗曰:“沙场征戍客,寒苦若为眠。战袍经手作,知落阿谁边?畜意多添线,含情更著绵。今生已过也,重结后身缘。”兵士以诗白于帅,帅进之。玄宗命以诗遍示六宫曰:“有作者勿隐,吾不罪汝。”有一宫人自言万死。玄宗深悯之,遂以嫁得诗人,仍谓之曰:“我与汝结今身缘。”边人皆感泣。[2]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页。
唐玄宗开元年间,宫女受命为戍守边关的士兵缝制棉衣,有位宫女在棉衣中题了“袍中诗”。此诗情思清丽,自然流畅,既想象到了戍边士兵的苦寒境地,又倾注了绵绵情思于针线,并寄托了虚无缥缈的希望。对宫苑深深的宫女来说,这一“袍中诗”壮举,于绝望中寻找希望,颇有现代女性的风范。让读者感到慰藉的是,唐玄宗“成人之美”,将作“袍中诗”的宫女嫁给了得诗的士兵,使有情人终成眷属。《本事诗》“情感”类另一则故事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主人公换成了中唐文人顾况与宫女。《本事诗·情感第一》载:
顾况在洛,乘间与三诗友游于苑中,坐流水上,得大梧叶题诗上曰:“一入深宫里,年年不见春。聊题一片叶,寄与有情人。”况明日于上游,亦题叶上,放于波中。诗曰:“花落深宫莺亦悲,上阳宫女断肠时。帝城不禁东流水,叶上题诗欲寄谁?”后十余日,有人于苑中寻春,又于叶上得诗以示况。诗曰:“一叶题诗出禁城,谁人酬和独含情?自嗟不及波中叶,荡漾乘春取次行。”[3]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6页。
无疑,这则故事中的宫女“题诗”亦清丽婉约,情发自然,也得到了偶然得诗的诗人顾况的答诗回应。作“袍中诗”的宫女事发生在盛唐唐玄宗时期,而这则故事发生在中唐时期,有效仿之嫌。但身锁宫苑的宫女这种主动改变命运、积极追求爱情之举,仍然值得称道。中唐诗人元稹的《行宫》云:“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4][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410、第12册,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4552页。一般来说,寂寞无聊到白发才是那时的宫女命运,但这两则故事中的宫女却才思绝伦,勇气可嘉。可以说,因为孟启的高远卓见,作“袍中诗”的宫女、得诗的戍边士兵、“成人之美”的唐玄宗,也应该是“盛唐气象”的代表。一个时代的伟大不仅仅在于王侯将相的丰功伟绩,也在于人与人之间惺惺相惜的风雅之举。
孟启这类题材的捻出,具有重要的两性文明识见。在孟启之前,主体在诗歌创作中书写女性的美好,自屈原开创“香草美人”传统以来基本上都是以男性为主体的视角。既使女性本人作为主体创作的诗歌,也少有积极主动追求爱情的书写。在古典诗歌史上,从《诗经》开始,女性一直处于“被看”的地位,一直在男权视域下被书写。而这两位采用诗歌雅言书写情感的宫女,却是以主体的视野表达了心性情感,让人称赏。
孟启无疑有着两性平等的意识。这在其选取颜延之《秋胡行》中的诗句“生为长相思,殁为长不归”,亦可窥一斑而知全豹。《秋胡行》的故事最初见于汉代刘向的《列女传·鲁秋洁妇》,古辞原意赞颂了秋胡妻之刚烈,后世文人多沿袭旧意以题名写诗。在林立众作中,颜延之抛却“秋胡戏妻”的故事原貌,别出心裁地站在秋胡妻的角度来控诉秋胡的不良之行,最后慨叹无人相伴终老的遗憾,吟唱着描绘女子不为强权所逼的《诗经·国风·召南》之《行露》诗,从容跳河赴死。关于《行露》诗,朱熹注解言:“不为强暴所污者,自述己志,作此诗以绝其人。”[1]程俊英、蒋见元注:《诗经注析》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45页。颜延之用此典故彰显了秋胡妻的人格风骨。对《秋胡行》诗的评鉴,清代文人贺贻孙《诗筏》云:“若其浑古淡宕,汉、魏而后,而不多得也。”[2]郭绍虞编选:《清诗话续编》第1册,富寿荪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47页。颜延之的人物风雅亦体现在对女性的高远识鉴上,颇为值得深思的是,他所交好的其时诗名不彰的陶渊明也创作了被后人诟病书写心仪“美人”的《闲情赋》。所以,《本事诗》以颜延之与谢庄事作为“嘲戏”类开篇绝不是信手为之,对比“高逸”类开篇的李白故事,这体现了孟启思深意远的卓见。综上,众“美人”的超逸风采,不仅呈现了诗话中的人物风雅,更是古典文评史上的清丽景观。
三、“平等”视域的人物品鉴
孟启在《本事诗》“高逸”类开篇故事中对杜甫有着“诗史”的美誉,这也是历来杜诗研究的焦点。那么,《本事诗》对杜甫的发微之见,是否有潜在的对其“诗史”中“平等”精神的赞赏呢?邓小军早就明确提出,杜甫的“诗史”精神包含了“平等精神”,此种精神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发展。[3]参见邓小军:《杜甫的诗史精神》,《安徽教育学院学报》1992年第3期,第1-6页。以当下的文明思维来看,孟启的“本事批评”也包含了“平等”精神的视域,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对诗歌关涉风雅人物的品鉴,或感诗伤怀,或题诗应景,从帝王将相到普通士子一视同仁。例如,注重帝王与普通人等同的情感书写。在诗话中,一般常见的题材是歌女吟唱应景之诗,让人铭感共情,而孟启在诗歌品评中却借用雅言比较细腻地书写了帝王情感,《本事诗·事感第二》载:
天宝末,玄宗尝乘月登勤政楼,命梨园弟子歌数阕。有唱李峤诗者云:“富贵荣华能几时,山川满目泪沾衣。不见只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雁飞。”时上春秋已高,问是谁诗,或对曰李峤,因凄然泣下,不终曲而起,曰:“李峤真才子也。”又明年,幸蜀,登白卫岭,览眺久之,又歌是词,复言“李峤真才子”,不胜感叹。时高力士在侧,亦挥涕久之。[1]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1页。
从开元盛世到天宝末年,唐朝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面对岁月无情、江山动乱,听到契合心怀的诗歌,唐玄宗和普通人一样伤心感怀,以至于两次凄然感叹“李峤真才子也”。玄宗听的这首诗节选自初唐文人李峤的《汾阴行》,这首诗情感凄婉,映射时事,深深打动了亲历“安史之乱”的唐玄宗,以至于一旁伺候的高力士也潸然泪下,君臣都共情了这首诗所传达的意蕴。孟启选取的这类诗歌平铺直叙,有直刺时事的“诗史”特征。又如《本事诗·情感第一》载:
朱滔括兵,不择士族,悉令赴军,自阅于毬场。有士子容止可观,进趋淹雅。滔自问之曰:“所业者何?”曰:“学为诗。”问:“有妻否?”曰:“有。”即令作寄内诗。援笔立成,词曰:“握笔题诗易,荷戈征戍难。惯从鸳被暖,怯向雁门寒。瘦尽宽衣带,啼多渍枕檀。试留青黛着,回日画眉看。”又令代妻作诗答,曰:“蓬鬓荆钗世所稀,布裙犹是嫁时衣。胡麻好种无人种,合是归时底不归?”滔遗以束帛,放归。[2]同上,第5-6页。
朱滔是唐德宗时期在“泾原兵变”时被拥立为帝的朱泚之弟,史书称其“变诈多端”[3][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200、第16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368页。,作为中唐藩镇割据的地方统帅,可以说是杀人如麻,当时为了扩充势力,征兵连普通的读书人都不放过。这则故事书写了一位诗才敏捷的读书人,因气质儒雅受到朱滔的关注,随即朱滔令其作诗,其不仅写了一首描述自己不幸境遇的诗,还很快写了一首代妻作答诗,最终打动了朱滔。绝妙的是,朱滔竟然在放其归去时还赠以财物。这两首诗同时也具备“诗史”特征,反映了战争对本来应该幸福生活的普通人的不幸影响。这则故事中,不仅有诗思敏捷的普通文人,也有名声不佳却表现得风雅动人的朱滔。
第二,推崇文人之间“平等”的风雅相交。中唐大诗人白居易、元稹的友朋往来,历来被人称羡,甚至白居易还留有名扬千载的《与元九书》。孟启渲染了“元、白”之间倾心相交的友情,如《本事诗·征异第五》载:
元相公稹为御史,鞠狱梓潼。时白尚书在京,与名辈游慈恩,小酌花下,为诗寄元曰:“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当酒筹。忽忆故人天际去,计程今日到梁州。”时元果及褒城,亦寄《梦游》诗曰:“梦君兄弟曲江头,也向慈恩院里游。驿吏唤人排马去,忽惊身在古梁州。”千里神交,合若符契,友朋之道,不期至欤。[4]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9页。
元稹、白居易心有灵犀,白居易游慈恩寺,饮酒解愁于是想到好朋友出差应该到了梁州,神奇的是,元稹真的就到了梁州,同时也写了诗寄给好友并说梦到白居易去游了慈恩寺。白居易诗中之事,竟然与元稹诗中之梦吻合。换言之,元稹的诗歌梦境竟然契合了白居易的现实之事,不得不让人称奇。孟启不仅选取文人交往的“知音”风雅,还书写了文人交往的胸怀境界,如《本事诗·情感第一》载:
李相绅镇淮南,张郎中又新罢江南郡,素与李搆隙,事在别录。时于荆溪遇风,漂没二子,悲蹙之中,复惧李之雠己,投长笺自首谢。李深悯之,复书曰:“端溪不让之词,愚罔怀怨;荆浦沉沦之祸,鄙实愍然。”既厚遇之,殊不屑意。张感铭致谢,释然如旧交。与张宴饮,必极欢尽醉。[1]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9页。
张又新、李绅都为唐宪宗元和年间的进士,但二人以前有嫌隙仇怨,张又新没想到在自己既丧子又罢官非常倒霉的情况下还被贬谪到了李绅的管辖地,他担心对方报复自己,于是写信向其道歉,没想到不但得到了李绅的痛快谅解,两人还由此成了朋友。文人之间的“平等”交游,是中唐社会的风俗之一,因白居易与元稹的密切交往甚至影响到了中唐的诗风走向,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中对此有详尽阐释。可以说,文人之间的这种“风雅”相交,是古典文化史上一道绚丽景观。
第三,不仅尊重女性,亦尊重零落江湖的僧人、道士。上文已经论述《本事诗》有性别“平等”意识及两性文明视域。“宫女题诗”题材,以女性为主体,是女性能突破人生极限追求幸福并最终赢得命运垂青的题材,有着一定的开创意义。最让人称道的是,孟启的宏大视域还拓展到了“江湖”,《本事诗》“高逸”类第二则故事就选取了杜牧与一位无名僧人的事迹,别有趣味。《本事诗·高逸第三》载:
杜舍人牧,弱冠成名。当年制策登科,名振京邑。尝与一二同年城南游览,至文公寺,有禅僧拥褐独坐,与之语,其玄言妙旨咸出意表。问杜姓字,具以对之。又云:“修何业?”傍人以累捷夸之,顾而笑曰:“皆不知也。”杜叹讶,因题诗曰:“家在城南杜曲傍,两枝仙桂一时芳。禅师都未知名姓,始觉空门意味长。”[2]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5页。
杜牧弱冠登科、名动京城,经常与同榜进士一起郊游,没想到在文公寺竟然遇到了一位“玄言妙旨,咸出意表”的高僧,杜牧拜服的同时作诗一首,一句“始觉空门意味长”感叹佛门的博大精深。此诗清人编撰的《全唐诗》收录名为“赠终南兰若僧”,除个别字词有出入,意蕴相同。此则故事寥寥数语,对比诗人此时境遇的“喧闹”,僧人“不知”红尘俗事的“寂寂”,反衬出江湖漂泊人士的闲适高逸,世外高人的气韵蓬勃而出,竟然引得了春风得意的青年士子追慕。除了对僧人人生境况的肯定,孟启还描述了道士的传奇。在《本事诗》“征异”类第三则故事,描述了大文豪韩愈及文友们与一位叫轩辕弥明的老道士的“石鼎联句”雅事,老道士突出的诗才、怪异的形貌,让在座宾客“无不叹异”。孟启从美人到僧人、道士的事迹选取,都有着“平等”的视域,《本事诗》这种别具一格的品鉴方式值得肯定。
此外,孟启《本事诗》关涉的诗人,遍及初盛至中晚唐,如初唐有李峤、苏味道;盛唐有李白、杜甫;中唐有元稹、白居易;晚唐有杜牧,等等。这种文学史的“诗史”格局,奠基了其诗话人物的“平等”视域。尤为值得肯定的是,这种视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我国古典文化对帝王将相、博学鸿儒的“神化”“圣化”传统,以“情感”为本位,从帝王将相到普通士子进而到美人僧道,一视同仁。因此,孟启《本事诗》兼有文学批评史与文化史的双重意义。
结语:“尽是人间第一流”
“本事”见性情,“诗话”载风雅,面对命运无常的人间惨剧,孟启的《本事诗》常常希望借助“灵异”之笔来主持公道,如其“征异”篇的“鬼母题诗”“落魄文人马相植月下古寺听白衣人吟诗”等,都充满了传奇色彩。这些故事的背后,是诗话编撰者悲悯之心的体现,具有深刻的人文关怀。尤为值得肯定的是,《本事诗》诗话评论主体“平等”的女性观,面对残酷的社会现实亦能借助作为雅言的诗歌,彰显心曲,发掘女性风采,这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我们应该看到,不同于传统儒家以“德行”为本位的人物品评,《本事诗》以“性情”为本位的评鉴准则,传递了古典风流人物的性格底色,呈现了中华古典文化的风雅流韵。“尽是人间第一流”[1]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卷95、第2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067页。,出自北宋诗人钱惟演的《赋竹寄李和文公》,他认为瘦竹、清秋、仙鹤都是人间第一流的景物,才性卓然的诗人、风骨溢人的美人、磊落闲适的僧人道士以及成人之美的王侯将相又何尝不是人间第一流的景观?诗话中的传奇故事,在一定程度上能消解现实世界的残酷与不公,能为善良的人们构筑一座不朽的心灵丰碑。《本事诗》的“本事批评”表明,诗话中有第一流的故事,故事中有第一流的人物,而人物又有超出俗流的风采。古典人物的这种“真性情”风雅,是古典文化注重生命书写的本来面目,更是中国古典文评的一道独特景观。
由上所述,孟启诗话视域下的人物风雅书写,可以归结为三点:一、人物的“幽默”是语言艺术的至高标准,而“嘲戏”般的“幽默”建立在对人性底色的深切认知之上。当“嘲戏”的对象是皇亲国戚等当权者时,用诗歌的雅言形式来表达内心的愤懑不满也更能彰显主体不卑不亢的文人气度。二、只有“性情”本然,才能超出俗流。众美至情至性的背后,不得不面对命运被权力操控的无力感,正是这种无力感,才显得抗争更为可贵。三、孟启诗话品评的“平等”视域,更有助于呈现人物的风韵风雅。总之,诗人、美人不畏权贵的意识,勇毅果敢的性情,以及诗话品评者的“平等”视域,最终成就了古典人物的风雅风采,这才是“本事批评”的底色,更是中国古典文评的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