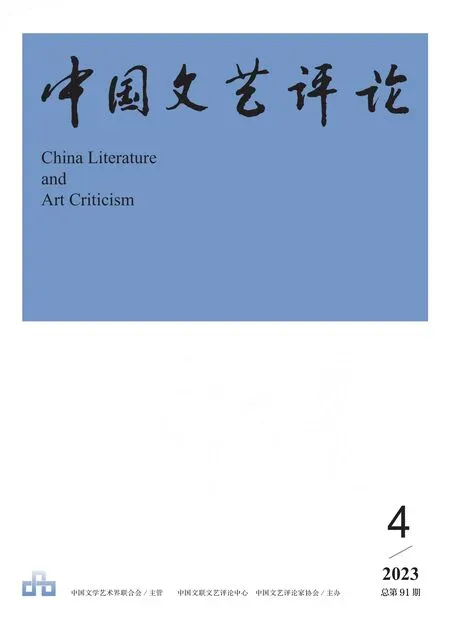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中国文艺的历史语境
■ 何中华
把握当代中国文艺的未来走向,就不能不回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所建构的特定历史语境。文艺与时代的关系是一个历久弥新的问题。在今天,这个问题必然有其特定的历史内涵。本文基于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时代背景,就中国文艺及其未来发展所面临的几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提出几点初步看法,以就教于学界。
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及其历史意蕴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其基本特点可以从多角度加以把握。限于本文主题,这里不能面面俱到地提出系统看法,仅就其中某些有限的方面予以探讨。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无疑包含着现代化的一般规定,但同时又有其中国特质。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社会所特有的经济条件、政治条件和文化条件,亦即中国的具体国情。作为“路径依赖”,它规定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独特性。我认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有两个方面的特点不容忽视:一是中国传统文化构成现代化需要扬弃的东西,但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其优秀因子又成就了中国式现代化所特有的文化优势;二是中国作为东方大国,其现代化过程事实上是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结果,因而选择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构成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一个突出特点。
在一定意义上,所谓现代化也就是告别传统。就此而言,传统文化无疑是现代化的一个阻碍因素,是消极的角色。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其实,传统文化同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并非机械地断裂,而是辩证地扬弃。当现代化在后现代语境中暴露出内在局限时,传统文化经由现代化本身的中介和激活,又构成现代化自我矫正赖以借鉴的重要资源。对于中国来说,现代化所带来的革故鼎新,并未妨碍中华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始终保持自我同一性。传统文化依旧是这一主体性角色的原初塑造者。同时,传统文化资源对现代化本身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能够发挥补偏救弊的积极作用。应该说,同“五四”时期相比,我们今天审视传统文化的视角和参照系无疑是更加深邃了,它已经超越启蒙视角所固有的历史囿限。随着现代化的内在矛盾及其带来的困境日益显露,传统文化的积极价值逐渐显现出来。它在现代化语境中被遮蔽掉的积极意义,到了后现代维度反而获得了重新彰显的契机。总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固然包含着现代化的一般规定,但它同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特有的国情是无法剥离开来的。这种“中国性”,使中国的现代化打上了深刻的中国烙印,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现代化异质于西方现代化的特征。
此外,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特殊性,还取决于马克思晚年提出的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所昭示的东方路径。从历史内涵看,中国式现代化的实际过程,也就是对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跨越”过程。在马克思所谓的“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来临之后,正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亚细亚特征,使中国对“卡夫丁峡谷”的能动跨越既成为必要,也成为可能。马克思当年的设想既揭示了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为特征的东方社会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同时又以移植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果”为条件。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实践表明,我们在实际的发展中,一方面实现了“跨越”,另一方面也实现了“移植”。如果说在一个落后的东方大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完成的是“跨越”,那么把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体制有机地结合起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成的则是“移植”。从文化的角度说,这一历史过程体现着现代与后现代双重维度的“叠加”。按照唯物史观的观点,资本主义及其市场逻辑构成现代化的世俗基础,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性“跨越”,则体现着“后现代”维度。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无疑是以扬弃的方式包含着西方现代化规定,但它又不同于西方式现代化道路及其特征。在一定意义上,这种异质性典型地表征为现代与后现代的交织和重叠。这一方面取决于中国作为东方社会,其文化及其传统在某种程度上避免了西方式现代化的弊端和局限,具有预防性的免疫作用;另一方面取决于中国社会对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实际跨越,因为这意味着现代化理念的扬弃,使中国式现代化带有文化上的后现代性质。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定语境中,现代化理念并非以纯粹的形式独立存在的,而是以扬弃的方式被包含在了后现代维度之中。因此,中国的后现代境遇同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有其本质的区别。在西方,后现代与现代之间存在着历时性的转换,最终陷入虚无主义窠臼;在中国,后现代与现代几乎是同时呈现,不是虚无主义的,而是建设性的,是向未来敞开着的。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所建构的历史语境,为中国文艺繁荣发展注入了时代内涵和历史的规定性。就此作出一种可能的解读,对于恰当地看待中国文艺的未来走向和选择无疑具有某种启示意义。
二、中国式现代化呼唤史诗般的作品涌现
如果说哲学是时代精神的反思性把握,那么文艺则是时代精神的审美把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意味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愿景的实现。从历史的长时段看,这无疑是一个划时代的转折点,其历史意义怎么估价都不过分。伟大的时代必然呼唤伟大的作品。作为中华民族正在完成的一项前无古人的历史伟业,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功,内在地要求文艺创作产生出一大批足以与之相匹配的作者和作品。无论从时代性还是从民族性角度看,中国式现代化都具有独一无二的性质。关于欧洲的文艺复兴,恩格斯曾说过:“这是人类以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次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激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61-262页。所谓“巨人”当然包括文艺巨擘。中国式现代化的意义,完全可以同文艺复兴相媲美。因此,它同样是一个需要巨人的时代。当代中国文艺不能辜负这样一个时代,它需要产生史诗般的作品,书写中华民族的心灵史,以便为这个时代“立传”。优秀的作品,其内涵必将是厚重、深邃和耐人寻味的,因为它积淀并浓缩着一个古老而智慧的东方民族的苦难史、奋斗史和复兴史。作为这一曲折、跌宕而又辉煌的历史的美学表达,它既是一个民族历史步履的见证,又是一个民族开启未来的昭示,从而能够使我们在现代化的狂飙突进中驻足反思,在迎接未来的挑战中获得深刻启迪和有力鼓舞。
诚然,对于文艺创作及其作品作一种庸俗的社会学解释是不恰当的。在这方面我们曾经有过深刻的教训,但不能因此就否认文艺构成时代的审美之维和审美之镜。因为文艺创作者的“此在”(Dasein)性,总是浓缩并折射着特定的时代精神及其历史内涵。正如丹纳所言:“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这是艺术品最后的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因此,“精神文明的产物和动植物界的产物一样,只能用各自的环境来解释。”[1][法]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第7、9页。曼海姆也认为:“艺术史已相当确定地表明,艺术形式可根据其风格而确定其时期,因为每种形式只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才有可能,并且它还揭示出那个时代的特征。”[2][德]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黎鸣、李书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76页。其实,这也是唯物史观早已承认并主张的基本观点。在唯物史观看来,文艺创作及其作品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修辞,属于上层建筑,它归根到底受制于特定的社会存在。因此,文艺不可能脱离或超越所处的时代,而总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文艺的这种历史制约性,是回溯性地把握所必须正视的一个基本事实。一方面,一切真正伟大的文艺都蕴含着永恒的母题,即对人性及其张力所作的审美观照和把握;另一方面,文艺的母题又总是带有时代特征,呈现为特定的历史形式,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会以某种特有的方式得以表达。一个文艺家无论怎样在主观上试图超脱时代的约束,割断与时代的勾连,回到纯粹“自我”也好,表达纯粹“个性”也罢,其作品依旧无法逃避时代的制约。问题仅仅在于,这种制约在文艺家那里究竟自觉与否,这无疑会影响到实际的审美创造,但制约本身却是无法否认的。
英国作家奥威尔坦率地承认艺术同政治的勾连,认为两者无法剥离。他说:“没什么书真正地不受政治偏见的影响。艺术与政治毫无关系这种观点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观点。”[3][英]乔治·奥威尔:《我为什么写作》,刘沁秋、赵勇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46页。他甚至认为:“一个人越是意识到自己的政治偏见,他越有机会在不牺牲自己的审美追求和文学忠诚的情况下演绎政治。”[4]同上,第248页。基于个人的写作经验,奥威尔说:“回过头去翻检我的所有作品,我发现,在我缺乏‘政治’意图时写的都是一些没有生命力的东西,它们成了一些华而不实的段落、没有意义的句子,准确的形容词和连篇假话,事实就是如此。”[5]同上,第250页。人在一定意义上乃是政治的动物,这从存在论层面上注定了人的一切活动,包括审美创造活动,归根到底都不能不带有某种政治含义。文艺创作的叙事方式当然是多维度的,既有宏大叙事,也有微观叙事,以至个体性的私人化叙事。但它们都以各自所特有的方式折射着时代精神及其内在诉求。中国文艺传统历来讲究“文以载道”和“诗言志”,即使是魏晋时期唯美主义的文艺思潮,也不过是当时的时代精神的反映。在此意义上,不存在超脱时代的文艺。不能要求所有的作品都变成直接反映时代的宏大叙事,但文艺的主流无疑应该担当这一历史使命。应该说,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这一点显得尤为突出而迫切。
三、在现代化语境中何以“诗意地栖居于世”
从历史的经验看,现代化的语境所决定的功利关系和技术统治的支配,使人的存在的审美维度被遮蔽。因此,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文艺何以为人们“诗意地栖居于世”开辟一种可能性,这成为一个需要回答的时代课题。
人类同世界打交道的方式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它包括真、善、美三个基本的向度。对此,康德的“三大批判”作过深刻的揭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也有明确的提示。马克思认为,作为人类掌握世界的一种可能的方式,艺术在本质上乃是审美的掌握。[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9页。海德格尔在援引荷尔德林所谓“诗意地栖居于世”时,暗示了审美关系对于人而言所具有的存在论含义。但是,在功利关系所主宰的格局下,这种存在方式是被扭曲或遮蔽的。马克思指出:“忧心忡忡的、贫穷的人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经营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独特性”;因为私有制的狭隘性,剥夺了人的审美能力,使人陷入“仅仅从外在有用性这种关系来理解”的局限之中。[2]参见[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7-88页。“美学”(aesthetics)作为“感性学”[3]作为“美学”一词的首创者,18世纪德国哲学家亚历山大·戈特利布·鲍姆嘉通用希腊语中的“aesthesis”一词来意指“感性知觉”(sensory perception),旨在创立一门基于感性知觉的关于美的科学。参见[美]M.M.伊顿:《美学讲演》,《美学研究》1988年第2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297页。,它所把握的对象在本质上是一个历史的规定。诚如马克思所言:“五官感觉的形成是迄今为止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4][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7页。现代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狭隘,以至于使“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感觉都被这一切感觉的单纯异化即拥有的感觉所代替”[5]同上,第85页。。如此一来,人们获得的不再是美感,而只是“占有”;对象也不再是美学的对象,而不过是“有用物”。因此,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说史》中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就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96页。
历史的经验教训使我们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发展的一个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它在一定意义上构成改革开放合法性的依据。事实表明,人为地消灭商品货币关系是危险的,它只能陷入马克思所批评的那种“粗陋的共产主义”。马克思强调说:“如果取消货币,那么人们或者会倒退到生产的较低的阶段(和这一阶段相适应的,是起附带作用的物物交换),或者前进到更高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交换价值已经不再是商品的首要规定,因为以交换价值为代表的一般劳动,不再表现为只是间接地取得共同性的私人劳动。”[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65页。这意味着两种可能性:一是人为地“取消”商品货币关系,它只能造成历史的倒退;二是通过历史本身的成熟来“取消”,即依靠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才能使生产“前进到更高的阶段”。前者是虚妄的,后者是真实的。历史的教训不可不察。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本身并不是目的,它只是历史赖以展开并完成自身的一个过渡环节。市场固然是有用的,但在时间和空间上又是有限的。“市场需要有它的地位;但市场也必须被界定在它的必要范围之内。”[2][美]阿瑟·奥肯:《平等与效率》,王忠民、黄清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55页。避免市场经济及其尺度的独断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它的优势所在。
从某种意义上说,以市场经济为世俗基础的现代化,其本身就意味着诗意的匮乏。世界一旦被纳入“为我关系”之中,就不可避免地沦为“有用物”。在一个资本逻辑主宰的时代,写诗变成一种奢侈。20世纪70年代,海德格尔在一首诗中说:“算计者愈急迫,社会愈无度。运思者愈稀少,写诗者愈寂寞。”[3]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下卷,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1264页。因为只有“运思”才是同“在”(Being)本身打交道,而不是同“在者”(beings)打交道。而只有同“在”本身照面,才能使人“诗意地栖居于世”。但现代化语境中的人所能够把捉的,仅仅是“在者”而不是“在”本身了。这正是海德格尔所批评的“‘在’的遗忘”的历史原因。也正因此“诗人”才会“寂寞”,因为功利关系剥夺了人们“诗意地栖居于世”的冲动和可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何以才能具有一种审美免疫力呢?这是中国式现代化向中国文艺提出的一个虽棘手却又必须回答的问题。
马克思曾经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把生产变成了科学的应用,而这种应用只有通过科学的物化形式即技术才能实现。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就说过:“自然科学……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但“它不得不直接地使非人化充分发展”。因此,对于人的存在而言,自然科学可谓是一把“双刃剑”。在马克思看来,由于“工业是自然界对人,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对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自然科学“现在已经成了真正人的生活的基础”。但是,另一个方面,它又不得不“以异化的形式”充当这种基础。[4][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9页。海德格尔也曾警告说:“技术越来越把人从地球上脱离开来而且连根拔起。”[5]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下卷,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1305页。启蒙精神及其建构的现代历史,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吊诡,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75页。
我们的问题是,在现代社会,审美方式在抵制人的物化命运的过程中能够并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从历史的终极目标来说,人“诗意地栖居”之来临,有赖于人的历史解放,亦即进入“自由王国”。但在当下,文艺只是作为职业分工的一个部门而存在,人的存在本身的审美维度,还只能在有限的条件下相对地达成。就此而言,当代文艺昭示了在现代技术宰制下的人类得以自我拯救的一条可能的路径。海德格尔指出:“技术之疯狂到处确立自身,直到有朝一日,通过一切技术因素,技术之本质在真理之本有(Ereignis)中现身。”在海德格尔看来,这种“现身”的场所就是“艺术”领域。他说:“由于技术之本质并非任何技术因素,所以对技术的根本性沉思和对技术的决定性解析必须在某个领域里进行……这样一个领域就是艺术。”[2][德]马丁·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孙周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36页。这个技术的艺术化方案,固然有其浪漫主义的局限,但不失为一种有限的解决。《庄子》有言:“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庄子·知北游》)这种“大美”,只有通过“因其固然”“依乎天理”所达到的“技—艺”的一致性才能实现。惟其如此,世界方能以其本真的状态自我绽现。这正是海德格尔之所以把“艺术”同“真理”内在地关联起来的缘由所在。离开了审美的态度,这种“大美”境界的开显便无从谈起。对于现代人来说,文艺创作及其作品并非是一种点缀或陪衬,而是建构我们的生存方式本身所需要的一个重要步骤,它构成我们最大限度地抵制功利关系和技术的宰制,以便在向物的沉沦中得以拯救的一种可能的路径。正是在这方面,中国文艺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是其应该担当的责任。如何在人的物化遭遇中葆有灵性,成为中国文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应该说,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制度优势,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有利条件。
四、文艺的美育功能对现代化偏颇具有矫正作用
从一定意义上说,理性精神作为使现代化成为可能的内在理由或根据,构成启蒙观念的实质。它意味着“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55页。。理性尺度所建构的主体是理性的自我。西方近代哲学的始祖笛卡尔提出的“我思故我在”,就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点。这种以肯定主体性为核心的理性精神,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逐步支配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理性的独断化造成了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失衡。科学作为理性精神最典型的文化形态,只能给出“是什么”的答案,却无法回答“应该如何”的问题。价值判断缘自另一个来源。在“重理轻文”的氛围中,教育模式和人格模式往往是畸形的。这也是现代化过程容易引发的危机。在这种危机中,审美教育的缺失尤为突出。因此,中国文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还肩负着美育的职责。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真、善、美都被纳入成就人的道德人格这一根本旨趣之中。因此,中国文化有其悠久而漫长的“诗教”和“乐教”的传统。审美创造及其产物,都离不开敦化德性和移风易俗的功能。这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突出特点,也是其优点。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东汉经学家包咸注曰:“思无邪,归于正也。”[1]程树德撰:《论语集释》(一),程俊英、蒋见元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85页。所谓“思无邪”,与《大学》所说的“诚意正心”内在相关,亦即王阳明说的“正其不正以归于正”[2][明]王阳明:《传习录》上,[明]陆九洲、王守仁撰:《象山语录·阳明传习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3页。之意。朱熹曰:“孔子之称思无邪也,以为《诗》三百篇劝善惩恶……其要归无不出于正。”[3][南宋]朱熹:《读〈吕氏诗记·桑中篇〉》,曾枣庄主编:《宋代序跋全编》卷一五五,济南:齐鲁书社,2015年,第4406页。又曰:“盖诗之言,美恶不同,或劝或惩,皆有以使人得其性情之正。”[4][南宋]朱熹:《诗集传》,赵长征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18页。不独《诗经》为然,其他的艺术形式也是如此。《礼记》曰:“乐者,通伦理者也。……唯君子为能知乐。……知乐,则几于礼矣。礼乐皆得,谓之有德。”(《礼记·乐记》)关于绘画,唐代张彦远说:“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发于天然,非繇述作。”他还说:“存乎鉴戒者,图画也”,“图画者,有国之鸿宝,理乱之纪纲。”[5][唐]张彦远撰:《历代名画记》,周晓薇校点,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2页。由此可见,绘画的道德教化功能十分明显。
在人的教养方面,审美方式无疑具有独特的优势。孔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包咸注曰:“兴,起也,言修身当先学诗也。”[6]程树德撰:《论语集释》(二),程俊英、蒋见元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682页。宋儒程颐诠释道:“诗发于人情,止于礼义,言近而易知,故人之学,兴起于诗。礼者,人之模范,守礼所以立其身也。安之而和乐,德之成也。”[7]《河南程氏经说》卷第六,[宋]程颢、程颐:《二程集》下册,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149页。这可谓是中国古代的美育思想之渊薮。清末民初之际,是社会大转型时期。此时的王国维特别强调美育可谓是有其特别用心的。王国维说:“美育者一面使人之感情发达,以达完美之域;一面又为德育与智育之手段,此又教育者所不可不留意也。”[8][清]王国维:《论教育之宗旨》,姚淦铭、王燕编:《王国维文集》第3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58页。蔡元培也有丰富的美育思想,他强调说:“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我之见,利己损人之思念,以渐消沮者也。”[1]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说》,《蔡孑民先生言行录》,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16页。蔡氏认为,美育对于人生境界的提升,实有其重要作用。他们对于美育的提倡,隐含着一个用意,即在现代化即将来临时寻找一种免疫性策略。今天,这依旧是一个有待完成的任务。对此,中国文艺责无旁贷。
一个人的健全人格,需要通过文化的全方位浸染和熏陶才能成就。在中国古代,人格的养成可谓是全息性的。例如,孔子就讲究所谓的“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但到了宋代,二程曾抱怨当时的教育路径越来越单调和狭窄,唯剩读书一途。这一教训值得我们警惕和借鉴。以《诗经》为例,程颐说:“如今所传之《诗》,[古者]人人讽诵,莫非止于礼义之言。今人虽白首,未尝知有《诗》,至于里俗之言,尽不可闻,皆系其习也。以古所习,安得不善?以今所习,安得不恶?”[2]《河南程氏遗书》卷第十七,[宋]程颢、程颐:《二程集》上册,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78页。程颢则云:“古人为学易,自八岁入小学,十五入大学,舞勺舞象,有弦歌以养其耳,舞干羽以养其气血,有礼义以养其心,又且急则佩韦,缓则佩弦,出入闾巷,耳目视听及政事之施,如是,则非僻之心无自而入。今之学者,只有义理以养其心。”[3]《河南程氏遗书》卷第十五,[宋]程颢、程颐:《二程集》上册,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62-163页。教育的方式越来越单一,失去了全方位的文化熏陶。这是当时宋儒面临的问题。此类教训值得深思。二程曰:“古之人,耳之于乐,目之于礼,左右起居,盘盂几杖,有铭有戒,动息皆有所养。今皆废此,独有理义之养心耳。”[4]《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一,[宋]程颢、程颐:《二程集》上册,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7页。又曰:“今之学者,唯有义理以养其心。若威仪辞让以养其体,文章物采以养其目,声音以养其耳,舞蹈以养其血脉,皆所未备。”[5]《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二,[宋]程颢、程颐:《二程集》上册,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1页。程颐曰:“古人有声音以养其耳,采色以养其目,舞蹈以养其血脉,威仪以养其四体。今之人只有理义以养心,又不知求。”[6]《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二十二,[宋]程颢、程颐:《二程集》上册,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77页。总之,人格的养成在古时是全面的陶冶涵泳,而今却仅有理义养心之一途。这是宋儒当年的慨叹。值得反省的是,在现代化的狂飙突进中,道德人格的养成对于中国文艺提出了怎样的问题?我们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又该如何回应这类问题?
五、文艺的民族品格是融入“世界文学”的优势
中国式现代化绝不是在一个孤立封闭的环境中实现的,恰恰相反,而是在马克思意义上的“世界历史”崛起的过程中实现的。其本身就是全球化的产物,同时又实质性地介入了全球化的进程。在一定意义上,全球化乃是现代化的当代形式,毋宁说是一种深度的现代化。这一历史语境,无疑对中国文艺的走向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以往的历史表明,市场经济在时空维度上的深化和拓展,对文化的民族性规定具有解构作用。马克思揭示了这一作用的历史形式,他说:“货币发展为世界货币,商品所有者也就发展为世界主义者。”因为“商品就其本身来说是超越一切宗教、政治、民族和语言的限制的”。它所造成的历史后果,必然是“随着同国家铸币对立的世界货币的发展,商品所有者的世界主义就发展为对实践理性的信仰,而与阻碍人类物质变换的传统的宗教、民族等等成见相对立”。[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142页。在某种意义上,全球化正是市场经济的广泛世界化的结果,它构成人类文化均质化趋势的经济基础和历史根源。在这一格局下,“民族性《is but the guinea’s stamp》[‘不过是基尼上的印记而已’]”。如此一来,在商品所有者眼里,“整个世界都融化在其中的那个崇高的观念,就是一个市场的观念,世界市场的观念”。[2]同上,第143页。
因此,全球化内在地蕴含着一种文化均质化趋势,它使得文化的地域狭隘性被日益突破。对此,马克思指出,随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6页。。歌德也说过:“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4][德]爱克曼辑录:《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113页。然而,这种趋势固然意味着现代化的进步所要求的抽象普遍性,但也蕴含着内在的可能性限度。这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从世界总体看,就像生物多样性一样,文化多样性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须臾不可离的绝对前提。但文艺创作及其作品若丧失了地方性风格和特点,就将遮蔽掉民族个性,从而妨碍文化多样性的有效维系。二是如果舍弃民族性维度及其文化传统,文艺作品就不可避免地沦为空洞的抽象形式,这样的作品必然缺乏丰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内涵,从而是肤浅和苍白的,无法具备足够的审美魅力。黑格尔说过:同样一句话,从孩童口中说出和从老人口中说出,其味道大不相同。因为后者浓缩了一个人一生的沧桑和历练,前者不过是鹦鹉学舌而已。三是民族的主体性诉求无法得到满足。正如索尔仁尼琴所说的,“晚近流行世界各民族齐一的说法,要在现代文明的冶炉里融化各民族间之差异。……在这儿可以恰当地说:民族性的消失,其祸患绝不亚于大家面貌相同,性格一样,无法辨认。民族性底差异乃人类之财富,是不同民族性格的结晶,即使是其中最小的晶体,亦有其独特的色彩。”[1][苏]索尔仁尼琴:《为人类而艺术》,崔道怡等编:《“冰山”理论:对话与潜对话》上册,北京:工人出版社,1987年,第412页。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语境中,格外需要自觉地弘扬中国审美的独特传统。中国艺术讲究的是表现、神似、写意,这迥异于西方自古希腊以来的那种以再现、形似、写实为取向的审美传统。中国的工笔画虽然貌似求在其“工”,这不过是表象,究其实质依旧不过是以真写意罢了。正如沈括所言:“书画之妙,当以神会,难可以形器求也。”[2][宋]沈括撰:《梦溪笔谈》,金良年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59页。即使是工笔画,追求的终究是意境,而非工整。这也类似于王国维对于“词”所作的解释:“词之雅郑,在神不在貌。”[3][清]王国维:《人间词话》,姚淦铭、王燕编:《王国维文集》第1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148页。以中国花鸟画为例,至唐代已趋成熟,越来越求其“工”。然而到了宋初,其风格有一大变。这便是徐熙的出现。与黄筌不同,徐熙的作品一反唐代以来的那种重形似和写实与铺陈,追求主观的意趣。“徐熙的花鸟画,虽然注意形似,可是他已不再拘于形似,只是假花鸟的形态,作个人生命之表白,所谓‘意出古人之外’,所谓‘神’且‘妙’,即指此点而言。徐熙实开了花鸟画的新境界。”[4]岑家梧:《中国艺术论集》,上海:上海书店,1991年,第58页。这与其说是开辟了新境界,不如说是向古典风格的复归更恰当些。书画同源,按照唐代张彦远的说法,“周官教国子以六书,其三曰象形,则画之意也。是故知书画异名而同体也”[5][唐]张彦远撰:《历代名画记》,周晓薇校点,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页。。而“书,如也。”[6][清]刘熙载:《艺概》,《刘熙载文集》,薛正兴点校,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87页。老子曰:“上善若水。”(《老子·第八章》)“若”字即相似,而非等价的关系,不是“是”;它构成象征和隐喻的基本结构。这种表征方式,归根到底源自《易传》所谓“观物取象”的方法。此所谓“象”,非抽象之象,乃象征之象。清季学者朱声骏说:“天地间有形而后有声,有形声而后有意与事,四者文字之体也。意之所通而转注起焉,声之所比而假借生焉,二者文字之用也。”[7][清]朱声骏:《说文通训定声自叙》,徐世昌等编纂:《清儒学案》卷第一百四十九,沈芝盈、梁运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5801页。王国维亦曰:“六书之字,作始于象形。”[8][清]王国维:《〈中国名画集〉序》,姚淦铭、王燕编:《王国维文集》第1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130页。这一传统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并在中国文艺的未来发展中继续发扬光大。
惟其如此,我们才有底气和资格在本土化与全球化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早在19世纪上半叶,德国思想家歌德就指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只有植根于本土、出自本国一般需要,而不是猴子式摹仿外国的东西,才是好的。”[1][德]爱克曼辑录:《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24页。20世纪80年代,画家吴冠中也说:“青年人……他们大都只想从此奔向美利坚和法兰西。……我看,真正想在艺术上作出世界性的贡献,那么他们还是要回来的。中国的巨人只能在中国土地上成长,只有中国的巨人才能与外国的巨人较量。”[2]吴冠中:《吴冠中文集》,成都:四川美术出版社,1989年,第406页。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决定了中国文艺一方面必须融入世界潮流,另一方面又不能以牺牲自主性地位为代价。否则,我们在审美创造上就无法给出“谁的现代化”,又是“为谁的现代化”之问题的答案,从而陷入现代化主体缺位的困境。这就应了那句老话:“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总之,以审美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以民族性的视角反映中国文化及其传统的独特个性,这不仅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需要,也是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需要。在以“世界历史”为基础的全球化的演进中,其深远意义必将逐步得以彰显。
总之,对于中华民族来说,中国式现代化无疑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历史伟业,是一次“凤凰涅槃”。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国文艺必将大有作为,也理应诞生不负时代的伟大作品。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现代化都有其特殊性的一面,也有其普遍性的一面,它总是包含着使现代化“是其所是”的一般规定,中国式现代化同样也不例外,由此决定了它所建构的历史语境,使中国文艺必须直面现代化进程本身带来的诸种问题。也正是在积极地回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一方面成就了中国文艺的创作本身,另一方面也使得中国式现代化通过中国文艺所提供的审美创造而趋于更加健全和完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