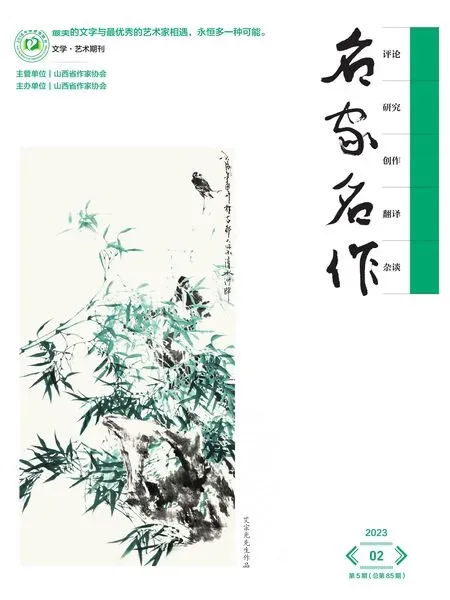《左传》晋楚三次大战的叙事艺术
余瑞欣
《左传》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叙事完整的编年体史书,记载了春秋时期二百五十四年间的历史。作为一部具有极高史学价值的文学作品,其既理清了史实又不失文采,所以《左传》晋楚三次大战的叙事艺术值得关注。
一、分叙法
分叙法,顾名思义,“以两文或两文以上叙两人两事,或同时或不同时,回互激射,以明是非功过之所在者”。一方面,分开叙述可使各要素得以明了,在复杂纷繁的历史叙事中颇有拨云见日之感;另一方面,将不同要素的同一方面逐个列出,有助于读者加以比较,从而对事物的发展方向有所把握。
分叙法虽为分述,但整体的合一性并未被破坏,从而保持了节奏感和审美平衡,这正符合中国“整体性叙事”的特点。在对战争的描述中,作者极其注重分叙时格局的比例平衡,善于从君臣关系、民众状态和战略制定等方面论述交战双方的情况,以小处见大局,条理清晰,缓急有致。晋国和楚国作为春秋时期的两个大国,各自盘势一方,二者的势力组成颇为复杂。在城濮之战、邲之战和鄢陵之战中,以晋楚为争霸主力,兼有其他国家的参与。《左传》作者“对叙晋楚二军,或通篇一线双行对叙”,将晋楚二国在战争中的状况一一明了。通过对城濮之战、邲之战和鄢陵之战的分析,可详细领会分叙法的妙处。
在僖公二十八年的城濮之战交战中,以晋国为主线,其叙述大致可分为两部分,上半部分主要叙述了晋国的谋略——文公为了能够有更大的把握战胜楚国以救宋,听从了先轸的“喜赂、怒顽”之策,用方与楚盟的曹、卫之田贿赂齐、秦二国,既争取到了中立的齐国和秦国,又让楚国不得不战。晋国君臣合力,以曹、卫为媒,分离楚国的联盟,争取到了中立的齐国和秦国,继而增强了战力。以易化繁,叙事功力之深可见一斑。下半部分主写战事,前一层始于交战之际前夕,叙述重耳之梦与请战之辞通过分叙晋楚二国的主将在战前的一谨慎一焦躁的态度,由此可知战后的成败走向。后一层则自“已巳”始,正式进入对交战场面的描写。相比晋国的翔实叙述,对楚国的叙述注重其特点——从开始就显现了情况的不乐观。开战前便出现了君臣相左,且并未得到及时解决,这一君臣矛盾贯穿了城濮之战的始终,是楚国败绩的源头。
在城濮之战的叙述中,详写晋国,特写楚国。在一晋一楚的分叙中,不但交代清楚了历史情况,同时还在对比中以示高下。
再者,在晋楚间的第二次大战——邲之战中,分叙法的运用更显张弛起伏的不同。楚围郑,晋救郑。未几,二国皆有一次进退之辩。
在晋楚大战的叙述中,或以晋为先,间以楚;或以楚为主,比之以晋。一晋一楚,运用分叙法起到了明情示理、回互相较的作用。晋楚二者内在的强弱、整乱、顺逆、合散之势,由此观之。分叙之详细明确,使得读者更易理解和接受战局的结果。与此同时,一晋一楚的格局对称协调,布局平衡舒缓,既不混乱也不显突兀,娓娓道来的叙述中显现出一种平和的美感倾向。分叙法因其利于描述宏大历史时空下的大规模事件,而被后世广泛模仿和沿用。
二、 因果叙事法
《左传》中对战争的记叙秉持着“实录”原则,在对史实的记录中也着重凸显历史发生的过程的因果必然性。
(一)重在战前,揭示原因
《左传》中除了杰出君王的文韬武略外,贤臣良将鼎力相助的过程也是其战争叙事着力描绘的部分。
首先,在城濮之战中晋国的贤臣也至关重要。郤縠兼备德义;子犯明礼信、知曲直,是为重卿;先轸在僖公二十七年便言“报施、救患、取威、定霸,于是乎在矣”。正是因为君臣辑睦,上下成谋,所以才能胜利。反观楚国,中军之帅子玉刚而无礼,成王无心应战。君臣不和,主帅独断。两国成败的原因揭示得非常清晰。
其次,在邲之战中,楚国的胜利同样离不开最高统治者的仁德。对外,宣公十二年楚国围郑之时,眼看楚国军队破城在望,只因楚庄王不忍郑国“国人大临,守陴者皆哭”,便果断退师。在“郑伯肉袒牵羊以逆”后,楚庄王不顾左右的劝阻,选择了“退三十里而许之平”。一位不分国界、心怀大爱的仁君的形象跃然纸上。
于内,楚庄王推行了一系列措施,从而达到了“德立、刑行、政成、事时、典从、礼顺”的境界。有这样一位领导者,楚国在邲之战中的问鼎也就不足为怪了。而此时的晋国,中军之将桓子方才上任,无甚威信;先縠刚愎不仁,独断专行;其余将士晕头晕脑,不知所适。由此观之,在开战前,晋胜楚败的基调就已经定下了。
《左传》通过对人事方面的因果分析,突出了历史中道德因素的重要性,阐明了道德善恶对历史走向的影响。同时,借此宣扬了鲜明的仁政德治思想,证明了“仁德尚义”的重要性,以警诫后人。
(二)轻描战中,简不失精
《左传》中的战争交战过程向来比较简略,但在篇幅不多的交战场面描写中,却能极尽神来之笔,勾勒出人物特色,屡屡有点睛之处。
在城濮之战中,晋国狐毛、狐偃带领上军,对抗子西率领的楚国左师;先轸、郤溱带领中军,对抗子玉率领的楚国中军;栾枝、胥臣带领下军,对抗由陈、蔡二国组成的楚国右师。二军交战只寥寥数句就结束了,但晋国“虎皮蒙马”和“曳柴伪遁”的计策却让人眼前一亮。
在邲之战中,有几处战间片段描写得尤为精彩:“晋魏锜求公族未得,而怒,欲败晋师。请致师,弗许。请使,许之。遂往,请战而还。楚潘党逐之,及荧泽,见六麋,射一麋以顾献,曰:‘子有军事,兽人无乃不给于鲜?敢献于从者。’叔党命去之。”
魏锜被潘党追赶,在此间隙中竟然还能“射一麋以顾献”,可见魏锜的技艺高超和志勇过人。同为“二憾”,赵旃也不失个性:“赵旃以其良马二济其兄与叔父,以他马反。遇敌不能去,弃车而走林。逢大夫与其二子乘,谓其二子无顾。顾曰:‘赵叟在后。’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于是。’授赵旃绥,以免。明日以表尸之,皆重获在木下。”赵旃在逃脱过程中,将好马让给叔父和兄弟,自己则遇敌被困,其举可嘉;而逢大夫弃二子以救赵旃的举动,更是令人感动。
这些战争片段的描写,不但用三言两语揭示了战争的残酷与多变,更是借此笔触点化出了众多人物其独特的个性特点,令人耳目一新,读之难忘。
(三)战后处理,极具意义
《左传》的战后处理不但是对胜负结局的补充,更是对道德因由的呼应。《春秋左绣》中有评:“左氏文大抵首尾相配,此独上下回绝,尽文格之变,然其脉络抑何融以密也。”因果相应,前后相照,浑然一体,这是《左传》的叙事魅力所在。
在城濮之战中,《左传》作者以晋国之胜宣扬德政。晋文公胜而不骄,终于在城濮之战中一战而霸;晋臣先轸、栾枝等贤良同心同力,一心为国。故《左传》认为晋国胜在“能以德攻”。而楚国子玉无爱人之德,虚浮自负,贪财好物。他不听楚王劝告,白白葬送了申、息子弟的性命,唯有自戕以谢罪。
在邲之战中,楚庄王厚积薄发,终于使得晋国成为手下败将。他的眼光突破了历史时空和个人得失的局限性:战争旨在安民平乱、立威和众;修筑京观意在警戒,绝非自矜。
在鄢陵之战中,楚国再次败于晋国。鉴于城濮之战中的子玉自戕,楚共王不愿看到子反自责过深。可惜与子反不和的子重出言相逼,在子重的一再逼迫下,子反答之以“虽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侧,侧敢不义?侧亡君师,敢忘其死”后而卒。楚国重蹈覆辙,继城濮之战损失子玉后又失子反,自此逐渐退出了中原争霸的主力阵营,渐渐趋于颓势。由此可见,爱民之德不仅限于普通的民众,也包括犯下错误的臣子;宽厚好德不仅来自统治者的胸怀,也包括同僚间的理解与包容。
战争既是政治矛盾的外现,也是人性碰撞的暗影。除了对人文因素的促进之外,因果叙事亦有“由行为自身之因果关系,证明善恶在历史中应得的劝惩”的作用,其既使得历史事件叙述合理化,也是文学自觉性的滥觞。
三、 预叙法和补叙法
预叙法是在事物发展前的叙述方式,大多是一语成谶,充满了“天命不可违”的宿命论色彩。补叙法是“对已发生之事的事后追忆,以完善事件的整体性”。《左传》通过预叙法和补叙法,既增强了文本的可读性,又完善了文本构成,体现了人文因素在文学发展中的不断增强,从而推进了宏大历史叙事的进一步发展。
(一) 瞻望前景的预叙法
《左传》的预叙具有人文色彩的文学性。《左传》中预叙的应验,一方面基于历史发生的逻辑,另一方面出于对“实录”原则的遵循和教诲后人的需要,预叙的事情大多都得以应验。
《左传》中对战前场景的描述,有诸多臣子的个性描绘及其相关的谏言和劝告,他们在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军事状况后,做出了对战争结果的预测,因而这种预测往往是客观正确的。
在城濮之战前蒍贾认为子玉其人刚而无礼,“过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预言了子玉带兵必败的结局,而城濮之战的败局也证实了蒍贾之言。在邲之战前,士会就楚国的讨郑之举和国内情形做了一番评价,认为其“不可敌也,不为是征”。在晋郑两国相会时,栾武子又言楚国内政清明,军队有备,子良与师叔二质皆为贤良,故楚不可克。
《左传》中的预叙多阐明因果报应的过程,从而“内在的伏应关系使因果顺序得以展开”。在此过程中,宣扬了积极的道德因素对历史发展的重要性。它不但以设置悬念的方式吸引了读者,还启发了后世文学的发展,尤其是小说中预叙的运用。
(二) 缀之于后的补叙法
春秋时期各国混战,诸事繁杂,为了将来龙去脉展现清晰,使文本的完整性得以提升,补叙必不可少。《左传》中的补叙之事皆为确定发生的、围绕叙事中心的篇章。
在城濮之战中,子玉梦河神一事既是对其战败之果的呼应,也起到了完善前文结构的作用。通过子玉在战争全程中所展露出的个性,得以窥见其全貌。其人不仅自大之极,而且吝啬财物。一个自私自利、不懂取舍、不善国事的令尹形象由此得见全貌。相比之下,对晋国战后处理的补叙则进一步解释了其取胜的合理性。晋国中军在大泽时,司马杀了违反军令的祁瞒;回国后,杀了违反军令先行回国的舟之侨。晋国君臣各司其职,陟罚臧否张弛有度,故《左传》作者赞之“惠此中国,以绥四方”。
在邲之战中,晋楚两国间的冲突缘于郑国。楚王围郑,而晋救之。乍看之下,郑国作为小国,在晋楚的夹缝间求存,处境着实艰难。而实际上,却非如此:郑国并非因受强权压迫而至困,却是源自内政之乱。因此,在郑国杀了鱼臣和石制后,君子评之曰:“史佚所谓‘毋怙乱’者,谓是类也。”《左传》作者对此事的补叙说明,表明了其对小人作乱的鄙夷之情。
在鄢陵之战的交战过程中,补叙了有关晋楚二国的善射名将的轶事:在甲午的前一日,潘党与养由基比赛射箭,二人所射之箭皆穿透了七层皮甲,但楚王以“不尚智谋”为由,斥责二臣“大辱国”。养由基因此在第二日的交战中不能及时射箭,以至于楚王痛失一目。养由基射箭技艺之高超,达到了所射尽死的境界;但其被禁,在无形中使楚国减损了战力,这也为楚之败局做了铺垫。
《左传》中补叙法的使用,补足了主线情节之外的支线剧情,在丰富了主要人物角色的同时,勾画出了众多小角色,从而完善了整个事件的发生过程。同时,补叙亦打破了叙述者作为全知者的绝对视角,从而加入了更加丰富多样的个体意识,将《左传》的历史时空变得更为宏大广阔。
“《左传》之叙战,在提供经验教训,作为后世之龟鉴。”在晋楚两国间的三次大战中,《左传》作者主要通过分叙法、因果叙事法、预叙法和补叙法阐释春秋笔法中的微言大义,进而宣扬德义与仁政的思想主张。
分叙法将战争中的各方要素加以明晰,在阐述说明中暗含对比;因果叙事法在探求不同历史层面的逻辑因果时,将史德与史实串为一体,进一步阐发了春秋大义的内涵;预叙法和补叙法完善了宏大的历史叙事,多角度、全方位地展开对宏大场面的叙述。
《左传》作为先秦叙事散文的最高峰,其建立的叙事范型被后世不断地发扬,从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结构特征和叙事倾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