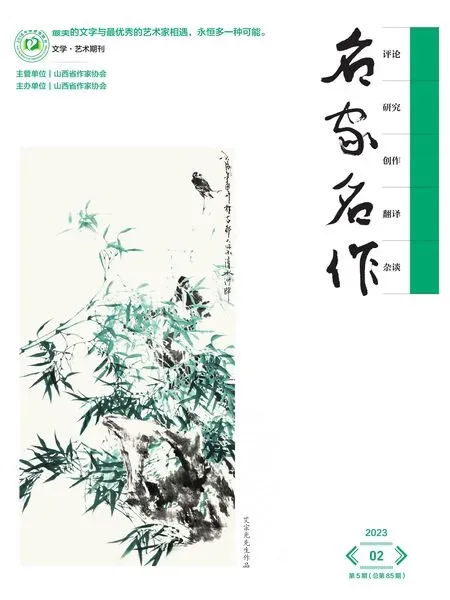论苏童《米》的人性叙事
——以织云和绮云为中心
王 一
一、引言
在格非的《欲望的旗帜》《敌人》、孙甘露的《访问梦境》、叶兆言的《枣树的故事》等多部小说对人性、历史、欲望进行书写后,鲁枢元总结其为文学的“向内转”,即“从人物的内部感觉和体验来看外部世界,并以此构筑起作品的心理学意义的时间和空间。小说心灵化了、情绪化了、诗化了、音乐化了”[1]。苏童的《米》深入人性结构的内部,对人性中潜在的层面进行描摹,不断在关于欲望的隐喻和“突破口”中呈现生命的真实状态。小说《米》围绕织云、绮云等人物之间发生的有关欲望、财富、罪恶和死亡的沉痛故事,将人性的纵深彻底暴露给人看。在苏童的书写中,人物总是陷于充满种种暗喻的巧合旋涡中,无法摆脱命运的沉重,在诸多突发性因素的合力下展现了人物命运与历史情状的复杂纠葛。
以往的研究以《米》的伦理情境阐释、细节败笔分析等方面为主,本文则以《米》中织云和绮云所展现的人性维度为切入口,揭示苏童是如何在小说中“以女性美艳的衰颓、个人生存境遇的沦落和凄楚、对外在世界的反抗”[2]构成叙事的情境,考察小说所表现的在“人情世情的冷暖、新欢与交恶的变奏”[3]下个人的命运与时代的不可兼容性,并探究苏童是如何描摹人“身陷深渊绝境之中而不自觉的意识状态和行为方式”[4]的。
二、织云:女性困境
苏童笔下的女性往往是在性格上阴暗扭曲、在精神上承受着压抑、在命运上具有宿命般的悲剧性。织云作为《米》中极富特色的女性形象,其性格中有着对贫苦人民的同情与怜悯、对个性自由的张扬与放纵,同时也体现出对权势和地位的迷恋与追求,以及扎根于其心灵深处的传统封建观念。
初见五龙时,织云惊骇于他宛如死人般青灰的脸色,“你要是有病可别站这儿,我最怕染上天花霍乱什么的”[5]。而听到五龙解释自己是过度饥饿的缘故,织云却能慷慨地施予其一碗米饭,成为五龙逃亡途中第一个对他伸出援手的人。赴宴归家的织云发现露宿在米店门口的五龙,她也是发自内心地怜悯五龙的遭际,“就让他睡这儿吧,没家的人多可怜”[6]。长期浸染在瓦匠街冷漠残酷、麻木自私氛围中的织云,依旧能留有一颗怜悯的心。她同情五龙无家可归的经历,给予五龙微末的温柔和善意。她不像冯老板和绮云那样为了一碗米饭斤斤计较,反而让五龙“别理这些吝啬鬼,能吃几碗就吃几碗,哪有不让人吃饱的道理”[7]。织云在凛冽的冬季细心地发现五龙脚上穿着的是破胶鞋,便主动带他上街买了一双能够抵御寒冷的帆布面的棉鞋。苏童以一种“历史勾兑法”[8]展现出织云的故事。她的行为选择并不能被简单地定义为高尚,却在时代的残酷与冷漠下展示出些微人性的光辉。
同时织云又是一个泼辣大胆、放荡不羁的人。宴会上六爷不需女客陪坐,织云口无遮拦道:“谁稀罕陪他?我还不愿意坐他边上呢。”[9]六爷在瓦匠街是有权有势的恶霸,几乎人人都对其敬而远之,但织云的言语一方面暴露出她的泼辣大胆和无遮无拦,另一方面展现出当时她颇受六爷的宠幸,恃宠而骄,过着富足又虚荣的生活。面对冯老板将米店大门锁死不让其回家,织云的反应则是在门外大喊大叫:“我只是在外面玩玩,又没去妓院当婊子,为什么不让我回家?”[10]见父母置之不理,织云便“爬到了柴堆上窸窸窣窣地抽着干柴”[11],“喊着爹娘的姓名说,你们再不开门,我就放火烧了这破米店,顺便把这条破街也一起烧啦”[12]。她叛逆而放纵,忠于虚荣享乐,不顾旁人的闲言碎语,从十四岁起便心甘情愿地做了吕老板的姘头,以出卖肉体作为生存的资本,甚至骚情勾引阿保和五龙。哪怕阿保最终因此而丧命,她也没有流过一滴眼泪。“这世道也怪,就兴男人玩女人,女人就不能玩男人……老娘就要造这个反。”[13]这一突破世俗道德规范的想法体现出织云本真的欲望,以及人性中的多种可能性。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在“禁欲主义”盛行的时代,织云敢于追逐“本我”,即“原始的自己,包含生存所需的基本欲望、冲动和生命力”[14],但她依然没有挣脱时代的枷锁,而存有深刻的封建传统价值观念。浓重的封建男权文化一直笼罩在织云的世界中,这也是造成其人性扭曲和悲剧命运的罪魁祸首。当她嫁给五龙后,曾经隐隐萌发要与五龙安稳生活的念头,面对五龙强烈的报复行为,她劝道:“我嫁了你,你娶了我,我们认命吧。”[15]后她又选择投奔六爷做第六房姨太太,自私地将绮云的命运交付于五龙,理直气壮道:“你也该要个身强力壮的男人帮着撑持店面。”[16]织云对情爱的追求以及她所受的封建思想的束缚,在小说中叠化在一起,呈现出人性的悖反,以及历史、生命和社会力量的交相为用。
苏童说:“在很多时候她们有作茧自缚的选择……我们一直觉得是封建礼教、男权主义压迫着女性,但女性自身的问题(或者说是弱点)怎样导致了自己的悲剧,这是我感兴趣的问题。”[17]织云日渐走向毁灭的终局,便与其自身欲望的强烈和虚荣心的驱使密不可分。从第一次接触六爷,她便忘不了六爷那双滑过自己腰间的手。“她喜欢六爷代表的另一个世界,纸醉金迷的气氛使她深深陶醉”[18],这种虚荣的生活被她视为一种莫大的荣誉和骄傲。她的自轻自贱有时并非出于无奈,更多的是一种主动选择。织云主动选择了曾经抛弃她的六爷,“我跟着六爷总比跟着五龙强,六爷有权有势,我不能两头不落好”[19]。但她却遭到了六爷的唾弃和吕公馆上上下下所有人的歧视,多年来受尽嘲讽,“红颜青春犹如纸片在深宅大院里孤寂地飘零”[20]。苏童小说中的女性在面对世俗利益时,常缺乏理性思考,而更愿意追逐现实利益,最终陷入无处可退的人生绝境。“宿命的原罪”,贯穿于苏童“所窥视到的历史中。由此,性与暴力,不是一个外在的故事要素,而是根源于人类本性的欲望,在他的作品中获得一种形而上的历史动力的含义。苏童以对历史的这种洞察,颠覆了20 世纪理性主义衍生出来的历史观;或者说以对人的欲望本能的发现,补充了阶级论的历史观”[21]。当我们理解了织云的行为逻辑的时候,就能看到苏童是如何对权力、欲望、伦理等命题展开书写的——摆脱了强调历史潮流、忽视个体声音的传统历史小说的创作手法,对被欲望裹挟的迷茫的生命情状进行描摹,对时代与生存的本质要素和逻辑内核进行呈现。
三、绮云:思想枷锁
张清华曾说:“《米》是将历史分解为生存、文化和人性的内容的一部杰作。它异常细腻和感性地解释了种族文化心理和生存方式的互为因果的关系。”[22]事实上,苏童的思考并不止于种族文化心理层面,更多的是探究人物灵魂的多重轨迹,提取人物内心深处的人性“公约数”。如果是织云是沉沦、纵欲的象征,那么绮云身上则具有清高、封建的色彩。绮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受着五龙的性挑逗,她为此怀着深深的厌恶。她想尽各种办法来保护自己,防止五龙对她的“玷污”。她惯常地怨天尤人,埋怨命运的不幸和上天的不公,冯家的一切都不能不使她感到恶心。但这些反抗和埋怨都没能改变她的命运,一开始誓死不从的绮云最终还是向生存的困境低头了。她呜咽着将不幸归咎于自己的父母,“爹,娘,你们把我坑苦了”[23]。她色厉内荏,难以逃脱封建男权文化的樊笼,“也许我只好嫁给他了,嫁给他,嫁给一条又贱又恶的公狗”[24]。绮云身上既展现出人情的空缺、欲望的遏制、人性的压抑以及困厄中的反抗,还呈现出“对生命的委琐、存在的文化病态满怀疑虑和惊悚”[25]。等级观念、男尊女卑等思想在绮云身上根深蒂固地延续着。因冯家第五十四代没有男丁,绮云决定让五龙以“冯五龙”的名义在家谱中补上这一空缺,“他好歹是个男人,我的名字不能写就写他的吧”[26]。族谱的修缮“意味着对社会秩序、家族的成功与荣耀的重视”[27]。女性不得入本家族谱,不仅呈现出男权社会的阴影,也体现出女性地位的卑微。绮云长期浸润于封建传统思想的洗礼,深切认同并执行“女性不得入家谱”这一思想。但当五龙患上致命的花柳病时,绮云想做的是立刻找出冯家的家谱,把五龙的名字从家谱中剔除。她情愿让冯家的第五十四代空着,也不能让五龙的名字玷污这个清白了几个世纪的米店世家。她认为家族的清白远远高于男人的存在,因而她最终选择亲手斩断五龙和冯家千丝万缕的关系,以此告慰父亲和列祖列宗不安的亡灵。
如斯艾蒂所说:“不能只把男性看作唯一的压迫者,妇女也可以被看作压迫者的同盟,并有可能成为最主要的压迫者。”[28]如果说苏童对男权阴影下女性形象的描写着重呈现了封建文化消极的一面,女性的人性和命运悲剧带有一种无奈与被迫的意味,那么苏童对于同性之间关系的考量则更多暴露了女性自身的人性弱点和价值缺失。在小说《米》中,绮云和织云是一对亲姐妹。然而,她们相互对立,见面就吵,连冯老板也毫无办法。织云处处风流,像防贼一样防着自己的妹妹绮云。而绮云一向自视甚高,从小鄙视姐姐:“你当你是什么东西?你就知道跟臭男人鬼混,臭不要脸的贱货。”[29]在苏童的小说中,女性个体的生命历程往往呈现出一种宿命的“常态”:“在一种被压抑、被控制、被奴役、被改造的状态下”展现生命的颓废和衰败,“时间的进展过程所带来的却是身不由己的衰废,不论是身体、家族、朝代都是因盛而衰”[30]。“驳杂的生存空间是她们的共同特点,该空间在某种外力的作用下便会瞬间坍塌,自我无法逃匿。”[31]亲情的断裂与消泯显示出时代的嘲弄。
四、结语
陈晓明曾言:“此时的苏童对所谓人类的真实处境没有兴趣,他关注的只是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人们生存状态突然敞开迸发出的诗意火花,这些火花竟然使得所有的生存苦难变得异常美丽。”[32]在这个关于生存与毁灭、欲望与痛苦的小说外壳之下,苏童以细腻的笔触书写出“夸张变态的性欲,疯狂的野心,糜烂的身体,破败的家族”[33],从而使得叙事的意义重心偏向人性的原始品质。欲望作为一面映照人性的镜子,呈现出小说中人物内在的质地。苏童笔下的这些人物如风中之烛、水中之萍,时时都可能被生活的欲望之海所吞噬、摧毁。情欲和物欲往往是展现人性幽暗之处的出发点,一步步将人物拉向崩溃的结局。而织云、绮云的生命轨迹便成为那一段段荒凉而混沌的现实的隐喻。
在《米》中,苏童通过织云和绮云等人物形象的书写,在诗与思之间凝构强大的张力场,呈现出黑暗人性开掘与抒情的文笔相结合的混沌的美学效果。他将现实的情境融入个人的故事中,展现出原本具有个性的生命在利益的驱动和思想的封锁下心灵的扭曲,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戕害似乎不需任何外力,就足以造成心灵世界的千疮百孔”[34],显露出悲凉之美,散发出淡淡的幽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