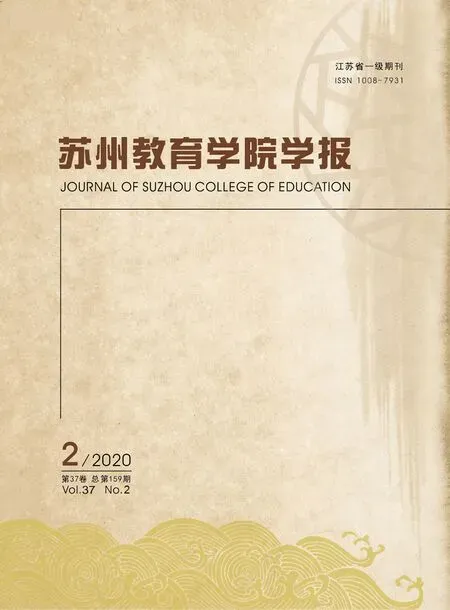流亡与虚无:《米》中五龙人生悲剧研究
芦静静,王 红
(广西大学 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4)
苏童是先锋文学的代表作家,其长篇小说《米》[1]是先锋文学的经典之作。在小说《米》中,主人公五龙因“走出去的诱惑”而踏上通往城市的道路,开始了他充满欲望、屈辱而又暴力、仇恨的生活。在城市中,五龙凭借自己的阴谋诡计得到了年少时期所缺失的米、钱和权力等,可谓收获颇丰。但在人生弥留之际,五龙想要回到那个曾经“什么也没有”的故乡,最终天不遂人愿,他还是死在通往故乡的火车上,完成自己“回不去的流亡”的人生悲剧。五龙终其一生所得到的不过就是一场残忍的、令人绝望的虚无。纵观五龙一生,可发现其所有的疯狂、变态、令人无法接受的行为背后都有强大的心理动因,这个心理动因便是马斯洛所说的人在不同阶段的不同层次的基本需要。马斯洛在《动机与人格》中曾经对人的基本需要层次进行过划分,他指出,人的基本需要主要包括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和归属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这五种基本需要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排列过程(并非固定)。马斯洛还指出,人在每一个时期表现出来的各种需要的程度是不同的,但都会有一种基本需要占据主导地位,其他需要处于从属地位。总体来说,动机是人从事各种活动的内部原因,基本需要属于一种类似于人类先天本能的性质,在其得不到满足时,人可能会表现出种种行为,即一旦寻求某种需要的行动受到阻碍,便会诱发一些病态的猎取和疯狂的表现。正如马斯洛所言:“在任何一种基本需要受到挫折时,很可能表现出病态,或者至少不如健康的人。”[2]40本文主要从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出发,研究《米》中五龙的人生悲剧,解读五龙在人生各个阶段的行为,以及作为相应动机的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和归属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阐释五龙人生悲剧发生的原因,以此重新认识五龙的流亡经历和人生选择,而这与以往仅从文学方面解读五龙人生悲剧的研究相区别。
一、城市生活:走出去的诱惑
小说《米》在一开始,便鲜明地展现了城市富裕的物质环境和乡村贫瘠的生活,尤其是天灾人祸所带来的悲惨场景,可以说城市和乡村的强烈对比已然表明了五龙从乡村逃到城市的原因。五龙在运煤货车上颠簸了两天两夜才到达城市,见到各种灯红酒绿的广告、搔首弄姿的女人和饿死在路边的异乡人,他发出感慨:“这就是乱七八糟千奇百怪的城市,所以人们像苍蝇一样汇聚到这里,下蛆筑巢,没有谁赞美城市,但他们最终都向这里迁移而来。”[1]3-4这句话不仅是五龙的心理写照,也是初入五龙眼中的城市光景。城市以其物质的极大富裕散发出巨大的魅力,诱惑着每一个生活落魄的农村人来这里开始他们新的奋斗、新的人生。五龙的家乡是枫杨树,那里曾经是一个大米仓,人们以耕种为生,米对于当地农民来说就是生命,就是他们世世代代繁衍并生活下去的根本。当枫杨树遭遇水灾、旱灾时,这些农民或留在家里活活饿死,或逃到城市寻找生机,五龙也是如此。在这样的天灾人祸中,五龙忍受过最令人绝望的恐惧与饥饿,看到过最令人触目惊心的遍野饿殍,所以为了能够吃上米,为了不再挨饿,为了能够活下去,他从饿死人的乡村逃亡到能够使他活下去的城市。此时,米对于五龙来说,就是活下去的希望,是一个人生存念想的寄托,是抵抗天灾人祸的信念。正是由于五龙有过这种极度缺乏米、缺乏食物和挨饿的经历,才造成他日后对米的极度渴望与需要;同时,也是米激起五龙对城市的向往、对米店的渴望,从而激起他对维持活下去的基本生理需要的寻觅——拥有抵抗饥饿的米。进城后,五龙所面临的难题就是:如何吃饱?如何吃上米?可以说,对于一个即将饿死的人来说,全部能力都投入到解决饥饿的活动中,除了食物,其他任何兴趣都没有了。为了能吃到一块卤猪肉,五龙可以管地痞阿保叫爹;为了能吃到米,他可以长期忍受着米店冯氏父女三人对他的谩骂轻视、无情剥削和身体伤害;为了拥有米店,他娶了怀了别人孩子的织云。即使五龙霸占大鸿记米店并拥有成堆成堆的米后,他对米的狂热追求也未曾减弱过。无论走到哪里,五龙都要带着几粒米,他还严厉地要求家人吃米时一粒不剩,而且在他临终时,也要带着一火车厢的米回乡。对于此时的五龙来说,生活本身的意义就是吃,米就是世界,世界就是米。从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来看,五龙“食”的生理需求满足感的缺失,刺激了他对米的狂热追求。他最初也只是为寻觅缺失的生理需要而产生想要活下去的简单欲望,但是慢慢地,这种简单的欲望会因为人的贪婪本性而变得越来越复杂,最终成为一种对生理需要的病态的掠夺和索取。至此,五龙对米的狂热追求也有了合理的解释,而不仅仅是人们看到的那个对米变态索取的表象。
在城市中,五龙为填饱肚子生存下来固然容易,但城市以它特有的生存机制和文化认同拒绝和排斥了外乡人加入。初到码头时,五龙便受到了地痞阿保的各种虐待和辱骂,无父的五龙被地痞流氓强迫喊“爹”,还要像狗和兔子一样被人耍弄。从踏入城市的那一刻起,他的人格和尊严便开始被践踏、被侮辱。而后,五龙虽然在米店里做工勉强解决了饥饱问题,但他曾经委曲求全、丧失尊严获取食物的方式并没有换来城市生活的安稳。他在米店里受到冯氏父女三人的各种剥削、迫害和辱骂,老板冯氏无情地压榨五龙的劳动,同时又像嫌恶和提防狗和鼠一样地对待他,在利用、榨尽之后买凶杀他;妻子织云经常辱骂他、利用他,并咬断过他的脚趾头,最后又因荣华富贵的缘故狠狠地抛弃了他。冯氏父女三人自以为是地把五龙当作傻瓜、猪、狗,甚至是一块石头和一条遮羞布,就在这样恶劣的生存环境中,一方恶霸六爷还虎视眈眈地威胁着五龙的生命安全。
总的来说,这座城市对他的排斥、侮辱和蔑视都在提醒他一个外乡人在城市中的艰难与不易。五龙受到来自城市的人身威胁和人格歧视,此时个人的安全需要和尊重需要是缺失的,即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安全感和身份认同感是没有的。人的基本需要被威胁和掠夺,必将带来同等程度或更高程度的寻觅和补偿。五龙遭受的辱骂和暴力越多,他寻觅这种安全需要和尊重需要的愿望便越迫切,他心中的仇恨也就越强烈,想要获得的权力也就越多。城市里安全需要的缺失给了五龙去歼灭敌人的动机,也使他策划的那些阴谋诡计得到有效实施。阿保和织云的偷情使五龙有机会除掉阿保。老板冯氏的恶病让五龙摆脱了控制,逃离了被奴役的命运,并且成为拥有米店一切的一家之主。织云抛弃五龙投奔六爷,却意外地成为深宅大院里孤苦无依的洗衣娘,织云的凄惨处境更是宽慰了五龙被侮辱、被抛弃的心。绮云被五龙长期霸占,并成为他泄欲的工具,绮云无法挣脱的命运也消解了五龙被欺压、被剥削的仇恨。最后,五龙用暗算的手段除掉了对自己安全需要威胁性最大的六爷,俨然代替六爷成为了地方一霸。
总之,这些损害五龙生命安全需要和尊重需要的人或势力,都在五龙以恶抗恶的方式中土崩瓦解、灰飞烟灭。在此过程中,五龙获得了作为城市人的身份认同和尊严。随后,为展示和标榜自己城市人的身份,五龙出现了一系列极端疯狂的行为。他最极端的行为之一是敲掉了那曾经吃糠咽菜、在冬天冻得打战的牙齿,换了一口闪闪发光的金牙。他说:“我以前穷,没人把我当人看,如今我要用这嘴金牙跟他们说话,我要所有人把我当作人看。”[1]127这句话是五龙真正地想要标榜自己作为城市人的心理活动的展现,也代表了五龙与农村过往的告别。
在从乡村逃亡到城市的过程中,五龙从一条狗到一个人,从一个要饭花子到米店主人,从饱受饥饿的煎熬到拥有成堆的米,从被欺压到欺压别人,从一个逃离农村的人变成一个留在城市的人。这不单是一个角色的转换、一个身份的更替,更是基于个体的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和尊重需要多重缺失的情况下对于城市的极端掠取和反抗。至此,五龙对个人基本需要的疯狂寻觅既有了现实生存的合理性,也有了历史生存的合理性。从更深层次上来讲,五龙这些疯狂的行为完全来源于社会。尔虞我诈、弱肉强食的社会现实剥夺了五龙原本善良的本性,造成他人性的异化,谱写了一曲痛彻心扉的悲歌。
二、怀乡情结:回不去的流亡
在《米》中,那座城市像一个铜墙铁壁的围城,又像一个充斥着欲望的迷宫。城市里生活的每一个人或被幽闭或自我幽闭在其中,无力自救。对于五龙来说,城市是其梦想发酵和欲望膨胀的“天堂”,那里可以有米堆、女人、权力和金银财宝,但没有家的温暖、 生活的快乐和亲人的友爱,有的只是唯利是图、相互倾轧、仇视与残杀。这样的城市生活很难满足五龙的精神需要,他开始对城市产生厌倦。尽管五龙得到了米店,除掉了阿保、六爷,成为城市里的新霸主,完成了对城市的占领,但他强烈地感受到精神的孤独、空虚——“父不父” “子不子”“妻不妻”,并不断地质疑人生:“怎样的人生才是有价值的?”此时,他仿佛已把城市看透,最终发出这样的慨叹:“狗娘养的下流的罪恶的都市,是一个巨大的圈套,诱惑你自投罗网,为了一把米,为了一文钱,为了一次欢情,人们从铁道和江边码头涌向这里,那些可怜的人努力寻找人间天堂,他们不知道人间天堂是不存在的。”[1]169在五龙的精神世界里,城市里发生的一切只不过是一个幻影,阴暗丑陋的城市给人带来沉重的伤害,物欲、肉欲掩盖了人的精神性。
五龙在城市中富甲一方,精神却极度贫乏。可以说,五龙之前所获取的基本需要的满足并不能自动地解决归属感、生活目的和人生意义等问题,此时他缺失的不是物质,而是精神世界里的爱和归属。正如五龙所言:“他是米店的假人,自己的真人还在枫杨树故乡里。”[1]112故乡才是五龙爱和归属需要的意义源头,才是五龙坚守存在的自我生命之根,也只有在那里,他才能找到实实在在的本我。故乡是你无论贫穷或富有时所向往的生活意义的源头,它也是每一个漂泊者躲不开、扔不掉的牵挂。因此,每当五龙在城市中受到伤害时,他就会想到故乡的人、牲畜、水稻、棉花、房屋……五龙在城市里漂泊无依的心终于找到归属和去向。于是,他买下了故乡枫杨树的水稻地、棉花田、祠堂、晒场和所有房屋等,并设想有一天带着米堆衣锦还乡的场面。他用这些东西来完成自己儿时的梦想,也用这些东西彰显自己在城市中的人生价值。在生命弥留之际,五龙对故乡的这种归属感更加强烈与迫切。随后,五龙带着一火车厢的米,走上了还乡之路。五龙最后的还乡,既代表了他对故乡的眷恋,也代表了他在城市突围的失败;既表明他对物质需要的放弃,也表明他对爱和归属需要的寻觅。
五龙在城市里度过自己的一生,看似得到了金钱、权力和女人,但失去了健康、幸福和生命,就像五龙临终前反思与醒悟的一样——除了那一车厢的米自己没剩下什么。小说结尾部分写到五龙仍看见他像一株稻穗、像一朵棉花漂浮在那片浩瀚的苍茫大水之上,渐渐远去。五龙的人生结局就是城市生活开始之前的场景,这也暗示着五龙在城市里的一切都是虚无。而对于五龙来说,其人生成就和人生价值不仅仅是那些物质财富,更是他自己内心渴望成为的那个强者和那个衣锦还乡的故乡梦。五龙这种自我实现的需要,在城市里无法找到,在农村亦是如此。
纵观五龙一生,他的确是在个人基本需要的刺激下才开始自己的城市生活,但在面对巨大物质利益时,五龙无法抑制自己膨胀的欲望,终于成为欲望的奴隶而被欲望主宰了一生。马斯洛曾云:“当人的肌体被某种需要主宰时,还会显示出另一个奇异的特性:人关于未来的人生观也有变化的趋势。”[2]20在个人需要的缺失和寻觅中,五龙不仅人生观发生了改变,而且整个人生轨迹也发生了改变。他就像一个迷途的灵魂,走上了一条不知所终的旅程,处在永无归期的漂泊中,一直在寻找自己的归属,却永远也回不到枫杨树故乡。
五龙,一个来自贫苦农村的都市外乡人,他逃离那个受苦的农村来到城市,并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城市人,但并没有得到城市生活的幸福感、宁静感、归属感,于是又开始了从城市到农村的逃离。五龙处在城市与农村这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的夹缝中,既无法割裂农村的血脉,也无法真正成为城市人。五龙在自我实现的曲折之路上,完成生存即毁灭的悲剧。五龙的悲剧结局虽然令人痛心,但有摧枯拉朽的力量,让城市一切“美好的事物”轰然坍塌。五龙精神乌托邦的幻灭,不只是他一个人的幻灭,更是无数流浪者的还乡梦的幻灭。五龙的人生悲剧,不禁让读者陷入深深的悲恸和绝望之中,沉浸在一片悲凄阴郁的感伤氛围里。五龙漂泊流亡的一生也让小说有更深刻的疼痛感——读者为五龙的命运而激愤、悲哀。
三、价值意义:人性恶的揭露
苏童曾言:“我觉得《米》的写作是非常极端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是我对于人性在用小说的方式做出某一种推测,我把所有的东西都做到最极致,是负方向的,反方向的。”[3]在《米》中,苏童把五龙推到人性的负方向、反方向,五龙身上好像穷尽了人性中的所有丑恶。他用阴谋诡计、铁血暴力的方式成为米店的主人和城市的霸主,以变态的性暴力虐待身边的女人等,苏童以这种极端的方式塑造五龙这个人物形象,并将其恶作为他整个人性的归属,然而,“人性之恶并不能带来灵魂的安宁,与恶相随的是人本质上的孤独体验和灾难性的命运”[4]。五龙人性之恶的走向,必将导致他毁灭的悲剧命运。
在这场悲剧中,五龙在城市里每走一步、每做一件事,背后都凝聚了人的动机——基本需要,这些基本需要确实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和追求。如果人没有需要,那么人类的实践也就不存在了。而个人欲望的形成主要来自自我基本需要的不足、缺失和匮乏,这就注定个人要通过不断地追求和实践,才能满足各种层次的需要和欲望。因此,五龙在需要和欲望的驱使下,开始了他一次又一次的阴谋欺诈和巧取豪夺,而且每一次胜利和收获都刺激着他内心深处欲望的膨胀,并且这种欲望一发不可收拾,导致五龙的死亡和悲剧。五龙因为欲望而想获得城市里的一切,但恰恰也是因为欲望的无限膨胀而遭到毁灭。欲望既给了五龙幸运的生存,又给了他残忍的毁灭。从更深层次上说,五龙本身就是一个欲望符号,在消费欲望的过程中,他丧失金银财宝、权力美女等欲望本身的所指对象,逐渐成为欲望本身的能指对象。总体来说,欲望具有双面性,适度的欲望需要会使人奋发向上,过度的欲望需要则会使人忘乎所以乃至毁灭。一个人的欲望膨胀过程展现的是物质极度匮乏之后的极度贪婪,而导致这个结果的主要原因就是个人需要与社会环境之间的矛盾。
五龙对米、性、安全、尊重需要的疯狂追求,其行为背后是需要动机的指引,而这需要动机所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城市与乡村的极大矛盾造成的。城市的严酷环境仿佛是乡村人性格突变、人格扭曲的渊薮,又像是人丑恶行径和社会恶习的染缸。而五龙心中的乡村世界无疑是纯洁无邪、美好天真的净土,凝结着人类全部信仰的生命之源。五龙城乡逃亡的失败,既是努力追求而终不可得的无奈,也是对城乡矛盾冲突的无奈。五龙从农村到城市再回到农村的历程,否定了城市所展现的文化属性和价值利益,肯定了乡村精神世界和美好心灵归属。而《米》正是通过五龙的堕落与颓废展现出城市文化中阴暗扭曲的一面,揭露了人性恶的根源。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五龙的罪恶行为仿佛可以被消解与颠覆。
马斯洛曾明确指出:“所有的人类关系、所有的人类制度以及整个人类文化,都是以人性为依据的。”[2]305《米》这部小说的全部魅力都集中在五龙这个主人公的刻画上,尤其是五龙人性中最溃烂、最变态区域的展现。苏童也是通过五龙这个人物形象写出人性的丑恶、顽劣、卑微和暴虐,但并不是一味地堆砌和渲染种种罪恶。苏童一方面透过人性之恶写出人生命的艰难和无望的挣扎,这些艰难与挣扎也从另一方面反映出生命的本质,即尽管生活充满了各种艰难,人性也有与生俱来的缺陷,但生命始终昂扬向上。从这个方面来看,苏童“不只是为了写出生活的存在形式,重要的还是为了写出民族某种性格的生命存在形式,即把各种层面的因素都挤压到生命的形式中,写出生命的躁动、生命的扭曲”[5]。苏童将生命的哲学蕴含于五龙厚重、荒芜而又变态的生活中,以此完成了更为丰富的人性诗学。
四、结语
基于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视角解读五龙的人生悲剧,就会发现五龙所有的疯狂想法、所有的变态行为以及他那畸形人格形成的原因,是人生某个阶段某种需要的极度缺失与匮乏,导致他对某种需要的疯狂寻觅、满足,甚至是过度的补偿。重新认识和阐释五龙从农村到城市再到农村的逃亡经历,其人生最终还是逃离不了流亡与虚无的悲剧命运。五龙既不属于城市,也不属于农村,他一直漂浮在家乡那场具有毁灭性的茫茫大水之上,渐渐远去……可以说是个人基本需要的欲求与缺失、梦想与现实的无情错位、城市梦与故乡情的残忍割裂,使五龙成为精神畸形、心理变态的可怜者。五龙的一生是痛苦的,这种痛苦源于他对生活目标的错误把握;五龙的一生是可怜的,这种可怜源于他只是按照自己的方式追求所需要的一切。笔者认为,五龙的痛苦、五龙的可怜、五龙的悲剧,折射出当代人所面临的种种困境。正如苏童所言:“它负载的命题就是我设想的人类的种种困境,它们集中于五龙一人身上。这个人既属于过去也属于现在,人带有自身的弱点和缺陷,与整个世界、整个社会种种问题发生关系,陷入困境。”[6]苏童的人性抒写直指人本身,关怀人的心灵处境和精神痛苦,从而使小说《米》获得最为本源的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