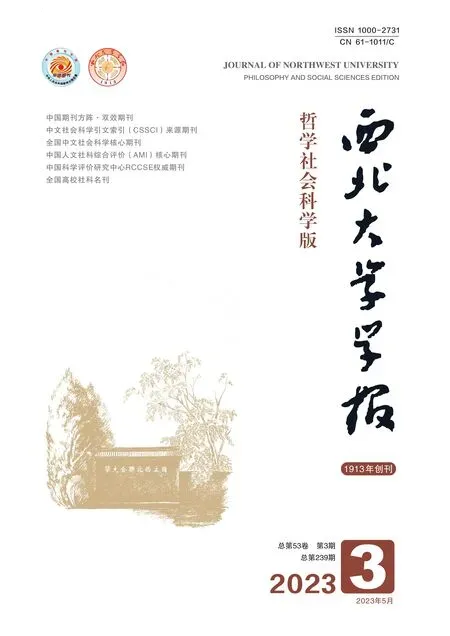中国古典美学的自然范畴的基本命题
王中原,王熠晨
(1.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2.西北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在哲学的领域里,范畴是一个存在论层面的术语,它意指并揭示事物存在的基础实事上的规定性;在中国古典美学的领域里,美学范畴是承载某一美学理论形态诸概念和命题的基本词语。自然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一个范畴,鉴于其在中国古典美学中的特殊位置,在特定的意义层面上我们甚至必须称之为“中国古典美学范畴体系中的基本范畴或‘元范畴’”[1]226。学界对自然范畴的研究呈不断深化的趋势,表现为从概念和命题的梳理、美学内涵的发掘与整理向探究其所凝聚的美学思想推进。在美学思想研究的层面,对自然范畴的基本美学命题的探究是一个重要课题。自然范畴的基本命题聚集着该范畴最根本的美学观念和核心的美学思想,唯有探入这一命题之中,我们才能本质性地洞察自然范畴的概念与命题系统及其在中国古典美学中的位置。截至目前,学界关于自然范畴的基本命题的专题性研究还存在着较大的探索空间。为实质性地推动这一课题的研究,本文拟基于当代美学的思想视域对自然范畴的基本美学命题进行专题性的探究,在廓清自然范畴的基本美学命题的基础上,尝试对自然范畴及其在中国古典美学中的存在做出洞察和揭示。
一、自然范畴及其美学内涵
自然范畴的实质是以自然为基本词语来思考和表达文艺美的本质与规律。刘绍瑾在谈到中国古典文学理论中的自然概念的时候,认为古代文论中存在着一个以自然概念为核心的潜在的、隐性的文学理论体系[2]。事实上,在中国古典美学的范围中也存在着这样一个事实:基于自然一词的一系列概念和命题构成了一个文艺美学的理论形态,后者涵盖了现今所说的文艺本质论、文艺作品论、文艺创作论和文艺鉴赏论的所有区域。围绕自然一词所生成的文艺美学体系从理论层面展现了自然范畴的内涵,因此,我们应该从该文艺美学体系着手分析自然范畴的美学内涵。
自然一词在现代汉语中更多地意指物理学范围内的自然(自然事物、自然界、大自然),这一维度上的含义在古汉语中则是由天地、万物、山水、山川、宇宙等词语来表达的,古汉语中的自然一词另有所指。古汉语中的自然一词是由“自”和“然”合成的。许慎认为“自,鼻也。象鼻形”,段玉裁认为“自”与“鼻”同音同义,“于鼻息会意。今义从也、己也、自然也,皆引申之义”[3]136。按照上述释义,“自”与“鼻”同义,“鼻”意指自己,“鼻”之气息意指自身活生生的存在,我们据此可以把“自”释义为本己的自身存在、自己存在。关于“然”字,《说文解字》释义为“然,烧也”,段玉裁训为“如此,尔之转语也”[3]480,意即一种“如此”“如是”“像这样”的存在状态。“自”与“然”合起来就是自己如是、自己如此、自己这样的存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段玉裁认定自然一词是“自”的引申义。自然一词的含义的进一步规定是由中国哲学思想实施的,源始的规定出于老聃。自然在《老子》一书中意指形容词或抽象名词性的“自己如此”[4]255,根据现行的哲学话语,“自己如此”是哲学存在论层面的对存在的规定,意指出于自身的、是其所是的本己存在,亦即,从自身而来成其自身的存在。在老子那里,“自己如此”(自然)同时指涉道的自身开启和万物之存在状态两个层面的规定性。自然范畴正是从自然的哲学存在论含义中汲取了它的美学内涵。
自然一词首先刻画道的基本特征。《老子》第二十五章中的“道法自然”一句显明了这一点,因为道的自身开启本质性地现身为自然,所以我们说道以自然为本己的法则。道是中国哲学的最高词语,按照中国哲学的说法,道是万物的本根,本根即万物存在的终极根据或本源。作为第一性的最根本者和最高者, 道是一切根据的根据, 因此, 道只以自身为根据, 道效法、 遵从自身, 自己如此。 正如钱穆所云: “《老子》本义, 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至高无上, 更无所取法, 仅取法于道之本身之自己如此而止, 故曰道法自然。 非谓于道之上, 道之外, 又别有自然之一境也。”[5]430“道法自然”所表达的是道以自然(“自己如此”)的方式本质性地现身, 这一存在论上的规定性正如王弼所说:“道不违自然,乃得其性,﹝法自然也﹞。法自然者,在方而法方,在圆而法圆,于自然无所违也。自然者,无称之言、穷极之辞也。”[6]66由于道是以自身为根据的终极本源,思想的追问必须指向并止步于此,若问何以有道,答曰:道自己如此。道不知其然而然、自然而然地如此现身。基于这一存在论上的源缘,自然完全能够替代道而成为它的另一种称呼,例如,魏晋玄学就认为自然即道[7]164。
作为本根,道生万物,遣送万物以自由存在,万物皆源出并依于道而存在。因而从形式上也不难看出,在文艺实践的领域,文艺创作者、文艺作品、文艺鉴赏者皆本源于道。同时,思想对文艺美的本质和规律的揭示必然要追溯到作为本源的本根,因此,中国古典美学的文艺本质论必定要通过道来经验、思考和表达文艺美的本质。在这方面,中国古代的文艺本质论的基本观念是文艺之美本源于道。以文学理论为例,“文以明道”“文以载道”“文以言道”等命题所表达的正是文艺美本源于道的观念。如上文所述,鉴于自然与道的同一,中国古典美学用自然一词来表达文艺美的本质,此即文艺之美本源于自然的文艺本质论。《文心雕龙·原道》认为天下之文皆是道之文,文学之美(文)本源于自然之道。关于书法的本质,蔡邕认为“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8]6文艺美本源于自然的观念表达了中国思想对文艺本质的如下认知:文艺从道的自身开启中源出和存在的实情表现为合乎自然,即表现为“自己如此”“自然而然”。由此,李贽认为“盖声色之来,发乎情性,由乎自然”[9]124,诗歌的本质则在于“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10]65。
道作为万物存在的本根具有以下两个层次的含义:其一,道是万物产生的本源,即道生万物,万物归本于道;其二,道是万物存在的真宰,道贯通和支配万物的存在,道“养育”万物。在老子看来,道作为万物的真宰乃是一种柔和的力量,它赋予万物以自然存在(亦即自由存在),诚如“水利万物而不争”。老子以自然来言说道创生、释放和庇护万物于自由存在中的情态。《老子·五十一章》认为万物是由“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器成之”,道与万物的关系是“生而不有,为而不持,长而不宰”,因此“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道虽生养万物,但从不剥夺万物的自由,此即“夫莫之命而常自然”[11]508。这个意义上的道之自然还有另一层含义:道对万物的生养皆出于自身的根据,自然而然因而不知其所以然。因此应该“希言自然”(《老子·二十三章》)。道作为本根也奠定了人生存的根据[12]180。同时,由于人(确切地说是理想意义上的圣人)作为“域内四大”(道、天、地、人)之一在万物之中具有显突的地位,人及其生存被赋予了特别的本质,那就是效法于道。效法道是人的本然使命,人应该遵从道去守护万物的存在,上述意义上的自然表达了这种道德使命的本质规定性,这就是《老子·十七章》所说:“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这种生存规定性同样也表现为自然,如王弼所说:“万物以自然为性,故可因而不可为也,可通而不可执也。……圣人达自然之性,畅万物之情,故因而不为,顺而不施”;“自然,其端兆不可得而见也,其意趣不可得而睹也。无物可以易其言,言必有应,故曰‘悠兮其贵言’也。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不以形立物,故功成事遂,而百姓不知其所以然也”[6]78、43。
艺术家对美的创造即符合于上文所界说的圣人之自然。文艺创作包括创作的准备和实施两个阶段。文艺创作的准备阶段要求艺术家能够领悟道之自然运化,艺术家领会自然之道的前提是一种对自身的扭转,即通过老子的“涤除”或庄子的“心斋”“坐忘”以通于道,诚如张彦远所说:“凝神遐想,妙悟自然,物我两忘,离形去智。”[13]40-41“妙悟自然”即通于或“同体”于自然(之道)。艺术家创作的准备阶段是“妙悟自然”,创作的实施阶段则是(应和于道的)自然而然、不知其然而然地创造艺术作品,一如道对万物的创生,用孙过庭的话说就是“同自然之妙有,非力运所能成”( 孙过庭《书谱》)[8]125。“妙悟自然”“同自然之妙有”的文艺美的创作论的根据,既在于文艺美本于自然的文艺本质论,也在于中国文化对文艺创作的经验和认知。文艺创作需要艺术家进入并保持一种无功利的心境,中国古典美学将这一心境领会和表述为体道悟道的经验,这一事实与“道法自然”观念的结合必然促成了“妙悟自然”的观念。关于艺术创作中的直觉、灵感、无规律的合规律性、无目的的合目的、天才创造等事实,中国古代思想将其把握为“无意”“无工”“无法”,由于中国哲学以自然一词表达和承载这些观念,古典美学必定要用自然来表达艺术美创造的本己特征。这就是说,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自然’作为哲学范畴,其核心内涵是‘无为’;作为文艺美学范畴,其核心内涵也是‘无为’,即自然而然、不假造作”[1]85。
道对万物的生养是自然而然的,这一自然表达了道令万物自然(自己如此)地存在的情态,所以老子说圣人要“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老子·六十四章》)。“辅万物之自然”中的“自然”说的是万物如同道一样从自身中现身出场、自己如此地存在,这也是自然之道的一层内涵,后来王充的《论衡》、郭象的《庄子注》都对之进行了更明确的阐发,认为物之自然即物的自生自存。根据这一内涵以及上述自然论的文艺美的本质观和文艺美的创作观,我们不难得出文艺作品之美的自然论:文艺作品之美也是自然的,亦即出于自身而从自身中自然而然、自己如此地达于存在。古典美学称文艺作品之美的这种存在特征为“化工”“天工”“天成”。同时,从文艺作品本身的实情来看,与其他人工制作的器物相比,文艺作品表现出显突的类生命特征,即像生命有机体一样出于自身的根据而来使自身达于存在,艺术家创作文艺美的实质好像只是为了辅助文艺作品的自生自存,中国传统文化对这一事实的著名表述就是“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因此,中国古典美学对文艺作品之美的存在特性的认知和表达必然要诉诸自然一词,用司空图的话说就是:“生气远出,不著死灰。妙造自然,伊谁与裁。”[14]24“妙造自然”说的就是文艺作品之美——自然,其中的一层内涵是文艺作品的美表现为那种自生自存的生命生长般的“气韵生动”和是其所是的“清真”。
文艺作品之美作为自然的另一层内涵关涉于文艺作品的本体。文艺作品于万物之中区分自身的本己要素在于它是美的作品,文艺作品的本体在于美。而文艺作品的美乃是在作品这一事物上发生着的自然之道,或者自然之道在作品中的发生,因此,宗炳的作为审美的“澄怀味象”实乃“澄怀观道”,诚如马丁·海德格尔所说,美的本质是真理以自行置入作品的方式而发生[15]37。这里的真理会通于中国哲学中的道的自身开启。因此,从其本体来看,文艺作品的自然就是所谓的美,就是在作品中达于本质性现身的自然之道。凭借自然之道的内涵及其规定性,文艺作品的自然解释了文艺审美中的真理经验(“此中有真意”)以及对至善(成造化之功)的经验等。在上述意义上,文艺创作所“妙造”的“自然”即意指作为文艺作品之本体的美,如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说:“元曲之佳处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而莫著于元曲。”[16]98很显然,在这里自然即美。
既然自然范畴的文艺作品论认为文艺作品的存在特征及其本体作为美就是“自然”,使文艺作品之美达于真正意义上的存在(亦即实现)的文艺鉴赏就是对自然的悟入,这就是自然论的文艺鉴赏的审美观。钟嵘所说的“自然英旨”即表达了这样一种审美经验[17]25,姜夔对此有更清晰的理解:“非奇非怪,剥落文采,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曰自然高妙。”[18]68基于这样一种文艺鉴赏的审美观念,自然一词也被用来表达一种不事雕琢、浑然天成、天真清新、生气远出的文艺审美经验类型,如“自然可爱”(通于“清水芙蓉”)“自然之味”“自然之品”(司空图《诗品》)等。藉此,中国古典美学还用自然一词来表达文艺作品的审美品级,在所有的品级中,能够促成自然之审美经验的才是最高的鉴赏品级,即“自然者为上品之上”(张彦远)[13]38、诗以“自然妙者为上”(谢榛)[19]127。
自然范畴以自然为基本词语来经验、思考和表达文艺美的本质与规律。老子哲学对自然一词的烙印以及中国古典美学对文艺审美实践的独特把握共同促生了自然范畴,其美学内涵展开为一个完整的文艺美学形态:文艺本源于自然(文艺以自然为宗)的文艺美的本质论、“同自然之妙有”的文艺美的创作论、“妙造自然”的文艺作品之美的作品论和“妙悟自然”的文艺审美论。
二、自然范畴的基本命题
上文对自然范畴的美学内涵的探讨为进一步探析其基本命题提供了一个研究基础。对自然范畴基本命题的探讨旨在追问一种怎样的关于美的本质的领会奠定了这种自然论的文艺美学观念。即便并不存在着关于自然范畴的基本命题的明确表达,但这绝不否认该基本命题在中国古典美学中的隐性在场,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以当今美学的眼光对其进行探问和揭示。
蔡钟翔认为自然范畴表达了“美在自然”的观念,并把“自然”理解为“中国传统的最高审美理想”[1]69,这一见解与李贽的“以自然之为美”[9]124一道从审美理想的角度解释了自然范畴崇尚自然的审美观念。从自然范畴崇尚自然的角度看,自然俨然就是文艺实践所追求的终极归宿——美。同时,鉴于自然范畴以自然一词为基本词语来对文艺美进行经验、思考和表达这一事实,我们在此可以预先做出一个猜度,先行地把自然范畴的基本命题阐释为:美即自然。
初步的论证基于自然范畴的美学内涵。因为文艺以美为其存在根据,所以文艺的本质、文艺创作、文艺作品、文艺欣赏都必须以美为根基,而自然范畴对文艺美的经验、思考和表达就聚集于自然这一基本词语之上。事实上,“以自然为美”“美在自然”中就包含着美即自然这一领会,只是后者一直处于蔽而不显的境况中。
在哲学存在论层面,自然描述作为万有之本根的道开启自身的实情,作为名词的自然可以用来指称道本身。用现行哲学话语来说,道作为中国思想最高的词语其本质性现身就是所谓的存在之真理,而美则是这种真理的一种根本性发生方式[15]43。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美即道的一种根本性现身方式。因此,美即自然的命题从义理上是说得通的,美即道的一种根本性现身方式意在表明:“美即自然”命题中美与自然并非等同,美是得到进一步规定的自然。因此,我们对自然范畴的基本命题的阐释须得更进一步,以阐明美是道的何种现身方式以及何以要用自然来称谓这种现身。
美是道的何种现身呢?《老子·二十一章》将道的现身描述为:“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今及古,其名不去,以阅众甫。”[11]255“道之为物”讲的是道的现身或发生,道之现身显示为从“无”向“有”的生成,这一生成乃“有”和“无”的共属一体,老子用“恍惚”“窈冥”加以刻画。道从“无”向“有”的生成首先是显而为“象”,道本身所显之“象”为“大象”,因此“执大象,天下往”(《道德经·三十五章》)。基于道生万物这一源缘,“象”既是道的现“象”,也是万物的现“象”。作为后者,“象”向“有”的进一步生成乃是“物”的显现。“物”在此指的是万物之“形”(感性外貌),如《老子·五十一章》所说:“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器成之”,道、德、物、器是一个逐渐从虚无到实有的生成过程[11]508。“物”在道现身的过程中所处的位置是成“形”。“象”的更具体的“有”乃是“形”,即万物的形貌或外观。而道本身所现之“象”是区别于它所生成的万物之形象的,所以有“大象无形”(《老子·四十一章》)的说法。在此,王夫之关于《周易》和《尚书》中的“象”和“形”的阐述也可以作为参考:“盈两间者皆道也。可见者其象也,可循者其形也。出乎象,入乎形;出乎形,入乎象。”[20]1003“物生而形形焉,形者质也。形生而象象焉,象者文也。形则必成象矣,象者象其形矣。在天成象而或未有形;在地成形而无有无象。视之则形也,察之则象也。所以质以视章,而文由察著。未之察者,弗见焉耳。”[21]411因此,老子所说的“其中有物”的“物”还不是具体实存的万物,而是万物在其中摆出自身的外观形象,万物经由展露外观而达于存在,而具体实存的万物则是“形”与质料结合而生成的“器”,此即“器成之”的含义。道现身为万物的“形象”,从同一性的角度来看,万物的“形象”即是道的现身,道作为“精”(精气)贯通于万物的“形象”中,此即“其中有精”。上述图景既显示了道自身生成的生命特征,其生长和活力也揭示了万物源出于道的真实存在情状(万物之情)。后者即先秦哲学中作为“真实”的“情”,老子说“其精甚真,其中有信”,由此,我们可藉之洞察历史与万物存在的真理,此即“自今及古,其名不去,以阅众甫”。经过上文的阐述,这里需要进一步提出的问题是:《老子·二十一章》言说的这种道通过万物之“形象”而现身的方式是否就是我们今人所说的美呢?
道之现身召唤人的在场,这对于人来说就是观道、体道和行道。这也对人提出了特别的要求,要求人保持虚静的心境,即所谓的“致虚极,守静笃”(《老子·十六章》)、“涤除玄览”(《老子·十章》)。南北朝时宗炳将这种虚静心境称之为“澄怀”,表明“澄怀味象”( 人在虚静心境下对万物的“形象”的观照) 作为“澄怀观道”就是所谓的审美[22]211。这就是说,《老子·二十一章》中的道通过万物的“形象”而现身的方式就是美,这在刘勰那里得到了更为明确的表达。《文心雕龙·原道》说:“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10]1刘勰说的“道之文”即是《老子·二十一章》中以“精气”贯通的“象”和“形”,刘勰以“文”指称万物的这种“形象”,并且认为作为“五行之秀”“天地之心”(亦即“道心”)的人能够对“文”进行参悟(“惟人参之”)。人在感性观照层面对“道之文”的参悟即是审美,如刘勰所语:“傍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至于林籁结响,调如竽瑟;泉石激韵,和若球锽。”[10]1作为美的显现,“文”向人的感性观照开放自身,刘勰确切地指出了这一点:“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10]1“形”“声”主要对应于人的视听,但也包含了人的所有的感性觉知。刘勰认为“文”作为美不仅只有自然美,“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欤”,对于人来说,“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10]1。“言立而文明”说的就是人工创造的文艺美,文艺之美同样也是道之“文”,亦即同属“自然之道也”。 因此,皎然认为苦思与雕琢也能够达到自然,诗要“至丽而自然”,而取境并非不要苦思:“又云,不要苦思,苦思则丧自然之质。此亦不然。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23]26,39
至此我们不难得出如下结论:在老子那里,美是道通过万物之“形象”而现身的方式,亦即美乃道向人的感性观照的敞开。这解答了美是一种什么样的自然——美是道的何种发生方式。下面我们来澄清自然范畴为何要以自然一词替代道来表达美的经验。
经由老子思想的烙印,美被经验和表达为道的一种现身方式,而道的基本特征就是自然。因此,美的本质就被界说为经由“精气”贯通的“象”与“形”而显现出的道的“自己如此”“自然而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实情。通过“审美”经验,观道者或悟道者本人就被移入这种自然真境中,个中的境况即“自然高妙”。同时,美的实存也具有自然的特征,根据《文心雕龙·原道》的表述,美之开显的情态是“夫岂外饰,盖自然耳”,无论天然生成的自然美还是人工创作的文艺美都合于“自然之道”。因此,王夫之认为文艺之美“自然灵妙,何劳拟议哉?”[19]147。此外,魏晋南北朝是中华民族审美和美学自觉的时期,而主导这个时期的玄学思想倾向于用自然一词来领会和思想道,这一历史的实情从美学思想史的角度解释了自然范畴何以要用自然一词来替代道。
综上所述,我们把自然范畴的基本命题把握为美即自然。在该命题看来,美是自然的一种根本性现身方式,亦即美乃向人的感性观照开启自身的自然之道。
三、从美即自然的命题看自然范畴
自然范畴用自然一词表达中国古典美学对美的本质的特定领会,用现行美学话语来表述就是,自然范畴的美的本质观乃是:美即自然。鉴于美即自然的命题与作为中国思想基本词语的道的源缘,自然范畴在中国古典美学的范畴体系中是一个居于核心位置的基本范畴。叶朗认为“美学范畴和美学命题是一个时代的审美意识的理论结晶”[22]4,进一步讲,在一种美学传统中居于核心位置的基本范畴则是处于该传统之内的范畴和命题的思想结晶。自然范畴以及围绕该范畴而生成的一系列概念和命题植根于中国古典美学对于美的独特经验和思考,这一范畴显突地标识了古典美学思想的特征。
从美即自然这一基本命题所持有的美学观念来看,自然范畴通过回溯到作为中国思想本源性词语的道来源始地思考美的本质,这种从本根论层面对美所作的存在论思考必然是最根本性的、第一位的美学思想。经由老子思想的规定,自然一词凭借其存在论内涵——作为本根的道的自身开启的情态以及万物本源于道的存在状态——表达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存在之真理(万有的真相、实情)的独特理解。正是基于此,自然范畴使用自然一词来表达古典美学对文艺美的本质及其规律的经验和思考。在上述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自然范畴突出地展露了中国古典美学的基本特征。自然范畴把以美的方式发生的道(即真理)之开启自身的运作把握为自然,这种作为美的自然被经验和表达为天真、清新、生气盎然、高妙无痕;文艺的审美创作被理解为(像道那样)自然无为的自由创造(“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具有不事雕琢、天然化工的特征;文艺作品的美被视为道之自然发生所具有的自然高妙、自然灵妙;文艺审美鉴赏则被认为是对文艺作品中发生的自然之道的悟入,此即同体于自然、妙悟自然。从比较美学的视角看,这一由美即自然的基本命题所奠定的自然论文艺美学体系典范地展现了中华美学的本土特色,我们知道,如此鲜明和完整的自然论的文艺美学观念在其他民族文化的美学思想形态中并不多见。
在美即自然的命题中,自然一词的确切含义是道的一种发生方式,以这种方式发生的道通过“象”和“形”而现身为美,这一美学思想可溯源于道家的道论思想。在老子看来,道之自然具有以下三层内涵:首先,自然是道出于自身之故的自行(“自己如此”“自然而然”的)发生;其次,自然是作为本根的道令万物“自然而然”的存在,道“无为”“不争”而赠予万物以自由存在;最后,自然是对人之本质的规定,理想意义上的人(圣人或王)的使命在于顺应道之自然(“人法道”),“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所规定的乃是人的自然——亦即人的自由。以此来看,美即自然的命题实际上从美学角度表达了一种以人道应合天道的“天人合一”的人文观念,后者认为作为人的最高使命的自由的本质在于遵从自然之道、顺其自然地辅助万物之自然(自由存在)。在当前的思想语境下,这种人文观念能够为在现代历史中造成深重灾难的西方形而上学的人道主义观念的解构提供一种思想启发,在反思和克服现代性问题上与后现代思想具有异曲同工之妙。正是在“天人合一”观的护送下,中国古人的历史性生存才被置入一种相对安然的境地,这一思想观念在当代则作为“生态智慧”和“生态伦理”启迪着我们的历史实践。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自然范畴凭借自然一词在美学思想领域演绎了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思想根基的“天人合一”观(1)钱穆以96岁高龄在其绝笔之作《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之贡献》中断言:“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观虽然是我早年屡次讲到,惟到最近始澈悟此一观念实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参见汤一介《读钱穆先生“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之贡献”》(载《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4期)。,并通过美学和审美把中华民族的历史性生存护佑入这种人文观念的作用范围之内。
在美即自然这一命题那里,美本质性地现身为自然,而审美所追求、专注和归属的东西无非就是此一美而已。因此,美即自然命题的内涵也包含了以自然为最高审美理想的美学观念,这一思想观念奠定了自然范畴以自然为美的美学信条。在这个方面,自然范畴表达了中国古典美学崇尚自然的审美精神。崇尚自然的审美精神被自然范畴表达为文艺“以自然为美”“美在自然”。在这一观念看来,文艺创作虽由人亲力亲为,但其理想却是像道造化万物那样自然而然,文艺作品虽由人作,但其理想却是“有若自然”“宛若天开”,并且能够把欣赏者“自然而然”地置入对自然之道的妙悟之中。与人工制品相比,自然事物的存在更本真地持留着自然(而然)的状态,以自然来思考道的魏晋玄学就尤为重视对自然事物的经验,有“以玄对山水”之说。与人工制品相对来说,自然这一审美理想比较突出地寄寓在自然事物之美上,因此正是崇尚自然的审美精神参与并促成了自然审美在魏晋时期的自觉。自然范畴也从美学层面促成了以自然美为表现题材的中国山水艺术(山水诗、山水画、山水园林等)的兴起,促生了自魏晋就开始兴盛的自然审美传统(2)与此相比,西方自觉的自然审美始于14世纪,划时代的事件是彼得拉克在西方首次登山欣赏自然风景;而西方自然审美的完全意义上的兴起则始于18世纪。。这一审美史的事实引发了中国古典美学对自然美的重视,由此生成了一种具有民族特色的山水美学形态,这也是中国古典美学崇尚自然的审美精神的一个表征。
从其实质上来看,美即自然的命题是自然范畴对美的本质的思考。美的本质观是第一性的美学观念,我们对某一美学思想的探究必定首先要将其美的本质观收入视野。虽然中国古典美学中并没有美的本质观这一现代的美学话语表达,但我们不能由此就断言中国古典美学没有关于美的本质的思考,从而没有属于自己的美的本质观。古典美学并不唯一地用美一词来称谓我们当今美学所称谓的美,其对美的独特思考和称呼体现于一系列与美同等的词语上,如“意象”“意境”“妙”“自然”“情与景”等。从美即自然的命题来看,自然范畴的自然一词实际上承荷并表达了古典美学对美的本质的一种思考,自然范畴由此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洞察中国古典美学的本质性视界。同时,鉴于自然范畴在中国古典美学中的位置,我们能够藉之以观入中国古典美学思想的核心之处。这一认知使我们能够深入洞察自然范畴及其所直接关涉的一系列范畴[1]179,由此而提供出一个重要的理论参照系,使得我们能够进一步探究自然范畴与古典美学的其他重要范畴(如意象、意境、妙、文等)之间的本质性关联。
四、结 语
自然范畴以自然为基本词语来经验、思考和表达文艺美的本质和规律,其所生成的一系列概念和命题构造了一个完整的文艺美学形态。这一源于老子哲学对自然一词的规定而生成的文艺美学形态展露了自然范畴的美学内涵,其中的根本性美学观念乃美即自然这一基本命题。本文尝试性地探索旨在寻获一个本质性的基础视界,藉之我们得以清楚地洞察自然范畴及其在中国古典美学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存在。在中国审美文化史上,自然范畴从思想或理论的维度参与、构建了中国古典艺术实践,自然范畴展示自身为一个经验和思考中国古典艺术的理论视窗,在这个方面,美即自然命题揭示了古典艺术以自然为美、崇尚自然的审美精神。对于自然范畴的基本命题的进一步研究有着广阔的学术空间,其中尤为重要的向度是美即自然命题与中国古典美学其他核心范畴的基本命题(如美即意象、美乃道之文等)之间的关系研究。这一专题的研究将促成我们更充分地把握自然范畴的基本命题,藉之以更合乎实情地廓清中国古典美学的范畴体系与思想内核。
——河北省优秀群众文艺作品巡演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