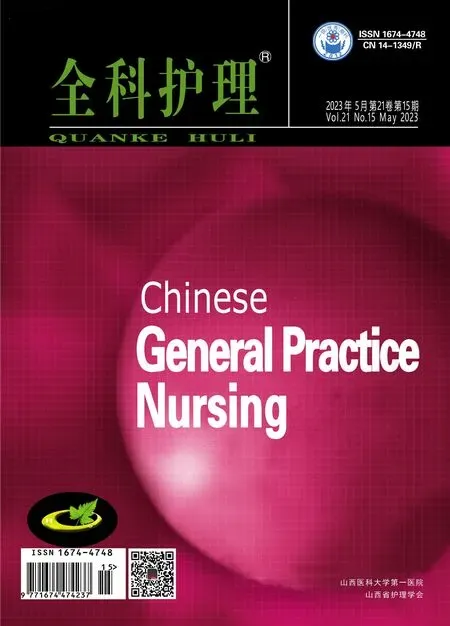非自然创伤性丧亲者哀伤干预研究进展
黄 展,邱 芳,刘梦婕
灾难和事故往往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据报告,“5·12”汶川地震共计造成69 227人遇难,2020年我国共发生244 674起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达61 703人[1],近年来,国内多起突发性灾难事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如2019年末至今未完全停止的新冠疫情、“3·21”东航MU5735航空器飞行事故机上132人全部遇难[2]、湖南长沙“4·29”特别重大居民自建房倒塌事故造成53人遇难、青海大通“8·18”山洪灾害造成23人遇难……死亡数字的背后是一个个家庭的破碎,更揭示着一个庞大的丧亲群体——遇难者家属。遇难者家属是事件中哀伤程度最为强烈的人群,更应是哀伤抚慰对象中的一个重要主体,国内现有哀伤干预的研究通常聚焦在ICU病人及其家属,非疾病的创伤性事件的丧亲者的哀伤干预的研究较为少见,因此对国内外关于创伤性丧亲者的哀伤分期与概述、干预措施及开展现状进行综述,为我国的非自然创伤性哀伤辅导本土化提供依据。
1 非自然创伤性丧亲者的概念及其哀伤干预现状
1.1 非自然创伤性丧亲者的概念 非自然创伤性丧亲指亲人由于生命或疾病发展规律以外的因素作用而提前发生死亡,例如凶杀、自杀、事故和自然灾害等事件造成的丧亲[3-4]。创伤性丧亲导致丧亲者出现不利于身心健康的持续悲伤,目前,国际上使用不同的术语来诊断这种悲伤反应,在DSM-5中,它被标记为“持续性复杂丧亲障碍(Persistent Complex Bereavement Disorder,PCBD)”[5]。ICD-11包括“长期悲伤障碍(Prolonged Grief Disorder,PGD)”[6]。这些诊断用以促进评估创伤性丧亲者的丧亲之痛,并能够提供有效的治疗[4]。
1.2 非自然创伤性丧亲者哀伤干预的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研究丧亲之痛的影响因素,其中丧亲事件(原因)的不同,对丧亲之痛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意外事故、自杀、自然灾害、战争等具有突发性和创伤性的丧亲事件对丧亲者的影响较重[4]。Raphael等[7]将这类事件造成的丧亲称为“traumatic loss”,意为“创伤性丧失”,Edward[8]宣称这类事件阻扰了丧亲者对亲人死亡的接受。多项研究报告表明,创伤性丧亲者中,患精神障碍疾病如PTSD、CG、抑郁症的概率,高于经历自然丧亲的丧亲者[9-10],Kaltman等[11]的研究表明非自然创伤性的丧亲者的丧亲之痛超出自然死亡的丧亲之痛的正常程度。Nakajima等[3]阐述创伤性丧亲者悲伤的生理机制和生物学基础,为创伤性丧亲的哀伤干预和并发的精神障碍治疗提供了依据。
国内少见对创伤性丧亲者丧亲之痛的理论研究,主要为对灾难丧亲者和自杀遗族的家庭功能研究[12-13],集中于对灾后丧亲者心理危机干预和哀伤辅导[14-15],在实践层面丰富对创伤性丧亲者哀伤干预的研究。
对非自然创伤性丧亲者的哀伤干预已不是某场灾难或意外事件后的特例,而是当今社会需要面对的广泛问题。根据胡晓林等[16]的研究,2008年汶川地震264名遇难者家属在地震1年后,所有的遇难者家属都表现出抑郁症状,常见包括情绪低落、工作兴趣下降、焦虑、能力下降和激动。Smid等[17]的研究发现,因事故、灾难而失去亲人可能会带来持续性复杂丧亲障碍的症状。Eisma等[18]的研究表明疫情期间的遇难者家属以及幸存者发生了更严重的急性悲伤反应,且更易患延长悲伤障碍。因此,对经历灾难、事故等重大伤亡事件的个人和家庭以及团体进行哀伤干预尤为重要,有助于使遇难者家属适应亲人离世,更好恢复家庭、社会功能[19]。
2 非自然创伤性丧亲者丧亲之痛的测量工具
2.1 创伤性悲伤清单自我报告(the Traumatic Grief Inventory-Self Report ,TGI-SR) 由Boelen等[20]于2016年开发,TGI-SR包括PCBD的所有16种症状,一项PGD症状(即第12项:“感到震惊/震惊”),以及一项“功能障碍”项目(即第13项)。TGI-SR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失去亲人的清单,第二部分包括18个项目,测量丧亲者最痛苦的丧亲反应。使用TGI-SR在168例具有创伤性丧亲经历的病人和167名2014年7月17日乌克兰空难的丧亲者中进行测试,所有18个项目、17个PCBD项目和11个PGD项目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8~0.95,结构效度好[21]。TGI-SR凭借其可靠性和精简的内容,用于创伤性丧亲筛查与评估,以及确定需要在临床进行更全面评估的创伤性丧亲者。
2.2 迁延悲伤量表修订版(Prolonged Grief-13 Revised,PG-13-R) PG-13由Prigerson等[22]于2008年开发,于2021年修改为PG-13-R,共有13个条目,其中3个定性评分项目,10个定量评分项目,量化评分采用Likert 5级评分法。PG-13-R的计分方法为计算10个量化评估条目总分,与迁延悲伤障碍程度呈正相关[23],有助于对创伤性丧亲者个体进行分类并采取措施。在672名丧亲者中进行了测试,PG-13-R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3~0.93。后由霍平乐等[24]首次汉化PG-13-R并在200例PG病人中测试,PG-13-R中文版Cronbach′s α系数为0.85,显示量表具有良好的评定者信度。
2.3 国际长期悲伤障碍量表(International Prolonged Grief Disorder Scale,IPGDS) 由Killkeely等[25]于2020年开发,包含基于ICD-11的PGD新标准的13个项目的普通量表和针对文化适应的19个项目的补充量表,发现有创伤性丧亲经历的丧亲者具有更高的悲伤评分,目前有德语和中文2个版本。在德国的214例和中国的325例丧亲者中首次得到验证,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96和0.97,具有较强可靠性。
2.4 事件影响量表修订版(Impact of Event Scale-Revised,IES-R) IES由Horowitz等[26]于1979年开发,是测量创伤后应激反应的调查工具,1997年由Weiss等[27]进行修订,形成IES-R,测评不良事件对测试者的影响,分3个维度,共有22个项目,采用5级评分制,大于35分即为PTSD。2007年由郭素然等[28]进行汉化并检验,其Cronbach′s α系数为0.902,表明具有良好的评定者信度。
3 哀伤的分期
根据1964年提出的安格乐理论[29],丧亲者的哀伤过程分为6个阶段:冲击与怀疑期、逐渐承认期、恢复常态期、克服失落感期、理想化期、恢复期,在相应的哀伤阶段针对其特点做出对丧亲者有利的干预措施,减轻丧亲伤害,降低哀伤反应。
4 对创伤性丧亲的哀伤干预
4.1 冲击期与怀疑期 本阶段的特点是感觉麻木、否认、抗拒接受死亡事件,这一点在意外死亡的情况下最为明显[29]。
4.1.1 丧亲者的社会支持和应急保障 Aoun等[30]的研究表明,丧亲人群中未获得足够社会支持的,有46%~49%的身体健康情况恶化的可能性;而在获得足够社会支持的丧亲人群中,该比例仅为17%~18%,可见社会支持对丧亲之痛有着缓冲作用。由于对亲人遇难的消息感到震惊和怀疑,遇难者家属第一时间前往事发地求证事实、寻找亲人,如“3·21”东航MU5735航空器飞行事故遇难者家属两百多人前往事故现场[31],6·1东方之星旅游客船倾覆事件遇难者家属前往事发地。东航MU5735事故救援组为遇难者家属预订当地的酒店,并为其配备心理救援团队,保障前来的遇难者家属基本生活需求和急性悲伤期的哀伤诉求。东方之星沉船事件发生后,当地组织为前往的遇难者家属提供全天候的食宿保障[32]。
4.1.2 心理急救(Psychological First Aid,PFA) 由于公共事件的突发性和不可控性,突然的丧亲事件常常引发丧亲者强烈的哀伤反应[33]。丧亲者甚至因突发事件失去工作、财产[34],在多种压力之下会导致巨大的身心创伤,出现延迟哀伤反应或滞后哀伤[35]。此外,自然因素和政策制度常导致交通阻断和社交隔离,加重丧亲者的无助感。据报告,东航MU5735事故救援组第一时间配备了心理救援团队接待遇难者家属,保障了前来的遇难者家属在外的基本生活需求和急性悲伤期哀伤诉求[36]。
4.1.3 规范媒体报告 媒体时代下对灾难事件的舆论信息传播报告呈现一定的失序和混乱[37],灾难舆情信息的传播常呈现出非理性化,滋生大量针对事件或遇难者的谣言,导致丧亲者认知偏差,产生负面认知,引发负面情绪等[38],对遇难者家属造成巨大伤害,升高延长哀伤、抑郁及焦虑情绪的危险因素,加重丧亲者哀伤[39]。根据Michael等[40]理论, 在应对公共紧急事件时,官方应掌握信息发布主动权,实时提供信息 ,实事求是地发布报告,在谣言生成之前,把控舆论方向,并且加强社交媒体平台管理,管制自媒体对灾难事件过度解读和不实报告,减少谣言生成,避免遇难者家属再受到不必要的伤害。
4.2 逐渐承认期 认识到亲人死亡的事实,于是出现发怒、哭泣、自责和空虚等痛苦表现。穴位刺激调控:穴位刺激调控法即穴位电刺激,采用9 V,40~50Hz低频治疗仪刺激劳宫穴和内关穴[41],刺激该穴位具有解除心悸、焦虑和安神养心的作用[42],穴位刺激调控法在精神疾病领域得到广泛应用[43],该方法用于灾难后丧亲者心理干预,在汶川大地震救援工作中得以实践,取得良好效果[44-45],有助于灾难后丧亲者哀伤辅导快速进行。
4.3 恢复常态期 丧亲者带着悲痛的心情开始处理死者的后事,完成与丧失客体的分离,开始回归正常生活。如期举行的丧葬仪式:丧葬仪式对于丧亲者的哀伤有特殊修复功能;丧葬仪式为丧亲者提供了特殊的时空,进行与丧失客体的分离、获得集体支持以及寄托哀思,维持与已故亲人的情感联结[46-47],从而更好地从丧亲之痛中恢复[48],因此丧葬仪式对丧亲者来说有着积极的心理动力学意义和心理治疗价值,并且对灾难后的丧亲者有更加重大意义[49]。
4.4 克服失落感期 此期是设法克服痛苦的空虚感,但仍不能以新人代替失去的、可依赖的人,常常回忆过去的事情。叙事护理:朱慧[50]的研究表明,叙事疗法在地震丧亲者哀伤干预中有积极作用。丧亲者(幸存者)叙述事件发生前后的经历或与亲人相关的生活事件,对事件进行积极构建,感受亲人间的温情,重新融入社会和家庭。但是当丧亲者处于急性悲伤期时,常表现出抵触情绪,以致加重负面情绪[51]。因此在哀伤干预实践中应该首先评估丧亲者的认知水平和情感状态,确保其处于持续且较为稳定的哀伤状态。
4.5 理想化期 认知行为疗法(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CBT):合理情绪理论(Rational-Emotive Therapy,RET)是认知行为疗法中的基本方法。丧亲者的负面认知往往加重丧亲后的哀伤反应如焦虑、抑郁等。将丧亲者对灾难、事故认知合理化,有利于产生更合理的哀伤反应,减少抑郁、恐惧等情绪产生。Lenferink等[52]的研究表明认知行为疗法对2014年乌克兰空难遇难者家属有良好的减轻悲伤症状作用。同时,Bryant等[53]的研究证明结合暴露疗法的认知行为疗法对丧亲后的PGD病人有着更佳作用。
4.6 恢复期 在恢复期,身体得大部分功能都恢复,但悲伤并未消失,丧亲者时常回忆起已逝亲人,这一时期的哀伤干预宜选用时空因素上更便捷、经济成本更低的措施。在线哀伤干预:丧亲者的恢复期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成本较高的干预措施使丧亲者难以长期负担,从而加剧悲伤症状[54],因此在线哀伤干预是一种较好解决方案,线上干预形式目前主要有邮件干预、基于网页和手机APP的干预[55],主要方法是在线CBT[56]。通过互联网提供CBT能够减少丧亲者在寻求丧亲支持中的阻碍,如协调处理学习和工作、照顾家庭的时间和出行不便[57]。此外,在线CBT可以降低治疗成本,使需要支持的人更容易获得治疗[58]。
5 可行性分析
5.1 个人层面 遇难者猝然长逝,丧亲者未能与亲人道别,难以表达哀伤,陷入哀伤剥夺的状态[59]。在非自然丧亲者中,近一半丧亲成年人患有PGD[60],是自然丧亲者的500%[60-61],在丧亲者生活中主要受到影响的有生理功能和社会功能,其中社会功能主要包括工作、活动和人际交往[62]。根据Oexle等[63]的研究,创伤性丧亲者受社会支持程度显然有助于缓减丧亲之痛的一系列反应,因此对非自然创伤性丧亲者进行哀伤干预是十分必要的。
5.2 社会层面 国内疫情平静后,人们在疫情期间遗留下的心理创伤,曾被放大的焦虑,暴露出生死观教育的缺位,在追求经济发展的今天一时难以消解。胡宜安[64]认为,如果能处理好丧亲带来的悲伤,走出死亡的阴影,自己回归常态,这也是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健康回归。
5.3 国家层面 2020年初疫情爆发时,国家卫健委牵头派出两批次共300名心理卫生工作人员前往湖北进行“救心”工作[65],国家对人民心理创伤和悲伤需求十分关注。2020年3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民政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66],强调关注因公殉职者的家属、病亡者的家属,做好心理疏导和哀伤辅导。因此,探索特殊情境下的哀伤辅导策略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6 面对的挑战
6.1 医护和社会工作人员缺乏专业的丧亲护理相关知识 目前我国安宁疗护的发展尚且处于起步阶段,丧亲支持作为安宁疗护中的关键部分。根据Dodd等[67]的研究显示,专业人员在术语、标准和诊断方面缺乏共识,给丧亲者带来的帮助有限。
6.2 社会大众对丧亲支持的认知不足 受儒家“重生忌死”的传统思想影响,国内公众通常规避死亡相关话题,避讳死亡相关信息[68],丧亲者往往不愿接触和了解丧亲支持,拒绝被提供哀伤支持。
6.3 缺乏政府主体的有力支持 由于我国较少存在哀伤辅导的相关社会组织,丧亲支持的推行缺乏动力,需要强有力的政府领导、协调各方,和不同组织如社区、精神心理工作者以及社会工作者之间的密切合作对丧亲者度过哀伤至关重要。
7 小结
面对亲人猝然长逝,遇难者家属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丧亲支持帮助丧亲家属愈合伤痛,让家属在亲人离世后尽快恢复正常生活。心理救助人员应探索适合我国文化的非自然创伤性丧亲支持模式,提供个性化干预措施,以恢复各事件遇难者家属心理健康,促进社会心理健康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