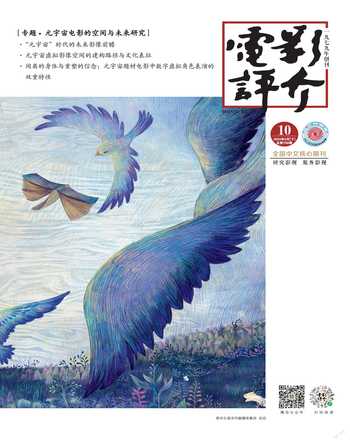中国影视作品中的传统音乐、“知己”情结与乐器意象
李艺

对于仅仅有近百年历史的电影与电视艺术而言,中国传统音乐浓缩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内涵的艺术形式,在年轻的视听艺术对比下可以说是一位古老的东方“智者”。当“年轻”的电影艺术与“古老”的中国古典音乐艺术相遇,音乐的旋律本身、乐器与演奏者在画面中的再现方式、演奏风格和指法技巧等种种元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电影的整体美学风格与艺术呈现。民族音乐作为一个历史悠久、意义稳定的“他者”,是怎样被再现为影像、又是如何被纳入叙事?
本文将围绕这一问题,从传统音乐与影视艺术的“碰撞”出发,探讨中国影视作品中对传统音乐的各种呈现方式:它们一方面成为参与电影叙事的重要意象,另一方面也被征用和“再造”为“知己”情感交流的中介,作为象征性的文化符号承载和召唤着对崇高情感的想象。对电影中的传统音乐进行检视,不仅有助于更好地解读视听文本,同时也能够为构建电影的民族性表达的命题提供启示。
一、传统音乐元素的多重呈现方式
电影美学理念与表现形式的配合,是将传统音乐元素融汇于影视作品中的关键。中国传统音乐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民族美学形式的高峰之一,当下的影视剧作品勇敢地攀登这一高峰,不仅要突破音画对位形式与神话传说题材的舒适圈,转向浩瀚的中国历史文化开辟新的故事蓝海,更要挑战国产影视剧的叙事容量限度和叙事内容深度,在思维呈现、景观呈现、意蕴呈现三个层次上,同时体现民族音乐与影视艺术结合的、具有新意的民族美学形式。
在思维呈现上,应当在以传统音乐为主题的影片中采用恰当的视听形式与配乐,让影视作品的美学理念与技术前提相匹配。“将蒙太奇的原则运用于电影音乐会有助于它在当前的发展阶段更加胜任,首先只因那些媒介的进展一向是相互独立的,把它们整合起来的现代技术并非由它们所产生,而是由新的复制设备的出现所促成的。蒙太奇充分利用了有声片附属性的美学形式,把完全外在的关系变成了一种实质性的表现性元素。”[1]换言之,传统音乐与电影视听形式的结合应该以增强两种艺术在当前发展阶段的表现力为题中要旨,在两种媒介自身审美形式的独立性中充分利用有声片附属性的美学形式。
在景观呈现上,传统音乐元素赋予影视剧作品具有民族特色的创作思维与文化形象,为中国电影的创作与中国电影学派的研究提供新的切入视角。例如《长安十二时辰》(曹盾,2019)的第一个镜头出现了唐朝时广泛流行的五代曲颈琵琶,由一名身处歌栏酒肆的美人弹奏。琵琶起源于古代印度,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并被加以改造;这一样式的五代曲颈琵琶呈实心,颈后弯曲近直角,腹呈半梨形,颈上有弦轴五根,属于四弦曲项琵琶。这一五弦的样式只流行到唐代,到宋代教坊中便不再使用了,五弦曲颈的样式也逐渐被四弦直颈的样式所取代。在唐代,琵琶分为四弦曲项和五弦直项,琵琶一般是指四弦,而五弦琵琶被专门称为五弦。《旧唐书·礼乐志》中记载:“琵琶、五弦及歌舞伎,自文襄以来皆所爱好,至河清以后,传来尤盛。”[2]可见五弦琵琶是唐代的盛行名物。《长安十二时辰》中琵琶一出场,无需多言,便将观众带到了琼楼玉宇、金碧辉煌的国际大都市——长安城;而《长安十二时辰》中使用的《清平乐》《短歌行》《长相思·在长安》等配乐也运用了琵琶这一具有盛唐特色的乐器。值得一提是,琵琶女采用的是中国曲项琵琶在唐代典型的抱持法,即将琴体横于怀中,琴首向左下方倾斜,富于时代特征。在清脆的音色与灵活多变的曲调中,源于西域、盛行于唐代乐舞中的琵琶也成为盛唐景观与盛世气象的一部分。这样的视听呈现,不仅令影视剧作品与故事背景贴合,充满传统审美韵味,更有助于传承与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审美观念,切实探求新时代背景下蕴含在影视作品中的文化自信。
如果将景观的呈现层面进一步延伸,便可以在意蕴呈现的层面上发掘传统音乐与民族乐器的应用潜力。当传统音乐以客观音乐的形式出现在影片之中,抑或民族音乐的琴身被摄入到镜头、框定到银幕上之时,二者之间总是显示出不同文化与美学之间的微妙张力,进而显示出超越语言表达的独特韵味。例如在电影《刺客聂隐娘》(侯孝贤,2015)中,导演为了将古琴完整放置在画面中,特地采用了两种画幅比。在大多数镜头中,镜头的长宽比为1:41;但在有嘉诚公主抚琴和她道出“青鸾舞镜”典故处,影片画幅比变为1:1.85。这一场景采用中景镜头拍摄,嘉诚公主身披华服,将一把古琴横置于膝上弹奏,人物与琴成为画面的中心与主体,前景和中景的草木、背景中大片的白牡丹伴随寂寥的琴声徐徐摇曳,展現出清幽寂静的氛围。导演侯孝贤本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一场景使用宽银幕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一种构图上的考虑:由于古琴的长度超出了画面边框,只有放宽比例才能让琴身完整入镜。[3]导演固然可以将古琴放置在对角线上,让琴与角色分离,或更换拍摄角度来保持整部影片在形式上的统一性,减少技术上的问题;但对于这一幕的主人公嘉诚公主而言,从小远嫁到藩镇独自生活的自己,就宛如“青鸾舞镜”中“见类悲鸣”“奋舞而绝”的青鸾一般孤独,她通过琴声状说内心借喻自己,响亮的裂帛之声也逐渐转变为表现清远幽寂的泛音,恰恰体现出此时她内心由激越到平静的变化。借用德国学者阿多诺和汉斯·艾斯勒在《论电影音乐》中的表述来说,公主手中的琴与琴乐对这一场景而言“不是装饰性的,而是本质性的”[4]。这一场景中的古琴并不仅仅意味着一种乐器道具呈现在外在的视听景观上,更作为主人公身体与灵魂的一部分参与到影像深层意蕴之中;与此同时,电影的叙事建构或美学营造也在某种程度上因中国传统音乐的要素介入而展现出更为独特的样貌。
二、“知己”情结的内涵与外延
中国民族乐器历史悠久,几乎与华夏文明同时诞生。东汉《风俗通义》记载伏羲氏“削桐为琴,绳丝为弦”,《礼记·乐记》则载“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此外还有《山海经》中的“帝俊生晏龙,是始为琴”之说。[5]尽管事实究竟如何尚无定论,然而民族乐器在周朝确已存在,并且至少在两千年前就具备了相对完整的美学系统早已成为学界共识。无论是音色与旋律的借用,或者展现演奏的场景,影视作品中的传统乐器依然携带着自身的文化性。其中较为典型的一种,便是乐器演奏时通过乐曲达成的心意互通之感,即大众所熟知的是伯牙子期“高山流水,知音难觅”的传奇故事及其衍生的意蕴。按照《吕氏春秋》中的记载,琴师俞伯牙与钟子期互为知己,二人由琴结识,留下了“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佳话;而当子期死去,伯牙便“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足复为鼓琴者”。[6]通过这一典故,古典乐器在今人之视角中往往被看作是高雅贤士缔结君子之交的纽带。
中国影视剧中普遍存在通过传统乐器的合奏和对奏表现知交情谊的场景。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知音》(谢铁骊、陈怀皑、巴鸿,1981)便讲述民国初年社会身份差距巨大的蔡锷与小凤仙通过古琴相知相恋的故事。《知音》以女扮男装的小凤仙以激越的《潇湘水云》抒发欲报国而不得的情感,被蔡锷制止而后演奏《流水》开始;以病重中的蔡锷孤身在日本医院中听到一丝若有若无的琴音,而前往蔡锷湖南老家途中的小凤仙在船上弹琴断弦结束。影片中慷慨激越的古琴演奏交代了电影的时代背景和人物性格[7],奠定了整部电影的叙事基调;也将身份悬殊的主人公通过琴曲引为琴中“知己”,在沉重的历史基调下展现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特有的轻盈与浪漫。历史传奇影片《赤壁》(吴宇森,2008)中诸葛亮与周瑜切磋琴艺的“斗琴”片段,也通过演奏古曲,由相互试探到互明心意。这一场景采用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唐建平特地重编的《流水》版本,古琴演奏指导为古琴演奏家赵家珍。[8]二人的演奏首先以激昂慷慨之气作为开端径直进入主题,此段借鉴大曲《广陵散》的部分旋律,具有戈矛杀伐战斗的意味,仿佛意欲以此营造激越肃杀的气氛;继而合入另一支旋律,从而预示二人意欲结成同盟、联合抗曹的决心,相互应和同时又显得有所龃龉,暗示瑜亮二人虽惺惺相惜、互为知音,却终究不免一战。这一场景并无一句对白,镜头只在演奏者的面部表情与手部动作之间来回切换;但古典音乐与运镜的配合,不仅传递出此时由紧张到舒缓的人物关系与人物情绪,还扮演了两位智者谋士之间互相引为知己、缔结吴蜀政治联盟的中介角色,同时也为片中两人亦敌亦友、惺惺相惜关系的可能走向提供了想象空间。
在人人向往的“知己”情怀中,也有影视创作者借民族乐器与传统音乐进一步探讨“知己”的深层内涵。影视剧中传统民乐独奏的场景中,尤其能体会“知己”所“知”的深刻内涵。与其说所谓“知己”之“知”意味着透过琴音望向他者、叩访他者,不如说,这是一个以他者为镜,照见自我的过程。例如《山河令》(成志超、马华干,2021)中常抱琵琶出场的蝎揭留波,不仅用南音琵琶琴首向左上方的斜抱法表明其身份,还以琵琶独奏展现自己的情感诉求。出身南疆的蝎揭留波从小便是独自一人长大,既无亲人又无师门;琵琶不仅是他的武器之一,也是孤独者表情达意的工具。蝎揭留波企图通过琵琶找寻知己,在感慨知己难觅之时,实际上是在空无一物的世界中,希望从他者身上辨认出自我、辨认出某种“理想化的自我客体”[9]的过程。独自一人从南疆远赴中原的蝎揭留波以琵琶状说内心又欲说还休时,一身黑衣的自身也与黑色的琵琶融为一体,成为空无之中一片倾听心声空鸣回响的空间。蝎揭留波以琵琶建构自身,发现自我,这一自我的发现过程却是以“知音”的缺席为前提的。可见,制作人、编剧与导演不仅在叙事便利和文化符号的意义上征用了传统音乐关于“知己”的内涵,也在视听意象所蕴含的复杂性上有所自觉,经由传统音乐而展开关于“知己”意涵的外延进行叙事时展现出深刻的思考。
三、“观物取象、立象尽意”的民族乐器
影视作品中的民族乐器也常常作为“意象”出场,在点明时代背景、渲染基本情绪以外,以“象”增“意”营造出独特的意象世界。影视作品中的意象世界是对“自我”有限性的超越,是对“物”的“实体性的超越,是对主客二分的超越,从而回到本然的生活世界,回到万物一体的境域,也就是回人的精神家园,回到人生的自由的境界,是超越与复归的统一”[10]。中国影视剧中的民族乐器与现实中的民族乐器相对接,也将想象的历史意象与现实空间相融合,在现代视听艺术的展现下凝结民族想象和文化自豪感,不仅令传统民族乐器再次焕发出盛世华音的光彩,也从形式与技巧等方面为中国当下的影视剧创作拓宽了思路,提供了一条不同于商业化和西方化的中国故事讲述经验。
《长安十二时辰》第八集中有一个琵琶局部的特写镜头,而这一把没有露出全貌的琵琶就是一把五弦琵琶。李龟年、李白为首的诗人俊杰饮酒后抱琵琶站在二楼临时搭建的一块木板上即兴配乐作诗,需要在一曲琵琶曲结束前作成诗才能走下木板,成诗者在众人的欢呼和掌声包围中受到英雄般的待遇,不成者则要跳到一楼的泉池中脱身,引得满堂风流名客起哄叫好。参与诗酒琵琶集会的有唐玄宗的亲侄子汝阳王,也有平民,他们坐在一起喝酒论诗,展现出一个足够包容和自由的社会。
在中国的影视实践中,对宏大历史的视听呈现不能仅仅是一处包含着的奇幻想象,也不仅是那些华灯万盏,歌舞升平中无根无据、千篇一律的风流才子、悦目佳人。“这是空前的古今中外的大交流大融合。无所畏惧无所顾忌地引进和吸取,无所束缚无所留恋地创造和革新,打破框框,突破传统,这就是产生文艺上所谓‘盛唐之音的社会氛围和思想基础。”[11]对于盛唐诸多景观的展现应当如同盛唐诗歌的创作一般,从外在的富贵风华以及卓越武功下沉至具体生活方式与意象中。《长安十二时辰》中的胡琴、琵琶、胡笳等民族乐器作为展现“唐风”的具体意象,充分展现出唐王朝文化融合的氛围,胡汉之间的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丰富多样的民族乐器与其他意象一同伴随着主人公的脚步遍寻长安的亭台樓阁、扬州的勾栏瓦肆、塞北大漠、江南水乡、田园风光等等,具体展现出从南至北的地域跨度,从庙堂到江湖的社会架构,造就了大唐丰饶的物产和特有的异域风情,成为装点大唐的璀璨珠宝。
结语
民族乐器与传统音乐寄托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内涵和象征体系,当前影视剧的创作超越了简单化的符号意义,作为古老艺术的年轻“智者”介入其中,为人们检视传统音乐在视听呈现中的创意性转化命题提供了新的思考路径。
当传统音乐作为意象在电影中得以再现时,它不单内在于某种民族文化认同的召唤机制,而亦可能深刻地参与到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视听形象的再创造当中。今后,中国电影如何再现和使用传统音乐,如何经由丰富多样的民族乐器意象来辅助影像叙事、营造美学外观、唤起民族认同等问题,都将为人们在当今的时代格局中思考华语电影应如何讲述中国故事、如何构筑具有中国气韵的影像表达,以及如何理解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提供新的启示。
参考文献:
[1][4][德]特奥多·W.阿多诺,[德]汉斯·艾斯勒.论电影音乐[M].刘斐,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16,40.
[2][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全十六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5:11.
[3]侯孝贤,谢佳锦,王志钦.《刺客聂隐娘》:阐释的零度——侯孝贤访谈[ J ].电影艺术,2015(04):107.
[5][8]耿慧玲.琴学论衡:二〇一五琵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重庆:重庆出版社,2016:51,29.
[6]张双棣.吕氏春秋·孝行览[M].北京:中华书局,2022:315.
[7][明]朱权.神奇秘谱(下卷)[M].北京:音乐出版社,1956.
[9][美]克里斯托弗·拉什.自恋主义文化 心理危机时代的美国生活[M].陈红雯,吕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78.
[10]叶朗.美在意象[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7.
[11]李泽厚.美的历程[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315.
【作者简介】 李 艺,女,贵州铜仁人,贵州大学音乐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