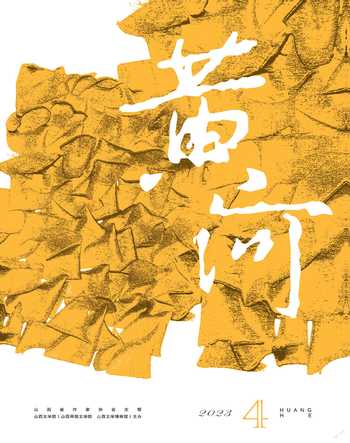自然与灵魂:当代小说的叙事生态学
曾攀
生态学(Ecology)这个概念最早由恩斯特·海格尔(Ernst Haeckel)于1866年提出,他认为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体同外部环境之间关系的全部科学”,在这个意义上,我更愿意将“生态”视为一种具有总体性意义的方法,特别是将之纳入小说叙事范畴中加以考量时,便意味着从自然到灵魂的修辞链条中,“生态”的观念参与到精神以及伦理序列的构造,这个过程是有机的,也是多元的,其常常于宏阔处,在纵深中,创生修辞的肌理。
具体来说,这凸显的是一种从自然到灵魂的叙事生态学,当然,此间不仅可以透析出小说叙事的內外表里,更意味着开掘内心的、探照灵魂的尝试。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小说所描述的自然,如何进入人物主体的人性及其灵魂腹地,与之对话、协商、汇通,如何与小说的修辞结构相互嵌合,传递出整体性的意义属性?这就涉及到叙事生态学的一种,简而言之,从外部的环境,到内在的生态,小说叙事中自然与灵魂的交互,主要呈现为对照式、沉浸式与超拔式的三种范型。
周蠧璞的长篇小说《日近长安远》(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写罗锦衣和甄宝珠两个性格、路径、命运殊异的女性,她们是村中邻里,从北舞渡出走来到城市,然而很快甄宝珠便折返回乡,罗锦衣则一直在城市摸爬滚打,善恶交加。最后,遍体鳞伤的罗锦衣回到乡土,那里无不是清新的自然、醇厚的人情,“一切都回来了,接上了”,她仿佛未曾离开过,她的灵魂在归途中得到了休憩。回望过往,罗锦衣百感交集,“记得小时候,某一天清晨醒来,天地寒肃,屋后空地上,一片白茫茫,将昨天干枯的落叶覆盖,低头细看,是针鼻大小的露珠,结成小小的颗粒。手指轻轻滑过,它们温柔地融化了,趴下哈口气,它们顺从地流淌了。”而如今,那些恒久不变的自然依旧在发挥效用,“转眼之间,它们又恢复了晶莹的颗粒。如此微小的体积,却因数众,足以改变世界。”在罗锦衣那里,她在外面世界经历的创痛、犯下的罪愆,都衍化为了灵魂的了悟:“炉边半小时,人间数十载,在罗锦衣心里,是做了一场长梦……”在故乡,罗锦衣的内心不断得到沉淀,乡土的自然引向精神的救赎。在她那里,能够“改变世界”的,是自然的生态、人心的情状,也是对欲望心理的修补或修正。小说正是通过乡土与城市、罪恶与良善等多重对照,实现乡土自然对内在灵魂的疗治功能。
论及文学的生态维度,乡土世界是一种天然的素材。李约热的短篇小说《捕蜂人小记》(《民族文学》2021年第8期)写第一书记的驻村见闻及现代视阈里的乡土人情。野马镇农民赵洪民一度向往城市生活,在木板厂务工,心旌动摇,恋上了工厂老板钟铁的女儿钟丽华,以致辜负了妻子赵桃花,最终也折戟沉沙,只能黯然离开。无奈又或自愿地,他同样返回乡里,回到妻子身边,投身自然过起了捕蜂人的生活,那是他的谋生手段,更是疗愈灵魂的方式。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小说,涉及到了当代小说叙事的深层生态观念。面对这场伦理的风暴,赵洪民赎罪的方式是回归乡土与自然,与赵桃花结婚、离婚,再结婚。他到蜂群中去,当一个捕蜂人,“那群野蜜蜂越来越近。赵洪民和李作家一人一把装满沙子的塑料容器,严阵以待。他手指上的绑带格外醒目。”小说沉入乡土的生活世界与自然世界,呈示出传统对现代的纠错功能,以唤醒新的价值伦理。赵洪民朴质、踏实,他最终一头扎进乡土的自然之间,沉浸于一个个养蜂与捕蜂的现场,忘却了劳累和疼痛,养家糊口、经营家庭,以实现自我的救赎。
冯骥才的长篇小说《艺术家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主要写三个艺术家楚云天、洛夫、罗潜的生活及精神走向,牵引出当代中国的一个艺术群体,在他们身上,体现出美学精神的当代遭际。故事最后经历种种的生离死别,而“自然”成为了超脱灵魂的媒介,主人公楚云天为追念友人,踏上了缅怀之旅,“心中忽然涌出一种情感,一种对那位刚刚夭折的天才,对那位至死还是默默无闻的伟大画家的痛惜,悲哀,不平!这情感一下子与眼前这片了无人迹却无比壮美的山水融为一体。”人物情感的悲喜通过“自然”得以生成,且达到升华,这是经由艺术与美的超拔式融入实现的。在这个过程中,从自然到灵魂固不是平坦之途,往往历经曲折与停滞,甚至度过断裂与悲怆,终而达成灵魂的超脱和生命的超越。另一部长篇小说艾伟的《镜中》(浙江文艺出版社2022年),小说透过建筑的、戏剧的、音乐的、宗教的,当然也包括文学或曰叙事的多元镜像,解析主体心理,透视深层人性。在不同的媒介对照中,人的灵魂得以充分辩证,历史的与现实的、自我的与他者的、宗教的与世俗的,一切若在“镜中”,这是无限的与无极的,未竟的与未然的,更是繁复的与美学的,经此生成关于灵魂叙事的结构诗学,从自然到灵魂的多重路径在此可见一斑。再者还想谈一谈孙甘露的长篇《千里江山图》(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其是雅致的也是通俗的,是难得一见的打通雅俗的好作品,也是虚构的也是实证的,这是一部虚构作品,却又处处对应着历史,不架空,也不浮夸,虚实相生写上海,写一座现代的城市,有宏大的旨归,叙写言说又常常落到实处;不仅如此,这个小说是历史的也是未来的,革命、谍战、牺牲,是惊险的、惊奇的,同时充满烟火气,布满了对现实的摹写,也充溢着对未来的构想。值得一提的事,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是宋代青绿山水一种,代表着历史化之“自然”的再现,而孙甘露的《千里江山图》则将历史归置于革命叙事之中,还原革命的“自然”与革命者们的历史色彩/格调。
与所述论题多有相关的,还有当下如火如荼的“新南方写作”的文学思潮,这里牵扯的话题很广泛,我主要以“新南方写作”的代表作品葛亮的《燕食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厚圃的《拖神》(作家出版社2022年),以及朱山坡的《萨赫勒荒原》(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和凡一平的《四季书》(中国青年出版社2022年)为例,阐释当下的文化多元主义的探询。《燕食记》写饮食文化,特别有意思的是里面提及粤菜形成的多元传统,及以饮食味核心贯串的地方性文化的多样探索,重要之处还在于,如小说所提及的粤菜的形成路径和发展动向,其中不同菜系的融合,不同生活方式的互渗,代表着文化的多元交叉并且还原了此一过程的驳杂繁复,透露出一种价值生态与精神生态的本来面貌。《拖神》也是很有意思、非常庞杂、也极为丰富的文本,写出了三教九流、龙蛇混杂的南方民间世界,其中充满了种种野性、神性、魔性,以潮汕地区为中心的“南方”的“生态”,映射成方言的、民俗的、生活的镜像,不同主体在这样的意义体系中,如万花筒般呈现出内在的光影。“南方”是一种地方性的风物、风景、风气之呈现,自然之景象中,往往包孕着人性与灵魂的向度。朱山坡的短篇小说集《萨赫勒荒原》,一是天马行空的虚构,二是矢志不渝的冒险。这里面有密切的关系,正因为小说是一场盛大的虚构,所以叙事者才敢如此放肆,如此忘乎所以,在人物的以身犯险中,推衍至主体的边界和人性的临界点,在故事的纵深甚至幽暗的时刻,洞察现实的真相与真义。“荒原”的自然形态之中,无不隐喻着灵魂内部的焦灼及其对于焦灼的反抗。
在这里我想特别提及一个有意思的文本,凡一平的长篇小说《四季书》。小说讲的是上岭村民韦正年传奇曲折的一生,以一个人沉浮跌宕的小历史,实际上撬动了二十世纪以来百年中国波澜壮阔的大历史。那些微观的与壮阔的时间,如四季般周而复始,也归寂,也重生,完成生命的与自然的宏大隐喻。实际上小说蕴蓄着一种潜在的内在价值序列:首先是个人史观,生活史、情感史、奋斗史;其次是革命史观,如故事讲述的20世纪中国的革命进程;再则是生命史和自然史。也就是说,小说最终是从个体与历史中跳将出来,对生命与自然加以观照。一个隐含的信息却是,在一轮四季的时序之后,又会有新的一轮四季更替重新开始。不得不说,我们的每一天都是新鲜、新颖的,好的文学给予我们的也是这样的不断得到更新的生命气象/想象,我们也得以借此去创造新的世界。纵观主人公韦正年传奇与现实交织的一生,从最初因病被父亲抛弃山洞,仿佛是海德格尔存在主义式地被“抛入”这个世界,却得到了拯救,仿佛自然万物如蚂蚁,但是不可或缺的则是革命、爱情,以及亲情、友情的滋养和激励。最后人物主体彻底融入了这个世界,以自我生命的消亡,化入万物与自然之中。小说在结构上非常独特、完整,其中能够凸显文本内在的伦理:生活的、革命的、经济的,更是生命的与自然的指向。从较低的价值层级,不断演化到更高的精神和生命的意义层级。从理性的主体到情感的主体,包括反思和忏悔的主体、自然的主体,其中少数民族地区的边地的人情人性,与高度理性化的现代主体不断交叉重合,又多有不同。可以说,《四季书》以边地及其自然为视角、中介,去开掘人心人性的深广度,并借以经验、发现乃至重新讲述百年中国的历史进程。
同样是在南方,孙频的小说《海鸥骑士》(《收获》2023年第2期),大海与陆地代表着两个迥然有别的世界,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态系统,小说写父辈的隐与现,述及父亲在大陆上几乎没有朋友,甚至语言能力都退化为古生物。“可以一整天不说一句话”,由此可见海洋之子的内心所向,两个世界的碰撞,对人的内心无疑是充满震荡甚至是撕裂的。小说提到父亲从海上回来,也曾试图做一个“陆地生物”,其间毫不讳言人类从生灵到生物的转变,却并不是刻意贬低主体自身的存在可能,而是为了揭开另一种人生,打开另一重生命的类型以及精神的状况,“在我记忆中,父亲也不是没有在海陆之间挣扎过。有一年父亲真的从海洋踏上了陆地,提着全部行李,打算开始做一只陆地生物,因为母亲对两地生活长年累月的抱怨,大约还因为觉得我从小缺失了父爱,总之,出于对家庭的愧疚和补偿,他真的一咬牙下了船,在航运公司谋了份差事。但这个过程只持续了半年,那半年时间里,父亲看起来干旱而笨拙,如一只刚刚开始进化的史前动物,离开海洋,误入了陆地,言语变得愈发稀薄了。人际关系的周旋使他看起来愈发干旱愈发史前,古老如一只鲎,我时常想在他身上浇些水,怕他会在陸地的社交中干渴而死”,他们的生存意念、认知系统和话语方式,都与一般意义上的陆地生物迥异。他们往往被视为蛮荒,也不得不忍耐空寂的折磨,在海陆之间看船,成为了我和父亲真正的唯一交集,而书信的往来则成为母亲与父亲的有效沟通。这样也就使我有了一个“幻影父亲”,在“风和云居住的远方”,我们采取或实或虚的方式形成或隐或显的交流。随着父亲的跳海失踪,我翻来他的遗物,第一个日记本是他的海上日记,更多的是写实。第二个日记本是他记述的海上传奇,多与海难相关,但均为虚写,第三个日记本“贴满了不知从哪里剪下来的各种名画和印刷品”。在其中,能够见出作为海员的父亲的爱好,或曰寂寥,父亲的经历震动着“我”,“我”也下决心要追随父亲的脚步,去大海做个水手。于是海洋视阈便从间接经验进入了直接经验,而这其中涉及到的双重“生态”体系的切换以及从自然到灵魂的转圜,经由陆地—海洋、父—子、虚—实、生—死等多重维度生成,最终还推及更为广阔的天地,那不仅是宇宙自然的星团密布,而且意味着内在世界的灵魂镜像/径向。在“我”寻找父亲的下落并且探询他的精神世界的过程里,作为海员的“我”试图抵达更多人的秘密,也在其中见证着天地的浩瀚,“烟花在海天之间绽放,银紫荆如一座忽然从海底长出的热带岛屿,岛上长满了五颜六色的热带植物,榕树、海麻、椰子、槟榔、木莲、榄仁,还有更多叫不出名字的植物。它们攀着月光迅速向星河生长,藤萝交缠,又纷纷捧出了自己的花朵或果实。那些花朵和果实因吸饱了月光和星光,都闪烁着一种珍稀的光华”。由此稍加拓展如是之地方路径与海洋题材的文学新动向,其内部往往自成一种不可或缺的环境/精神生态,并且以自身新的整体性结构,形塑有意味的叙事生态学,于焉获致超拔的伦理指向和价值认同。
当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对照、沉浸与超拔此三种范型并非孤立存在,常常兼而有之,如陶丽群的中篇小说《七月之光》(《民族文学》2020年第3期)写西南边境的大山之中,在对越自卫反击战负伤的士兵老建,遭遇了身体的与情感的创痛,然而他复员后归入自然,完全沉浸于山野与森林之中,“他更喜欢和林子里的安静融为一体,像暮年的生命一样寂静”,同时与他的爱人洛组成家庭,并且领养了一个孩子,一家三口就生活在那片苍茫的土地上。出人意表的是,小说最后,自然的与情感的双重慰藉,逐渐将老建的精神/身体疗愈。不得不说,小说中的内外对照、生命沉浸以至最终的超越性愈合,都指向从自然转圜至灵魂过程中的复杂立体。也由此见出,文学在融聚自然与生态的观念时,不能局限于主题先行与概念主导,而应还原文学文本世界中的众声喧哗与多元价值,回归人物主体的欢喜悲愁以及成长或倒退,并逸出其外,探询当下自然镜像中的成型化变,以对照、沉浸甚或超拔的形式,引导人心与人性的走向。正如雅克·马利坦《艺术与诗中的创造性直觉》提到“诗性直觉”时所称:“诗性直觉既是创造性的又是认识性的,因此,就作品的产生而言,它尤其会被认为是创造性的,而就被它把握了什么而言,它尤其会被认为是认识性的。”值得一提的是,好的文学不仅存在于凡俗的人间、现世的生活、繁复的自然,同时也走向辽远的想象、广阔的天地,蕴生着丰富的人性与诗性,恒久之中的瞬间,也有瞬息万变的永恒。充溢着人世的、自然的与生命的体悟,词藻的华丽或素朴,情感的亲切与浓烈,写天地自然更多有灵性于其中。不仅如此,从自然到灵魂的过程,还清晰地显露出叙事者/写作者的“认识论”,从生活到天地,从灵性到智性,从万物到思想,多元复杂的交互和交叉,构成了意味深远的叙事生态学。
生态文学自19世纪初期美国浪漫主义文学中萌芽,其重要旨向之一就是要解决文化、经济、宗教、现代化等一系列问题,而不单是自然生态的本身,这在艾默生、梭罗等作者的文本中都有所阐发。20世纪初,英国学者乔纳森·贝特(Jonathan Bate)在《大地之歌》中发出对现有文化的质疑:“我们究竟从哪里开始走错了路?”直至21世纪的当下,文学叙事的生态学走向,不断拓展成其广义与泛化的形态,也不断拓宽着自身的边界,由是形成一种“生态”的文学。美国学者伊琳·詹姆斯(Erin James)曾提出生态叙事学的理念,并将“环境”的认识扩大至包括“陌生的、创造的、非现实主义的环境再现以及人们对环境的体验”,不仅如此,所谓的“风景”也是政治、历史、环境、文化等综合而成的产物。这就意味着,真正具备“生态”观念的文学需要回到叙事的范畴之中,同时又放置于更广阔的界域去,寻求政治的、宗教的、文化的介入,进而成为一个视角、一重维度与一种方法,于焉建构内部的精神机制与伦理导向,真正地介入人的精神结构和主体无意识,成为精神、情感、文化的内在反应与自然映射。
宕开一处说,全球化发展的当代逻辑正不断产生逆变,在新世纪的第二、三个十年遭遇严峻的挑战乃至颠覆,如何重新思考当代人的存在方式,反思既定的现代发展伦理与文化逻辑,成为世界范围内不得不回应的命题。因而,当代中国文学或许需要内源性地生成关于生态发展及未来路径的叙事形態,重塑“生态”叙事的历史意义,为新人文时代的发展秩序与价值探询提供多元的可能性。需要指出的是,这其中并不意味着单向度地强调环境、自然和生态,不与既有的社会文化形态和政治经济状况相参考,不真正跟人性、人心、人情相与结合;事实上,在文学叙事中,生态的人性化与人性的生态化,生态的形式化与形式化的生态,存在着深层次的叠加。质言之,书写自然并非就是文学生态化的根本用意,也不是涉及保护生态爱护环境的文艺实践就是生态美学,而且,“生态”不是作为政治正确与文化正确横亘于文本之中,更不是植入文学肌体之内成为既定的理念性存在,这其中势必应当生成有机的结合与叙事再生产的过程。
犹记很多年前读清末曾朴的《老残游记》,小说里有很多环境与景物描写,人置身于自然,自然也内化在人心与历史。这是老残个人化的游记,也是对现代中国的观览与辨析。就在如是这般的现代装置中,小说较早发现了晚近以来真正的“自然”以及何为“自然”,其不再是伤春悲秋、落花流水、雕梁画栋等,而是内在的自我注入历史与自然,外部的世界得以真正形成特定价值序列中的精神实感与伦理情态。在此过程中,小说叙事重要的是恢复人与自然的复杂性纠葛,而不是理论先行与简单输出,纯然正确与无可指摘之物,也并非文学叙事的题材意旨。换言之,广义的文学生态伦理需要与社会政治历史进行兼容,与文化话语有效交互,需要对人的存在本身加以充分的反映,在全球化/后全球化的时代精神状况下,通过复杂多元的美学结构形态,实现内源性的生成。这就意味着,对于不断延展与扩大的叙事生态学,其从自然到灵魂的渗透历程,需要真正建立在文学内部的语言建制、伦理织造、主体发抒、情感结构等加以讨论,才能形成有意味的自然观念与美学构形。
责任编辑:宁志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