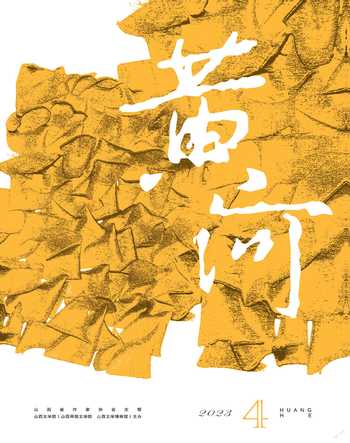雨天,在唐人街咖啡店
下午,下了一天一夜的雨还没有停的意思,但小了。我踱进唐人街的“多多”咖啡馆,没来得及把雨伞合起,柜台后面就响起女售货员的温柔嗓音:“你好,请问要买什么?”我能说的只是“等等”。
天空阴沉,户外光线已显不足,里面更加昏暗。抬头看,过高的天花板上吊着两盏低度数日光灯。电费固然省下,但咖啡馆和烛光晚餐的餐厅不同,务须明亮。小家子气的后果一目可见———只坐着四个客人。生意清淡,使得按小时拿薪水的售货员无聊透顶,这就是为什么她过分性急地和进门的客人套近乎。
我此来,是因等候去看牙医的老妻,找个地方消磨一个半小时,并无意买什么。然而不买而白坐,脸皮够厚吗?低头看玻璃柜台里头,陈列的是各种包点,不乏家乡的传统糍糕,如咸鸡笼、芋头糕、软饼、咸煎饼、萝卜糕。抬头,墙壁上挂的价目表,还列着从未见识过的南瓜馒头、红薯馒头。可是不饿,受不了售货员过分殷切的眼神,点了一杯咖啡。“不要别的吗?”她问。我说,看看再买。
咖啡是自助式,我从咖啡机上斟了一纸杯,热是热的,但过分稠,天晓得是多少个小时前泡的。乌黑的色地,恰与此刻的环境匹配。我在靠墙处坐下,面对窗外。
出于可笑的惯性,但凡阴晦的天气,进入缺乏明亮光线的所在,无论茶餐厅、咖啡馆、茶楼、餐馆,我必产生特别的条件反射———鲁迅的《在酒楼上》于脑际泛起。这篇小说年轻时念得烂熟,如今不但记得情节,连字句也仿佛有人在耳畔朗诵似的。此刻“响”起的是关于船户女儿阿顺容貌的一句:“平常的瘦瘦的瓜子脸,黄脸皮;独有眼睛非常大,睫毛也很长,眼白又青得如夜的晴天,而且是北方的无风的晴天,这里的就没有那么明净了。”与眼前情景形成强烈反差,如此,恰增加了张力。
鲁迅夫子笔下的“酒楼”,外面铅色的天,里头空空如也,墙壁粘着枯死的霉苔。在入骨的阴冷和寂寥反衬下,废园里几株繁花满树的老梅和十几朵茶花,“赫赫的在雪中明得如火”。至于人,“我”的独酌也好,与不期而遇的友人对饮也好,抑郁之状可掬,热的只有温过的绍酒,“煮得十分好”的油豆腐,以及嫌淡薄的辣酱。老实说,愈是老,下意识对这种阴冷文字愈加排斥,如果有书可选,我可不读收录此文的《彷徨》,而会读点寄兴悠远的诗,如纪伯伦,里尔克的。
什么书也没带,只好东张西望。这店的东主不知换了几茬,我猜都是台山人。数十年间,由于这里较为偏僻,我来的次数不算多,每一次都听到售货员与顾客只以台山话交谈。声高且杂沓,一如故乡的墟场,只少了猪崽被阉时比鬼哭还恐怖的惨烈之声。
咖啡涩得近似“易克斯普拉索”(意大利浓缩咖啡),但我不抱怨。若讲协调,咖啡之黑与忧郁的氛围恰恰相称。扫视店内陈设,家具无不老旧。柜台上方供奉关老爷的神龛前,海碗盛着大如椰子的“发糕”,显然是春节的供品,用逾量的发粉炮制的,“发”得像一天飙半尺的春笋,作为生意兴隆之兆。
这个店平时生意可以,否则无法解释它缺乏“地利”的优势,却在激烈的竞争中幸存。眼下却不行,一位老先生和一位老太太在靠落地窗处坐着,两个购物袋搁在空椅上。两人只点了一杯热茶,一只菜肉包,貌似“分享”,其实是为了避雨,和我一样,不吃点说不过去。老太太看雨差不多停了,站起来,拿起拐杖,姗姍走出;而老先生不知何时消失了。我看到他们的桌子上留下一件毡帽,差点站起来,走到门口提醒她。但老先生从后面走来,原来刚才上洗手间去了。他并没有随老太太离开,坐下来,把残余的茶喝下。他们是什么关系?都独往独来,可见不是夫妇。那么,是乡亲,还是“灵魂伴侣”?两个已老到情欲成为奢侈品的同胞,在格外感受独居之苦的时空里,相聚一两个小时,亏得雨的成全。老先生把毡帽戴上,郑重地扶正帽沿,也离开了。
我转而注意到背后的两位中年白人。我进门时他们已在。从制服看,一个是警察,一个是消防员。警察分局离这里一个半街区,消防站离这里一个街区。我观察到,他们不是在享受“咖啡时间”,因法定一节为半个小时,早已超过;那么是偷懒?是休班?是另有职责?对售货员来说,警察可是求之不得的免费保安员,他们坐镇,没人敢行抢。他们在高谈阔论,不时发出笑声。放在平日,纯粹的台山乡音与正宗的美式英语此起彼落,无疑是可爱的多元景观。
我无心偷听,沉浸于一段往事,它就发生在这里。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陪父执辈的舜叔进来,是午后,没有下雨是肯定的,不然我们就无法在大街上溜达多时,直到累了,才想到喝咖啡。那一次,客人不少,清一色的台山人。两人在这里,都吃了家乡驰名的“钵仔糕”。我喝咖啡,他喝港式“丝袜奶茶”。
一如《在酒楼上》的“我”和久别的朋友吕纬甫,话题不是励志,而是深沉灰暗的往事。这位长我二十多岁的乡亲,我从前并不认识,但早闻大名。他是公社一级的干部,资格够老,却永远是科员。多次惹祸,都为了直言。我知道他起步是文学青年,读过歌德的《浮士德》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在他讲故事的时候,一个小个子男人进来,买了一杯咖啡,转身欲离开。舜叔站起来,叫住他:“急什么,一起坐坐嘛!”
我也认出阿超来了。他是我小时候斜对门邻居,比我大两三岁。从三十多年前的1962年起,不曾见过面。但他和在唐人街一家客栈当清洁工的舜叔,不但同住一栋大楼,还一起喝过许多次咖啡。我惊喜地趋前,拍拍阿超的肩膀,问:“记得我吗?”他扫了我一眼,没回答,显然,他对我是不是熟人毫无兴趣。阿超没落座,以随时要走的姿态站立,对舜叔大声说:“我外甥阿豪,考上哥伦比亚大学,今天接到通知!”舜叔适时地兴奋起来,连声祝贺。阿超意犹未尽:“知道哥大吗?常春藤名校!阿豪十二岁才去纽约,第二年就进了天才班,成绩要是落在全级前三名以外,他妈不让他睡觉,罚抄书!小子有出息,我早看出来了……”
舜叔和我当然努力附和,其他顾客竖起大拇指,满堂赞美声,再加点温度,就是普天同庆了。阿超顾盼自雄一会儿,满怀感慨地说:“想我谭某人,落魄一世,受尽欺负,幸亏外甥高中,替我和阿从出了气。”说着说着,抽起鼻子来。舜叔俯身,看了看小个子阿超的脸,温和地说:“这不,守得云开了嘛!”阿超竟嚎啕大哭。舜叔手足无措。别的看客愕然,不明白这位因无所事事而每天必在唐人街各家咖啡馆腻上半天的小个子,以异乎寻常的热情夸外甥倒也罢了,干吗突然伤心至此?舜叔却善体人意,轻拍拍阿超单薄的肩膀,说,好了好了,喜事临门……
阿超把悲伤释放之后,也晓得大家在看他的笑话,边揩泪边走出门,连和舜叔道别也忘记了。舜叔不再说自己的往事,转而解释阿超为什么动了感情:
阿超还有个弟弟,叫阿从(我插话:阿从和我同年,小时候一起玩桃园结义,他太瘦小,只准扮刘玄德)。这难兄难弟,幸亏有母亲的“义弟”上下打点(我又插话:这通天的人物叫阿稔,当过公社政法部长),在最难出境的年代拿单程签证去了香港。本来可以过上好日子,坏就坏在小时候被母亲纵惯了,好逸恶劳,一无所长,读书又少,只是初中肄业,在九龙住了20年,从没正经工作过,只打散工,领点综援。难得的是兄弟相依为命,多年来合租只有一间双层床的“笼屋”,熬了过来。80年代末,他们移民旧金山,因太瘦小且笨手笨脚,无法找到工作,一直领福利金。如今年过半百,没娶亲,合租我负责清洁的客栈一个最小的单房。同病相怜,外出总是一对,成为唐人街的一个景观。今天是例外,因为弟弟接到外甥的喜讯后,兴奋过头,喝了半斤“五加皮”,醉倒在床上。哥哥按捺不住自豪感,独自出来。向所有熟人报喜。舜叔说,阿超大哭,不是为了外甥,而是感怀自家身世,唉……
说到这里,舜叔仰头呷干奶茶,下了结论:“人是不能改变的,但戴的面具会换。今天,你看,阿超犯糊涂,竟戴上外甥的面具。这也好,倒霉蛋总得有一次露脸的机会。”
我点头,想起《在酒楼上》,灰颓的老式文人吕纬甫替昔年邻居的女儿———长睫毛,“眼白青得如夜的晴天”的阿顺,买了两朵剪绒花,一朵大红,一朵粉红,远道而来,不料阿顺已辞世。阿超比他好运,有一个“争气”的外甥供他消减此生的怨气。
我喝完咖啡,该离开了。警察和消防员的聊天持续着,声音大了起来,顾客都听得清楚;他们在比赛说笑话。我怕他们怪我偷听,疾步走出。背后,是他们的笑声,但未必是笑我。街上,雨停了,满目明亮。回头看咖啡馆,灰暗如故。
【作者简介】刘荒田,广东省台山人,1980年移居美国。已出版散文随笔集38种。曾获2009年首届“中山杯”全球华侨文学奖散文类“最佳作品奖”,2015年获“新移民文学笔会”“创作成就奖”。2017年“世界读书日”编辑人为第十九届上海读书节推荐十本书,散文集《你的岁月,我的故事》入选。
责任编辑:李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