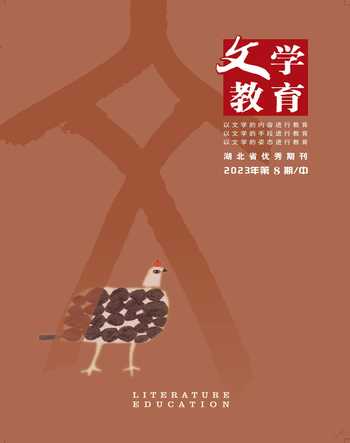当代昆曲教育模式探索与研究
储意扬
内容摘要:当代昆山市昆曲教育模式可划分为文化教育和表演技法教育。文化教育囊括景观建设和代际传承的“濡化”教育以及创新剧目和跨媒介“昆曲+”的“涵化”教育。表演技法教育则侧重探讨昆曲在小昆班、曲社、昆曲夏令营三个主阵地的教授情况。基于对教育现状的分析,提出优化当代昆曲的教育模式的可行之策,即昆曲普及和昆曲传承两手抓、由单一教学模式向多元化沉浸式教育的转变、探求更为正规系统的教学模式。
关键词:昆曲 教育模式 昆山
昆曲,又称“昆腔”“昆山腔”,元朝末年起源于江苏昆山一带,2001年被列入首批“人类口述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昆曲受到广泛关注,但人才断档仍是昆曲教育中的最大痛点,教育传承仍面临曲高和寡、青黄不接、模式单一等问题。因而在曲乡探索昆曲教育模式、体认昆曲文化精髓尤为重要。本文意在爬梳21世纪以来昆曲在发源地昆山的传承、发展情况,研究昆山昆曲文化教育和表演技法教育的模式与现状,探求优化昆曲教育模式的有效路径,使之适应新时代发展之需。
一.与地域、时代相结合的昆曲文化教育
21世纪以来,戏曲传承不再拘泥于剧种、班社、师徒内部,而是转向更广阔的社会。社会普及性的昆曲文化教育呈现出与地域特色、时代背景紧密结合的新风貌,本章借用文化学“濡化”“涵化”概念,将昆曲文化在代际之间传递延续的教育模式,界分为“濡化”教育;将所处同一时空的昆曲文化与其他学科、媒介互动的模式,用“涵化”教育加以探讨。
1.地域特性下的濡化昆曲教育
巴城“昆曲小镇”和千灯昆曲特色区块为代表的文化风貌区作为昆曲人文历史的策源地,具有文化贮蓄的力量,潜移默化地熏育着乡邑后辈的心灵。昆曲表演者、研究者以讲座、展演等形式进行代际间教育,也对自然环境进行艺术性的美学建构。
(1)“一镇一区”为代表的景观建设。据吴新雷等学者对于《南词引正》的追溯,昆山腔的发源地有两个重点,“一是作为昆山腔原创歌手顾坚的家乡——千墩浦流域的千墩(今名千灯);一是传承黄幡绰戏弄伎乐的宝地——傀儡湖流域的绰墩。”[1]昆山的“一镇一区”建设即围绕两处发源地开展。
巴城昆曲小镇保留老街肌理,引育文化名人,为昆山市民和外来游客提供了全景式综合性可赏可学的昆曲历史文化风貌区。景观建设下的濡化昆曲教育有助于提升地域形象,发展旅游经济,巴城昆曲小镇和千灯昆曲特色文化重点区块作为发源地昆曲文化的空间投射,反映了昆山对于昆曲的认同度正逐步提升。景观建构后作为具有标志性的物质符号,不断加强昆曲的地域性文化认识,成为“昆曲姓昆”合理化、自信化的物质符号。此种意义上,“一镇一区”为代表的景观建构是传统濡化教育的延续,又在现代景观构建下持续生产生成。通过优化昆曲的文化空间,从可观、可触、可感的物质景观中复现昆曲萌生和发展的土壤。“一镇一区”为代表的景观是写在昆山大地上的昆曲教材,以“物”的方式,默默承担起昆曲的文化建构与文化教育。
(2)老一辈昆曲艺术家的代际传承。如果说“一镇一区”为昆曲的濡化教育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场所,由老一代昆曲艺术家主持、举办的讲座、导赏等专题教育则是濡化的重要形式之一。以人为载体,对昆曲的传承体系和思想内涵进行世代教育是昆曲教育最为本体的形式,由此形成纵向的传承。
自《昆山昆曲发展规划(2018 -2022)》出台后,昆山着力实施“昆曲发展”文教结合工程和“昆曲发展”主体培育提升工程。杨守松工作室、俞玖林工作室等镇级昆曲文化教育基地先后建成开放。昆曲工作室以昆曲演出为基底,围绕剧目背景、演员行当、角色解读等方面,提供昆曲名家的专业讲解,通过昆曲文化知识普及为市民欣赏演出穿针引线。市民聆听知名演员分享演出心得体会、观摩经典片段,了解专业演员演出的潜台词和对角色、情节的处理,打通昆曲入门桥梁。
景觀建设与代际传承存在互动的生产过程,“一镇一区”担任代际教育的重要场所,代际教育反之也拓宽了景观的知名度,赋予其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
2.时代背景下的涵化昆曲尝试
昆曲教育想要超越传统领域,就要改良创新,与时代背景建立联系。昆山昆曲文化教育采取“涵化”的形式,即昆曲与其他传播媒介等产生密切、持续的接触,促使昆曲文化增殖,形成综摄的样态。
(1)囊括时代特质与地方文化的新剧目。“一个剧种兴旺发达的鲜明标志是,随时有体现时代精神和新创作作为新血液补充进来。经过实践检验的一批好戏逐步得到保留而成为传统剧目,新剧本不断产生,促使演出剧目的更新,这样必然带来演出质量的提高,剧种的生命力就强。”[2]昆曲与昆山地方文化融合、重新建构,不断延展舞台与生存空间,丰富昆曲内涵。
2018年10月,昆剧《顾炎武》开锣首演,将戏曲与地方文化和地方先贤相融,在语言上容纳了地方方言作为点缀。剧目中,家乡昆山之于主角的重要程度被凸显,由“食昆山稻米,勿忘乡恩”“南下昆山”“重归乡园”等台词可知,在顾炎武战场抗击清兵和修订《明史稿》身倦之时,昆山成为抚慰其心灵的精神乌托邦。顾炎武与康熙帝的对话更是将本土地域认同感推至新高度,顾炎武用昆山话公布身份——“我是昆山人”后,康熙帝随即赞誉“昆山的奥灶面好哇”“昆山的昆曲妙哇”,这样的念白设计在每场表演中皆赢得台下观众叫好。此外,昆山当代昆剧院根据当下时事和观众审美趣味排演现代戏。2020年的《峥嵘》(又名《春晓》)基于疫情时代抗疫题材创作,作品以昆腔演绎生活中的日常对话,蕴含昆山方言、昆山特产奥灶面、昆山台商夫妻等大量地域元素。《峥嵘》婉转悠扬的昆曲唱腔与快节奏当代生活相协调,消解了新旧之间的割裂感,探索出一条“昆曲与时代共呼吸的艺术之路”。如柯军在2008年“演出前的话”所说,“在大灾大爱大情面前,艺术创作历来不会失语,艺术此刻自有担当。”昆曲成为禳解民众消极情绪的重要艺术表现形式。
(2)新时期跨媒介“昆曲+”教育。随着媒介演进,戏曲文化的教育形态也随之延展,“媒介视角下的戏曲特性与媒介演进的逻辑之间相互适应、相互配合,创造出适应人的情感需求的新场景,形成新的观演方式,从而促进戏曲形态的衍生。”[4]昆曲由传统本体教育模式转为新时期跨媒介的“昆曲+”教育。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指出,应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宣传和能力培养,通过“向公众,尤其是向青年进行宣传和传播信息的教育计划”,使非遗“在社会中得到确认、尊重和弘扬”。2012年,昆山巴城台商林德政先生制作昆曲动漫《粉墨宝贝》,在剧中贯穿对昆曲专有名词的知识性讲解,以动漫形式传扬昆曲文化。2021年,昆山市信义小学依托俞玖林工作室排编昆曲广播操,采用昆曲韵律和山膀子、按掌、弓箭步等昆曲动作,使昆曲与广播操跨界碰撞。
昆曲与其他艺术形式、科学技术的融合成果也陆续映入市民眼帘,如昆曲书法、昆曲绘画、昆曲茶艺、昆曲礼仪等;“昆曲+科技”实现了数字科技引领昆曲文化教育,2022年8月戏曲百戏(昆山)盛典期间,《浣纱记》的直播首次将3D全息投影技术运用至昆曲表演中。不将“昆曲+”作为生产口号和发展经济工具,在跨媒介、跨形式的同时严格保证成品质量,才能“跨”得不生搬硬套、牵强附会,优良的“昆曲+”并非两个艺术形式的简单叠加,而是开拓性的艺术再造和自然流露。
二.戏以人传的昆曲表演技法教育
非物质文化遗产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方式,经身口相传得以延续。在“戏以人传”的特性影响下,昆曲表演技法教育成为昆曲“衣钵”传承的根本。
1.昆曲在小昆班的教授情况
小昆班是兼具昆曲传统传承教育方式和学校教育的昆曲技法教学形式。1991年[3]小昆班在第一中心小学首次创立,截至2021年,昆山各区镇小学已设立21个小昆班,30年来已培训逾5000名昆曲学员,获得上百个国家级奖项,百余名学员选拔进入专业戏曲院校深造,其中近20位成为专业演员。“小昆班”采用传统程式化和创新形式相结合的教学方法。据笔者对第一中心小学小昆班教师、学生家长访谈结果显示,学生主要于低年级年龄段通过教师遴选和自愿报名进入小昆班,学员人数约占班级总人数5%。在校期间上课频率为每星期3至4次,假期则安排集训,一般于寒暑假放假后和开学前安排7天左右的全天授课。
谈及昆山小昆班可取之处时,少数家长认为优势为学习昆曲、传承非遗;更多的则聚焦于儿童可获得的“实际效用”,如强身健体、锻炼心性等。不少家长注重少儿学习时获得的愉悦艺术体验,认为昆曲在精神层面潜移默化的影响对尚在成长阶段的孩子提升自我认知是非常有好处的。扮演昆曲角色时,少儿既能学习表演技能,又能感受不同的人生际遇,“沉浸”在特定情境中获得的体悟往往比长辈的耳提面命更能引起共鸣。
2.昆曲在曲社的教授情况
昆山昆曲曲社既有由官方支持、政府主导下建设的昆曲文化设施,如昆曲学社;也有由社會力量参与保护传承的昆曲研究会、缘源昆曲社等昆曲社团,曲社定期开展昆曲讲堂、社友拍曲等活动,为市民提供学习昆曲的平台。现阶段选择曲社学习昆曲者年龄跨度较大,由10岁至70岁,其中30岁至50岁的学习者居多。昆曲学社昆曲基础班和昆曲成长班各教授三支唱段,一套身段,昆曲结业班教授三支唱段,一个折子戏片段。昆曲成年班的师资为江苏省苏州昆剧院优秀演员,教授昆曲唱念、身段基础知识。
昆曲的演唱形式,历来有几种说法。一是顾曲,指昆曲的欣赏或评析;二是拍曲,专用于教曲和学曲;三是度曲,是清唱昆曲的雅称。昆曲在民间曲社中多采用拍曲的方式教授,以缘源昆曲社为例,曲社邀请俞派传人作为讲师,根据学员基础划分专业班和基础班。指导戏曲念白,确保每一个字的声调阴阳、音量高低的匀称,提供气息运用和发声方式等层面的技术性指导。曲社基础班拍曲课则借助新媒体技术,在学员认识、掌握工尺谱的基础上,介绍所学曲目剧目和剧作家的背景常识,再进行曲目的学习。
3.昆曲在夏令营的教授情况
昆山当代昆剧院自2016年起打造昆曲夏令营品牌活动,面向7至12岁的青少年招生。夏令营中,青少年能在台前幕后切身体验唱、念、做、打。夏令营根据青少年的年龄阶段与基本情况,划分不同班级并设置不同教学目标。其中,初阶班要求结营时学员会一小段昆曲唱腔和一些昆曲身段指法、台步圆场;进阶班要求学员掌握一整段的昆曲经典唱段和身段表演;高阶班要求学员单独表演一段昆曲经典折子戏片段。夏令营将教学、体验、互动融为一体,不断补充昆曲文化课程,优化昆曲教学体验感。
以上介绍了当代昆曲表演技法教育在不同场所开展的情况,值得一提的是,一些教育场所兼具昆曲文化教育和表演技法教育的功能。部分名人工作室和文化教育单位也与技法表演培训单位对接,为昆曲教育提供有力指导。
三.优化昆曲教学模式的可行之策
在时代需求不断改变和物质资料不断演进的视野下,当代昆曲教育理念和授习方法需要以更前沿的视角来审视,本章基于前文对于昆曲教育现状的分析,提出相应的优化建议,期望为未来昆曲教育提供一定的参考。
1.昆曲普及和昆曲传承两头抓
昆曲教育传承讲求“戏以人传,口传心授”,技艺精湛的人才毋庸置疑是昆曲发展的重要支撑。然而当下出于兴趣学习者多,实际传承者少,以小昆班为例,大多数学员出于培养课外兴趣的目的学习,最终走上昆曲专业道路或报考艺校者仅不足20%,走“精英化”的教育道路往往会让曲艺面临生存困境。因而在当代昆曲教育中,既不能走“精英化”的道路,设置较高的学习门槛让昆曲成为只能供瞻观的“博物馆化石”,也不可急于求成,试图让全体市民学会昆曲技法,了解昆曲内涵。
如昆曲演员俞玖林在采访时所述,小昆班培养和教学的初衷不仅是让孩子们学会昆曲或参加表演,更大的初心是给每个孩子种下一颗“种子”,静待开花结果。实际教育中需要正视昆曲不可能成为“大众化文化”的客观现状,通过昆曲普及与昆曲传承两头抓的种种努力让昆曲成为“小众化文化”。在普及昆曲的过程中让更多市民了解昆曲,挖掘有意愿者进行基础训练,选拔有能力者报考艺校传承昆曲,为剧团输送“新鲜血液”,进而实现传承和保护。
2.单一教学模式转为多元化沉浸式教育
由于市民在昆曲了解、学习道路上日益增长的体验性、互动性、时尚性需求,传统单一的昆曲教学模式难以跟上时代的步伐,多元化沉浸式的昆曲教育成为时代之需。
文化教育方面,昆曲借助更丰富的媒介平台以多样化形式进入生活空间,文化资本介入也驱动着昆曲教育和传播路径转型。余光中说,昆曲艺术不应是一枚仅供收藏的古币,而应成为一种流通的硬币。昆曲成为曲乡市民“有美感的生活方式”,市民可在游玩赏景中普及昆曲知识,昆曲文创产品、昆曲酒、昆曲编织等特色产品业态的发展也为昆曲文化的传承起有益助推作用。表演技法方面,昆曲教育不仅要教授技艺本身,更要在技艺传授的同时兼顾艺术美感与教化作用。学生和学生家长重视昆曲功法技艺的训练,也重视昆曲对孩童艺术修养和思想品德的培养。
3.探求正规系统的教学模式
从专业教学角度看,现阶段昆曲教学需要足够的课时保障基本功的持续训练。然而正视昆山昆曲教育的实际情况,多数昆曲教学平台受限,仍为不定期或短期教学,未能形成常态化教学模式。在中小学应试教育的大环境中,非应试的昆曲学校教育处于较尴尬的地位,往往被家长列入拓宽青少年兴趣的可有可无“选修”课程。部分家长在孩子进入高年级本应开始学习剧目的时期,出于学业重、作业多等因素考量,让孩子放弃昆曲学习。在现行教育体制下,亟需立足义务教育和昆曲教学的现状和需求,探寻更为合适、更有利于平衡两者的途径。
昆曲在源生地昆山市的教育模式由文化教育和表演技法教育两方面构成,二者具备各自的受众、内容及模式,但在一些场合又重叠交叉、相互渗透,共同为“知昆曲、懂昆曲、会昆曲”提供环境和技术支持。在昆曲教育事业拓展、教学方法增多的当下,教育模式仍应进一步优化,兼顾昆曲普及和昆曲传承,借助多元学科、媒介,实现单一教学模式向多元化沉浸式教育的转变,探求更为正规系统的教学模式,将昆曲教育引领至更高层面。
参考文献
[1]吴新雷:《论玉山雅集在昆山腔形成中的声艺融合作用》,《文学遗产》,2012年第1期.
[2]陸萼庭:《昆剧演出史稿》,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61页.
[3]《中国昆山昆曲志》编纂委员会:《中国昆山昆曲志》,广陵书社,2021年版,第11页.
[4]杨玉:《媒介演进中的戏曲形态衍生》,《戏曲研究》,2021年第1期.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1年度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KYCX21_3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