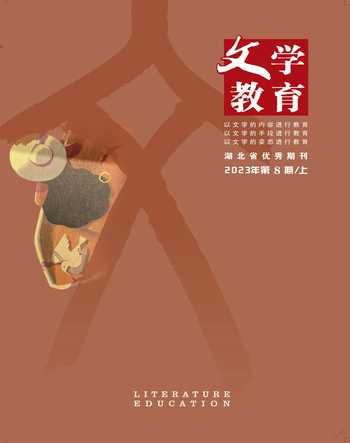山姆·谢泼德《情痴》中的后现代戏剧特征
朱晓欣
内容摘要:山姆·谢泼德是美国当代著名的剧作家,以其先锋戏剧实验成名于外外百老汇剧坛。他剧作家地位的巩固和提高得益于他所创作的系列家庭剧。不同于早期的作品,这些家庭剧呈现出回归现实主义传统的倾向。但在表象之下,家庭剧还体现了一些新的创作特征,即后现代主义戏剧特征。谢泼德正是依靠这些传统现实主义所无法包容的特征来破除现实主义的幻象。基于此,文章对《情痴》的戏剧结构、演员表演、舞台布景中的后现代主义意蕴进行分析,进而探讨有关幻象与现实的主题。
关鍵词:山姆·谢泼德 《情痴》 幻象与现实 后现代主义
山姆·谢泼德(Sam Shepard)是美国剧评界公认的他那一代人中最卓越的剧作家。迄今为止,他已创作四十多部舞台剧,除了1979年的普利策奖,他还获得过十一次奥比奖。他在早期的作品中常常运用反传统的先锋派技巧,但到了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他创作了一系列的家庭剧,包括《饥饿阶级的诅咒》、《被埋葬的孩子》、《真正的西部》、《情痴》和《心灵的谎言》,这些家庭剧不仅使他名声大噪,而且成为其戏剧创作的转型与成熟的标志。评论界有关谢泼德家庭剧创作风格的探讨大致可分为两种声音,一种认为家庭剧呈现出回归现实主义的倾向,是一次“现实主义的再访”[1:65];另一种则认为剧中现实主义元素的体现并不能说明其完全回归到传统的戏剧模式中,而是发展为一种“另类的现实主义戏剧”[2:11]。这两种观点都指出家庭剧与现实主义戏剧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在内容上反映了现实的家庭问题。然而,谢泼德在剧中还运用了大量的非现实主义戏剧技巧,因此很难将其归为纯粹的传统现实主义戏剧。在“现实主义”的幻象之下,谢泼德仍然致力于各种戏剧手法与技巧的实验,杂糅现实与非现实、超现实元素,使其家庭剧呈现鲜明的后现代主义特征。此前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前三部家庭剧,而缺乏对《情痴》(Fool for Love)深入且全面的讨论。文章从戏剧结构、演员表演、舞台布景这三个方面来分析《情痴》中的后现代主义特征,进而探讨该剧最突出的一个主题——幻象与现实的交叠。
后现代主义是一个多元的概念,很难用明确的语句定义,留下的印象常与不确定性、反权威、拼贴、杂糅、解构等相关。在众多的阐释中,哈勒·弗斯特把后现代主义分为两种矛盾的对立面:“一种是渴求通过解构现代主义来反抗现状的后现代主义,另一种则是否认运用解构的方式但赞同对抗现状的后现代主义”,分别叫做“反抗的后现代主义”与“反作用的后现代主义”[3:xi-xii]。“反抗的后现代主义”鼓励对传统的批评解构,而“反作用的后现代主义”则追求对各种传统真理的回归[3:xii]。不过,对传统的回归并不意味着要完全倒退到旧模式,而是将传统中的活力元素加到后现代的多元融合中,并实现对传统的重新发展。《情痴》中对现实主义元素的运用体现的就是“反作用的后现代主义”,既继承传统,也超越传统,甚至创造传统。
一.戏剧结构
《情痴》是一部独幕剧,讲述了一对情人,爱狄和梅,深陷复杂的爱恨关系,欲爱不能,欲罢不堪,他们的矛盾源于一个事实——他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妹。表面上,该剧与现实主义戏剧尤为接近,有着连贯的情节和情感纠葛、紧张的矛盾冲突和并非曲折的线性叙述。现实主义戏剧通过逼真模仿现实生活而真实地反映现实世界。为了突出《情痴》的现实性,一方面,谢泼德将个人经历溶入到作品中,讲述了父子、爱人间的矛盾,探讨了婚姻与爱情等社会问题;另一方面,他沿用了古希腊神话悲剧题材。
观众可以在爱狄和老人身上窥见谢泼德和他父亲的影子。谢泼德从小生活在动荡不安的家庭里,父亲时常酗酒、离家出走,并把脾气发泄在家人身上,这引起谢泼德极度的不满,也加深了父子间的隔阂,但他又无法割舍血浓于水的亲情。他在创作中反复言说了父子间矛盾交织的关系、无法剪断的血缘纽带和无法摆脱的基因遗传。男女、爱人之间的矛盾也始终存在于谢泼德的生活中。他本人经历了多次情感的转变,与妻子奥兰·约翰森的婚姻也在维持了十五年之后破裂,因为他在拍摄电影时爱上了女演员杰西卡·兰吉。而在离婚后不久,谢泼德便创作了《情痴》。在欲望与家庭责任感的冲突之下,谢泼德深刻地体会到了撕裂的痛苦。他当时的感受就如爱狄和梅的情感分裂一样,挣扎于道德与情欲、理智与情感的矛盾泥潭。剧中同时爱上两个女人,并周旋于两个家庭的老人也可以说是谢泼德当时困境的反映。谢泼德用自身经历展现了一个最为真实的舞台,他不仅想以赎罪的姿态揭露和抨击缺乏责任心的家庭关系,而且更是为了直面自我之根。对他来说,《情痴》的创作就是一个自我发现之旅。
除了赋予该剧以自传色彩来反映现实,谢泼德还继承了古希腊神话悲剧题材。亚里士多德认为只有发生在大家族的苦难事件才是最完美的悲剧题材。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德斯,这三位古希腊悲剧鼻祖,都将发生在阿特柔斯、俄狄浦斯这样大家族中的乱伦、谋杀、复仇等灾难事件当作他们悲剧创作的源泉。在现实主义家庭剧中,家庭伦理的题材得到延续,如威廉斯《欲望号街车》中布兰奇被姐夫强奸,奥尼尔《榆树下的欲望》和谢泼德《被埋葬的孩子》中母亲与儿子的乱伦以及杀婴事件的发生。《情痴》也重复了乱伦的悲剧,展现的是一对同父异母兄妹之间强烈的情感。这对兄妹是承担了父辈荒唐罪行的替罪羊,他们那违反伦理道德的关系永远阻碍着两人相爱。谢泼德通过这种“子偿父债”的情节揭示了无法摆脱的罪恶与遗传。
从题材到情节,不少现实主义戏剧元素都得到了继承,使观众获得情感的宣泄与共鸣,营造了舞台幻觉。但这种幻觉只是暂时的,是一种似是而非的假象。剧中大量充斥的非现实主义元素反驳、解构着现实,非常规的形式和无法解释的内容破除了先前架构的熟悉模式,更直接地反映了现实的多变与不可知。
《情痴》虽有较为完整的情节,却留下了一个模棱两可的开放式结局。该剧随着音乐的响起而开始,梅做出一连串矛盾的行为:既强烈渴望又激烈排斥着离开后再次出现的爱狄。几轮纠缠之后,爱狄的情妇女伯爵突然放火烧了他的马车,爱狄以此为借口离开了旅馆,梅见状也收拾行李出走了。然后,老人指着凭空虚构的“照片”并认定“照片”里的女人是他的爱人,此时,音乐再次响起,戏剧落下帷幕。这样突兀且模糊不清的结局不禁让人感到疑惑,爱狄真的又离开了吗?梅会去哪里?爱狄和梅的结局会是怎样?老人是爱狄和梅想象中的存在还是说爱狄和梅的故事才是老人构想出来的?谢泼德不愿把已经解决的结尾塞给观众,而是把疑问留给他们。他认为,“解决问题不是结尾,是一种扼杀。”[4]开放式结局不仅为观众提供了思考空间,而且彰显了戏剧结构的非连贯性和不确定性,直指现实多变的本质。此外,剧中还处处充满无法解释的空白和神秘地带。女伯爵是否真的存在?她的真实身份是什么?为什么她要跟踪爱狄,向他们开枪,在马车上放火?在没有任何确切线索的情况下,答案不得而知。而且,过去本身也是一个争议。爱狄和梅所讲的关于他们父母的故事相互矛盾,观众很难判断谁的故事是真是假,尤其当梅说到爱狄母亲自杀时,老人异常震惊,强烈要求爱狄把这部分重讲一遍,因为他觉得“这个故事根本说不通......这是我一生中听过最愚蠢的版本。”[5:54]看来,过去的故事有多个版本并且结局可以任意改变。剧情变化多端,众说纷纭。神秘的空白和真真假假的过去为该剧蒙上了一层虚构的面纱,使开放的结构变得更加松散与无序,观众由此意识到自己在剧场的地位,在想象中积极参与戏剧的创作。谢泼德以扑朔迷离的空白和嘎然而止的结局质疑了意义的确定性,实现对传统戏剧模式的超越。
二.演员表演
后现代社会理论家贝尔认为,“后现代美学是一种视觉美学。视觉艺术为现代人看见和想看见的事物提供了大量优越的机会,这与当代观众渴望行动、参与,追求新奇刺激、轰动效应相合拍。”[6:366-67]谢泼德的戏剧常靠演员表演营造视觉冲击,比如夸张的动作、象征性的舞台形象,具有直喻与刺激的效果,更直观地传达某种情绪或瞬间感受。他对表演有一套理念:为了表现某个瞬间的内心现实,演员需要占有角色的感情世界与行为动机,让角色演化为自我的一部分,并进入自我感情空间表演。
爱狄和梅的内心世界始终通过演员肢体动作的表演而形象地外化。梅最初的舞台形象是:“两腿分开,胳膊肘在双膝上,双手无力地交叉在两膝之间,头向前低垂,脸凝视着地板。”[5:20]仅透过这一个姿势,观众便可以迅速感受到梅那疲惫、脆弱和孤独的心情。幕启,演员一连串夸张、突变的行动表现了爱狄和梅那爱恨纠缠的矛盾情感。梅总是深陷撕裂的痛苦,既害怕被爱狄抛弃,又忍不住被他所吸引。当爱狄承诺留下来的时候,她“爆发愤怒,跳下床,用拳头猛打他。”[5:21]但是如果爱狄转身离开,她又会极度痛苦地尖叫着“别走!!!”然后“紧抓着枕头,抱在胸前,接着把脸埋到床上,哭了起来。”[5:22]而当爱狄再次出现时,他们非常温柔地相拥而吻,突然,梅“使劲地用膝盖撞击他的下身”[5:26],但爱狄走了之后,梅那强烈的丧失感又再次袭来,边哭边扶着墙走到角落里。从梅如同精神分裂般的行为可以感受到,在面对和爱狄之间无止境循环的处境时她那绝望与无奈的心情。这些突变的动作从视觉上冲击着观众的感官,让他们集中到各个瞬间释放的情感。爱狄和梅内在的骚乱和歇斯底里更是通过他们愈加激烈的行为显露无遗。他们总是砰地关门,用胳膊肘或头部撞墙,响声被低音鼓放大,发出“又响又长”[5:26]的轰鸣。肢体动作强化为听觉冲击,表演变成了纯粹的感官轰炸。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与爱狄的互动过程中,梅总是贴着墙走或呆在角落,以保持一定的距离。她还常常躲在浴室,喜欢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里面,这表明梅是一个极度缺乏安全感的人。在经历被爱狄和父亲多次抛弃之后,她心有余悸,却又渴望陪伴。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她才如此躲躲藏藏。除了动作之外,梅的形象在颜色的衬托下变得更加立体丰满。在爱狄回忆起他们初次见面时,“浴室的门很慢地无声地开了,露出了梅,她站在门框上,身后黄色的光照在她的红衣服上”[5:50],在这个场景,红裙、黄光以及轻开的门无不散发出一股魅惑的气息,捕捉住使他们都成为情痴的情欲的狂喜。在谢泼德眼中,没有任何语言能比这个穿着红裙的魅力女人更贴切地反映了主题。同样,观众可以从爱狄的形象中窥见古老西部的衰落:他穿着破旧的牛仔套装,被困在沙漠边缘一个肮脏的汽车旅馆里,无缘无故地用绳子不停地打着活结,将它在自己头顶上旋转,愤怒地用套索去套每一根床柱子。他像着了魔一样莫名其妙地做起这一系列动作,仿佛要倾泄被压抑许久的情绪。那种对于情感现状的怒火、无奈与痛苦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演员在舞台上展现了生动的视觉形象和激烈的形体表演,使戏剧成为流露人物每个瞬间感受的身体游戏。谢泼德非常重视主观意识和情感,他创造的人物的内心世界是如此丰富与变化无穷,以至于观众有时會对这瞬息万变的表演摸不着头脑。谢泼德指出,要理解他的人物,“应更多地以拼贴画的组建和爵士乐的即兴表演的词汇来考虑。”[7:62]人物是由不同的情感碎片组成的整体。表演,是“一种控制的无序”[8:4],每一个瞬逝情感就是一种无序,而表演就是控制好一次次情感爆发的接连出现,为观众展现多层次的内心现实。当观众沉浸于眼前的内心世界而产生幻觉时,演员马上带来另一轮的情感宣泄,这样观众就被拉出先前的幻觉而意识到人物多变的内心现实。
三.舞台布景
《情痴》一开始,熟悉可信的布景就让作品有了透明度,容易得到观众的理解。逼真的汽车旅馆在台上再现,旅馆中的家具陈设惟妙惟肖。但当所有人都产生幻象时,谢泼德不按常理出牌,在总体写实的布景中融入超现实与非现实的设置,比如与舞台分开的平台、非寻常的灯光和声音,这些抽象元素解构着幻觉,让观众在错位、震惊与思考中体验到真实生活的本质。
台上特别设置了一个延伸出舞台、与舞台分开的小平台,似乎暗示着在这里发生的事情是非现实的。老人的存在印证了这个猜想:“他只存在于梅和爱狄的心中,即使他们可以直接与他谈话并感觉到他的物理显现。老人对待他们就像他们都存在于同样的时间和空间里。”[5:20]他时不时地插嘴,对爱狄和梅说的话发表评论,在他们的互动中时隐时现。显然,他并不是科学理解下的“正常人”,这个平台也已然演化为一个精神空间。但是,爱狄可以走到平台上给老人倒酒,而且当梅讲述爱狄的母亲自杀时,老人为了反驳梅从平台走上了主舞台。此时,象征着过去的老人跨越平台来到当前的现实舞台,想象的空间与现实的场景交叠,幻想与现实、过去与现在之间的界限不复存在。谢泼德设置这个平台是为了告诉观众过去以及老人的影响一直在爱狄和梅的心中挥之不去,折磨着他们;平台的存在也使得叙事时间空间化,实现了时空的无限延伸、幻想与现实的自由转换。事实上,谢泼德想展现的是一个不受现实空间所限制、更为广阔宏大的精神空间,因为只有在那里,超自然的力量才会出现。在非现实的时空变幻交错中,《情痴》不仅推倒了“第四堵墙”,更营造出自由、流动的精神世界。
平台上,老人的出场由灯光控制。随着灯光的明暗变化,戏剧在过去与现在、幻象与现实之间来回转换。舞台灯变暗时就轮到老人登场,意味着当前的场景由现实变换到幻想中。第一次是在老人指着墙上一张不存在的“照片”跟爱狄讲述他想象着与“照片”里的女歌手结婚,此时,“舞台灯暗了一半,聚光灯缓缓地打在老人身上。”[5:26]老人一讲完,聚光灯变暗,舞台灯再次开到最亮,焦点回到爱狄和梅身上,场景从幻想变回现实。接着,梅抱怨起她脑海里总是出现爱狄和女伯爵一起的画面,她自己也不知道这个画面是真是假,可见梅难以区分想象与真实。通过灯光控制下场景的转换,老人与梅关于他们想象中的照片/画面的论述进一步证实了对于那些相信虚幻的人来说心理现实等同于经验现实,强调了现实与幻象之间的界限是模糊交叠的。第二次灯光变化出现在梅因爱狄的离开而哭泣时:聚光灯打在老人身上,舞台灯又变暗了一半。老人回想起梅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不停地哭,他把梅带到牛群当中,她马上就不哭了。听到这,现实场景中的梅也突然停止了呜咽,同时舞台灯迅速变亮,聚光灯熄灭。灯光的变化成功地将回忆中的过去与当前的情形联系到一起。而当聚光灯第三次打在老人身上时,“舞台灯保持不变”[5:47],表明此时过去与现在、幻象与现实完全重合了。在这样的灯光设置下,过去故事的三个不同版本分别由爱狄、梅和老人讲述,使观众陷入更深的混乱当中。而且,故事叙述过程中,“灯光慢慢下移,变成又蓝又绿的月光。”[5:50]尽管舞台指示明确地说这是月光,但蓝绿色一点也不像是月光的颜色,给戏剧增添了一丝奇异且梦幻的色彩,故事也变得愈发不真实。除了舞台灯和聚光灯混淆观众的感知之外,汽车前灯也阻碍着观众产生舞台幻觉,它们被描述为“两束刺眼的、不像‘现实主义的白色强光。”[5:36]观众可以从前灯出现的频率和强度鲜明地感受到其非现实的特征。它们总共出现了五次,每一次都是横向划过舞台,透过窗户照射到观众,有时甚至在远光灯与近光灯的转换中来回弹跳,让观众明显感受到它们的存在。在非现实的灯光影响下,观众猛然从幻觉中醒悟过来,重新审视眼前的现实。
声音在剧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以其超自然性震撼、间离着观众。布景上的门与低音鼓和麦克风连在一起,每当门被砰砰地关上时,就会发出异常大的声音和回响。观众可以从门的巨响感受到爱狄和梅那刻骨铭心又强烈的情感:通过放大每一次进出门的冲击效果,观众被这超自然的声音时刻告知着他们之间愈演愈烈、几乎失控的感情。更重要的是,门作为内与外的隔绝物,可以把危险的事物挡在外面。每一次大力关门发出的响声都在叫醒着活在情欲幻象中、对外面威胁一无所知的梅。被放大的声音形成一股能量流,内化为感性震撼力,使演员与观众集体获得潜意识的情感交流和直感层面的共同感悟。同时,道具声音的失真会让观众敏锐地察觉到舞台的虚构性,进而从幻境中挣脱出来,于陌生化的氛围中体会层层内心现实。
现实与非现实、超现实舞台元素的碰撞、杂糅不仅创造了更为广阔流动的时空,也颠覆了观众既有的审美期待,让他们在幻象与现实的出入、情感共鸣与间离中不断体味其中的意蕴。
谢泼德以敏锐的目光发现了现实主义戏剧巨大的影响力和无限的发展空间,在对传统的回顾中完成了一次后现代创作的转变。他在剧中融合了各种现实、非现实与超现实元素,使其呈现出一种难以归类的大杂烩现象。这种将各种艺术形式进行杂糅、无中心、多元论的方式正体现了后现代主义的风格,也直喻着当代社会的纷繁复杂。谢泼德让全剧游走于现实与想象、真实与虚构中,在二者的无序转换中展现出一个真假难分的世界。通过神秘莫测的空白,多层内心现实的表演展现以及不同时空层次的交叠,他让观众在熟悉与陌生之间,在非理性宣泄与理性思考中感受到情感的真实,重新审视现实的意义。其实,谢泼德所理解的真正的现实就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存在于对现实世界的感悟中。他鼓励每个人梦想的世界在信念的坚持下成为后现代社会的真实。
参考文献
[1]Hart, Linda. Sam Shepards Metaphorical Stage [M].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87.
[2]Bottoms, Stephen J. The Theatre of Sam Shepard:States of Crisis [M].Cambridge: Cambridge UP,1998.
[3]Foster, Hal. “Postmodernism: A Preface”,in The Anti-Aesthetic: Essays on Postmodern Culture[C]. Port Townsend: Bay Press,1983.
[4]Lippman, Amy.“Rhythm and Truth:An Interview with Sam Shepard”[EB/OL].www.americantheatre.org/198
4/04/01/rhythm-truths-an-interview-wit
h-sam-shepard/.
[5]Shepard, Sam. Fool for Love [M].San Francisco:City Lights Books,1983.
[6]朱立元.《當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7]Shepard, Sam. “Angel City”, in Fool for Love and Other Plays [M].New York Bantam Books,1984.
[8]Rosen, Carol.“Emotional Territory:An Interview with Sam Shepard”[J].Modern Drama,1993,36(0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