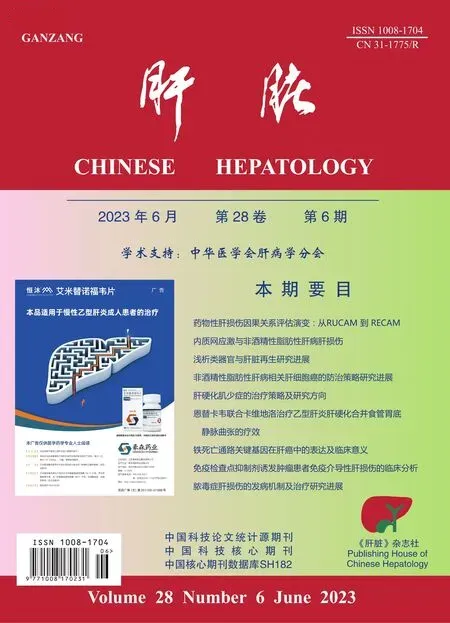浅析类器官与肝脏再生研究进展
刘文明 鄢和新
肝脏再生、干细胞生物学、细胞培养技术、诱导多能干细胞(iPSC)技术、类器官培养等领域近几十年来稳步发展,与二代测序技术、生物信息学、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技术和生物工程等高新技术产业交叉融合突破了既往研究的瓶颈,使得肝病再生领域逐渐成为焦点并在全球范围内方兴未艾。肝脏因其强大的再生能力可以承受长时间的损伤,并能够在受损后再生主要的实质性组织。因此,肝脏一直是人们研究器官再生的主要器官。人体肝脏可以耐受70%的肝切除术,啮齿类动物可以承受90%的肝切除术,斑马鱼甚至可以在肝细胞接近完全死亡后发生肝再生[1]。肝脏再生正在被视为肝移植的替代手段用于终末期肝病治疗。尽管肝移植仍然是治疗晚期肝病的唯一有效手段,然而供体不足、并发症和长期免疫耐受阻碍其在临床上的广泛应用。肝脏再生的目的便是克服这些困难。首先,肝再生的目标是在不可逆损伤之前促进内源性肝组织修复再生。其次,当肝脏的内源性再生能力不足,或是肝脏遭受损害不可逆(如失代偿期肝硬化),肝再生的目的是替换受损的细胞或组织。与健康的自体或同种异体肝移植相比,肝再生不受器官可用性的限制,使用自体细胞移植能够消除免疫抑制,无需手术,减少产生并发症的风险。
终末期肝病细胞疗法已探索了几十年,报道较多的是使用肝细胞和间充质干细胞(MSC)治疗。这些开创性的研究推动了基础研究领域肝再生的最新进展,产生了令人振奋的结果,但也存在不容忽视的弊端。原代肝细胞是最早被证明有效的可用于治疗急性肝功能衰竭的细胞之一,但有限的供体和植入效率低制约其推广使用。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显示出良好的抗炎作用,但植入细胞通常不能替代受损组织。近年来,肝脏类器官技术的发展已经成为一个突破点去应对这些挑战。
一、肝脏类器官简述
类器官多指源于干/祖细胞在体外三维培养的细胞或组织,通过细胞自组装模拟发育阶段的时空变化,从而形成的类机体组织(如初级类器官)。类器官系统由人体组织或iPSC产生,可模拟不同的器官或组织,例如肝脏、肺、肾、心脏、大脑和肠道[2]。在肝病学研究中,出现了大量不同的3D培养系统和模式,使用各种术语(如肝-胆-胰类器官;肝脏类器官;肝胆类器官;胆管细胞类器官;胆管类器官;导管类器官;肝芽等等),导致了科学文献中概念使用混乱,缺乏准确性。为解决这个问题,肝、胰和胆管(HPB)类器官联合会最近发表了一份共识文件,旨在定义一个通用的命名法[3]。文件中对类器官定义为:源自多能干细胞、祖细胞或分化细胞通过细胞与细胞间和细胞与基质间的相互作用,自组装形成三维结构,可体外模拟天然组织的结构和功能特征。该小组进一步将类器官分为三大类,包括(1)上皮细胞类器官:来自单个器官的单胚层细胞;(2)多组织类器官:来自单个器官的多胚层细胞;(3)多器官类器官:来自多个器官细胞类型的类器官。
二、肝脏类器官培养
肝实质由上皮细胞(肝细胞和胆管上皮细胞)组成,非实质由基质细胞、内皮细胞、免疫细胞和间充质细胞组成。其中肝细胞约占肝实质的95%,肝细胞类器官技术主要应用于研究生长发育、组织稳态和疾病模拟,若没有肝细胞类器官技术,这些复杂的过程都难以在体外重现。来自于前肠的肝祖细胞、原代肝细胞均被报道在体外通过类器官培养保留了肝细胞的结构和功能,但它们在体外存活时间很短。一项突破性研究报道于2013年,Huch等[4]通过将Matrigel与肝细胞生长因子(HGF)、表皮生长因子(EGF)、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FGF)和R-spondin混合用于培养分离的肝细胞,建立了成年鼠来源的肝脏类器官培养体系,该方法培养的类器官具有自我更新能力、良好的遗传稳定性且可长期扩增。即使是单个LGR5+细胞也具有自组装成3D结构并分化为功能性肝样细胞的能力。通过调控cAMP和TGFβ信号通路对培养基进一步优化,使得人肝细胞类器官体外成功构建并扩增,尽管其成熟度与功能仍比源组织低[5]。Clevers和Nusse实验室基于这一成果开发了新的系统,以类器官形式长期培养小鼠和人原代肝细胞[6-7]。与以往的培养系统相比,用类器官培养模式使肝细胞移植和再生能力进一步增强。
众所周知,肝脏具有独特的胆管网络和血管结构,肝脏的胆管结构对于其发挥解毒功能至关重要。Tanimizu等[8]通过在I型胶原和ECM的混合物中培养肝细胞和EpCAM阳性胆管细胞的混合物,建立了肝胆管类器官培养系统。为了提高移植物的存活效率,Takebe等[9]从多潜能干细胞衍生来源的肝内胚层细胞、内皮细胞和间充质细胞形成肝芽结构,采用这种模式成功地在体外模拟Alagille综合征、α-1-抗胰蛋白酶(A1AT)缺乏症、多囊肝病以及癌症等。Koike等[10]使用前肠和中肠类器官的混合物对早期内胚层形态发生进行模拟,这些类器官通过内陷和分支过程自发组织成复杂的结构,包括肝脏、胰腺、肠道和胆道祖细胞,成功模拟了前肠-中肠边界肝外胆管树的早期发育。该系统的建立为肝脏发育提供全新的研究策略,并为在体外开发功能性“迷你肝脏”单元奠定了基础。
三、胆管类器官培养
尽管胆管细胞占总肝实质的比例不到5%,但胆管疾病占成人肝移植的25%~30%和儿童肝移植的70%。以往关于胆管的培养主要由iPSC分化为成肝祖样细胞,随后这些细胞向胆道谱系转化,尽管iPSC细胞在治疗中存在弊端,但其产生的细胞具备了关键的胆管上皮细胞功能,成功地用于疾病建模和药物筛选[11]。 胆管上皮细胞和肝祖细胞培养的胆管类器官表现出胆管细胞关键标志物的表达,如CFTR、形成初级绒毛等[12-13]。文献报道,微绒毛在相邻近的肝细胞间发育成紧密的复合接连体,一旦复合体形成,毛细胆管的内腔就可被打开,形成一个充满胆汁液的胆管腔。尽管体外培养的胆管类器官呈现较好的功能属性,但培养过程中它们也会失去一些胆管分化特征,表现出共同的类器官特性,这些细胞在体内、外的身份(肝内、肝外、胆囊)不固定,呈现可塑性,暴露于不同胆汁酸和胆汁浓度的类器官可以恢复与微环境相对应的体内特性[14]。然而,这些类胆管结构在人体中能否真正行使胆管功能仍然存疑,直到Sampaziotis等建立的胆管类器官移植到胆管损伤的人体内,发现确实能整合进原有胆管并修复损伤部位[12],这一忧虑终被打破。该模型的建立为治疗胆管损伤性肝病的细胞疗法铺平了道路,即在实验室里培养的“小胆管”可以作为功能替代部件,修复受损的胆管,恢复患者自身肝脏的健康。
四、肝非实质细胞类器官培养
已知肝星状细胞(HSC)是肝脏内主要的间充质细胞,在基线时处于静止状态,用于储存维生素A液滴。暴露于毒素或感染后会激活HSC,导致ECM在肝脏中的沉积增加(纤维化),从而引起肝硬化和门脉高压。Koui等[15]通过诱导iPSC衍生的HSC能够在体外扩增,Coll等[16]通过诱导成中胚层祖细胞建立了iPSC衍生HSC的方法,Ouchi等[17]利用源自健康人类供体和肝脏疾病的iPSC产生不同类型的细胞,如肝细胞、星状细胞和库普佛样细胞,它们准确地在实验室中重现炎症、纤维化和肝病的其他特征。这些系统可以作为研究HSC活化、肝纤维化、肝毒性的实验模型。
五、肝脏类器官的应用
在研究领域,肝脏类器官是进行生长发育、细胞-细胞间相互作用、疾病模拟、药物筛选和机制研究的强大系统。在临床研究中,肝脏类器官提供了一个可用于药物筛选和个性化治疗的平台,同时还提供了一种基于再生医学开展细胞治疗的细胞源。在这种模式下,自体患者来源的类器官可与生物支架和再生活性因子结合,产生特定的组织工程移植物,用于患者治疗[18]。肝脏类器官具有明显的优点:(1)产生功能较好的细胞;(2)具有良好的遗传稳定性和扩增能力;(3)能建立结构相对复杂的功能单元;(4)是组织工程较好的细胞源。其缺点也不容忽视:(1)所用基质胶源于小鼠,具有小鼠组分污染与致瘤风险,开发新型混合凝胶耗时长且成本高昂;(2)受供体可用性的限制;(3)脱细胞支架进入人体组织受限制;(4)类器官的培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对于需要现成再生细胞药物的急性肝衰竭患者不太可能;(5)患者自体来源的原代类器官受疾病影响,往往呈现较低的再生能力。克服这些限制需要建立灵活的监管机制,比如目前Matrigel同时也被类器官以外的其他细胞治疗产品使用,其临床进展将有助于缩短类器官的临床试验周期。
用于移植的细胞必须符合某些标准,才能提供可行的治疗策略。首先,移植的细胞需要具有较强的功能。其次,对于全身效应(例如,循环血液中A1AT的分泌),移植物需能长期存活并整合到宿主血管系统中。第三,从基础研究到临床应用,移植的细胞必须具有规模化扩增的能力与临床应用的安全性。最后,细胞疗法不适用于需要进行重建的手术(如胆道重建)。因此,单纯的肝细胞移植不足以完全恢复肝功能。为了应对这些挑战,可能需要对含有胆道系统的多细胞类器官进行异位移植。这些“迷你肝脏”可在肠系膜、脾脏或肾包膜下进行异位移植,以挽救药物性肝衰竭动物模型。尤为可贵的是,这些类器官可形成具有功能性血管的独立“迷你肝脏”单元,新生血管自发地整合到宿主的血管系统中,使其适合异位移植[19]。
肝脏类器官的发展在高速前行,优缺点兼具,如何在培养过程中放大优点,弱化缺点是肝脏再生领域未来研究的热点。
利益冲突声明: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