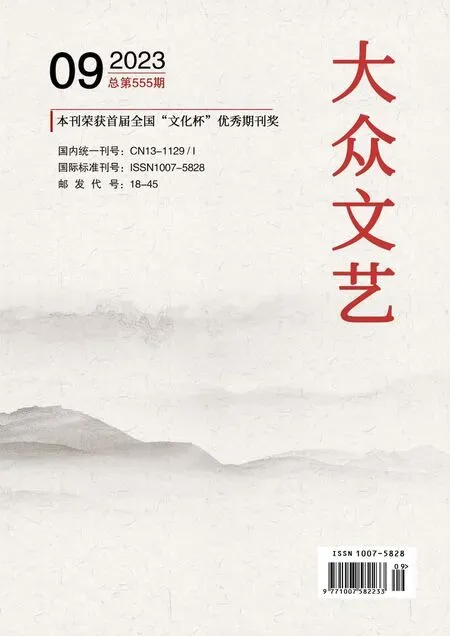动画艺术治疗治愈功能的心理机制探究
赵玉 刘凯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艺术学院,江苏南京 210044)
近些年来,动画艺术的治愈功能逐渐被发现和挖掘,动画艺术治疗从中孕育而生,并作为一种心理治疗手段逐渐被应用于实践。动画艺术治疗的对象具有广泛性。既包括那些已经产生心理异常问题,需要进行专业治疗的心理疾病患者,也包含了存在创伤经验和不良情绪体验但尚未构成心理异常问题的普通观众。心理疾病患者在治疗师的引导之下创作动画,通过创作将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心象”投射进动画作品之中,借助这种方式,患者可以自由又隐晦地表达内心的不安与痛苦,召唤自己被压抑的创伤记忆。而治疗师能够在此基础之上对症下药,协助患者完成自我觉察,帮助其重新整合情感和现实记忆。普通观众可以借由欣赏动画作品来完成心理治愈。观众在动画故事情节、角色塑造、视听元素的引导和刺激之下全身心卷入,借由自己以往的文化积淀、生活经验和情绪体验等自发地进行召唤、移情,继而产生共鸣、宣泄、情感补偿等心理活动,从而完成自我觉察、自我实现的心理治愈。
动画艺术治疗能够应用于实践,得益于动画艺术具有治愈与补偿的功能。之所以具有这些功能,是因为在创作或欣赏动画的过程中,有心理投射,压抑、召唤与整合,移情与共鸣,宣泄与补偿等心理机制在发生作用。本文将结合具体的动画作品,研究在创作和欣赏动画的过程中,这些心理机制是如何作用于心理疾病患者和普通观众,实现其治愈功能的。
一、心理投射
心理投射,指个体依据其情绪情感的主观指向,将自己的性格、态度、动机或欲望等特征转移到他人或他物上。动画艺术治疗中的心理投射机制主要体现在患者通过创作动画来完成心理状态的投射,帮助治疗师了解其心理状态,提高治疗效率。一般来说,患者会根据自己的主观经验、认知和喜好来进行创作,此时,心理投射就发挥着巨大作用。此外,由于投射有时是在无意识的状态下发生作用的,因此,除去患者主动赋予动画的特征、情感外,往往还会有未被察觉到的情绪情感以及价值观等被投射到他所创作的动画作品之中。
以澳大利亚导演亚当·艾略特创作的定格动画影片《玛丽与马克思》为例来说明心理投射机制如何发挥治愈功能。《玛丽与马克思》描绘了跨越洲际之间的两个年龄悬殊的笔友之间长达20年的友情。导演亚当·艾略特说,这部影片的灵感完全来源于他的生活。艾略特儿时生活在澳大利亚的乡下,父亲是一名小丑演员,母亲则是个美发师,因为生性羞涩、不爱说话,他总是待在自己的房间里,用家里的包装盒、卫生纸筒等做各种小玩意儿。他有一个笔友,是个犹太人,体型庞大,患有阿斯伯格症,两人书信往来了很多年。艾略特在动画《玛丽与马克思》中投射了很多他个人的影子,他自闭、羞涩、怯懦,但是他没有压抑自己,而是通过动画的创作,将无意识的意象投射到动画作品中去,并用动画角色的成长来探索内心与生活的平衡,导演本人以及观看动画作品的观众都能够在其描绘的情绪中得到疏解和释放。
意象与隐喻是承载投射机制的载体。动画影片中呈现的各种意象都具有象征意义,明示或暗示某些信息与情感,从而成为一种“隐喻”的存在。在这部动画影片中,导演艾略特就通过色彩意象的隐喻传递出许多情感信息。
影片中,艾略特用微妙的色彩区别了两位主人公的生活。描绘马克思的画面以黑色和灰色为主,视觉效果近似于黑白电影,玛丽的画面多以棕色色调为主,但仍然没有鲜艳的色彩。黑白灰都属于无彩色,无彩色只有亮度的变化而没有色调的差别,导演通过无彩色的使用突出马克思单调乏味的生活。棕色色调偏暗,给人暧昧、不鲜明、模糊不清的感觉,隐喻玛丽沉闷、忧郁的性格。玛丽的出现给马克思的生活增添了色彩:玛丽的彩色自画像、棕色的巧克力、玛丽送的红色绒球等。影片中的“色彩”意象即是一种隐喻,喻指快乐,导演将这种隐喻投射进动画作品中,通过直观的颜色变化来强调玛丽对于马克思的非凡意义。
由上,在心理投射机制的作用下,导演亚当·艾略特以自己的真实生活和情感体验为原型,描绘出了玛丽和马克思的形象以及他们之间古怪又可贵的友情。艾略特本人也通过创作完整地表达了其心理状态的动态变化,并跟随动画角色完成了“替代性成长”的治愈过程。[1]
二、压抑、召唤与整合
压抑是指个体将一些自我所不能接受的痛苦经历或冲动有意识地排除在意识之外,并将之压制到潜意识之中。压抑是一种“动机性的遗忘”(motivated forgetting),表面上看起来事情已经被个体忘记,而事实上它只是在意识领域消失,但是仍然存在于潜意识之中,并在某些时候影响着个体的言行。召唤正是在压抑基础上产生的。在某一特定情景的刺激之下,个体被压抑在潜意识中的创伤经验与当前情景会发生重合,从而产生相应的情绪反应,完成召唤。[2]整合则是要求正确地处理异化的情感和存在偏差的现实记忆,使之回复到健康状态。动画不仅能触发召唤,还能帮助患者更好地整合自己。
以PTSD群体在创作动画时的表现来说明在动画艺术治疗中,压抑、召唤与整合的机制如何实现治愈功能。PTSD患者可以通过动画创作来完成心理治愈。以色列动画电影《与巴什尔跳华尔兹》就描绘了战后PTSD患者的生活。导演阿里·福尔曼曾亲身经历过黎巴嫩贝鲁特难民营大屠杀的事件,战后他患上了PTSD,并遗忘了与战争有关的部分记忆。为寻回记忆,他开始进行动画创作同时接受心理治疗。动画是从一个噩梦开始讲起的,“它们伫立在那里,号叫着,26只恶狗,我知道他们表情的含义--他们是来杀戮的。”这个噩梦召唤出了福尔曼关于战争的记忆:这26只恶狗正是导演本人和朋友瑞恩当年在黎巴嫩的村庄里巡逻时打死的26只狗。恶狗的噩梦隐喻着大屠杀的残忍,20多年来,它一直折磨着导演及其战友的内心。[3]动画中,导演本人的梦境也屡次出现:夜空中巨大的焰火,海岸线上仿佛白昼的城市,年轻的士兵涉水上岸,端着枪、迷茫地面对绝望号哭的村民。面对这样血腥的战争记忆,压抑、遗忘和梦境是他们仅有的逃避手段。
为了重组记忆,导演本人在心理治疗师的帮助下访问了亲历过这场大屠杀的人。和他的战友一样,福尔曼也曾质疑过这场屠杀的存在。人在经历一些残酷的事情后会患上PTSD,将痛苦的记忆压抑在潜意识中,暂时遗忘掉。战争对福尔曼及其战友产生了难以磨灭的创伤,因此他们只能选择对记忆进行遗忘或者臆造,但生命中真实存在过的痕迹是不会消失的。大屠杀的记忆在福尔曼访问别人时回忆起的记忆碎片和对自己的拷问中逐渐被召唤出来,一点点拼凑完整。影片的最后50秒不再是动画,而是当年大屠杀的真实影像记录。[3]至此我们也得知,导演梦里的城市就是贝鲁特,空中落下的也不是焰火,而是为了方便“屠杀工作”的照明弹。
由上,导演福尔曼通过创作动画的方式探索了内心世界,召唤出被压抑的战争记忆和情感,并随着动画的演进逐渐将之整合到现实记忆之中。借助动画的创作,导演重新触碰了青年时期的创伤记忆,并实现了由压抑到召唤到整合的治愈过程。
三、移情与共鸣
移情,指个体将自身的情感转移到他人或他物身上。共鸣则是指个体受到外物情感的感染,基于自己过往的情感经验所产生的相似的情感感受。移情与共鸣两种心理机制在动画艺术治疗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2]它们赋予了动画生命力,成为导演与受治疗的观众之间达成情感共通的桥梁。
治愈系动画的流行恰好能为我们佐证在动画艺术治疗中,移情与共鸣两种心理机制对普通观众的治愈作用。治愈系动画诞生于日本,且在日本已经发展的相当成熟。近些年来,治愈系动画的身影也开始出现在欧美动画中。以2009年上映的动画影片《飞屋环游记》为例,该片讲述了天真可爱的“小冒险家”罗素阴差阳错之下搭乘了老人卡尔去往天堂瀑布的“飞屋”,一老一少在经历千难万险后终于抵达了天堂瀑布,老人完成了与妻子的承诺,还在天堂瀑布发现了自己和妻子儿时的偶像——冒险家查尔斯·蒙兹,却没想到蒙兹是个无恶不作的坏人,之后经历了一番搏斗,老人和小孩罗素终于又回到了自己生活的社区。
一般来说,往往是与普通观众具有相似的生活经验、情感感受、心理特征的人物形象更容易触发移情心理机制。《飞屋环游记》的主角正是如此,没有英雄主义,也没有超能力,主角卡尔只是一位失去了妻子的老人,独自在木屋里过着平淡的生活。这种平淡也平衡的生活很容易让观众产生移情作用。影片前十五分钟描绘了卡尔与妻子相遇相识相知相伴的温馨爱情故事,让观众了解到木屋对于老人的重要性以及老人对天堂瀑布寄托的饱含回忆的复杂情感。木屋是卡尔与妻子爱情的象征,而对美好爱情的向往是大部分观众所共有的情感,因此,老人的愁思和对妻子万般思念的感情就很容易与观众产生情感共鸣。因为拆迁需要,建筑公司希望卡尔能离开木屋去养老院居住,这件事情打破了卡尔的平衡。为恢复平衡,守住见证爱情的木屋,卡尔选择用气球带领木屋起飞,飞去天堂瀑布度过余生。数以万计的气球托起木屋的画面成为《飞屋环游记》中给观众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场景。色彩绚烂的气球、缓缓上升的木屋、先前铺垫过的情感基础配合安静、舒缓的音乐和音效,这些都使得“飞屋”与观众心中已经存在的情感符号发生重合,因此,这一场景才能触发观众心中的共鸣机制。最终,卡尔与罗素终于克服艰险,重新回归平静的生活,观众的情感也随之发生改变——渴望维持新建立的平衡。
由此,治愈系动画作为移情与共鸣心理机制发生作用的载体,以描绘日常生活、刻画人物细腻情感、引导观众随角色的情绪变化而逐渐接受心理暗示、产生代入感为依托,使普通观众在观影时能够自发地产生移情作用,并在故事和情感的转陈、重复、升华中达到一次又一次的情感共鸣,从而实现温暖人心、抚慰心灵的治愈功能。[1]
四、宣泄与补偿
未完成事件是格式塔心理学范畴的概念,指个体需要却尚未获得圆满解决的情感。这些缺失的情感并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消失,相反,由于个体没有充分体验、感受过这些情感,这些缺失的情感就徘徊在潜意识之中,并对现实生活产生不好的影响。未完成事件一旦形成,往往会持续存在,直至个体勇于面对并处理这些未完成的情感。个体需要回到未完成事件上,把情感表达出来。解决方法一般有宣泄和补偿两种。这里专指情感宣泄与情感补偿。
情感宣泄与情感补偿是动画艺术治疗中最基本也最常用的方法。人在有情绪和情感问题的时候尤其需要别人心理上的理解和支持,情感宣泄正提供了这样的出口。当观众在动画作品中看到那些自己内心需要得到认可的情节,他们内心的疑惑或不安实际上是得到了新的验证。情感宣泄正是在观众已经产生了移情的情况下,借助动画角色的成长和叙事的推进而完成的一次情感疏通。情感宣泄引导观众打破内心原本的平衡,为其注入新的能量,重新建立起新的平衡。而情感补偿往往是人们进行艺术欣赏的缺乏性动机。一个生性懦弱的人偏爱欣赏江湖、武林、打打杀杀的电影,一个渴望朋友的观众更容易被描绘友情的作品打动。情感补偿与未完成事件关系密切,它为观众提供了弥补内心情感缺失,满足心理需求的途径。观众能够在动画故事情节的引导之下,充分体验过去缺失的情感,从而使未完成事件获得解决。
优秀的动画作品能够触发观众宣泄与补偿的心理机制。以奥斯卡最佳动画短片《父与女》为例。这部动画作品以亲情为主题,情节简单,风格强烈,全片没有对白,依靠画面和音乐的配合来烘托气氛、表达情感。《父与女》讲述了父亲与女儿两人骑单车来到海边,父亲向女儿道别后出海,之后女儿骑单车来岸边等候,年复一年,直到生命终结的故事。亲人离去的孤独、寂寞以及对亲人的思念之情是能使大部分观众产生共鸣的情感,因此,观众才能在已经代入的情况下获得宣泄与补偿心理机制带来的治愈作用。
短片中有许多重复性的情节和场景,在《父与女》中,女孩九次来到岸边等候父亲。简单的情节和相似的场景重复出现,一方面推进叙事,另一方面也起到了情感堆叠、情感积蓄的作用。在《父与女》中,小女孩在孩童时与父亲分别,后来分别在童年、少女、交友、结婚、生子、衰老和死亡的阶段回到岸边等待父亲。这样的叙事看似平铺直叙,实际上则是引导观众在一次次的重复,一次次的等候中堆叠情感,积蓄能量,等到小女孩已经变成年迈的老人,再次回到父亲离开时搭乘的小船边,伛偻着躺下来,仿佛又再次回归父亲的怀抱时,观众心中堆叠的情感才终于能够冲破阻碍,宣泄出来。短片的最后,女孩与父亲相见并且相拥在一起,由此,女孩对父亲的这份长久的思念之情终于获得了表达。在这里要说明的是,女孩未必见到了真实的父亲,而是她幻想与父亲相见,她与父亲在已经干涸、长满芦苇的河床上相拥,实际上是小女孩心理情感表达的完成。她将思念之情表达出去,实际上是使自己的这份思念之情获得圆满解决,是补偿自己这一生的期待与守候。观众心中类似的情感缺失问题也能够在这样的情感描绘中获得补偿。
由此,优秀的动画作品为观众提供了一个由内而外的自足的情感宣泄和情感补偿的系统。在宣泄与补偿的心理机制的作用之下,普通观众通过欣赏动画不仅可以宣泄个体内心孤独、寂寞、思念等的情感,还可以通过故事情节的引导来弥补内心情感缺失的部分,帮助个体直面未完成事件,从而达到缓解情绪、治愈心理的效果。
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详细探究了触发动画艺术治疗治愈功能的心理机制。并结合具体的动画作品,论述了在动画创作和动画欣赏的过程中,心理投射,压抑、召唤与整合,移情与共鸣以及补偿与宣泄四重心理机制发生作用的具体方式和表现。
动画艺术治疗是动画艺术与心理学相互碰撞、相互融合的产物,彰显出学科融合的可能性与发展前景。动画艺术治疗不仅能够在专业领域帮助治疗师和心理疾病患者更好地解决心理问题,而且能引导大众释放心理压力、宣泄不良情绪、实现自我觉察和自我治愈。近些年来,探讨精神、心理问题的动画影片、动画短片、科普动画等越来越多,但动画心理学相关的理论研究相对匮乏。重视动画与心理治疗结合的理论研究,能够反向推动动画作品的创作,为其注入更深刻的内涵和社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