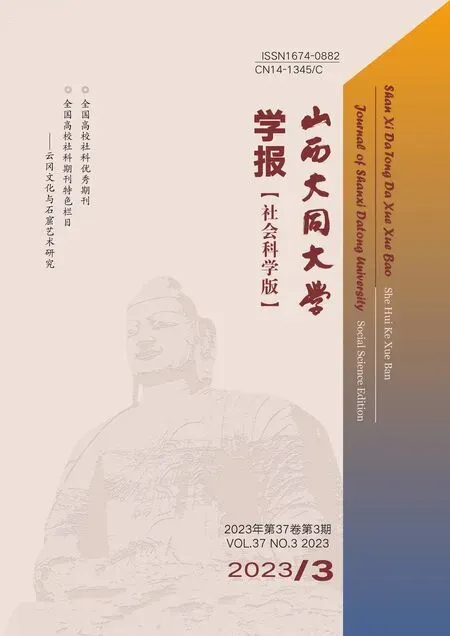论魏晋南北朝史官任用的文学因素及其意义
郑华萍
(江苏警官学院基础课教研部,江苏 南京 210097)
魏晋南北朝是史官制度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有关当时史官与文学的关系,历来研究者大多仅关注史书的文学性,而忽略了史官任职资格中的文学因素。所谓史官,即由帝王任命的记言记事的官员,在魏晋南北朝时主要包括著作官、撰史学士、兼职史臣和监修国史及起居注者。具备相当的文学素养和才能是这一时期史官任用的重要条件。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史官被选任的要求中看出,正如刘知几所说:“其有才堪撰述,学综文史,虽在他官,或兼领著作。”[1](P287)根据正史人物传记、《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材料的统计,这一时期有史官经历的文士至少有一半。尽管史才应是选任史官的首要条件,但相较之下,文才却是这一时期对任职者的普遍要求。
一、魏晋南北朝史官任职资格考
关于魏晋南北朝史官任职资格问题,迄今无人详考。笔者细究当时史官被任职的情况,发现原因主要有四方面:优秀的史才、杰出的文才、出色的“策能”以及门第品级。但是史才和文才之间并没有严格的划分,存在交叉的部分。优秀的史官大多学综文、史,博闻多识,为史学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其一,史官的职责主要是撰史和修起居注,史才也就成为首选条件。魏晋南北朝有不少文人因史才出色而被任史官。据记载,西晋时如华峤“有论议著述之才”,[2](P1476)遂与中书共参著作事;郭琦“博学,善五行,作《天文志》《五行传》,注《榖梁》《京氏易》百卷”,晋武帝“以琦为佐著作郎”;[3](P2436)东晋时祖纳举荐王隐时称他“清纯亮直,学思沈敏,《五经》群史多所综悉,且好学不倦,从善如流。若使修著一代之典,褒贬与夺,诚一时之俊也”;[3](P1698)何充、庾冰推荐谢沈时称“有史才”,[3](P2152)遂迁为著作郎,撰《晋书》三十余卷;徐广重视荀伯子的才学,于是荐任佐郎,“助撰晋史及著桓玄等传”;[4](P1627)王韶之因私自撰写《晋安帝阳秋》,“时人谓宜居史职,即除著作佐郎,使绪后事。”[4](P1625)南朝时梁裴子野曾“删撰为《宋略》二十卷。其叙事评论多善”,沈约见而叹曰:“吾弗逮也。”深受当时兰陵萧琛、北地傅昭、汝南周捨的称赞。因此,吏部尚书徐勉言之于高祖,授著作郎,“掌国史及起居注”;[5](P442-443)北朝时北魏段承根受崔浩赏识,“以为才堪注述,言之世祖,请为著作郎。”[6](P1158)李敷引荐程骏时称“骏实史才,方申直笔,千里之任,十室可有。请留之数载,以成前籍”。[2](P3675)以上所举的善于著述、博综经史、撰写史志等都属于“史才”范围,士人由此而走上“史途”并积极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可见其在史官选用上的重要作用。
其二,杰出的文才是当时史官任职的重要资格。史官除了撰写史书和起居注外,在有诏命时还需校整图书,撰哀册文、碑文、奏议等,而这些职责的实现都离不开杰出的文才。因文才而任职史官的如西晋张载的《濛汜赋》为傅玄称赏,故“为之延誉,遂知名。起家佐著作郎,出补肥乡令。复为著作郎”;[3](P1518)东晋郭璞的辞赋为世所称,“后复作《南郊赋》,帝见而嘉之,以为著作佐郎。”[3](P1901)干宝“少勤学,博览书记,以才器召为佐著作郎”;[3](P2149)萧梁任孝恭的才学为高祖所知,遂“召入西省撰史”[5](P726)等等。北朝虽尚武,文学发展落后于南朝,但也有一批颇富才学的史官。如邢产属文,“少时作《孤蓬赋》,为时所称。举秀才,除著作佐郎”[6](P1449);少时即以文学知名的阴仲达为崔浩所知,荐曰“凉土才华”,[6](P1163)遂参与修史,征为秘书著作郎;韩兴宗“好学,有文才。年十五,受道太学”,[6](P1333)司空高允引参著作事;李谐“风流闲润,博学有文辩,当时才俊,咸相钦赏”,[6](P1456)崔光引为兼著作郎;秘书监李凯因裴景融的才学“启除著作佐郎”,[6](P1534)后迁辅国将军、谏议大夫,仍领著作;孙搴以文才著称,被“太保崔光引修国史”[6](P1534)等等。由上可知,史官的任职方式主要有四种:士族子弟的起家官、皇帝直接任命、因才能为他官推荐、以他官兼任史官。而任职的共同原因是“才堪著作”。
其三,优秀的“策能”是当时史官任职的又一资格。魏晋南北朝选官设“秀才科”,虽出自荐举,但也有策问考试,尤其是南北朝时期。《北堂书钞》引《晋品令》曰:“策秀才,必五策皆通,拜为郎中。一策不通,不得选。”[7]士人因对策称旨而被任史官者,如刘宋时扬州秀才顾练和豫州秀才殷朗“所对称旨,并以为著作佐郎”;[4](P56)顾愿“大明中,举秀才,对策称旨,擢为著作佐郎”;[4](P2087)北魏的韩显宗“太和初,举秀才,对策甲科,除著作佐郎”;[6](P1338)裴延俊“涉猎坟史,颇有才笔。举秀才,射策高第,除著作佐郎”;[6](P1528)卢观“少好学,有俊才,举秀才,射策甲科,除太学博士、著作佐郎”[6](P1871)等等。秀才对策的要求较孝廉经试更难一些,更注重士子的才学文采。因策问而受到赏识并进入仕途,可见这一时期选官对才能的重视。
其四,魏晋南北朝在选官上践行九品中正制,门第为重要因素。这一时期门第森严,有高门、一般士族、寒族三个层次。通过对魏晋南北朝史官门第的统计,可以明显地发现任职史官者以高门居多,始终占据着该职位的比重超过44%(魏晋44.4%,刘宋73.5%,南齐77.3%,萧梁44.7%,陈朝47.1%,北魏61.5%,东魏、北齐53.7%,西魏、周59.3%),其中尤以宋、齐、北朝为盛。其次是一般士族,他们在选任中占有明显的优势。寒族子弟虽也有因文才而进入著作局或史馆的,但人数特别少。此外,这一时期还有因门第而起家或解褐著作官者,著作郎中有西晋的挚瞻,刘宋的何求,萧齐的刘绘,萧梁的刘遵、徐敬成,北魏的司马消难;著作佐郎中有东晋的孙盛、王修、王蕴、蔡廓,刘宋的萧映、王秀之、萧惠基、王奂,萧齐的王瞻、萧藻、张率、萧介、萧洽,萧梁的徐悱、陆襄、柳敬礼、柳仲礼、蔡允恭,陈的陆从典,北魏的郑敬祖、李希礼、崔谦、薛聪等等。当时选官注重门第,历来颇受研究者的关注,于此所列史官的任用史料正可佐证此点。
综上所述,史官被任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并且在不同时期,其重视因素亦不同。魏晋时,史官选任不重门第,看重才学,一般士族及寒士因才能入选史臣者较多;至南北朝时,门第变为史官选任的重要参考因素,尤其是著作佐郎,成为士族子弟的起家官,但自身所具备的才能是仕途顺畅的保障之一。
二、文学因素与史官任用
史官,众所周知,首先具备的必须是史才,而魏晋南北朝史官选用却极为重视文才,这是为什么呢?文才在史官任用的过程中到底有什么作用呢?拥有优秀的文才又对史官存在多大影响呢?这些问题的解决对于我们理解文才在当时史官任用中的作用有着重要的意义,亦有助于进一步了解这一时期的史官制度。
其一,文学素养是选任史官的标准。《晋书·职官志》载:“著作郎始到职,必撰名臣传一人。”[3](P735)这是两晋选拔著作郎官的独特方式,要求史官必须具备撰传记的能力。南北朝史书中虽没有明确规定选任史官的标准,但从任职者的经历、才能及作品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史官选任较为重视文学素养,如著作郎陆机“天才秀逸,辞藻宏丽”,张华尝誉之曰:“人之为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3](P1480)兼掌著作的任昉“雅善属文,尤长载笔,才思无穷,当世王公奏表,莫不请焉。昉起草即成,不加点窜。”[5](P253)为一代词宗沈约所推挹;兼领著作的陆琼“幼聪慧有思理,六岁为五言诗,颇有词采”,[8](P396)博学善属文,京师称为神童;著作郎崔浩“少好文学,博览经史,玄象阴阳,百家之言,无不关综,研精义理,时人莫及”[6](P807)等等。著作(佐)郎、撰史学士以及兼、领郎官者,虽号称史官,但其实文才胜过史才,长于文笔。刘勰曾说:“孙盛干宝,文胜为史。准的所拟,志乎典训。户牗虽异,而笔彩略同。袁宏发轸以高骧,故卓出而多偏。孙绰规旋以矩步,故伦序而寡状……后汉才林,可参西京;晋世文苑,足俪邺都。然而魏时话言,必以元封为称首;宋来美谈,亦以建安为口实。何也?岂非崇文之盛世,招才之嘉会哉!”[9](P701-702)可见当时即使是以史学知名者,亦具有较好的文学才能,史馆里多为文才。此外,从一些制诰中也可以发现这一点,如杜之伟《求解著作启》中的“或清文赡笔,或强识稽古”,[8](P455)高祐《奏请修国史》中的“著作郎已下,请取有才用者,参造国书,如得其人,三年有成矣”。[2](P3657)即要求任职史官者必须具备一定的文才。
其二,突出的文才是良史的要求之一。曾巩在《南齐书目录序》中说:“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10](P288)优秀的史家必须具备德、学、识、才相统一的素质,其中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史才”。所谓“史才”,即修史者的文章技术,无论叙事还是文采,都与文才密切相关,恰如章学诚曾言:“夫史所载者事也,事必藉文而传,故良史莫不工文。”[11](P258)综观史籍中明言记载的堪称“史官之尤美,著作之妙选”[1](P288)的良史,如陈寿“善叙事,有良史之才”;[3](P2137)孙盛的《晋阳秋》“词直而理正”[3](P2148)、干宝的《晋纪》“简略,直而能婉”,[3](P2150)故世人称为良史;李彪“生自微族,才志确然,业艺夙成,见擢太和之世,輶轩骤指,声骇江南,秉笔立言,足为良史”。[6](P1402)还有华峤、陆机、束皙、虞预、裴子野等等,他们大多文才赡富,博综经史,具有明显的文人特征。
其三,史官的作品及史书中对作品的选录影响了时人的文学观。魏晋南北朝是士族兴盛的时代,出现了很多文学大族。同时,也出现了一批史官世家,祖孙、父子、兄弟、叔侄先后或同朝为史官者不在少数。长辈的提携教育,同辈之间的学习切磋,形成了深厚的家学渊源,为后辈树立了榜样。如高阳新城许氏,许珪,宋著作郎;孙许懋,梁天监初以征西鄱阳王谘议兼著作郎,著有《风雅比兴义》《述行记》等;曾孙许亨“少传家业,孤介有节行。博通群书,多识前代旧事,名辈皆推许之”,[8](P458)以太中大夫领大著作,知梁史事,撰有文笔六卷;玄孙许善心“述成父志,修续家书”,[12](P1428)成《梁史》70 卷,并著有《符瑞记》等。一门五代有四代人曾任职过史官,在叙事和行文上都具有某种相似性;再如彭城刘氏,刘绘,解褐著作郎,著有《刘绘集》;子刘孝绰,号曰神童,少时帮父亲草写诏诰,起家著作佐郎,有文集数十万言;孙刘谅,著作佐郎,“少好学,有文才,尤博悉晋代故事,时人号曰‘皮里晋书’。”[5](P484)此外,刘孝绰的从弟刘遵、从侄刘刍也任职过著作郎。《梁书》曾言:“孝绰兄弟及群从诸子侄,当时有七十人,并能属文,近古未之有也。”[5](P484)殊不知他们不仅善属文,有一些还曾任职为史官。类似的还有河南阳翟的褚湛之、褚渊、褚寂之,昌黎棘城的韩兴宗、韩显宗、韩子熙,河南鄚县的邢祐、邢敏、邢邵、邢峦、邢产、邢子明、邢昕等等,不管在文学作品上还是在史书的撰写手法上,无不具有秉承性。此外,史官对史传人物文学作品的选录、品评与鉴赏也直接影响了他人的文学审美,对后人认识这一时期文学的价值及特点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最后,文学素养是良好君臣关系的调节剂。史官有撰史任务时即在著作局或史馆修史,闲暇时或教书讲文,或随从帝王大臣宴游,诗酒唱和,赋诗作文,或侍从讨论义理。好的文辞不仅可以引起帝王大臣的注意,展示自己的才华,亦可美化形象,为君臣关系涂抹色彩。如曹魏的王沈“正元中,迁散骑常侍、侍中,典著作,与荀顗、阮籍共撰魏书,多为时讳,未若陈寿之实录也。时魏高贵乡公好学有文才,引沈及裴秀数于东堂讲燕属文,号沈为文籍先生,秀为儒林丈人”;[3](P1143)刘宋的江智渊“爱好文雅,词采清赡”,世祖十分赏识,摆设私宴,“多命群臣五三人游集,智渊常为其首。同侣未及前,辄独蒙引进”;[4](P1609-1610)萧梁的刘孝绰“尝侍宴,于坐为诗七首”,为高祖所赞,“由是朝野改观焉”[5](P480);萧子显的才华为高祖所赏,“每御筵侍坐,偏顾访焉”,太宗亦“素重其为人,在东宫时,每引与促宴”;[5](P511-512)北魏的程骏常与显祖论《易》《老》之义,显祖“顾谓群臣曰:‘朕与此人言,意甚开畅’”。[6](P1345)他们都因才能而得以在帝王大臣面前崭露头角,并得到赏识,进一步拉近了君臣关系。
总而言之,史官的文学素养在任职和仕途升迁上有着重要的作用。这一时期的史官与文人紧密联系在一起,如刘节所说:“从三国起直到隋末,凡是文人,很少与史学没有关系。所谓‘才堪著述,学综文史’的,都网罗在史家之列。”[13](P71)大批文人入史职,史官群体文化素质整体较高,是此时期史官制度的典型特征。
三、意义
魏晋南北朝统治者大多好为文学,士族之间亦以文学相标榜,因文才而进入仕途者颇多。史官选用响应上层领导者的号召,极为重视文学才能,吸引了更多的人重视文学。社会对史官及其作品的认可影响了一代文风,并促进了文学自觉的进程。
首先,魏晋南北朝史官任用重文才对当时及后世的文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史通》言:“但自世重文藻,词宗丽淫,于是沮涌失路,灵均当轴。每西省虚职,东观伫才,凡所拜授,必推文士。”[1](P233)大批文士进驻史馆,不仅参与修史,还撰写诗文,成为当时文坛的主要代表,执一时文坛牛耳,如晋末宋初的谢灵运、宋齐的沈约、魏齐的邢邵。谢灵运“少好学,博览群书,文章之美,江左莫逮……每有一诗至都邑,贵贱莫不竞写,宿昔之间,士庶皆遍,远近钦慕,名动京师”,[4](P1743、1754)开启了山水诗创作的新风,后世追随者不断;沈约“博通群籍,能属文……撰《四声谱》,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寤,而独得胸衿,穷妙其旨,自谓入神之作”。[5](P233、243)他的四声说对当时五言诗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梁书·庾肩吾传》言:“齐永明中,文士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至是转拘声韵,弥尚丽靡,复踰于往时。”[5](P690)邢邵“十岁,便能属文,雅有才思,聪明强记……自孝明之后,文雅大盛,邵雕虫之美,独步当时,每一文初出,京师为之纸贵,读诵俄遍远近”。[14](P475、476)与温子昇、魏收并称“北地三才”。在他们周围都有一批朋友相互赏析文章,讨论文学。在谢灵运周围,有谢惠连、颜延之、范泰、刘义真、何长瑜、荀雍、羊璿之等;在沈约周围有谢朓、王融、何逊、任昉、周颙、范云、吴均等;在邢邵周围有阳固、裴伯茂、邢罘、陆道晖、王昕等。他们相互唱和、相互支持,共同的诗文活动引领了一代文风,在当时文坛上掀起了一丝波澜,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其次,魏晋南北朝史官任用重文才促进了社会重文学的风气。这一时期的史官大多以文学见长,很多都有作品传世。依据正史本传和《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经籍志》等的记载,我们可以发现,史官中很多都撰有集。魏晋史官80人,其中50 人有集,占62.5%;南朝史官108 人,其中42人有集,占39%;北朝史官166 人,其中25 人有集,占15.1%。李善注《文选》选录了先秦到梁代共130人的作品,其中任职过史官的有23位,并且选诗最多的三位诗人陆机、谢灵运、江淹都担任过史职。这一时期的文学在特定时间范围内形成一种群体风格,而每一种代表性的风格中都有史官的参与,如太康诗风中的张载、张亢、陆机、陆云、潘岳、潘尼,游仙诗的代表郭璞,玄言诗的典型孙绰,元嘉体中的谢灵运,永明体的典范沈约、宫体诗的代表徐陵,小说界的干宝、吴均、陆琼,文学批评领域的陆机、徐陵,“北地三才”的温子昇、邢邵、魏收等等。创作如此丰富、风格如此多样化的史官,我们不得不承认他们在当时文坛上的影响力,而这种结果的产生与任用史官时重视文才有着莫大的关系。这一时期的史官在官品上虽只是六品、七品,但著作官属于清官,实际政治地位远高于同品级的其他官员,为高门士族所喜任。史官选用重文才,感染着社会上其他阶层的人,或欲以文才进入仕途,或欲炫耀文才以便得到重视。他们纷纷加入到文学创作的大流中,创造了浓厚的文学氛围,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推动了社会喜好文学的风习。
最后,魏晋南北朝史官任用重文才是文学自觉的反映,也是促使文学自觉的重要因素。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说:“他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s Sake)的一派。”[15](P382)这一时期是文学自觉发展的特殊时期,文学素养是士人所共同追求的目标。史官选用重文学素养即文学自觉化在史学领域的反映,是文学对史学的渗透和影响下的产物。李少雍说:“这三部史书(《宋书》《南齐书》《魏书》)在不同程度上都是六朝文风的体现者,与文学发展的总进程有密切关系。而且,不论在记事载言方面,还是在刻画人物形象方面,史传文学都代表着当时叙事文学的最高成就。”[16]史官群体有意识地将文学手法运用到撰写史书的过程中,以“文”运“笔”,以致刘知几感叹:“此乃绮扬绣合,雕章缛彩,欲称实录,其可得乎?”[1](P191)从史的角度来考量文学,为文学活动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反之,史官任用重文学素养又加速了文学自觉的进程。同时兼具史官与文士的身份,其创作为文学注射了新的活力,如史书中单列《文苑列传》并选录文学作品,陆机在《文赋》中对文体的分类,李充在《翰林论》中对文体风格的论述,沈约的“四声”“八病”说及其对诗歌审美创作的影响,对文学自觉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总之,魏晋南北朝史官在任用的过程中极为强调文学才能,是当时政治文化背景的深刻影响和本身职责的根本性要求。他们在任职前以文才名当时,任职后更是人尽其才,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不仅在史学上留下了足迹,更在文学领域引领了一代文风,对后世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史官与文士身份的“一身二任”现象,在魏晋南北朝史学史与文学史上都数见不鲜。这一时期史官任用尤其重视文才,亦导致了一些弊端,如史书的文学性、文字的晦涩等,从反面证明了文学的发展对史学的渗透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