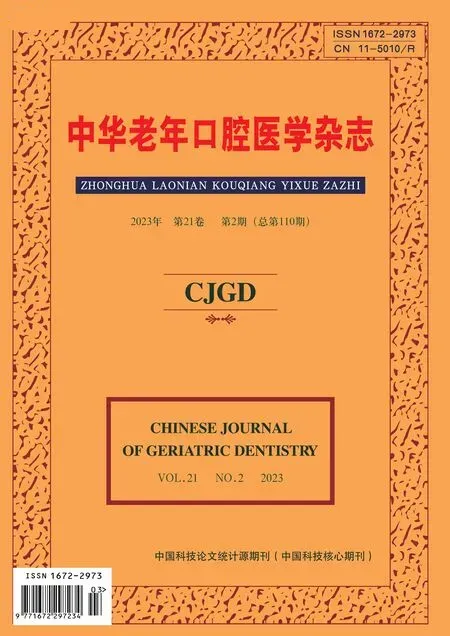牙周炎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关系研究*
曹红霞,孙晓军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是由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SARS-CoV-2)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性疾病。SARS-CoV-2 属于冠状病毒β 属,基因组为线性单股正链RNA,可通过表达刺突蛋白(Spike Glycoprotein,S 蛋白)介导病毒包膜与细胞膜融合来实现入侵和感染[1]。目前公认的COVID-19 诊断标准为[2]:(1)具有新冠病毒感染的临床表现,如发热、咳嗽、咽痛、肌肉酸痛、嗅觉味觉减退等,严重者可出现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甚至多器官功能衰竭;(2)具有以下一种或以上病原学、血清学检查结果:①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阳性;②新冠病毒抗原检测阳性;③新冠病毒分离、培养阳性;④恢复期新冠病毒特异性IgG 抗体水平为急性期4 倍或以上。
老年人是COVID-19 的易感人群,也是重型和危重型病例的高发人群。研究发现50 岁以上的COVID-19 患者占53.6%,死亡率高达93.7%[3],且随患者年龄的增加,COVID-19 病死率呈逐渐上升趋势[4],严重威胁老年群体的生命健康。
牙周炎是以菌斑微生物为始动因子引起牙周附着丧失、牙槽骨吸收,最终导致牙齿脱落的慢性感染性疾病,发病率及严重程度随年龄增长而增加[5-6],与肺炎、哮喘和慢阻肺等多种呼吸系统疾病密切相关[7]。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COVID-19 与牙周炎的相关性也受到关注。最新研究发现伴牙周炎的COVID-19 患者住院风险和死亡风险显著升高,干嗽、乏力和呼吸困难等临床症状较无牙周炎患者明显增加[8-9],推测牙周炎对COVID-19 的发展有促进作用。可能机制为牙周炎患者通过为SARS-CoV-2 提供储存场所,促进其全身传播,或牙周细菌吸入呼吸道及细菌毒性产物经破溃的袋内上皮进入血循环诱发机体产生免疫炎症反应,甚至参与细胞因子风暴等方式影响COVID-19 的发生发展。本文就牙周炎与COVID-19 的相关性及可能的作用机制作一综述,以期为牙周炎与COVID-19 关系的深入研究及防治策略提供参考。
1 牙周炎与COVID-19 的临床流行病学研究
牙周炎可加重哮喘、慢阻肺和肺炎等呼吸系统疾病的严重程度[7],推测牙周炎也可能与COVID-19 相关。2020 年Patel 等[10]首次报道了一例COVID-19 疑似病例伴有严重口臭、龈乳头坏死和自发性牙龈出血等坏死性牙龈炎症状,提出了牙周炎与COVID-19 相关的证据。随后多位学者进行了系列流行病学和临床研究探索牙周病与COVID-19的关系。Larvin 等[11]将14466 名COVID-19 患者根据BMI 分为正常、超重和肥胖,并将自述的牙龈出血、牙龈疼痛和牙齿松动作为牙周炎诊断指标,结果显示COVID-19 患者的住院率和死亡率随着BMI 的增加而增加,而肥胖组中牙周炎患者的死亡率显著高于无牙周炎的患者(RR=3.11;95% CI:1.91-5.06),表明肥胖与新冠患者较高的住院率和死亡率有关,而牙周炎可能会增加肥胖对COVID-19 死亡率的影响,进一步支持了Patel 的假设。随后该学者又在另一项1616 名COVID-19 患者的回顾性研究中[12],以同样的方法评估牙周状况,发现牙周炎虽然与COVID-19 感染无显著相关,但死亡风险显著升高(OR=1.71,95%CI:1.05-2.72)。Marouf 等[8]对568 名COVID-19 患者的研究中,依据X 线片邻牙间牙槽骨丢失量评估牙周健康状况,采用回归分析排除年龄、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混杂因素后,发现牙周炎时COVID-19 患者的辅助通气量(OR=4.57,95%CI=1.19-17.4)、ICU 入住风险(OR=3.54,95%CI= 1.39-9.05)及死亡风险(OR=8.81,95%CI=1.00-77.7)均明显增加,提示牙周炎可能促进了COVID-19 的发生发展,以上研究中牙周病的指数使用了临床表现,患者自述,口腔影像学检查结果对牙周炎与COVID-19的关系进行了初步探索,随后学者们开始采用更专业的牙周病学临床检查指标对其进一步研究。Gupta 等[13]检测了82 例COVID-19 患者的牙龈出血指数、牙周探诊深度和牙龈退缩量,首次探讨COVID-19 严重程度与牙周各临床指标间的关系,多变量回归分析显示探诊深度>5mm 患者的辅助通气风险和死亡风险显著大于探诊深度为2-5mm的患者(P <0.05),伴发牙龈出血时COVID-19患者的住院率和辅助通气量增加了3-4 倍。Anand等[14]在一项79 名COVID-19 患者和71 名健康受试者的病例对照研究中,发现COVID-19 患者口腔内附着丧失程度较健康者更重(2.28±0.56 VS1.15 ±0.42,P <0.001),推测COVID-19 可能与较差的牙周状况有关,与Gupta 的研究一致。最近一项研究依据最新的牙周炎分期标准将294 例COVID-19 患者分为I-IV 期[15],探讨高分辨率计算机断层扫描(HRCT)图像中肺部病变受累面积与牙周炎的关系,发现重度COVID-19 组的牙周炎发生率为87.5%,III-IV 期牙周炎发生率为81.82%,均显著高于轻中度组(P ≤0.001),I-II 期牙周炎主要发生在轻度COVID-19 患者中(84.44%),Pearson 相关分析显示患者肺部病变面积与菌斑指数、探诊出血阳性位点百分比、探诊深度呈中度相关(r=0.53-5.64),提示牙周炎越严重,COVID-19 的重症发生率越高。
为避免观察性研究中混杂因素和反向因果关联对实验结果的干扰,学者尝试采用孟德尔随机化法(Mendelian randomization,MR)从基因的角度探讨牙周疾病对COVID-19 的易感性和严重性的影响。MR 利用遗传变异的分配随机性和时序优先性有效避免了因果推断中的干扰问题,近年来广泛应用于探索疾病的危险因素和复杂疾病间的双向因果关系等,并可以揭示疾病间新的关联[16]。Wang 等[17]从大样本全基因关联研究(GWAS)汇总数据中选择rs1156327、rs1633266、rs17184007、rs17718700 和rs3811273 共5 个与牙周炎密切相关的单核苷酸多态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NP)位点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孟德尔随机化分析发现牙周炎与COVID-19 高易感性显著相关(OR=1.024,P=0.017,95%CI 1.004-1.045),住院患者组与人群组比较中,牙周炎与COVID-19 的严重程度显著相关(P <0.05),提示牙周疾病可能是COVID-19 易感性和严重程度的病因之一。
虽然有研究表明牙周炎与COVID-19 具有相关性,但很多研究是通过统计学方法进行风险因素调整后的间接证明,因此牙周炎是否与COVID-19的相关还需更多的直接证据及更严格的研究设计进一步证实。
2 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 与牙周组织
口腔内牙菌斑生物膜中可检测出SARSCoV-2[18]。Comies 等[19]在70 名COVID-19 确诊患者中发现13 名患者牙菌斑生物膜中SARS-CoV-2病毒检测呈阳性,阳性患者鼻咽拭子样本病毒载量显著高于阴性患者(P=0.012),患者发热、咳嗽、咽痛等临床症状的发生率也是阴性者的2-3 倍,提示口腔内牙菌斑生物膜可能有利于SARS-CoV-2 的蓄积,并作为病毒入侵的第一道关口在COVID-19发生和传播中发挥重要作用。牙龈组织和龈沟液中也发现了SARS-CoV-2。Matuck 等[20]采用RTPCR 技术检测7 名COVID-19 死亡患者,发现5 名患者的上颌第一磨牙近中龈乳头呈现SARS-CoV-2阳性,首次证实牙龈组织中存在SARS-CoV-2,提示牙龈组织可能是SARS-CoV-2 的靶点。Gupta[21]等也在33 名COVID-19 患者中通过同样的方法检测发现63%的患者龈沟液样本存在SARSCoV-2。弗林蛋白酶、ACE-2 和跨膜丝氨酸蛋白酶2(Transmembrane Protease Serine 2,TMPRSS2)是SARS-CoV-2 感染宿主细胞,使病毒与宿主细胞膜紧密结合进而实现入侵和感染的关键因子。Sakaguchi 等[22]对牙龈组织、硬腭上皮和颊黏膜等口腔组织进行了免疫组化染色,结果示牙龈上皮中弗林蛋白酶、TMPRSS2 和ACE-2 均呈阳性表达,且非角化龈上皮的表达水平高于角化龈上皮,提示牙龈上皮和龈沟液内的SARS-CoV-2 病毒与感染相关分子特异性结合而定植于牙周组织,因此牙周组织不仅是SARS-CoV-2 入侵和感染的重要部位,还可能是SARS-CoV-2 全身传播的潜在来源,在预防病毒传播时应考虑这一来源。
3 牙周细菌与COVID-19
合并细菌感染的COVID-19 患者与单纯SARS-CoV-2 感染相比,入住ICU 的比例、住院时间及辅助通气量均显著升高[23-24]。Moreno 等[25]对1594 名COVID-19 住院患者的电子病例及相关实验室检查结果进行回顾性分析,发现合并细菌感染的患者死亡率为25%,显著高于无细菌感染患者(6.7%);Zhou 等[26]对54 名COVID-19 死亡患者的临床病程分析显示约50%的患者伴有继发感染,38%患者死于感染性休克,提示细菌感染是COVID-19 病情加重的重要危险因素。
牙周细菌可通过与唾液混合进入呼吸道,大约一半健康成年人在睡眠期间会吸入唾液,而老年人由于咽喉敏感性降低、吞咽反射功能下降及呼吸道纤毛运动障碍导致唾液吸入风险进一步增加,为牙周细菌进入呼吸道提供了有利条件。此外需要辅助通气的危重症患者难以通过咳嗽或吞咽清除口腔分泌物,须经口气管插管帮助清理,此过程中可使口腔中的牙周细菌迅速从口腔或上呼吸道向肺部迁移。Chakraborty 等[27]对提取的来自中国、巴西、秘鲁、美国等多个国家COVID-19患者肺泡灌洗液的宏基因测序数据分析中,发现具核梭杆菌、卟啉单胞菌、普氏菌和链球菌等多种牙周细菌定植于患者的肺组织中,虽然目前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牙周细菌与COVID-19 严重程度有直接关系,但研究发现当牙周细菌进入肺部时,在病菌及其毒性产物如内毒素等的影响下,支气管和肺部的ACE2 表达显著增加[28],此外SARSCoV-2 主要通过介导过度的免疫炎症反应致使肺组织严重受损,而牙周细菌可引起类似炎症因子的过表达,如CRP、IL-6、IL-8、IL-1β、TFN-a 等[29],从而进一步加剧这一反应进程,因此SARS-CoV-2和牙周细菌的联合感染可能会增加COVID-19 患者不良预后的风险。
4 牙周炎与COVID-19 的炎症联系
外周血中CRP、D-二聚体、IL-6 和铁蛋白等炎症因子水平进行性升高是COVID-19 由轻症向重症转化的重要预警指标[30],Gapta 等[13]在82 例COVID-19 患者的血清炎症标记物水平分析中,发现伴牙周炎患者的C-反应蛋白、D-二聚体、铁蛋白等血清水平高于无牙周炎患者,并随牙周附着丧失程度、探诊深度和牙齿缺失数量的增加而增加(P <0.05)。Said 等[31]将1325 名COVID-19 患者根据x 线片是否发生牙槽骨吸收以及有无牙周治疗史分为牙周健康组、牙周治疗组和牙周炎组,发现牙周治疗组的D-二聚体、CRP 和铁蛋白等血清水平显著低于牙周炎组(P <0.05),回归分析显示牙周治疗组的辅助通气风险与牙周健康组相比无明显增加(AOR=1.28,P=0.768),而牙周炎组的辅助通气风险较高(AOR=3.91,P=0.022),提示牙周炎可能促进COVID-19 的发展,而牙周治疗能够减少体内炎症因子的产生,降低全身系统性炎症负担,可能有助于避免COVID-19 相关不良并发症的发生,改善牙周炎症保持牙周健康对COVID-19 的预后有一定积极作用。然而由于牙周治疗过程中产生的飞沫、气溶胶和血液可能增加SARS-CoV-2 传播风险,因此COVID-19 与牙周干预治疗的关系有待更多的研究。
5 牙周炎促进COVID-19 发展的相关机制
目前牙周炎与COVID-19 之间的作用机制尚不清楚,现有研究提示牙周炎可能通过促进病毒入侵、引发免疫炎症反应甚至参与细胞因子风暴等途径影响COVID-19 发生发展。
COVID-19 伴有牙周炎症时,牙周袋可能充当病毒和细菌的储存库[32]。SARS-CoV-2 病毒可与牙周组织直接接触或通过感染的免疫细胞及血液迁移定植于牙周袋中[33],袋内上皮ACE-2 和TMPRSS2 表达也显著增加,间接促进了SARSCoV-2 在牙周组织中的感染和复制[34],同时牙周袋构成的密闭空间也为病毒复制提供了有利环境。因此牙周袋可能增加局部组织SARS-CoV-2病毒载量。牙周致病菌进入呼吸道后可上调支气管和肺泡上皮细胞SARS-CoV-2 病毒的重要受体ACE-2 的表达,因此在病毒感染中发挥重要作用。
细胞因子风暴是SARS-CoV-2 感染的常见病理现象,也是COVID-19 从轻症向重症和危重症转换的重要节点[35],牙周炎时牙龈卟啉单胞菌、具核梭杆菌和伴放线菌等细菌可诱导人支气管和肺泡上皮细胞产生IL-6、IL-8、IL-1β、TFN-a 等炎症因子,并在24 小时后达到高峰[36],LPS 也可激活NF-kB 炎症信号通路[37],促使体内C 反应蛋白、D-二聚体和纤维蛋白原的水平升高和炎症细胞因子大量产生,引发机体产生免疫炎症反应损伤肺组织,这些炎症因子可进一步刺激巨噬细胞、中性粒细胞、T 细胞等免疫细胞甚至激活NLRP3 炎症小体导致更多的细胞因子释放进而参与细胞因子风暴的发生[38-40]。
6 总结与展望
目前关于牙周炎影响COVID-19 进展的直接证据较少,其作用机制也尚未明确,牙周炎可能从基因易感性,炎症反应等方面与COVID-19 的易感性,严重程度相关,因此关注COVID-19 患者的口腔或牙周状况对COVID-19 的预后评估以及避免不良并发症具有重要意义,更严格设计的基础和临床研究,更多的直接证据将成为未来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