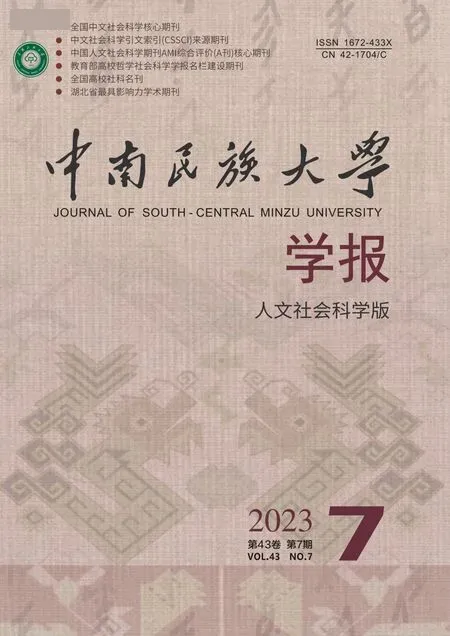北朝山水文学与集体记忆书写
胡大雷 辛 梓
(广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1)
南北朝文学的一个突出特点即“山水方滋”,山水文学以描摹山水景物为主要特征,以诸种文体为谱系。北朝文学的“山水方滋”,体现为集体记忆书写。所谓集体记忆,是指一个群体或社会成员共享的记忆,“集体记忆的首要任务是传递集体认同”,“社会借助集体记忆来传达规范和价值”[1]。集体记忆或能够作为社会进化的动力,即记忆被人们所共享、传承以及在一起建构着某些事或物。本文要讨论的,即北朝山水文学显示了怎样的集体记忆?集体记忆给予北朝山水文学怎样的原创动力?体现着怎样的民族精神?以下详述之。
一、“礼报”“敬求”:集体文化记忆成为山水审美的基调
北朝盛行以文辞“礼报”“敬求”山水,其代表文体即祭祀文。山川和人类的生产、生活、社会治理密切相关。《尚书·舜典》云:“望于山川,遍于群神。”[2]126说的是古代从“望”(祭)名山大川开始再遍祭群神。古时有“三代命祀,祭不越望”[2]2162的说法,即祭祀不能越境,故祭名山大川又含有巩固自己领土的意味。作为少数民族政权的北朝,还保持着原始信仰传统,甚重祭祀,其中就有山水祭祀。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太延元年(435年)六月甲午诏书中说:“礼报百神;守宰祭界内名山大川,上答天意,以求福禄。”[3]85《魏书·乐志》称:“奏姑洗,舞《武德》,巡狩以祭四望山川。”[3]2839山水祭祀讲究“敬”与“求”,既表达崇敬之心,又表达人类的诉求,实现人类与自然山水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望。刘勰《文心雕龙·祝盟》曰:“若乃礼之祭祝,事止告飨;而中代祭文,兼赞言行。”[4]祭祀本只是以物质“告飨”的仪式,但当“资乎文辞”而引申到“兼赞言行”,于是使祭祀由仪式演变为文学。祭名山大川之文,对山水形貌风神的描摹与人类对山水的态度与愿望的表达,实际上就是在书写人类的集体文化记忆,由此奠定了北朝山水文学的“身份”以及审美核心。
北魏孝文帝元宏《祭嵩高山文》,先写早在人类之前嵩高山的诞生及其光辉获得百神与区夏人民的顶戴,这是先民的精神依托,再写嵩高山在当代的山水景色:
曰乎皇魏,飞虬玄并;螭腾穹象,用九黔嬴。新邦兴略,丕猷罔清;佗琼指阴,淹翠湿亭。河图旷览,升中阙铭。朕承法统,诞邀休宏。开物成务,载铄成龄;迁宇柳方,阐绳廛城。则直之兴,百堵若星;日躔流馥,月陆芬馨。锵旋紫宿,景曜黄衡;鸾声嘒嘒,鸑和嘤嘤。归盖如云,还辀若霆;惟嵩岩岩,峻极昊青。惟邑翼翼,长启魏京;荐玉告虔,用昭永贞。纳兹多福,万国以宁。[5]104
北魏迁都洛阳后,在“礼报”“敬求”的祭祀文中,将人们观赏到的乃至心目中的嵩高山景象,落实到“纳兹多福,万国以宁”,希冀给世间带来福音。
景物描摹是祭山之文的重要组成部分。北魏孝文帝元宏的《祭岱岳文》曰:“岱宗穹崇,梁甫盘崛。青丘崎嶬,春阯郁律。肇生庶类,启光品物。上敷神工,下融灵秩。载协化文,四气以溢。百王镌成,莫不兹室。”[5]96泰山景色笼罩在神秘气氛中。高允的《祭岱宗文》道:“正趾坤元,作镇东夏,齐二仪以永固,崇至德以配天,故能资元气以造物,协阴阳而变化。”先是为泰山唱颂歌,后又描摹泰山的景物:“若其岩岭峭峙,川谷幽深,神怪谲诡,倏忽百灵,吐纳风云,育成万品,摄生之所归焉,祯祥之所萃焉。”[5]96此文比元宏之作具体生动,其中还突出期望泰山对民生、国运的护佑,这是全天下人民的愿望。
北朝祭水之文存世者较多,北魏孝文帝元宏作《祭河文》,前部分泛泛地歌颂黄河:“坤元涌溢,黄渎作珍。浩浩洪流,实裨阴沦。通源导物,含介藏鳞。启润万品,承育苍旻。惟圣作则,惟禹克遵。浮楫飞帆,洞厥百川。”[5]123后部分则叙写当代的黄河景象,突出的是迁都后的新景象:“朕承宝历,克纂乾文。腾鸾淮方,旋鹢河濆。龙舲御渎,凤旆乘云。泛泛棹舟,翾翾沂津。宴我皇游,光余夷滨。肇开水利,漕典载新。千舻桓桓,万艘斌斌。”[5]123最后,作者期望“保我大仪,惟尔作神”。可见,人的愿望就是要得到“河”的支持。与祭山不同,祭水之文中特别提到“肇开水利,漕典载新”与水道运输景象,这是人类向“水”汇报自己的行为。孝文帝元宏又有《祭济文》,既歌颂济水,又写人类在济水中的活动:“瞻洪津而怀德,乘长波而钦智。泛龙仪之郁穆,璨玉轩而浮被。沉璋璧之明物,冀牲洁以归寄。”[5]131这是求神祈福,提出“敬”与“求”的主题。
北朝征战南朝,面对水乡泽国,往往祭水以乞求“水灵”助其战争胜利。隋开皇元年,卢思道接受朝廷指命而为《祭漅湖文》,先是叙写天气常阴霖雨,阻碍了王朝的向南用兵。“淮夫百神受职,水灵为大。皇王御宇,率土无外。当使日月贞明,天地交泰。雨师止其霖沥,云将卷其蔚荟。东渡戈船,南耸雕旆。收尉佗之黄屋,纳孙皓之青盖。然後革车旋轸,戎卒凯歌,楚俘雾集,冀马星罗。无德不报,有酒如河。神之听之,斯言匪蹉。”[5]142这是求神,祈求“水灵”令“雨师止其零沥,云将卷其蔚荟”,以成就对南朝战争的胜利。
祭江河文,一般都以江河的形象叙写,突出向其“敬求”之意。隋元帅晋王敬祭淮河,薛道衡有《祭淮文》,先说隋朝平定北方后对南朝陈的讨伐,后愿水神助自己在江南水乡之地战斗胜利。隋元帅晋王敬祭南渎大江之神,薛道衡有《祭江文》,祈求江神令“蛟螭窜于洲渚,帷盖静于波涛”[5]127,以使大军渡江歼敌、统一南北。
山水祭祀文作为北朝山水文学的一种文体,以“敬”与“求”两大要素,奠定了人类对山水的态度,确定了人与自然山水之间关系的心理基调与情感基础,实在应该是“真情实意,溢出言辞之表”[6],突出人类对山水的态度,这是山水祭文的最高境界。东魏时,高昂为西南道大都督,进军商、洛时,渡河祭河伯曰:“河伯,水中之神;高敖曹,地上之虎。行经君所,故相决醉。”[7]1146他要与河伯共醉,意谓两相平等,河伯不可作威以阻止其渡河。高昂如此高傲,但只是戏谑之辞,并非北朝山水祭祀之文的主流。
山水祭祀文,是在叙写集体文化记忆中的山水景物,呈现出某种神圣性、超验性、真知性。当预先设置了“敬”与“求”的观念,那么其笔下景物不免多有概念化、公式化的倾向。
二、集体审美记忆成为北朝山水文学叙写模式
山水叙写的集体记忆模式,指叙写的山水,或并不一定是自己的亲身游历,或并不重在自己的亲身游历与体验,而是历代的或当代世人的集体审美记忆,所谓“山川之美,古来共谈”[8]。
孔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其中蕴含了人类长期以来对山水比附道德的集体记忆。北朝时的山水叙写,比起个人体验来,往往更重集体记忆。如《水经注》记载山水,往往叙写山水的历史纪事,或现实,或神话,都是一种集体文化记忆。又,北朝阳固的《北都赋》曰:“茂丘,茂山也,盖恒岳之别名,派水从西来,甚大,至茂山之西,沉伏于地,过山而复出,其大如初;世言避恒岳之灵。”[9]188这里写到都市所处的山水位置,以山水描摹出之,这本是历来传统,是人类对作为地理位置的山水的集体记忆。汉代以来扬雄、杜笃、班固、张衡、左思的都邑赋,都是如此写法。
北朝的山水叙写中,还有集体审美记忆。当人们观览到山水的巨大力量造成某些惊险的场面时,世人的集体记忆则呈现出某种恐惧感,如《水经注》载:
孟门,即龙门之上口也。实为河之巨阸,兼孟门津之名矣。此石经始禹凿,河中漱广,夹岸崇深,倾崖返捍,巨石临危,若坠复倚,古之人有言,水非石凿,而能入石,信哉。其中水流交冲,素气云浮,往来遥观者,常若雾露沾人,窥深悸魄。其水尚崩浪万寻,悬流千丈,浑洪赑怒,鼓若山腾,濬波颓叠,迄于下口。[10]102
之所以称其为集体记忆,是因为其中所述的是从“古之人”以来的“往来遥观者”的山水感受。在人身安全的前提下,恐惧感会转换成为对山水的审美。《水经注》曾记载东晋袁山松言:“常闻峡中水疾,书记及口传,悉以临惧相戒,曾无称有山水之美也。及余来践跻此境,既至欣然,始信耳闻之不如亲见矣。其叠崿秀峰,奇构异形,固难以辞叙。林木萧森,离离蔚蔚,乃在霞气之表,仰瞩府映,弥习弥佳,流连信宿,不觉忘返,目所履历,未尝有也。既自欣得此奇观,山水有灵,亦当惊知己于千古矣!”[10]793所谓“书记及口传”,就是突出集体记忆,而此处对三峡“水疾”的“临惧相戒”已转换为审美体验。又如《水经注》载:“(滱水)东北二面,岫鄣高深,霞峰隐日,水望澄明,渊无潜甲。行李所迳,鲜不徘徊忘返矣。”[10]285“行李所迳”是指大多数观览者,对于“岫鄣高深”而“徘徊忘返”,就是在审美了。就山水文学来说,如此感受的叙写最为可贵,意在给世人提供审美对象。即使前述的山水祭祀之文,也是把山势的高耸险恶等,转化为壮美以颂扬之,以引导世人审美。
对集体记忆中的山水叙写,许多存在于口传之中,北朝时流传着许多对特殊景貌山水的歌谣、谚语吟咏:
其山高处可三四里,登山东望秦州可五百里,目极泯然,墟宇桑梓与云霞一色。其上有悬溜吐于山中为澄潭,名曰万石潭,流溢散下皆注于渭。东人西役,升此而顾,莫不悲思,其歌云:“陇头泉水,流离四下。念我行役,飘然旷野。登高远望,涕零双堕。”是此山也。[9]243
(汉水)涝滩,冬则水浅而下多大石。又东为净滩,夏水急盛,川多湍洑,行旅苦之。故谚曰:“冬涝夏净,断官使命。”言二滩阻碍也。[10]658-659
(黄牛滩)南岸重岭叠起,最外高崖间有石,色如人负刀牵牛,人黑牛黄,成就分明,既人迹所绝,莫得究焉。此岩既高,加以江湍纡回,虽途迳信宿,犹望见此物,故行者谣曰:“朝发黄牛,暮宿黄牛,三朝三暮,黄牛如故。”言水路纡深,回望如一矣。[10]793
太白山甚高,上恒积雪,无草木。半山有横云如瀑布,则澍雨。人常以为候,验之如离毕焉。故语曰:“南山瀑布,非朝即暮。”[9]192
如叙写三峡之水的“峻激奔暴”,以渔者歌“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10]790来衬托之。配以历代歌谣、谚语,更可知所叙写的景物是获得世人认可并构成集体记忆的,且山水景物具有某些特殊性,是值得叙写的。郦道元《水经注》中的山水描摹,是集体记忆的山水形象之集大成,其序一方面称是“脉其枝流之吐纳,诊其沿路之所躔,访渎搜渠,缉而缀之”的亲身考察,另一方面又称是“辄述《水经》,布广前文”[10]1。他对山水实景的叙写,即整合了古往今来山水游历的集体记忆。

尧盖临河颍,汉跸践华嵩。日旂廻北凤,星旆转南鸿。青云过宣曲,先驱背射熊。金桴拂泉底,玉琯吹云中。古辙称难极,新途或易穷。烟生山欲尽,潭净水恒空。交松上连雾,修竹下来风。仙才道无别,灵气法能同。东枣羞朝座,西桃献夜宫。诏令王子晋,出对浮丘公。[5]106
此类诗作,山水景物往往是富丽堂皇的,是为了体现皇恩、皇威,颇有在实景基础上的造景抒情的意味,体现出士人陪同侍从皇帝出游所叙写山水的特征。北朝山水文学,往往要叙写路程之中所发生的古事,如:
(崔光)寻以本官兼侍中、使持节,为陕西大使,巡方省察,所经述说叙古事,因而赋诗三十八篇。[3]1487
(常景)出塞,经瓫山,临瀚海,宣敕勒众而返。景经涉山水,怅然怀古,乃拟刘琨《扶风歌》十二首。[3]1804
所谓“所经述叙古事”“经涉山水,怅然怀古”,就是有意识地把今人与古人联系在一起构成集体记忆,在此语境中叙写山水。又,即便是流放性的“远戍”,也要把身之所处的山水景色告诉亲朋好友,如孙万寿在《远戍江南寄京邑亲友》中写道:“晚岁出函关,方春度京口,石城临虎据,天津望牛斗。”“裹粮楚山际,被甲吴江濆。吴江一浩荡,楚山何纠纷。惊波上溅日,乔木下临云。”[11]2639如此大笔墨地叙写山川,就是要与亲朋好友构成一种集体记忆,以抒发寄托作者情怀。
南朝山水诗多重个人体验,如谢灵运山水诗,就是“怀新道转迥,寻异景不延”[11]1126,探索奇景以抒发情感,故白居易称其“壮志郁不用,须有所泄处,泄为山水诗,逸韵谐奇趣”[12]。北朝也有个人体验之作,如北朝后期的山水诗作品,又如袁翻出为平阳太守,甚不自得,遂作《思归赋》,赋中叙写他乡的山水景色。如此叙写是为了衬托作者的“思归”之情:此时此刻,自己家乡的山水景色,一定清晰地呈现在作者的脑海之中。总的来说,北朝山水文学叙写重集体记忆,与个人体验之作交相迭现,交相辉映。
三、玄思:集体记忆中的人生哲理
北朝的山水文学,往往叙写作者面向山水时对人生哲理的玄思,以此传达出对当前人生价值的看法,这是以玄思来实现“自我”的发现。而这种玄思往往是古来哲思者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可谓是集体记忆的一种表达。
北魏高允的《鹿苑赋》,叙写由凉入魏的昙曜凿雕云冈石窟,赋中写到石窟所在地鹿苑的景象:“恬仁智之所怀,眷山水以肆目。玩藻林以游思,绝鹰犬之驰逐。”[13]3651这里突出石窟是僧侣遁世隐修之所,而山水对北朝文人来说,实际上往往就是玄思之所。又如北魏张渊的《观象赋》称:“夜对山水,栖心高镜,远寻终古,攸然独咏。”[3]1953即是作者对山水引发的玄思与吟咏,把山水当作玄思之境。如《水经注》载涑水东陂晋兴泽曰:“其西则石壁千寻,东则磻溪万仞,方岭云回,奇峰霞举,孤标秀出,罩络群山之表,翠柏荫峰,清泉灌顶。”“是以缁服思元(玄)之士,鹿裘念一之夫,代往游焉。”[10]171“思元(玄)”“念一”等修道之士,不怕艰难险阻,就是为了来此玄思。在《水经注》中,此类记载不少,如:
(清水)瀑布乘岩,悬河注壑二十余丈,雷赴之声,震动山谷。左右石壁层深,兽迹不交,隍中散水雾合,视不见底。南峰北岭,多结禅栖之士;东岩西谷,又是刹灵之图。竹柏之怀,与神心妙远,仁智之性,共山水效深,更为胜处也。[10]223
(颍水)山下大潭,周数里,而清深肃洁。水中有立石,高十余丈,广二十许步,上甚平整。缁素之士,多泛舟升陟,取畅幽情。[10]512
由此便有带着玄思意味的山水诗创作,如郑道昭的《于莱城东十里与诸门徒登青阳岭太基山上四面及中扫石置仙坛诗》[11]2206,诗中既有山岭景物叙写,也有山中“仙房”景物叙写,最终落笔在山中的儒家、道家经典的讨论:“依岩论《孝》《老》,斟泉语《经》《庄》。长文听远义,门徒森山行。”作者强调在大山之中开展的是玄思活动,于是结尾说“栖槃时自我,岂云蹈行藏”,说明“栖槃”是为了玄思,而非考虑“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问题。其他山水诗如温子昇的《春日临池诗》“莫知流水曲,谁辩游鱼心”[11]2222,也蕴含着玄思。这些玄思,均是集体记忆中的儒道情怀。

北朝山水诗叙写山中生活,尤为出色,如杨素的《山斋独坐赠薛内史诗》[11]2676二首。前一首对山居景色的描摹,由远及近,远山、风云、深溪、日出、鸟散,又由兰庭到竹室,落花、细草一一落笔到“幽”;“幽”是诗人玄思的结果,于是便有“临风望羽客”之想,渴望脱离人世进入“羽化而登仙”的玄境。后一首叙写户、窗面向山景,独自享受着“寂寂幽山”,“独坐”“鸣琴”都是为玄思而设。从“谁知无闷心”的玄思来说,这是从多少代士人“独善其身”的人生境界的集体记忆,达到了“自我”的发现、叙说个人的社会价值。又如薛道衡的《敬酬杨仆射山斋独坐》,其诗曰:
相望山河近,相思朝夕劳。龙门竹箭急,华岳莲花高。岳高嶂重叠,鸟道风烟接。遥原树若荠,远水舟如叶。叶舟旦旦浮,惊波夜夜流。露寒洲渚白,月冷函关秋。秋夜清风发,弹琴即鉴月。虽非庄舄歌,吟咏常思越。[11]2683
前面全力叙写山水之景,末二句用典,以越人庄舄吟唱越国乐曲以示不忘故国,既叙写自己的思乡之情,又回归山水之理,此中“独坐”成为北朝诗人面向山水玄思的专有意象。此处的玄思,则是集体记忆中的家园情怀。
在北朝,多有以山水为家园的作品,如祖鸿勋去官归乡里,在《与阳休之书》中肆力描摹其家乡雕山的景象,称处于其间,“杳然不复自知在天地间矣”[14];又述“乃还所住。孤坐危石,抚琴对水,独咏山阿,举酒望月”,于是乃有“听风声以兴思,闻鹤唳以动怀”[14]的玄思。
从北朝文人在山水中玄思,可知其与东晋玄言诗的不同。玄言诗往往以时间为基础,如郭璞的《答贾九州愁诗》云:“广莫戒寒,玄英启谢,感彼时变,悲此物化”[11]862;卢谌的《时兴诗》曰:“形变随时化,神感因物作。澹乎至人心,恬然存玄漠”[11]885;孙绰的《秋日诗》道:“山居感时变,远客兴长谣”[11]901;王羲之的《兰亭诗》曰:“悠悠大象运,轮转无停际”[11]895;殷仲文的《南州桓公九井作》云:“四运虽鳞次,理化各有准”[11]933;等等,都是以四季的变化引发的玄理叙说。北朝山水诗中的玄思所体现的集体记忆,则以山水空间为基础,讲求地点,以山中景物为归心、静心、养心的场所,由此玄思实现“自我”。
四、山水文学中的人工建筑:集体记忆新的关注点
人类如何在山水自然中显示自己的存在?这主要体现为山水开发。如何将山水开发成为集体认同?这是北朝山水文学集体记忆书写新的关注点,是当时人所自豪的,也是藉此种形式表达对山水的崇敬。
为了巡幸的便利,太武帝拓跋焘于太平真君三年(442年)在阴山北麓建造了行宫,其后,拓跋焘于太平真君六年(445年)、九年(448年)均巡幸广德宫。建宫之时,适逢被南朝刘宋灭国的后仇池国国君杨难当来投靠,遂将该行宫取名为广德宫。《水经注》载:“山无树木,惟童阜耳,即广德殿所在也。其殿四注两夏,堂宇绮井,图画奇禽异兽之象。殿之西北,便得焜煌堂,雕楹镂桷,取状古之温室也。”“刻石树碑,勒宣时事。《碑颂》云:‘肃清帝道,振慑四荒,有蛮有戎,自彼氐羌,无思不服,重译稽颡,恂恂南秦,敛敛推亡,峨峨广德,奕奕焜煌。’”[10]79-80人造的广德宫及居于其中的住客,于是成为山水的主人公;广德宫是大山里的新景物、新景点,虽然“刻石树碑”是为了“勒宣时事”,但是对山水、对建筑的叙写是必不可少的,这种叙写以记忆前代事迹为基础而展开。
北魏高允的《鹿苑赋》,叙写由凉入魏的昙曜凿雕云冈石窟,叙写开凿于山水之间的石窟,张扬其建筑在山水之间的意义。一是“若祇洹之瞪对,孰道场之涂回,嗟神功之所建,超终古而秀出,实灵祇之协赞,故存贞而保吉。凿仙窟以居禅,辟重阶以通术”[13]3651,石窟所在的整个山水,都成为佛教场所。“祇洹”即祇园,“祇树给孤独园”的简称,为印度佛教圣地之一。“道场”,诵经礼拜的场所。二是“澄清气于高轩,伫流芳于王室。茂花树以芬敷,涌澧泉之洋溢”[13]3651,如此乐土般的境地,正是世人记忆中的佛教圣地。
阙名的《石门铭》,先叙“此门盖汉永平中所穿,将五百载。世代绵迥,屯夷递作,乍开乍闭,通塞不恒”[13]3796;再叙北魏正始四年(507年)梁、秦二州刺史泰山羊祉“开创旧路”,永平二年(509年)完工;又叙其路上景色:“水眺悠皛,林望幽长,……千载绝轨,百两更新。敢刊岩曲,以纪鸿尘。”[13]3796现实的景象,不正是历代人们所念想的通途所在吗?于是,款款叙来的新修道路上的山水景物已不重要,集体记忆中愿望的实现,才是作者所关注的重点。
北魏宣文帝时,元苌任雍州刺史,作《振兴温泉颂》,除了叙写温泉的山水景物外,作者还多叙温泉的建筑景物。“乃翦山开鄣,因林构宇,邃馆来风,清檐驻月”[13]3585,元苌所自豪的,是他所建造的温泉建筑与山水天然景色交相辉映;“望想烟霞,迟羽衣之或顾,愿言多士,恕因兹以荡秽”[13]3585,是他所建造的温泉建筑,或能招引仙人,更为“多士”造福。
北魏神龟年间,在洛阳宣阳门外四里的洛水上作浮桥,所谓“永桥”。常景为此而作《汭颂》[15],文中先颂及洛水及洛阳。如果说颂扬是公式化、概念化的,那么常景叙写的是世人集体记忆中的洛水及洛阳。接着,作者颂扬洛桥的建设令洛阳“水陆兼会,周、郑交衢”,于是“爰勒洛汭,敢告中区”,笔下全是新生事物。然后,再颂洛水两岸人工建筑,谓:“南北两岸有华表,举高二十丈。华表上作凤凰,似欲冲天势。永桥以南,圜丘以北,伊、洛之间,夹御道有四夷馆。”作者归因到北魏皇朝“魏箓仰天,玄符握镜,玺运会昌,龙图受命”[15],才会有如此景物与气象。
北周唐瑾的《华岳颂》,前半部分叙写西岳华山“盘纡嶻嶭,刻峭峥嵘”的形貌,并有华山之中“信群帝之所休憩,众神之所肸响”的神话故事叙说,落笔于“国荷其庆,民赖其福”[13]3912-3913,这是某种集体记忆。重点在于后半部分的叙写修葺华山祠宇,“前代曾创祠宇,兼植柏树,历年兹多,榱栋崩褫,树亦往往残缺”,“别更列植青松二千余根。堂庙显敞,房廊肃穆,芬哉薜席,赫矣神居,桂酒徐斟,清哥缓节,无复沾濡之事,岂有颠沛之容”[13]3912-3913。以此为由,叙写北周文帝的功绩。最后称:“穷地之险,极天之峻。川泽通气,山薮藏疾。灵岳峨峨,清干秩秩。隈积冬霰,峰留夏日。雷霆以之,风云自出。”[13]3912-3913一颂华山,二颂祠宇,重在以集体记忆中的西岳华山叙写来歌颂当时朝廷重建的祠宇这一新生景物。
庾信的《终南山义谷铭》,颂“大冢宰晋国公命凿石关之谷,下南山之材”的事迹,对义谷景物多有描摹,以自古以来的景物“寥廓上浮,峥嵘下镇。壁立千丈,横峰万仞。桂月危悬,风泉虚韵”来凸显、对比“凿石关之谷”的人工奇观:“乘舆岭阪,举锸云根。八溪分注,九谷通源。北涵桐井,南浮石门。模象《大状》,规绳百堵。胶葛九成,徘徊千柱。桂栋凌波,梅梁乘雨。疏川奠谷,落实摧柯。事均刊木,功侔凿河。”[16]文中歌颂晋国公大兴人工建设之举,称之为“义谷”。
对建筑在山水之间的人造工程、诸种建筑的叙写,是北朝山水文学新的叙写点,明钟惺称南朝“(谢)玄晖以山水作都邑诗”[17],此可谓相互呼应。而北朝山水文学新的叙写点,正是在集体记忆的观照下才显得更为出色。
五、山水之间的文学活动:集体记忆与山水同在
北朝山水文学的文本崇尚在山水之间展示,表现出北朝山水文学多将集体记忆保留在山水之间,欲与山水同在,让山水成为文字的“山水符号”记忆贮存的媒介。
据郦道元的《水经注》所载,北朝时期山水之间的碑刻甚众,如:“徐水三源奇发,齐泻一涧,东流北转迳东山下,水西有《御射碑》。徐水又北流西屈迳南崖下,水阴又有一碑。徐水又随山南转迳东崖下,水际又有一碑。凡此三铭,皆翼对层峦,岩障深高,壁立霞峙。石文云:皇帝(太武帝拓跋燾)以太延元年(435年)十二月,车驾东巡,迳五迴之险邃,览崇岸之竦峙,乃停驾路侧,援弓而射之,飞矢逾于岩山,刊石用赞元功。夹碑并有层台二所,即御射处也。碑阴皆列树碑官名。”[10]292从“迳五迴之险邃,览崇岸之竦峙”等句,可知这些碑刻中不乏山水描摹的文字。
北朝山水文学盛行以刊石为重要载体之风。拓跋鲜卑由游牧民族崛起,迁居盛乐立都,建立代国、北魏,前期的几个皇帝总要在夏天巡幸漠南及阴山地区,巡察北疆安全。农业文化追求稳定,游牧文化追求流动,北朝皇帝往往把自己的巡幸经历铭刻在大山里,北朝将军也把自己的征战经历刻写在大山里,刊石勒铭,既要把人类的行为告知山水,也要将山水游历经过以坚实的物质材料保存起来,令其成为记忆,这便是北朝山水文学发生的某种先导因素。据《北史》记载,太武帝拓跋焘太平真君四年(443年),“行幸中山”,“次于恒山之阳,诏有司刊石勒铭”[7]55。《魏书》载:“太安四年(458年),车驾北征,骑十万,车十五万两,旌旗千里,遂渡大漠。吐贺真远遁,其莫弗乌朱驾颓率众数千落来降,乃刊石记功而还。”[3]2295和平二年(461年),拓跋浚巡幸,“灵丘南有山,高四百余丈。乃诏群官仰射山峰,无能逾者。帝弯弧发矢,出山三十余丈,过山南二百二十步,遂刊石勒铭”[3]119。征战中的“刊石纪功”本是有传统的,《周书》记载,陆腾征讨蛮獠,山路险阻:“遂量山川形势,随便开道。蛮、獠畏威,承风请服。所开之路,多得古铭,并是诸葛亮、桓温旧道。”[18]此称“古铭”,即指诸葛亮、桓温进军此处。也有对行军经历刊石勒铭的。《水经注》载:十六国时,“卢龙(塞)之险,峻坂萦折,故有九之名矣。燕景昭元玺二年(353年),遣将军步浑治卢龙塞道,焚山刊石,令通方轨,刻石岭上,以记事功,其铭尚存”[10]345-346。《魏书》载:“皇兴四年(470年),予成犯塞,车驾北讨。……(显祖)乃选精兵五千人挑战,多设奇兵以惑之。虏众奔溃,逐北三十余里,斩首五万级,降者万余人,戎马器械不可称计。旬有九日,往返六千余里,改女水曰武川,遂作《北征颂》,刊石纪功。”[3]2295-2296《文选》赋有“纪行”类,录班叔皮(彪)《北征赋》、曹大家《东征赋》、潘安仁《西征赋》。按惯例,“纪行”是以叙行历而见志,应该有景物描摹,可惜《北征颂》今已不见。撰作《北征颂》并刊石纪功,一方面是让记忆依赖于外部的“符号贮存系统”;另一方面则是让后来人观赏、体认这些石碑、铭文,通过对历史的记忆,传承民族精神。
北朝多有以山、水之名命题为某某山水铭、某某山水颂、某某山水碑,颂名山大川,这些铭、颂、碑都是立于山水之间的。北魏郑道昭的《天柱山铭》,佚文中尚存片段景物叙写:“孤峰秀峙,高冠霄星。实曰天柱,镇带莱城。县崖万仞,峻极霞亭。据日开月,丽景流精。朝晖岩室,夕曜松青。九仙仪彩,余用栖形。龙游凤集,斯处斯宁。渊绵穷想,照烛空溟。道畅时乘,晔光幽明。云门烟石,登之长生。”[13]3712铭文围绕“天柱”二字叙写名山景色,以“登之长生”作结。郑道昭之子郑述祖说,“镌碑一首,峰之东堪石室之内,复制其铭”[13]3864,这是刻立于山峰之中的,正是由于有碑、有铭,才使子孙后代有永久的记忆。郑述祖亦有《天柱山铭》,叙写天柱山的钟灵神秀、宏伟雄阔,一颂天柱山,二颂祖先。此为摩崖石刻,原石高约3.5米、宽约3米、厚约2米,原在山东省平度市大泽山镇的天柱山西麓,后虽被破坏,但亦有残石四十余块藏于平度市博物馆。郑述祖把“铭”镌刻于石崖,希望“孝思”永存。刊山勒铭,山水之铭、颂、碑等把人的行为刻写在山水之间,并把人的行为告知大山大川,这也是向世世代代的人们彰显不朽的历史功绩。
北朝人的山水吟咏,也时常在山水之间展开,“至若娈婉丱童,及弱年崽子,或单舟采菱,或叠舸折芰,长歌阳春,爱深绿水,掇拾者不言疲,谣咏者自流响”[10]290-291,“谣咏者自流响”,这是游览山水的现场吟咏。又如郦道元讲自己在巨洋水的现场吟咏:“炎夏火流,间居倦想,提琴命友,嬉娱永日,桂笋寻波,轻林委浪,琴歌既洽,欢情亦畅。”[10]618朝廷也多在山水之间组织文学活动。“孝文帝南巡至新野,临潭水而见菖蒲花,乃歌曰:‘两菖蒲,新野乐。’遂建两菖蒲寺以美之。”[9]819又如孝文帝在上党之铜鞮山,命元勰作诗,其诗曰:
问松林,松林经几冬?山川何如昔,风云与古同?[3]572
在山水之间吟咏山水,不仅是人类的文学活动,而且也是人类与山水共咏的、互动的活动。在山水之间吟咏山水,山水文学与山水一起构成集体记忆。北朝由于山水诗不算非常发达,而令山水文学谱系中各种文体的山水叙写有所特别的显现,由此又显现出集体记忆给予北朝山水文学的原创动力,这便是北朝山水文学给文学史提供的新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