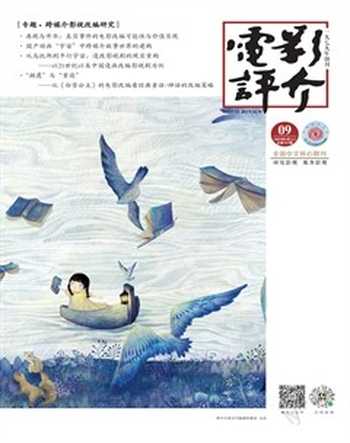图像本体论中的电影实践:视觉解释与进化论
曹亮

在关于电影本质与表述方式的各种理论中,基于基本视觉感官体验的图像本体论被认为构成了电影艺术的基础。电影的图像本体论涵盖了“电影起源心理学”和“电影语言进化观”,最早由安德烈·巴赞提出。电影从本质上讲是一种“视听”尤其是“视觉”艺术或文化产品,在人们说“看电影”的同时,也在观看中获得了思索性的审视与视觉性的评判。通过电影中的种种形象,人们对画面中的角色与静物有了“好”“坏”“美”“丑”等基本判断;电影艺术就是在这种最基本的视觉判断中形成的。与日常生活中“看到”的一般性体验不同,电影让大家“看到”了一件现实事物的另一种存在方式。本文称其为围绕着图像本体论的观看实践。而在这一实践的背后,“看”依然存在诸多解读方式,它是人类生物性与文化交织作用的结果,不仅带给了人们诸多视觉性的艺术体验,也塑造了人类本身。
一、图像本体论与审美意识的产生
毋庸置疑,电影是一门通过视觉进行体验的视觉艺术,“研究电影”“欣赏电影”“通过电影放松心态”都可以被归结为“看电影”——尽管几种体验的出发点、目的与选择的影片都大相径庭,但电影创作出来就是为了给观众“观看”的。容易被忽略的是,“看电影”这一想法本身就是从电影的图像本体论中获得的——在《摄影影像的本体论》一文中,巴赞提出,电影对事物原貌进行再现的本性构成了电影美学的基础。因为一切艺术都是以人的参与为基础的,唯独摄影给了物本身摒除人类意识介入的特权,摄影取得的影像因此具有自然的属性。[1]在图像本体论的前提下,电影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美学的观看行为。这样美学的、沉思的观看与审视,并非自然状态下单纯的“看”。自然的“看”是行为的、内嵌的,是从属于某一特定目标的,这一状态让观看主体对自然界敞开了自身,但并没有达到对世界的反思或审视。大多数时候,“观看”达不到“凝视”也不代表任何意义上的审美。但图像本体论却恰恰是以这种非审美视点的审美化来达到艺术主张的。
在中国,对“小人物”命运的关注和书写成为左翼电影以来中国电影的重要传统。在《神女》(吴永刚,1934)中,为了养活自己和儿子挣扎在社会的最底层的女主人公从事着卑贱的工作,但这一份工作却磨灭不了她美好的心灵;《万家灯火》(沈浮,1948)中,公司职员胡智清无力处理一家6口人的生活就业问题,没本事的弟弟出去擦鞋被挨打,贤惠妻子的担忧和抱怨让母亲听到了,愤怒的母亲要带着乡下人离开他,原本平静的生活陷入了混乱之中。在戴锦华教授看来,这种“看见”的力量正是中国电影自身的传统。“某种小人物的日常悲喜剧,某种社会的伦理-政治立场,某种直面现实、饱含进取与悲悯基调,同时召唤和安置人的中国叙事样式,你会发现从彼时到今日,不同时期仍会有不同的电影自觉呼应着,或者不期然地重现着中国在自己的电影史当中所形成的路径、传统。”[2]中国左翼影片的叙事结构同样是含蓄、朴实而严谨的,没有大的情节冲突,没有过于深恶痛绝的压迫,只是在生活中循序渐进的矛盾的累积下使矛盾的张力突然爆发,让观众眼前一亮,现实主义电影终于在观众最真实的感受中得到了共鸣。
在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其他影片中,一种基于现实主义的本体论频繁出现。《偷自行车的人》(维托里奥·德西卡,1948)中,导演使用了许多纪录片式的跟拍视角,跟拍里奇父子两人在罗马的街道上穿梭来往打工和找回自行车的过程。即使是真正目击一对父子做这些事,也需要调用我们的眼睛和其他感官。这种观看是自然发生的、下意识的、直接的。这部影片既不批判,也不怜悯,甚至扮演男主角里奇的演员也只是一个同样面临失业窘境的银行职员。影片只是客观地捕捉了现实中的片段,又在不加修饰的情况下使观众看到了它们。《温别尔托·D》(维托里奥·德西卡,1952)展示了一位勤勤恳恳的小公务员风烛残年的艰难困苦,他沉重蹒跚的脚步与孩子、小狗轻快的跑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垂暮之年的艰难动人心魄;《孩子在看着我们》(维托里奥·德西卡,1944)中,一个天真无邪的男孩被迫先后经历了目睹一系列人生变故,反映了大人荒唐行为的背后,家庭破裂对孩子们成长过程产生的不可磨灭的影响。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优秀作品总是会让人产生某种无形的压力,一种天人交战后无奈惨淡的状态带给人的压迫感。
画面塑造了人们的审美意识,也促使人们形成了关于“观看”的概念,并影响和改变了人们使用视觉本能的方式。“圖画成了一种观看的工具,成为一种评价标准,我们以此来评价直接的认识,至少是某些认识图画把观看从一种在背景中运作,指导我们把工作与游戏的技能转化成一种专注的充满思想的评价活动。”[3]在图像本体论下,电影改变的不仅是“观看”这一过程,更是人们所看到的东西,或者至少是人们对所见之物的概念。《神女》中的孩子给母亲展示学校中学到的体操动作,女主角模仿着孩子稚嫩的动作,母子俩笑得纯净自然,但其中的现实伤痛与最真切的无奈在电影史上蜿蜒了几十年,影响了无数电影人的创作实践;当“跟踪者”成为“跟镜头”,当“偷自行车的人”成为世界电影史上最经典的形象之一时,我们可以看着父子俩在大雨里哆嗦地找寻着他们的自行车。即使是在现代电影理论或形式主义电影理论中,种种理论文化规范也不会阻止人们去屏息凝神地观察一帧画面、一个人物;相反在现实情境中,即使得到允许,通常人们也不会像凝视着电影角色一样在现实中去盯着真实的人或者景物,凝神静气长久地将目光放置在其上。电影与其说是审美意识的结果,不如说它是产生审美意识的前提。相比审美意识,电影的图像本体总是具有先在性的。
二、具象与抽象“物象”的视觉解释
图像本体论主张电影和照相一样,都是对生活的记录与对现实的再现,这一理论的核心和基本观点是影像与客观现实中的被摄物的同一性,即被摄“物”应该以其在现实中存在的方式作为“物象”展现出来。可以说,“物”与“物象”之间的同一性构成了经典电影现实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石。日常生活中,人们会理所当然地将眼前所见的一切当作亟待认识的对象或使用的工具。如果我们尝试一种置身事外的立场,以超验的眼光去观看去审视,而不是去使用,这件东西就会被赋予“形象”的特征。“物”与“物象”的关系揭示了电影与现实在视觉图像方面的差别:在电影的世界中,一种依赖观影行为产生的观影意识会让人们看到人的形象与物的形象本身。电影中的世界是投影产生的“虚像”,但它却会以独特的图像本体基础上让我们意识到物质的特殊性,它会重新提出“世界是由物质组成的”这一现代人习以为常的观点。与现实中的物不同,电影中的“形象”是独立、中性与物质性的东西,它无法被银幕外的人类所使用,且有它本身的属性。总而言之,电影为人类提供了一种置身事外的审视视角,并让人们以这种方式思考和观看现实“真正”的样子,而不是在使用某件物品的基础上理解它的可用性。从这一角度来看,现实主义的图像本体论是一种标准根据,这种标准让人们形成了关于观看行为的视觉意识,标准观看行为的结果则形成了关于“物象”的概念。
在图像本体论实践的过程中,电影呈现了一件独立物品应有的状态,它让人们以冷静和敏锐的目光通过银幕观察这件物品本身。此时,“物”才会真正从物质世界中显现出来。因此,“物象”的显现是审视行为的结果,也是借助图像工具对世界进行认识的结果。只有当人们在主观上有意识地调动高等审美思维时,才会把“物象”带进电影艺术的视野中。以《暴裂无声》(忻钰坤,2017)中丰富多样的物象为例,象征稳固的三角形与三角形的崩塌是影片中重要的意象群:昌万年办公桌上的金字塔,张磊在山上堆出的石块,以及坍塌的山体,都显现出了三角形棱锥的形状,代表着阶层、等级、地位、权力;电影片尾山体忽然坍塌,象征人们出卖良心、违背道德等等,导致金字塔失衡,从而坍塌,或者说正义天秤倾倒;同时,也象征着张保民内心希望的破灭、对人性的失望。《暴裂无声》不仅仅是一部悬疑片,还包含了对社会、人性、阶层等主题的探讨,解读空间巨大,电影中的各种人物、道具、符号也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往往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拒绝这种第三视角的审视,认为它只属于文化,不值得信赖。但当电影将这一器物摆在人们面前时,却不会被其联系的一套文化规约所冒犯。这是电影的意义之一,它被创作出来就是为了让我们审视自身的生活。
在具象化的物体之外,电影还提供了另一种对抽象之物的展现,它同样处于美学的审视之中。例如《天才捕手》(迈克尔·格兰达吉,2017)中的爵士乐。这部影片讲述了同样身为文学天才的柏金斯与伍尔夫惺惺相惜,二人性格迥异却不约而同地支持着对方。在一次沟通出现问题时,性格跳脱的伍尔夫带沉静内敛的伍尔夫来到黑人酒吧,将柏金斯最喜欢的歌曲以爵士乐的风格演奏。在旋律相似却截然不同的风格中,伍尔夫率先兴奋地伴随音乐跳了起来;柏金斯一开始并不为所动,后来也用皮鞋打起了节拍,继而绽放出笑容,与他一起大笑起来。这段表演中,音乐与围绕着音乐的动作成为了重要的物象,柏金斯以富有层次的表演展现了他逐渐被音乐感染的过程,而音乐与舞蹈也被赋予了不同于生活经验的强烈感染力。“美学的审视,如前所述,是一种超然物外的沉思的审视。它是一种视觉评判,而绝不单单是一种直觉反应,无论感受多么强烈。使它成为审美的恰恰是因为它源自于一种好奇心,且对自己要做反应的意向漠然置之。”[4]电影让大家看到的是一件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物品的样本。如果退后一步,用超脱的视角重新审视,也许会看到全然不同的风景。爵士乐本身演奏风格随意,其视觉构成也具有较大的发挥空间,因此也一直为电影艺术家所青睐。《海上钢琴师》(朱塞佩·托纳多雷,1998)中激烈的斗琴场面,还有在钢琴弦上一触即燃的香烟、《心灵奇旅》(彼特·道格特、凯普·鲍尔斯,2020)中乔伊·高纳在演奏时身边场景的变幻、种种奇异场景的出现,都源于此。电影本身即是为了让我们审视而被创造出来的更加真实的现象,它不仅提高了“物象”的特殊性和重要性,也重申了“物”本身的意义。
三、艺术进化论与电影认知的生态学
尽管在传统的学科分类中,文化艺术与生物学是两个迥然不同的分类范畴;但实际上,由人创造的一切文化艺术都不可能完全游离于人类的生物性之外,审美意识与人类的生物性紧密相关,并随着技术发明与文明进步不断演进。进化论作为奠定现代科学文明的基础性成果被提出和接受,生物学家以一种超越人类的视角审视了物種演进的过程。在我们讨论进化论时,讨论更多的并非信仰科学的可靠性,而是信仰人类认知能力的可靠性。因此人类试图通过各种手段了解自己作为一个物种的生物本性——其中就包括电影——这也是一种最根本的自然主义。如果没有艺术,那么个体仅仅能拥有个人的身体和经验,也只能用自己的感官来体验世界,或借助文化与科学来认知、衡量世界的尺度;每个人描述世界的方式,也都会受到其个人特别兴趣需求价值观或立场的影响。这些是我们的局限。而电影或其他艺术形式,在这一方面的作用相当于科学方法,它的意义在于让我们超越这一局限。
在近些年越来越流行的电影认知理论中,约瑟夫·安德森通过引入詹姆斯·吉布森的生态学方法,开辟了电影认知理论的新思路。生态学概念来源于生物学,同时也是环境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生态学分析最新的弹幕电影、交互观影等电影形式,会发现这些新的观影方法与电影形式是借由网络信息传播技术引导受众形成的一种新的行为模式及组织形态。例如《秦时明月之龙腾万里》(沈乐平,2014)中,发行方与影院联动开发了一种即时评论的分享系统,它直接将使用评论覆盖在影片文本之上,可以让观众在观影的时候通过弹幕与其他观众进行交流。很大程度上来说,弹幕的发生是人们建诸智能手机平台或者说平板这种个体化的观赏活动上的一种参与活动,一种积极的接受活动。《秦时明月》系列本身拥有一部优秀的武侠故事所具备的一切元素,例如借助于历史重大事件阐发的民族精神,宏大叙事带来的磅礴气场,延续自现代武侠小说的、“侠高于武”的核心价值等;在多部电视动画剧集之后,这部知名IP的电影新作本身即携带了话题性与互动性,具备了能够展现中国动漫美术实力和中国古典文化底蕴的文化基础。在此基础上,媒介技术充分改变了观影情景,赋予了诸多动漫迷们充分交流讨论的空间,让受众对影片的观赏和整个解码行动都在全新的技术条件下得到了支持。
在生态学与电影学的融合中,思想与文化之间的生态关系、人与世界时间的生态关系都被赋予了全新的理解空间。“当安德森将‘生态学概念引入电影认知主义研究时,至少强调了两点:一是电影之所以‘看起来真实,是因为观众感知电影的方式与他们感知自然的方式相似,造成了感官上的‘迷惑;二是某些电影之所更加流行(譬如经典好莱坞电影),是因为它们更符合观众的感知习惯,因而更容易被观众理解。”[5]这一观点并不是说艺术一定要被还原为生物学或进化论现象。这样的还原代表的不是科学或理性而是对科学和科学原则的幻想;同时,艺术也不能被还原为天生的审美意识。相比艺术,审美意识有着更为广阔的施展空间。况且,想要在艺术缺席的情况下弄懂审美意识的存在是不可能的——是岩洞中的古老创作给予了人们原始的视觉图像,又是千百年来的诸多创作实践使得审美意识成为了可能。
结语
人类所有的文明成果都无法游离于生物性之外。审美意识的产生与人类的生物天性密切相关。对于图像的执着与视觉审美意识,早已存在于人类基本的感受与行动之间,并根植于生物性的生活方式之中。人们是被自身文化与活动模式局限制的动物,同时又不仅仅是动物;我们在满足于从事生存活动之外,还有千头万绪的思想。
参考文献:
[1][法]安德烈·巴赞.电影是什么?[M].李浚帆,译.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9:315.
[2]戴锦华,胡亮宇.距离之外,空间之内:奥斯卡、电影与今日世界——戴锦华访谈[ J ].电影艺术,2022(03):107.
[3][4][美]阿尔瓦·诺伊.奇特的工具:艺术与人性[M].窦旭霞,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20:51.
[5]于欣彤.科学视角与学科融合:安德森“生态学”视角下的电影认知理论研究[ J ].当代电影,2022(01):1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