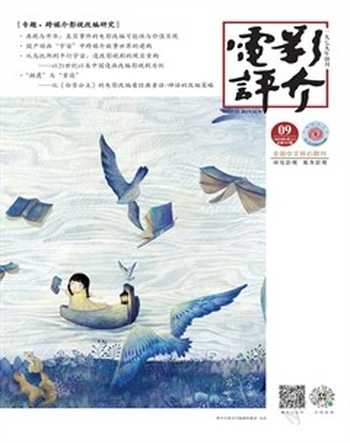重组实践立场下的电影符号与电影语言
高煦函 刘宇

人类的所有活动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层阶。在基础的技术组织层次上,人们有对话、运动、舞蹈等基本的、不由自主的运动,这是出于天性或习惯形成的第二天性,它们塑造和组织了人类自身。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许多简单的第一层级活动具有社会属性与文化特征,并而在更高的阶段上孕育出新的活动,如诗歌,舞蹈,音乐,电影等艺术。这些活动来源于前一阶段、却又重塑了前一阶段的活动。其中,电影就是一种相当典型的、第二层阶的重组实践。电影的发明立足于现代一系列科学研究的成果,电影艺术与电影符号学的形成则与20世纪以来的认识活动语言学的发展紧密相关,电影的实践同样紧密联系着它被组织的语境。其中,电影语言与电影符号构成了这一立场或环境的重要因素。在重组实践的立场下探讨电影符号与电影语言的形成与作用,既是一种电影学的知识考古,也对解释电影艺术的魅力与将来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重组实践立场的悖论性解析
顾名思义,重组实践的立场分为两大部分:首先是重组,其次是实践。在前者强调的功能性意义上,电影之所以能从一门再现事物的技术成为艺术,关键的一步便在于去除现实之物所处的环境与背景,使它们变得陌生化;并通过这种陌生化的路径,让观众去思考那些原本“理所当然”被接受的方式和背景。诚如克拉考尔所说的,摄影术的美学原则在于摄影师应用他没有个人特色和艺术装饰的手段的方法,摄影成果与其原本之间“未经改动的现实”和“偶见的事物”[1]展现出了真实的美感——人生本身就是片段化或含糊不清的。摄影术与电影都是复刻现实的手段,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本身不是一门艺术。因為“这种艺术概念模糊了摄影师在再现现实时那种独特并真正属于造型性质的努力——既再现客观现实的重要方面,但同时又不破坏现实原貌,这样就使镜头焦点中的素材显得既完整而又明白易懂了”[2]。相比之下,后者强调的则是电影实践的实际环境与语境,强调电影对于人类而言的实践特征。电影语言与电影符号只有在其被使用的语境下才有意义,剥离其语境的电影符号不过是毫无意义、只能代表物质世界片段的符码。脱离了重组实践的具体语境,电影符号作为艺术的意义就不复存在了。在实践视角下,一部电影就是一件特别的工具,一种奇异的认知手段,电影人或“迷影人”通过这样的工具来审视我们自己本身。综上所述,重组实践这一立场本身就带有一定的悖论性:一种认识性电影艺术究竟是工具性的、还是反工具性的?它的意义体现在何种层面上?
回到电影艺术诞生的最初时刻。如果说电影艺术的进步产生于摄影术的发现与发明,那么基于科学发明的感光胶片、胶片的洗印技术,以及出于各种目的制作和使用这些化学胶片的行为则可以称之为技术基础上的组织活动。这些组织活动在最基本的认识层面上,与原始岩洞中的炭笔绘画一样,形成了对我们所处环境的图形描绘。卢米埃尔兄弟时期的早期电影作品有选择地拍摄了工厂大门敞开、工人下班走出工厂、水浇园丁、火车在铁轨上行驶的画面,将这些不可能二次复现的情景记录保留了下来;在中国,早期电影人也在《定军山》等戏曲片中发现了京剧(尽管只有表演图像而无声音)的另一种再现方式。此后,戏剧化的布景也影响了一批早期中国电影,例如《劳工之爱情》(张石川,1922)用全景视角同时拍摄上下两层楼时,画面平面构图配合比例中略显失真的楼梯道具,整个场景便宛如戏剧舞台上的布景一般。然而,自然世界永远是无穷无尽的,人们永远无法以拍照或者摄像的方式使之穷尽;拍摄再多的影片或视频作品,人们也依然会感到对自身所处的环境缺乏认知,海量的图像信息反而会提醒我们人类始终处于迷失之中。于是,许多经典电影理论家都求助于更高层的艺术与哲学,让电影艺术在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引领人类找到方向。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在历史书写方案的高度“现实”中重新审视了电影与摄影术之间关系,提出了现实概念本身的不稳定性,因此电影可以被看作是从毁灭的历史中对物质现实的救赎;雨果·明斯特伯格求助于康德的哲学和美学,以电影深入生命和意识的根本所在。它们被永远地封闭在了因果关系的世界里[3];爱因海姆则将心理学引入电影理论,在借鉴格式塔心理学的基础上提出了形式主义美学与电影表意的基础[4]……在电影理论发展到战后电影的时期时,纪实主义电影理论家巴赞以《摄影影像本体论》中“人类保存生命的本能”成为了主导电影实践发展的重要力量。“对抗时间流逝这件事本身是为了满足人类基本的心理需求,因为‘死亡代表的正是时间的胜利。人们为了保持外貌,硬是以人为的手段将身体从时光手中夺回、精心藏匿,试图夺回对自身生命的掌控权。才在明知终将而至的死亡面前,汲汲营营于维持肉身的不老。”[5]尽管人们在观影过程中不会想到人类族群的古老梦想,但这些时间的确存在于人们真切的、重大的需要当中。
换言之,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技术如何进步,电影艺术的发展始终扎根在如此深刻的事实之中,让人们明白为何电影艺术的时间总是与我们的切身感受有深刻的渊源。从这一角度而言,电影重组实践的“立场”与其说是一种排除其他方向的、言语的唯一位置,不如说它是一种开放、包容的多元性视野。在这一视野中,电影就像是绘制地图。关键在于,绘制地图并不是为了收藏,甚至可以说不是为了单纯地记录路途;而是为了以这种工具性的方式表现现实空间的延展,这种任务源于一种迫切的、对于真实的追求。电影艺术及其实践既是构造人类“是其所是”的重要活动,也是在此基础上不断重新构造人们自身的实践,是某种试图弄懂我们自身的实践。人们的生活、语言与文化都是由既有的有机组织构成的,电影把人们的组织带进我们的视野,如此一来便重新组织了人们。二阶活动的重新组织实践尽管产生于一阶活动的组织基础,但它并非在层级上高于第一阶层的活动。它源自人类活动内部的一种持久而深刻的动力,这种动力促使人们在第一阶段的种种组织现象中发现自己,重新构造自己。因此,电影与人们的生活之间存在着一种根本、真实、至关重要的关系。即使对电影故事发生的背景并不了解,优秀的电影也总能令观众获得深切的共鸣。这样的重组实践反过来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
二、重组立场下电影符号的有效性
语言学家普遍认为,文字与古老的口头语言相比只是近一万年内的晚近发明。口语属于人类的生物传承,而文字则是约定俗成的、文化的产物。同样,电影符号与电影语言的概念也是由视听符号和影像书写在人们语言生活中的作用形成的,拍摄电影的方法由于得到了电影语言的组织而变得循规蹈矩,原本自发性的拍摄经常体现为既有语法的组合。在一个电影作用于客观再现的世界里,百年间无数优秀的电影作品为我们的形象刻画做出了示范。此后,再要脱离电影的形象去刻画形象,或拍摄卢米埃尔时代的电影就几乎不可能了。即使是电影学院的学生完成作业,他们也是在根据既定的电影语法取“编导”电影,他们引用和抽取他们学会的拍摄手法、镜头剪切、指导演员的表演方式和蒙太奇风格,原本那种天然的、随心所欲的、未经雕琢的刻画形象动作仿佛都来自于同一动作库,全部盖上了电影文化的烙印。“符号”与“语言”这两个术语在电影理论中经常混用,例如“电影符号学”与“电影语言学”的同义便能证明这一点,它们都指一种根源于索绪尔语言学的方法论。本文中的“符号”将更加强调其视听构成“展现”的方面,而“语言”则更重视其中“语法”与“书写”的一面。
在人类社会中,那些被认为有携带者的意义而接收的感知被定义为“符号”,每一种有实用目的的使用物或行为,都有可能带上符号意义,反过来,每一种共使用的物也都可以变成符号,每一个物都是“符号-物”。“它可以完全成为物,不表达意义;也可以向纯天然的符号靠拢,不作为物存在。任何‘符号-物都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移动,其使用部分与表达意义部分的成分分配,取决于接收者如何解释。”[6]在电影符号学的理论上,电影符号学明确强调了影像能指与所指之间的任意性。然而,具体影像表达何种含义能构成这一符号结构单元的“直觉”,大部分电影创作者与观众之间仍然保持着相对的默契;那些看似繁复多义的复杂意象,反而是导演刻意控制的。
在电影被发明后,其他关于图像再现的艺术也或多或少地受到了电影符号与电影语言的影响、电影不仅会指导人们该怎样刻画形象,而且让人们从先验的独处或熟悉的环境中的体验中抽离出来。这个过程的后果是,机械刻画形象和电影创作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因为我们刻画形象时电影的痕迹无所不在。这就是电影艺术的重组方式,它能重组是因为它能被领会、被消化,然后再次作用于一阶的活动。值得注意的是,人们似乎不会意识到这种直觉恰恰就是重组实践立场下的全新直觉,而不是第一次实践立场中完全契合人类天性的直觉。在电影将大到眼球的景别放上银幕供观众欣赏之前,这样细微的动作只能在文学描绘中出现,很难在日常生活中被普通人的肉眼注意到,而且并不是一种常见的表达。而在电影将这一细微的反应放大为一个完整的动作、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电影符号之后,这一符号便会摆脱电影媒介的塑造作用,出现在各种媒介的语言结构之中:漫画中将人物瞳孔绘制得较小以表示此人内心的震撼、动画中瞳孔连续的放大与缩小也同样如此;现代文学中“瞳孔突然缩小”的文字描绘方式与其代表的画面感也随之可见,例如中国电影《狙击手》(张艺谋,2022)中多次出现对狙击手瞳孔的特写、《吉祥如意》(大鹏,2020)中女主人公在对乡下生活感到不适时镜头推向角色眼睛等;就连电影中也出现了相似的表达:变焦摄影机镜头的缩短表示对焦和定焦的动作,以及“聚精会神地看”这一心理状态——或许这一动作才是瞳孔缩小动作出现在电影中的契机。“按要求我们应把字词作为图形元素来考虑,它们可以也应该写在一起。请注意,作者把单词、句子、词组的归类视作理所当然,这本身就已表明,关于语言是怎样构成的,我们早已有一个本体论深植文化之中了。”[7]电影符号并非从外部来代表现实事物,形成图形和形象。但是,如果不是已有样本告诉我们怎样以影像书写介入并表现现实,我们也很难在其中发掘人类与艺术相互构造的关系。我们用视听语言表现的不是客观现实,而是独属于电影艺术的话语或符号。以重组实践的立场来看,电影表现出的声音也不是全然如照相术所表现的那种家庭照片式的形象。电影符号不是我们可以冲印在胶片上的印痕,也不是抽象的狂想,而是摄影机镜头能够捕捉到的电影符号。影像书写不会脱离影像符号的领域,书写本身就是符号达成的目的之一。
三、重组实践下电影语言的指示性
摄影术的发明证明了现实事物是可以被技术手段“摹写”的。以某种方式将生活中的形象保留下来,是我们的天性——遍布全球的文明遗迹能够较好地反证这一点。电影的拍摄愈发展现了这一事实,让人们去观察各种图形,去解读其中关于我们自身的信息。同时,电影中的形象与力量又反过来影响并塑造了我们关于刻画形象的观念。其中,电影符号与电影语言在对形象的刻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成熟的电影符号与电影语言具有陌生化与凝聚精神的力量,能将现实中那些具有样本或示范作用的典型凸显出来,从而赋予我们指示性的力量。
自始至终,客观世界是可以通过影像书写的。电影可能不是客观世界的镜子,而是客观世界本身一种展现自我的方式。与其说它是人类反射客观世界的镜子,不如说它是世界自主自为的呈现。在重组实践的意义上,它也反映了人类描绘世界的自我形象。在电影语法实践的立场上,镜头与镜头之间的剪辑遵循着人类自然的視觉习惯,越轴、同景别切镜、直视镜头等行为都可能导致观众“出戏”;但一些有意为之的空镜头、镜像画面、长镜头中的沉默,同样是电影语言的一部分。中国东北的地域电影也有着相似的特性,近年来的《钢的琴》(张猛,2010)、《东北虎》(耿军,2021)等影片都对东北地区空旷广袤的原野、废弃的钢铁基地厂房等景物“情有独钟”。在电影语言的角度上,这些沉默的场景作为连接演员表演的“空镜头”,表达了空缺、断裂的意义。在这些影调低沉、情感沉郁的影片中,高耸的烟囱、一望无际的荒原、大块裸露的岩石一起构成一种特有的、指向“东北”的沉默表达。在俄罗斯电影《利维坦》(安德烈·兹维亚金采夫,2014)的一组典型镜头中,官僚主义作风的市长告诫已经完全世俗化的牧师,告诉他要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解决问题,还嘲笑单纯的牧师像个孩子。在两人离开镜头中后,摄影机将画面逐渐推向壁龛上的三尊金属塑像,这三尊塑像在电影符号学的意义上可以被解读为冷漠的面孔。兹维亚金采夫的电影语言承袭自塔可夫斯基,《回归》(安德烈·兹维亚金采夫,2003)中苍白低饱和的色调、沉郁的风格与晦涩的寓言感,《无爱可诉》(安德烈·兹维亚金采夫,2017)中无人呼应的呐喊、失去尊严的父亲长久的沉默、席卷银幕的漫天风雪莫不如此。兹维亚金采夫的影片已经成为一种别具特色的斯拉夫民族电影语言。在使用这门语言进行表述时,导演以冷寂的影像符号作为指示性的语法,在符号的基础上形成关于语法和语言的思考和体验。
结语
当下,两拨电影符号学热潮及广泛应用于其中的宏大理论逐渐过时,但实践重组的立场却给人们提供了审视这门对电影影响深远的理论的新契机。如同文字就是语言的影像一样,在德勒兹等哲学家看来,电影构成了世界自身的影像,影像书写揭示了世界的样貌。“一部出色的影片中,如同一切艺术品,其中总有某种敞开的东西。你每次探究其为何物时,总会看到那就是时间,是整体,就像它们以迥然不同的方式在影片中所表现出的那样。”[8]德勒兹所称的“时间”或“整体”便是世界本身。
参考文献:
[1][2][德]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电影的本性:物质现实的复原[M].邵牧君,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15,21.
[3]邵牧君.西方电影史概论[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15.
[4]王微.鲁道夫·爱因汉姆的媒介论与电影形式主张[ J ].电影评介,2021(15):59.
[5][法]安德烈·巴赞.电影是什么?[M].李浚帆,译.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9:107.
[6]马睿,吴迎君.电影符号学教程[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31.
[7][美]阿尔瓦·诺伊.奇特的工具:艺术与人性[M].窦旭霞,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20:51.
[8][法]吉尔·德勒兹.在哲学与艺术之间(全新修订版)[M].刘汉全,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