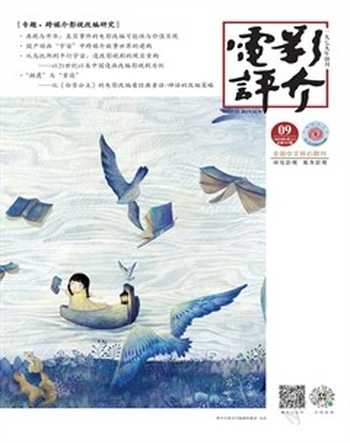再现与升华:真实事件的电影改编可能性与价值实现
马梅

近年來,不少由真实事件改编的影视剧,它们在事件发生之后甚至在事件尚未完结的时候就开始记录、再现事件,试图探寻事件的意义、凝聚共识、保存记忆,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反响。其中《亲爱的》(2014)、《湄公河行动》(2016)、《我不是药神》(2018)、《中国机长》(2019)、《中国医生》(2019)、《中国救援·绝境36天》(2021)、等几部口碑和票房较佳的电影都由真实事件改编而来,那么何种真实事件可能被改编电影,改编何以实现?
一、真实事件的电影改编的意义
在现实生活中,每天都发生着大大小小的事件,这些事件对于当事人往往具有一定的意义,其中一些突发性的意外事件、灾难事件甚至会对当事人的人生造成巨大的影响,比如使人生境遇发生反转、陷入绝境;当然也有的当事人因为在危机事件中的优秀表现而成为英雄模范人物;还有一些事件甚至具有全国意义、国际意义。但是,这些事件中的大多数事件对于他人和整个社会来说,其意义可能并没那么凸显,或者说与其相似的事件很多,不断有新事件发生,哪怕是对当事人造成重大影响的事件也在时间的流逝中成为旧事件,即便当事人没有遗忘,他人和社会也早已经遗忘。
如何对抗这种遗忘?哪些事件需要减慢其被遗忘的速度而尽可能留存在人们的记忆当中,以发挥其价值呢?哪些事件能够进入电影创作者的视野而被改编?跨媒介改编、呈现,包括电影改编是一种重要的方式。媒介记忆是人类一切记忆的核心与载体,媒介使得记忆突破了个人和集体的界限,既需要存储久远,也需要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中传承、转换和传播。[1]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社会记忆的保存与传播所依赖的主要媒介也不同,有用空间偏向的纪念柱、纪念碑、建筑等实物进行的空间传播,这种空间传播往往还和节庆纪念仪式结合;也有时间偏向、利用简便的符号系统进行记载、跨越时空的大众传播媒介。电影改编对于真实事件的呈现与传播而言,不仅再现了事件,也使真实事件的意义得以凸显并升华,使其在一定时间和代际内传播传承。
二、真实事件的电影改编可能性分析
真实事件和电影改编是一场“双向奔赴”,并彼此助力。从彰显真实事件的意义、对抗遗忘来说,电影改编给予真实事件的一次托举,而真实事件给予了电影改编鲜活的素材,实现了电影对现实生活的反映;从发挥电影的社会功能来说,真实事件是电影的源头活水。
首先,那些产生重要社会影响的突发灾难性事件较有可能被进行电影改编。2019年上映的《中国机长》是根据2018年5月14日四川航空3U8633航班机组成功处置险情的真实事件改编,机组执行航行任务时,在万米高空突遇驾驶舱风挡玻璃爆裂脱落、座舱释压的极端罕见险情,生死关头,机组人员临危不乱、果断应对、正确处置,确保了机上全部人员的生命安全,创造了世界民航史上的奇迹。电影集中呈现了“中国民航英雄机组”成员与119名乘客遭遇极端险情时的各种表现,表现了中国民航人在危机关头的职业精神和在危机关头的无畏互爱,谱写了一曲英雄之歌、中国精神之歌。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仅仅通过他们在飞机上处置危机的一系列操作来表现这种大写的精神,一方面情节会淡薄,叙事节奏也会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另一方面电影的观念表达可能会脸谱化、概念化,很难直抵人心。电影改编从真实事件本身往前延伸,通过飞行前机组成员及部分乘客的休闲时光、恋爱婚姻家庭状况、工作中的竞争与合作等情境,勾勒了众人出场的“底色”。这样的人生背景展现了不同年龄段、不同性格、不同生活状态的人们在生死关头的精神面貌、情感特点,从而让性格的表现和精神的书写更有厚度,更加可信。
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C.Wright Mills)曾言:“他要想知晓自己的生活机会,就必须搞清楚所有与自己境遇相同的个体的生活机会。”[2]当今世界是一个“风险社会”①,充满各种不确定性:一方面是罗萨(Hartmut Rosa)所说的科技加速、社会变迁加速、生活节奏加速[3],这种加速既可能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极大的便利,使社会物质生活资料极大丰裕,也可能让还不完全成熟的科技发明给社会带来危险。比如克隆人、机器人带来的伦理风险,比如汽车的普及和道路、人等要素之间的矛盾带来的交通事故风险及人身残疾等。可以说,自然具有的风险、技术引发的风险、制度引发的风险、政策或决定造成的风险以及个人造成的风险,[4]不知道哪一个会在哪一天发生在个体的身上。那么当这种风险突然成为现实时,个体应该如何应对?《中国机长》给予人们一种替代性的体验与学习,观众会将自己代入进去,不仅学习到了一些必要的知识,拥有了应对未知风险的安全感,也可能与剧中人产生共情,完成情感的升华和人生理念的确认与强化。当然,《中国机长》不仅仅给予人们应对风险、危机、灾难的知识和对于风险感受的共情,电影还通过对平凡的机组成员在危机时刻敢于担当、正确处置的种种叙事,完成了英雄机组的群像塑造。创作者也借此实现了以日常之善来克服“平庸之恶”进而达到为英雄的刻板印象祛魅的创作意图,并也可能获得广泛而持久的社会动员效果。[5]《中国机长》聚焦空难风险,《中国医生》聚焦新冠疫情这一全球性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中国救援·绝境36天》聚焦矿难救援事件,这些电影所展现的突发灾难、公共危机面前的凡人成长叙事等,可能产生动员的效果和对日常英雄主义绵延持久的唤起。
其次,那些扰动人们的生存和生活状态,引发伦理争议和社会争议的事件也较具电影改编价值。现实中,每个人都要经历生老病死、生儿育女、劳动学习,人生大多数时候是平静平淡的,也是安稳幸福的。但是有一天这种状态被打破了,疾病、孩子丢失,改变了家庭生活的常态,造成了家庭的经济困难和情感重创,可能引发社会对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社会治理、社会安全等基本民生问题和社会根本问题的热切关注。
电影《我不是药神》由白血病患者行走在现有法律边缘,求药求生的真实故事改编。电影真实地呈现了社会对于重症看病难、看病贵、“非法药”和“假药”、非法代购、医疗卫生政策、社保政策、情与法、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等问题的广泛讨论,最终推动相关部门修改了关于假药认定的法条。
除了以上这类真实事件外,还有一些涉及国内国际经济社会发展的大事要事也常常被改编为电影,如电影《湄公河行动》是对中国商船在东南亚地区湄公河金三角流域遇袭,船上13名中国船员全部遇难的“湄公河惨案”这一真实事件进行的电影化呈现。
三、精妙的电影改编助力真实事件的价值实现
电影改编可以让真实事件的社会意义得以充分彰显,让事件蕴含的社会议题得到更加广泛的关注,甚至可以让相关问题得到解决。而这一切的实现无疑得益于精妙的电影改编,是电影改编在内容和形式诸多方面的创新叙事、艺术传达、意蕴升华,让真实事件从自然的物质界成长为精神世界的精华,成为深刻影响人们心灵的艺术精品。
首先,真实事件的电影改编往往高扬现实主义的创作美学,聚焦“人”的境遇与情感,表达深沉的人文关怀,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宗旨。在现实生活中,对于《我不是药神》代购“假药”的真实事件,人们往往是从法律的角度来看问题,只是把它当成一个时间流程的“事”,公事公办,事情处理了就结束了。而电影改编则聚焦其中的“人”,在内容上抽丝剥茧,呈现了人在事件中的种种境遇、喜怒哀乐、命运沉浮;呈现了人在事件前后的发展变化,在对比、流变中凸显了“事”对人的身心伤害,对其家人和周围环境的影响,从而让一个真实事件不仅有了客观的事态信息,还有了丰富的情感信息、思想观念信息,引发了人们深沉的思考。
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10月15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论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时指出:“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6]当前由真实事件改编而来的优秀电影作品,能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的冷暖、人民的幸福放在心中,把人民的喜怒哀乐倾注在自己的笔端,讴歌奋斗人生,刻画最美人物,坚定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信心。《中国机长》《中国医生》塑造了从灾难事件中站出来的、成长起来的凡人英雄,表现了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从问题角度切入的电影,如《我不是药神》《亲爱的》,也都努力从矛盾当中具体的人的视角出发,塑造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内心冲突和挣扎的人,按照现实本身的发展逻辑寻找出路,推动问题解决,展现人民群众的精神风貌。
其次,电影改编充分运用典型化的创作手法,使真实事件的戏剧冲突更加明显,情节更加丰富曲折,人物形象更加饱满,从而产生较大的艺术张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艺创作是观念和手段相结合、内容和形式相融合的深度创新,是各种艺术要素和技术要素的集成,是胸怀和创意的对接。”[7]从真实事件到传得开、影响大、深受人民喜爱的电影,是一个巨大的飞跃,这个飞跃是从简单的事件的口语叙述或文字记录,变成一个情节曲折、细节丰富、将事态情态意态信息融为一炉的艺术品。当然,有些真实事件已经由媒体进行了一定的报道,或者是简要的消息,或者是情节较为丰富的通讯、报告文学;有的可能已经有电视媒体运用电视新闻、电视纪录片等对其进行了呈现。但是这些媒介呈现和媒介叙事仍然是纪实性的,往往会因为新闻纪实作品对于时效性和真实性的至高追求,而不能够进行某些取舍、夸张、嫁接、集中、改变。在改编时,电影作品遵循的是艺术创作规律,多采用典型化的创作手法,其可以把社会上相近、相关、相似的多个人的故事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使主人公的经历更加丰富,从而更容易唤起观众的情感和思想反应。
电影《亲爱的》将多个丢失孩子的家庭寻子故事及其中的不同的悲情较多地集中在男女主人公身上,并且将男女主人公和孩子的关系设置成夫妻不和、孩子是唯一的纽带的情况,凸显了孩子重要性。那么在孩子丢失,纽带断裂的情况下,便会爆发出巨大的冲突、其中的悲怆就会更加浓烈,生活中的不和谐因素便会不断推动情节的曲折变化。而作为收养孩子的养母,电影呈现了乡村妇女的贫穷坚韧、善良泼辣,将不孕不育、夫权压迫、性别不平等相结合造成的对孩子的渴望、想要留下孩子的疯狂愚昧都加诸于她身上,更将其放置在充满集体暴力,试图留下不属于他们的孩子的村庄宗法制的背景下,这一切更凸显了其命运的悲怆,凸显了贩卖人口问题的复杂性和解决问题的难度之大。这种人物塑造手法和情节设置,加大了电影的艺术张力,令人无法释怀,而且也能够让不同经历、文化、思想基础的观众各取所需,在自己既有的认知结构中来认识电影,获得与自己相匹配的艺术满足。电影《我不是药神》则通过对真实事件中的人物和故事进行反向改编,实现精神升华来凸显“转变”。例如,真实事件中的主人公帮助他人购药并不收取任何费用,其利他精神在量的计量上可能是以0为起点逐渐攀升的;而电影主人公一开始是收取一定费用来为他人代购的,也不是全然无私的,其利他精神在计量上可能是从负数开始往上攀升的,是受到某些感召才转变成全然的利他,這里有一个反转,其前后行为和品格有一个较为强大的对比、转变,使剧情更加曲折,艺术张力更大,也更吸引人。
再次,电影改编运用了丰富精妙的视听语言,使真实事件更具艺术灵韵,也使创作者的创作意图得到贯彻,从而充分彰显其社会作用。真实事件被用口语或文字转述给观众时,语言文字符号的抽象性使得事件本身情节过程的具体情况损失不少。真实事件本身的来龙去脉只有当事人清楚,当事人也往往因其所处的角色和关系的位置固定,其局内人和剧中人的限定身份使得他可能只知道自己视角之内的东西。电影改编则不同,摄影机使观众能够体验所有剧中人的感受。匈牙利电影理论家巴拉兹·贝拉(Béla Balázs)指出摄影机“不可避免的主观性”,“每一个影像都有一个视觉角度,每一个视觉角度都是某种关系,而且不仅仅是空间关系。每一次对世界的再现都包含着一种世界观。因此,每一个场面调度,每一个摄影机取景角度都意味着人内心的一种改变、一种调整。即没有比客观更主观的东西了。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固定在每个影像上的印象都变得极富表现力了。”[8]电影的这种用客观来表现主观的方式,极为巧妙。他还说:“导演无需论证自己的观点,他以简单的光学效果让人们接受了他的观点。”[9]当前,电影改编还可以运用多种摄影技巧,例如蒙太奇、特技、调色等技术手段来巧妙表达创作意图,可以说,电影充分运用艺术技巧、符号实现了观点的传达;而在呈现真实事件的新闻作品中,由于对真实的现实的追求,记者和编辑往往只能客观地记录和呈现现实,这导致其艺术感染力有限,对现实的干预作用也受到了限制。
德裔美籍电影理论家鲁道夫·阿恩海姆(Rudolf Arnheim)认为“技术构成艺术的实现条件,而艺术则体现技术的运用价值。”[10]技术与艺术是共生关系,不同技术给予了创作不同的基础和可能性,这就是“技术可供性”意涵的一部分,用好了技术手段,将能够助力艺术表达,使作品的灵韵、美感、詩意得到充分彰显。在对真实事件的电影改编时,创作者利用各种运镜、构图、光线、声画组合、蒙太奇等艺术技巧,使得真实事件的过程、细节能够被重组、放大,使现实时间被拉长、或缩短、或重叠并置、或倒错交叉而成为光怪陆离的电影世界,产生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的跃升效果。电影中的演员表演,如上述真实事件的电影改编,大量优秀演员的倾情表演,进一步提升了作品的美学意义,其社会作用也从审美接受中连带发生,这就是潜移默化。正如伊芙特·皮洛(Yvette Biro)所说,“身姿手势的生动性,它与原有情节的内在联系,也意味着氛围和情调是信息的天然伴侣;它们不是从外部附加在信息上的,它们可以焕发出事件的情感内容和内在实质”,“形体动作,不论多么自然化,多么依附于躯体动作,它的抽象化作用绝不会低于最富分析性的描述,甚至充满象征的诗”。[11]
结语
当下不断推陈出新的信息传播技术和艺术表现手段,使得电影的造梦本领更加强大。电影如果能真正实现观念和手段的结合、内容和形式相融合的深度创新,集成各种艺术要素和技术要素,实现胸怀和创意的对接,就必然能更好地反映现实、引导现实、影响人的思想和灵魂,进一步发挥其强大的社会作用。
参考文献:
[1]邵鹏.论媒介记忆活跃与凝固的尺度与张力[ J ].新闻爱好者,2015:32-37.
[2][美]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M].李康,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5.
[3][德]哈特穆特·罗萨.新异化的诞生:加速社会批评理论大纲[M].郑作彧,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5-7.
[4]杨雪冬.风险社会与秩序重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16-20.
[5]战迪,邓慧敏.当下中国电视剧叙事中日常英雄主义的阐释向度[ J ].文艺争鸣,2021:192-193.
[6][7]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2015-10-14)[2023-01-22].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0/14/c_1116825558.htm.
[8][9][匈]巴拉兹·贝拉.可见的人:电影文化、电影精神[M].安利,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157-158,160.
[10][德]鲁道夫·阿恩海姆.电影作为艺术[M].邵牧君,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7:227.
[11][匈]伊芙特·皮洛.世俗神话——电影的野性思维[M].崔君衍,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3:44-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