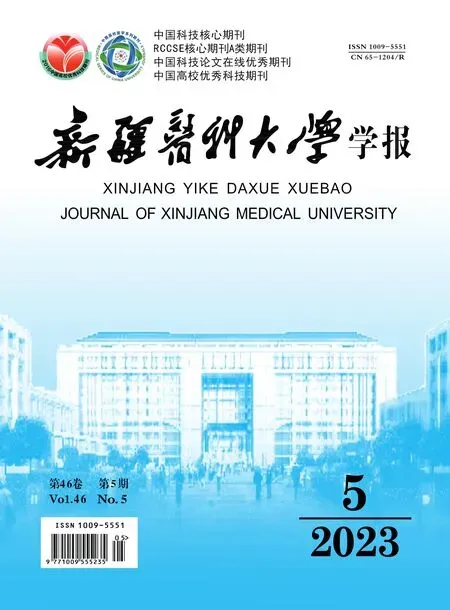牙龈卟啉单胞菌与常见消化系统恶性肿瘤相关性的研究现状
龚忠诚, 买热拍提·买明, 李晨曦, 热孜万姑丽·亚森
(1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附属口腔医院) 颌面肿瘤外科, 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口腔医学研究所, 乌鲁木齐 830054)
1 牙龈卟啉单胞菌的主要特征
慢性感染是癌症发展中重要的流行病学决定因素,近20%的人类恶性肿瘤与感染因子有关[1]。牙龈卟啉单胞菌(Porphyromonasgingivalis,P.gingivalis)的致病因素多样,包括其自身结构成分,如脂多糖(Lipopolysaccharide,LPS)、菌毛、热休克蛋白(Heat shock protein,HSP)和分泌成分,如牙龈素(gingipains)和外膜囊泡,它们刺激相邻上皮细胞产生各种细胞因子[2],包括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s,ILs)和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alpha,TNF-α),从而促进肿瘤微环境(Tumor microenvironment,TME)中的炎症反应[3]。P.gingivalis同时是一种兼性胞内细菌,能入侵多种宿主细胞,包括牙龈上皮细胞、内皮细胞、血管平滑肌细胞、树突状细胞和神经元[4]。研究证实P.gingivalis涉及多种系统性疾病[5],如心血管疾病、神经系统疾病、自身免疫病、呼吸系统疾病、代谢性疾病、不良妊娠等。
P.gingivalis生长所需的代谢能来自蛋白质分解产物、血红素和维生素K。P.gingivalis产生的牙龈素和肽基精氨酸脱亚胺酶(Peptidyl deaminase,PAD)成为其发病机制中的重要因素。牙龈素会导致局部组织破坏,扰乱宿主的抗菌防御,导致口腔和肠道内共生细菌过度生长及播散。菌群失调导致有毒代谢物的增加,这促进了与心血管疾病和自身免疫相关的代谢紊乱[2]。
囊泡是细胞膜的一部分,大小为50~300 nm,形成于A-LPS和具有C-末端结构域(CTD)的蛋白质(如牙龈素、PAD或血红素结合蛋白35)组成的双层膜结构[6]。菌毛促使细菌黏附宿主细胞、与外基质分子、细胞因子和纤维蛋白原、CD14、β2整合素、TLR(toll样受体)2、4结合[2]。这些相互作用使促炎因子合成,如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MCP-1)、TNF-α、IL-1β、IL-6、IL-8等,并诱导多细胞间黏附分子-1(ICAM-1)、血管细胞黏附分子-1(VCAM-1)、P-选择素(P-selectin)、E-选择素(E-selectin)、CD40、CD80和CD86的表达[7]。其中IL-8能够启动可结合血红蛋白的受体(HbR),以捕获卟啉环和血红素,从而获得P.gingivalis生长所需的铁[2]。它的LPS结合高度敏感的模式识别受体(Pattern recognition receptors,PRR)如TLR后[8],通过转录因子-核因子-κB (NF-κB)依赖性TNF-α的产生,激发涉及胞外调节蛋白激酶(Extracellular regulated protein kinases,ERK)的炎症,激活p38和c-Jun氨基末端激酶(c-Jun N-terminal kinase,JNK)以及上调纤溶酶原激活物抑制剂(PAI)-1的表达[9],故LPS对细胞串扰的作用对P.gingivalis的毒力至关重要。P.gingivalis与牙周来源致病菌能够侵入上皮和结缔组织,后进入血液导致菌血症[10]。
2 P.gingivalis与消化系统恶性肿瘤
2.1P.gingivalis与口腔鳞状细胞癌口腔鳞状细胞癌(Or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OSCC)TME中多样化的微生物组成分与癌前组织并不相同,P.gingivalis等牙周病原体与癌变关系密切,P.gingivalis感染增加OSCC患者的死亡风险[11]。它能够入侵肿瘤细胞,并在胞质中繁殖,周围的正常细胞亦可受其影响。研究表明,P.gingivalis作为慢性牙周炎(Periodontitis,PD)和侵袭性牙周炎(Aggressive periodontitis)的优势菌,促进OSCC的发生发展[12]。目前普遍被学者接受的4个机制如下:(1)P.gingivalis诱导上皮-间质转化(Epithelial-mesenchymal-transition,EMT):在EMT过程中,上皮细胞失去本身的特性,获得间充质干细胞自我更新特性以及肿瘤细胞的迁移和侵袭特点[3],此过程存在于多种上皮细胞来源的肿瘤中。EMT由一组转录因子控制,包括锌指蛋白1/2(Zinc finger E-box binding homeobox 1/2,ZEB1/ZEB2)、SNAIL转录因子、TWIST转录因子和Slug转录因子等。P.gingivalis上调ZEB1/ZEB2水平[13],其中ZEB1与间充质细胞标志物基质金属蛋白酶(Matrix metalloproteinase,MMP)-9和波形蛋白(Vimentin)增加有关。P.gingivalis还参与磷酸化GSK3-β通路来调节EMT的发生[5,13]。(2)P.gingivalis抑制细胞凋亡,促进肿瘤细胞增殖:被P.gingivalis感染的上皮呈现出与癌变密切相关的抗凋亡特性。细菌LPS与宿主细胞表面的TLR-4受体结合,从而激活NF-κB蛋白复合物。NF-κB调节细胞基因转录,炎性环境引发NF-κB失控[9],该复合物随后进入细胞核,激活细胞因子基因的转录,如IL-6基因。IL-6过度刺激JAK1/STAT3信号通路进而抑制细胞凋亡,同时参与线粒体凋亡、细胞的分化、迁移和增殖[13]。P.gingivalis可上调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的表达,诱导肿瘤血管形成[14]。细胞因子信号转导抑制因子(Cytokine signal transduction inhibitors,SOCS)3属于SOCS家族蛋白,是miRNA-203的靶点[7],它的过表达通过JAK/STAT3等途径降低细胞增殖、诱导细胞凋亡和部分G0/G1阻滞[14]。研究提示P.gingivalis感染的人牙龈上皮细胞(Human gingival epithelial cell,GEC)中miRNA-203水平升高,SOCS3和SOCS6水平降低[14]。核苷二磷酸激酶(Nucleoside diphosphate kinase,NDk)是一种广泛存在于真核和原核结构域的酶。它在核苷酸代谢中必不可少,催化磷酸从NTP(核苷三磷酸)转移到NDP(核苷二磷酸)的过程。P.gingivalisNDks不仅可以通过磷酸化Hsp27的丝氨酸残基诱导细胞凋亡[8,14],而且能抑制嘌呤能受体(P2X7)的ATP活化,减少上皮中IL-1β的产生[8]。IL-1β则是启动γ干扰素(Interferon-γ,IFN-γ)的关键因子,IFN-γ可产生肿瘤抗原特异性CD8+T细胞,此过程使肿瘤逃避免疫监测[7-8]。(3)P.gingivalis促进肿瘤细胞侵袭和转移:P.gingivalis感染后MMP-1和MMP-2以及proMMP-9的水平明显上调,其机制可能是通过ERK1/2-Ets1、p38/HSP27和PAR2/NF-κB通路诱导pro-MMP-9表达,而牙龈素将其转化为MMP-9,导致IL-8依赖性MMP升高,OSCC细胞株的侵袭力增强[14]。P.gingivalis还可以通过参与巨噬细胞极化来促进OSCC的发展,P.gingivalis的LPS激活的巨噬细胞条件培养基促进II-IV期肿瘤的原发和转移性头颈部鳞状细胞癌(Head and neck squamous cell cancer,HNSCC)细胞系的侵袭[15]。P.gingivalis抑制巨噬细胞吞噬SCC细胞株(Cal-27),诱导巨噬细胞功能极化成M2型肿瘤相关巨噬细胞(Tumor-associated macrophages,TAMs),上调TAMs和Cal-27细胞中肿瘤分子编码基因的表达,从而引发OSCC的免疫逃避[16]。(4)P.gingivalis形成有利于TME的炎性环境:慢性炎症能够促进肿瘤的发生发展。巨噬细胞作为非特异性免疫中的主要细胞,它们随循环系统迁移到身体的大部分组织器官中,诱导IL-1β、IL-6、TNF-α和其他促炎因子的合成和释放[4]。这些因子抑制细胞凋亡,进一步扰乱细胞周期,为OSCC创造有利条件。NF-κB的激活同样是细菌引起炎症的主要因素之一,LPS结合TLR4后通过NF-κB信号通路诱导炎症相关细胞因子的产生[11]。此外,P.gingivalis的免疫表达可能与C-X-C基序趋化因子配体2(CXCL2)和肿瘤相关中性粒细胞(Tumor associated neutrophils,TANs)呈正相关,三者与OSCC患者的不良预后有关[11]。P.gingivalis的促炎作用与促肿瘤作用相互交叉。
2.2P.gingivalis与食管鳞状细胞癌Gao等[17]对P.gingivalis在食管鳞状细胞癌(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ESCC)中的重要作用进行了研究,结果提示P.gingivalis可作为监测食管癌发生发展的重要生物标志物。他们从100名患者身上采集的61%的癌组织样本中检测到P.gingivalis。P.gingivalis感染是ESCC的一个危险因素。P.gingivalis感染亦与肿瘤的淋巴结转移和生存时间减少有关[18]。然而,在食管肿瘤微环境中,P.gingivalis是否是一种明确的致病因子或癌变组织中的微环境仅仅有利于它的定植,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P.gingivalis在ESCC发生发展中的作用机制与口腔癌有相似之处,亦通过促进EMT、干扰宿主细胞周期、促进肿瘤细胞的侵袭与迁移来实现。果蝇头状因子-3(Grainyhead-like3,GRHL3)是一种转录因子,参与伤口愈合、血管生成、上皮迁移、表皮分化和屏障形成。研究表明,与未感染的食管癌细胞相比,P.gingivalis感染的ESCC细胞系中GRHL3(miR-194的直接靶点)和抑癌基因PTEN(Phosphatase and tensin)的水平降低,p-Akt及miR-194水平上调,而miR-194的抑制或过度表达对食管癌细胞株(KYSE-30和KYSE-150)的迁移和侵袭有显著影响[18]。综上,P.gingivalis通过miR194/GRHL3/PTEN/Akt信号轴促进ESCC增殖和迁移。研究发现P.gingivalis在食道TME中通过触发NF-κB信号通路,促进ESCC细胞的增殖和转移[19]。Beclin1是自噬的关键调节因子,由Becn1基因编码, Beclin1在肿瘤发生中起着重要作用,P.gingivalis感染和Beclin1下调增强ESCC细胞(KYSE150和KYSE30)的增殖、迁移和抗凋亡能力[20]。研究表明P.gingivalis的细胞内侵袭通过转化生长因子-β(TGF-β)依赖性转录因子(Smads)/Yes相关蛋白(YAP)/具有PDZ结合基序的转录辅激活子(TAZ)增强ESCC细胞的增殖、迁移、侵袭和转移能力[21]。Smads/YAP/TAZ/TEA结构域转录因子1(TEAD1)复合物的形成对于启动下游靶基因、诱导EMT至关重要。此外,P.gingivalis还能通过跨膜蛋白GARP上调增加TGF-β的分泌和生物活性。
2.3P.gingivalis与胰腺癌胰腺癌(Pancreatic cancer)的预后极差,5年生存率仅为10%左右[22],其中胰腺导管腺癌(Pancreatic ductal adenocarcinoma,PDAC)是最常见的胰腺恶性肿瘤类型,其转移风险高,约占所有胰腺癌病例的90%[23]。口腔中的P.gingivalis感染及牙周病增加了胰腺癌发生的风险。P.gingivalis引起的TLR激活可以刺激胰腺,并显著加速小鼠胰腺癌的发生[24]。一项体外动物实验结果提示P.gingivalis促进胰腺导管细胞中TGF-β信号通路的激活[25]。有证据表明,TGF-β及其下游信号分子在胰腺癌发生中起关键作用[26]。TGF-α信号通路可能参与益生菌对PDAC进展的抑制作用。口腔中接种P.gingivalis可加速胰腺上皮内瘤变(PanIN)的发展,益生菌可能通过降低癌细胞增殖,抑制PanIN进展和EMT的发生[25]。在胰腺TME中,P.gingivalis可招募TANs,并增加CXC和中性粒细胞弹性蛋白酶(Neutrophil elastase,NE)的释放,产生促炎性微环境,有助于胰腺肿瘤的进展[27]。P.gingivalis等相关菌群感染通过miR-21水平升高和PTEN水平降低来促进胰腺癌细胞转移和化疗耐药[28]。可见,P.gingivalis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是胰腺癌发生和发展的一个生物标志物。
2.4P.gingivalis与其他消化道肿瘤尚无证据表明肝癌与P.gingivalis的直接关系,但相关研究表明P.gingivalis参与非酒精性脂肪肝(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NAFLD)、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on-alcoholic steatohepatitis,NASH)及肝纤维化等疾病的发生发展[29-30]。使用高脂肪饮食(HFD)诱导的NASH小鼠模型,P.gingivalis感染后加重了肝脏炎症和纤维化。P.gingivalis和LPS刺激可诱导造血干细胞和肝细胞产生TGF-β1和半乳糖凝集素-3(Gal-3),它们在肝纤维化的进展中发挥重要作用。P.gingivalis的亮氨酸-异亮氨酸-缬氨酸(Leucine-isoleucine-valine,LIV)系统可能通过诱导支链氨基酸水平的增加而加重NAFLD和NASH。P.gingivalis和放线菌也有助于肝硬化患者胰腺癌的发生[31]。
口腔病原体与胃癌(Gastric cancer,GC)前病变之间尚无明确联系。有研究显示在高P.gingivalis检出的个体中,牙周病原体与胃癌前病变的风险相关性增加,口腔内的有菌环境以及牙周病原体可能与胃癌前病变发生有关联[32]。目前仅有研究表明PD病原菌中的具核梭杆菌(Fusobacterium nucleatum,F.nucleatum)和胃癌有关联[33],尚无证据表明单独P.gingivalis与GC的发展有关。消化道肿瘤患者的口腔微生物群显示出更高的细菌多样性,如P.gingivalis、龈下福赛斯坦纳菌(Tannerella forsythia,T.forsythia)、齿垢密螺旋体(Treponema denticola,T.denticola)和伴放线聚集杆菌(Aggregatibacter actinomycetemcomitans,Aa)[34]。
结肠黏膜属于厌氧环境,pH值高,有利于P.gingivalis黏附,继而通过促进微环境中炎症因子的释放,最终促进结肠癌的发生。此外,结肠菌群受口腔细菌的影响,特别是长期持续感染P.gingivalis引起肠道菌群失调。除P.gingivalis外,其他牙周病原体包括放线菌,也可以播散至结肠,口腔与结肠的这种连接关系是口腔细菌介导全身炎症反应的另一种途径[10]。Lin等[35]通过实验证明P.gingivalis的GroEL蛋白能够通过增强内皮细胞的功能以及血管生成加速肿瘤生长,并降低小鼠模型的生存率。还有一项研究[36]显示C57BL/6N小鼠持续5周感染P.gingivalis,可导致内毒素血症,降低回肠紧密连接蛋白(Zonula Occludens-1,ZO-1)基因的表达水平。P.gingivalis在结直肠癌发生发展中的作用机制仍需深入研究。
3 启发
P.gingivalis是牙周炎的主要病原体,可直接或间接地引起全身其他脏器的各种损害。在肿瘤方面,首先,口腔牙菌斑中筛查P.gingivalis可以初步筛查易感人群,有助于癌症的预防和早期诊断;其次,改善口腔卫生在一定程度上可降低癌症发病的风险。联合使用抗P.gingivalis疗法和手术、放疗或化疗,新辅助治疗是阻断P.gingivalis促进消化系统肿瘤的方法。深入研究P.gingivalis在恶性肿瘤中的作用,有助于指导个体化治疗,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WHO在2007年提出应鼓励促进口腔健康,将其作为健康生活方式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减少P.gingivalis的负荷被认为是可变因素,牙周治疗对预防OSCC有直接或间接的积极影响,在抗菌药物的使用方面仍需要进一步探索。对于食管癌,目前常用的血清标记对ESCC的早期检测和进展没有足够的敏感性和特异性。ESCC患者唾液中唾液链球菌和P.gingivalis的表达显著增加,这些细菌结合考虑到年龄、性别、吸烟、酒精摄入和过热饮食偏好时,对ESCC有较高的预测价值[37]。进一步研究P.gingivalis对胰腺癌的作用机制,有助于降低胰腺癌的死亡率。对P.gingivalis的致病机理进行阻断有望预防疾病、减弱其影响和改善预后。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作者贡献声明 买热拍提·买明:起草文章;热孜万姑丽·亚森:文献检索,收集及整理;李晨曦:分析并解释相关内容,文章修回、审阅;龚忠诚:研究设计,监督指导,文章审阅,获取研究经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