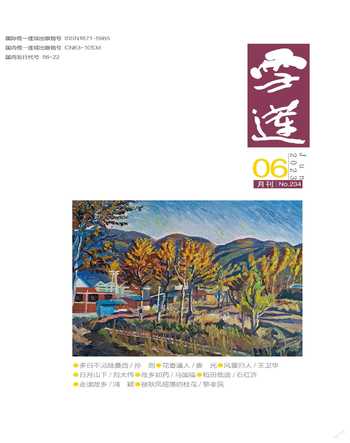火车即将载我前行
我们的火车,在下午三点准时到达曲丹。当我们从四川出发,我曾对此行充满无尽的担忧。那时候无论是网络媒体,还是电视上,人们听到最频繁的词,就是“春运”。这么些年,我一直呆在四川,每一年都巧妙地避开春运,好像那是一场洪流,而本身我是不会水性的懦弱者。但这次,我想,我没有选择的余地。
我所定义的异乡,并非在四川的城市之间穿行。当我长到三十岁后,越来越对目前逼窄的人生感到不满。我时常会怀着忧伤的情绪想念四川以外的地方,虽然我并未涉足那些地方,但我知道,在我国许多地方,一定有高山大海、幽谷松林,还有小桥古镇……
现在是弥补人生遗憾的时候了,但我来不及准备。我需要三五天,或者更长的假期,这个压根说不准。我站在领导办公室,难为情地将请假理由合盘托出——我是个不愿意撒谎的人,即便这也许算是家庭丑闻。
火车在傍晚出发。我们四个人提前一个小时在候车大厅汇合。天已经很冷了,天气预报说明天开始,会有大雪降临。对于我来说,雪是新鲜的东西,已经有十来年没有见过它的真面目了。
在候车大厅,戴秀珍左手里攥了五百元钱,右手将弟弟的手臂紧紧抓住。她的丈夫郑建国,蹲在地上,手指夹着未点燃的烟。
“这个怎么能由你出呢?”弟弟想挣脱戴秀珍的手,努力挣扎向相反的方向迈步。
“许多事还要麻烦你们兄弟俩,再说,郑勇和你们家宋乔也正在处朋友。”戴秀珍并不放手。
“那我们就更不能要了,”我努力挤出笑容,站在他们之间,“从小,爸爸就教育我们,要堂堂正正,不占人便宜。”我想年长的一代,是最讲究家规的,所以,这样的拒绝,应该可以起到效果。
郑建国从地上站了起来,我以为他要说点什么,但他只是斜斜地站着。在戴秀珍身侧,他矮小的身材,显得弱了许多。
我们终究没能成功拒绝掉戴秀珍的好意,收下了那笔旅费。在我点头示意后,弟弟用手揉搓了几次刚做完手术、还未痊愈的鼻子,然后将钱接了过来。我想这样做,对于这对年老的夫妇是莫大的安心。在此之前,我们从未谋面,在候车大厅,他们提着大大的白色塑料袋,紧紧跟在我们后面。
外面下了些雨,当我们站在拥挤的大厅看进站口时刻表时,我侧身看了他们几眼,他们头发已经花白,上面沾着未散尽的水珠。在他们的眼睛里,我看到了未知和惶恐。其实他们并不知道,四个人当中,现在最能倚仗的,是弟弟。而我,也像他们一样,在这之前,从未踏出四川半步。
“别说四川,就是府城,我们也并不常常去的。”当我们终于坐进火车,放好行李后,戴秀珍说出了他们的窘迫。郑建国依旧沉默着。
火车开始向大山深处爬去,车轮摩擦铁轨发出踢嗒踢嗒声。这让我想起马修·连恩那首辽远忧伤又舒缓的《布列瑟农》,在歌曲的结尾,有长串车轮碾过铁轨发出的声音,我一直认为,那是旅行者期盼能听到的最浪漫的声音之一。在那声音背后,你能想象,旅人紧紧靠在敞开的车窗前,瞭望远方,那窗棂上,兴许还有未尽的夕阳。
现实是,我的记忆有些落伍了。多年前我坐过的绿皮火车,那时的车窗是可以打开的。推开小小的窗,满眼是无尽的旷野。多年后,当我再次坐上火车,宽大的玻璃窗牢牢地封闭着,至于旷野,应该是有的,但当我想起应该欣赏窗外的风景时,迎接我的,是夜幕下旷野上偶尔隆起的小山坡。借助那些山坡,你才得以知道,火车正在夜里穿行。
过道上,售货员又过去一遭。我们开始笑郑建国,此刻他身前的桌上,已经摆了喝完一半的小酒。他举起酒瓶,向我们示意,我们摇头,惊讶地看着他,周围人也是一样。在火车上就着零食饮一瓶小酒,大概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但人们的眼光,明显认为那是比在过道上抽烟还令人厌恶的事。更何况,同我们一样,等待他们夫妇的,是一场没有眉目的灾难。
世上总有这样的人,无论陷入怎样的窘境,总能从容应对。我和弟弟感叹,也许拥有这样特质的人,要好过我们这些匆匆忙忙生活的人。上天不会因为你心急火燎而让问题提前得到解决,这是我们得出的结论。一路上,我们刻意避免聊到郑勇和我妹妹宋乔。我们和邻座的人有简单的聊天,只说是去曲丹办事,我们尽量装出闲适的表情,不让人家以为同身处漩涡的两家人同乘一车。
火车再次拐进长长的隧道,随后停了下来。人们说到了列车长休息的时候了。这列火车开得不快,甚至有些慢吞吞的。当我们开始出发,看着窗外缓慢后退的树时,我便担心,无法按时到达曲丹。
弟弟一路上留意着微信群消息的更新。文字啊,语音啊,这一天,这个临时组建的群已经堆满了未读信息。陌生的面孔,用急切又陌生的文字、声调在群里公布事件的进展。
“所有人都被带走了,不是府城警方。是跨省缉拿。”
“问题不大,只是协助调查。”
“我们带了律师过去,在正式审问前,应该有律师介入,教他们怎样回答审问。”
看完这些纷繁的消息,我疲倦地笑着,弟弟则努力睁大眼睛继续翻看那些如垃圾般堆积的消息。
“都是些煞有介事的人。”我感叹。
“我们该怎么办?”弟弟指的是我们原本該像其他人一样,带一位律师在身边。我对他苦笑。出发时,我取走了家里仅有的两千元存款,而他,也取走了仅剩的一千元。律师,对我们这个拥有三个孩子、七个成人的家庭来说,简直就像是一种奢侈的概念。如同上海外滩的那些房子、4S店里那些名贵的车子、电视上那些身材绝妙、面容绝美的女明星。
“我们只能尽己所能。你忘了我们此行的目的?”我的回答也许让弟弟失望。这个家庭多年前就分散到两个不同的城市,就像解体了一样。父亲母亲和弟弟一家在府城生活,而我新组建的家庭,在嘉城。两个城市的车程,不过两个小时而已,但连接我们的,只是思念。我们怀揣梦想,离开故乡多年,当初的离散,是为了将来的永聚。这是我当初最大的理想,但二十年过去了,我们在各自的城市,艰难又顽强地活着,离永聚越来越远似的。
“是的,给她送去御寒的衣物,再有两百元钱。电话上说,其他什么都不需要。如果能见她一面,是最好的。”弟弟无奈而伤感。他的脸很瘦,颧骨高高耸起,这是少年就开始漂泊的人通常有的脸型。
这让我想起了宋乔的过去。
五岁前,我尽过做大哥的责任。在老家的门前,将她的手丢开,教她走路;在她上初中的时候,我去看她,将拳头奉献给那些欺负她的镇上的小流氓。后来,我远离家乡,读了大学,我们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少。在她初中快毕业时,我接到她的求助信,说家里因为供我们兄妹三人,已经拮据到不行。她想我是否能资助她一些钱,好治好身上的恶疮,还有难以忍受的胃病。那时候我曾发过誓,说终有一天,会让她有很好的工作和生活,作为大哥,我会竭尽所能,帮助矮小懦弱的她。有一次去学校看她,离开时看她提着水瓶,瞬间就淹没在人海。后来,每当想到这样的场景,就在心里升起无限的同情和愧疚。我有不好的预感,在将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她不会有更好的生活。更多的挫折在等着她。
但谁能想到,几天前,她和我们失去了联系。是那种给人绝望的消失,彻彻底底,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应该叫“失联”。
在曲丹下了火车,我们重新打开那封从刑警大队寄来的信,按照信上的说明,我们距离宋乔所在的地方,还有两个小时的车程。曲丹的一切并不让我感到新鲜。多年前我所期盼的异乡之行,潦草到不行。当我们提着笨重的行李从车站出来,走过那些街道时,才发现,如果你去旅行,执意要去看每个城市的街道,那无疑是会失望的。你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这片土地上,人们对于城市的审美观点出奇的一致:火车站外的小吃店啦,擦鞋店啦,公交车站啦,问你去哪儿的黑车司机啦,努力说服你去住店的小旅馆老板啦,市中心的步行街啦……这里的一切设计,包括对生活方式的设计,都那样相似,它无法带给你任何新鲜感。
弟弟倒是发现了唯一的不同,“口音好难听”,当我们坐上去沙县的班车后,他咧着嘴向我们透露他的发现。郑建国终于露出笑容,他蜷曲着坐在戴秀珍旁边,就像她的孩子。
在沙县下了车,我们雇了一辆出租车。十分钟后,我让司机掉转车头,去市中心药店买了软膏和两袋棉签。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有一周的时间没有见过宋乔了,这时我才想到,在看守所里,现在最令她难受的,一定是困扰多年的恶疮。此时的沙县,夜幕降临,吹着比四川更萧瑟的风,行道树的叶子上,覆盖着厚厚的黄沙。我想象宋乔屈膝坐在冰冷的床沿,满目沮丧,不断地抓着通红的皮肤,那该是怎样难过的每分每秒。
“你们宋乔和我们郑勇谈了几年恋爱了,嘴里总是宋乔宋乔地念着,我们让他去开车,做人家司机,但他说要和宋乔在一起,去做手机营销。哪儿想到……”我们重新上了车,司机掉转车头,大概沙县的景象,让戴秀珍与我有了同样的心情。
“哪儿想到会这样呢?只是告诉我们电话营销,哪儿想到突然就失去了联系。整晚没有两个人的消息,全家人到处找。”弟弟慨叹着聊起当天全家人在府城寻找妹妹的场景。
“最后是查了大楼的监控,才知道被人带走了,妹妹被人抓着手臂,看样子很害怕,我们以为是被绑架了,连府城的警方也不知道消息。”
“最难的是,现在曲丹已经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定性为特大电信诈骗案。”我摸出手机,将网页打开给他们看。
“跨省抓捕,又召开了发布会。”弟弟将已经开始掉皮的皮衣向胸口拉了拉。我们走得匆忙,为了尽可能往行李里多装点妹妹的衣物,我们放弃了为自己多带衣物的想法。
现在,我们再也不用担心在陌生人面前聊起这桩令我们心烦意乱的“丑闻”了,因为我们已经在去往沙县看守所的路上了。这里的司机想必对这群行李沉重的旅客已经了若指掌。不用问,他知道我们陷入了某种麻烦。
我们终于站在了看守所的院子里。在我们正前方,挨着办公楼的,是两道高高的铁门。如果不推开那两扇铁门,你无法窥探到任何的景象。这就是现在困住妹妹的地方,在两扇铁门之间,隔着我们不同的人生。有的人,一辈子都不会看到这样坚固又高大的铁门,而有些人,糊糊涂涂地就被人抓着手臂扔了进去。人生的戏剧性在于,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你会身处何方,面临怎样的窘境。不同的想法,筑就了不同的人生轨迹。但我要怎样,才能将宋乔从这里拯救出来呢?这不同于我们常常提到的那种从刽子手、恶魔手中拯救人质。现在,宋乔站在了正义的对立面,至少那封通报信上是那样写的——涉嫌诈骗——是的,他们是这样通报的。看来是板上钉钉的事,这样,我们心中所存的那点拯救的想法,就变得毫无意义了。
我们在院子里停留了很长时间,所有人都沉默着,我们显得苍白而无奈。
“走吧,先把东西送进去。这么冷的天,早一秒送到他们手里,早一点暖和些。”我想到了在火车上,微信里那些同样焦急的家人们的话,这些神通广大的人说,看守所四面透风。
看守所值班室内堆满了大大小小的行李。
“是从府城过来的么?”看来这个看守所好长时间没有这么热闹了,值班警察几乎不用抬头看我们,就知道我们来自哪。
“是的,按照通知要求,我们亲自为他们送来过冬的衣物。”
“先填单子,带了什么物品都填写清楚。”他递给我们单子。
填完清单,我们将行李搬进值班室。他吩咐我们将行李通通打开,这让我有些担心。
“这个不能带。”最让我擔心的事还是发生了,他将那两支软膏和两袋棉签提出来,放在了办公桌上。
“但她有皮肤病,很严重的皮肤病,如果没有药,我怕她受不了。”弟弟有些急,戴秀珍站在我们身后。郑建国则在门外的过道上。
“棉签可以致人受伤,任何药物都严禁携带。这是规定。”他将规定指给我们看。
“可是……”
“好的,我们遵从这个规定,就不带药进去了。请问他们什么时候能收到这些衣物?”我将弟弟轻轻推开。
“很快。你们可以走了。”那警察并不看我。当我们转身时,他再次提醒我们,“把药带走。”
“你们先出去。”我将郑氏夫妇,弟弟推出门去,然后转过身,重新回到值班室,“那就麻烦你一定给他们带到,这药我拿回去。”我伸出右手,紧紧地握住他的右手,在他眼前,将那些药再次放进妹妹的行李。当我握他的手时,尽量将语气调整到如平板玻璃一样平整。在值班室另一角的办公桌前,背对我们,坐着另外一位警察。我可不想让这次握手,引起他的注意。
“好的,你放心,肯定会按时收到。”他的语气变得轻缓,迅速将手抽开。我看到他脸上有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
走出值班室,我长长舒了口气,人们谣传,能在看守所见到人,我以十年前学的那点法律基础做了否定。现在看来,我是对的,“见不到人。只能送东西来。”那警察对我说。
“药呢?”在合上值班室那扇门之前,我还对那警察哈着腰,嘴里说着拜托的话。看到我空着手出来,他们很诧异地看着我。
“药?送进去了。”我并不看他们,只是茫然看着沙县临近傍晚的天空。
“你是怎么做到的,他不是说不能带进去吗?”戴秀珍很机警地凑过来。
“一言难尽,阿姨。”我开始向着大门口迈步。
“那你有没有说宋乔和郑勇正在谈恋爱,是一起的。”戴秀珍追上我,身后是郑建国的骂声,“你个老不死的,人家不知道说啊?”
我加快了脚步,像逃离一样迈出去。我们距离看守所那两扇坚不可摧的大门越来越远,我们离宋乔,对,还有她那位不被我们接受的小男友越来越远了。他们追着我,想说点什么,我也想说点什么,但我只是把手掌摊开,举在空中摇晃。“别和我说话!”我对他们吼。
距离看守所二十分钟车程的地方,现在聚集了几十个从府城赶来的人。我们饥肠辘辘,在异乡吃了第一顿饭。我们点了三道菜,一个汤,打算好好吃一顿。这是我的主意。但看样子,郑氏夫妇并没有我们兄弟那样好的胃口,“我们已经尽力了。”我安慰他们,并向店家要第二碗白米饭。
“你们最好同我们一起住下,在这个宾馆对面,就是沙县刑警大队。在这里,我们可以随时了解实情进展。”说这话的,是有着浑圆脑袋的中年男人。看得出,他是这群人的主心骨。
“最新进展怎样?”我递给他一支烟。
“其他人都把东西送了进去,我请了律师去看守所。对了,你们给他们留钱没有。”他问我。
“留了。一千元。”
“一千元?”另一个年轻男人站起来,“信上只说让带两百元,在里面买洗漱用具。你留一千元,没有用,到时候这钱就去向不明了。”
“但我认为我们已经千里迢迢来了,为啥就不能多留点?”
我的这句话在人群里引起了短暂的争议。未等我继续问那“主心骨”男人时,已经有人推门而出,他们说要租车再去一趟看守所,要再留点钱给被关在看守所的那些年纪轻轻、甚至不谙世事的孩子们。他们出门时显得慌乱而虔诚,就像要去赴一场生离死别的仪式一样。
“他说的话是对的。”他们这样形容我的想法。
“那你见到你孩子了吗?如果请律师可以见到,我们也请。”郑建国又开始喝起了小酒。
“找了点关系,律师见到了孩子,我只能远远地看了一眼,不能走到跟前。”男人轻描淡写地说。
男人的话让我动心,如果花些钱,在当地聘请一位律师,能见到宋乔一眼也好。而且,我听到那些孩子中有人递话出来,说让家里请一位律师。
“你们请律师吗?大家都请了。”男人望着我。递给我一张写有密密麻麻字的纸。
“我们再商量一下。”显然,我的回答让男人失望,他转过了头,重新坐回到人群中。
戴秀珍大概看出了我们的难处,低下头很宽容地对着我们笑:“郑勇和宋乔本来就是在谈恋爱,所以这些费用我们出。不就是几千块钱的事,别担心,我们出。”
她说这话时,郑建国举杯的手停在了半空。随后,他将杯子所剩的酒一口饮尽。
“算了,”我低头看着桌面,“律师只是暂时充当一次你的眼睛。像我们这样的人家,请律师不是能力之内的事。”
我想起了在府城和嘉城两个等待消息的家庭。再有几天,就该是春节了。我们走的时候,几乎带走了所有的钱。父亲留在府城,继续做他的三轮车夫,依靠起早贪黑拉些乘客挣钱养家。而我呢,有待业的妻子,上学的孩子,还有沉重的房贷、物业费、水电费、电话费、光纤费……有那么一刹那,我觉得这样的想法太过自私,但我们都得活着,才有机会走到有曙光的那天。况且,那男人给我的那张纸,已经让我有些愤怒了。
“你们自己看!”我将那张纸给了他们,“什么10086、10000号工作人员,这就是宋乔推销手机时候的开头语。他们还年轻,应该在这次事件里吸取些教训。”
九点钟,我们要的白米饭仍旧没有端来。但我们已经就着白开水将桌上的菜吃得精光。明天,男人说他们要一起去刑警队施压,要对他们说这些孩子都年少无知,请求宽大处理。而我则决定要在这个夜晚离开沙县。
“十点钟还有去长风市的火车,我们去长风。”我们在那些焦虑的眼神中结账,推门而出。我再次记起,在此之前,我从未走出过四川。现在,我站在了异乡的土地上,绝不要这样昏昏欲睡地连夜坐火车回去。我们的火车,应该朝着长风加速驶去,没有人能摧毁这一夜我的这个决定。
“还是连夜坐车回四川吧。”这次,郑氏夫妇一起提出了异议。
“去长风干嘛?”弟弟也这样问我。
“在这之前,你们出过四川吗?”我问郑氏夫妇,他们不好意思地搖头,暂时舒展了一脸的沧桑。
“你去过长风市吗?那是这个省的省会,是六朝古都,”我顿了顿,其实我还想说“那儿曾经金戈铁马,恩怨情仇。我敢肯定,连那儿的风,都夹着无限的霸气和贵气”,但我打住了这不符合情境又有煽情嫌疑的演说,就像拿了一盆冰冷的水,浇向已经点燃的引线。那一刻,我几乎什么都不愿意多想,诈骗、看守所、律师、皮肤病、握手……我都想对他们说,见鬼去吧。
我想我恐怕过于感性了,当我做出这个决定,郑氏夫妇一定会陷入更大的困惑中。此刻他们并不做声,郑建国递给我一支烟,然后在风里试了三次,终于将烟点燃。戴秀珍则转过身,背对我们,遥望昏黄的路灯下那个三岔路口,那个路口可以给我们两种选择:在沉寂的街头拦一辆车,车头向左,带我们离开沙县;车头向右,带我们重新向看守所进发——如果这样做能见到宋乔和郑勇。但黑夜阻挡了路灯所能延伸的范围,就像阻挡了我们所有的勇气那样。
“所有发生的都让我们意外。失联、诈骗、看守所,还有这要命的冬天。我们就像受到了突然袭击。是的,这让我们慌乱。但现在,我们做了所有能做的,我们已经尽力。既然这样,为什么不可以把它当做一次意外的旅行?”在戴秀珍背后,我的感性在持续发酵,但我刻意避免使用那些可能让人感到晦涩的四字成语。诸如“金戈铁马”。
“你说呢?”她侧过身,去问吐着烟圈的郑建国。
“去吧,去长风,也不枉我们来这里一趟。”一路上,郑建国没有这样坚决过。但现在,他扔掉了仅剩的烟头,像做了生死决定似的。
“那就去长风。去看看。”戴秀珍重新转过身来,用那种足以让整个沙县泛滥的眼神盯着我。
我们的车终于启程了,那是通往长风市的。火车驶出长长的隧道,弟弟轻轻拍着我的肩膀,指着窗外说:下雪了。我望向窗外,在那一片白茫茫的夜里,倾听车轮碾过铁轨的声音。它让我想再听一听马修·连恩那首辽远、忧伤又舒缓的《布列瑟农》:
静静地,我站在布列瑟农
点点繁星缀着苍穹
它们是否也在布雷纳上空闪烁
并装点着另一边的夜空
你会是我甜蜜的归宿
但我必须离开你远走
而我的火车即将载我前行
不过我的心注定要停留
……
【作者简介】张满昌,1982年生,现居四川乐山市,四川省作协会员,供职于乐山市文化艺术研究所。作品见于《文艺报》《北京青年报》《安徽文学》《雪莲》《辽河》等报刊。
——府城鼓楼现状调查与保护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