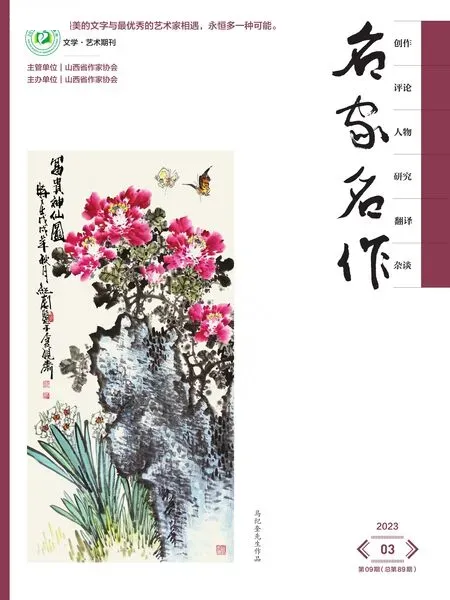约书亚·里夫金谈巴赫① 译者注:这篇采访是由Uri Golomb 所写、Michael Robert Williams 拍摄,于2000 年12 月1 日发表在Goldberg 杂志(已停刊)上。
宋 鸽
在“早期音乐”学界,不乏知识渊博的学者型演奏家,但像约书亚·里夫金②译者注: Joshua Rifkin,美国著名的音乐学者、指挥家、钢琴家和作曲家,1944 年出生于纽约市。Rifkin 是巴赫音乐的专家,他的研究重点是巴赫的键盘音乐和声乐作品,特别是清唱剧。作为指挥家,Rifkin 主要以指挥巴赫的音乐而闻名,他曾领导了许多巴赫合唱团和管弦乐团的演出,尤其是指挥小型合唱团和室内乐团演绎巴赫的音乐,这一演出方式在巴赫音乐演出中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应用。除了指挥和学术研究,Rifkin 还是一位杰出的钢琴家和作曲家。他的创作涵盖了许多不同的音乐风格,包括流行音乐、爵士乐和古典音乐。他还是一位多产的录音制作人,推动了很多音乐作品的录制和发行。这样在两个领域都取得了同等成就的音乐家则为数不多。作为一位指挥家、古钢琴和钢琴演奏家,他的常规曲目涵盖了自文艺复兴开始的声乐音乐,从巴赫、亨德尔,到乔普林、斯特拉文斯基和Revueltas③译者注:Silvestre Revueltas(1899—1940)是墨西哥最著名的作曲家之一,同时也是一位指挥家和小提琴手。,等等。里夫金制作的音乐具有惊人的清晰度和音乐性,不仅注重细节,同时又具有非凡的流畅性——能够让音乐自然而优美地流淌。作为一名音乐学家,他经常打破传统假设,凭借着历史证据的基础,对音乐进行深入分析;将已知事实、合理推断和未被证实的假设区分开来;基于此种周密的思考,源源不断地进行着开创性的研究。
在许多人心中,里夫金是一位单一领域的音乐家。他是第一位声称巴赫的合唱音乐大部分是为一组独唱者而写的学者,并且也是第一位相应地演奏该类作品的指挥。他的这一理论在20 世纪80 年代引发的争议至今仍然存在,尽管近年来里夫金的研究结果越来越受到学界的认可,但对他来说,这种持续的争议是有点恼人的。他说:“20 年过去了,人们对这件事情过于重视了。早就该让它消逝于尘埃,而去追求由音乐发展而来的更有趣的问题。对于像 Parrott、McCreesh 和Kuijken 这样的人来说,这几乎不值一提。这就像是在问:“嘿,伽利略先生,您怎么看待那些仍在争论太阳是否绕地球旋转的人们?”一点意义也没有!音乐的创作涉及很多其他的东西。
这次采访主要基于我与里夫金的一次对话,当时我正在撰写关于巴赫《B 小调弥撒》录音的论文,始终聚焦在巴赫的音乐和他音乐中演奏的力量。随着里夫金最近出版了新版本的《B 小调弥撒》,这个话题依然相关;不过,我试图将这个话题放在里夫金更广泛的成就、兴趣和哲学的背景下来探讨。
Uri Golomb:作为演绎巴赫宗教音乐作品的艺术家,您并不与巴赫有宗教信仰的共鸣,这是否对您的演绎有所影响呢?您认为了解巴赫的神学对演绎者来说重要吗?为什么?
约书亚·里夫金:很显然,如果我认为与巴赫宗教信仰的共鸣是以演绎他的宗教音乐作为先决条件,那么我就要非常彻底地改变我的生活:要么成为一名18 世纪的德国路德教教徒——这是真正的“历史演奏实践”;要么就放弃演奏巴赫。当然,了解巴赫的宗教信仰并不会有什么坏处——就像了解德语(甚至可能更重要),或者,略微改变领域,如果你指挥《巴比伦王纳布科》的话,了解意大利复兴时期的政治是必要的。实际上,我已经吸收了不少18 世纪路德教的文化。我了解赞美诗,了解德语的《圣经》甚至好过英语的《圣经》等。但是,在音乐中要理解的是蕴含在音符之间的语言——事实上,正是这种音符内部的语言,而不是宗教,吸引着几乎所有人对巴赫的热爱。
不可否认,对于这种用音符谱写的语言,某些文化背景的人会比其他人更容易理解一些;维也纳人听着圆舞曲长大,凭直觉地比我们更能“摇摆”它的节奏。但是这些差异并不是不可逾越的,把它们作为原则只会让你陷入有害的身份政治领域。我的意思是,难道只有奥地利和波西米亚犹太人才能演奏马勒吗?只有非裔美国人才能演奏爵士乐吗?只有德国反犹主义者才能演奏瓦格纳吗?
另外,“共享巴赫的宗教信仰”实际上指的是什么?对上帝的信仰?对耶稣的信仰?还是对路德在18 世纪的神学思想的信仰?我不认识任何人规定这是演奏巴赫音乐的先决条件;那么我们应该从哪里划线呢?任何音乐家都具有某种形式的灵性;就让我们在此结束吧。
Uri Golomb:您是一位技艺精湛的键盘演奏家,同时也是指挥家。您与一个小型室内乐团演奏巴赫的音乐,这种音乐可以在没有指挥的情况下演奏,不过您仍然登台指挥。您如何回应那些认为指挥的存在在这些曲目里本就是过时的人?
约书亚·里夫金:我认为这种说法充其量是一种过分简化。现代管弦乐的指挥家指的是——掌握着全方位的控制和解释权威的概念——这在18 世纪是不存在的。但指挥本身是存在的,解释权威也是存在的。当一个意志坚定的作曲家,比如巴赫,在指挥自己的音乐时,怎么可能不是解释权威呢?无论如何,历史演奏的主要关注点不在于演奏条件——我们不是在试图回到没有暖气的托马斯教堂,在寒冬的清晨演奏,虽然那样可能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有用的见解,但我们最主要的兴趣在于探寻声音和风格方面的问题。
当然,不同的曲目需要不同的演奏方法: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需要比巴赫的任何曲目都花更多的时间打拍子;马勒的音乐似乎以某种方式预设了强有力的指引,而这些可能是早期音乐所不需要的;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或瓦格纳的《女武神》不会简单地从一个群体潜意识中产生。此外,我实际上并不指挥我们演奏的小型作品。但无论力度强弱与否,许多潜在问题——尤其是一个指挥应当有多大的控制权力,下达命令与合作激励之间的确切关系等——在各个方面仍然存在。
Uri Golomb:有些人批评您,还有大多数使用“一人一声部”的合唱团成员,认为你们不够进取,即“坚持”使用女高音和男高音,而不是像巴赫那样使用男孩童声。
约书亚·里夫金:首先,这种批评假设执行“一人一声部”这一决定基本上是一种考古学决策,更多地受到重现过去的愿望驱使,而不是为任何可能的音乐考虑。真是胡说八道!话虽如此,如果我们拥有像巴赫那个时代最好的男童高音歌唱家,我想我本人也会使用他们的。但是,由于训练方法的变化,更不用说男孩们变声年龄的提前,我认为18 世纪的男童高音已不再存在,就如另一种广为人知的18 世纪男高音的处境一样。此外,我认为男孩唱的童声女高音在合唱音乐会中并没有扮演重要角色。
无论如何,有证据强烈表明,巴赫和其他人之所以使用男孩,是制度原因而并非音乐,并且只要其他任何类型能够胜任女高音他都乐于使用。对于巴赫来说,男孩的童声女高音、阉人歌手和假声男高音之间的区别,其重要程度可能只是与P rschmann、Eichentopf 和Denner制作的双簧管之间的差别一样重要。
Uri Golomb:无论如何,您似乎并不在所有的演出中都追求历史演奏的真实性(无论如何定义)。以一个极端的例子为例——您曾经在英格兰的三教区音乐节上①译者注:三教区音乐节(The Three Choirs Festival)是一个历史悠久的音乐节,它由英格兰的三个教区合唱团共同主办,这三个教区分别是威尔士的格洛斯特教区、英格兰的赫里福德教区和英格兰的韦尔斯教区。该音乐节每年轮流在这三个教区的大教堂举行,始于1715 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音乐节之一。用英语上演了《马太受难曲》,并且使用了全编制合唱团——这或许是您有意违背作曲家意图的情况之一。是什么激励了您进行这场演出呢?
约书亚·里夫金:三教区音乐节邀请我演出《马太受难曲》是在我和巴赫室内乐团参加BBC 晚会两年后的事情。很明显的是,他们希望实现更具巴洛克风格的表演,但我认为,与其试图用不适合的编制开展一种“启蒙性的”“巴洛克式的”表演,不如更有趣地参与这个音乐节悠久、高尚和迷人的传统。Ivor Atkins②译者注: Ivor Algernon Atkins(1869—1953),英国作曲家、合唱指挥和风琴家。和 Edward Elgar③译者注:Edward Elgar(1857—1934),英国作曲家,被誉为“英国音乐的国父”。曾为音乐节准备了一份《马太受难曲》的英文版本,这个版本在英国已经成为英文标准版的《马太受难曲》。 Novello④译者注:英国著名音乐出版商和剧院公司,由W.W. Novello 在19 世纪初创立。如今提供了现代制作版的 Elgar/Atkins 版本,对这个版本我曾试图追溯其来源。大教堂档案馆的人给了我访问他们所有材料的权限:旧的节目单、详细而丰富的新闻评论、一个年轻的合唱团成员在音乐节前跟随 Atkins 学习《马太受难曲》时留下的笔记,记录了他们讨论的一切。 Novello 为我们弄到了一套旧的分谱。我指挥的合唱团可能还不够大,但我们有钢琴演奏的持续低音,我们还保留了原始的片段,用英语演唱,以及尽可能多地获取他们当时的速度,等等。一旦我们获得了这些信息,我们就有能力自己研究。我不是试图重建古老的表演,但是像历史演出一样,我试图“插入”某个过去的点,越过之间发生的许多事情。
那是一次美妙的经历,我非常喜爱它。显而易见的是,其结果是一场后现代主义的、后历史主义的表演。20 世纪和19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巴赫演奏的诠释都是基于对巴赫所谓愿望的追求;即使是支持用钢琴而不是大键琴演奏键盘作品的论据也是以巴赫“真正”想要什么为框架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现在已经从中解放出来了。正是适当的“历史性”表演的成功使我们得以自由地做其他的一切——只要我们没有自欺欺人。
Uri Golomb :在《巴赫的合唱理想》①译者注:原著Bach’s Choral Ideal,中文版《巴赫的合唱理想》于2002 年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一书中,您写道:“对于合唱的规模和配置的考虑,远远不只是涉及如何实现的问题,它们直接关系到巴赫音乐构思的核心。”换句话说,这不仅仅影响了音乐的声音,还影响了它的意义。您能详细说明一下吗?
约书亚·里夫金:在我们使用传统的“合唱”力来演奏巴赫的作品时,我们在许多方面都不知道这些作品的真正内涵。现在我们正在揭示这一点。我知道这听起来可能有点自大,但我会坚持这一观点:即通过对原始乐谱的研究,我们获得了自己对音乐的解读,这是自巴赫时代以来一直被掩盖的。
对我和我合作的音乐家而言,从合唱到“一人一声部”这样一种过渡,引发我们重新审视音乐演奏的所有方面。你不能仅仅减少歌唱家的人数而不改变其他任何东西,并期待从中得出任何可行的结果。我们必须调整我们的演唱方式,比如线条的塑造、文本的表达以及音响平衡等。这种改变也影响了速度、声乐/器乐的平衡、器乐乐器的分句和发音等方面。然后我们必须将所有这些细节重新整合成一个连贯的整体。最终,这些作品的身份认同对我们而言也发生了改变。
现在,我无法以各种方式量化这一点,但我可以举个例子。以《马太受难曲》的开头乐章为例,该曲主要由两个不同的声乐组组成,每个声乐组由四名歌手组成。起初,两个声乐组以对话方式进行,但并不一起演唱。然后,在第73~75 小节,他们合并为一个合唱:整个音响突然从一人一声部变成了两人的双声部,这就创造出了一个美妙的戏剧高潮。而当每个合唱都已经由双声部组成时,两个合唱团分开唱和一起唱的区别其实根本看不出来——这样的话戏剧效果也就没有了。
当然,这只是在使用巴赫所想的配器时得到的某种关于弹性演绎的一个例子。与其说是一个独唱者或一个完整的合唱团,不如说你获得了一个巨大的可能性范围,从而产生了更丰富的音响、权衡和表现手法。对我来说,旧的演奏方式会导致音乐的贫乏。
Uri Golomb:您曾经说过,您预计室内乐合唱团/古乐器组合将像巴赫琴弓一样消失因为它是一种被标榜为历史重建的创新,一旦被证明是没有历史根据的,就几乎消失了。您真的相信或希望合唱团在将来停演巴赫的作品吗?
约书亚·里夫金:我热爱合唱团,它们是多么美妙的一种团体,能够演绎出美妙的音乐。如果没有勃拉姆斯的《德意志安魂曲》和贝多芬的《庄严弥撒》,我们会在哪里呢?(顺便说一下,我的一个同事怎么可以对“我的”小合唱团在巴赫的演唱上做出讽刺的评论,然后只用40 名歌手演唱勃拉姆斯的《德意志安魂曲》呢?用一种一刀切的方式对待所有作曲家——40 名歌手演唱巴赫,40 名歌手演唱勃拉姆斯吗?这是荒谬的——勃拉姆斯需要150 名歌手:我从未以这样胆大妄为的方式对待勃拉姆斯的作品。)
合唱团习惯于考虑大范围的音乐史——从14 世纪开始——是他们的领域。大多数这种曲目并非为他们而写,但如果他们想演出——那也很好,只要不自欺欺人。钢琴和大键琴之间的古老战争已不再是一场斗争了:很少有钢琴家会严肃地声称当他们演奏巴赫的音乐时在他们的乐器上实现了巴赫的意图。但一旦这场战斗结束了,人们就可以自由地说“但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待整个事情”,这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我在三教区音乐节上演奏《马太受难曲》时所做的,也是我现在用现代钢琴演奏巴赫时所做的。
如果合唱团及其支持者能够说:“看,我们知道我们做的事情是巴赫从未想过并且可能会讨厌的。但这并不重要,因为我们喜欢它。我们今天还活着,我们有这些传统和活动,这对我们很重要。”那么这将是一个更加健康的局面。但我们大多数人仍然想说:“巴赫真正想要的是我所做的和喜欢的。”而很难说:“我才不在乎巴赫的那种方式。我非常珍视他的音乐,但我不关心他的意愿。”我们仍然不是足以摆脱这种想法的后现代主义。但是,如果人们能够面对这一点,那么让一百朵花绽放,让一百种巴赫演绎流派兴盛。也许在40 年后,现代合唱团与古乐器的结合将足够历史悠久,变得越来越有趣——要知道,任何事情都是有可能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