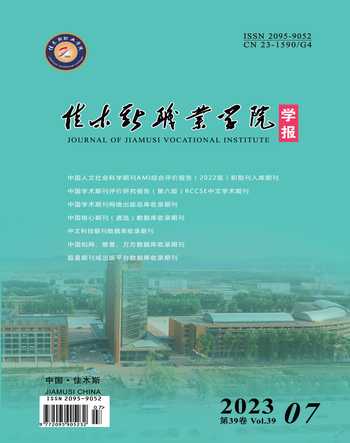论汪曾祺散文的审美日常化
李彬
摘 要:汪曾祺享有“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的赞誉,于文学的沃土中开辟出一脉平实、雅洁的日常审美风格。他的散文创作始终推崇“几近生活的真实”“审美日常化”,也因此在其散文作品里形成了“润物细无声”的风格,与文本细密嵌合,成为他探索现实世界的有力支撑。文章通过分析“审美日常化”在汪曾祺散文中的特点,试图从一个新颖的角度去挖掘其散文的独特魅力,试图更好地阐释汪曾祺的审美观,品味他散文的审美意蕴。
关键词:汪曾祺;散文;审美日常化
中图分类号:I20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9052(2023)07-0-03
在散文创作中,汪曾祺致力于追求“自然朴质”,没有风花雪月的朦胧色调,没有恢宏壮美的辽阔意境,从概观上看似乎缺乏一种“纵横乾坤”的气象格局[1]。他的独特之处在于“审美日常化”的凸显,即摒弃从灵魂维度“俯视万物”的立场,对含有强烈功利色彩和媚俗消费的创作给予拒绝,进而另辟蹊径,以一种温情与敬畏的眼光去关怀芸芸众生所处的日常生活;找到雅俗共赏的文学道路,借此打破“审美与日常生活的界限,将日常生活纳入审美观照的范畴。”[2]
汪曾祺的笔触游走于人世间,并在其中发掘美、呈现美,从而将非审美的变成了美的,使审美普遍化,由个人的日常经验生发到平和朴质的浩渺世界,承接了中国古典的传统韵味,绽放出“人性”的光芒,在中国文学的山河里熠熠生辉,自成一派文风。
一、点石成金:日常生活生发的审美观照
审美观照这一美学范畴,在中国有着深厚的渊源传统,是“审美主体对审美客体进行意向性的投射,从而生成具有审美价值的意象”的审美实践[3]。在汪曾祺的笔下,由日常生发的审美观照,是一个隐逸于文字背后的创作者将点滴生活翻覆成淡雅之美的通透过程。
(一)寻觅世间风物之美
1.人间草木
在汪曾祺的散文里,草木等自然意象作为日常生活中具有“原始性”的存在,经过笔墨的锤炼打磨,犹如琉璃玉片被放置进汪曾祺的散文中,使读者由外朝内的探索过程萦绕着清淡朴质之感。
世间树木不似花草娇艳,却有坚韧厚重的内在。汪曾祺在《冬天的树》中,以一种别样的角度呈现了树木磅礴的张力。冬季时节,万物凋零萧瑟,汪曾祺从繁复华丽的意象中跳脱出来,选择刻画冬天的树。树木米粒般的芽苞开始透出点娇红,是作者当时所见;而树很快吐露新芽,如“火焰燃烧在风中”,又是他进一步的联想。一实一虚间,平常之树,一反常态,变得鲜活勃发,纯粹的自然之美油然而生。
山川与人群交汇之所,少不了繁花的点缀。只见汪曾祺笔下,玉湖潭白得耀眼的洋槐花,喧哗地盛开,仿佛下了一场大雪;春风里绽放的千顷菏泽牡丹,重重叠叠编织成蜜的海洋;六瓣的紫薇,一朵朵簇成碎碎叨叨的球,在和风中扯起脆亮的小嗓子。动与静交融的片刻,无数花蕾的灵魂于散文中得以复活,那种生命的热闹由文本向外溢出,却又缓缓流淌着宁静的光阴。
2.虫鱼鸟兽
除了花草树木外,虫鱼鸟兽一类日常中的微末形象,同样坐落于汪曾祺广袤的文本中。这些被他视为人间风物的“小生命”,像是放大镜背后无限延展的生命群落,在审美的边界往内聚,最终蜕变为生活中象征着自然源动力的结晶,含育着美的趣味。
《瓢虫》里不知是好是坏的瓢虫,让人分不清科学与艺术;《螃蟹》里,汪曾祺借《梦溪笔谈》与拉萨风俗谈螃蟹,引出凶恶与滑稽的对比;《蝈蝈》里被人们称为“叫蚰子”的蝈蝈,总是呱呱叫,有时可能会隔着竹篾咬你一口[4],一种顽皮娇憨之态跃然纸上。
不止有斑斓的昆虫图鉴,还有友人兆华家里飞来的“灵通”麻雀,养猴人手底下坐拥上百只猴众的威严猴王,昆明人家绣墩上卧着的雪白小猫等。种种生灵不经意潜入文本中,以一种灵动自由的生存状态填满视野。它们俯仰坐卧之间的情态可掬、恣意随性,更使得生活亲切炽热的气息扑面而来。
或是草木之类,或是虫鸟之流,俱在汪曾祺赋予的拟人化的描绘中彰显出生命动感,它们始终是活着的,热闹的。这些世间风物的存在,并非只作内容的画龙点睛之笔,更是起抛砖引玉之效,以此及彼,由物推敲延展至人,勾画一条“物中存我”“人物一心”的文脉,为作者对于人类个体生命的思索与叩问埋下伏笔。
(二)品尝人生百态之味
1.食味人间
“民以食为天”,记忆里不曾褪色老去的饮食风味,是汪曾祺与日常最为亲密的共鸣纽带。在他的笔下,西南边陲昆明:充斥着汽锅鸡氤氲的汤雾、饵块咯嘣的脆香。水乡之地高邮:街上叫卖的“杨花萝卜”剔透饱满、鲜红多汁,冒着红油的咸鸭蛋入口即化。北方古城北京:搭配薄脆大饼下胃的老豆腐,用牙签扎取的“宫廷小吃”豌豆黄。凡此种种,于散文间弥漫人生的至情味道。
《自得其樂》中,作者谈到做几个小菜,对于伏案写作的人大有益处,且是很有意思的[5]。他沉迷于这种“意思”,用淮扬的煮干丝招待聂华苓,故意引起她的故国之情;为台湾作家陈怡真准备一道素炒云南干巴菌,惹得她用塑料包带走这道台湾没有的美味;自创塞肉回锅油条,把不同的鲜嫩叠加,酥脆至极,声动十里。亲和平淡的词句间,升腾起熔铸生活酸甜苦辣的热流,作者手与笔的翻飞,便由着热流的牵引,在生活与文学中诗意地栖息。
人们对于饮食的情感,在散文的长焦镜头里,掘出一份坦荡的入世之道。“食”,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相紧密联系,这件最为平常的事,最是能体现生活的醇美。汪曾祺将此作为文学勾连大千世界、饮食男女的桥梁,在每一道菜品的热气中,在每一次舌尖的感知里,把中华地域熔铸了万年的灿烂文明投射在纸上,不似惊鸿,却胜工笔。
2.脚底云烟
汪曾祺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斋作家,他乐于走出书本与外界接触,领略人世景光。因此,他笔下的日常,不仅涵盖他个人熟悉的日常,还有他足迹探寻过的每一寸土地上世代传唱的生活。
在他的散文里,你可以探寻江南生活风和日丽、小桥流水的清歌慢调[6];可以瞥见小四合院、小胡同角落里京城日子的柴米油盐;也可以捕捉昔日昆明城中西南联大、寻常巷陌的窈窕倩影,生活的多姿之态和丰饶之面得以淋漓尽致地展现。
这些镌刻了作者游走痕迹的土地上,种种小人物成为他关注的视野中心,玉潭渊每年为采花而来的蜂匠,水乡带有猛厉印象的猎人,爱吃“手把肉”的蒙古原居民……这些人悠扬缓慢的喜乐轻轻回荡在文字中,谱写出了动人弦音之曲。土地与人,相依相生,互为镶嵌,在不同的天涯海角构筑着相似的“故乡”。
汪曾祺的散文话语里,有植物虫鸟拟人化的生命形式,也有小人物在人间烟火处的生命质感。从风物迁移至人情,作者手眼中的物与人,并没有惊世骇俗的美与力量,而是在他自然的叙述中返璞归真,“审美日常化”也因此在散文中修筑了坚实基础,深入生命本质。
二、匠心于襟:日常生活铸就的士人情怀
学界或读者在谈论汪曾祺的散文时,围绕语言、文本展开是一个极为常见的现象,却鲜少去思考他在其散文话语中所展露的精神色彩。汪曾祺散文中蕴蓄的士大夫文人的雅致情调,是其个人秉持的“绚烂至极归于平淡”的审美追求的凝聚,承接了从古至今中国文人的文章气脉,在时光的积淀中,汇聚成一种淡定、悠远、温润的腔调。
他在散文创作中扮演时代细节的记录者,不去追求反映社会的大浪潮,从平淡的小視角楔入,看似游离于繁华之外,实则是用笔尖去发掘日常事物内的亘古美学价值和浓厚文化意蕴。汪曾祺用一生岁月铸就的“日常化”士人情调,追根溯源是他经汉语文化滋养所形成的一种怀有世俗、热爱生活的生命品格,这也是为何他将写作视野放置到日常中,拥有“日常化”审美倾向的重要因素。
(一)厚德载物的儒思
汪曾祺的散文,不存在延宕的历史波澜,亦没有残酷的人事冲突,他始终遵循着“淡泊”的原则,与时代保持疏离感,与生活拉近距离,营造一个“古朴自然有人味”的散文世界,展示的是生活期间的芸芸众生和睦相处的平淡画面,并树立起一面“厚德载物”的精神旗帜。
“厚德载物”作为儒家思想是留在他生命里最深刻的烙印,极大影响了其人生与创作。那种大地运载万物、各遂其生的兼容并包,在汪曾祺的身上得到了温情顺遂的延续,而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道德与生命印记,又是他播撒在散文中的美的种子。
沐浴着古典书香成长的汪曾祺,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他对中国儒家传统的绘画书法均有涉猎,他将画画与书写的写意、布局用于创作,色彩的选取咬合、笔画的飘忽回转,给予了汪曾祺在笔尖灵活运用儒家思想精髓的契机。散文中对于各种典籍的信手拈来,对于儒、道、释等文化观念的折射,一方面反映了厚德载物所蕴含的容纳百川的气度;关于世间万物的凝眸,关于人事百态的杂谈,则寄托着厚德载物所象征的“民胞物与”的感情理想[7]。
儒家文化在汪曾祺身上投下的温暖厚实的剪影,为他的一生增添了唯美的脚注。他在文字中的之于儒思的坚守,也通过笔墨所表达着:始终关怀生活与生命,以儒士的胸怀包容万物。
(二)适性恬淡的道意
汪曾祺的士人情调不仅仅是“厚德载物”的温润,还有“清静无为”的淡泊。他崇尚的适性恬淡的道法,为他在俗世辟出心灵的一隅,自然的旷远超逸在悄然中渗透进来,使他在时间和空间上有足够的广度和深度去触摸生活,将直面日常时的审美情感提升为与生命相系的美学境界。
毕飞宇曾说:“汪曾祺的背后站着一个人,那就是陶渊明。如果再把时间拉远一点,他的背后还有一个人——老庄。”[8]世人多称赞他是古代士大夫的遗韵,却往往只强调他“儒”的一面,忘了他所象征的士大夫,并非渴望庙堂之高,更多的是偏居江湖之远,不求兼济天下,只愿布衣着身,茕茕独立;从膨胀的欲望中解脱,免于人间浮华的诱惑,追求冲淡虚静的生活情趣[9]。也正是这种平和淡泊的气度,赋予他的散文率性洒脱之气。
汪曾祺的一生,历经时代和命运的坎坷,却仍然可以随遇而安,怡然自得。经历战争的颠沛流离,不忘写下西南联大的名士风采;匍匐在“文革”的硝烟中,不抱怨不沉沦,种着土豆与葡萄,左手一本《中国马铃薯图谱》,右手一篇《葡萄月令》。他在岁月中修炼出的旷达潇洒的道法,成为保护他怀中文学火焰不灭、赤子之心永存的天然屏障,阻隔了不幸与苦难的侵蚀。
漫长生活的洗礼,剪裁出汪曾祺文笔中入世与隐逸交融的复杂情怀,使他的散文不需言语的雕琢,便可在平淡的字里行间窥见儒家的温厚与道家的淡泊。儒思和道意恰到好处的熔聚,在文本内容的基础上,为“审美日常化”于散文中的构建添砖加瓦,砌刻出“朴素适度”的生命雕饰。
三、悠然天成:日常生活沉淀的自然美学
(一)以小见大:从一粒沙看世界
汪曾祺的散文,善用“以小见大”的写作手法。所谓“以小见大”,指他常从一些日常的小视角切入,聚焦于个体生命的呈现,进而延伸出一种生活智慧。他的散文中没有波澜壮阔的场景描写,更多的是在普通的事物现象上投射尊重的目光,在平凡中发掘“伟大”,赋予无声的个体以强大的生命。
《芋头》中,老旧公寓的煤块里舒展肥厚绿叶的芋头,在香港方块豆腐似的层叠空间里,使人获得一点生活的勇气;《长进树皮里的铁蒺藜》描绘的柳树,攀爬在身上的铁蒺藜长进了树皮,“带着一圈长进树皮里的铁蒺藜继续往上长”[10]不与苦难妥协,给人一丝生的希望。小处着眼,蔚为大观。普通之物经汪曾祺思想的锻造,升华为蕴藉旺盛生命的存在。
不悲观不漠视,微末间诠释意义,细节处展露风度,这种穿过一粒沙去看待整个世界的生命姿态,凝聚于日常的偶然与必然中,以一种朴实的力量行走于文本间,透射出汪曾祺纯净的生命观念——用“和谐与适度”的审美钥匙,荡涤苦难,传递生命的透明清澈。
(二)回归本真:走进生命之初
作为作家,汪曾祺总是能将万物与人类放在自然的视域下去观察,“平视”的眼光给予了他解锁生命本真的天赋。他“不被社会虚假的生命价值观所遮蔽,解构了‘以人为中心的狭隘文明论”[11],把众生物类从浮躁中救赎,让生命与自然复归原位,还原成存在本身,生命本身。那三圣庵里不拘法礼的铁桥和尚、沽源之地纯澈的露水与草原、捡枸杞的两个幼稚老孩子,无一不是从日常生活的喧哗中“回归”,展露着生命的纯洁光芒。
汪曾祺的自然美学,作为构造他散文中“审美日常化”的主心骨,仿佛一棵拔地而起的遒劲千年松,支撑了半边笔墨江山。等风一来,树身摇曳,清音顿起,四溢的枝丫便在文本中以一种隐晦却旺盛的生命力蓬勃发展,于无声中演绎雅致,最后抵达一种“天人合一”的自然境界。
四、结语
这种散文的诗意之美,来源于汪曾祺对自身文学创作理念的坚持。他习惯用一种温暖视角去诠释独属自身的审美与情感,与其说他善于发现日常生活中的美,不如说,是他对于生活的热爱,赋予了日常闲适清雅的美感。汪曾祺留下的散文这碗“茶”,在文学的长河里,不仅没“凉”,还始终于滚烫中彰显着“审美日常化”的品格。
参考文献:
[1]王尧.“最后一个中国古典抒情诗人”——再论汪曾祺散文[J].苏州大学学报,1977(4):595-603.
[2]康艳.“审美日常化”理论话语辨析[D].辽宁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
[3]张晶.审美观照论[J].哲学研究,2004(4):67-72.
[4]汪曾祺.人间之味[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8.
[5]汪曾祺.万事有心,人间有味[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9.
[6]文学武.汪曾祺散文论[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0(1):77-79.
[7]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精神[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8]毕飞宇.小说课[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9]张咏梅.中国人色彩审美心理的形成及特征[D].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
[10]汪曾祺.自得其乐[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8.
[11]葛辉.老子的自然美学价值观[J].江苏社会科学,2011(3):
165-170.
(责任编辑:张咏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