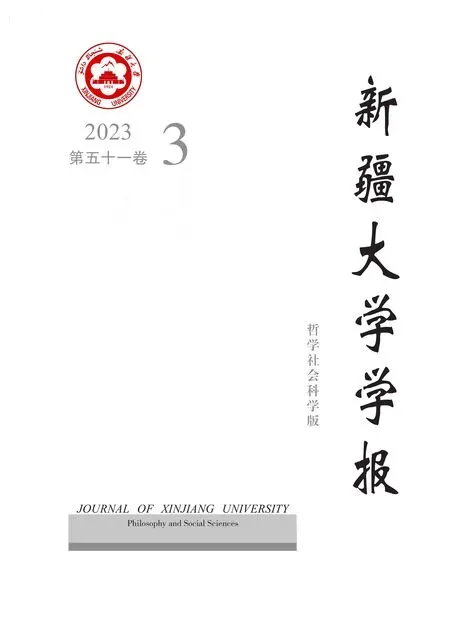汉代经营西域的统治支点与战略设计*
黎镜明
(西北大学 中国—中亚人类与环境“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 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文化遗产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胡鸿将“华夏帝国”扩张的制约因素归纳为三点:一是“集权帝国”自身的动员成本和离心倾向;二是地理环境以及经济生态;三是原住人群的政治组织形态。①参见胡鸿《秦汉帝国扩张的制约因素及突破口》,《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1期,第184⁃203页。笔者曾尝试对第一点进行过论述②参见黎镜明《边郡与汉代的边疆经略——以敦煌郡对西域事务的介入为中心》,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0年,第41⁃65页。,后两者则无疑属于边疆作为特殊区域的自身脉络。作为宏观和一般意义上的通论,胡鸿的阐述无疑是出色的,且大体对应了布罗代尔所谓的“长时段”(地理时间)和“中时段”(社会时间)。③参见费尔南·布罗代尔《文明史纲》,肖昶、冯棠、张文英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9页。然而牵涉到具体的边疆经略史事,难免有鞭长不及马腹之嫌,尚需更多“短时段”的史料支撑。地理、社会、事件中任一个维度的缺乏都会使我们的研究流于片面。有鉴于此,文章拟从汉代西域的地理环境、经济生业和政权组织形式、地缘政治格局等入手,把握汉廷经营西域的空间逻辑、成本考量和交聘策略,进而梳理汉代的西域治理设计。
一、汉代经营西域的影响因素及因应方式
(一)地理上的“边”与“远”
松田寿男指出:“正如用点线来表示出天山山脉的两侧那样,在山体的南北一连串地排列着数不尽的绿洲。如果换一种看法,那么,长长地浮现在沙海上的所谓‘天山半岛’,在其南北两岸把很多的绿洲像珠子或肉串似地串联起来。这些绿洲实在可以看作是设在‘天山半岛’的停泊场”[1]3。以海为喻,松田氏传神地为受海洋季风影响的“湿润亚洲”区域的人们勾勒出西域的地理图景。然而涉及“海”与“岛”的空间关系,似仍可增润几笔:两岛之间的海上几乎无处不可通航,岛民也可绕过临近的岛屿直接与远方产生接触。而相邻绿洲间的联系通常只能依赖一条有内陆河或地下水流经的道路,从一个绿洲出发前往远方必须经过临近的绿洲。相较于真实海洋上的岛屿所织就的绵密交通网络,“沙漠岛”(绿洲)间的道路系统远为稀疏。西域绿洲间的交通更多呈现出点线结构的特征,线路上的某一点被切断通常就意味着失去了这一点后面的整条线路乃至整个远方。故而仅从军事地理角度来说,覆盖西域绝大部分面积的沙漠是缺乏意义的,真正具有战略价值的是呈原子化分布的绿洲,所谓的“奄有西域”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奄有西域上的绿洲,而经略西域的要旨在于确保绿洲间的道路通畅。
除了迥异的地理形态,巨大的东西跨度是汉廷经营西域必须克服的另一重地理限制。史书以“边远”指称边疆民族地区肇始于《后汉书·西南夷列传》中所谓“汉氏征伐戎狄,有事边远”[2]卷96,2060。某种程度上,“边”“远”连称、“称边必远”的认识是秦汉尤其是武帝大举开边的副产品:伴随着边界向“蛮夷”居地的不断推移,边疆与核心区的空间距离也不断变远。①郑君雷以“边远地区”作为西汉时与中原对应的一个地域概念,其“边远”所涵盖的西北朝鲜、辽西辽东、内蒙古中南部、河西、河湟、四川盆地、云贵高原、岭南、东南沿海基本上皆可以视作当时的边疆地区。参见郑君雷《西汉边远地区汉文化的形成模式》,《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0年第12期,第163⁃165页;《西汉边远地区汉文化结构中的西域》,载《北方民族考古》第2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180⁃189页。各区域间的海拔差异、地形变化又使“边远”拥有比直线距离更丰富的地理含义。具体到西域,史载其地“与汉隔绝,道里又远”[2]卷96,3929,“且通西域,近有龙堆,远则葱岭,身热、头痛、县度之厄”[2]卷96,3931。敦煌以西的白龙堆“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3]。
逐级递增的交通阻力以及由此造成的人员物资投送能力递减是汉廷在各个方向扩张遭遇的普遍困境,其中西北面临的局面又颇为特殊和复杂,具体而言,司马迁虽称西北的天水、陇西、北地、上郡诸郡“畜牧为天下饶”,但又紧接着说“然地亦穷险,唯京师要其道”[4]卷129,3261。更多只是想表达该地经济的畜牧业特征,在以农业作为立国之本和经边主要财源的汉代,不应过分高估其在“天下”的经济比重。河西四郡初开时,“立郡沙石之间,民不能自守,发屯乘城,挽辇而赡之”[5]。即便后期经过发展,河西的人口数量和经济总量仍逊色于内地。②依据昭帝始元二年(前85)的户籍材料,敦煌仅有112 00户,38 335人,人口仅是上郡的1/16,西河郡的1/18。参见张德芳《从出土汉简看敦煌太守在两汉丝绸之路上的特殊作用》,载《丝绸之路研究》第1 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第101⁃109页。又史载成帝时“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国,给使者往来人马驴橐驼食,皆苦之”[6]卷96上,3893。
另一方面,河西受制于两山(北山与祁连山)夹立的地理环境,四郡只能一线排开,直面广袤西域的只有敦煌一郡,以一郡之力专制西域则嫌不足,中央介入则又所费不赀。松田寿男以为“从中原到天山方面去,通常是渡过黄河,并以位于西方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诸绿洲,……总称为河西的地方为‘桥梁’”[1]8。称敦煌等为“绿洲”不仅体现了河西具有与西域相似的地理特征,也隐约指出其农业和人口规模狭小。“桥梁”一语则折射出河西与西域难以深入嵌套的窘境。
(二)西域人群的经济生业和组织形态
对于人类社会而言,水的意义远远超越了其原始自然属性。③唐代敦煌文书S.5874中有“本地,此是人血脉”等语,而中古道教文献中多见“泉者,地之血”,“水乃地之血脉”的表述,应可视作社会现实在信仰层面的投射。在河西、西域等干旱地区,水甚至具有神性。如《元和郡县图志》载:“悬泉水,在县东一百三十里。出悬泉山,汉将李广利伐大宛还,士众渴乏,引佩刀刺山,飞泉涌出,即此也。”参见胡同庆《敦煌文献“水是人血脉”出处溯源》,《敦煌学辑刊》,2016 年第4 期,第1⁃4 页;王明《太平经合校》卷45,北京:中华书局,1960 年,第119⁃120页。在干旱地区更是如此④如松田寿男在论述其将oasis(绿洲)定义为“沙漠岛”的初衷时,指出“此前将其译作膏地或沃地,……这个词是将沙漠视为不毛之地作为前提。可是,沙漠是因为没有水才荒芜的,绝非土壤本身贫瘠。”松田寿男《丝绸之路纪行》,金晓宇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9页。。天山南坡与昆仑山北坡的融雪形成了水源,当地的聚落分布因绿洲形态而呈原子化分布,而这又深刻形塑了当地的政治、社会面貌:对水资源的控制导致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控制,城邦发展趋于深化和集中,政治体呈现出阶序化特征,⑤如张广达指出:“由于从事灌溉农业,古老的社区发展起来,重要的城市国家得以形成。”参见张广达《塔里木盆地的城市国家》,载B.A.李特文斯基《中亚文明史》第三卷,马小鹤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年,第240页。此外,由于诸国与汉和匈奴等进行的远程贸易换得的并非是经常可供民众日常消费的必需品而是珍稀物品,这一点又得到了强化;⑥参见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73页。绿洲有限的农业潜力则限制了其人口承载能力,单个城邦国家规模有限。尽管鄯善、龟兹等政治体规模稍大,但“这些大国大抵以某一较大绿洲为中心,兼并相邻的较小绿洲而形成。盖各绿洲之间相距较远,跨越长距离沙漠的统治成本较高,从而限制了其规模”[7]。
城邦诸国之间囿于高昂的统治成本无法组成一个更大的、阶序化程度更高的政治体。这一逻辑对其他渴望统治西域的政治体来说也同样适用。历代中原王朝对疆域的要求基本上是以是否适宜农耕、是否能够产生足以养活当地居民的粮食为标准的。①参见葛剑雄《论秦汉统一的地理基础——兼评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2期,第20⁃29页。在这一意义上,本地的粮食产出能够最低限度供应军事、行政机构运转的区域,便是成本、收益大致平衡的区域。具体到西域,以乌孙为代表的“行国”“地莽平、多雨、寒,山多松樠。不田作种树,随畜逐水草,与匈奴同俗”[6]卷96下,3901。婼羌则“辟在西南,不当孔道……随畜逐水草,不田作,仰鄯善、且末谷”[6]卷96上,3875,农业条件欠佳。天山以南的绿洲区域从理论上说,一旦满足基本的灌溉条件,能够具备比雨养农业区更稳定的产量保障,但这需要动员大量人财物力进行较大规模的水利建设。然而城邦诸国通常势力寡弱,难以承担大型工程的负荷。
(三)西域的地缘政治格局
汉代关注西域问题最初是基于国家安全的考量,从武帝时联合乌孙以“断匈奴右臂”,到哀帝时扬雄上书:“且往者图西域……乃以制匈奴也。”[6]卷94下,3816再到东汉张珰“乃知弃西域则河西不能自存”[8]等可知,汉世的西域经略始终服属于抗击北方游牧政权的战略大局。这也决定了在汉廷的西域设计中,军事利益往往超越经济、文化考量而具有优先性,地缘政治因而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②如余太山认为“(西域)这些政权是作为中原王朝的天然盟友受到中原王朝、从而也受到‘西域传’编者注意的”。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研究》绪说,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3⁃4页。
斯蒂芬·沃尔特认为国家之所以结盟主要是为了制衡威胁,而影响威胁的因素则有综合实力、地缘的毗邻性、进攻实力和侵略意图等。最终,“国家结盟的目的是制衡对自己构成最大威胁的国家,而不一定是实力最强大的国家”[9]。综览张骞凿空前后的西域地缘政治格局,以综合实力而论,汉匈并强、乌孙在伊犁河流域则“最为强国”。从地缘的毗邻性看,“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常居焉耆、危须、尉犁间”[6]卷96上,3873。乌孙居匈奴西北,通过天山山谷间的道路对莎车等国保持较大影响力,③《汉书·西域传》载姑墨、龟兹、焉耆、捐毒等国“北与乌孙接”,休循、捐毒、尉头国“衣服类乌孙”,而宣帝时“莎车国人计欲自托于汉,又欲得乌孙心”。又关于乌孙与南疆诸国之间的道路,《汉书·傅介子传》载:“匈奴使属过,当至乌孙,道过龟兹。”松田寿男认为:“在天山山路中间有很多难走的路,距离也很长,著名的木素尔岭便是其中最好的例子。这条路线作为连接阿克苏和伊犁方面的要道,……最高处据说达到3 600 米。”参见松田寿男《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陈俊谋译,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年,第21页。又《新疆图志·道路志三》载:乌什“城北四十里雅满苏卡伦,一百二十里至贡古鲁克山口,有径通伊犁”。贡古鲁克山“有地曰……北郭罗,为通伊犁之伊克哈布哈克卡伦,越贡古鲁克达巴罕,以达乌什”。苏北海据此认为在沙俄未侵占伊塞克湖以前,此为从伊犁通向南疆的主要道路。参见苏北海《西域历史地理》,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8页。而汉最初距西域舞台则相对遥远,大月氏“又自以远汉,殊无报胡之心”[4]卷123,3159,乌孙“自以汉远,未知其大小”“宛以西,皆自以远”。至于进攻实力和侵略意图,游牧经济的不自足性使匈奴在周边政权眼中往往十分危险。④王明珂认为:“以牛马等为贸易资本,更使得匈奴需要对外掠夺牲畜——环境中有太多不确定因素,使得牧民心理上永远觉得畜产匮乏,并没有‘盈余’畜产可资交易。”参见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73页。史载匈奴在西域置僮仆都尉,“赋税诸国,取富给焉”[6]卷96上,3872。实质是“一种对待奴役部落的办法”[10]25。而匈奴击走月氏、乌孙,以月氏王头颅为饮器的行为无疑属于王明珂所谓战略性掠夺(strategic raids)。⑤参见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36页。至于汉的军事威胁,大宛贵人曾言:“汉使数百人为辈来,而常乏食,死者过半,是安能致大军乎?无奈我何。”[4]卷123,3160相较匈奴,汉廷总体上是一个“温和的巨人”。据此,尽管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但基本可以认定,为了对抗匈奴共同造成的威胁,乌孙、城邦诸国、汉之间存在联合的诉求。
综上所述,汉代经营西域受到多重时空条件的影响。地理因素是其中“结构性的存在”:依靠狭长的河西走廊无法实现西域与中原的环套链接,西域广袤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得一个完整的权力网络难以形成,汉廷的势力分布更多呈现为一些长短不一、疏密不等的“触角”,“触角”只能通过唯一的道路获得由内到外的补给。原住人群的经济生业和组织形态无法提供郡县制得以成立的两个基本条件:编户和赋税,开发成果的维护成本过高。多种势力交互的地缘政治格局为西域增加了复杂的外部因素,经常出现短促而剧烈的变化。与之相应地,汉代采取了灵活的因应方式:在空间逻辑上,着重控制行政治所、屯戍据点和交通线路,点线结合。在统治形态上因俗而治,实行消耗最低的间接统治。在交聘策略上,善于分化、瓦解敌对阵营,最大限度地利用同盟和属众。在以上多重因素的交互作用下,汉代在西域先后进行过三种战略设计。
二、“大夏之属皆为外臣”:汉代的大西域设计
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天子数问骞大夏之属”,张骞在介绍了乌孙的情况后谏言:“今诚以此时而厚币赂乌孙,招以益东,居故浑邪之地,与汉结昆弟,其势益听;听则是断匈奴右臂也。既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4]卷123,3168。此为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的直接诱因。相较于单纯为了与月氏结盟的第一次出使,张骞此次为武帝规划了将大夏之属“招为外臣”的远景,而其战略设计的支点就是乌孙。然则此处实际可分解为三个问题:何谓外臣?何以汉代需要外臣?何以张骞认为结好乌孙即可将招其西诸国为外臣?
刘瑞详细辨析秦汉文献及出土简牍中有关“外臣”的记载,指出:
被称为“外臣”者虽然名义上是汉王朝的“外臣”,但实际上在自己的统治区域内均拥有完全的自主权。经济上完全自主。拥有独立的军队和完全自主的指挥权,无需报请汉王朝批准。拥有独立的外交权,往往对邻近少数民族形成统属关系。[11]
具体到西域,则西域都护管辖的“三十六国”因其与汉明确的统属关系而为“内臣”无疑。乌孙最初是独立于汉的大国,但到哀帝时,汉与匈奴约定“中国人亡入匈奴者,乌孙亡降匈奴者,西域诸国佩匈奴印绶降匈奴者,乌桓降匈奴者,皆不得受”[6]卷94下,3819。可见最迟此时乌孙已无独立的外交权,成为汉之“内臣”。①关于乌孙隶属于汉的确切时间,学界有西域都护设立时和元康二年乌孙上书请立汉外孙元贵靡为昆弥时等不同认识,参见杨建新《关于汉代乌孙的几个问题》,《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2期,第66⁃79页;刘光华《也谈汉代的乌孙——〈关于汉代乌孙的几个问题〉商榷》,《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3期,第33⁃43页;李大龙《西域都护的设立不是乌孙和西汉关系转变的标志》,《西域研究》,1993年第1期,第55⁃58页。故而我们在界定西域地区“外臣”范围时,首先应聚焦那些始终保持独立地位的政权,且此类政权仅仅在与汉保持名义上的隶属关系时才可被称为“外臣”。具体则有所谓“皆以绝远,不在数中,其来贡献则相与报,不督录总领也”[6]卷96下,3928的难兜、厨宾、乌弋山离、安息、大月氏、康居等。
史载“本匈奴盛时,非以兼有乌孙、康居故也;及其称臣妾,非以失二国也”[6]卷96上,3886,又“(罽宾)其乡慕,不足以安西域,虽不附,不能危城郭”[6]卷96上,3892。既然“外臣”对现实政治缺乏实质影响,何以汉廷需要煞费苦心地与其维持一种名义上的君臣关系?仅将其归咎于武帝的好大喜功无疑未达其间:纵观整个帝制中国时期,即便因国力衰微或崇尚文治而“未必诸番真入贡”,也必“驰想海邦兼日出”。胡鸿认为华夏与“蛮夷”间存在相互建构的一面,“蛮夷”必须在华夏主导的帝国秩序中扮演特定的角色:侵略者、臣服者或朝贡者。②参见胡鸿《帝国符号秩序中的夷狄》,《能夏则大与渐慕华风:政治体视角下的华夏与华夏化》,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80页。王柯也认为在中国古代“多重型天下”的体系中,“四夷”也被看作必不可缺的一部分,参见王柯《中国,从“天下”到民族国家》,台北:政大出版社,2014年,第264页。然而我们仍可进一步追问:如果说击败侵略者树立了中原政权“华夏保卫者”的形象,将侵略者转化为臣服者足够确立“华夏”相对于“蛮夷”的优势地位,则朝贡者(外臣)的角色是否多余?
葛兆光关于历代《职贡图》的研究或可深化我们的理解。案《职贡图》的绘制传统虽肇始于梁元帝,但葛氏指出,先秦典籍中即有中国自居中央、蛮夷定期进贡的“先王之制”,而汉代遗留的“天下帝国”的历史记忆也镌刻进后世《职贡图》的思想脉络之中。换言之,“职贡”之所以较晚成“图”,主要是囿于技术性条件的限制,而其“万邦来朝”的思想内涵则早已发育成熟。图像上的中原王朝绝不会是“月明星稀”般孤立的存在,而是“在异国殊俗的对照之下,想象自己仿佛众星拱月的天下帝国”[12]。据此,在中原王朝的自我想象中,朝贡的蛮夷种类越多、居地越远、习俗越是离奇、语言越是“重译乃通”,越能体现出本朝功业的超迈古今、德泽的无远弗届。元狩、元鼎年间正值汉代扩张高潮,中原王朝比此前任何时候都更有希望将“万国来朝”变成现实图景,故而对招抚“大夏之属”表现出别样的热衷。而乌孙则是汉廷实现梦想的“最后一公里”。
案张骞二次西使时,姚大力所谓更具开放性格的准噶尔盆地①参见姚大力《沟通欧亚的“瓶颈”:新疆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西北民族研究》,2018年第3期,第139⁃154页。尚在匈奴的牢固控制之下,直至宣帝神爵年间,匈奴日逐王降汉、汉军在与匈奴“六争车师”中取胜②关于史书中“降日逐,破车师”的考辨,参见李炳泉《关于汉代西域都护的两个问题》,《民族研究》,2003年第6期,第69⁃75页。,乃以郑吉“并护车师以西北道”[6]卷70,第3006。中原与中亚的交通主要还是途径南疆诸国,也因此,武帝伐宛前大宛贵人相互计议:“汉去我远,而盐水中数败,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绝邑,乏食者多。”[4]卷123,3174活跃于特克斯河和伊犁河流域的乌孙虽然相较寻常绿洲大得异乎寻常③王炳华指出《汉书·西域传》所载乌孙户、口、兵数超过了西域都护所属的其他西域诸国的总和。参见王明哲、王炳华《乌孙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6页。,但仍不能自外于整个西域空间格局的点线结构,乌孙居地无疑是向极西输送影响力的地理枢纽。
地理阐述虽然言之成理,但在解释变动短促的事件时则略显空泛,汉廷更切实的考虑当是基于乌孙在河中乃至整个中亚的地位。毫无疑问,在汉乃至匈奴势力进入中亚之前,中亚诸国间已有广泛而深入地交流,甚至确立了彼此间的政治秩序和贸易规则,④如史载:“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目,多须髯,善市贾,争分铢。”参见《史记》卷123《大宛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174页。又史载成帝时:“而康居骄黠,讫不肯拜使者;都护吏至其国,坐之乌孙诸使下,王及贵人先饮食已,乃饮啖都护吏,故为无所省以夸旁国。”乌孙诸使座次靠前显示了其强大的区域影响力,而康居“以夸旁国”则说明中亚诸国也有自身的一套关系体系。参见《汉书》卷96 上《西域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第3893页。无论汉匈,撇开旧有区域关系体系的主导者之一乌孙而改弦更张,都既无可能也无必要。相反,依靠乌孙的威望、渠道及其对当地风土、语言、道路乃至贸易规则的熟悉,无疑能够最快站稳脚跟。⑤如余太山认为:“通过乌孙,匈奴间接控制了从伊犁河流域西抵伊朗高原的交通线。”参见余太山《西域通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48页。而张骞抵达乌孙后“间道”派遣副使前往“大夏之属”,如无乌孙的首肯乃至“导译”,也难免事倍功半。从后续的历史发展来看,张骞对武帝的进言深具远见卓识,史载“乌孙使既见汉人众富厚,归报其国,其国乃益重汉。其后岁余,骞所遣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4]卷123,3169。
三、都护天山南北:汉代的中西域设计
在《战略论》中,利德尔·哈特超越了以往战略研究仅关注战争本身的局限,提出其“大战略”理论。其中又以“间接路线”思想最为引人注目。哈特认为几乎所有的决定性胜利都并非单纯由军事冲突造成,而是某一方先让对方丧失协调和平衡所致。而为达到这一目的,需要“避免向坚固的阵地作正面的突击,尽量从侧翼采取迂回行动以猛击最要害的地点”[13]7。关联至汉史领域,汉廷“断匈奴右臂”的战略也常给人以一种侧翼牵制的印象。⑥如拉铁摩尔认为:“在汉代,匈奴游牧民族深入中国内地,汉族也更远地深入草原。这些都可以叫作正面战争或长城战争。有时与之交替发生的,是新疆绿洲地区的侧翼战争。”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48页。有鉴于此,笔者认为该理论或可在相当程度上为汉匈争夺西域的史事建立新的、合理的解释。
将西域定义为汉匈战争的侧翼战场需要回答一个基础性问题,即汉廷经略西域的根本原因,拉铁摩尔认为汉廷的意图在于建立与绿洲诸国的同盟并对诸绿洲进行防御性战略。⑦参见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48页。拉氏的阐述也可得到史料的印证。如所周知,张骞最初希望招诱大月氏“东居故地”,因不得要领而转求乌孙,甚至当浑邪王降汉,“而金城、河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后,“乌孙王既不肯东还,汉乃于浑邪王故地置酒泉郡,稍发徙民以充实之”[14]。河西既可拱手予人,则其时汉廷对直接经略西域亦缺乏兴趣。①吴礽骧、余尧也指出:“但当时汉王朝尚无在河西徙民屯田的意图,更无建郡之事。”参见吴礽骧、余尧《汉代的敦煌郡》,《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2期,第24⁃32页。又汉廷“凿空”西域当有切断匈奴与城邦诸国经济联系的用意,但没有证据表明汉廷此举是为了充实自己的财政,②如马长寿比较汉匈在西域的经济政策,指出“属汉之后,西域各国只向汉朝的都护纳一定的贡赋,而不复以马畜、旃裘、粮食等物供给匈奴。”马长寿《北狄与匈奴》,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8页。经济目的也无法解释汉使西行往往厚赂诸国以至府库空竭的行为。据此,土地、人口、物产等财富在汉代的西域经略中更多是作为手段,是为更高的政治目标即战胜匈奴服务的。换言之,在汉廷看来,经营西域最重要的不是自己能得到什么,而是能使匈奴失去什么。
西域对匈奴的意义首先是经济上的。前已指出,游牧经济的不自足性使其极为依赖对农耕区域的贸易和掠夺,而在与汉廷沿长城沿线的战争频频失利后,南疆诸国就成为其获取农耕区域物资补给的主要来源。③诚如马长寿所言:“北匈奴南侵的计划既经失败,它唯一的出路便是威胁西域诸国,希望从那里再剥削城邦国家的财富,以接济漠北的贫困。”马长寿《北狄与匈奴》,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6页。首先,“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的诸“城国”是匈奴度过饥荒重要的粮食来源。其次,匈奴对铜铁器及其原料具有很大的需求。④参见林幹《匈奴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46页。而鄯善、婼羌“山有铁,自作兵”,莎车、龟兹等国有铁山或山出铜铁,无疑属于匈奴“税敛重刻”的对象。⑤王宗维认为:“西域若羌、楼兰能作兵器,姑墨、龟兹等有铜、铁、铅,莎车、和田多玉,获取这些特产以供匈奴贵族使用,也是一种形式。”参见王宗维《塔里木盆地的古代居民及其与匈奴的关系》,《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2期,第6⁃27页。另外,“匈奴在其间(天山南北麓和昆仑山北麓)设关卡,收商税,护送旅客,担保过山,都可以收到不少的报酬,有时还掠夺行商和马队的货物”[10]31。
控驭天山南北诸国不仅可以切断匈奴财源,削弱其战争能力,更重要的则是促成匈奴内部的统治失序。⑥此处牵涉到草原政权不稳定的政治结构。如傅礼初认为:“部落的忠顺不能永远通过武力来维持,而是要通过收买,想要当上统治者的人必须给予部落一些他们自己无法获得的好处。想让他们情愿加入一个持久的超部落政治体,只提供防御保护是不够的。……财富是另一个要点。”傅礼初《生态与社会视角下的蒙古人》,才仁卓玛译,载《西北民族论丛》第19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281页。《史记》这样描述战争与匈奴政局的关系:“其攻战,……所得卤获因以予之,得人以为奴婢,故其战人人自为趋利,……故其见敌则逐利如鸟之集,其困败则瓦解云散矣”[4]卷110,2892。又史载宣帝本始三年(前71),匈奴先后遭遇暴雪和军事失利,“人民死者什三,畜产什五,匈奴大虚弱,诸国羁属者皆瓦解,攻盗不能理”[6]卷94上,3787。信息方面的考虑或许也值得重视,史书曾记载西域诸国“役属匈奴”的一种特殊形式亦即“为匈奴耳目”[6]卷96上,3876,又楼兰王“尝为匈奴间”[6]卷70,3002,西域作为匈奴情报来源的地位不容忽视。据此,汉廷进取西域尤其是天山以南城邦诸国,恰如利德尔·哈特所言,“最漫长的迂回道路,常常又是达到目的的最短途径”[13]13。
要确保“间接路线”持续生效就必须保持对天山以南诸国的控制。山南诸国间松散的政治结构一方面使得汉廷有可能对其进行统属,但另一方面,由于总体来说集权化程度不高,各个城邦通常可以自行决定贸易和从属对象,如果不全部被纳入汉廷主导的政治体系,就无法达成封锁匈奴的效果。故而有必要在诸国间维持一个常设的统治机构,这个机构必须胜任三种角色:诸国间利益关系的协调者、诸国安全的保障者以及汉代意志的代表。
然而以何种形态确立对西域尤其是南疆诸国的统治呢?中原的郡县制、匈奴的僮仆都尉制、西域的王侯制是其时可供参考的三种智力资源。从郡县制传统中成长起来的“初郡”“边郡”无疑在当地缺乏设置条件。汉廷没有奴役诸国、征收赋税的诉求,僮仆都尉式的胡式统治显然也无法照搬。而且在这一模式下,诸国“虽属匈奴,不相亲附。匈奴能得其马、畜、旃、罽而不能统率与之进退”[6]卷96下,3930。本地王侯作为“精英中介”,其统治受制于外部势力,也无法完全代表汉廷的意志。最终,以西域都护统领天山南北道诸国,但主要依靠当地王侯自治成为就当时而言最好的制度安排。①需要指出的是:都护统领下的诸国自治不能仅仅被视作中原王朝对西域传统的妥协。汉代始终保持着以中原传统渗透、改造西域政制的努力。史载诸国“自译长、君、监、吏、大禄、百长、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皆佩汉印绶,凡三百七十六人”。拘弥国有“主簿”,诸国首领虽名为王侯,但需要遵循汉代官僚制度的规范,与内地官员一样依赖文书、馆驿等形式进行信息沟通。其废立嗣绍也要如内地官员的升迁陟黜般以汉廷意志为准绳。随着日复一日与都护乃至汉廷的公务往来,王侯愈发适应汉廷的日常统治,其作为中原官僚体系一员的观念也逐渐被形塑。换言之,都护制度将当地王侯塑造成特殊的“汉官”,使他们易于认同和参与王朝秩序。
四、敦煌的战略缓冲区:汉代的小西域设计
毫无疑问,河西在汉代是进取西域的重要基地。但另一方面,由于该地人口大量由中原迁徙而来,且在政治制度和生计方式上与中原大体保持一致,久而久之,包含河西在内的“西州”在西汉晚期已经成为帝国不可或缺的“旧疆”。②参见薛小林《西州与东汉政权的建立》,《史学月刊》,2015年第1期,第20⁃31页。既为旧疆,则汉代当然具有对斯地斯民的安全保障义务。如所周知,河西西面虽与西域衔接,但主要的外部威胁来自匈奴,西域因此带有河西与匈奴间战略缓冲区的色彩。③如江娜也指出:“西域诸国作为西汉中后期才纳入汉王朝边疆板块的部分,是汉匈博弈中极为巧妙的缓冲地带。”参见江娜《汉代边防体系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22页。
方汉盛时,在汉匈围绕西域的冲突中,西域既是火药桶,又是吸收冲突的缓冲地带,都护府麾下的屯田吏卒和诸国兵通常能就地消解匈奴的攻势,河西大体宁谧。西汉末年以降,随着汉廷在西域力量的衰退,河西的安全形势日益严峻。史载明帝“永平中,北虏乃胁诸国共寇河西,郡县城门昼闭”[2]卷88,2909。安帝永初年间罢置西域都护“北匈奴即复收属诸国,共为边寇十余岁”[2]卷88,2911。而“敦煌太守曹宗患其暴害”诸语揭示此处“边寇”的方向主要是河西。东汉中期以后,敦煌更俨然是东汉经营西域的中心。④参见谢绍鹢《汉代西北边郡代管边外事务试析》,《西域研究》,2015年第2期,第1⁃6页。
需要注意的是,相较西汉,东汉在西域的战略半径大为收缩,战事主要集中在鄯善、车师、蒲类、伊吾等,对三十六国中偏西的西夜、子合、无雷等统治远不如西汉稳固,更缺乏经略乌孙、大宛以西的宏图。顺帝时汉廷复置伊吾司马,虽名为“设屯田如永元时事”,但已非将其作为经略西域前哨,仅是因其“傍近西域,匈奴资之,以为钞暴”[2]卷88,2912。其时汉廷真正着意经营的是东天山诸国,而目的则主要是以其拱卫河西,有鉴于此,笔者称之为小西域设计。
五、余 论
汉代除依靠官僚实现对广土众民的理性行政外,还统治着具有多元文化及族群属性的人群,并且宣称具有超出实际势力范围的普世统治权。⑤参见胡鸿《秦汉帝国扩张的制约因素及突破口》,《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1期,第184⁃203页。具体到西域问题上,则汉廷经营西域首先是出于对华夏区域的安全保障,其次是为了建立对“内属”诸国的统治,又时常体现出对招“远夷”为“外臣”的兴趣。综合此前论述,汉代以乌孙、都护府、敦煌郡为统治支点,依托盟友、城邦诸国、边郡的实力,分别以徕远国、安天山、固河西为目标进行了三种战略设计。
由于统治支点和依托力量的不同,三种设计的有效性和稳定性并不一致。乌孙作为盟友在武帝伐大宛之役中“持两端”,成帝时西域都护郭舜称康居遣子入侍是“其欲贾市为好,诈之辞也”[6]卷96上,3893。远国“徕”否并不能由汉廷单方面决定。中西域设计主要依靠屯田士卒和诸国兵,曾经起到过很好的效果,班超曾言:“以夷狄攻夷狄,计之善者也。”时人亦尝称赞班超为都护时“不动中国、不烦戎事”[2]卷47,1582。但诸国的忠诚很大程度上受汉廷对其“内属”的态度以及边吏个人素养影响,从根本上则取决于汉匈势力在西域的消长。⑥陈忠、班勇等皆曾指出若汉廷对西域弃而不救,则其必从属匈奴。班超也曾说西域诸国“怀鸟兽之心,难养易败”。参见《后汉书》卷47《班超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586页。至于小西域设计,笔者曾指出:边郡的战略地位、经商渠道和自然资源为当地吏民带来进仕路径、商业利润和衣食根本。维护此类利益以及自身家园的热望,使得边郡吏民成为汉廷经边最可依恃的力量。①参见黎镜明《边郡与汉代的边疆经略——以敦煌郡对西域事务的介入为中心》,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0年,第65页。
需要指出的是,这三重战略设计绝非相互孤立、彼此割裂的。某一设计在某一时期居于主导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支撑其他设计的因素就此消泯。徕远国无疑需要以汉廷对天山、河西的牢固统治为基础。如宣帝时乌孙有变,“汉遣破羌将军辛武贤将兵万五千人至敦煌,遣使者案行表,穿卑鞮侯井以西,欲通渠转谷,积居庐仓以讨之”[6]卷96下,3907。章帝时,班超二次击破焉耆,“于是五十余国悉纳质内属。其条支、安息诸国至于海濒四万里外,皆重译贡献”[2]卷88,2910。则“大夏之属皆为外臣”是“都护天山南北”的积极效果之一。安天山既需要河西作为稳定的进取基地,也受到中亚“远国”的局势影响。而东汉乃至以后的中原王朝即便无法“广地万里”,但显然难以抗拒“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4]卷123,3166的诱惑。据此,三种西域设计的边界并不总是凝固的,而是保持了开放和流动,何种战略设计居于主导地位则通常取决于该种战略利益的优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