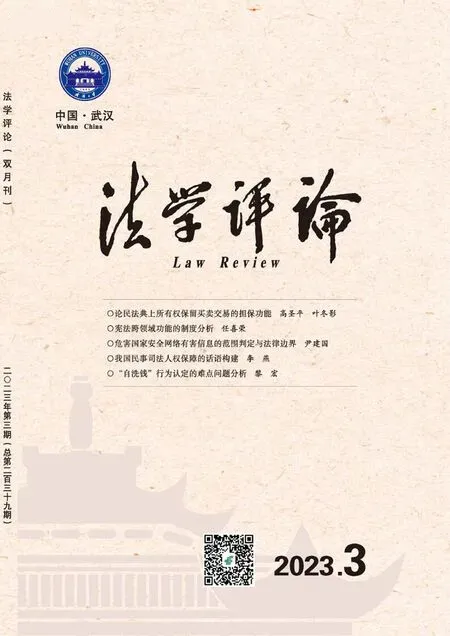计算法学研究范式的阐释与构建*
肖金明 方 琨*
计算法学是新时代新科技发展、新法治新法科建设的产物。侧重计算科学与与法学交叉融合的计算法学近些年来备受学界关注,已成为重要的学术学科领域和人才培养专业方向。一方面,以新兴科技赋能现代法学教育。教育部发布《新文科建设宣言》,国内知名高校开办计算法学、数据法学、人工智能法学等专业,致力于新法科人才培养,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新法科建设的初步成效。另一方面,支撑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的计算法学学术发展比较显著,立于计算法学作为大数据时代学科演化之果的准确定位,基于法律实证研究的法学范式变革的明确定向,计算法学已经在知识积累、理论沉淀、方法经验等方面取得较大进展。(1)参见申卫星、刘云:《法学研究新范式:计算法学的内涵、范畴与方法》,载《法学研究》2020年第5期。但实事求是地讲,当前计算法学呈现出学术研究多点突破、散状交织等特点,在主要命题、基本范畴和方法论上发展不足,有必要系统阐释和建构计算法学研究范式,以为新时代新法科建设与研究范式之转换做出自主知识和理论创新贡献。我们拟以计算法学研究的前提、逻辑和演化为要旨,考察计算法学研究的格局特征与发展态势,整合构成计算法学研究范式的基本理论和核心命题,致力于构建面向时代发展、法治进步和科技创新、兼具学科视野、理论关怀和实证思维的计算法学研究范式,以推进新时代数字法学、数字法治和数字中国建设。
一、新科技发展与法学研究范式问题
研究范式源于20世纪库恩超脱传统学科束缚与研究方法惯性而创造性使用。他从科技革命视域展开构建,让科技革命与范式转换(Paradigm shift)在技术进步与社会变迁意义上进行延伸。(2)[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6-188页。现代法学建基于工业文明,以规训公权力和保障私权利为基本轴线,分别从法的价值判断、规范研究与实证分析层面形成法哲学、法教义学、社科法学的研究范式。(3)参见苏力:《中国法学研究格局的流变》,载《法商研究》2014年第5期。三者研究轴心在理解、理性与经验间转换。具言之,法哲学探寻法的正当性基础,系法价值层面的元命题,在不断理解权力与权利中作出理性的价值判断与选择;法教义学立足法的合法性依据,以语义分析法规范的内涵、适用规律等,以理性确保权力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维系权利的期待性;社科法学直指理想状态中的拟制法(Positive Law)具有不确定性,而面向事实状态的法规范于复杂社会有不同表现形式,需以经验明确法对权力和权利的具体意义。然而,技术进步与社会转型却致使法学研究范式定性日益消解。从霍布斯指出人的理性计算是现实社会的基本单位,到莱布尼茨提出通过计算解决法律纠纷,再到边沁提出计算道德和法律义务的成本收益、实现多数人最大幸福的功利主义法律观,还有韦伯提出将合理性与现代性结合而实现“通过计算以及信息的收集和记录实现对世界的控制”,等等。(4)参见[英]韦恩·莫里森:《法理学:从古希腊到后现代》,李桂林、李清伟、侯健、郑云瑞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3-106、188-207、288-305、416-421页。理性、计算主义日趋与法治相通相融,名家著述更为法学研究范式之转换奠定思想基础。随着新一轮科技与产业革命的深入推进,生产力革命必然带来生产关系、社会结构、治理机制的深刻变革。这无疑对工业革命时代法学理论及其研究领域冲击极深,法治理论或面临局部失效之窘境。在大数据、云计算等新科技深度影响下的法学研究命题、范畴、方法等因而亟待革新,以顺应时代发展与社会变迁之需。
“我们站在技术革命的边缘,而这将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生活、工作和相互联系的方式。从规模、范围和复杂性来看,这一转变将不同于人类以往所经历的一切。”(5)[美]吉姆·海史密斯、琳达·刘、大卫·罗宾逊:《EDGE:价值驱动的数字化转型》,万学凡、钱冰沁、笪磊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21年版,第1-2页。法学研究在数字信息文明的基本轴线为支配与控制,即数字权力在共同体与个体的合理配置以及数字化权利的利用与保障。法学在回应科技发展过程中与计算科学、数据科学等研究日趋交融,表现在逐步从个案经验分析向类案统计与预测演变,日趋交叉使用数学建模、机器学习等其他学科知识方法,研究对象选取从法规范本身转向法内外因素。计算法学(6)计算法学在国际上又表述为computational law computational jurisprudence computing law computable law等。如参见Jens Frankenreiter, Michael A. Livermore. Computational Methods in Legal Analysis. Annual Review of Law and Social Science, 2020, 16:39-57.作为将计算科学(如科学计算、计算机技术)、数据科学(如机器学习、数据挖掘)、工程科学(如控制论、系统论)与法学交叉融合的新兴学科和研究范式应运而生。其一,计算法学强调计算与技术在社会变迁中的阐释、理解、提喻功能。(7)参见Abebe R, Barocas S, Kleinberg J, Levy K, Raghavan M, Robinson DG. Roles for computing in social change. FAT 2020 - Proceedings of the 2020 Conference on Fairness, Accountability, and Transparency, 2020, 252-260.即通过现代技术赋能的“工具箱”及其方法论去捕捉法学领域无法处理的现象和问题,通过精确计算形式化地揭示法律、政策与决策的风险,通过计算加深对复杂社会中利益博弈的理解与价值的权衡,进而逐步厘清技治主义及其边界。其二,计算法学在学科交叉中不断扩张研究领域。即人工智能、区块链、元宇宙等新兴技术的法律应用和规制共同构成法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对象,数字正义、数据安全等成为数字时代法治领域的重要命题。其三,计算法学研究轴心和范围面临双重转换。即随着计算能力提升与数字化转型紧密相连,自然语言处理、法律检索、诉讼预测与大数据侦查等新兴法律科技的研发和应用,需要计算法学的知识创新,以支撑法律科技的运用与自洽。
虽然数字革命改变社会科学核心领域以及带来“经验社会的危机”,(8)参见Savage M, Burrows R. The coming crisis of empirical sociology. Sociology, 2007, 41:885-899.但计算法学仍秉承现代法学深厚的理论根基,并在数字时代的学科变迁与范式转换中凝聚法律与科技的结晶、形成法学研究的范式。其一,计算法学在本体论探讨数字信息文明对法治产生的结构性影响。计算法学绝非仅是数字数据、计算方法、科技简单相加,还应是建立在计算社会中的法治世界观与方法论,(9)参见Cioffi-Revilla C. Computation and social science. In: Introduction to 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 New York: Springer, 2017, pp.35-102.强调科学与法学的本体认知性命题;其二,计算法学规范论旨在对法治领域中数字信息技术加以应用和规制,通过学科交叉创新法学知识体系,进而化解新兴科技面临的立法完善、司法适用等难题,并提供实验、预测等新解决方案;其三,计算法学还在法律数字化领域使用建模、模拟、算法等建构法律科技系统,(10)参见张妮、蒲亦非:《计算法学导论》,四川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页。使其数字化转型。因此,构建计算法学研究范式,是计算法学作为新法科重要研究范式体系性建设与整体性发展的前提。
二、计算法学研究范式的主要命题
作为回应数字信息文明对法治冲击而展现超越计算的计算法学维度,其始源于计量法学与法律信息学,发展于法社会学、法经济学与犯罪学的拓扑,成形于计算社会科学诞生与新法科理论与实践之中,并通过包容传承了法律概念、因果关系推理、制度实践与结构等内容,形成计算法学研究体系。这固然是计算法学范式建设的必然选择。而要进一步实现计算法学的创新发展,则需要在法治的历史叙事中理解制度设计的内在机理,把握计算法学的立论根基与构建历程,(11)参见季卫东:《计算法学的疆域》,载《社会科学辑刊》2021年第3期。才能捕捉计算法学多元面相、支撑计算法学研究范式体系构建。基于此,我们立足于计算法学的元理论、一般理论与具体理论层面,尝试阐释计算法学得以不断推演与展开的三个命题:法秩序有序性、整合模式和法治协调共生,从而阐明计算法学自创生的理论演进路径。
(一)计算法学研究范式基础原理:法秩序有序性
从元理论层面观之,计算法学旨趣乃理性的控制权力与支配权利,并在其交互建构中发展相应的新理念、新命题和新范畴,进而以计算法学一般原理来实现规制转化。然而计算法学内容体系庞杂,基于计算法学研究范式之整体性,还需根本性原理以作奠基。而纵观不同文明的法律系统从简单向复杂、低级向高级的有序进化,我们认为,从法律功能及其流变出发,以法秩序有序性作为计算法学研究范式的立论基础。法秩序有序性是指法律系统应协调内部各要素相互运作而维系法律定纷止争的功能,确保法律系统调整运作的正当性,实现法追求的正义理想。与规范法学通过内部建立逻辑关联性、完整性与严密性的规则等级体系以实现法秩序有序性不同,计算法学意为法秩序有序性应聚焦于结果有序性,即从决策维度实现权力的理性控制。
因现实中的不同条件与因素会影响法秩序结果有序性,故法秩序实现程度之可预测性指标已成为经验转化、结果评估等重要衡量标准。(12)William C. Heffernan. The Dual Problems of Legal Justification: A Key to the Unity of Karl Llewellyn's Jurisprudence.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1978, 45(3):654-694.在此意义上,计算法学法秩序有序性命题包含三个维度:第一,获得计算法学方法论的正当性基础,为范式转换找到立论支撑。作为计算法学研究范式的基础原理,法秩序中的结果有序性要求法律决策具有可预测性,而可预测的法律结果又须公平正义以解决纷争、满足行为预期和社会内在需求。这就需通过理性的法学方法论来实现法秩序结果的可计算性,以此确保系统运作及结果合理正当,否则极易陷入法律语言模糊的“空缺结构”陷阱,并造成法律决策因个性、偏好等主观差异产生结果不确定性、差异性和研究领域泛化。所以,法秩序有序性此间蕴含法律理性之意涵,即法律推理之经验理性与利益衡量之计算理性,并将公平正义等诸法律价值之实现视作为构成性价值,以满足法律系统运作稳定、决策结果合理、社会行为预期等价值需要。第二,建立计算法学的各种知识衔接,避免逻辑矛盾,解决研究范式偶在性。实证法学论者将法律概念转化为精确化研究的可观察可操作对象,融合科学理性与工具理性,推进法律概念微观化、法律推理符号化、法律研究技术化,(13)参见叶启政:《从因果到机制:经验实证研究的概念再造》,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20年版,第12页。建立以法律数量化为表征的计量范式。计量法学从法律预测转向司法与法律的科学研究,赋予实现法秩序结果有序性更多的实践性与可操作性。数字时代随着大数据、算法、算力与计算技术不断发展,计算法学在工具与价值的关系中更为兼容,有序生成研究领域、理论逻辑与价值体系。一方面,计算法学关注法律制度环境等结构性因素与情感态度等主观性因素,通过算法模型及其数据分析、理论建构来展现司法裁判量刑规范化、法律运行正当化的秩序图景;另一方面,计算法学借助知识图谱、科学实验等多元化、技术化的手段,致力于法律实践减少主观性、提升客观性、增强合理性与实效性。由此可见,计算法学与计量法学乃一脉相承。第三,将新兴法律科技融入计算法学范式进行细致考察,分析法律数字化立论起点与具体逻辑的价值结构。尽管现实中法律科技的面相不尽相同,有概括为法律系统中的科学和信息技术的应用,也有理解为法律服务及其系统的数字化与智能化,(14)Christopher L. Hinson. Legal Informatics: Opportunities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Journal of Education for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2005, 46(2):134-153.但无碍于计算法学考察法律科技的内涵和功能,以及从工具与价值的二元结构视角发现意义关联。展言之,法律数字化为计算法学提供了丰富的“工具箱”,且通过法律文件自动检索、法律服务自动化、智能司法量刑等技术应用实现资源优化配置,进而提高司法效率与司法实践可预测性,使计算法学具有“工具理性”与“构成性价值”相互通融的复合关联性。可以说,从法律系统功能与研究范式演迁中提炼出法秩序有序性的元命题乃计算法学研究范式的基础和出发点,得以解决计算法学本体论中价值存疑与序位问题,以及避免科技发展带来的技术反噬。
(二)计算法学研究范式一般理论:整合模式
在厘清计算法学各技术工具与理论价值的关联后,需要建立计算法学与规范制度的实践勾连。计算法学研究范式一般理论的立足点是从法规范与实践中发现计算法学元理论的适用场域,提炼具有体系性的逻辑构造,以作为计算法学研究范式奠基性的理论命题。从研究范式的代际变迁来看,计算法学不仅是以研究方法嵌入法学理论与实践中,且是在逐步整合法学理论与新兴技术发展的知识谱系,在此基础上发展计算法学的普遍性原理,并形成自身的观念体系。观念的现实化在个人行动向社会行动组织合成中发挥价值沟通功能并付诸实践。这便既要赓续元命题之价值观照,也需把深嵌的知识方法统筹整合,在现实语境中探讨规范制度的具体建构。因此,整合命题注重规范、秩序和实践的统一和对话,要求明确新科技发展的方法嵌入、理论边界和现实需要,乃数字时代的知识重构。
一方面,计算法学与法社会学、法经济学等学科交叉相融,体现在置身于社会外部视角,通过精细化与数量化的研究方法考察法规范的立法和司法效率效能。(15)参见Nelson LK. Computational grounded theory: a methodological framework. Sociological Methods &Research, 2017, 49:3-42。另一方面,计算法学深嵌于刑事司法与犯罪治理等实践领域,在充分运用法律科技来提高效率、规避风险的同时还审思法律科技的边界与限制。计算法学以人类社会行动和效用理性为导向出发点,连接认定法律因果关系认定中的行为及其后果、人类社会理性选择等因素,聚焦社会行动与现实,提供面向司法裁判与量刑的算法模型(16)法律计量模型还影响了法律改革以及反垄断评估、人身伤害赔偿损害、刑罚量刑考量等制度设计。参见[美]理查德·A·波斯纳:《法律理论的前沿》,武欣、凌斌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35页。及其可操作的解决方案。而在智能社会以科技创新的研究手段,整合法律系统与外部系统的制度化规范体系与规范性秩序模式,使计算法学法秩序有序性的可计算命题具备更为丰富的模型与多元的适用空间,进而不断拓展新领域、生成新知识。因此,计算法学在法秩序有序性条件下整合了效率命题、合理性命题与正当性命题,使计算法学与规范制度建立多重实践上的价值关联,并以此运用至计算法学理论命题现实化转换层面,从而实现法规范形式理性与实践结果的平衡推进,以及权力控制、权利保障的结构更新。
随着数字时代大数据侦查等犯罪治理实践不断深入,整合模式命题应在计算法学方法论推进的同时实现法规范秩序与公平正义的价值目标。择重而述,从菲利等学者将生物学、社会学等实证方法结合理解犯罪原因与生态,(17)参见Emilio Jorge Ayos. Prevención del delito y teorías criminológicas: tres problematizaciones sobre el presente. Estud. Socio-Juríd., Bogotá (Colombia), 2014, 16(2):265-308.到复杂社会的犯罪事实得以具备可观察可识别的外部特征,以及基于犯罪率等指标制定的刑事政策。计算法学或以线性回归、逻辑回归、泊松回归等(18)回归模型意在寻找合适参数去满足数据的规律情况从而拟合方程、构建模型。线性和逻辑回归基于最小二乘法展开,泊松回归则是处理离散数据且因变量为有序的非负整数而重构的模型,可应用于犯罪率等计数变量的建模分析。参见司守奎、孙玺菁主编:《Python数学实验与建模》,科技出版社2020年版,第369-390页。算法完善犯罪率的建模与分析场景,或以犯罪事实和数据为基础研究自我控制程度、身体和心理健康、刑罚惩罚力度等因素的犯罪影响程度、影响因子,或以犯罪场景构建系统(19)该系统在输入证据、犯罪事实等数据后再智能组合建模来生成可信场景网络,或就仿真情景为犯罪预防提供依据,可实现信息差异性分类与可视化等功能。呈现刑事犯罪可视化、提高犯罪控制效率,都旨在找到犯罪人本质与所涉法律制度、观念和行为的刑罚适用普遍性规律。另外,计算法学也为犯罪控制与预防而使用高科技工具亦面临适用价值限制。从中国大数据侦查的理论与实践来看,犯罪技术使用的制度设计需建立完善的应用和审查机制,这便涉及到比例原则、权利保障与技术使用正当性之要求,旨在实现犯罪控制和预防的有序性。因此,从整合模式命题来看法秩序有序性的建构与完善,就要将计算法学的观念、制度、实践等加以整合,即计算法学不仅系法律中工具理性的存在,它更作为法律观照现实的价值共识。换言之,计算法学整合模式蕴涵体现于法律制度设计、权力理性控制的实践之中,这不仅对权利支配和保障大有裨益,法治秩序亦于规范和实践的整合关系中展开有效构建。
(三)计算法学研究范式具体命题:法治协调共生
关于数字时代法规范的协调和适用、受新科技发展深度影响的法律制度设计与安排等问题,构成计算法学研究范式的具体命题。对计算法学研究范式具体命题的探讨,不但需融贯元命题与一般命题之法理,还需观照时代背景与实现法规范的现实复杂环境共生。又因法的规范性源自于人类社会的规定性,使法规范在实践中发挥规划与预防风险等功能。(20)参见宾凯:《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对于技术风险的决策观察》,载《交大法学》2020年第1期。我们认为,计算法学应置于数字中国现实中回应科技发展带来的新风险以及提出的新方法、领域和命题,以法治消融科技发展带来的不确定性以及导致的环境复杂性,在法的元规范层面构造法律与数字的互动空间和规范边界,从而在整体构建协调共生的数字法治。那么,计算法学研究范式就应以法律与社会以及科技的协调共生作为其论域的具体命题。
法治协调共生命题要求计算法学着眼于数字信息文明法规范整体逻辑、注重在衔接新科技发展基础上实现法秩序有序性。质言之,法治协调共生命题含义如下:其一,法律系统基于规范制度整体性,需与数字经济、数字政府、数字社会等发展过程中新事物、新问题建立因果联系,在“法律问题数字化”与“数字问题法律化”之间扩张法规范的整体适用、革新数字法治理论体系和实践模式;其二,数字中国的法治秩序与治理图景就要在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网络安全法与宪法以及各部门法的协调中实现法秩序统一性,并统合新科技发展有序向善的导向性,形成良性的互动循环。如果说法秩序有序性命题解决了计算法学本体的价值取向问题,整合模式命题解决了计算法学规范的合理性问题,那么计算法学在数字法治的具体建构和实践,即是进一步实现复杂系统中数字与法治协调共生,使“数字问题法律化”获得规范支持,亦使“法律问题数字化”交融于法学范式之中。比如人工智能行为因偏离法律因果关系的归责模式,故要在人工智能、算法等多元结构中考察行为风险与重构因果关系认定模式。(21)参见刘志强、方琨:《论人工智能行为法律因果关系认定》,载《学术界》2018年第12期。在这意义上,对科技创新及其社会行动的概念化理论化成为计算法学具体命题展开的关键轴。“计算+”的计算法学借助新方法理解复杂社会系统,使法律系统将规范制度协调于各外部系统。随即规范性问题就转化为数字时代智能社会的核心议题,并通过计算法学构成结合性的关联理论以适应变迁和发展。为此,为实现法秩序有序性命题、法治协调共生命题,计算法学还需不断夯实阐释时代变迁、法治秩序与治理模式的理论基础,运用丰富的“工具箱”理解与重构智能社会,进而提升法律系统回应数字时代复杂社会问题的解释力,才能使数字法治及其研究范式更具理论自洽性与开放性。当然,基于数字时代复杂社会问题不存在最优解和唯一解,立于计算法学风险预防和秩序维护的研究视域,数字法治要在科技迭代语境下寻求“历史与发展”“社会与技术”的规范自觉,(22)参见龙卫球:《科技法迭代视角下的人工智能立法》,载《法商研究》2020年第1期。在工具理性与制度建构之间实现规范价值协调。一方面,法治协调共生命题中的“数字问题法律化”要基于整体性对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考察技术本质,作超越历史时空的抽象化概括,厘清法律政策、道德伦理等规范界限,并实现法规范对人工智能调整的开放和沟通。另一方面,“法律问题数字化”则要达成法律系统与外部系统的协同运作,以不断探索和完善数字法治的时代适应性。计算法学在洞察法律研究的问题以及结构化立法和司法数据基础上,经由计算科学、数据科学、工程科学来提供研究方法、开发算法模型、研发计算技术和程序应用、建立计算科学实验体系等,(23)这包括自动信息提取、复杂系统建模(如预测性建模Predictive Modeling、探索性建模Exploratory Modeling)、社会仿真模拟、虚拟实验室实验和计算建模、人机交互协作等。从而为法律诸具体问题及其制度设计提供数字化的解决方案,促进法治数字化转型。因而,计算法学在法律与科技二者相互融贯,在理论、经验与事实之间建立法规范的有序衔接,共同推动数字法治的理论革新、建构数字治理秩序。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法秩序有序性命题为计算法学研究范式完成了本体价值和理论引领的法理证成,整合模式从计算和法规范的理论、秩序与制度实践的逻辑关系中建构了计算法学的制度依托和实践支撑,而法治协调共生付诸规范与新科技发展的融合和转型提供了解决方案与技术支持。因此,数字信息文明的计算法学研究范式承袭法学研究范式基础上开拓创新,从元命题、一般命题、具体命题的三个维度构成数字时代的计算法学理论。
三、构建计算法学研究范式的基本课题
计算法学的主要命题在于阐明其内在价值、理论视域和实践逻辑,为研究范式的体系性奠定了基础。在数字时代,计算法学若要发展为成熟完善的研究范式,还需构建多层次、多领域、多范畴的基本课题。即计算法学的基本内涵、发展面向和具体追求等还需由表及里地剖析,从不同视角注入原创性知识,从而推动整合计算法学研究范式体系。为此,我们尝试从诠释、叙事和法理三个层面构建计算法学研究范式的基本课题,在形成计算法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的过程中创制我国计算法学话语体系。这对提高我国计算法学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以及数字中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诠释层面:计算法学研究范式的概念话语
工业革命时代法学虽实现学科分化与知识体系专业化、精细化,形成不同法学领域,但亦造成自身视域盲区和知识之间龃龉。(24)参见刘剑文:《论领域法学:一种立足新兴交叉领域的法学研究范式》,载《政法论丛》2016年第5期。现今对数字信息文明而衍生的新兴领域法学探索,构成了计算法学的不同面向,因而计算法学研究范式的概念话语就需通观全局来构建理论体系。又因交融计算法学的计算科学、数据科学、工程科学亦为知识话语,(25)参见[法]利奥塔尔:《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车槿山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8-100页。故数字时代计算法学就应在完成新旧知识关系替代基础上实现知识结构话语统合,以便与法学各领域及其他学科的沟通。究而言之,计算法学研究范式的概念话语统合具有历时性,既需整合信息技术法学(或计算机法学)、网络法学(或互联网法学)、人工智能法学与数据法学,也要承袭发展计量法学与数字法学。首先,在研究对象维度,随着计算机信息技术出现到Web1.0发展至Web3.0,(26)Web1.0表现为静态信息场景技术,发展至Web2.0则注重交互体验技术,进而现实Web3.0在集成Web体验的基础上旨在实现机器将能够以类似于人类的方式理解和编目数据的技术。参见Rudman, R. and Bruwer, R. Defining Web 3.0: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he Electronic Library, 2016, 34(1):132-154.信息技术法学、网络法学等逐步兴起。其注重信息技术与网络的法律规制,也关注其具体技术的法律应用,在此过程中形成人工智能与法学交叉融合的人工智能法学和以大数据、隐私、信息为基础的数据法学。国内外也相应地设置了关联学科与课程。上述探索使法律与科技的调整更为深刻化精细化,但却因各自概念和内涵不同及各有侧重而有所局限。若彼此因话语不同而难以沟通,又何以兼纳科技创新带来的新兴事物。而基于“计算+”的计算法学,因计算具备数学运算、符号推理、阐释、理解、提喻等丰富维度,而能将计算机信息技术、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统合其中,形成相对开放的概念话语。其次,在研究方法维度,计算法学作为超越计量法学的“数据密集型科学”,(27)参见于晓虹、王翔:《大数据时代计算法学兴起及其深层问题阐释》,载《理论探索》2019年第3期。在大数据分析、整合、交互中的建模、预测和评估等领域建树颇丰,并伴随着计算社会科学的发展于算法、模型等维度不断延伸。与此同时,以“数字+法学”为结构的数字法学在理论上展现了现代数字生活逻辑与重组了法学知识体系,乃现代法学的“转型升级”。(28)参见马长山:《数字法学的理论表达》,载《中国法学》2022年第3期。然而,数据法学不能解决数据自身的统计相关性和法律因果性问题。数字法学虽关注法律的科技赋能却缺位法律数字化层面的探讨。这无法涵盖以技术为导向的法律自动化(如人工智能机器人可以习得法律)。而以“计算+法学”为结构的计算法学研究范围更为广阔,能在法律大数据基础上推进法学可计算性课题,推进计算技术、计算方法、计算理论与法学相契合。由此观之,“计算法学”统揽科技与法律关系创新研究,致力于数字时代法律和科技关系重构,可以此为本推进计算法学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
从上述梳理来看,学科和领域的划分固然有助于知识传承,却容易限制对知识的反思和创新。因而,计算法学在诠释层面应超越传统学科界限,统合数字信息文明中不同对象和方法,再组合地重构法学与计算科学、数据科学、工程科学的异质性知识跨界交融,全面、深刻地理解与重构法学研究范式。计算法学就应如“造血细胞”般具有自我更新和发展能力,成为数字信息文明中适应社会变迁、技术发展的新型范式,促使新兴现象、事物、技术和方法等成为概念话语中的重要范畴,从而驱动知识的有机生成。如元宇宙结合了不同虚拟、实境而形成新空间,那么计算法学对元宇宙的探讨就要交叉学科的知识支持,也要在解构技术特征、内在性质等方面加以具体化规制,并将技术置于现实语境考量。而以“法律数字化”反照元宇宙等新兴科技赋能与适用场景,计算法学对数字信息文明的理性观察与合理回应在于理论体系化、技术具体化、规制现实化之间不断瓦解和再组合,从而构建调整内容来支撑范式框架。须指出的是,从计算机科学、统计学等外部视角进行的观察,都仅是一种描述性的分析,不过是法学与其他学科交互碰撞中对存在风险与挑战的发现。而规范性的研究需要从计算法学自身逻辑视角才能证成。因此,计算法学除要在数字信息文明中完成概念话语整合外,还应在数字中国建设过程中不断提升自身兼容性,主动寻求法学与其他技术、知识、信息的融合,而其他学科亦需保持足够开放性,否则法学研究范式之转型会流于形式。
(二)叙事层面:计算法学研究范式的逻辑构成
如果说数字时代计算法学系在探索应对科技引发技术与伦理风险中不断重构法秩序,那么计算法学还需叙述从规范到制度与实践的有序生成之过程。其基本路径有三:在方法论维度,数字技术充分发展使得以机器学习、结构化数据为基础的法律计算日趋普及。(29)法律计算指运用计算科学和数据科学的原理技术展开的法学研究领域。参见左卫民:《中国计算法学的未来:审思与前瞻》,载《清华法学》2022年第3期。那么付诸法律大数据研究使立法实验与评估、司法裁判与量刑等与算法模型深度结合,(30)参见王禄生:《论刑事诉讼的象征性立法及其后果——基于303万判决书大数据的自然语义挖掘》,载《清华法学》2018年第6期;Wang Fang, Guo Liang. Do Confessions Contribute to Lenient Punishments in China?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Crimes-of-Intentional-Injury Trials. Tsinghua China Law Review, 12(1), 2019, 59-85。就使法规范制度及其实践结果可预测,进而推进计算法学可计算性课题、连贯法秩序有序性的元命题。这些描述性、预测性等法律计算建模固然能提高法的可预测性。但由于机器学习在本质上是对“黑箱”的模拟,(31)参见Jake M. Hofman, Duncan J. Watts, et al. Integrating explanation and prediction in 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 Nature, 2021, 595:181-188.所以基于最小二乘法的算法只能廓清所学习数据之间的相关性,不足以揭示多元性和非线性结构人类社会的因果关系。简言之,“量化”的法实证并不能推导出具有“应然”的法规范。此外,由数据输入转化为结果输出的“算法黑箱”看似提高法学可计算性的效率效能,实则使法律大数据间的关系缺乏法律推理而降低精确性实效性。而算法隐含的人类社会歧视、偏见等问题更可能随技术发展而不断加剧。那么因果关系作为法律系统理解行为的关键,计算法学可计算课题需要在方法论维度有所推进:一方面,通过数据挖掘不断追问相关性基础、发现法律大数据各变量规律,从“强相关性的因果关系”转向“作为生成过程的因果关系”;(32)Guillaume Wunsch, Federica Russo, Michel Mouchart, Renzo Orsi. Time and causality in the social sciences. Time &Society, 2021, 1-33.另一方面,回归理论关怀视角,置身数字时空寻求“理解行为的解释”,(33)Couldry N and Hepp A. The Mediated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Cambridge: John Wiley &Sons, 2018, pp. 5.以法理认定与重构因果关系。因而,计算法学实证研究不能停驻于数据统计分析和建模,其背后隐含着法律计算与新行为主义法学的意义关联,需在理论解释的价值关照中证成。
在规制论层面,数字时代新一轮科技与产业革命造成人类活动在线上虚拟空间与线下物理世界深度融合,致使大数据、信息、隐私有序地成为法律规制基石,(34)参见申卫星:《数字权利体系再造:迈向隐私、信息与数据的差序格局》,载《政法论坛》2022年第3期。并以此衍生出数据安全与权利、算法规制、人工智能著作权等新兴科技的法律规制问题。这不能仅通过法规范的教义分析来应对问题和挑战,还应置于数字空间作出理性回应,以实现对数字权力和权利的支配与控制,并为数字中国建设加以规范和保障。展言之,首先,从数字空间的人造性来看,人为制造的虚拟数字世界虽超越维度地扩展人类活动空间,但亦使空间创造者实质拥有掌控秩序的权力,那么法律规制就应转向数字空间的实际控制人;其次,从数字空间的互构性来讲,随着技术越来越成为人类生活生产的重要变量,由元宇宙等所构成的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联系日益紧密,则数据、算法等新兴技术亦会反塑现实,故而法律规制就应转从“虚拟—现实”双重规制,将平台等不同场景兼纳其中;最后,从数字空间的时空性而言,透过感知系统将现实空间反应至数字空间,且在云计算等技术加持下动态实时地处理大数据,使数字空间得以映射至图形空间与构建“数字孪生”(35)数字孪生(Digital Twin)是一种数字化的理念和技术,基于数据和模型,并集成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的模拟仿真系统,能根据数据实验反馈动态调整从而真实揭露物理实体的真实变化。的智能空间,因而数字空间的法律规制面临着个体与互动适应性、个体与数字强异质性等问题。为此,数字时代法律规制不能再随便套用工业时代法学知识,而应在进一步厘清法律与科技界限、人机界限的基础上,以计算法学构建完整的数字法治秩序,完善数字空间治理模式,探索现代化治理路径。
在数字化领域,法律科技为法律问题数字化与智能化创造了更大可能,我国法律科技当推“智慧法院”“法律可视化”和“法律智能系统”。其中,智慧法院核心系通过机器学习、人工智能法律推理提供规则适用指引、类案推送等功能。法律可视化是结合图论把复杂法律关系、行为结构等以图像形式直观表达。法律智能系统最初源于计算机对法律文本分类梳理,随后FOLAW、LRI-Core等智能系统迭代发展,通过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本文分析等技术不断创新。然而,“自由意志和社会变革等基本因素往往使决策者和影响者的行为无法准确预测”。(36)Frank Pasquale, Glyn Cashwell. Prediction, persuasion, and the jurisprudence of behaviourism. University of Toronto Law Journal, 2018, 1:63-81.法律科技在发挥提升整体效率效能的同时亦有所局限,或面临因数据、算法造成的主观偏见与理解偏差,或因法律语言模糊性以及时间、场景和类型的转换而降低法律文本计算精确性,(37)Theodore Bach. Same-tracking real kind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Synthese, 2022, 200(2):118.或因可视化图像简化而导致法律关键信息隐藏丢失、表达关系信息扭曲,等等。就目前法律科技实践观之,法官判案的能动因素与智能系统的数据、算法偏见等问题难以完全克服。因而,法律科技只能代替重复性劳动,以作减轻工作量、提高效率、促进沟通理解之用。但长远来看,法律问题数字化需要计算法学不断调适法律人工智能的算法模型和完善智能系统,从法律科技实践中提炼数字法治的思维方式,推进法律思维与计算思维的融合。须指出的是,法律数字化领域的特殊性还在于规则与算法的互动。计算法学还需进一步关注法律科技的正当性与规范性问题,完善数字法治的规范制度建构,提高其适应性与规制合理性。
(三)法理层面:计算法学研究范式的理论基设
数字时代计算法学在实践中还需进一步构建研究范式的理论基设。计算法学的概念话语、逻辑路径固然触及计算法学研究范式的形态、架构等方面,然深嵌于计算法学内部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前提,更为著力构建之本。即对数字信息文明中关涉数字权力、权利的支配与控制与数字法治作根本性价值理解。于此看来,科学技术在不断瓦解现代性的同时也在不断重构现代性,那么人与科技的关系就触及数字法治的底层逻辑。列奥施特劳斯指出,科学技术应在法律与道德、伦理与政策的控制下有序发展,否则将对权利造成灾难性侵害。(38)参见[美]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4页。从“信息茧房”将视野束缚于既定信息而使自由意志受影响,到人脸识别技术滥用致使基本权利受侵害,再到因算法偏见而造成的歧视与不公正对待,还有老年人等弱势群体难以逾越数字技术鸿沟,等等。这些问题实乃数字法治之前提性问题,即如何实现数字正义,为数字权利保障提供基本的支持。就此,作为计算法学研究范式理论基设的数字正义就是对其元命题、元理论、元叙事的法理阐释,具有为数字法治实践发挥超越时空限制的共时性指导意义。
以构建我国的计算法学研究范式观之,数字正义的理论基设需关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数字治理的三个前提:其一,在历史发展中人与科技的关系曾使人“沦为机器的附庸”,(3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7页。甚至引发法治危机,故在“回到马克思”语境下重构人与科技的关系,对阐释数字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其二,不同于传统法治社会,大数据世界的一切都将被数字化、标签化,且数据和技术若不受拘束可能造成难以控制的社会效应,(40)See Yannis Theocharis, Andreas Jung Herr. 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 and the Study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2021, 38:1-22.故数字时代还需强调公平正义、伦理道德、技术向善作计算法学的理论基础。其三,因数字空间的人造性与互构性使平台等成为数字生活新兴主体,建基于此的数字法治就需更具开放性和包容性以面对智能社会的复杂问题。因而,探索适应多元数字主体、多元规制路径的数字法治成为实现数字正义的实践必然。为此,计算法学的数字正义课题蕴含着技术向善、数据包容、协同共治等要求。具言之,计算法学视域下的协同共治强调数字世界中平台等多元数字主体以及法律、算法代码等多元规制手段都应于共生的空间中发展。即以刚性的法律、柔性的道德伦理和中性的技术推进复杂工程的数字治理。经由建立多元主体、规则形式的兼容系统和良法善治的共治结构,借以推进法律制度与数字科技的深度融合、发挥技术基础性作用与法律保障性机制,使法律和算法代码相辅相成,促进数字治理与数字经济的良性循环。另一方面,由于全球数字服务中数据流通涉及个人、企业、社会与国家,跨越国内与国际,故而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语境下为实现数字正义的计算法学就需保障数据安全和自由流通,在大数据、隐私和信息的差序格局中建构数据所有权、使用权、用益物权、管辖权等权利体系,并以数据包容为理念不断实现数据资源优化配置与完善数字权利保障机制。(41)参见周尚君、罗有成:《数字正义论:理论内涵与实践机制》,载《社会科学》2022年第6期。最后,数字正义意味着计算法学研究范式还须赓续现代法治的公平正义、人权保障等价值理念。即计算法学不能对普适性价值置之不理,其内在价值亦非随科技进步而不断变化,否则将导致计算法学研究范式蕴含的正义价值逐渐模糊化。因而,技术中立不是计算法学的当然立场。其必须以技术向善为价值基础,必须反对数字领域的技治主义倾向,必须强调人的主体性价值地位,进一步保障数字权利和维护公平正义,否则人类将因技术而反噬自身。总而言之,计算法学研究范式以数字正义为其理论基设,在法律与科技的互动实践中完善规范体系,在面向人与科技关系的理论问题上彰显价值关怀,在探讨构建数字法治秩序的现实问题上体现法理阐释,不断提升新法科计算法学的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