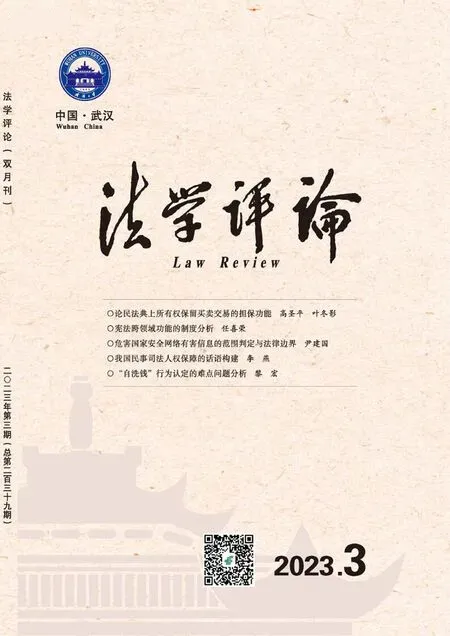论民法典上所有权保留买卖交易的担保功能*
高圣平 叶冬影*
一、问题的提出
依据我国《民法典》的规定,买卖合同为典型的双务、有偿合同,买受人负有支付价金的主给付义务,而出卖人负有交付标的物并转移所有权的对待给付义务。在出卖人交付标的物但买受人未给付价金的情况下,出卖人的价金债权即面临着不获清偿的风险,不利于买卖交易的达成和展开。买卖双方通过所有权保留条款约定,在买受人未给付价金或者履行其他义务之前,标的物的所有权由出卖人保留,出卖人的价金债权借由所有权的强势效力得到了有效的保障。(1)参见王立栋:《〈民法典〉第641条(所有权保留买卖)评注》,载《法学家》2021年第3期;王洪亮:《所有权保留制度定性与体系定位——以统一动产担保为背景》,载《法学杂志》2021年第4期。如此,所有权保留买卖交易的社会机能除了促进商品的销售之外,通过在所有权移转效力上附加条件(给付价金或者履行其他义务)的方式,达致担保标的物价金债权清偿的效果。(2)参见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释义》(上),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405页。这一精巧的交易结构一经运用,即发挥了巨大的信用供给功能。(3)参见王轶:《论所有权保留的法律构成》,载《当代法学》2010年第2期。
在优化营商环境的大背景之下,统一动产抵押、所有权保留买卖、融资租赁、让与担保、保理等各种动产担保交易形式的交易规则,就成了民法典编纂过程中的重大任务。(4)参见高圣平:《民法典担保物权法编纂:问题与展望》,载《清华法学》2018年第2期;罗培新:《世界银行“获得信贷”指标的法理分析及我国修法建议》,载《环球法律评论》2019年第2期;纪海龙:《世行营商环境调查背景下的中国动产担保交易法》,载《法学杂志》2020年第2期。在尊重当事人之间就融资担保交易结构的合意安排、维系各种动产担保交易在形式上的区分的基础上,《民法典》对《合同法》上所有权保留买卖交易规则作了相应完善。其一,明确将所有权保留买卖合同纳入担保合同的范畴(第388条第1款),承认其担保功能;其二,就出卖人的所有权采行登记对抗主义(第641条第2款);其三,在买受人违约之时,出卖人有权取回标的物,但出卖人取回后尚得容许买受人回赎,买受人不回赎的,出卖人即可再另行出卖标的物,并以变价款清偿价金债务,实行“多退少补”(第642条、第643条)。这些规则无不受到功能主义立法模式的影响。但在既有的物债二分、所有权绝对的体系中,嵌入功能主义元素,产生了诸多概念与体系上的冲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以下简称《民法典担保制度司法解释》)就这些冲突提出了部分解决方案,明确所有权保留买卖交易中如下几个方面适用或者准用担保物权制度的相关规定:“一是有关登记对抗的规则;二是有关担保物权的顺位规则;三是有关担保物权的实现规则;四是关于价款优先权等有关担保制度”。(5)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21年版,第43页。但不无遗憾的是,与《民法典》同步实施的另两部司法解释却作出了与此不同的司法政策选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买卖合同司法解释》)仍然保留了《民法典》编纂时未采纳的“买受人已经支付的价款达到总价款的75%时,出卖人不得行使取回权”的限制规则(第26条);(6)同前注②,黄薇书,第408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以下简称《企业破产法司法解释二》)仍旧依循形式主义进路处理相关的争议问题(第36条、第37条和第38条)。(7)参见邹海林:《所有权保留的制度结构与解释》,载《法治研究》2022年第6期。这两部司法解释中的相关规定并未准确把握《民法典》上新规则的功能化转向,增加了本已争议不断的规则冲突的解释难度。本文不揣浅薄,拟就《民法典担保制度司法解释》起草中的争议问题一陈管见,以求教于同仁。
二、所有权保留买卖交易的功能化转向
所有权保留买卖交易等以所有权作为担保工具的交易是否应纳入动产担保交易制度中予以统一规范,是国际统一实体法运动中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鉴于所有权保留买卖交易不同于担保交易的形式上的结构安排,多数国家和地区的解决方案是将其排除于担保交易之外。在既有的物权概念体系之下,担保物权系在他人财产上设定的以担保主债权得以实现的物权,而所有权保留买卖交易中出卖人所保留的是所有权。如此,出卖人是标的物的“真正所有人”,而不是担保物权人。在这一以交易形式为规则架构基础的形式主义立法观念之下,如买受人未能及时清偿价金,出卖人所关注的不是就标的物强制执行而使其债权得以受偿,而是基于其就标的物的所有权而主张恢复对标的物的占有。(8)See Jan H. Dalhuisen, Dalhuisen on Trans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Commercial, Financial and Trade Law Volume 5:Financial Products and Services, 8th ed.,Oxford: Bloomsbury Publishing Plc, 2022,p.26.如此,尽管所有权保留买卖交易中出卖人的所有权起着担保价金清偿的作用,但通常受合同法调整,容许当事人的自主安排,并不受担保物权公示要件及其他规则的约束。
相反的做法是将所有权保留买卖交易纳入动产担保交易法的调整范围,将之等同于担保交易。其理念在于,具有相同经济功能的融资担保工具应被同等对待,摒弃各类动产担保交易形式彼此之间的区分,适用统一的设立、公示、优先顺位和违约救济制度。在这里,传统意义上形式主义的概念化并不重要,起决定作用的是交易的效果,而不是其形式或者权益产生的方式。(9)See William L. Tabac, 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Title under the Uniform Commercial Code, 50 Maryland Law Review 408, 409(1991) .功能主义的立法方法旨在确保动产担保交易制度的全面性、一致性和透明度,将出卖人、出租人和贷款人等信用提供者置于公平的竞争环境之中,并减少债权人为应对各种融资担保工具之间不同的尽调要求,从而降低整体交易成本。(10)See 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UNCITRAL Legislative Guide on Secured Transactions, New York:United Nations, 2010, pp.23、56.这种立法方法在概念上的简洁性,以及统一的规则体系所带来的交易效率的提升和交易成本的降低,广受赞扬,但也不乏批评意见。基于交易的担保目的和实质,即将债权人就标的物的权利重新定性为担保物权,改变了当事人的交易安排和既定的物权结构,破坏了物权法定主义。不过,“尽管[功能主义]很复杂,语言不熟悉,风格也很陌生,但即使不作为区域性和国际性动产担保交易法改革的典范,也可能发挥重要的思想来源作用。”(11)Harry C. Sigman, Security in Movables in the United States-Uniform Commercial Code Article 9:a Basis for Comparison , in Eva-Maria Kieninger,ed., Security Rights in Movable Property in European Private Law,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54.
据此,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动产担保交易立法指南》和《动产担保交易示范法》采取功能主义立法方法,将所有权保留买卖交易纳入动产担保交易的调整范围,明显倾向于对购置款融资工具采取所谓的“统一处理法”。但考虑到一些欧洲国家的反对意见,也允许对所有权保留买卖交易等购置款融资工具采取“非统一处理法”,将其中的标的物所有权明确归属于出卖人。但即使采取“非统一处理法”,这些权利亦应“适用与购置款担保权功能等同的规则,从而确保购置款融资的所有提供者均得到平等对待”。(12)See 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supar note , p.63.《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DCFR)同样采取了折中路线,在采纳功能主义立法方法的同时,并没有将保留所有权交易纳入统一的担保物权概念之中。就起草者看来,支撑这种担保工具的法律概念是基于债权人保留完整的所有权。(13)See Selma de Groot, Three Questions in Relation to the Scope of Book IX DCFR,in Sjef van Erp,Arthur Salomons ,Bram Akkermans, eds.,The Future of European Property Law, Munich: sellier european law publishers GmbH, 2012,p.139.该草案第九卷在尊重欧洲既有法律传统的基础上,明确区分了担保物权与保留所有权交易,但这一区分仅在两个领域才有意义:担保物权的设立及担保物权的实现。在其他领域,如对抗第三人效力、优先顺位、违约前的救济及解除,保留所有权交易事实上与担保物权并无区别,均适用统一的规则。(14)See Ulrich Drobnig ,Ole Böger,eds., Proprietary Security in Movable Asset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230.
如此看来,是否完全采纳功能主义的立法方法,最终还是取决于立法者的政策选择,在简洁、效率与合同自由之间寻求平衡。吸收功能主义的合理元素,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将所有权保留买卖交易重新定性为担保交易,也不意味着在所有方面均适用于担保交易相同的规则,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如何在其他关键问题上形塑动产担保交易制度,如公示、优先顺位和权利实现等。(15)See Anna Veneziano, A Secured Transactions’ Regime for Europe: Treatment of Acquisition Finance Devices and Creditors’ Enforcement Rights, 14 Juridica International, 89(2008).另参见纪海龙:《民法典动产与权利担保制度的体系展开》,载《法学家》2021年第1期。如此,功能性的形式主义则成了动产担保交易法制改革的可选路径之一。(16)See Roderick A Macdonald, Article 9 Norm Entrepreneurship, 43 Canadian Business Law Journal 240, 254-255, 288 (2006).
我国《民法典》尊重当事人基于自主意愿架构交易结构的合同自由,将所有权保留买卖交易中出卖人就标的物的权利界定为所有权。但是,《民法典》第388条第1款中又规定,“担保合同包括抵押合同、质押合同和其他具有担保功能的合同”。这里的“其他具有担保功能的合同”包括所有权保留买卖合同。(17)参见王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的说明——2020年5月22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20年特刊。亦即虽然所有权保留买卖合同不是典型的担保合同(抵押合同、质押合同),但基于其具有明显的担保功能,也就被视为担保合同,出卖人所保留的所有权也就被视为担保物权。(18)参见王利明:《担保制度的现代化:对〈民法典〉第388条第1款的评析》,载《法学家》2021年第1期;高圣平:《动产担保交易的功能主义与形式主义——中国〈民法典〉的处理模式及其影响》,载《国外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如此,我国《民法典》采取了功能性形式主义的立法模式,这也增加了相关规则之间解释上的困难。
第一,在形式主义进路之下,在买受人未给付价金或者履行其他义务之前,标的物的所有权归属于出卖人。在《民法典》既定的动产物权变动公示原则(第208条、第224条)之下,出卖人就普通动产的所有权无须登记,即可对抗第三人,此为《民法典》第114条所规定的物权概念使然。但《民法典》又在第641条第2款规定,“出卖人对标的物保留的所有权,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其规范目的在于是消灭隐形担保、维护交易安全,其前提是“被保留的所有权并非一个真正的所有权,在各个属性上与担保物权越来越接近”。(19)同前注②,黄薇书,第405页。据此,《民法典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第67条明确指出,所有权保留买卖交易中未经登记的出卖人所有权不得对抗的第三人范围及效力,参照动产抵押权的相关规则处理。如此即导向功能主义。
第二,在形式主义进路之下,当买受人违约之时,出卖人自可基于其对标的物的所有权主张取回权(《民法典》第642条第1款)。出卖人取回标的物是基于其所有权,本无就标的物的剩余价值与未受清偿的价金债权之间进行清算的义务。不过,《民法典》第642条第2款和第643条的文义表明,除非当事人之间另有约定,出卖人取回标的物之后尚有清算义务,不能保有标的物的剩余利益。就此而言,出卖人所保留的所有权仅具形式意义,更多的是作为担保目的而存在,功能主义转向至为明显。
第三,在形式主义进路之下,买受人就标的物并无处分权,未经出卖人同意,自无权转让标的物或者在标的物上为他人设立担保物权(《民法典》第642条第1款第3项),第三人仅得在构成善意取得的情形之下才能主张其对标的物的所有权或者担保物权。(20)参见周江洪:《所有权保留买卖的体系性反思——担保构成、所有权构成及合同构成的纠葛与梳理》,载《社会科学辑刊》2022年第1期。但是,《民法典》的相关规则显示,出卖人保留的所有权的效力仅限于就标的物价值优先受偿,标的物的所有权还是基于法律的拟制移转给了买受人。(21)参见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七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21页。如此,买受人就标的物即有了处分权,《民法典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第56条和第57条即据此将正常经营活动中的买受人规则及超优先顺位规则准用于所有权保留买卖交易。由此看来,《民法典》改变了所有权保留买卖交易中出卖人与买受人之间的权利结构,进一步体现着功能主义转向。
综上所述,我国《民法典》采行功能性的形式主义,一方面确认所有权保留买卖交易作为典型交易而存在,明定其中出卖人就标的物享有所有权,另一方面又强调所有权保留买卖交易的担保功能,在登记对抗、权利实现等方面向动产抵押权靠拢,相关规则彼此之间的冲突较为明显,尚须经由解释消解这些冲突。
三、物权法定主义与所有权保留买卖交易的功能性形式主义
“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规定。”我国《民法典》第116条所确立的这一物权法定原则,仍然是民法典财产权体系化的工具,也是《民法典》物权编与合同编分别设置的基础。这一体系结构安排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功能主义的产物。在提取公因式、总分结合的立法技术之下,《民法典》将类似的概念统一在总则、小总则(如“物权”编之“通则”分编、“担保物权”分编之“一般规定”等)之下,并为某些特定的交易模式增加具体的、特别的规则(如“担保物权”分编之下的“抵押权”“质权”等)。《民法典》将法政策上确定为物权的权利之中所有具有担保功能的相似概念统一在“担保物权”的元概念和标题之下,至少与功能主义立法方法非常相似。但当涉及基于所有权的担保交易之时,民法典上的功能主义就到了极限。
依据《民法典》第641条第1款的规定,所有权保留买卖交易中,在买受人给付价金或者履行其他义务之前,标的物的所有权由出卖人保留。在物权法定原则之下,所有权这一“物权的种类”自有其法定的“物权的内容”。依据《民法典》第240条的规定,所有权的内容体现为,权利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有学者即据此认为,出卖人在所有权保留买卖交易中对标的物的所有权,即使在经济意义上具有保全价款债权的功能,但也缺乏担保物权在“种类”“内容”“设立”乃至“法效”等方面的物权法定主义基本元素。物权法定主义决定着功能主义发挥解释作用的空间,《民法典》第641条至第643条规定的所有权保留买卖制度,不具备将保留的所有权“功能化”为担保物权的条件。(22)同前注⑦,邹海林文。尽管基于《民法典》第388条第1款“担保合同包括……其他具有担保功能的合同”的规定,以标的物所有权为基础的担保合同自可作为担保物权的发生依据,但在体系上,它确实与《民法典》将所有权赋予出卖人相抵触,(23)参见谢鸿飞:《〈民法典〉实质担保观的规则适用与冲突化解》,载《法学》2020年第9期。存在过度干涉当事人合同自由之嫌。(24)参见冯洁语:《民法典视野下非典型担保合同的教义学构造——以买卖型担保为例》,载《法学家》2020年第6期。
本文作者认为,尽管《民法典》将所有权保留买卖交易中出卖人保留的权利界定为“所有权”,并非物权法定主义之下“担保物权”,但是这一“所有权”已经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完全所有权,已如前述。《民法典》第240条关于所有权的定义性法条为所有权的类型化提供了依据。其中的“依法”表明所有权人行使其所有权并非绝对自由,而须受法律规定的限制。(25)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物权编理解与适用》(上),人民法院出版社2020年版,第209页。针对不同类型的所有权,“依法”一语意味着法律上所规定的限制也就不尽相同。如业主行使其所有权不得危及建筑物的安全,不得损害其他业主的合法权益(《民法典》第272条);处分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及对共有物,应当经占份额2/3以上的按份共有人或者全体共同共有人同意(《民法典》第301条)。如此,在法律上对所有权保留买卖交易中出卖人所有权的内容作出限制,亦属当然。
《民法典》事实上已经将所有权区分为完全所有权与担保性所有权两种类型,(26)参见张家勇:《体系视角下所有权担保的规范效果》,载《法学》2020年第8期;同前注①,王立栋文。赋予了两种所有权不同的内容。一如抵押权之下不动产抵押权与动产抵押权的区分、一般抵押权与最高额抵押权的区分,虽然均为抵押权,但其内容上却存在着差异。就所有权保留买卖交易中出卖人的担保性所有权,《民法典》上规定的区别于完全所有权的内容举其要者有:
第一,《民法典》第641条第2款关于“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的规定,已经表明所有权保留买卖交易中出卖人的所有权并不具有所有权的完整权能。出卖人的所有权在未予登记的情形之下,不得对抗抵押权人、质权人、善意受让人、善意承租人、查封扣押债权人、破产管理人,(27)参见高圣平:《民法典动产担保权登记对抗规则的解释论》,载《中外法学》2020年第4期;同前注①,王洪亮文。亦即此时的所有权并不得对前述权利人就标的物主张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出卖人的所有权即使已行登记,也不具备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能,(28)就处分权能,尚存解释上的分歧。同前注,周江洪文;同前注①,王洪亮文。依据《民法典》第641条第1款,出卖人保留的所有权只为一个目的而存在:确保买受人给付价金或者履行其他义务,(29)同前注①,王立栋文。也就体现为出卖人对标的物交换价值的直接支配性和排他性。如此,出卖人除就标的物价值依法享有优先受偿权外,不享有基于完全所有权的其他权能,即出卖人的担保性所有权表现为单面性的价值权属性。(30)同前注,张家勇文。
第二,《民法典》第642条、第643条所规定的“取回-回赎-再出卖-清算”的出卖人权利救济规则,已经不同于完全所有权。在完全所有权之下,所有权人自可基于《民法典》第235条规定的所有物返还请求权而主张取回标的物。如此,所谓取回权仅仅只是所有物返还请求权的一种体现,所有权人据此取回标的物之后,并无法定的清算义务。但在所有权保留买卖交易中,买受人未给付价金或者未履行其他义务之时,出卖人取回标的物的,无论依据第642条第2款“参照适用担保物权的实现程序”,还是依据第643条第2款在买受人未回赎之时的另行出卖标的物,均须适用清算法理,即“出卖所得价款扣除买受人未支付的价款以及必要费用后仍有剩余的,应当返还买受人;不足部分由买受人清偿”。(31)同前注①,王立栋文。如此,出卖人据以取回标的物的基础权利——担保性所有权的内容与效力已经不同于完全所有权,出卖人的取回权行使程序及清算义务均清楚地表明出卖人的担保性所有权的价值权属性。
第三,虽然物权变动的公示方法并非物权法定原则的当然内容,(32)参见常鹏翱:《物权法定原则的适用对象》,载《法学》2014年第3期;同前注,张家勇文。但《民法典》第641条第2款规定的出卖人所有权的登记对抗规则,已与《民法典》第208条和第224条所确立的动产物权变动公示的一般规则不一致。动产所有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民法典》第224条)。出卖人就标的物的所有权,并非基于所有权保留买卖合同而取得,而是基于此前的生产或者交易而取得,如此,所有权保留买卖交易中在买受人给付价金或者履行其他义务之前并不存在物权变动,也就无须满足物权变动所需的公示要件。(33)同前注,张家勇文;同前注,周江洪文;同前注⑦,邹海林文。但是,在所有权保留买卖交易成立之时,出卖人原本享有的完全所有权即转化为担保性所有权,由此即受担保物权公示要件的约束。(34)参见刘竞元:《民法动产担保的发展及其法律适用》,载《法学家》2021年第1期。在所有权保留买卖交易中,占有标的物的事实状态已经无法起到公示标的物之上的权利负担的作用。如不采取登记公示方法,第三人尚须付出巨大的调查成本以探知标的物上的真实权利现状,势必损害交易安全。(35)同前注②,黄薇书,第405-406页。《民法典》第641条第2款的规定与同属价值权的动产抵押权的登记对抗规则相统一,进一步强化了出卖人的担保性所有权不同于完全所有权的特性。(36)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理解与适用》(二),人民法院出版社2020年版,第616页;刘保玉:《民法典担保物权制度新规释评》,载《法商研究》2020年第5期;同前注,纪海龙文。
综上,《民法典》已经明确地表达了所有权保留买卖交易中出卖人所有权的特定权利内容。从本质上而言,所有权保留买卖交易中的所有权被限定为特定目的的所有权,更多地服务于所有权的担保功能,(37)同前注,周江洪文。彰显了其中价值权属性和担保物权效力元素,解决了物权法定主义之下完全所有权与担保性所有权之间的龃龉。由此可见,所有权保留买卖交易中出卖人所有权的特殊内容已由《民法典》明确规定,并不与物权法定原则形成真正的冲突。(38)同前注,张家勇文。
四、买受人的法律地位与标的物的转让
在所有权保留买卖交易中,出卖人保留的所有权属于担保性所有权,仅具有担保功能。如此,买受人的法律地位也就不仅仅只是买卖合同之下的债务人(给付价金或者履行其他义务)和债权人(请求移转标的物所有权)。在买受人给付价金或者履行其他义务之前就标的物究竟享有何种性质的权利,对于判定买受人处分标的物的法律效果以及确定性地解决由此而生的权利冲突至关重要。
(一)买受人对标的物的处分权
虽然法律改革家们认为,在所有权保留买卖交易等所有权融资工具中,所有权的归属并非确定动产担保交易的核心要素。在制定法律之时完全可以就所有权归属不作明确规定,仅在设立、公示、对抗效力、优先顺位、权利实现等方面作出类似于动产担保物权规则的规定即可,以此回避所有权担保交易的重新定性问题。(39)See Roderick A Macdonald, supar note , at 254-255; Anna Veneziano, supar note, at 89.但就我国《民法典》关于所有权保留买卖交易的既定规则而言,设立、公示、对抗效力及权利实现等方面的规则已与动产抵押规则相趋同,但就动产抵押权的优先顺位规则(包括一般规则和超优先顺位规则)是否可得准用于或者类推适用于所有权保留买卖交易,尽管《民法典担保制度司法解释》已经做出相应的政策选择,但仍然颇受质疑。(40)同前注,周江洪文;同前注⑦,邹海林文。如此,在解释论上首先确立所有权保留买卖交易中买受人就标的物的处分权或者所有权,就显得尤为重要。
基于功能性形式主义进路,我国《民法典》一方面将标的物的功能性所有权的权利人确定为出卖人,另一方面并未明确规定买受人就标的物享有何种权利。但是,其中相关规则还是可以推断出:买受人实质上享有标的物的所有权或者处分权。
第一,依据《民法典》第641条第2款和《民法典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第67条、第54条的规定,出卖人对标的物保留的所有权如未经登记,不得对抗买受人的查封、扣押债权人和破产管理人。此时,标的物的全部价值归于买受人的全体债权人,出卖人仅得就其无担保的价金债权与买受人的其他债权人依法分配标的物的价值。如此,标的物的所有权在解释上归属于买受人,否则无法解释买受人的其他债权人(查封、扣押债权人和破产管理人)缘何能够参与标的物的价值分配。
第二,《民法典》第643条确立了出卖人权利实现时的清算义务,标的物超出价金债务的剩余利益均归买受人所有。由此表明,出卖人就标的物的权利仅限于未获清偿的价金债权,标的物所有权除去价金债权的部分必须由买受人保有。“既然规定出卖人得就自己之物变卖求偿,则法律拟制标的物之所有权已移转于买受人。”(41)同前注,王泽鉴书,第221页。只不过买受人的所有权上负有出卖人的担保负担。(42)See Ronald C.C. Cuming, Catherine Walsh ,Roderick J. Wood,Personal Property Security Law, 2nd ed.,Toronto, ON: Irwin Law Inc., 2012,p.256;参见纪海龙:《民法典所有权保留之担保权构成》,载《法学研究》2022年第6期。如买受人届时给付了价金或者履行了其他义务,则该担保负担消灭,买受人确定地获得标的物的所有权。(43)同前注①,王立栋文;同前注①,王洪亮文。
第三,我国民法典上已经允许未来财产设立担保,(44)参见谢鸿飞:《动产担保物权的规则变革与法律适用》,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20年第4期。参见谢在全:《担保物权制度的成长与蜕变》,载《法学家》2019年第1期。《民法典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第53条规定:“当事人在动产和权利担保合同中对担保财产进行概括描述,该描述能够合理识别担保财产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担保成立。”这一规定为未来财产进入融资担保领域提供了技术工具。所有权保留买卖交易中,买受人一旦依约定给付价金或者履行其他义务,即取得标的物的完全所有权。如此,买受人自可在法律上处分其未来取得所有权的标的物,亦即无论买受人转让标的物或者在标的物上设立担保物权,均属有权处分。(45)同前注①,王立栋文。
如此看来,在所有权保留买卖交易中,不管出卖人是否授权或者同意买受人处分标的物,买受人就标的物的处分均属有权处分。正是基于此,《民法典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第67条才作出了所有权保留买卖交易中出卖人的所有权未经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的范围及其效力参照动产抵押权规则处理的规定;第56条、第57条才作出了所有权保留买卖交易同样准用正常经营活动中的买受人规则和超优先顺位规则的政策选择。但不无遗憾的是,《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26条第2款规定:“在民法典第642条第一款第三项情形下,第三人依据民法典第311条的规定已经善意取得标的物所有权或者其他物权,出卖人主张取回标的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这一规则以所有权保留买卖交易中买受人无处分权为基础,采纳了以无权处分为前提的善意取得构成,(46)同前注,周江洪文。至为可议。在体系解释上,《民法典》第642条第1款第3项所规定的买受人“将标的物出卖、出质或者作出其他不当处分”,不宜解释为从归属意义上标的物的所有权人还是出卖人,(47)相反意见参见前注,张家勇文。而应被解释为只有“不当的”出卖、出质或其他处分“造成出卖人损害”时,出卖人才能行使取回权(实质上系实现其担保性所有权)(容后详述),(48)同前注,纪海龙文。并不表明买受人没有对标的物的处分权。
(二)买受人转让标的物之时的法律后果
买受人转让标的物之时,出卖人与转得人之间的关系,既受出卖人的担保性所有权是否登记的影响,也受正常经营活动中买受人规则的约束。
1.买受人在其非正常经营活动中转让标的物
出卖人的担保性所有权已经登记的情形之下,买受人转让标的物虽属有权处分,但转得人依动产所有权的物权变动规则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之时,自是受到其上既存的出卖人担保性所有权的约束。如买受人以转得价金清偿债务,出卖人的担保性所有权作为从权利,因其担保的价金债权的消灭而消灭;如出卖人的担保性所有权因买受人的转让行为受到损害,无论是基于出卖人取回权规则,还是类推适用抵押财产转让规则,均能得出出卖人可就标的物主张变价权和优先受偿权的结论。依据《民法典》第642条的规定,此种情形之下,出卖人取回权的行使条件成就,如出卖人与买受人、转得人不能就标的物的取回达成协议,自可参照担保物权的实现程序,主张就标的物优先受偿。与此同时,还可类推适用《民法典》第406条的规定,(49)参见孙宪忠、朱广新主编:《民法典评注·物权编(4)》,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224页;同前注①,王立栋文;孙超:《民法典体系下所有权保留出卖人权利的实现路径与对抗效力——从实体法与程序法结合的视角》,载《人民司法》2022年第25期。出卖人的担保性所有权不因标的物的转让而受到影响,在出卖人取回权的行使条件成就之时,出卖人自可就标的物主张权利;如出卖人的担保性所有权因买受人的转让行为受到损害,出卖人还可主张价金物权代位。
在出卖人的担保性所有权未经登记的情形之下,买受人转让标的物亦属有权处分,如转得人为善意,依据《民法典》第641条第2款的规定,出卖人的担保性所有权不得对抗该转得人,该转得人取得标的物的无负担的所有权。出卖人此际不得就标的物主张优先受偿权,在解释上,标的物上出卖人的担保性所有权消灭。(50)同前注,高圣平文;同前注①,王立栋文;同前注①,王洪亮文。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转得人,应以已依物权变动规则取得所有权者为限。已经签订买卖合同但未受领交付的转得人,在法律地位上仍属债权人,自不属于不得对抗的“第三人”。(51)同前注,高圣平文;同前注,孙超文。但如转得人非属善意,依《民法典》第641条第2款的反对解释和《民法典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第67条的规定,出卖人的担保性所有权并不消灭,仍然可以在权利实现条件成就之时就标的物主张权利。有观点认为,“无论如何,动产抵押情形,并不能仅仅因为抵押人转让标的物就行使抵押权,而所有权保留则是发生取回权的必要充分条件。”(52)同前注,周江洪文。但就《民法典》第642条第1款的文义而言,并非买受人转让标的物,出卖人即可行使取回权,尚须满足买受人转让标的物“造成出卖人损害”的要件。在解释上,买受人转让标的物并不当然“造成出卖人损害”,例如买受人在转让标的物之后,仍然如期依约清偿分期价金债务。此际,仅得在买受人未按照约定给付价金或者完成特定条件之时,出卖人才能就标的物主张权利。
2.买受人在其正常经营活动中转让标的物
动产抵押登记制度的引入,改变了传统法上的动产物权公示方法,直接导致动产交易的相对人尚须查询登记簿才能确定性地保有其利益,这不仅增加交易成本,而且影响交易便捷、害及交易安全。(53)参见刘春堂:《动产担保交易登记之对抗力》,载《物权法之新思与新为——陈荣隆教授六秩华诞祝寿论文集》,台湾瑞兴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版,第379-380页;董学立:《美国动产担保交易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63页。为维护交易安全,《民法典》第404条增设正常经营活动中的买受人规则,明定“以动产抵押的,不得对抗正常经营活动中已经支付合理价款并取得抵押财产的买受人”,通过豁免买受人的查询义务以克服动产抵押制度固有的缺陷。(54)同前注⑤,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书,第484-485页。《民法典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第56条并将正常经营活动中的买受人规则扩张适用至所有权保留买卖交易和融资租赁交易,其理由在于,“《民法典》已将所有权保留买卖和融资租赁中的所有权规定为非典型担保物权,而所有权保留和融资租赁的标的物也是动产,且以登记作为公示方式,因此也存在类似动产抵押制度的局限性。”(55)同前注⑤,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书,第485-486页。
学说上有观点反对这一解释方案。其主要理由在于,所有权保留买卖交易中的买受人并不享有标的物的所有权,其地位与并不因抵押权的设立而丧失处分权的抵押人明显不同。标的物的转得人首先要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始有该标的物上是否附有担保负担的问题。转得人无法依正常经营活动中的买受人规则消灭标的物上的权利负担,而只能依善意取得构成予以处理。(56)同前注,周江洪文。在解释上,《民法典》第404条的“动产抵押”,系指“一般的动产抵押以及浮动抵押”,(57)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物权编释义》,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504页。据此应当排除正常经营活动中的买受人规则对于所有权保留买卖交易的适用。(58)同前注①,王洪亮文。
已如前述,所有权保留买卖交易中出卖人保留的仅为担保性所有权,法律上拟制标的物的所有权已由买受人享有。买受人转让标的物并不构成无权处分,善意取得制度自无适用空间,其法律后果仅存在转得人是否无负担地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问题。在买受人转让标的物构成其正常经营活动的前提之下,转得人并无查询登记簿的义务,自可基于其支付合理价款并取得标的物占有的事实主张免受标的物上既存的出卖人所有权的约束。此时,出卖人不得对转得人就标的物主张所有权,在解释上,标的物上的出卖人所有权因转得人取得所有权而消灭。(59)同前注,谢鸿飞文。
尚存疑问的是,如转得人非为善意,知道标的物上存在出卖人的所有权之时,是否仍有正常经营活动中的买受人规则之适用?《民法典》第404条的文义至为清晰,正常经营活动中的买受人规则并无转得人善意的构成,仅强调转得人“已支付合理对价”。由此可见,该规则的适用并不与善意取得制度相勾连,也不属于善意取得制度在特定场景之下的适用情形。至于第641条第2款所定登记对抗规则明确只保护善意第三人,但就《民法典》第404条与第403条、第641条第2款的适用关系而言,前者属于特别规定,后者属于一般规定,前者自应优先于后者而适用。正常经营活动中买受人规则的适用,并不以出卖人的所有权未经登记为前提。尽管《民法典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第56条第2款指出“前款所称担保物权人,是指已经办理登记的抵押权人、所有权保留买卖的出卖人、融资租赁合同的出租人”,“举重以明轻”,在出卖人所有权已经登记的情形之下,尚不得对抗正常经营活动中的转得人,在出卖人所有权未经登记的情形之下,更不可对抗正常经营活动中的转得人。
五、标的物的抵(质)押与权利冲突的解决
在承认买受人有权处分标的物的前提之下,买受人即有权以标的物为他人设立抵押权或者质权,由此即出现同一标的物之上出卖人的担保性所有权与抵押权或者质权之间的冲突,相关优先顺位规则的适用即有了讨论的余地。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民法典》第642条第1款,买受人“将标的物出卖、出质或者作出其他不当处分”,且“造成出卖人损害”,是出卖人行使取回权的事由之一,但是,出卖人取回标的物之后,尚须按照相应的优先顺位规则分配标的物的变价款。
(一)竞存担保物权之间优先顺位的一般规则的准用
出卖人的所有权具有价值权属性,与抵押权、质权的权利属性大致相当。同一标的物上如存在出卖人的所有权、担保物权人的抵押权或者质权,这些权利的内容均为就标的物优先受偿。基于此,同一标的物上出卖人的所有权与其他债权人的抵押权相竞存之时,自应准用《民法典》第414条第1款所确立的竞存担保物权间优先顺位的一般规则,按照登记时间的先后确定彼此之间的优先顺位:登记的优先于未登记的;先登记的优先于后登记的;均未登记的,顺位平等。(60)参见高圣平:《民法典动产担保权优先顺位规则的解释论》,载《清华法学》2020年第3期;同前注①,王洪亮文。同一标的物上出卖人的所有权与其他债权人的质权相竞存之时,自应类推适用《民法典》第415条的规定,按照登记、交付的时间先后确定彼此之间的优先顺位。(61)参见李运杨:《〈民法典〉动产担保制度对功能主义的分散式继受》,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2年第4期。
有观点认为,尽管出卖人的所有权的功能在于担保价金债权的实现,已与完全意义上的所有权异其内容,但也不能因此得出出卖人的所有权就是担保物权的结论。《民法典》第414条第2款规定的是“其他可以登记的担保物权”,这里的“担保物权”自文义而言并非“所有权”或者“具有担保功能的合同”,因此不能直接得出所有权保留买卖交易中出卖人的所有权适用或者准用该款规定的结论。(62)同前注,周江洪文。
在体系解释上,《民法典》第641条第2款在所有权保留买卖交易中植入了登记制度,“从功能上讲,保留的所有权实质上属于‘可以登记的担保权’”。据此,所有权保留买卖交易“同样可以适用本法物权编第414条的规定”。(63)同前注②,黄薇书,第406页。《民法典》第388条的体系效应之一在于,具有担保功能的交易形式中,债权人就标的物的权利即为功能化的担保物权,并由《民法典》第414条第2款之“其他可以登记的担保物权”所涵盖。(64)同前注,王利明文。
《民法典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的一系列规定采纳了上述观点。其一,第1条“所有权保留买卖……涉及担保功能发生的纠纷,适用本解释的有关规定”的规定表明,“有关担保物权的顺位规则”应予准用于所有权保留买卖交易。(65)同前注⑤,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书,第43页。其二,第56条第2款关于正常经营活动中的买受人规则的适用范围中,将“所有权保留买卖的出卖人”纳入“担保物权人”的范畴。其三,第57条关于超优先顺位规则的具体适用中,将“保留所有权的出卖人”与提供购置款融资的动产抵押权人等量齐观。
(二)超优先顺位规则的类推准用
经济理论表明,给予购置款融资者相对于其他担保权人的超优先顺位,有利于防止对债务人财产的过度控制和促进再融资的展开。(66)See Jan Jakob Bornheim, Property Rights and Bijuralism: Can a Framework for an Efficient Interaction of Common Law and Civil Law Be an Alternative to Uniform Law? Tübingen: Mohr Siebeck, 2020,p.384.其正当性在于,如若不是购置款融资人新注入的信用支持,这些财产就不会进入债务人的财产基础。这一理由显然适用于所有权保留买卖交易中的出卖人和融资租赁交易中的出租人。(67)See Catherine Walsh,‘Functional Formalism’ in the Treatment of Leases under Secured Transactions Law:Comparative Lessons from the Canadian Experience, in Spyridon V. Bazinas,N. Orkun Akseli,eds.,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Secured Transactions Law:Essays in honour of Roderick A Macdonald,Oxford and Portland, Oregon: Hart Publishing, 2017,p.27.从超优先顺位规则的规范目的出发,所有权保留买卖交易中的出卖人是最值得保护的就物信贷的权利人。(68)同前注①,王洪亮文。所有权保留买卖交易中,同样是以标的物担保购置款(买卖价金债权)的清偿,考虑到所有权保留买卖交易的经济目的,而不仅仅虑及其形式上的法律结构,出卖人的购置款价金债权应与抵押权人的购置款贷款债权就标的物的价值进行公平竞争。(69)See Anna Veneziano, European Secured Transactions Law at a Crossroad:The Pitfalls of a ‘Piecemeal Approach’ to Harmonisation, in Louise Gullifer,Stefan Vogenauer, eds., English and European Perspectives on Contract and Commercial Law:Essays in Honour of Hugh Beale, Oxford: Hart Publishing, 2020,p.412.如此,在动产浮动抵押权设定后抵押人又购入新的动产时,无论是在该动产上设立抵押权或者保留所有权的出卖人,还是为动产购置款的偿付提供融资而在该动产上设立抵押权的债权人,均可主张适用《民法典》第416条的规定,就该动产的变价款享有超优先顺位。(70)同前注⑤,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书,第491页。正是基于此,《民法典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第57条将《民法典》第416条所定购置款抵押权的超优先顺位规则扩张适用于所有权保留买卖交易和融资租赁交易。
有学者认为,在物权法定原则之下,所有权保留买卖交易中出卖人的所有权不得被解释为购置款抵押权,在满足《民法典》第642条第1款规定的条件之下,出卖人自可主张取回标的物,并依照《民法典》第643条的规定就标的物行使权利以实现价金债权。(71)参见邹海林:《价款债权抵押权的制度价值与解释》,载《北方法学》2021年第4期。这一观点固守形式主义进路,坚持出卖人是标的物的“真正所有人”,自当优先于同一标的物上的在先担保物权。但我国《民法典》上所规定的出卖人所有权仅具担保功能,基于第642条和第643条仅能得出出卖人可就标的物优先受偿的结论,尚不能当然地认为出卖人的担保性所有权优先于同一标的物上的在先担保物权。
学说上有观点认为,购置款抵押权与所有权保留买卖交易中出卖人的所有权同为优先保障购置款债权的权利,两者之间功能重叠,(72)参见石佳友:《解码法典化:基于比较法的全景式观察》,载《比较法研究》2020年第4期。但法律构成却不同。一则,第641条第2款所确立的出卖人所有权的登记规则并无宽限期的规定;二则,出卖人借由其所有权而主张优先于同一标的物上的担保物权的效力,在买受人不履行给付价金或者其他义务之时享有取回标的物的权利。(73)参见谢鸿飞:《价款债权抵押权的运行机理与规则构造》,载《清华法学》2020年第3期;章诗迪:《价款担保权规范适用的体系性解释》,载《浙江学刊》2021年第4期。在《民法典》第416条消除了出卖人价金债权担保的手段或者条件的欠缺,以法定化和简单易行的制度构造,足以满足出卖人以其在所有权保留买卖交易中的所有权来担保价金债权的非典型担保的所有市场需求。此际,应严格适用物权法定主义,拒绝承认所有权保留等非典型担保的担保物权效力。《民法典》第641条规定的所有权保留与《民法典》第416条规定的价款债权抵押权之间存在制度结构的明显差异,解释上更缺乏消除差异的具体方法,难以实现“同等对待”所有权保留买卖和购置款抵押权的解释目的。(74)同前注,邹海林文。
本文作者认为,尽管我国《民法典》第416条所规定的购置款抵押权对应于比较法上的“Purchase Money Security Interest”(PMSI),但它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独立担保物权类型,而是动产抵押权的特殊优先顺位规则。如将其解释为一种不同于动产抵押权的独立担保物权类型,一则《民法典》上并未就其设立、登记等作出特别规定;二则如未登记或者未在宽限期内登记,其效力若何,不无解释上的疑问。将其解释为动产抵押权的特殊优先顺位规则,则更容易取得体系上的贯通。作为动产抵押权,本采行登记对抗主义,并基于其登记时间取得就标的物受偿的优先顺位,但如该动产抵押权系担保购置抵押财产价金的清偿,且在标的物交付后10日内办理了抵押登记,则该动产抵押权将具有超优先顺位,可以优先于在先公示之其他担保物权。如未在标的物交付后10日内办理抵押登记的,则仅能适用《民法典》第414条所确立的一般优先顺位规则。(75)同前注①,王洪亮文。因此,《民法典》第416条所规定的,并不是不同于动产抵押权的他种担保物权,而仅仅只是动产抵押权的一种特殊的优先顺位规则。(76)不过,从类型化的意义上,尚可认为,购置款抵押权系动产抵押权的亚类型,与非购置款抵押权相对而称,其类型化标准是主债权是否属于标的物的购置款。如此看来,所有权保留买卖交易与《民法典》第416条所规定的超优先顺位规则并不发生功能上的重叠。在解释上,基于《民法典》第642-643条的规定,出卖人仅具有就标的物优先受偿的地位,在《民法典》第414条的规则体系之下,仅得依登记的时间取得相应的优先顺位,并不能优先于在先登记的浮动抵押权。仅仅在满足第416条规定的各要件之下,出卖人就标的物才能取得超优先顺位,优先于在先的浮动抵押权。
六、出卖人权利的救济路径与清算法理的贯彻
担保物权的实现,素有自力救济和公力救济之分,但不管采取何种救济路径,均需在债权人快速和低成本的程序需要与保护债务人和第三人利益之间寻求良好的平衡。(77)See E. Dirix, Remedies of Secured Creditors Outside Insolvency, in Horst Eidenmüller,Eva-Maria Kieninger ,eds., The Future of Secured Credit in Europe,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2008,p.223 et seq.两者之间各有利弊。自力救济虽是国际公约和国际软法文件所倡导的方向,但在标的物由买受人占有的情形之下,基于我国目前的信用现状,出卖人取回标的物必将遇到买受人的阻碍,且受制于清算法理的适用,《民法典》所建构的买受人保障措施略为复杂。公力救济虽能更好地保护买受人的权利,但如公力救济的程序冗长且费用高昂,则可能给出卖人带来不适当的负担。如此,充分地利用实现担保物权案件特别程序的简速裁判功能,改变目前该程序在司法实践中运行不彰的现状,应为契合我国国情的不二之选。
(一)“取回-回赎-再出卖-清算”规则的体系解释
我国《民法典》上所确立的“取回-回赎-再出卖-清算”的出卖人权利实现机制,即为自力救济的程序设计,在本质上也是一种担保物权的实现方式。(78)同前注②,黄薇书,第409-413页;同前注①,王洪亮文。《民法典》在强化出卖人权利的自力救济路径的同时,为买受人和第三人也提供了强制性的保护措施。一则,出卖人的自力取回尚须买受人同意;二则,出卖人取回标的物之后,尚须容许买受人回赎,以继续履行买卖合同;三则,买受人未回赎的,出卖人并不当然保有标的物的剩余价值,尚须履行清算义务,实行“多退少补”。此已与《民法典》上相对禁止流抵(质)契约的立法态度相同。(79)同前注①,王洪亮文。由此可见,我国《民法典》上所确立的出卖人权利实现机制已经不再是基于完全所有权的救济规则,而更接近于担保物权的实现规则。
在《民法典》确立的出卖人权利实现机制之中,出卖人取回标的物不再是其行使所有物返还请求权的体现,而仅仅只是其试图就标的物进行变价的第一步,(80)See Ronald C. C. Cuming, Secured Creditors’ Non-Statutory Remedies:Unfinished Business, 91 Canadian Bar Review 243 ,257(2013).一方面是造成买卖人心理上的压力,督促买受人及时清偿价金债务;另一方面是保障出卖人顺利变价标的物,以寻求权利的自力实现。(81)参见武腾:《〈民法典〉的权利实现规定与司法程序配置》,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2年第1期。由此而见,出卖人取回制度,“应解释为系出卖人就物求偿价金之特别程序”。(82)同前注,王泽鉴书,第166页。其一,从《民法典》第642条、第643条的规范目的来看,出卖人保留所有权的目的,仅在于确保价金债权的受偿,出卖人就标的物的所有权的内容,已经转化或者缩小为对标的物交换价值的支配,实质上仅具有担保物权的作用,已如前述。其二,出卖人取回标的物,只是导致买受人占有的丧失,并不是解除当事人之间的买卖合同,买受人的价金给付义务仍然存在,出卖人仍得就标的物变价,从而使买受人的价金给付义务得以全部或者部分消灭。如此,出卖人取回标的物仅系出卖人就标的物主张实现其价金债权的程序之一。其三,就所有权保留买卖交易中出卖人的缔约目的而言,出卖人既已出卖标的物予买受人,其所关心者也就在于如何使其价金债权得以足额清偿。如此,出卖人就标的物主张其价金债权的获偿,合于买卖合同系以自己的财产换取他人金钱的本来意旨。(83)同前注,王泽鉴书,第220-221页;刘春堂:《动产担保交易法研究》(增订版),作者1999年自版,第158-159页。至于既然出卖人本属标的物的所有权人,为何还要就自己之物变价受偿之质疑,(84)同前注,王泽鉴书,第220-221页。正是基于《民法典》上就所有权保留买卖交易中出卖人的所有权作出了不同于完全所有权的规定,出卖人取回标的物之后,即不能保有标的物的剩余利益,规定出卖人仅得就标的物优先受偿,更是还原其担保性所有权的本来内容。“只有将保留所有权按照担保权来把握,才能解释出卖人为何需要就‘自己所有之物’进行变价求偿。”(85)同前注,武腾文。
我国《民法典》上就所有权保留买卖交易的法政策上的调整,同样也影响着出卖人所保留的所有权在买受人破产清算时的实现机制。由于出卖人就标的物仅享有担保性所有权,并不享有完全所有权,其效力仅限于就标的物优先受偿。由此而决定,在买受人破产清算之时,出卖人仅得主张破产别除权,不得主张破产取回权。(86)参见章诗迪:《民法典视阈下所有权保留的体系重构》,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2年2期;同前注,李运杨文。不无遗憾的是,《企业破产法司法解释二》第2条仍然规定所有权保留买卖交易中的标的物不属于债务人财产;第37条及第38条仍然以破产取回权为基础架构出卖人的权利实现。从与破产财产的关系来看,破产取回权和破产别除权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破产取回权的标的物之剩余利益不属于破产财产。(87)参见徐小庆:《论所有权保留中出卖人之破产取回权》,载《上海法学研究》集刊2021年第22卷,第127页。在所有权保留买卖交易中,标的物的剩余利益并不由出卖人保有,反而归属于买受人及其破产债权人,已如前述。由此可见,出卖人并不享有破产取回权。如此,结合《民法典》第641条第2款所规定的登记对抗规则,在出卖人所有权已经登记的情形之下,出卖人可以申报有担保债权;在出卖人所有权未经登记的情形之下,出卖人仅得申报无担保债权。
(二)出卖人权利的实现条件
在将出卖人取回权定位为就标的物求偿的程序性权利的情形之下,《民法典》第642条第1款所定出卖人取回权的行使条件实际上即为出卖人担保性所有权的实现条件,与担保物权的实现条件相当。依据该款的规定,出卖人取回权的行使条件可由当事人另行约定,由此体现着该款的任意法属性。如当事人没有相反的约定,买受人“未按照约定支付价款,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支付”、“未按照约定完成特定条件”或者“将标的物出卖、出质或者作出其他不当处分”,造成出卖人损害的,出卖人有权取回标的物。
《买卖合同司法解释》原第36条第1款规定:“买受人已经支付标的物总价款的百分之七十五以上,出卖人主张取回标的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确立这一规则的主要考虑是,在买受人已经给付75%总价款的情形下,取回权的行使会损及买受人的期待利益;即使此际不赋予出卖人以取回权,出卖人也可以采取其他救济方式,如请求给付全部价款、解除合同等。(88)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551页。在《民法典》将出卖人就标的物的权利明确为担保性所有权的背景之下,以买受人已给付的价金比例为据否定出卖人取回权的行使,正当性不足,也与《民法典》第416条关于超级优先顺位的规定不相吻合。(89)同前注②,黄薇书,第408页。“所有权保留若是担保构成,债务不履行的数额并不会限制担保权的行使”,(90)同前注,周江洪文。否则,剩余未受清偿的价金债权即失去标的物的物权保障,从而沦为普通债权。(91)同前注①,王洪亮文;同前注,纪海龙文。如此,这一对取回权的限制损害了出卖人的利益,且有违所有权保留约款之目的。(92)参见李永军:《论民法典形式意义与实质意义上的担保物权——形式与实质担保物权冲击下的物权法体系》,载《西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因此,民法典编纂过程中并未采纳这一规则。(93)同前注②,黄薇书,第408页。令人遗憾的是,在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对既有司法解释进行整理的过程中,《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26条仍然保留了合同法时代所确立的这一规则,直接引发了解释论上的冲突。(94)同前注,周江洪文。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承认买受人有权处分标的物,也并不排斥法律规定买受人“将标的物出卖、出质或者作出其他不当处分”为出卖人行使取回权的事由之一。此时,买受人对标的物的处分“造成出卖人损害”之时,才能触发出卖人行使取回权。其一,在买受人在其非正常经营活动中将标的物转让的情形之下,如出卖人的所有权已然登记,出卖人自可以其所有权对抗恶意的转得人,此时出卖人的利益不受损害;如出卖人的所有权未经登记,出卖人的所有权不得对抗善意的转得人,此时出卖人的利益受到损害。其二,在买受人在其正常经营活动中将标的物转让的情形之下,不管出卖人的所有权是否登记,出卖人的所有权均不得对抗标的物的转得人,此时出卖人的利益受到损害。其三,在买受人将标的物出抵或者出质的情形之下,结合《民法典》第641条登记对抗规则和第414条优先顺位规则的规定,确定出卖人与质权人、抵押权人之间的优先顺位,难谓“造成出卖人损害”。(95)参见王瑛:《论融资租赁承租人擅自转租租赁物时出租人的法定解除权》,载《法学评论》2021年第6期。就买受人对标的物的处分不损害出卖人的利益的情形,《民法典》第642条第1款第3项此时即无适用余地;就买受人对标的物的处分损及出卖人的利益的情形,出卖人自可基于《民法典》第642条第1款第3项的规定行使取回权。但在标的物的所有权已由他人取得的情形之下,出卖人的取回权是否可得实现,存在疑问。此时,可以类推适用《民法典》第406条的规定,(96)同前注,孙宪忠、朱广新书,第237页。请求买受人将其转让所得的价款提前清偿债务或者提存。
(三)出卖人权利实现的程序供给
1.协商取回→回赎→再出卖→清算
即使满足《民法典》第642条第1款所规定的取回权的行使条件,出卖人取回标的物尚须买受人的配合。此时,即有了出卖人与买受人协商的必要。标的物的协商取回,类似于《民法典》第410条所定“协议实现”,(97)同前注,李运杨文。其目的同样是“就物求偿”,以标的物的价值清偿未受清偿的价金债务及其他义务。出卖人尚须在取回标的物之后依据《民法典》第643条的规定履行清算义务。依据《民法典》第643条的规定,买受人有权在合理期限回赎标的物,也有权在放弃回赎权后请求出卖人以合理价格转卖标的物并将超过买受人欠付价金及必要费用的部分予以返还。如出卖人不以合理价格转卖标的物或者不返还标的物价值的超额部分,买受人也仍然有权申请人民法院拍卖、变卖标的物。(98)参见刘贵祥:《民法典关于担保的几个重大问题》,载《法律适用》2021年第1期;同前注⑤,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书,第539页;同前注,孙超文。
2.无法协商取回:诉讼取回标的物
既然自力取回受阻,出卖人自可寻求公力取回,通过诉讼取回标的物。《民法典》第642条第2款“可以参照适用担保物权的实现程序”中的“可以”不能理解为“只能”。亦即,在当事人之间不能协商取回标的物之时,并非仅有“参照适用担保物权的实现程序”一途,出卖人尚可通过诉讼取回标的物。(99)同前注,刘贵祥文。《民法典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第64条第2款前段规定:“出卖人请求取回标的物,符合民法典第642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即属此理。在解释上,出卖人通过诉讼取回标的物之后,同样受到《民法典》第643条的约束,容忍买受人在回赎期间内回赎标的物,买受人未予回赎的,出卖人再以合理价格将标的物出卖,实行“多退少补”。(100)同前注⑤,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书,第539页。
为防免出卖人诉讼取回标的物之后的再行出卖所带来的程序延宕,《民法典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第64条第2款后段提供了在出卖人提起的取回标的物的诉讼中一并清算的程序路径。在出卖人诉讼请求取回标的物之时,如买受人反诉请求出卖人返还标的物价值超过欠付价金及必要费用的部分,或者买受人抗辩标的物的剩余价值超过欠付价金及必要费用,请求人民法院拍卖、变卖标的物,则人民法院对买受人的主张应一并予以处理。(101)同前注⑤,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书,第538页。这一程序设计以买受人反诉或者抗辩为前提。
3.无法协商取回:就标的物主张优先受偿权
既然自力救济受阻,出卖人自可寻求公力救济,就标的物主张优先受偿权。此时即“可以参照适用担保物权的实现程序”。这里“担保物权的实现程序”,在文义上并不仅限于《民事诉讼法》上所规定的“实现担保物权案件”特别程序,尚包括出卖人提起普通民事诉讼程序以实现其权利的情形。《民法典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第64条第1款规定:“在所有权保留买卖中,出卖人依法有权取回标的物,但是与买受人协商不成,当事人请求参照民事诉讼法‘实现担保物权案件’的有关规定,拍卖、变卖标的物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这里仅允许“当事人通过非讼程序的方式实现担保物权”,(102)同前注⑤,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书,第538页。同旨参见前注②,黄薇书,第409页。至为可议。如出卖人向买受人提起民事诉讼,同时主张价金债权和就标的物的优先受偿权,自无不许之理。尽管借由实现担保物权案件程序,“出卖人可以省去诉讼环节,直接向法院申请执行,达到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效率的目的”,(103)同前注②,黄薇书,第409页。但在我国目前“实现担保物权案件”特别程序运行不彰的情形之下,承认普通民事诉讼程序的适用至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