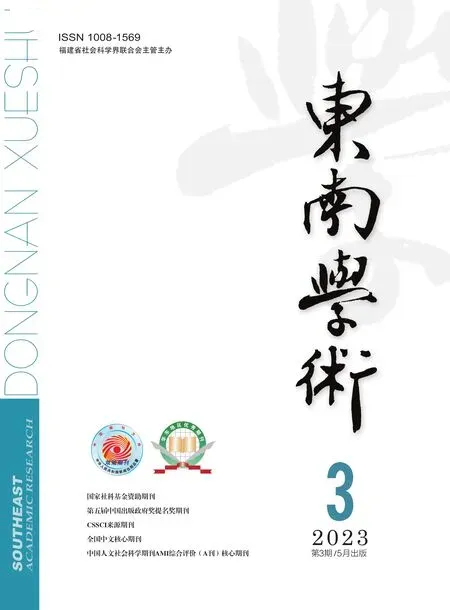作为生存媒介的元宇宙:意识上传、身体再造与数字永生
宋美杰 曲美伊
引 言
获得永生是人类的终极梦想,抵御死亡是人类的永恒课题。 无论是通灵、修仙、炼丹还是干细胞、器官移植、基因编辑,人们一直试图利用各种技术突破生死界限,探求永久存续的可能。 数字化与人工智能的发展带来了数字永生(digital immortality)这条跨越生死的新路径。 巴登和伯顿等将数字永生定义为人死后主动或被动地以数字形式延续其存在的方式。①Maggi Savin-Baden,David Burden,and Helen Taylor, “The Ethics and Impact of Digital Immortality”,Knowledge Cultures,2017,5(2),pp.178-196.在现有技术条件下,“逝者AI”是数字永生的主要应用模式,借助逝者的数字足迹(digital footprints)来“还原”逝者,使其以数字化形式永久存在并具备“可互动性”。 如Replika、HereAfter AI 采用收集过往聊天记录等方式,模拟出一个具备交流沟通能力的逝者聊天机器人。
逝者AI 仅是数字永生的过渡阶段,机器学习所训练出的“虚拟逝者”既非逝者的完全复制体,也非逝者本体,而仅是一种“模拟”。 库兹韦尔认为,21 世纪30年代末人类可以实现“人脑上传”,逐步地把智力、性格和技能转移到非生物载体上,①库兹韦尔:《奇点临近》,李庆诚、董振华、田源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年版,第119-120 页。实现真正的永生。 而有关非生物载体及生存空间的设想,可以进一步延展为基于元宇宙的“数字来世”(digital afterlife)。 元宇宙,原为1992年科幻小说《雪崩》塑造的一个平行于现实世界的虚拟世界,名为“Metaverse”(元宇宙,又译为超元域)。②Neal Stephenson,Snow Crash,New York:Penguin Random House,1992,pp.14-15.元宇宙强调虚拟与现实间的融合,在其搭建的数字场景中逝者能够以数字虚拟人的形象实现“重生”。 反观当下,支撑元宇宙的诸多技术还处于早期探索阶段,③王天夫:《虚实之间:元宇宙中的社会不平等》,《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4 期。数字来世最关键的意识提取/转移项目,如回春研究(Rejuvenation)、④Abou Farman,On Not Dying: Secular Immortality in the Age of Technoscience,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System Press,2020,p.17.脑机接口、⑤喻国明:《未来媒介的进化逻辑:“人的连接”的迭代、重组与升维——从“场景时代”到“元宇宙”再到“心世界”的未来》,《新闻界》2021年第10 期。蓝脑计划等也尚在实验进程中。
实际案例的缺失限制了我们对于元宇宙来世更深层次的想象,而克塔滕贝格(Eric Kluitenberg)指出的“幻想媒介考古”路径则提供了崭新的研究视角。 顾名思义,幻想媒介或虚拟媒介(imaginary media)指非实际存在的、虚构的媒介,是被用以“调和不切实际的欲望的机器”。⑥埃尔基·胡塔莫、尤西·帕里卡编:《媒介考古学:方法、路径与意涵》,唐海江等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65、47、53、47 页。幻想媒介考古试图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研究技术装置的历史,转向对技术媒介、传播媒介的各种想象,⑦埃尔基·胡塔莫、尤西·帕里卡编:《媒介考古学:方法、路径与意涵》,唐海江等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65、47、53、47 页。其考古对象聚焦于故事、绘画、印刷品、电影、歌曲、广告等。⑧Eric Kluitenberg,Book of Imaginary Media:Evcavating the Dream of the Ultimate Communication Medium,Rotterdam:NAi Publishers,2007,p.8.幻想媒介考古注重虚拟与现实的复杂联系,考察“已实现的与渴望的媒介之间持续进行的相互作用”,⑨埃尔基·胡塔莫、尤西·帕 里卡编:《媒介考古 学:方法、路径与 意涵》,唐海江等译,复旦大 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65、47、53、47 页。目的在于“研究那些穿越了不同历史和话语环境而仍在发挥功效的想象性因素”。⑩埃 尔基·胡塔 莫、尤 西·帕 里 卡编:《媒 介 考古 学:方 法、路 径与 意 涵》,唐海 江 等译,复旦 大 学出 版 社2018年版,第65、47、53、47 页。科幻电影作为幻想媒介考古的主要研究对象,从已知科学原理和科学成就出发展开技术想象,更为具象化地传递出人类对未来技术发展的愿景、预言和警示。 数字永生与元宇宙来世虽在当下停留于构想阶段,但以此为主题的科幻电影如《黑客帝国》[TheMatrix,1999,2003(5),2003(11),2021]、《头号玩家》(ReadyPlayerOne,2018)、《失控玩家》(FreeGuy,2021)等,已经构建了融宇宙、超宇宙或平行宇宙的未来。⑪张经武、范晨:《融宇宙、超宇宙与平行宇宙:科幻电影中的元宇宙想象》,《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22年第8 期。
本研究沿着“历史—现在—未来”的时间维度,借由起死回生之议题展现媒介技术发展史与“意识-身体”二元论、一元论之间的相互成就。 笔者首先从生死之间的传播实践出发,梳理人们利用媒介存储信息、对抗死亡的过程,将历史中的媒介作为后视镜,探索数字永生中隐含的技术、身体问题;随后将科幻作品视为数字永生的预言,以幻想媒介考古为方法,探究科幻影视作品中所呈现的数字永生未来与现有技术条件下人们所持有的“身-心”观念之间的互文和指涉关系;进而思考:以数据化为基础的元宇宙将如何构建一个“数字天堂”来承载人们的永生梦想? 怎样的新媒介技术能够使得生者穿梭于虚实之间进而实现灵肉分离的生存状态?
一、数字在场:生死界面的媒介转向
(一)第三持存:从灵媒到社交媒体
在灵与肉关系的哲学对话中,死亡与不朽等议题被不断提及,也由此构成了生死相联的思想前提。 笛卡尔认为,心灵与身体独立存在且可以相互分离,死亡是肉身的泯灭而并非“灵魂的缺失”。①勒内·笛卡尔:《论灵魂的激情》,贾江鸿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5 页。柏拉图指出,灵魂赋予身体生命,灵魂不朽意味着生命的持存,人也因此有望获得永生。②柏拉图:《斐多:柏拉图对语录之一》,杨绛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98-102 页。与身心二元论相反,歌德将人的生命视作灵肉合一的整体,坚信精神具有不朽的性质,“永生”源于个人孜孜不倦的精神活动。③艾克曼辑录:《歌德谈话录》,洪天富译,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75、342 页。无论是身心分离还是灵肉统合,其中都渗透着对于“精神不朽”的认同,也意味着肉体的消亡并不是一切的终结,精神灵魂终将以新的形式重现或延续,④刘琴:《生死叠合:离场记忆的情感仿真、拟化同在与数字永生》,《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2年第9 期。这鼓舞着人们开展了一系列有关连接生死与灵魂永生的尝试。
人类借由中介与逝者沟通的愿望古已有之。 19 世纪初,灵媒(medium)作为连接生死间暧昧关系的存在开始流行。 在彼得斯看来,处于生者和死者之间的灵媒,其身体被塑造为一种“跨越鸿沟”的中介(intermediary),⑤约翰·杜海姆·彼得斯:《奇云:媒介即存有》,邓建国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56 页。逝者的灵魂可以暂时注入其中与在世的亲人交流,这种生死沟通方式隐含了灵魂与肉体可以“分离”的认识论。 19 世纪中期,灵媒从“肉身”逐渐进化为文字、绘画、舞蹈、唱歌等。⑥约翰·杜翰姆·彼得斯:《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邓建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142、203、138、206 页。“文明记录和传输的可能性有多大,灵异世界就有多大”,⑦约翰·杜翰姆·彼得斯:《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邓建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142、203、138、206 页。留声机、电话、摄影机等每一次媒介技术的革新都激发了人们探索灵魂世界的热情。人与逝者不再是直接的“对话”,而是以媒介为中介的“传播”。 电报让远距离的即时通信成为可能,也让大众赋予其招魂(spiritualism)的想象可供性,承担跨越生死的媒介角色。⑧约翰·杜翰姆·彼得斯:《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邓建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142、203、138、206 页。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网络空间再一次拓展了生死沟通的可能性。 媒介化生存的当下,社交账号、游戏软件、电子相册中留下了大量数字痕迹(digital remain),囊括了用户的身体数据、地理位置、生活记录、情感表达以及社会关系等信息。 “媒介既界定又放大了幽灵世界”,⑨约翰·杜翰姆·彼得斯:《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邓建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142、203、138、206 页。即便用户离世,平台也会保存与延续逝者的生前信息,犹如数字幽灵在0/1 代码中偶尔闪现。
互联网不仅是数字化存续的基础设施,还构成了生死之间互动的界面。 身体、位置、行为、心理等人的物理实体的各种属性被映射为数据,⑩彭兰:《“数据化生存”:被量化、外化的人与人生》,《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 期。这类似于斯蒂格勒所谓的“第三持存”(tertiary retentions)。 斯蒂格勒将第三持存视为“意识的代具”,指那些留存下来的记忆因为可以克服时间而成为“能够免于死亡的特例”。⑪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3:电影的时间与存在之痛的问题》,方尔平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133 页。互联网通过记忆外化的方式将日常生活中即使最微不足道的点滴都存留下来,“特例”至此转化为“日常”。 无论是李文亮的微博⑫周葆华、钟媛:《“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社交媒体、集体悼念与延展性情感空间——以李文亮微博评论(2020—2021)为例的计算传播分析》,《国际新闻界》2021年第3 期。还是科比的Instagram,数字化生命历程以保存个人网络足迹、再现数字个体的方式塑造了一个具备“技术精神性”的数字灵魂。
从“肉体”到“机器”,从“具身”到“离身”,灵媒的演变映射了人类从面对面传播到技术中介传播的变革。 然而,通灵者的身体、电报的噪声、摄影术成像的偏差等表明,上述“灵媒”所促成的“逝者回归”仅是一种幻象。 逝者再现的过程是物质技术、悲痛情绪与持续联结(continuing bonds)欲望所交织出的剧目。 逝者已矣,但数字痕迹永存。 日常生活的数据化让人们能以近似孪生的方式重构逝者的“虚拟实体”,以“数字在场”的方式缅怀过去。 相对于其他媒介而言,社交媒体提供了一个生者与逝者共同在场的数字悼念空间,这隐喻了一种媒介主导的“身心二元论”:数字化时代“灵肉分离”的交往本质。
(二)生死沟通:从AI 到虚拟现实
无论是灵媒招魂还是在社交账号下倾诉,生死之间的互动仅支持生者对逝者的单向诉说,而接近人类对话水平的聊天机器人则赋予了人们与逝者对话的能力。 人工智能应用以逝者的数字痕迹与对话数据为资源,借助深度学习与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模仿逝者的交流习惯。 2015年,Replika 创始人凯达(Kuyda)收集了自己与已故好友在社交媒体上的大量对话信息,通过“训练”3500 万条英文文本和3000 万条俄文文本建立了两个神经网络,最终生成了一个AI 版本的故人。①陈静:《数字遗产:死后即焚与数字永生》,2022年4 月14 日,https:/ /mp.weixin.qq.com/s/_Npp9b1OrVTnmtba9vH7Bw。微软2021年获批的聊天机器人专利通过采集逝者的图像、语音文字、社交信息等数据来“复活”逝者。②Tom Knowles,“Chatbot Could Let You Speak to Relatives beyond the Grave”,The Times,2021,p.19.Hereafter AI 的口号是“永远不要失去你爱的人(Never Lose Someone You Love)”,其支持复制一个在语气、声音和外观上都与逝去亲人相似的聊天机器人。③肖琴:《78 岁美国作家成为全球首个“数字人类”,意识在云端永生》,2019年9 月2 日,https:/ /mp. weixin.qq. com/s/CXlmIRoXxrlpbkW5JEoq4A。这些聊天机器人多以专门为对话任务设计的BlenderBot 和DialoGPT 作为底层框架,④Ilya Lasy,Virginijus Marcinkevicˇius,“Dialogue System Augmented with Commonsense Knowledge”,Vilnius University Open Series,2022(5),pp.68-76.不仅拥有长期记忆,还可以利用互联网搜索信息来补充对话背景。
生死“对话”的本质是灵魂的模拟,而3D 建模、虚拟现实与触觉模拟技术则进一步还原了逝者的形象,让逝者“可见”且“可触”。 2015年,在邓丽君20 周年虚拟人纪念演唱会上,数字王国特效公司(Digital Domain)通过虚拟现实和全息影像技术复原了邓丽君的音容与神韵,让这位故去多年的歌手重新走上了舞台。 但“虚拟人”(virtual persons)所拥有的身体仅是一种光影构成的“图像”,无法实现人与人互动过程中的身体参与,而触觉带来的“可感”恰恰是真实性与情感的物质基础。 如韩国MBC 电视台纪录片《见到你了》的制作组提取因病去世小女孩娜妍的影像资料,结合虚拟现实、AI 语音合成、3D 建模、动作捕捉技术等制作了“数字人娜妍”。 与之前可见不可感的虚拟人不同,娜妍母亲可以通过触觉反馈手套与女儿玩耍,并能真切地体验到拥抱时身体的接触。⑤环球网:《韩国母亲用VR 与去世女儿重逢:能看到、听到、摸到她》,2020年2 月11 日,https:/ /baijiahao.baidu.com/s?id=1658201543298558655&wfr=spider&for=pc。
虚拟现实与触觉模拟技术为生死交流增加了身体与空间维度,进一步还原了现实生活中的互动场景。 通过模拟肉身交互时的感受,将逝者的声音、相貌、身体与灵魂统合,实现了从“AI 引魂”到“VR 身体”的逝者再现。 技术假体突破了生死沟通中身体缺席的历史困境,为人们制造出一种虽死犹生的幻象。
二、意识上传:元宇宙来世的数字自我
齐林斯基(Siegfried Zielinski)在《虚拟媒介之书》中指出,“真正的虚拟媒介是那种与外界隔绝的、仅在解释学意义上存在的机器”,尽管如此,其隐含意义却对媒介的现实世界产生了影响。①Eric Kluitenberg,Book of Imaginary Media:Evcavating the Dream of the Ultimate Communication Medium,Rotterdam:NAi Publishers,2007,p.30.因此,幻想媒介考古的意义在于发现那些尚未实现但具有象征意义的未来媒介构想,探寻其中隐含的技术欲望及其对现实媒介的塑造与影响。②褚儒、袁倩倩:《作为主题的幻想媒介——当代科幻电影的媒介想象》,《当代电影》2021年第1 期。克塔滕贝格通过“变体学”方法探究幻想媒介的多义性与多样性,根据个案总结出“与灵魂世界交流的虚拟媒介、与‘他者’交流的虚拟媒介、作为拯救媒介的虚拟媒介”等八种幻想媒介。③转引自埃尔基·胡塔莫、尤西·帕里卡编:《媒介考古学:方法、路径与意涵》,第56-64 页。对于科幻影视作品而言,幻想媒介考古具体的操作方式是将作品本身视为分析文本,搜寻其中出现的幻想媒介并进行建档与归类,④赵乔:《媒介考古学视阈下的电影研究》,《电影文学》2020年第11 期。进而将幻想媒介作为欲望对象和批判对象,分析其展现了哪些人们求之不得的欲望,⑤褚儒、袁倩倩:《作为主题的幻想媒介——当代科幻电影的媒介想象》,《当代电影》2021年第1 期。而后回望现实世界,揭示其所隐喻的对技术的反思。
永生作为人类孜孜以求的终极梦想,同样被投射在科幻影视编织的幻想媒介之中。 本研究选取以“数字来世”为主题的科幻影视作品,探讨逝者与生者以数据形式共存于虚拟世界时,生死沟通将呈现出何种模式? 元宇宙中的“数字自我”(digital self)与现实世界中的“肉体自我”(flesh self)会构成一种怎样的关系? 在数字来世的预想中,死亡不再是消逝,而是割舍了“肉体自我”,这将如何改变我们对生死的看法? 科幻作品将虚拟世界想象为“逝者”的栖息之所,作为生存媒介的元宇宙为技术发展与应用提供了怎样的预警?
(一)极致数据化:上传元宇宙的前提
从文字、声音到图像、触觉,数字媒介为还原、复现逝者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可能。 拉格维斯特认为,数字来世(digital afterlife)这一概念包含了社交媒体中的逝者痕迹、数字遗产与数字记忆、逝者的数字化与超人类行为者,⑥Lagerkvist Amanda,“Existential Media: Toward a Theorization of Digital Thrownness”,New Media & Society,2017,19(1),pp.1-15.其概念的核心在于数字化。 科幻电影中所呈现的元宇宙世界无一不处于一种“极致数字化”的状态:个体一切活动与信息都被收集与记录,并最终成为塑造数字自我的元件。 意识上传(mind uploading)、思维克隆(mind clone)、大脑仿真(brain emulation)成为进入元宇宙的主要技术路径。 意识上传不再是借由数字痕迹“模拟”逝者,而是通过捕捉脑海中每条数据的方式,将人类的思维由物理实体传输到计算机、云端或其他载体之中。 思维可以被复制、转移、保存以实现全脑仿真,因此意识上传成为元宇宙幻想中数据化的终极表现形式。 通过科幻影视作品的考古分析发现,按照数据化程度与意识上传方式的不同,元宇宙永生可归纳为“孪生”和“再生”两条路径。
第一类路径,通过对生活数据的挖掘以“数字孪生”方式还原逝者。 数据化生存走向极致后,仅依靠收集个体的网络数据痕迹就可以生成一个数据自我。 英剧《黑镜》第二季第一集《马上回来》中,女主人公玛莎将已故男友艾什在社交网络中留存的所有信息上传到智能软件中,模拟出了一个与逝者性格、说话方式极度相似的“AI 艾什”。 在添加行为及图像数据后,一个具备身体的“机器人艾什”就取代了逝者与女友生活在一起。 影片中,从生活数据的挖掘到生产数字克隆体的过程构成了一条还原逝者的产业链条。 但生活数据的主要挖掘来源是社交媒体,因而被还原的“AI 艾什”拥有更好的性格、更细致的皮肤与更精致的五官形象。 生前的自拍P 图和社交媒体中被优化的自我呈现制造了一种被美化过的数据,最终在人死后反作用于自身。 正是由于“真实艾什”与“完美艾什”的差异,女友将其弃于阁楼。这揭示了以数字孪生方式还原逝者的困境——较难获取真实数据,而更为讽刺的是,制造虚假数据的人正是我们自己。
第二类路径,借助神经科学以意识传输的手段“再生”逝者。 虽然只要有足够的信息,任何事物都可以自动化,但基于过往数据所模拟出的逝者终究不是具备意向性、发展性的人自身。 沿着这一思路,脑神经上传技术成为实现云端生存的一条主要路径。 亚马逊出品的美剧《上载新生》(Upload)设计了一个“重生系统”,并展示了意识上传的完整步骤。 首先,通过大脑的逆向扫描读取上传者的全部记忆。 随后,记忆被数据化并存储于云端,运营商通过建模和算法技术全方位还原逝者的身体特征及身体感知。 最终,数据构成了逝者的意识,代码构成了逝者的身体,逝者彻底被数字化从而成为元宇宙场景中的一部分,获得“再生”。 但以计算机程序取代神经突触连接的上传方式导致人的记忆存在被修改和替换的风险。 影片中男主角需要进行格式化以恢复至其刚上载时的状态,才能修复被仇家删除的记忆。 但这也意味着他将丢失上载后的记忆,忘记在数字天堂所经历的一切,包括女主角。
以上两种路径都是对极致数字化生存的想象——人类将脱离肉身和时间的枷锁。 如库兹韦尔曾预言的那样,“在未来,我们将能够把自己的意识上传到网络,有效地从我们身体移走的数据中创造出活生生的、不朽的自我”。①Bollmer,David G.,“Millions Now Living Will Never Die: Cultural Anxieties about the Afterlife of Information”,Information Society,2013,29(3),pp.142-151.逝者不再是被机器模仿、复制的数字存在,而是真正的、具备独立意识的虚拟身体。 但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摆脱肉身与时间意味着数据胁迫、促逼着人类采用“消除生命”的方式来延续生命。 如同《上载新生》中女友为了让遭遇车祸的男主角“永生”,将本可以继续接受治疗的他强行上传到虚拟世界。 生命政治学就此演变成姆贝贝(Mbembe)所说的“死亡政治学”(Necropolitics)——为了让人活着,就要让人死去。②Mark Andrejevic,Automated Media,New York:Routledge,2019,p.17.
(二)数字天堂:元宇宙的场景搭建
“关于数字技术的问题就是关于人类存在的问题。”③Lagerkvist Amanda,“Existential Media: Toward a Theorization of Digital Thrownness”,New Media & Society,2017,19(1),pp.1-15.承载意识的虚拟身体只有依托强大的云端才能实现永久性存续,那么元宇宙无疑是虚拟人绝佳的栖居之地。 元宇宙凭借庞大的存储容量、融通虚实的交互功能与立体多维的虚拟场景,为人类构建了一个死后的数字世界。 作为一种连通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聚合类技术,科幻作品中的元宇宙天堂可划分为“延续”与“新生”两类场景。
第一种元宇宙天堂打造了类现实的来世生活。 技术打造的元宇宙来世场景是对现实生活世界的复刻,逝者的虚拟形象也是基于其生前的身体样貌特征建模而成。 如《上载新生》中的元宇宙来世Horizen Lakeview,其主体结构模拟了现实世界的豪华酒店,运营商设计了四季变化的自然场景、食物丰盛的餐厅、具备个性化功能的教堂……元宇宙中的每项服务和物品都需要支付相应的金额后才能使用,在秩序上也与现实世界没有差异。 意识上传后,逝者可以在运营商提供的数字化重生环境“LakeView”酒店里继续生活,他们能够思考、交流,具备全感官体验且与现实世界产生联结。 甚至现实世界中的品牌也设计了同品牌的虚拟产品销售给上载人,现实世界所隐含的各种阶层差异及价值取向在孪生空间中依旧存在。①彭兰:《虚实混融:元宇宙中的空间与身体》,《新闻大学》2022年第6 期。
第二种元宇宙天堂更倾向于颠覆现实世界,建立一个“转世”与“新生”的全新世界。 在英剧《黑镜》第三季《圣朱尼佩洛》中,圣朱尼佩洛系统本是使用沉浸式怀旧疗法帮助帕金森患者康复的医疗技术。 处于病危阶段的老年人可以重新设定自己的样貌、性别及年龄,亦可以选择不同的年代进入体验。 人们甚至可以调整自己的身体参数,如更改对疼痛、触觉、味觉的灵敏度以获得全新的感官体验。 自由天堂的设计让许多病人沉湎其中不愿退出,并选择死后将自己上传。 因此在这一系统中“生死间传播”升级成为“生死共在”,从而生成了一种崭新的生存媒介。 影片所呈现的数字天堂中没有明显的阶级,人们可以冲破现实世界的禁忌相爱、体验、冒险,以弥补在世时的缺憾。 圣朱尼佩洛作为一种典型的乌托邦,隐喻了失去法律与道德束缚的“转世”元宇宙必然潜藏着数字社会危机。
三、虚拟身体:元宇宙来世中的身体自我
(一)永久存续:身体的缺失与重建
当逝者的意识上传到云端后,肉身不在而思维永恒,一个虚拟的自我得以不朽。 然而,去身体化的技术场景反而凸显了身体的意义所在,进而唤醒了人们对于肉身的关注与渴望。一如《上载新生》里上传者渴望拥有感冒、打喷嚏等知觉体验,元宇宙纪元中人的具身性问题便随之凸显出来。 触觉作为五感之首,具备反应直接性、无中介性、在场感、交互性等特质,是人类与外部世界进行交互时最基本的、最直接的通道,②张再林:《论触觉》,《学术研究》2017年第3 期。触觉媒介的接入让生者与逝者在虚拟中传递真实情感,延续现实中的亲情与爱情。
为了重建失去的肉身,科幻影视作品分别预想了两条解决路径。 一是将意识载入新的赛博身体。 在科幻电影《阿凡达》中,腿伤残疾的前美国陆战队队员杰克通过医学设备使自己的意识与具有和他相同基因的阿凡达化身联结,他的意识随着阿凡达身体进入另一个星球,并在那里展开了更有意义与成就感的人生。③吴优:《数字时代文学文本审美特征的身体化转向及其中的媒介管喻》,《文艺争鸣》2022年第6 期。在《太空堡垒卡拉狄加》的衍生剧《卡布里卡》中,父亲将女儿佐伊全的意识副本从虚拟世界V-World 中抽离并载入生物机器人中。 二是通过数据编织还原感官体验,并借助触觉媒介连通虚实。 如《上载新生》中,运营商以数字建模技术再造了逝者的数字化身体,并通过算法模拟出类现实的感官体验。 对于残障群体而言,在虚拟世界中他们反而可以获得完整的身体。 战争中失去双腿的退伍军人卢克死后,元宇宙来世的设计师为他重新设计了双腿,使其能够体验到行走跑跳的真实感受。 借助穿戴式触觉设备和VR 眼镜,生者能够以可触摸的数字形象探望留存于数字天堂的逝者,相隔两域的爱人可以相拥亲吻,老人能够抚摸自己的儿孙,在生者与逝者的相互触碰中,肉身缺失的焦虑逐渐得到缓释。
像彼得斯所认为的那样,过去的交流是“克服中介性的身体”触摸灵魂,而电子媒介时代却是“跨越中介性的灵魂”触摸身体。①约翰·杜翰姆·彼得斯:《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第326 页。身体的缺失勾连着人的主体性、物质性、社会性和实践性。②彭兰:《智能时代人的数字化生存——可分离的“虚拟实体”、“数字化元件”与不会消失的“具身性”》,《新闻记者》2019年第12 期。触觉媒介技术的加入使得虚拟身体暂时性地摆脱空间障碍,能够与现实身体相互触碰、感知。 而身体缺失不仅是元宇宙最显要的问题,也影射了当下世界“身体缺席”的现实——图像化、中介化的社交更依赖于视觉,却压缩了触觉与身体感。 据此,回归身体、还原感官成为当前及未来技术发展需要锚定的发展方向。
(二)身心可分:脆弱的虚拟性身体
元宇宙中面临的另一个身体危机是肉身与图像身体之间的差异。 德国艺术史家汉斯·贝尔廷认为,死亡是身体的永恒缺席,图像就是对永恒缺席之身体的重新召回。③转引自刘铮:《图像、身体与死亡:汉斯·贝尔廷“图像的具身化”》,《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 期。无论是现实还是科幻作品中的元宇宙,身体都是以图像的形式呈现于手机、电脑或VR 眼镜的界面之上的。 当生者退出应用,回归现实,作为图像的逝者却被屏幕阻隔,成为被动的图像存在,仿佛被豢养的电子宠物般,召之即来,挥之即去。 因此,身体的差异仍旧是生死沟通失衡的主要因素。
当肉身与灵魂分割,虚拟性身体的脆弱性便凸显出来。 《上载新生》中逝者的意识与数字自我寄居于元宇宙天堂,原本由身体承载的记忆、情感与思想被转移到大型服务器设备上继续运行。 以数据形式存在的虚拟性身体可以“下载”到移动硬盘中,而一旦硬盘损坏或丢失,便将面临永远消失的风险。 数字人摆脱肉身的同时失去了肉身的庇护,成为充满不确定性的虚拟身体。
“只有在有生命的地方,那里也才有意志”,在尼采看来,身体代表着权力意志本身。④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详注本)》,钱春绮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130 页。“身心可分”进一步激发了人类复制、利用、操纵意识的野心,逝者的意识也如其他数据一般成为可以买卖与再开发的商品,《黑色博物馆》《黑镜·白色圣诞》《人生切割术》等科幻作品对此提出了警示。 如《黑镜》第四季第六集《黑色博物馆》中,囚犯在执行死刑后其意识被迫以全息影像的方式重生,成为博物馆的展览品,日复一日遭受着电击制裁,甚至被无限分离出意识副本作为纪念品。 又如《黑镜·白色圣诞》,职业驯化师马特通过调整时间流速等手段驯化了女子手术提取出的意识副本,使其成为服务于“本我”的智能管家。
拥有一个“原本并不拥有的身体”,还是“还原”自己的身体,抑或是“优化”自己原本的身体? 元宇宙无身体(肉体)的情境促使我们反思意识与身体的关系:脱离身体存在的意识是否具备主体性和自由意志,是否无限可分? 数字克隆出的意识副本能否作为独立存在的个体而不受额外的奴役和伤害? 诚然,虽然我们现在仍然无法完全回答和解决这些问题,但可以在发展数字技术的进程中时刻秉持一种理性与人文关怀,使生而为人的意义免于被异化和消解。 在诸多影片揭示的智能算法重构人与技术关系的语境下,或许“符号具身”才是向人类主体性复归的本真路径。①冯月季:《符号学视角下智能算法对人类主体性的消解及其反思》,《东南学术》2022年第5 期。
四、“我”的终结:元宇宙来世的身份与阶层
(一)我是谁:虚拟人的身份焦虑
元宇宙中个体的矛盾之处在于虚实终究有别,算法塑造的虚拟人与现实自我势必形成强烈对比。 如《上载新生》中,上载过程由专门的扫描医师进行操作,大脑中的记忆将被数字化成文件,并转化为虚拟化身的记忆。 但数据化意味着可修改与可删除,一旦某些记忆文件丢失或被刻意删减,虚拟化身也会失去这段记忆。 此外,化身(avatar)设计师还需要根据逝者生前的数据再造一个3D 数字身体,而数字建模这种模仿技术却是一种静止的技术,赋予了虚拟人不会凌乱的发型和永远年轻的身体。 系统只保留美好的体验而忽视了复杂多变本身才是真实感的主要来源,过于完美的技术设定催生了数字身份焦虑。 像《马上回来》中的艾什一样,数据公司利用逝者艾什在社交媒体中的数据还原了他的身体,但社交媒体中自我呈现的“我”是经过美化与理想化的自我,这与真实自我之间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差异。 社交媒体数据更多地展现了艾什完美的一面,因此重生的艾什看起来更帅气、健康、有礼貌,而正是完美带来的不真实感时刻提示着艾什逝者的身份。
后人类身体是人类主体与机械主体共在的身体。 对应到元宇宙中,在世者的身体是自我与数字自我构成的双重躯体,而永失肉身的逝者则面临着排除双重自我的矛盾,以实现数字层面的纯粹主体性。 电影《流浪地球2》中,科学家图恒宇将已故女儿丫丫的意识存储进量子计算机中并不断迭代,使其成为具备自主意识、对话自如的数字生命,然而依靠既往数据与亲人记忆造就的虚拟生命难以真正等同于人类。 数据能够记录人、代表人,甚至在特定的情况下能够塑造人、成为人。 长久而固定的环境变化可能引发生物的进化,数字生命在数据与代码的世界“永生”,其环境也会对“我”进行再造,如此境遇下的自我是否陷入了忒修斯之船悖论? 如果意识被数据锻造,身体被技术编织,那么“构成要素”被不断置换下最终形成的“我”,是否还是原来的我?
在此基础上,虚拟世界的焦虑感还来自于程序设计导致的行为确定性与数字代码运行结果的必然性。 那么,元宇宙空间中人们所经历的生活、拥有的记忆又将如何定义? 一如《黑客帝国》中经典的红蓝药丸选择,人类的躯体被毫无知觉地浸泡在培养舱中,而意识存活于数字世界。 当人们开始察觉自己熟知的一切皆由代码和数据构成时,仍会有人坚定地选择回归现实,即便虚拟世界完美无缺而真实世界一片荒芜。 又如《流浪地球2》中的“数字生命计划”最终被“移山计划”所取代,人类选择了肉身的迁徙而非虚拟的永生,这也映射了影片中的那句“没有人的文明,毫无意义”。
(二)权力而非游戏:数据不平等问题
当今,诸多科技公司对元宇宙进行了一种游戏化的诠释与实践,《第二人生》《机器砖块》等开放式虚拟游戏具象地再现了元宇宙的愿景,②胡泳、刘纯懿:《元宇宙转向:重思数字时代平台的价值、危机与未来》,《新闻与写作》2022年第3 期。科幻作品却警觉地发现并批判了“元宇宙即游戏”的设想。 虚拟空间中人与世界一同化为数字,根植于现实的不平等观念与阶级固化也将被复制、挪用,甚至演进为更加棘手的问题。 首先,阶级差异在元宇宙来世中以数据权力的形式存在。 如《上载新生》中,人们的任何一个举动与需求都将消耗流量。 数字化的生存空间被划分为不同级别的套餐,在酒店层生活的富人生前拥有的大量资本,在人死后转化为无限的流量供其享受“天堂”生活。 当上传者无法负担流量资费时,其会被降级到酒店地下室的2G 生活区,成为2Gigs:每个月仅有2G 流量以维持简单活动,流量耗尽后则进入待机状态。 看似乌托邦的元宇宙里,暗含了巨大的阶层差异与等级分化。
“元宇宙即权力”,当元宇宙作为连通生死及虚实的中介被广泛应用时,其也形成了一种新的权力所在。 《头号玩家》影片中呈现了现实资本与元宇宙世界的交易,大公司与富裕阶层在元宇宙中依旧掌握操控他人的权力,现实世界中资本占有的差异与偏见同样被挪用到元宇宙场景中。 “任何元宇宙的独占者都会借着无上的权力,试图让数字交往的世界走向数字集权。”①杜骏飞:《数字交往论(2):元宇宙,分身与认识论》,《新闻界》2022年第1 期。又如《上载新生》中人们死后的栖居之所不再由人决定,人类的身后世界变成了一场资本的比较与争夺。 曾经,人们能够自主决定以何种方式结束或继续自己的生命,而数字来世剥夺了人的选择权。 数据成为人生处境与走向的决定性因素,人类分外珍视的自由与自我被元宇宙象征的技术权力持续消解。
对幻想媒介的考古让我们得以穿越至未来,从而以更清醒和审慎的思考维度应对当下如火如荼的元宇宙技术浪潮。 将目光投向现实世界,可以发现人们正在追逐着影片中勾勒的关于极致数字化的幻想。 万物互联时代下,人的数据化特征无时无刻不被捕捉和记录,而“自我”则被压缩为扁平的画像、无差别的代码。 技术的力量已经从身体表面渗透至身体内部,②宋美杰、徐生权:《作为媒介的可穿戴设备:身体的数据化与规训》,《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0年第4 期。从消费领域渗透至价值观念,这要求研究者回到现实,分析数据与算法如何塑造一种新的技术权威,又应借助何种方式促成“自我”的回归。
五、结语:元宇宙的死亡观
“斯宾诺莎(Spinoza)曾经问过一个问题,身体能做什么? 有一件事很清楚——身体会死。 但数据能做什么? ……数据可以永生。”③姜红、胡安琪、方侠旋:《生死界面:与逝者的数字“交往”》,《传播与社会学刊》(香港)2022年第62 期。
本研究既鉴往知来,梳理历史上的生死沟通媒介,又“鉴来知往”,借助科幻电影对元宇宙的想象展开思想实验式的讨论。 一直以来,人类相继利用不同的传播手段探索生命留存的可能以及生死沟通的边界。 从逝者的在场、生死的对话,到未来世界的数字来世,人们通过想象与实践对抗着肉身的离场与生存的孤独。 数据代码构成的精神实体超越了灵媒的幻术,逝者的数字痕迹作为第三持存以“数字在场”的方式留存于网络空间。 人工智能与自然语言处理(NLP)技术以机器学习、模拟对话的方式满足了在世之人“何处话凄凉”的沟通欲望。 虚拟现实、触觉媒介则在“还魂”基础上增加了可触、可感的肉体仿真。
逝者的“复活”既由当下的技术可供性支撑,又被现阶段的技术水平限制。 元宇宙的幻想媒介考古与生存媒介分析为我们指明了元宇宙技术所隐含的“新死亡观”。 首先,在元宇宙世界中死亡的发生并不必然。 当人类从肉身(碳基生命)转化为数据(硅基生命)后,人类的死亡就是可以被克服的。 其次,信息论(Informatics)将成为元宇宙主导的意识形态。 人的自我(self)、记忆甚至能力(abilities)都可以转化为“信息”,因此意识(consciousness)、意向性(intentionality)和身份都可以更为精确地计算、测量、评价乃至排序。 在此情景中,死亡不再完全参照生物学上的评估标准,而是逐渐成为有关信息恢复的工程问题。①Abou Farman,On Not Dying: Secular Immortality in the Age of Technoscience,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System Press,2020,p.20.
基于数据实现永生的构想,我们得以窥见元宇宙世界里意识、物质与身体所形成的复杂关系。 实现永生的前提是在元宇宙中建构一个完整的“数字自我”(digital self),而其必然由一个“肉体自我”(flesh self)在数字世界留存的一系列数字足迹所构成。②任苗青:《从数字自我到数字永生》,2022年4 月14 日,https:/ /mp.weixin.qq.com/s/aMI4hJmXCw7hR2m7uxagaA。由此,意识来源于身体又脱离身体,“数字自我”成为超越物质又被物质包裹的存在,数据、意识与个体在线上与线下的相互交织中产生更为紧密的关联。 这也呼唤了一种统合身体与意识、肉体与数据、“人”与“非人”(non-human actors)的综合性视角。 如非表征理论借鉴行动者网络理论中的“拟客体”(quasi-objects)概念,将网络空间中的“行动者”视为各种非自我元素(硬件、内容信息、代码、病毒)中衍生而成的混合物(hybrids)。③宋美杰:《非表征理论与媒介研究:新视域与新想象》,《新闻与传播研究》2020年第3 期。因此,物质性、超人类和非表征维度将是探究元宇宙世界中人的主体性以及如何持续地创造世界等问题的重要切入点。
维兰·傅拉瑟认为,人类传播以编码世界的形式在我们周围披上了一层面纱,这一面纱由科学和艺术、哲学和宗教编织而成,而且越纺越密,让我们忘记了孤独与死亡。④Vilém Flusser,What is Communication,Andreas Ströhl(Ed.),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2,p.4.而在科幻影视所铺陈的未来中,死亡已经被消除,这凸显了人类在建造元宇宙来世的路上极有可能遭遇的身体缺失、主体性消解和阶层区隔等问题。 当然,在数字永生到来之前,身处当下的研究者还需要思考网络空间的数据痕迹与被遗忘权、逝者社交账号的归属、纪念账号与亲人的持续联结感、数字遗产与继承等现实问题。 向前眺望,亦需要进一步讨论当人作为数字结构存在时是否可以与其他数字意识合并,以及数字化、元宇宙空间的永生是否为人类真实的夙愿? 借由技术传输意识、创造来世,通过数字的形式建立一种对生命存续的确定性,这是人类对身后世界的独特解读,亦是媒介技术对永生追求的挑战与再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