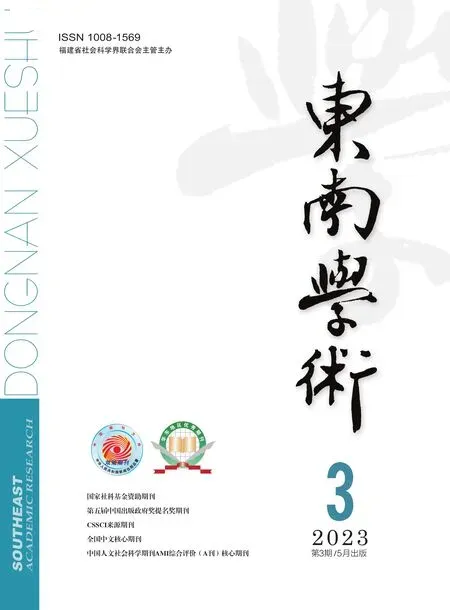论未成年人的医疗决定能力
穆冠群
一、问题的提出
近些年来,未成年人的医疗决定已成为一项世界性的重要社会议题。 尤其是疫情大流行时,未成年人在诊疗过程中的隔离、接种、治疗等方面,是否有权作出医疗决定? 在一些微整形或非手术性美容方面,未成年人可否不经过父母同意而独自决定? 在一些特殊医疗程序中,如人工流产、戒毒治疗、骨髓捐献、放弃维生等方面,未成年人的个人医疗偏好又应被置于何种地位? 立法层面与现实生活之间不断撕扯,导致未成年人的自主决定权处于两难局面,欲寻求解决之道,归根结底绕不开“医疗决定能力”这一核心问题。
医疗决定能力的立法模式目前主要有两种:一是“决定能力”模式,以英美国家为典型代表,即只要患者具有与某项具体的医疗决定相适应的能力水平,该项决定便具有法律效力;二是“行为能力”模式,以我国为代表,即只有患者具备民事行为能力才有权独立作出医疗决定,否则该项决定不会被法律认可,更不会被医疗服务提供者遵从。 虽然我国《民法典》中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制度允许未成年人在其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范围内从事民事法律行为,但结合我国的医疗实践来看,医疗决定行为目前并未落入该区域。 进一步来讲,医疗决定采取所谓的行为能力模式,实际上指的是达到完全行为能力标准。
不同立法模式会导致不同的结果:以完全行为能力作为医疗决定门槛是人为拔高权利行使标准的不当做法,会对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及生活产生不良影响,尤其体现为行为能力瑕疵但意思能力充分者(如成熟未成年人)的医疗偏好和自主权利无法实现。 相较之下,在立法和医疗实践层面,吸取医疗决定能力标准的优势因子,则能够为消除该种立法困局给未成年人群体带来的现实隐忧提供有力帮助。 由此,我国《民法典》及相关医疗卫生法律规范应当加快完善步伐,为医疗决定能力制度的本土化嵌合与改造找到适由之路。
二、医疗决定能力制度的域外经验
“医疗决定能力”(medical decision-making capacity)概念源于英美法。 以英美为代表的域外国家对医疗决定能力问题的探讨较为成熟。 通过梳理,笔者试图勾勒该制度的完整体系,其中包含三部分:一是医疗决定能力的内涵,二是一般推定和例外规则,三是科学合理的决定能力评估系统。
(一)“医疗决定能力”概念溯源
美国《统一医疗决定法案》(Uniform Health Care Decisions Act,UHCDA)将其定义为:个人理解重大利益、风险以及拟议治疗措施的替代方案的能力,以及作出并传达这项医疗决定的能力。 纽约州《家庭医疗决定法案》(Family Health Care Decisions Act,FHCDA)也对“决定能力”进行了术语解释,系指理解拟议诊疗的性质和后果的能力,包括了解拟议诊疗的益处和风险以及替代方案,并作出知情决定的能力。 具体来说,如果患者能够理解诊疗的相关信息,包括诊疗的性质、诊断、治疗方案、替代措施、所涉风险以及预后等,按照自己的偏好和价值观对潜在利益和风险进行权衡并作出决定,同时能够准确把重要信息和决定表达给相关方,那么他会被认为具有医疗决定能力,其所作出的医疗决定具有法律效力。
(二)医疗决定能力的一般推定与例外规则
世界各国立法一般推定智力健全的成年人具有医疗决定能力,只不过对于成年年龄的规定有所不同。 由于个体间的差异性与法律行为的多样性,决定能力在许多情况下会凸显更为复杂和特殊之性状,从而不能被一般推定完全涵盖。 为此,普通法确立了一些例外规则,以填补一般推定之空缺。
1. 七岁规则
七岁规则(Rule of Sevens)是由英美判例法确认的能力规则。 该规则将未成年人的能力水平划分为三个等级:7 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被认为完全无能力;7 岁至14 岁的未成年人推定无能力但可被推翻(a rebuttable presumption of no capacity);14 岁至21 岁(21 岁现已被更改)的未成年人推定有能力但可被推翻(a rebuttable presumption of capacity)——如果同一司法辖区内存在截然相反的法律或法院判决,这一推定可被推翻。①Cardwell v.Bechtol,724 S.W.2d 739 (1987).John E.Steiner,Problems in Health Care Law: Challengers for the 21st Century (Tenth Edition),Burlington: Jones & Bartlett Learning,2014,pp.218-219.七岁规则与未成年人的成熟度密切相关,它关涉医疗领域中的决定能力、知情同意(包括普通诊疗、特殊医疗以及临床试验等)、父母责任以及医师责任等方面的问题。 除此之外,在侵权领域、刑事领域以及诉讼程序领域中都有所适用。 美国的密西西比州、北卡罗来纳州、田纳西州以及佐治亚州也采用了类似“七岁规则”的方法。
2.Gillick“成熟未成年人”规则
1980年,英国卫生部修订了青年人家庭计划服务指导纲要并发布一项行政命令:在例外情况下,医生可合法地在不通知患者家属或在未经患者家属同意的情况下,给16 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开具避孕药。 Gillick 女士的孩子们都未满16 岁,她十分反对这项行政命令,并认为医生给她的任一孩子开处方都要经过她本人同意,因此,她请求法院确认该项行政命令违法。 在后续的几年内,经过法庭的多番较量,最后英国上议院以3 ∶2 的票数判决支持卫生部,再一次认定该项命令不违法。 Fraser 法官、Scarman 法官和Bridge 法官支持本案的初审意见,认为如果未成年人对事物具有足够的理解能力和成熟度,可自主作出医疗选择。 由此,Gillick v. West Norfolk and Wisbech AHA②Gillick v.West Norfolk and Wisbech AHA,[1986] AC 112.Abigail English,Lindsay Bass,Alison Dame Boyle,et al.,State Minor Consent Laws: A Summary,2010,Center for Adolescent Health & the Law,p.9.案确立了“成熟未成年人”(mature minor)规则,即16 岁以下的成熟未成年人具有医疗决定能力,可不经过父母的同意而独立作出医疗决定。 该项规则突破了既往的成年标准限制,在英美法中起到了里程碑的作用。
3.“独立未成年人”规则
“独立未成年人”(Emancipation of minors 或Emancipated minors)概念起源于普通法,可追溯至殖民时期的美国。③它指的是符合一定条件的未成年人,全部或部分(各州规定不同)享有成年人的法律主体地位,不再受父母或监护人控制,父母或监护人也不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成为“独立未成年人”的条件或途径包括:缔结婚姻、未成年人成为父母、与父母分开生活,并能够管理自己的经济事务、服兵役等。 独立未成年人有权就自己的医疗事务独立作出决定,无须通知监护人或取得其同意。 目前,美国至少有37 个州颁布法令明确授权独立未成年人与成年人相同的法律资格。 《法国民法典》也有类似制度,第413-7 条规定解除亲权的未成年人不再受父母权力约束,父母也不再对未成年人在解除亲权后给他人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
(三)医疗决定能力的评估系统
能力评估系统是各国关于决定能力立法背后的现实支撑。 它是一种医学临床技术,其量化考察与结果定性可用来衡量和判断法律规则所确立的“成熟”标准之满足与否。 能力评估是未成年人在法律层面实现自主决定权的重要一环,正因为有临床评估系统的强大支持,才使得相关法律规则能够落地,因此它具有基础性作用。 目前,评估手段主要包括两种:一是以医师临床判断为核心的主观评估,二是以评估工具为核心的客观评估。
虽然一些西方国家已经过患者权利运动的洗礼,但在患者决定能力评估方面,医师的主观评估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并通常作为评估程序的第一步骤。 一般情况下,医师借助一定方法完成患者有无能力的初步筛查,从而决定是否寻求或接受患者的医疗决定。 由于主观评估常会受到医师个人因素(如专业知识水平、个人经历和价值观等)的影响,为了能够客观、准确地考察患者的能力水平,还需借助一些客观的评估工具。 这些工具会考察各类指标和要素,最后得出一定分数或等级,数值越高表示认知功能越好。 常见的评估工具,例如麦克阿瑟治疗能力评估工具(MacArthur Competence Assessment Tools for Treatment,MacCAT-T)、能力评估工具(Capacity Assessment Tool,CAT)、同意治疗能力工具(Capacity to Consent to Treatment Instrument,CCTI)、霍普蒙特能力评估访谈(Hopemont Capacity Assessment Interview,HCAI)、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ntreal Congnitive Assessment,MoCA)等。
三、医疗决定能力制度的比较优势
域外经验为我国提供了广阔思路,不论从宏观层面的世界立法发展趋势上看,还是从微观视角的制度和规则的比较来讲,医疗决定能力制度优势明显,值得借鉴。
(一)医疗决定能力制度更符合国际法治文明的发展趋势
从国际整体层面来看,一些具有普遍性和广泛权威的国际法律文件,积极支持根据未成年人的成熟度来赋予其对自身事务的决定权或参与权。 如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12条①《儿童权利公约》(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第12 条规定,缔约国应确保有主见能力的儿童有权对影响到其本人的一切事项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见,对儿童的意见应按照其年龄和成熟程度予以适当的看待。、《世界医学会关于儿童医疗服务的渥太华宣言(2009)》“一般原则”部分第3 条②《世界医学会关于儿童医疗服务的渥太华宣言(2009)》(WMA Declaration of Ottawa on Child Health)“一般原则”部分第3 条规定,在儿童身上施行任何诊断、治疗、康复或研究措施,皆应取得知情同意……有意识能力的儿童,其意愿应予以考虑。、《世界医学会关于患者权利的里斯本宣言》第5 条③《世界医学会关于患者权利的里斯本宣言》(WMA Declaration of Lisbon on the Rights of the Patient)第5 条规定,应使未成年患者在能力允许的最大限度内参与医疗决策。 其理性决定应被尊重。、《在生物学和医学应用领域保护人权和人格尊严的公约:人权和生物医学公约》第2 章“同意”部分第6 条④《在生物学和医学应用领域保护人权和人格尊严的公约:人权和生物医学公约》(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Dignity of the Human Being with Regard to the Application of Biology and Medicine: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and Biomedicine)第2 章“同意”部分第6 条规定,未成年人的意见应予考虑,年龄越长、心智发育越成熟,决定意义越强。,以及《欧洲患者权利约章》“患者的14 项权利”部分第4 条⑤《欧洲患者权利约章》(European Charter of Patients’Rights)第4 条规定,在法定代理人代为知情同意时,应尽可能使未成年患者参与医疗决策,并得到其知情同意。等诸多条款,对于儿童在处理自身事务特别是医疗程序中的意见和决策,应结合其年龄、心智以及成熟程度,给予妥当的对待和足够的尊重。
从世界个别国家层面来看,诸多国家的立法明确鼓励具有相应能力水平的未成年人就自身的医疗事务发表意见或作出决定,甚至包括一些大陆法系国家(地区)。 代表性的立法如,《瑞士民法典》第19 条C 规定,有判断能力但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可以自主行使与其自身密切相关的权利。 《荷兰民法典》第447 条规定,年满16 岁的未成年人具有为自己订立医疗契约的能力,并可以作出与该医疗契约直接相关的法律行为。 《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第173 条,推定已满14 周岁的未成年人具有识别和判断能力,对于具有识别和判断能力的子女实施的医疗行为,仅得由其本人表示是否同意。 如果医疗行为会严重且持久影响身体完整或个人性情,需要具有识别和判断能力的未成年子女和法定代理人的双重同意。 《芬兰患者地位与权利法》第2 章“患者权利”部分第7 条规定,根据未成年患者的年龄和心智发育水平,应考虑其意见。 依未成年患者的年龄和心智发育水平,可以自行医疗决策的,应在与其充分沟通的基础上提供医疗服务。①唐超:《世界各国患者权利立法汇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02 页。可见,根据未成年人的心智能力和成熟度赋予其医疗自主权已是大势所趋,即使在大陆法系国家,意思能力也越发成为个体从事法律活动的核心,行为能力的立法弱化趋势已颇为明显。 面对当今世界的立法态势,我国现行法应尽快完善相关法律规范,以跟进世界法治发展的步伐。
(二)医疗决定能力的要求低于行为能力
英美法根据法律行为类型的不同对自然人的能力进行差异化要求。 具体来说,除医疗决定能力之外,英美法还对财产能力、婚姻能力、遗嘱能力、政治投票能力、诉讼程序中的作证能力等分别作出规定。 原因在于,不同类型的法律行为所需的能力水平不同,立法对于诸如复杂的交易行为要求较高,从而保护交易双方的利益和交易安全;但对于个体化偏好较强而利益计算属性较弱的非纯粹财产性法律行为来说,对能力的要求应更低一些。 对于医疗行为而言,患者能否充分理解诊疗的性质、作用、风险和后果等,才是直接影响决策的最重要因素,只要患者能够理解并表达出符合自己医疗偏好的决定(不排除某些情况下最佳利益原则的额外干预),法律就应认可,这与财产行为所需的能力要求有着本质区别。 客观来说,医疗决定能力的要求要低于行为能力,如果以后者作为医疗决定的前提条件,会提高患者行使自主权的要求,相应地,患者对于身体自治、人格自治以及生命自治的权利行使起点被抬高,这无疑会导致行为能力瑕疵者的人格减损并挫伤患者权利的实现效果,这一点已遭到诸多学者的质疑。②孙也龙:《医疗决定代理的法律规制》,《法商研究》2018年第6 期。 刘京、张祥志:《患者同意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之分离研究》,《北京化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 期。 李霞:《成年监护制度的现代转向》,《中国法学》2015年第2 期。
(三)医疗决定能力的评估系统更为科学
首先,决定能力制度以人的心智发展水平为内核,反映的是个体的生理和心理发育的客观实际,是“事实”而非法律拟制产物,因此更具真实性。 行为能力的构建核心是人的年龄,具体来说是以人的年龄来判断心智水平。 这实际上是绕了一个弯,且在绕弯的过程中,时常发生二者错位的情况。
其次,决定能力起初是一种要么有、要么无的“一刀切”式门槛概念,现今已演变成一种“可变能力”(variable capacity)的程度概念。③See Baruch A. Brody,Life and Death Decision Making,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pp.100-104. Barry R.Furrow,Thomas L. Greaney,Sandra H. Johnson,et al.,Health Law,St. Paul: West Group,2000,p.835.这是指,决定能力水平的坐标轴不只有0 和100 数值,取而代之的是坐标轴上的每个点都能够表示能力的水平与程度,具有极大的可量化性质,从而使得包括主观评估与客观评估在内的综合能力评估系统的评估结果更为精准。相较之,行为能力更多仅停留在法律概念上,更偏重于定性而非定量,它更多凸显的是坐标轴的两个极端——有或无,而限制行为能力可能表现为坐标轴接近中间区域的某些点,这些点对应的数值则仅限于极少数的固定类型的法律行为。 可见,这种能力认定方式较为僵化,科学性和准确性不足,甚至会导致能力评估系统无用武之地。 最终在行为能力制度下,未成年人的行动范围将被极大限缩。
(四)医疗决定能力制度更符合生活实际,有利于实现实质公平
行为能力的主要功能在于维护经济秩序的安全、效率与稳定,本质上是一种形式权利(公平)。 随着社会的发展,其愈发退化为一种主体资格的识别形式。 学界不禁质疑,以年龄为基础的行为能力制度是否应当进行变革?①王泽鉴:《民法总则》,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03 页。以现实生活为例,孩童被认为或被假定不具备对医疗决定后果的理解能力,但18 岁凌晨钟声一过,该孩童就突然拥有了一套完整的认知能力,就能够从时针溜过前一秒的不懂与无知,变成了成年人一样的全知全能。 这种假设显然荒谬。 法律虽应存在某种格式化标准,但须对其可能带来的不公正后果进行调整。②查尔斯·福斯特:《医事法》,刘文戈译,译林出版社2020年版,第52 页。成年与完全行为能力存在相关性但不绝对,即使未成年,结合其精神状况、智力水平以及收入状况等综合因素,也可能具有完全行为能力。③张新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释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37-38 页。年满16 周岁的未成年人与成年人,两者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是没有区别的,许多14 岁甚至8 岁的人可能比40 岁的人更为成熟。 也正如此,决定能力制度不以年龄为根本标准,它以人的心智差异性和特殊性为根据,更侧重于对患者在特定情境下能力是否适格进行个案考察,因而更能够实现实质公平。 所谓实现公平,最根本的意义在于个体能够合情合理合法地根据自己的真实能力实施相应行为,由此被行为能力“遗失”的那部分人群本应享有的权利便有机会得以实现。
(五)医疗决定能力制度更利于实现人的自由意志
行为能力制度的价值在于提高效率和保护交易安全,而决定能力制度则更有利于实现患者的自主意愿与个人偏好。 与诸如契约及商事行为等能够高度类型化的法律行为不同,医疗决定行为往往只关涉患者个人(或其家庭)的福祉,而与交易相对方无关,难以类型化处理。 由此可见,医疗行为具有高度私人化特征。 私人化体现为以患者个人(或其家庭)的价值观和医疗偏好为决策核心。 如果说普通诊疗中常以“理性人”或“最佳利益”标准为决策的出发点,那么在诸如维生治疗、生育、绝育、器官移植与捐献等特殊医疗领域中,患者个人意愿才是主导医疗决策的最关键因素。 此外,除本文前述的医疗适域范围内,决定能力制度还会影响到“场外”医疗决策,比如“预先指示”和“意定监护”制度的适用。 特别是在《民法典》出台后,“意定监护”制度已成为我国法治发展的一个亮点,如若在法律层面对个体的能力要求进行改革,该制度的作用范围也会相应扩大,这是对个人意志自由发展的极大利好。
四、医疗决定能力制度的本土化改造与构想
鉴于行为能力制度的潜在弊端以及决定能力制度的比较优势,在符合我国国情的前提下,如何将具体方案落实到我国的立法、司法实践以及医疗临床实践中,本文尝试从解释论、立法论和实践论三维视角进行综合分析,尝试提出规范改造对策与制度构建方案。
(一)行为能力二元制与解释论
有学者主张废除无行为能力制度,以限制行为能力制度取而代之,民法体系遂由完全行为能力和限制行为能力两部分构成。④中国民法典立法研究课题组:《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6、22-23 页。 朱广新:《未成年人保护的民法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26 页。 朱广新教授主张彻底废除无民事行为能力这一类型,认为下调年龄界限并非最佳方案,因为它没有解决无民事行为能力制度的双重缺陷。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可以顾及未成年人意思能力的个体差异,避免既行的年龄标准对行为自由的过度限制,同时会减少对最低年龄界限难以达成共识所引发的不必要争议。①山本敬三:《民法讲义I 总则》,解亘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4 页。 朱广新:《民事行为能力制度的体系性解读》,《中外法学》2017年第3 期。 杨立新:《民法总则:条文背后的故事与难题》,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71 页。王利明:《中国民法典释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54 页。在此基础上,以《民法典》第19 条为适用基础,对“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采取解释论路径,而且应采取扩大解释才符合此种规范改造之目的,将医疗决定行为涵盖进来,打破传统观念里只限“小额交易”和“生活必需”之狭窄范畴,促使更多法律行为类型落入相适区间,从而拓展未成年人能够从事的行为范畴。
值得深思的是,此种改造路径具有合理性且在理论上较为便捷,但在现实中却阻碍重重:一是因为在我国惯常的医疗实践中,医生面对未成年患者的做法是让监护人替代决定,无论其心理成熟与否。 试想,如果没有明确的法律赋权而仅靠解释路径,医疗机构不可能根据未成年患者的要求更不可能主动对是否“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进行解释或考察(评估),这是现阶段的客观实际。 二是因为解释论具有滞后性,并不能成为双方当事人的预先行动指引,只能作为司法裁判的依据。 具体来说,即使成熟未成年人认为自己能够或有权独立决策而与医疗机构发生争执,在就医之时也不会起到任何作用(评估程序不会因此而启动),只有在纠纷发生后到司法部门裁决时才可能定纷止争。 因此,解释论不能彻底解决问题,立法层面的深度改造才是必由之路。
(二)增设行为能力例外条款
在例外条款的设置上,我国的立法存在一些不足。
第一,我国法在限制行为能力区间内没有区分“长幼”差别。 未成年人也有年长和年幼之分,年长指的是较为成熟者,多数国家通常视12 岁或14 岁以上为年长的未成年人,这部分人群的心智水平更趋近成年人,因此应与年幼未成年人区别对待。 这体现在我国立法上,可增设行为能力例外条款,比如在《民法典》总则部分第18 条后增加一款,具体安排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仍坚持年龄标准,但对个人享有的权利类型或从事的行为范围没有限制,可表述为“年满×周岁(须经过科学论证,常见的如14 周岁或12 周岁)具有识别和判断能力的未成年人可以独立作出医疗决定,无须经过监护人同意”;另一种方式是不设年龄限制但仅限于一定的权利类型,可表述为“行使与自身密切相关的权利,具有识别和判断能力的未成年人与成年人无异”。
第二,我国法缺乏行为能力的推定和推翻规则。 《民法典》以年龄为基本标准将行为能力划分为三个界域,每个年龄段都对应相应的能力水平以及能够从事的法律活动范围,也就是说,个体要么能做,要么不能做某件事,其结果几乎不可能被推翻,立法也没有提供推翻通道,这种方法较为固定和静态。 “7 岁规则”给我们的启发是:如果我国法在现有框架内尝试增加推定和推翻条款,那么有关能力的规定就会变得更加灵活和人性化,比如可设置条款如“8 岁以下推定无行为能力,8 岁到14 岁推定有限制行为能力,但如有证据证明其具有从事这一行为的足够能力,该限制可被推翻;14 岁到18 岁推定有行为能力,但如有证据证明其不具有从事这一行为的足够能力,该推定可被推翻。”
第三,我国法尚未真正确立以“成熟度”为核心的个体能力考察标准。 《民法典》第19条所谓“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实际上应该以考察个体的成熟度为核心,但无论是本条所限,还是对本条的解释所限,都将限制行为能力人的活动局限于纯获益、小额交易以及“必需品规则”①“必需品规则”指的是与未成年人的生活或交易时的实际需要相适应的行为。 参见杨立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释义与案例评注》,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50 页。范围内,这里反映出的问题是,立法者和司法者认为限制行为能力人的智力只能适应上述三种活动,其他活动则无论其智力发育程度多高都不能够为之。 就目前情况来看,即使限制行为能力人足够成熟,也无权对医院的检查或手术单独表示同意,因为这种医疗行为和所涉医疗决定就立法者及相关解释者来看并不是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活动。 因此具有足够智力的未成年人实际上并不能够按照本条作出与之相适应的医疗决定。 在未来的立法完善中,我国法不妨吸收Gillick 标准,将个体的心智能力和成熟度作为行为能力制度的例外补充,从而赋予成熟未成年人医疗自主权。
(三)单设医疗决定能力条款
由于未成年人的医疗决定问题在法律行为中较有特殊性,因此以《奥地利普通民法典》《荷兰民法典》《丹麦患者权利法》以及《挪威患者权利法》等为代表的诸多国家立法将该问题单设规则。 如果步子能迈得大一些,我国可考虑单独设置未成年人的医疗决定条款,其合理性在于:首先,医疗决定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最重要、最典型的行为类型之一,因此能够证成单独创设规范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也容易实现类型化操作;其次,可以避免完全行为能力标准对成熟未成年人的直接否定,从而在根本上保障这部分患者群体的医疗权利。具体设置方式有二:第一种方式是在《民法典》第19 条后增加一款,以统领分则的相关规定,可表述为“年满×周岁具有医疗决定能力的未成年人享有对自身医疗程序的知情同意权,无须取得法定代理人的同意”;第二种方式可在分则相关条款,比如第1219 条后增加一款作为补充并彰显立法的明确态度,可表述为“未成年人如具有相应的医疗决定能力,医疗机构应当对其进行说明并取得本人同意”。
(四)构建特殊行为能力制度
客观来讲,不同的法律行为对个体能力的要求不应相同,而一般行为能力制度难以全面概括日常生活的丰富性以及不同行为类型所需的能力水平差异,因此在立法上构建特殊行为能力制度是一种合理模式。 为了避免法律行为的繁杂性给立法技术层面带来的困扰,只需将某些重要且典型的特殊法律行为进行类型化单列即可。 纵观域外国家和部分地区的法律制度,包括但不限于医疗决定能力、结婚能力②如《法国民法典》第九编第413-1 条及第413-6 条规定:未成年人结婚,当然解除亲权;已经解除亲权的未成年人,如同成年人,有实施一切民事生活行为的能力;不再处于其父母的权力之下。 参见《法国民法典》,罗结珍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6-137 页。 另,缔结婚姻后又离婚的未成年人,其能力在法律层面不受影响。 如美国科罗拉多州州法规定,任何已婚或离异的未成年人都可以决定医疗、牙科、紧急健康和外科护理等事宜而不需要父母同意。See Colo.Rev.Stat. §13-22-103.、劳动(雇佣、营业)能力③如我国《民法典》第18 条第2 款的“劳动成年制度”。 《日本民法典》第6 条规定的“营业成年制度”,即从事一种或者几种营业的未成年人,就其营业与成年人有相同的行为能力。 参见《日本民法典(2017年大修改)》,刘士国等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8年版,第4 页。、遗嘱能力④《德国民法典》第2229 条规定,年满16 岁的未成年人能立遗嘱,无须得到法定代理人的同意。 本德·吕特斯、阿斯特丽德·施塔德勒:《德国民法总论》,于馨淼、张姝译,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318 页。、收养能力、政治投票能力、宗教信仰选择能力、出身事宜办理能力⑤《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第141 条规定,有识别和判断能力但无完全行为能力的人,享有出身事宜的办理权。以及诉讼程序中的作证能力等,这些特殊能力类型通常被视为对一般行为能力制度的补充和突破。
医疗决定行为是一种重要的特殊法律行为类型,应被我国立法着重考虑。 就具体的条文设置方式而言,可放在《民法典》总则第2 章第1 节部分,表述为“(年满×周岁的)未成年人如果能够充分理解与其自身相关的医疗程序并能够清楚表达自主意愿,其作出的医疗决定与成年人无异”。 不容乐观的是,除劳动成年制度外,一些其他的重要特殊能力类型尚未得到我国立法的认可,比如未成年人尚不能通过缔结婚姻获得独立法律人格,更不能按照自由意愿和个人偏好进行独立的医疗决策。 可见,我国现行法对于特殊行为能力的规范十分欠缺,更未形成完整体系,在未来的立法发展进程中,这一部分内容应予以完善。
(五)认可意思能力的效力促进功能
未成年人无法自主决定是因为法律认可的是抽象能力,而非真实、具体的意思能力,实际上,行为能力概念已被泛化,是对个体意思能力的二次改造,其弊端有二:一是二者不能一一对应时会产生争议,二是两者之间谁为基准时常模糊。 要解决该问题,核心在于明确意思能力的首要地位,赋予其效力认定或促进功能。
从理论上讲,应提倡“促进型”意思自治,认可具有意思能力的限制行为能力人独立实施法律行为,也可在具体情况下承认无行为能力人的行为例外有效。 在行为能力不能吸收和替代意思能力的情况下,不应断然以行为能力作为法律效力的认定标准,而应以意思能力取而代之。①常鹏翱:《意思能力、行为能力与意思自治》,《法学》2019年第3 期。由此,成熟未成年人的医疗决定便可具有法律效力,这在拓展未成年人行为范畴和福祉保护方面具有突破性意义。
从司法实践角度看,我国关于未成年人行为能力的裁判大多也是从意思能力角度来论证,意思能力是法官判断行为能力的最本质因素。 比如,在冒某与骆某等婚姻家庭纠纷案②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8)京01 民终4718 号民事判决书。中,法院认为年满15 岁的未成年人,“可以认定其对姓名等与自身日常生活、学习密切相关的人身权益已形成一定认知”,是否更改姓名应尊重其本人决定。 在魏某1 与戴某变更抚养关系纠纷案③参见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法院(2016)苏0206 民初745 号民事判决书。中,法院认为“10 周岁以上未成年子女……具有一定的意思能力,其愿随魏某1共同生活的意见应予考虑”。 在陈某某与王某某婚姻家庭纠纷案④参见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鄂武汉中民终字第00116 号民事判决书。 该案为湖北法院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典型案例(2017)之一。中,法院认为“王某年满16 周岁,其智力和认知能力足以理解亲子鉴定的意义……故对其意见应予充分尊重”。 这些案件集中反映出:无论是在涉及姓名决定权、抚养选择权、亲子鉴定决定权还是探望权等案件中,未成年人的意思能力水平是法官重点考察的内容,如果法官认为未成年人能够理解案件所涉权利的基本含义和相应后果等,便会尊重其意见与愿望。 实际上,意思能力已成为法律效力的决定因素。
因此,在未成年人的医疗决定问题上,可提倡如下观点:第一,对于具有充分意思能力的(成熟)未成年人的医疗决定,我国立法层面应明确赋予其自主决定空间,司法实践层面应认可其医疗决定的法律效力,这是符合私法自治精神的。⑤我妻荣:《新订民法总则》,于敏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55 页。第二,意思能力存在个体差异是不可回避的事实,回避或忽视这种事实会导致诸多问题。 在行为能力不能吸收和替代意思能力时,为了克服意思能力与行为能力之间存在的偏差给行为人带来的权利减损,此时不应将行为能力作为影响法律效力的唯一因素,而应积极提倡意思能力的效力促进或决定作用。第三,我国相关医疗卫生法律规范,如《中医病历书写基本规范》第11 条、《病历书写基本规范》第10 条中关于完全行为能力的表述应作删除处理,这样才能彻底摒弃不甚合理的高门槛限制。
(六)建立科学的决定能力评估系统
目前,我国的患者能力评估体系尚未真正建立。 第一,主观评估和客观评估虽已被我国医疗机构采纳,但对于后者的利用并不充分,目前仍以医师的主观评估为主要手段。 常见的情况如,在精神分裂症患者入院时,医生通过观察、交谈、询问等方式获取信息后,利用以往的临床经验进行分析,在对疾病确诊的同时判定患者的决定能力。 主观评估的优势之一在于其灵活性和动态性之特点,可以有效实现患者的道德权益,尤其是在医生经验丰富、相关信息较为全面、疾病特异性较为明显的情况下,更能有效判断患者的决定能力。①罗光强、李凌江:《精神分裂症患者知情同意能力评估模式的伦理分析》,《医学与哲学》2010年第12 期。但对客观评估的利用缺乏也会导致一些问题,比如无法克服医师个人倾向(专业素养、文化背景、教育程度、价值观等)之弊端,缺乏程序上的完整性以及评估要素不甚细致、精准等。 第二,在主观评估中仍以单一、静态的结果方法为主,患者的决策是否“理性”、是否会带来“良好”结果,目前仍是医师判断的根本依据;也就是说,我国目前的临床经验中,尚未充分吸收功能方法和浮动方法之优势,未能根据患者自身情况、诊疗所涉风险、所拟决策重要性以及对患者福祉的影响等综合因素进行全面考察。 域外经验早已摒弃“或有或无”的能力衡量结果,根据患者实际情况得出“刻度性”精准结论已成大势所趋。 第三,我国既行的评估手段所适用的对象主要是精神疾病患者,而对智力健全的未成年人的能力评估却异常缺乏,甚至可以说尚未展开。 无论是理论界相关研究的明显不足,还是实务界对未成年患者权利保护的程序缺失,都能够证明这一点。 第四,我国客观评估的现状仍以对上述西方评估工具的中文译本②王雪芹、于欣、唐宏宇等:《麦克阿森临床研究知情同意能力评估工具简体中文版在精神分裂症患者中的信度和效度研究》,《中华精神科杂志》2015年第1 期。为基本参考,缺乏具有独创性和符合我国特有的民族性和文化背景的患者能力评估工具及相应设计。 第五,我国对于客观评估工具的应用较为单一,目前仍以MacCAT-T、MoCA 等典型工具为主,缺少多工具间的综合性、交互性以及多样性使用。
我国之所以在未成年患者能力评估方面不够完善,根本原因在于现行法的高门槛要求为实践操作设置了巨大阻碍并挫伤现实的强烈需求。 在社会主义法治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对未成年人决定能力的检测与评估已成为患者权利保护的必要举措。 它不仅能够保护具有决定能力的未成年人的充分自治,也能避免无决定能力患者受到不利决策的损害。 面对上述不足,我国应在医疗卫生单行法和相应的法规、规章上面,结合诊疗的具体流程对患者的能力评估进行系统化完善,从而使其名正言顺地成为患者医疗决策的前置(保护)程序。 诸如《执业医师法》第26 条、《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第13 条、《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33 条、《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62 条以及《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11 条等处增加一款将未成年人的能力评估问题以法条方式确立下来,具体可表述为“未成年患者就医时,可根据患者需要进行能力评估;具有决定能力者,医务人员应当向其本人告知并取得其(书面)同意”。
(七)个案考察机制与司法实践的联动
意思能力的个案审查旨在用具体场合的意思能力判断规则来确定法律行为的效力,相较于一般行为能力制度更能体现实质公平和鲜活的生命力,此时应避免把意思能力也定位为一个抽象概念。①李国强:《论行为能力制度和新型成年监护制度的协调——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的制度安排》,《法律科学》2017年第3 期。从其他国家的民法发展趋势上看,意思能力的个案审查正逐渐成为潮流。 在美国,患者承诺的有效性与财产行为能力无关,应视具体情形中患者有无意思能力及理解能力进行个案判断。②王服清:《论病患同意能力之问题与刍议》,《私法》2014年第1 期。德国法虽然仍保留限制行为能力人制度,但已由抽象行为能力变成具体行为能力。 有学者认为,德国民法改革最为彻底,在成年监护中实现行为能力去除化,直接对个案中各主体意志进行具体审查,以确保制度体系与生活事实的最大联系。③孙犀铭:《民法典语境下成年监护改革的拐点与转进》,《法学家》2018年第4 期。不断完善的日本民法按照法律行为的不同种类分别具体判断意思能力的有无,④大村敦志:《从三个纬度看日本民法研究——30年、60年、120年》,渠涛等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155 页。其更加注重以具体交易场合是否具备意思能力来确定法律行为效力,除非欠缺意思能力,否则法律行为并非无效。⑤近江幸治:《民法讲义I 民法总则》,渠涛等译,渠涛审校,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5 页。医疗决定能力个案审查制度的建立,将使行为能力瑕疵患者的意思能力得到最大化支持,⑥汉斯·布洛克斯、沃尔夫·迪特里希·瓦尔克:《德国民法总论》,张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22-123 页。这也会成为21 世纪民法典的一种创举。
在我国,确立医疗决定能力的个案审查制的最大阻碍在于效率挫伤。 如何在防止效率挫伤与最大程度维护患者实质权利之间进行平衡,不仅是对立法技术的挑战,更是一种规范制定的艺术体现,具体可参考如下方案:一是行为能力推定规则,即一般规定不具有行为能力的人可以用反证证明行为时具有行为能力,反之亦然;二是采取意思能力的形式审查和个案审查的“双轨制”策略。 这种两者兼顾的能力认定模式,以意思能力的法律拟制或形式审查为原则,辅之以意思能力的个案审查为矫正和效力补充。⑦彭诚信、李贝:《民法典编纂中自然人行为能力认定模式的立法选择——基于个案审查与形式审查的比较分析》,《法学》2019年第2 期。实际上,学界对于个案审查的质疑不用过于悲观,原因有二:一是虽然行为能力制度具有普遍适用性,但日常生活中人们对于一般行为能力的认定需求较少,而关涉具体能力的认定案件较多;⑧王竹青:《成年人监护中行为能力认定域外考察》,《法律适用》2017年第11 期。二是意思能力的个案考察在我国民法中早已存在,而非凭空臆造。 比如劳动成年制度中对于“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认定,对于限制行为能力人可从事“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活动的认定等,都需要对个体情况具体考量。 个案审查制度在立法中的明确化,需要以医疗实践和司法实践的顺利衔接为前提。 具体来讲,在医疗实践中,应充分利用主观评估和客观评估手段,以作为技术层面支撑;在司法实践中,应正当化行为能力高度盖然性证据推翻机制,并留给意思能力补足或矫正法律效力的空间,从而为实现患者自主权最大化提供可靠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