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里的科技与狠活儿
俞耕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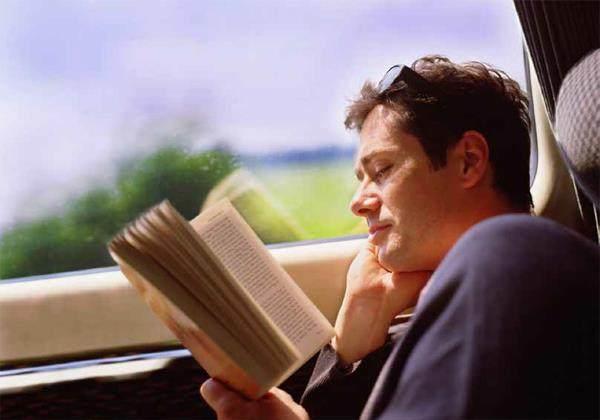
回想我的阅读,竟是从字典开始。还不认字时,我喜欢专挑字典里的生僻字,把它们写在田字格里。上了小学,姥爷有本《康熙字典》,附录里收有历代帝王的改元年号,不明所以,我就爱记这些。最早接触的东西也就形成了情结,所以精神分析总爱从童年里找寻创伤。我对历史的兴趣最早,启蒙读物是林汉达编写的《中华上下五千年》,即使现在看到书中的插图,还是那么亲切。

贵阳“钟书阁”书店,曾被美国《WIRED》杂志评为“全球10家最美书店”之一。
每次买书都像诸侯觐见
春秋战国、五霸七雄,这些遥远的文化记忆开发了我的精神世界。以一个3年级儿童的理解力,将周王室和诸侯兼并的关系看得云里雾里。但它也教会我,看书不要怕乱,慢慢捋总会有线索。那些故事对我的认识有很大冲击,我较早便放弃了非黑即白、单一直线的思考。历史上的大分裂时代,大家互为敌手,既看不惯也干不掉。生存更多时候要学会求同存异,而非你死我活。那时候遇到生字就查,拼音还写得密密麻麻。这就是儿童精神,不怕麻烦,有的是耐心。
如今还有教授问我,是否有家学渊源?我听了都暗自苦笑。父母是被耽搁的一代,年轻时学业荒废,匆匆上班,人生仓促得像赶公交。除了父亲因为爱绘画,还存有一些画册,家里基本没什么书。我的书都是上学后攒出来的。上世纪90年代,手头很紧,对于工人家庭,买书更是不匹配的奢侈。尽管如此,父母还是尽力满足我,印象深刻的是他们为我买的《白话资治通鉴》和《中华活页文选》,因为造价昂贵。我不止侵占他们很多周末,还花掉他们不少工资。这让我深感,如果不认真阅读,就是对父母的不公。
我儿时常去的书店基本都在西安城内,和周王室的“王畿”一样,每次买书都像诸侯“进城”觐见。而家附近的旧书摊方便多了,没事我就拿零钱去“踅摸”。和摊主讨价还价。诸如神魔人情、谴责志怪、历史演义等白话小说,我买了不少。虽然破烂,但基本是人民文学、上海古籍、中华书局出品的经典读物。后来我对图书版本,内文版式的偏好,大概都是童年养成的“毛病”。
我曾特别着迷于岳麓书社的“古典名著今译读本”系列,因为是白话译文,勉强能读懂一二,与中华书局、上海古籍的书比,相对便宜不少。封面花花绿绿,却显得格外古朴素雅。丛书品种从《国语》《战国策》到先秦诸子,有经有史有兵法。当时我专挑故事看,遇到议论的内容就跳过。就像不吃果肉的膳食纤维,只是吸口汁水而已。如将阅读比作投资,其必然具有“复利”效应,积累使本金增多,如杠杆使受益更大。世人皆知走出舒适区之难,但硬着头皮的自虐式阅读,最终也可能解锁技能,享受快感。
那时的中学图书室里,管理员只有一个校工老头。学生不能进入,只有通过一本索引目录,乞他找书。他横上桌子,堵在门前,像守着私产,防着贼。每递出一本书都不情不愿。莱蒙托夫、郭沫若、任继愈、朱光潜……那时我上初一,借到书就抄。若要问我当时能看懂多少,我认为没多少,但这不重要。抄书本身会形成反射记忆,对未成年人来说,比读书深得多。时至今日,我的记忆点还常停留在15岁前的老底上。
高一时我接触到了李泽厚、汝信等前辈的作品,发现美学竟可将艺术、哲学、思想史“合体”得如此好。以前我只对中国古典有兴致,对中西古今的比较互通根本没有了解。它为我读研时选美学专业,早早埋了伏笔。之后我对每个领域的阅读兴趣,可谓都由具体作者开启。读郭沫若令我喜欢中国历史;看諸子散文,令我爱上中国哲学;郁达夫、昆德拉和福柯,又分别让我对现当代小说、外国哲学有了热情。
鲁迅先生有过“抄古碑”的无聊苦闷期,而他的小说史研究,杂文的钩沉功夫,也多在那时奠定。我的中学记忆大多厌倦乏味。阅读给我的最直接影响是,当了文科生。高中物理老师曾当众讥讽我,“看来你选对了,你也只能学文科”。那副表情难看得诧异。可以说,读书使我“认识自己”,它贴近了生活的确定性。我明白自己厌恶什么,热爱什么。
直到高考前,别人刷题时,我还把西方文艺理论压在试卷下面看。后来报志愿,我全部填了中文专业。这专业“好处”是不学高数,真正把读闲书、搞文艺当本业,心安理得。对于阅读,我有底气说,长久的积累并未浪费,人生的精力更没虚耗。不论所学还是工作都高度合一,我就是那个锁定一只羊,死薅羊毛的傻瓜。但是我没有辜负自己,甚至从未否定、偏离过既有的设想。如今看,这种自我决定的意志,仍不可思议。
读研期间我开始着手于写评论。作为一个新手,我的开场不错,第一篇随笔就发表在《中国新闻周刊》上。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刊发过几篇文章后,我如愿以偿地吃上了“写作饭”。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不去搞学术,当高校教师,以此支持业余写作。这些话说来都很轻巧,写作不只要有空闲,更要有闲情。研究则意味一辈子围绕一个领域,一个对象的那几本书,翻来覆去倒鸡毛。
即使如此,我的阅读还是无可避免地从纯粹走向不纯粹。随着在文艺评论、文化评论和书评上的深入,从而把阅读和写作“绑定”起来。原先漫无目的翻闲书,如本雅明所说,像巴黎拱廊的漫游猎艳者。现在则成了带着评论任务去读书,心态从欣赏变成分析,难免索然。别人看书像吃鸡,关心味道。我却在意这只鸡的解剖如何、骨架怎样。
与以前书籍的匮乏相比,如今是出版过剩、诱惑过多,人的精力反而不够。富氧和缺氧一样会不适。以前读书并没什么选择困难症,能看到的就是名著。现在乱花迷人眼,泛读、跳读和略读,终归都是要做取舍。不同的类型定位,决定书的读法不同。为获取信息,可速读了解;为故事情节,可跳读消遣。为了学习语言质感、气息节奏、结构经营,就得细读文学经典;为了思维训练,提炼观念方法,跃升认识能力,则要精读学术名著。后两者多是研究性、学习型的阅读。我对图书的分类也由此而来,即“爷爷书”与“孙子书”。换成严肃的说法是“原典和非原典”。前者为数不多,经过历史考验与沉淀,是有公论的开创性著作。后者则大多是信息爆炸、知识输出下的产品。二者关系类似于黄金和一堆“金融衍生品”。精力不够时,多读“硬通货”可节省时间成本。原典代表了人类所能抵达的精神高度。但它们难度大、层级高、硬货太干,常令非专业人员望而却步。
所以,如今的人文社科出版物,大多是解读类、演绎类、闲话类、心得类和应用类书籍。即使讲国学历史,说《易经》兵法,也一定要和企业管理或者成功学扯在一起。说到“老庄孔孟”,更要夹带一堆为人处世的私货鸡汤。这些图书并非不好,而是太多。经典的普及其实远远不够,最专业的一流学者大多忙着论文和专著,他们对文化的传承和传播往往贡献甚少。相反,图书市场上却活跃着大批非专业作者,跨界去干专业的事。
深度阅读的反面是什么?
知识付费的兴起则将有声听书、说书结合起来,出现了大量以讲书带货为业的知识博主。他们给无暇读书的人提供心理按摩、情绪价值和廉价替代品。花上20分钟就有“专家”帮你梳理全书干货,让你开车通勤也可灌耳收听。原本就快餐式的阅读,连咀嚼都被省却,直接改成“输液”、灌“流食”了。前几年“知识焦虑”还是个热词,但如今AI让死知识变得并无价值。靠阅读获得知识的意义正在不断下降。提升认识、诞育思想、培育情感,才是阅读的关键。
最好的阅读状态是什么?我想与审美活动一样,是无目的的目的性。换言之,读书时不带功利,未来后知后觉,发现它“潜在有用”。我们的传统,一贯爱讨论有用性。如古人谈经世致用、学以致用,讲黄金屋、颜如玉这类诱惑。中小学语文一直考阅读理解,带着问题读文章,找标准答案。一旦发现读书不见得能换来好工作、好媳妇,立马就陷入“无用论”的极度空虚里。问题在于,我们从未把阅读视为本能需求,所以才有“寒窗苦读”这样的固定搭配。靠阅读放松的时代一去不返了,其休闲功能早已被电子设备、主机游戏、短视频所取代。与其说人们缺乏深度阅读,不如说数字时代人类的大脑神经产生了巨大变化。

如今的短视频和流媒体平台,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支配了人们的阅读精力,但却制造出新的焦虑。
在读图和影像时代,我们对文字的感受力、敏感度大大钝化。持续的感官冲击下,神经的兴奋阈值也越来越高。以至于我们已经对普通电影无感,要追求3D、4K和VR技术了。很难想象,我们还要借助原始的文字表达、画面还原、想象共情来实现有意义的交流,还能留有耐心。虽然,深度阅读爱好者仍旧数量庞大,他们仍在讨论如何用券囤书,还关心轻型纸、胶版纸,是典藏版还是特装本等话题,但更多已将纸书视为情结寄托。
纸质书不仅是文字的物质载体,还是情感与知觉的媒介,它具有占据空间的实在感。不光是触感质感、油墨氣息,甚至光是摆在那里不读,看看封面也很解压,如同集邮一般。但是电子阅读模拟了读屏模式,实现无纸化,改变了阅读习惯。原本带有诗意翻书的动作,也被呆笨的上下挪移、左右点击所取代。我们开始遗忘书的物理空间——书脊扉页、内文版芯。每一屏都消除了界限,成为无差别的绵延体。这也并非坏处,至少对我而言,电子阅读让我像刷手机一样——轻松、持续、更快看完一本书。
然而我们需要思考的是,深度阅读的反面是什么?是浅层阅读、碎片阅读,还是快餐阅读?这个问题,如同非要分出网络文学、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界限。所谓深度,可说是传统的、沉浸式。在充分移情入境中思考,或许再配上做一些笔记,才能找到些意义。
(责编:常凯)

什么对你的阅读造成了最大障碍?
最大障碍是注意力和持续感的问题,容易出现分神与间断。
最佳阅读场景是什么?
在旅途中的列车上,阅读相伴风景,嘈杂人群同样可提升抗干扰力。
深度阅读对你造成怎样的影响?
静气凝神,增进思维的深广。从知识中诞生思想,在语言中学会生存。
电子阅读设备可以为你带来深度阅读吗?
完全可以,比如读小说,并不像专业理论那么依赖纸质阅读。
阅读带给你最大的忧虑是什么?
人生太短,精力太少。书籍太多,空间太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