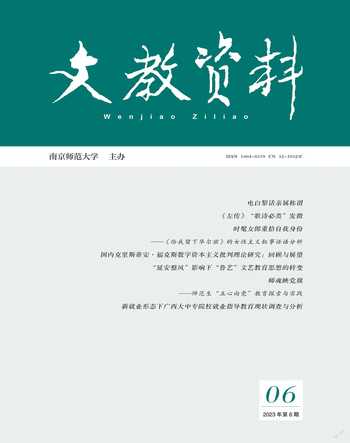从汉代拟骚之作看屈原形象建构
赵睿琪
摘 要:汉代楚辞学的兴起在屈原形象建构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屈原生平材料相对有限的情况下,拟骚的创作中夹杂了较多的汉代人主观成分,并因而建构起与屈作抒情主人公形象有所差异的屈原形象。在具体阐发过程中,拟骚对屈原赋作进行了有选择的沿用,并在具体词句的沿袭与更新上发挥了诗人的主体性,为拟骚中的屈原形象加入了新的因素。其中,黄老思想与儒家学说都展现出较大的影响力,使得汉代屈原形象建构拥有了更复杂多元的侧面。
关键词:拟骚 屈原 汉代 楚辞学
楚辞学兴起于汉代,是屈原接受史中难以忽视的一环。楚辞学在汉代的发展同样为后世学者理解楚辞、解读楚辞提供了基础。拟骚诗作为汉代楚辞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文学成就不高,该文体也没有在后世得到太多继承,得到的关注相对有限,但它同样折射出汉代人对屈原的认识,影响到屈原的形象建構,在今天的研究中仍然有其价值。
值得关注的是,在屈原生平经历和生活环境等方面,汉代相关文献资料内容存在不同程度的模糊,对楚地风俗等方面的描述也相当有限。在作为屈原文学评传的拟骚作品中,甚至出现了与屈原生平矛盾的描述。因此,我们有理由怀疑拟骚中的评述夹杂了更多汉代人对屈原作品的理解,进而建构出了一个经过汉人选择的屈原形象。本文从拟骚作品入手,探究在汉代屈原形象建构的情况及其形成因素,进而观测这一形象对后世的楚辞研究影响。
一、拟骚之作对屈原形象的建构
除去《哀时命》《惜隐士》两篇外,《七谏》等拟骚作品不仅被看作对屈原作品的模仿,更是对屈原经历,性格志向的评论与阐发。它们在篇名上非常相似,并都于一篇下分出几个单独篇目概述屈原生平。王逸的《楚辞章句》就指出了它们与屈原作品密切的联系。如《七谏》前有“屈原与楚同姓,无相去之义,故加为《七谏》,殷勤之意,忠厚之节也”[1],《九怀》题下又将“怀”解释为“怀者,思也,言屈原虽见放逐,犹思念其君,忧国倾危而不能忘也”[2]。它们的共同点是都从屈原的心理出发,描绘他放逐过程中的感受,阐发忠正之情。与此同时,他们创作时无可避免地加入了自己对屈原的理解,这一现象可以从多方面展开分析。
二、屈赋篇目的选择与继承
将拟骚的篇目进行对比,我们会发现它们在内容的选择上几乎一致。如《七谏》的“初放”,《九怀》中的“危俊”,《九叹》中的“离世”,均叙述屈原被流放过程中的悲苦;《七谏》的“怨世”,《九叹》的“怨思”,《九思》的“怨上”叙述屈原忠而被谤的怨愤,甚至在篇名上都极为相近。总体而言,在拟骚中侧重阐发的内容基本与《离骚》《九章》内容保持一致,大量地参考《离骚》的文辞,突出屈原作为“楚之同姓”不愿离开君王与故国的忠直与坚定。这样的内容侧重是如何选择的将是下文试图探究的问题。
在汉代流传的屈原赋作即便不及《艺文志》所载有“二十五篇”,至少也还有《九歌》《天问》等至今留存的篇目。相比《离骚》在拟骚之作中留下的显著痕迹,这几篇的影响可以称得上是微乎其微。将目光放到那些被拟骚作者忽略的作品上,《天问》从日月天地问起,表达了作者对天地万象与人类历史的思考,暗寓了“知我者其天乎”的悲悼。《九歌》更是具有极高艺术成就的民歌之作,在“洞庭波兮木叶下”的氛围中透露出屈原本人被放逐的哀怨,在汉代乐府与七言诗的发展中,《九歌》呈现出重大的影响。如郭建勋所说,“由楚辞体的上述三类句型演变成七言诗,是可以在早期七言诗形成的历史事实中得到验证的”[3]。乐府诗中的《箜篌引》《陌上桑》等乐,都与以《九歌》为代表的楚歌有密切联系。它的影响力在拟骚中的缺失令我们有理由怀疑,汉代作者创作时对屈作已经进行了选择性的继承与阐发。《九歌》被排除在外便是因为缺乏他们所关注的,对屈原“忠而被谤”的悲剧命运与“忠直”品格的描绘。
更具体的佐证来源于拟骚具体的词句沿用,诗中,大量句意与屈作几乎相同。这一显著特征是它们历代被评价为“词气平缓,意不深切,如无所疾痛而强为呻吟者”的主要原因之一,也同时折射出拟骚之作对屈作篇目选择的侧重。在东方朔《七谏》中可选摘如下词句沿用的典例。
户服艾以盈要兮,谓幽兰其不可佩。(《离骚》)
弃捐药芷与杜衡兮。(《七谏·怨世》)
桂蠹不知所淹留兮,蓼(原作“蟲”)虫不知徙乎葵菜。(《七谏·怨世》)
斩伐橘柚兮,列树苦桃。(《七谏·初放》)
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离骚》)
枭鸮既以成群兮,玄鹤弭翼而屏移。(《七谏·怨世》)
欲从灵氛之吉占兮,心犹豫而狐疑。(《离骚》)
欲高飞而远集兮,恐离罔而灭败。(《七谏·怨世》)
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离骚》)
宁为江海之泥涂兮,安能久见此浊世?(《七谏·怨世》)
时亦犹其未央。(《离骚》)
惜年齿之未央。(《七谏·沉江》)
惜予年之未央。(《七谏·自悲》)
朝饮木兰之坠露兮。(《离骚》)
饮菌若之朝露兮。(《七谏·自悲》)
女媭之婵媛兮,申申其詈予。(《离骚》)
念女媭之婵媛兮,涕泣流乎于悒。(《七谏·哀命》)
鸾鸟凤皇,日以远兮。(《九章·涉江》)
鸾皇孔凤日以远兮。(《七谏(乱辞)》) [4]
从以上引文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汉代拟骚作者对屈作篇目的偏爱,他们显著地倾向于《离骚》与《九章》。通过具体词句的对比,我们能够借此推断这种倾向出现的原因。它们突出的共同点是阐发屈原保持德行,却不为世俗所容的不平。然而与屈作相比,拟骚之作过度强化了怨愤之情,进而将具有一定片面性的屈原形象塑造了起来。《离骚》中,哀怨虽然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但在表达过程中包含了“余不忍为此态也”,“怨灵修之浩荡”,“虽九死其犹未悔”的自我表白,在指责卑鄙小人,怨恨君王不公之外,以生不逢时的感伤,“穷困乎此时”的绝望等心理形成了更为复杂且动人的抒情性诗篇。而《七谏·怨世》则运用大量具有对比性的意象象征君子与小人,又引用古人得志与“忠而被谤”的两类例子烘托屈原所在之时小人得志带来的不幸,最终引出屈原愿自沉江流的决定。在叙述的过程中,忠直与穷困的矛盾被推至顶峰,而其余的“亦余心之所善兮”的自我选择,对不容于世的坚定,相对被削减至了不易被读者注意的状态。此外,《怨世》篇的抒情性被大大削弱,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枭鸮既以成群兮,玄鹤弭翼而屏移”的冷静叙述,成功地强化了屈原忠直的形象。
此外,在经过篇目选择后,拟骚对直接引用的句子的处理仍有值得探究处。除去一些如“沾余襟之浪浪”等修饰性描述,被沿袭的词句大约可以分为以下两种:对世事混浊的形容,以及重要人物的再次出现。前者如方圆不能相合,又如鸾鸟凤凰的远离,后者如传说中的屈原姊女媭,以及用于象征怀王的灵修。它们描绘了屈原置身的环境,使得通过以上强化构筑出的自我形象建立在更真实的根基上。当《离骚》中的灵修伴随着大量香草意象被提及,抑或女媭与担任媒人的鸩,神话中的宓妃同样作为重要人物时,读者更容易将其理解为屈原创造出的虚构人物。但经过拟骚平实冷静的重述后,它渐渐接近被认同的屈原生平阐述,成为汉代屈原形象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转变在经过两次引用的“时亦犹其未央”中尤其得到体现,它在《离骚》原文中上下文为“及年岁之未晏兮,时亦犹其未央。恐鹈之先鸣兮,使夫百草为之不芳”,更多是年岁未老的自我勉励,充满抒情色彩。但在《七谏》中,这一熟悉的句子却转而成为屈原自沉时尚未到知天命之年的叹惋。作者将其改为“终不变而死节兮,惜年齿之未央”,成为复述屈原生平中“自沉”结局的重要词句,进而强化屈原以身殉国的形象。这一形象的强化来源于熟悉词语的位置改换。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能够看到,汉代人在创作拟骚的过程中,通过篇目的选择,具体内容的沿用等手段继承了屈原的作品,并对其进行分割与重组,强化了为汉人所称道的忠君,不与浊世同流合污等品质,进而建构起作为偶像的屈原形象。这样的选择在汉代楚辞学内部乃至对后世的影响中都是极为重要的。
三、影响汉代屈原形象建立的新因素
近乎偶像的屈原形象在拟骚中并不仅仅通过继承与改变屈作文本实现,作为具有主体性的汉代文人,即便在创作中受到屈原生平与辞赋的限制,仍然发挥着自身的创造力。他们在作品中加入的新元素,便带来了屈原形象建构中的新的议题。在已有的学术成果中,大量学者对屈宋赋作在汉赋中的继承加以分析,强调楚辞中士不遇,不平则鸣在汉代文人心中引发的共鸣。这无疑是合理的答案。然而,屈原形象建构的过程多在拟骚中加以完成。在创作过程中,作者如何通过理解进行新的阐发,并通过这些新因素建构屈原形象。这些细节中同样存在大量可供分析的空间。
这些新因素被加入的基础是汉代文人对屈作的解读。正如上文所说,在阅读屈作的过程中,伴随着对屈原生平并不完善的认知,汉代文人对屈原形象已经拥有了主观的侧重,这导致他们在创作中选取了重点篇目加以继承,也同样推动新阐发的出现。以具有争议的《惜誓》篇目为例,其中“攀北极而一息兮,吸沆瀣以充虚”[5]显著体现的道教思想便吸引了赵逵夫先生的注意,并以此作为它不应为贾谊所作的论证之一。然而,作为记叙屈原生平的拟骚诗,这一表达的基础是它下文所描绘的“飞朱鸟使先驱兮,驾太一之象舆”[6],本源于屈原《离骚》中“驷玉虬以乘鹥兮”上天的幻想。因此,即使《惜誓》折射出作者的道教思想,这样的阐发也建立在对屈原作品与思想的理解上。这样的分析前提是难以被忽略的。
在这样的基础上再来对读屈作与拟骚,能发现许多有趣的东西。最为突出的是黄老思想在其中的显现。相关的表达在多处都有出现,如《惜誓》中“吸沆瀣以充虚”“澹然而自乐兮,吸众气而翱翔”[7]。这些“吸众气”的表述虽在《远游》“漱正阳而含朝霞” [8]中有所显现,但在汉代的背景下仍更容易让人联想到道家的神仙方术。正如王逸所引的《陵阳子明经》体现的那样,陵阳子明在《列仙传》中有载,他通过白鱼腹中所藏的秘方得知炼丹之道,并“上黄山,采五石脂,沸水而服之”,因此而成仙。他的经历充满着神仙方术之学的奇幻色彩,可以想见今日已经散佚的《陵阳子明经》所载的吸气之法同样应归入道家养生之属。《惜誓》后文中的“念我长生而久仙兮,不如反余之故乡”[9]的表述,更是对屈原《离骚》中充满想象力的上天求女剧情进行充满了道家色彩的解读。屈原由幻想中与神灵并行的贤者,一变为通过修炼道术获得升天与长生。在这样的背景下再描绘屈原“贤者之逢乱世”的处境,并对他不愿离去故国加以微讽,所持的逻辑便显然与原作不同。黄老之学的影响在更多较为隐蔽的地方同样有表现,如《七谏·沉江》中“浮云陈而蔽晦兮,使日月乎无光” [10],语本《文子·上德》的“日月欲明,浮云盖之”。《文子》为先秦时期的道家学派著作,在汉初随着黄老之说的兴盛得到流行。又如《九怀·陶壅》的“道莫贵兮归真,羡余术兮可夷”[11]与老子返璞归真的思想同样有着紧密的联系。
黄老之学的影响无疑影响了汉代拟骚作者对屈原的理解与评价。《惜誓》结尾便称:“使麒麟可得羁而系兮,又何以异乎犬羊”,主张屈原应飘然远举,“见盛德而后下”或是“远浊世而后藏”[12],不被故国所限制,学会明哲保身。这样的评价在后世已经遭到了大量驳斥。然而,它同样构成了汉代屈原形象的一部分。需要看到,拟骚作者作出此类评价的前提是屈原已经有了“吸众气而翱翔”的经历,在天界能够澹然自乐。但反观《离骚》,无论是“退将复修吾初服”,还是“将往观乎四荒”[13],都未为飘然远举提供有说服力的前提,主人公试图“历吉日乎吾将行”的依据是向神灵占卜获得的好结果,这与“远浊世”的表述存在较大出入。唯有当《惜誓》、贾谊《吊屈原赋》等作品为《离骚》中的神游天界增加了成仙之术的色彩,并结合屈原有才而不见用的事实,屈原拒绝离开楚地,放弃周游各国的忠君形象才导致了屈原不知留住有用之身,未能飘然远去的讥刺。从这个角度看,黄老思想在汉代屈原形象树立的过程中,同样有其一席之地。
其次,在汉代楚辞学兴盛的过程中,儒学思想毋庸置疑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14]“依《诗》取兴,引类譬喻。”[15]《离骚》在汉代获得“经”的地位,并与《诗经》并称,儒家思想在对其解读过程中發挥的作用已经可见一斑。然而,在具体的拟骚创作中,要从具体词句寻找儒家思想的影响,相对来说是较为困难的。它更多贯彻于对屈原“执履忠贞”的整体理解上,也与屈赋的文学地位密不可分。但在大量细节上,拟骚体现出汉代文人认知中《楚辞》与《诗经》的关联,仍然能够作为辅助材料侧面体现儒家思想与屈原形象塑造的联系。
在援引《诗经》词汇入骚这点上,《九叹》相对具有代表性。在体例上,它分为九首短诗记叙屈原的经历感受,并在每篇末尾有以“叹曰”为首的四言句,用于抒发强烈的感情。这些四言句不仅在体裁上与《诗经》句式极为相像,更是化用了大量《诗经》中的词汇。如《怨思》篇末“山中槛槛,余伤怀兮”,其中“槛槛”形容车行声,出自《诗经·王风》:“大车槛槛。”[16]又如《惜贤》:“江湘油油,长流汩兮”,“油油”王逸注为“流貌”,出自《诗经》“河水油油”,“忧心展转,愁怫郁兮”又与《关雎》“辗转反侧”有所联系。[17]在《九叹》每篇篇末的抒情性结尾中,作为汉代诗学典范的《诗经》出现频率如此之高,至少说明了在刘向心目中屈原所思与《诗经》“风人之致”具有一致性,也进而加强了屈作与《诗经》的联系。正如前文写屈原“吸众气而翱翔”体现了作者基于神仙方术理解屈作那样,《九叹》中的《诗经》词汇在体现作者儒家思想同时,塑造出了屈原与《诗经》密不可分的形象。
在词语化用之外,《九叹》对屈原的生平也进行了大量带有儒家色彩的解读。最突出的是《逢纷》篇末的“遭纷逢凶,蹇离尤兮,垂文扬采,遗将来兮” [18]。所谓留下文字给后人品读的想法,在屈原作品中并无依据。王逸将其解读为“以遗将来贤君,使知己志”,已经有些附会屈作的意味。它的内涵更接近于《孟子》中所记载的孔子语:“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19]在孔子编纂完《春秋》后,他认为后人对他的褒贬都将基于此书,将论著与编纂的作用看得极为重要。汉代古文经更是来自孔府的鲁壁藏书。除此外还有《离世》:“去郢东迁,余谁慕兮?”在离开故国后产生的无所依从之感,同样与儒家思想中的忠君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与《离骚》中“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存在一定的隔膜。这些例子都能够从侧面证明儒家思想在屈原形象塑造中占据的位置。
四、结语
总体而言,在汉代文人对屈原生平认识存在模糊,对楚地地理文化的认知并不深入的情况下,他们对屈原作品的了解具有更强的主观色彩,又在这样的理解上建构起汉代楚辞学中的屈原形象。其中,拟骚作为楚辞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形象建构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拟骚诗中,创作者筛选了重点进行沿用继承的屈原作品,并运用屈作中的原始词句强化了屈原的部分特征。这些特征在经过汉代新的黄老思想,儒家观念等元素引入后,得到了进一步阐发,显得更为突出。最终,通过拟骚的文本,一个更复杂也更具有汉代色彩的屈原形象被建构起来,并为后世的楚辞学带来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2]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5] [16] [17] [18] (宋)洪兴祖.楚辞补注[M].白化文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236,268-269,1-50,235-267,227,228,229,116,229,240,278,231,18,2,292,298,285.
[3] 郭建勋,闫春红.再论楚辞体与七言诗之关系[J].中国韵文学刊,2009(3):1-5.
[14] (漢)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3:2994.
[19] 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0: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