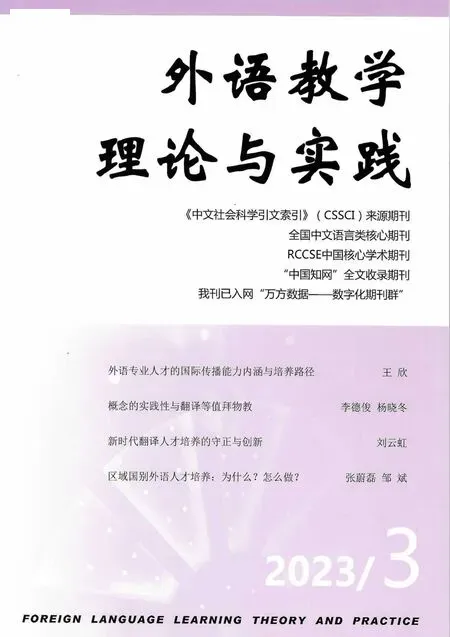视觉叙事视阈下的日内瓦会议中方外交口译研究*
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 人工智能语言研究院 许文胜
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 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经济人文学院 昌兰华
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 郑州科技学院 韩彩虹
提 要: 1954年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第一次以五大国之一的地位和身份参加讨论国际问题的一次重要会议。(1) 日内瓦会议是一个概括性的说法,本文系指1954年4月至7月举办的日内瓦会议,通常被称为第一次日内瓦会议或1954年日内瓦会议。本文从会议历史照片和影像资料出发,运用视觉叙事理论对中方外交口译进行研究。通过分析视觉文本,结合档案记载、纪录片以及回忆录等材料中的历史背景信息,以可视化的视角(visual perspective)对会场内外的口译活动及译员在历史进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进行了描述。研究发现,紧扣视觉叙事的本质,将视觉文本置于历史背景之下,能够更真实地还原口译场景并探究译员在历史进程中的多元角色。
一、引言
外交是通过会议、会谈等方式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以及国际争端和问题(徐亚男、李建英,1998: 3),其中所涉及的口译活动就属于外交口译范畴。外交口译研究近年来开始受到学界关注,但多数研究关注口译发生过程(姚斌,2022: 24),对于其他领域研究(如外交口译史的专题研究)相对较少。口译和外交通常交织在一起,历史年代越久远,两者之间存在的界限越模糊(Delisle &Woodsworth, 2012: 274),所以外交口译史研究通常包含于口译史研究之中。西方口译史研究起步较早,1956年德国学者Hermann的文章“Interpreting in Antiquity”讨论了口译职业的起源和译员在外交活动中的重要角色。(2)此文对后来的口译史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其原版德语文章由Ruth Morris翻译成英文,收录在奥地利学者Franz Pöchhacker等主编的The Interpreting Studies Reader(2002)中。此后,口译史研究逐渐受到学界关注。Roland(1982)和Kurz(1985)等人的研究都涉及外交口译领域。国内口译史研究起步相对较晚,马祖毅(1984)的翻译史研究和黎难秋(2002)的口译史专著涵盖了中国古代的外交口译活动。王宏志主编的论文集《翻译史研究》(2011—2018)与其著作《翻译与近代中国》(2014)也都涉及中国近代外交口译史研究。(3)《翻译史研究》共出版八辑,主要以中国翻译史为探究对象,注重个案研究,其中多篇文章涉及外交口译史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翻译研究出现文化转向,其研究重点逐渐超越文本本身。翻译研究与其他学科融合交叉,口译史研究也体现出跨学科的特征。西方口译史研究视角越来越丰富,绘画、明信片、照片以及视频等视觉材料在研究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Delisle &Woodsworth 2012; Fernndez-Ocampo &Wolf, 2014; Takeda &Baigorri-Jaln, 2016; Harrison, 2021),上述研究都包含了对外交口译的讨论。在国内,口译史研究材料仍旧相对单一(杨华波,2019: 75)。Lung(2011)对中国古代对外交往中口译活动及译员的部分研究依赖于图像史料的挖掘。毋庸讳言,国内口译史研究成果相对较少,以中国古代和五四前后为主,鲜有涉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口译史研究,研究材料和视角也有待丰富。
本研究选取五幅历史图片,从视觉叙事的视角研究新中国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中的外交口译活动。通过对视觉文本的分析和相关史料信息(包括档案记载、纪录片以及回忆录等)的梳理,重构会议期间中方外交口译活动,并对译员在历史进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进行描述,探究他们在历史进程中所扮演的多元角色。
二、研究框架——视觉叙事
Pimenta &Poovaiah(2010: 25)认为随着视觉研究与叙事研究的不断发展,视觉叙事亟需发展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他们将视觉叙事定义为“一种实质上且明确地在叙述一个故事的视觉内容”(2010: 30),这里的“视觉内容”指呈现具体事件的各类“视觉文本”。Kress和van Leeuwen(2006)将“视觉文本”(visual text)视作与“语言文本”(verbal text)相对的概念,用其指代各类视觉材料。本文中的视觉文本指社会符号学意义上的意识形态物质化的一种形式(Moerdisuroso, 2014: 90),涵盖绘画、照片、视频和电影等在内的以人类视觉体验为主导的材料。视觉文本具有叙事功能,如Barthes(1989: 2)所言:“叙事承载物可以是口头或书面的有声语言、固定或活动的画面、手势,以及所有这些材料的有机混合”。
“视觉叙事历史悠久,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但对视觉叙事的关注与研究却是较为晚近的事”(马全福,2018: 135),其发展与视觉文化研究紧密相连。匈牙利电影理论家Balzs(巴拉兹,2003)于1945年首次对视觉文化进行了论述。摄影技术的发展使得视觉叙事进入了黄金发展期(马全福,2018: 138),在此基础上,视觉叙事研究不断深入,其理论不断发展,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Kress &van Leeuwen(2001,2006)的研究等。Kress &van Leeuwen(2006: 1)认为“语言语法描述词如何组成分句、句子和语篇,而视觉‘语法’则描绘视觉元素(人物、地点和事物)如何在视觉‘陈述’中有机组合”。他们把图像作为社会符号来分析,指出图像涉及的“再现参与者”(图像中描述的人物、地点和事物)和“互动参与者”(图像的制作者和观众)之间存在三种关系,即“再现参与者”之间、“再现参与者”与“互动参与者”之间以及“互动参与者”之间的关系(Kress &van Leeuwen, 2006: 114)。本文聚焦视觉图像中“再现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并以此对口译活动场景,特别是特定历史背景下“再现”的译员角色进行分析。
近年来,国内学者开始将视觉叙事理论应用于翻译研究中,包括儿童绘本不同语种的叙事结构比较(陈冬纯、陈芝敏,2019)和多模态翻译策略研究(吴赟、牟宜武,2022;陈静、刘云虹,2021)等方面。对于视觉文本解读的另一热门研究领域是历史学研究。图形图像作为视觉文本的一部分一直存在于人类发展历史进程中,在史学研究中,“图像也占了一席之地”(Burke, 2001: 9)。“图像所传递的视觉语言是一种理解世界和历史的认知模式。”(李明哲、陈百龄,2014: 73)当然只有对图像进行合理解读,才能重构视觉图像所蕴含的叙事内容。龙迪勇(2007: 42)指出图像叙事的本质首先必须使空间“时间化”,即把图像重新纳入到历史时间背景之中,从而为瞬间凝结的图像提供有关联的时间线索。Toury(2001: 53)认为翻译不只是“生成话语(generation of utterances)”,它应被视为具有文化意义的活动,显然翻译研究离不开产生翻译活动的社会文化背景,这与图像叙事研究的本质相契合。
三、日内瓦会议中方外交口译活动
国际会议以国际化为其主要特征,需要提供包括会议口译在内的完善的语言翻译服务。1919年巴黎和会使用的英法交替传译被视为会议口译的开端(Phelan, 2001: 2)。二战后,联合国等国际性组织相继成立,会议口译经历了空前的发展(许文胜、程璐璐, 2020: 122),成为国际交流互通的重要途径。日内瓦会议与其他国际性会议一样对快速有效的语言转换有着巨大需求,因此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便是担任口、笔译任务的译员。新中国在国际舞台初露头角,它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一批合格的译员来筑起对外交流与合作的桥梁。
1. 译员的选拔
选拔翻译人员是为参加国际会议进行准备工作的重要环节。新中国第一批外交和翻译人员主要由当时外语院校的外语人才及原中央外事组懂外语的干部组成(徐亚男、李建英,1998: 19),但这两类人才数量严重不足。随着新中国的国际地位稳步提高,与中国建交或半建交的国家越来越多,翻译力量匮乏的问题突出,甚至会出现派不出驻在国语言翻译的情况(徐亚男、李建英,1998: 20)。在此背景下,政府需要从各方面调集和选拔翻译人才参加涉及多边外交的国际性会议,这从译员群体的构成可以得到印证。《在日内瓦会议上——熊向晖工作记录解读(一)》(2022)中提到了中国代表团成员的详细名单。在最后确定的人员名单中,翻译人员归属秘书组,王炳南任组长,共 26人,包括“俄文翻译李越然(政务院专家工作室资料组长)等 4 人;英文翻译章文晋(天津外事处长)、浦寿昌(政策委员会科长)等4人;法文翻译陈定民(北大教授)、董宁川(联大驻维也纳秘书)2 人”(傅颐,2022: 49-50)。名单显示,翻译人员是从各个岗位上抽调而来。同时,这是新中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参加国际多边会议,周总理非常重视翻译的质量,对翻译的选拔慎之又慎。曾任“毛泽东选集英译室”主任的徐永煐被邀请对初选的十几位参加口笔译的同志进行测试,对翻译速度和准确性进行评定,并分别确定了口笔译的人选,以及中译外和外译中的人选(傅颐,2022: 50)。俄文翻译李越然回忆道,“总理提出每个环节都要认真准备,甚至还组织了一次模拟会议,搞翻译练兵”(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2000: 195)。
由此可见,虽然翻译人员紧缺,需要调集各方人才,但是选拔和培训工作一丝不苟,非常严格。新中国政府为国际政治舞台上的首演做了充分准备,从译员的选拔工作也可管窥一二。
2. 外交口译活动
日内瓦会议中的中方外交口译,可分为大会口译和会场外各类外交活动中的口译。会场内的中方口译活动离不开会议的整体安排。日内瓦会议讨论的是朝鲜和印支问题,涉及多国代表参会。关于正式会议中的语言与翻译,在讨论朝鲜问题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做出如下规定:
正式语言有五种——法文、俄文、英文、中文及朝鲜文。每日轮换翻译。第一天,就是今天,用法文;第二天,就是明天,用俄文;第三天用英文;接下去用中文与朝文。今天的演说将连续译成法文,与法文同时,则译成其他三种文字。今天用法文所做的演说则将首先译成俄文。用五种正式语言以外的发言者,必须提供自己的翻译,将发言译成五种正式语言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2006: 31)
从上述信息判断,大会所采用的翻译方式是接力同传(relay interpreting),即通过第三方语言将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Shlesinger, 2010: 276),它是“会议口译的一种特有形式”(Setton, 2010: 69)。中文是大会五种正式语言之一,因此中方代表发言时无须提供自己的翻译,由大会提供同传。会场内多国代表出席,中方译员在会场为代表团成员与他国代表的临时交流提供口译,也为代表团成员提供意见或咨询。据俄文翻译师哲回忆,译员浦寿昌随代表团参会,“不离周恩来左右”(师哲、师秋朗,2001: 422)。师哲在回忆录中也提及了自己的工作任务:“开会时,我每场必到,即使不在翻译,也要一字不落地听其他人翻译,如发现差错,必及时纠正”(师哲、师秋朗,2001: 421)。
除正式会议外,中方在会场外的各类外交活动也涉及大量的口译任务,包括与其他国家主要领导及各界人士会晤、中方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以及代表团成员与记者的会见等等。据档案记载,会外的重要接触和磋商都有详细的谈话记录,并注明了会谈的时间、地点、主要参与成员,包括双方或中方译员的姓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2006)。另据熊向晖(2019: 95)回忆,“当时有许多国家(主要是法国)的人民团体拜访中国代表团,先后来访的各国人民团体有505个,共3800多人”。
综上所述,在日内瓦会议这种国际重大外交场合,口译活动无处不在。中国代表团在会场内外参与各种外交活动,积极宣传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并为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做出努力和贡献。
四、视觉叙事视阈下的口译活动分析
对于日内瓦会议的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会议的过程(侧重历史记载)、会议目的和意义,以及主要参会者的历史贡献,而对于会议中涉及的口译活动及其译员的贡献鲜有关注。有关口译活动的描述及译员信息散见于档案材料和与会人员特别是译员的回忆录中,研究者能参考的文字材料有限,因此“照片图像无疑是很好的切入点”(李澜,2018: 76)。随着口译史研究视角的多元化发展以及图像史料研究的兴起,我们可以从历史留存的摄像和摄影等视觉文本中获取并解读更多关于历史上的口译活动及译员信息。日内瓦会议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据记载,“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媒体和记者前来报道”(李云礼,2022)。中方负责新闻报道的除了代表团相关成员外,中国新闻单位组织了精悍的记者团远赴日内瓦,他们在新闻报道中也留下了宝贵文字材料、摄像和摄影资料。(4)据《1954年日内瓦会议追记》一文记载,新华社的刘东鳌是摄影记者,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也选派了苏河清、龙庆云两名摄影师前往日内瓦(杨翊,1999: 29)。
1. 视觉文本概述
由于年代久远,能获取的新闻图片有限,本文的五幅图片分别来源于thelocal网站上一篇关于日内瓦的文章(图1)、(5)详见https://www.thelocal.ch/20181010/in-pictures-geneva-the-worlds-incubator-for-peace-and-policy-since-1920/(2022-07-12)。解密档案(图2、图3和图4)(6)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自2004年起逐步解密开放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外交档案,本文所参考的主要档案材料来自于2006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一集)》,图2、图3和图4来自本书插页第3、4页。和央视纪录片《1954日内瓦风云》中的影像资料(图5)。(7)详见《1954日内瓦风云》系列第五集——和平之声https://tv.cctv.com/2016/11/11/VIDEfPnHLUuFyPxjNjOkasmH161111.shtml?spm=C52507945305.Pknrmn9ZARZj.0.0(2022-07-24)。图1、图2所定格的是中方在大会会场内参加正式会议的场景,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图3、图4展示了周恩来在会场外与英、法国家领导人的外交会面,它们是中方利用日内瓦会议积极展开外交活动并取得重大成果的见证;图5中周恩来与文化名人卓别林的会见则表明中方利用公共外交的渠道增进世界对新中国的了解。所选取的五幅图片见证了中方在日内瓦会议期间的各类外交(口译)活动,也为译员在场提供了证明。

图1. 日内瓦会议局部会场照片

图2. 日内瓦会议局部会场照片

图3. 周恩来会见艾登

图4. 周恩来会见孟戴斯-弗朗斯

图5. 周恩来会见卓别林
本次会议在日内瓦万国宫(又名国联大厦)举行,图1和图2分别拍摄于讨论越南问题和印支问题的会议会场。图1的文字说明记录了照片的拍摄时间为“1954年4月27日”,日内瓦会议开幕的第二天。除此之外,关于照片中的人物,只提及了“周恩来率领的中国代表团”以及“莫洛托夫率领的苏联代表团”。图2配文中提供了照片拍摄的大致时间为“1954年4月”,该图载于档案文件中,一一列出了中方参会人员的姓名。两幅照片展示的皆为会议的局部会场。图1中的中方代表,前排就坐的是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和外交部副部长兼驻苏联大使张闻天(从左至右),而后排从左开始依次是英文译员章文晋、外交部副部长王稼祥、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和代表团顾问乔冠华。图2中前排左起分别是李克农、周恩来和张闻天;第二排左起分别是章文晋、法语译员陈定明、英文译员浦寿昌、代表团顾问陈家康和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
图3和图4摄于花山别墅的会客室。图3下方的文字说明是“周恩来在驻地会见英国外交大臣艾登(1954年5月)”,交代了会谈的参与人、地点和拍摄的大致时间。图4下方的配文写道“周恩来在驻地会见法国总理兼外长孟戴斯-弗朗斯(1954年6月23日)”,同样交代了会谈的参与人、地点和拍摄的时间,不过记录的拍摄时间更为精确。颇为巧合的是,这两张照片不仅拍摄角度、背景基本一致,照片的文字说明模式也非常相似,同样都没有提及照片中的“第三人”——译员的信息。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一集)》(以下简称《档案选编》)中“会外接触和磋商”的谈话记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2006),可以确认图3位于中间的是英语译员浦寿昌,图4位于相同位置的是法语译员董宁川。
图5是《1954日内瓦风云》中影像资料的视频截图。它是这五幅图片中唯一一个室外会谈场景,展现的是一次非正式会见。1954年7月18日晚上,周恩来在驻地宴请喜剧电影大师卓别林及其夫人。图中聚焦的是前排三位人物,从右至左分别是周恩来、章文晋和卓别林,而位于后排的是乔冠华。
2. 口译活动的视觉叙事分析
图像资料记录下历史的瞬间,它们“像文字和口头证词一样也是历史证据的重要形式”(Burke,2001: 14)。以上所选取的视觉文本,一方面描绘的是一幕幕的会议(会见)活动(包含口译活动)场景,而另一方面也展示出其中的人物(包括译员)成为构建这一历史活动的必不可少的元素。
1) 会场内外的口译活动
图1和图2拍摄的是包含中方参会人员的局部会场照片。图1中,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英文缩写“P. R. O. C.”的席卡后坐着周恩来总理,而他的正后方是英文译员章文晋,图2中三名中方译员紧邻而坐于总理身后,这样的座次安排方便译员为总理及时提供意见和咨询等相关信息。日内瓦会议的讨论采取闭门方式,记者不能入内旁听或采访,只有在会议开始之前才允许记者进入拍照(何理良,2013: 63)。在第一次讨论越南问题的全体会议上,会议主席一开始就说道,“今天第一件事是给我们照相。这需要十分钟。现在我将请摄影记者进来照相”(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2006: 29),10分钟后记者们离开会场。同样,在讨论印支问题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一开始也有大致相同的流程。由于照片拍摄的角度问题,我们难以看清图1中周总理桌上摆放的其他物品,但是可以看见苏联外长莫洛托夫面前的桌上摆放的是话筒和耳机,显然是分别用于发言和收听同声传译的信息。《日内瓦会议与对外宣传》中刊载了一张同一位置的照片,(8)姚遥,2011,日内瓦会议与对外宣传,《对外传播》第9期: 28-29。能看见位于总理后排的王稼祥的手腕上挂着耳机,从中可以推断,此刻正式会议尚未开始,代表们在接受记者拍照的同时也在为会议做准备。
图3和图4的拍摄地点是周总理接待其他国家代表以及各界人士的花山别墅会客室。两幅照片中背景一致、座次安排相似,身后的橱柜中摆放着具有中国特色的瓷器、工艺品等。《1954日内瓦风云》中提到,“周恩来总理未雨绸缪,临行之前特地从故宫博物院,借了十二件国宝装饰别墅”,(9)详见《1954日内瓦风云》系列第四集——会场内外https://tv.cctv.com/2016/11/10/VIDEklcQDdASJALjvn6x7wwC161110.shtml?spm=C52507945305.Pknrmn9ZARZj.0.0(2022-07-20)以此展现中国浓厚的文化底蕴,这也是周总理的文化外宣策略之一。两幅照片中,外宾和周总理相邻侧身对坐,整个谈话的氛围看上去轻松自然,照片记录的这一刻每个人脸上流露着笑容。图3中周恩来与艾登谈笑正欢,而译员浦寿昌目光注视在照片之外,似乎在与艾登身旁的随行人员(或为英方译员福特)互动交流。(10)据《档案选编》记载,日内瓦会议期间中、英会外接触与磋商时英方陪同出席译员名为福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2006: 235)。浦寿昌右手握笔,左手拿着笔记本,与图4中译员董宁川相比,前者的手势更加放松,似乎也正沉浸在会谈的轻松氛围之中。图4中周恩来和董宁川同时注视着法国总理孟戴斯,董宁川同样右手执笔,左手拿着笔记本,目光专注在法国总理孟戴斯身上,很显然他在认真聆听或正在翻译。孟戴斯此刻注视着董宁川,但同时也似乎在与周总理进行眼神交流。三人并没有直视镜头,而是相互注视,给人一种“过程感(a sense of process)”(Kress &van Leeuwen, 2006: 55),这一“动态”的互动交流仿佛呈现给观众口译的实时发生过程。
图5中的这次会面是一次成功的公共外交典范。定格的这一刻,卓别林正注视着镜头,脸上露出的笑容很显然在向摄影师和潜在的观众传递关于此次会面积极、正面的信息。虽然截取的静态图片无法传递谈话的具体内容,但是从图中可以看出双方畅叙甚欢。总理与卓别林的顺畅沟通,起到重要作用的便是译员章文晋。再者,由于这是一次非正式会面,双方的交流所涉及的口译也无需笔记,章文晋并没有像图3、图4中的译员一样手握纸笔。因此,对于观众来说,图中译员的身份很容易被忽略,但是其作用却在双方轻松愉悦的沟通中显现出来。
2) 聚焦译员多元角色
Pym(2014: ix-x)提出翻译史研究“四原则”,强调了译者作为译史研究的中心地位。姚斌(2012: 73)认为,与笔译史相比,口译史研究更应以译者为核心。视觉叙事则为研究译员及其重要作用提供了更为直观的视角。“照片提供了一种容易被忽视的了解翻译行为的途径,特别是对于译员的角色以及他们的重要意义的了解”。(Edwards, 2014: 25)对于特定事件,照片和影像等视觉文本是历史拼图中不可缺少的一角。照片和影像中记录的人物(包括译员)仿佛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展现于观众面前,同时也使得研究者可以多角度探究译员在特定历史进程中的贡献。
在译员的诸多角色中,最基本的是语言协调者。没有译员,会谈中的双方就无法交流下去。一些比较私密的会谈只有核心人员参会,其他人员会被暂时排除在外,但是译员一定在场。译员因而具有很显性的特征,他们从实体上来说是显著的“第三方”。
根据座次安排和相关资料梳理比对不难确定图1和图2中译员的身份信息。图3和图4则记录下口译活动的瞬间,译员浦寿昌与董宁川皆处于照片中更加凸显的中间位置,这体现出译员在双方沟通交流中的显性作用。颇有意思的是,以上周恩来与英、法领导人的会晤中,译员位置突显;而中方在驻地与苏联外长、印支三国代表团团长的会见中,照片里只有各国领导的身影,译员并不在其中。(11)详见《档案选编》插页第3、5页照片。这固然与现场会见的座次安排有关,但从历史背景考察,译员微妙的沟通作用便显露无疑。Kress和van Leeuwen(2006: 47)认为,“视觉结构并不只是对‘现实’结构进行复制。相反,它们生成的现实世界的各种图像,与那些生成、传播和阅读这些图像的社会机构的利益紧密相连。它们是表达意识形态的。视觉结构绝不只是形式上的,它们蕴含重要的语义维度”。这意味着“视觉图像和语言一样,对社会现实和心理现实既具有复制作用,又具有重新建构的作用”(朱永生,2018: 22)。实际上,当时只有少数西方中立国家如挪威和瑞典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而英、法作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阵营国家尚未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人民日报》曾以《举世瞩目的日内瓦会议》为标题,(12)详见《人民日报》1954年6月13日第5版。用整个版面的照片报道了日内瓦会议取得的成就,其中位于版面中间的正是周恩来会见艾登这张照片(图3)。这也反映出,新中国期望利用日内瓦会议这一契机与英国等其他国家尝试建立联系,为日后与这些国家的关系进一步发展奠定重要基础。在这种情况之下,中方和英、法领导人的会见更要注重交流沟通的过程,因此译员的角色在这一政治背景下就显得尤为重要。王炎强(2020: 14)认为,译员显身与隐身需要从“人际关系、机构导向和社会因素等沟通的多个层面分析”。从中方对外宣传的角度而言,作为沟通纽带的译员,其形象在这两幅照片中被凸显出来。
译员作为中间方,保证不同语言的交谈双方得以进行顺畅的交流,这是他们最基本的职责。随着翻译研究的深入,译员角色的多元性已经得到学界普遍认可。译员的多重身份是由社会工作分工的复杂性所决定,也是由不同口译类型对译员的特定要求所决定。外交译员的政治身份突出,因为外交翻译关乎国家利益(施燕华,2009: 10),译员承担了外交和政治工作的使命(许文胜等,2021: 12)。
从视觉叙事的视角,我们也可以探究译员所扮演的政治角色。图3、图4的会谈中,译员与总理着装一致,都是中式服装——中山装,而艾登和孟戴斯身着西服。中方代表团为每位成员定制了中山装和西服。关于着装,外交部刚成立时规定中山装作为正式礼服用于重大正式场合,而一般外交场合可以穿西装(徐京利,2005: 252-253)。据译员管震湖回忆,临行前做预演时,李克农也和代表团成员交代了相同着装要求。(13)详见《日内瓦1954》第一集——临行之前https://tv.cctv.com/2016/11/07/VIDECIo2iOxNqXFMAix9viZg161107.shtml?spm=C52507945305.Pknrmn9ZARZj.0.0(2022-07-16)。虽然后来会议期间关于着装的要求没有严格规定,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山装仍然是大部分团员的首选。(14)同上。图3、图4中的小型会谈涉及人数有限,着装可帮助区分政治身份,图像中的西装和中山装作为文化标识将“再现参与者”之间的身份明确区分开来。《1954日内瓦风云》中提及,当董宁川顺利成为日内瓦代表团翻译时,他感到非常兴奋,这次成功入选实现了他“跨入政坛的梦想”。(15)同上。这说明董宁川对自己的这一政治身份有强烈的认同感。《中国近代留法学者传》也提到在日内瓦会议期间董宁川“努力学习,掌握情况,面对尖锐复杂的斗争,力求翻译准确通顺,充分表达了周总理既坚持原则又灵活的会上发言”(吕章申,2008: 407),这些都体现了外交译员的政治身份。
图5中的会见被称为一次天才的外交行动(刘国新,2000: 80)。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在驻地举办了许多会外活动,使得花山别墅成为中国对外宣传的阵地。总理在处理政府外交公务的百忙之中,还时时刻刻想着通过人民外交的途径(《我们的周总理》编辑组,1990: 310),在国际上广交朋友,争取更多的国家和人民了解、支持中国。借助于译员的桥梁作用,“通过与外国文化名人互动交流,此类人民外交活动既增进了外界对新中国的了解,也是对一些别有用心的西方舆论妖魔化新中国的有力回击”(国际在线,2019)。会议期间,总理要求“全体代表团成员宣传‘自己’,了解对方,结交朋友”。(16)详见《周恩来诞辰120周年特辑(四)》https://ishare.ifeng.com/c/s/v002Fd7xDs1n3Ht55mEtyg-_c1NiOC0PiA1ZJAxhQTTz----ntMR5UCZ--nho9UxhgRB6s9eZclT5auWEoRNgXczXmJX4g____(2022-08-27)。图片定格的这一瞬间,译员章文晋已超越了“中立”的语言协调人的角色,在观众眼中他也是一名对外展示中国新面貌的宣传员。外交译员“不只是一个传声机器,……(还是一名)革命干部”(施燕华,2013: 46),他们是有明确政治身份和任务的外交人员。
五、结语
文中选取的照片和视频截图展示的是日内瓦会议中方外交口译活动的缩影,为研究即时性的口译活动提供了可视化的素材,为通常被视为“隐身”的译员提供了显性的在场证明。视觉文本对于口译史研究已不是单纯的辅证材料,作者通过视觉叙事分析并结合历史文字信息重构了日内瓦会议中方外交口译活动场景,并挖掘了在特定历史背景与意识形态下的口译活动本质,凸显了中方译员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译员承担的不仅仅是语言转换的角色,他们积极参与到口译活动的构架和信息意义的共建中,成为历史的见证者,同时他们也是有着明确政治身份的外交人员。
由于口译的特殊性,早期口译活动的记录手段有限、内容不完整,口译史研究通常较为间接地依赖于史料记载和回忆录等材料。视觉文本描绘了包含译员在内的口译活动场景,为以译者为中心的口译史研究带来更直接的证据和更直观的视角。历史照片和影像资料的挖掘以及视觉叙事研究的不断发展为探索口译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与路径。借此,口译史研究也将取得新的提升和更大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