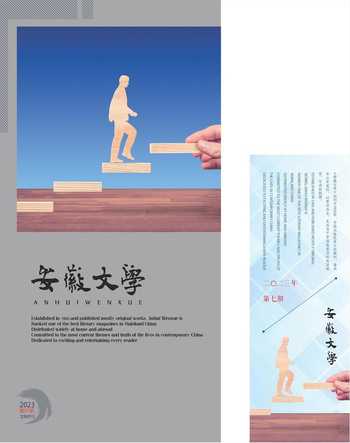农具帖
赵丰
犁
拂晓,鸡鸣,鸟叫。
大伯牵黄牛出门,牛背上架着犁。
麦子收了种玉米,大伯赶牛去犁地。
犁是耕地的农具,一根横梁连着厚重的刃,用绳子系在牲畜身上,用来耕出槽沟准备种玉米。
黄牛牵犁,大伯左手牵绳,右手扶犁,一脚一脚踩进泥土,一脚一脚慢慢拔起。犁在大伯的操纵下翻搅着田里的土,泥巴随着犁齿跳到大伯的身上。大伯赶牛的鞭杆儿光滑,鞭子细长。他的鞭子从不落在牛身上,因为它从不偷懒耍奸。大伯抽鞭是一种心情的宣泄,那种精神层次的张扬。他胳膊一扬,鞭子在空中绕一个很圆的圈,叭——,声音脆亮,黄牛就哞——一声响应。
哗哗哗——黄牛拉犁穿透泥土,泥土被犁撕成两半。从地这头犁到那头,再折回来,直至一片地犁完。
耕翻泥土,是犁生命的意义,是它别无选择的生存方式。犁想着,泥土是我生命的伴侣啊。于是,垦荒、翻地、灭茬、培土、收垄,犁总是迈着坚实的步子,沉重却幸福。
宽阔的泥土,是犁生命的背景。它的命运,系在泥土身上。它深深地插进泥土,表达它对于土地的虔诚。
犁着犁着,太阳就出来了,阳光渐渐浓烈。这是夏至的节气,阳气达到极致,天空辽远、阔达。日上三竿,大伯和黄牛都是一身汗。大伯让黄牛歇了,他也要喘口气。他脱了衫子擦着头上的汗,看看牛,瞧瞧犁。这对好搭档,陪了他大半生。大伯没读过书,当然不知道人类的农耕文明正是从犁开始的。史书记载,大约公元前2686年至公元前2181年的埃及古王国时期已有农民使用双牛牵引的原始木犁耕地,荷马时代已经用双牛牵引犁深耕。西亚、古巴比伦、古亚述以及南亚次大陆的古印度,使用铁犁牛耕大体上也在同一时代,即公元前10世纪前后几百年间。如此,犁的先祖在农具里是资历最老的。在中国,这个叫犁的家伙,也有着漫长的历史演变。新石器时期它是石头做的,叫石犁;到了商朝至汉代它变成了铜,汉代以后才成为铁。它的名字也不断翻新,铁辕犁、翻转犁、旋耕犁、解放式步犁、双轮双铧犁……人类社会发展至今,拖拉机替代了犁,它的使命也就结束了。
《说文》曰:“犁,耕也。”这是汉字里最早对犁的解释,所谓的农耕是由犁而来的。在农耕文明里,“犁”是“农”的图腾,其形象被书于神仙画或门额作为祖训,传给子孙后代。
大伯没读过历史,可他对犁的情感,丝毫不逊于我们的老祖宗。
太阳升至半空,大伯牵牛从地里回来,犁仍在黄牛的背上。进家门,大伯卸下犁,蹲下身用手抠下粘在犁上的泥巴,大娘给他递过来饭碗,他说不急,牛饿了,我先给它拌料去。
连 枷
麦子刚刚扬花,父亲去山坡上砍了一捆酸枣树枝回来,猫着腰在院子里又是用刀,又是动斧,将它们做成木条,拼接成一个扇形面,用牛皮、牛筋缠绕在那个扇形面上。然后他用砍刀在院子里的榆树上砍下一截木棍,削薄了木棍一端,架在火上烘烤。薄薄的棍头渐渐弯曲时,父亲让我帮着压实木排,他用铁丝把木棍与木排固定在一起,又用一根木轴将它们牵连在一起。
這是做连枷的过程,描述起来就几句话,但父亲却忙活了大半天。半下午的时光里,那个木条做的扇形面就被靠在土墙上晒太阳。
我知道父亲喜欢使唤自己亲手做的农具,不过连枷难做,他请教了三爷多次,才敢下手。
父亲一脸的笑,说:“这下就不用出门借别人的了。”
连枷,百度的解释是“用来击打谷类使壳剥落的农具”,碾儿庄人说它是“赶”麦粒的。麦子收回家,摊开在门前或院落的阳光里,用手摸摸麦穗儿干透了,就该使唤连枷了。村子人不叫使唤,叫甩。这活不光要力气,还要技巧。不会甩的人,甩上一阵胳膊酸困。刚开始父亲也不会甩,斜对门的三爷就过来给父亲做示范。他轻握连枷把,古铜色的肩膀上跳动着耀眼的阳光,与铺排在地的麦秆儿形成了一种呼应。三爷双臂轻举木排,运用手腕的力量旋转着木排和手柄的结合处,在连枷手柄快速下落的瞬间,才猛地转动平排,将一身的劲儿全部凝聚于手柄之上。那一刻,连枷如拉开的弓弦高高跃起,扇形的木排直击麦穗。经过“啪啪啪”一阵敲打,麦穗开花,麦粒落地,或在阳光下飞溅起扇形的麦浪。
这就是连枷脱粒的过程。
好多次,我都想在文字里描述三爷甩连枷的情景,但总是找不到感觉。是的,四季轮回的农事,农人都能将它们摆弄得妥妥帖帖,哪一样耕作的技巧,不是千百年来农人汗水的结晶?我昔日的文字总是高高在上,哪曾抚摸到泥土的气息和农人的汗渍?
连枷不光脱粒麦子,稻子、谷子、黄豆,都要用它。
父亲甩连枷,母亲也不闲着。连枷砸出的麦粒会飞溅到门槛下、墙角落、草丛里,母亲端个碗,弯腰一粒粒去捡。这当儿,雀儿扬着翅膀从屋檐下扑过来,母亲便扬起胳膊将它们一一赶跑。等到捡完了,母亲挑些瘪粒撒在土屋的窗台,让雀啄。
连枷始于何时,当是千年之前了吧。泛黄的书册这样简洁地记载它:“连耞,击禾器。其制:用木条四茎,以生革编之。长可三尺,阔可四寸。又有以独梃为之者,皆于长木柄头,造为擐轴,举而转之,以扑禾也。”唐之前,连枷是单纯的农具,唐人仿其形制加以改造,用于守城。
连枷,是村庄宽厚的手掌。
扁 担
木制的扁担形体扁圆,韧而有弹性,两端系上绳箍,或打上铁箍,烙上洞眼穿上铁钩,一是防止所挑物体从扁担上滑脱,二是方便捆扎和钩起物体。穿了铁钩的扁担,会像上了套的牛一样听人使唤。
扁担的作用是挑水、挑土、挑柴、挑粪、挑庄稼,铁匠、货郎、炸米花的,也是用扁担挑着担子四处晃荡。不过,他们肩上的扁担,就不属于农具的范畴了。
我有时想,碾儿庄就担在扁担上,一茬茬的人挑着扁担过着日子,故乡人的柴米油盐都被它一肩挑了。在舒缓悠长的时光里,扁担经过岁月的发酵,竟有了黄酒的清香。
肩挑扁担,关键是要找平衡点,把身子打开,攥住担子两端的绳,固定和调整好平衡点。没有平衡点,担子忽高忽低,行走吃力。其次是要学会借力,好的挑夫喜欢使用两头上翘的长扁担,负重后随挑夫的脚步上下颤动,扁担在肩上颤悠悠弹跳,挑夫身子的重心变化和步子的移动形成跳跃节奏,身摇摆,臂甩动,颤中有扭,颠中有跳,舞蹈般的一步一闪。这不是为了好看,而是为了减轻被担之物对身体的压力。如果挑长途,挑夫还要适时换肩,行家里手换肩不需要放下担子,身子一转,扁担就换了肩,像魔术师变戏法。
扁担的颤动,在我看来是柔情,是诗意。一头挑着太阳,一头担着月亮,如果少了柔情诗意,那日子便会漆黑无光。
晚霞落尽,唯有一抹夜风,挑担人不知所终。
扁担,被碾儿庄人长久地闲置了。主人当下的日子,离它渐行渐远。在老屋某个角落或者储藏杂物的偏房,它被随意冷落,阴暗的日子会一直陪伴到它消逝。既然无力改变主人的生活方式,它就唯有在黑暗中叹息。也许在梦里,它会露出甜蜜的笑。它是否梦见了稻谷、粪土、水桶,还有走街串巷的货郎?
那是它从前的乡村,从前的命运。
看见它,我的眼里依然会显出异样的光。
锄
一夜桃花开,母親带我去猫儿坡为起身的麦苗除草。
母亲从土墙的木楔子上取下两把小锄。她一把,我一把。
“一尺板子三尺把,尻子撅起腰猫下。”这是母亲指导我的锄地姿势。
与犁一样,锄也属于农具里的老字辈,其先祖可以上溯到春秋战国时期。自一出生,锄就是铁做的身子,刀身平薄而横装,被安置在一根长柄木把上。它的用途是松土、培土、间苗、除草,有大锄小锄、叉形铲形之分。以其用途广泛,锄的名字也五花八门:项锄、耪锄、镢锄、漏锄、稻锄、小锄……
古代诗人对于农具的吟诵,最多的是锄。“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唐诗人李绅《悯农二首》的这二句,后世妇孺皆知。李绅那首诗的背景应该是炎热的夏日,诗中的锄是父亲用的宽板大锄,也叫项锄,用来锄秋天玉米地里的杂草。
麦田里的棵棵杂草,与庄稼争水争肥争阳光,被我和母亲用锄连根铲下。在干干净净的田地里,我仿佛听见了锄亲吻泥土时那爽朗的笑声。
晚霞逝去,月光之下,锄皎洁的脸蛋,宛若少女般清纯。
锄幸得众多诗人、词人青睐。“五亩畦蔬地,秋来日荷锄。何曾笑尔辈,但觉爱吾庐。”陆游的《荷锄》是一首田园诗,与李绅的几句相比较,李诗味苦,陆诗味甜。为锄写出田园诗的诗人还有陶渊明,陶公的这二句:“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让锄拥有了诗情画意的生活情趣。辛弃疾的《清平乐·村居》更具生活情趣:“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一个五口之家,一座矮小的茅草房屋,屋旁一条清澈照人的小溪,溪边碧绿润目的青草。淡淡几笔,勾画出由茅屋、小溪、青草和锄头组成的和谐乡野。
荷锄而行,此为诗意。
如果说,前面几位赋予锄以生活之趣,宋词人张炎就为锄添加了浪漫。“仙子锄云亲手种”一句,极吻合作者作词“清空”“骚雅”之主张。作者之词常以清空之笔,书写万物之象。“锄云”,这是何等超越常人之想象。
镢
镢是刨地挖土的农具,用来挖坑和松土,头部是铁制的,由生铁高温锻制而成,握柄是木质的。整个身子由铁头、木把、镢楔(夹紧把与铁头)、铁匝(束子、固定把、楔)组成,按照用途分成耪镢、齿镢、菜镢、铁镐等。使用时两手一前一后,在前的一手用力将铁头向下刨,挖起泥土。
镢和锄都是摆弄泥土的老手,用法也类似,区别在于锄除草,镢挖地。
用镢挖地,要使出浑身的劲儿,但用力过度或碰到泥土之下看不见的大石头,镢前段的铁器容易和木柄分离。隔段时间,父亲就要在铁器和木柄的相接处洒些水,我问父亲为何,他说这样就不会因为连接处的木柄干燥收缩而脱落。每次从地里回来,父亲都要用干草或木棍除去铁器上的湿土,以免镢头生锈。
镢有一个称呼:镢头。这样叫着,就显示出了人性的亲切。是的,无论怎样的农家,都少不了这个农具。它把坚硬的土地开垦成良田,长出果实饱满的庄稼。镢想着,没有我,哪儿来的五谷丰登?在农夫的汗水里,它一脸正气,大有舍我其谁的架势。
在所有农具中,镢的使用频率是最高的。开荒、松土、开沟、挖渠、点种、刨根、撬石块……它是一个大男人,泥土在它面前,宛然一个夫唱妻和的女人,随它摆布。
碾儿庄一头在山坡,一头在平原。平原播种时用牛翻地,在山坡上就要靠镢。山坡上多石块,乡亲们常常是汗流浃背,将腰折成一条弧线,才能开挖出一块土地来。
木把高高扬起,铁头在阳光清风中闪闪发亮。在农人的手里,镢上下舞动,左抡右劈,用工笔绣花似的劳作,为大地织出一幅锦绣。那齐整的挖痕,如同刻意雕刻的艺术品。可谁知道,这般诗情画意的句子背后,掩藏的是农夫挥镢的汗水。
镢的用场不全在坡地,平原土地里的旮旯拐角(碾儿庄人叫角角地)无法用牲口来犁地,这就要镢出场了。
出工或收工,镢被农人扛在肩上。镢瞧瞧阳光,沐浴着风,神气地昂着头。
一个称作镢的农具,镌刻着千年农耕的痕迹。
耱
想起耱,便瞧见岁月的古老。现在的乡下,很难见到它了,也极少有人为它留下一张相片。
读过一则报道:1933年,山东滕县黄家岭出土了一幅东汉时期耕耱画像石(局部),前为一农夫驱一牛一马耕地,后为一农夫驱一牛耱地(粉碎、平整已耕翻的土地)。东汉之前是否就有耱,不得而知。
耱的身子用手指粗细的荆条做成,长条,两头有齿,用来平整翻耕后的土地,使土粒更酥碎,泥土更平展。否则种子撒进泥土后,天若久不落雨,就很难出芽。
一个矮壮的汉子领着一头黑骡子牵引着耱,出村走向田野之路。此情此景,是我少年时代夏天清晨里的一幅画面。麦收了,地犁了,要赶紧弥合泥土的那些裂缝,否则阳光会蒸发土壤表层之下的水分,玉米种子播下后会不好发芽。
骡牵着耱到了地头,矮壮的汉子将耱卸下,让它平躺在犁过的黄土上,接着汉子就站在它荆条编制的身上,让马或骡子牵着它耱地。汉子双手牵着牲口绳,直挺挺地站在耱的身上,为它增加压力。
耱是个急性子,总是抱怨着牵引它的骡子走得太慢。它坚韧的荆条在阳光下咧开大嘴,呼哧呼哧喘气,使劲把土块弄碎,把土缝弥合,在地面形成一层松软的土层,切断土中的毛细管,减少水分蒸发。因为有了耱,田里的泥土才有了熨帖的感觉。耱像是土地的梳子,将干裂、凌乱的土块细心地梳理得齐齐整整。一场雨后,玉米种子就从平展的泥土里出芽了。
耱看不见玉米的幼芽钻出泥土,耱完地,它安心地靠在农家院子的某个角落睡着了,等待秋风将它吹醒。玉米收了,牛犁了地,它会再次跟着主人下地。
那个矮壮的汉子我叫他德友爷,是耱地的把式,他体重大,将耱压得扎实,耱过的地平展如缎。他耱完了自己的地,就有人请他帮忙,乡里乡亲的,他从不推辞。他站在耱上,身子挺得笔直,头颅高扬,像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
耱完一片地,德友爷、黑骡子,还有耱,都在地头喘着粗气。
德友爷平息下来,拔出腰带上的烟锅,用烟锅头挖出烟袋里的旱烟,划了火柴点燃。之后,他就拉长目光,检阅自己耱过的地,傻傻地笑。
德友爷離开人世那年,拖拉机开进地里,犁、耱,以及牛和骡子都没有了用场。拖拉机深翻之后,一个碾磙似的家伙将翻起的泥土碾平,后来我知道,那家伙叫平田铲运机。
镰
布谷鸟叫了,有两声的:“布谷,布谷”,有四声的:“麦黄草枯,麦黄草枯。”清脆,悦耳。天热了,风暖了,人一出门,尽是晃眼的阳光。出村来到田野,人的手掌搭在眉头,一眼望不到边的麦穗在风中摇曳,似乎在呼唤着主人:快收我回去!
人就想到了镰。
镰是它的小名,大名镰刀。
镰被父亲挂在老屋外的土墙上,镰刃生了锈,黑乎乎的。在布谷鸟的叫声催促下,父亲精神奕奕地走出屋门,从土墙上取下镰,在磨石上洒了水,蹲在地上将镰刃贴在磨石上来回推动。等父亲直起腰,镰刃就一片锃亮。父亲磨完一把,又磨了第二把,给我手上塞一把,说,跟我割麦去。我刚上初中,父亲说十三岁了,是个大人了。
来到村外,金黄的麦田片片相连,像金色的地毯。田边的泥土已不再湿润,好多日子没有落雨了,泥土一片焦黄,正是下镰的好时节啊。父亲喜上眉梢,将镰举在头顶,划破一片阳光,掠来一缕夏风,然后猫下腰向我示范着下镰的动作要领。
父亲手握镰把,胳膊挥扬,手臂挥动间,割倒了一片麦子。他边割边捆,麦捆整齐地躺成一排。我割了不到一会儿,便满头的汗珠,父亲回头说,用镰刀不能浑身使劲,要把劲使在手腕上,胳膊抡圆,刀刃贴住麦秆了再使劲,你身子乱摇晃啥?我按照父亲的示范,一镰一镰地比划。割了有土炕大一片,我起身看父亲,他已经扔下我老远,汗水湿透了衣背也不歇口气。在他的心目中,麦子就是黄金,就是安稳的日子。
收麦的场景,被白居易写到了《观刈麦》这首诗中:“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那个“倍忙”啊,全家老少齐上阵,连“童稚”都要“携壶浆”给挥汗如雨的大人送水。
我家没有小孩儿,送水的事儿就归奶奶了。半上午时,奶奶一声吆喝,我和父亲歇了镰,在地头喝水,父亲用草帽扇着凉风,望着天上飞过的鸟儿。
多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是如此挥舞着镰刀,重复着一个姿势。在镰的挥舞下,片片倒下的麦子,以另一种方式接近土地,感受恩泽。
我还使用过一种弯镰,样子若一钩弯月。用它割草,一搂一大抱。
夕阳落山,西天一片晚霞,村庄的上空升起炊烟。父亲收了镰,歪斜着身子,向着炊烟的方向走去。
镰也回去。有炊烟的地方,是它的家。
筛 子
筛子的原料是竹篦,竹板条做筛口,细竹篦编筛帮,薄竹篾编网为筛底,故乡人叫它竹筛,圆形,有漏孔。网孔疏者为草筛,网孔密者为细筛,口径小者为小筛。
筛子的用途是过滤杂质,它长着慧眼,鉴别着粮食的真伪优劣,去粗取精。按其用途,筛子分草筛、圆筛、细筛、小筛、过筛多种。草筛用于为牲口筛草,分离草与杂质(沙土),以便择去旋筛时上浮的长草;圆筛用于麦、稻,在谷场上分离粮粒和柴糠;细筛分离粮粒、沙土和柴糠;小筛用于筛米。前者均为圆形,过筛是长方形,竹篾、铁丝编制的网为底,孔疏,用时斜撑,将被筛物撒在上面过滤。
无论哪种筛子,使用时双手要朝一个方向旋转,使被筛物形成漩涡,轻浮较长的柴糠浮于涡心,可用手抓了扔于地,较重的粮粒留于底,细小杂质则从网底漏下。
鸡这个名字与汉字“饥”音相同,肠胃功能极好,总是吃不够,祖母说它是饿死鬼托生的。它们在院子树根下簇拥,但见主人摇筛子,便集体起身,飞跑过来四散抢食,在筛子的下方争抢啄食从筛孔漏下来的细碎粮粒。
摇筛子,这个“摇”,我们这儿发音为xue。在外行人看来,它是个轻省活,这就错了,它使的劲全在胳膊腕。和我家住一条街的振明爷是xue筛子的高手,左摇摇,右摇摇,肩腰跟着旋转,混杂在粮食里的草屑在他的摇动下层层分离,沙粒从漏孔掉到地上,最后只剩粮食粒。振明爷笑着,来不及擦去头上的汗珠,急急忙忙将粮食颗粒摊在阳光下晾晒。
我用筛子捕过雀。用一根短木棍支起筛子,留一道缝支在地上,筛子下撒些粮食粒,木棍上拴一根长绳,另一头拉在手上,人远远躲开,等麻雀进去吃食时,猛然一拉绳子,筛子就完整无缝地趴在地上,一只,或者几只麻雀就成了俘虏。用火烤了,雀肉就是儿童的美食。
水 车
水车是乡村的歌手,吱呀吱呀,哗啦哗啦,在阳光下不倦歌唱。
田里有机井的地方,总是长着一棵弯腰的柳树。柳枝、柳叶婆娑的影子,为水车营造出一片阴凉之境。
水车又称孔明车,是古老的农业工具,相传为汉灵帝时的毕岚造出雏形,三国孔明改造完善后开始在蜀国灌溉农田。《宋史·河渠志五》云:“地高则用水车汲引,灌溉甚便。”
碾儿庄人使用的水车叫木轮水车,也叫翻斗水车,由木轮、大轴、水斗、出水槽组成,用铁蕊连接。水车架在圆形的、砖垒的井口,人或牲口推着车把转动,清亮的水就哗哗流出。
或夏或秋,若是久未落雨,热烫的阳光烘烤着草木,一种溽热的气息便会笼罩田野,禾苗干渴,叶片蜷缩,耷拉个脸,急需水灌。浇水之前先挖水渠,从井口到地头为主水渠,再挖若干支水渠,分流到地里浇灌干裂开缝的泥土。电闸一开,水车旋转,井水欢畅地沿渠奔向禾苗。一锅烟的工夫,漫了水的禾苗活泛过来,挺腰舒叶,肤色脱黄,绿生生喜人。再然后,禾苗拔节长高,结出果实。
水车转了,人便歇了,或坐或躺于树影里,听知了在柳树的高处鸣唱。歇一阵,拿了锨查看渠水,聆听青苗轻吟。
在我童年的想象里,水车是一副欢乐的表情,吱呀吱呀的齿轮摩擦声,仿佛孩童的咿呀学语;哗啦哗啦的出水音,宛若欢乐的旋律。
大江南北的不少景区,都安放着一个巨大的水车,此为古老的象征。流转了无数个岁月的农具,被赋予文化和审美的内涵,很欣赏设计者如此的创意。
诗人舒婷曾为水车写过这样两句诗:“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数百年来纺着疲惫的歌。”诗意凄婉,我不太喜欢。在我的意识里,水车是伫立在古老土地上的一位清婉的村妇。阳光或月光,将婀娜的柳枝、柳叶覆于其身。她在阴凉里旋转,鸣奏出快乐悠扬的旋律,浅吟低唱着乡村的抒情曲。
土 车
土车者,两横谓之轴,中位为座,驭者横其中,竖为辙也。在甲骨文里,“车”为象形字,篆字概同繁体,其异体较多,明显的区别在于车轮。最初车轮为圆形,后来为了书写方便成了方形,再后来两个轮子简化为一个。
在文字记载里,最早的车是木制独轮车,由独轮、双木把、车厢组成,是乡村最简单实用的运输农具。独轮车的发明时间可上推至西汉晚期,那时称为鹿车。《三国志》里有“木牛流马,皆出其意”的文字,也有文字说木牛流马就是独轮车,传说它的发明者为诸葛孔明。
独轮土车利用的是杠杆原理,把负载的抗力点靠近车轮这个支点而前行。乡村交通不便,窄路、窄巷、窄埂、窄桥、窄门,都无碍它的通行。起牲口圈,起茅坑,给田里运粪土,把成熟的庄稼运回村子,它是故乡的一头老牛,无论沉重,无论脏臭,它都不嫌。
拥有漫长历史的独轮车,咯吱咯吱响着,穿越了两千年的时光隧道,一直行驶到我出世,好像在等待我与它的某种缘分。因此对它,我不能不怀有敬畏之心。既然有缘,我对它就怀有情感。读中学的时候,我就开始练习推土车。要驾驭它,首先要掌握平衡。这技巧无需从师,全靠自己琢磨。刚开始推它,它偏与我作对,东倒西歪,气得我火冒三丈,它却一声不吭,用渴望的眼神望我,期待我再次推起它。渐渐地,我掌握了它的平衡,手掌用劲,两肩放平,脚步匀称,双目直视前方。如此,它便心领神会,和我配合默契。在我的推动下,它百依百顺,像个听话的孩子。
我會推独轮土车这件事,至今都让我感到自豪,我是个老实人,朋友们听了不会不信。看他们的表情,先是惊讶,继而佩服。
独轮土车被我视为青春的伙伴。现在的我,一回到碾儿庄就惦念起它,可是找遍它可能藏身的所有角落,也杳无踪影。我茫然若失,垂下头颅,在泥土乡道搜寻它曾经的辙痕。村子的路都铺了水泥,哪儿会有它的痕迹?心里也明白,我只是在温习一种情感的记忆。
逝去的时光里,独轮车曾带着孤独的况味,在乡村坑洼的小道上负重前行。
家乡人把土车叫地轱辘车,还有一个更形象的名字:蚂蚱车。负重行走时,它发出节奏明快的咯吱声,宛若秋风里蚂蚱在歌唱。
责任编辑 王子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