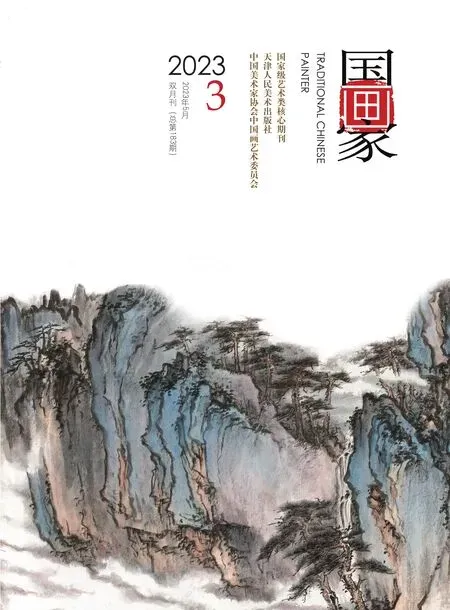回归与超越:中国画“尚古”传统的当代意义
南开大学艺术与美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博士后/孙贇路
一、传统与现代
中国画在20世纪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时代变局。一方面,为中国画艺术表现的丰富和审美理念的深化带来了重要契机;另一方面,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使中国画的精神根基发生动摇,进而引发传统中国画在表现技法、图式规范、艺术价值、审美趣味诸层面的畸变。自陈独秀之辈起,传统中国画被贴上“保守”“腐朽”“落后”的标签,对其彻底地改造以适应新形势成为20世纪中国画发展的主旋律。如果说20世纪初是“传统派”和“改革派”抗争、共存和互补的时代,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以面向自然和生活的集体意识和写实风格为特征的时代,那么自80年代以来则是多样化选择和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的时代。
整个20世纪关于中国画的探索和讨论可以概括为“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这一命题。在此过程中,“中国的传统”与“西方的现代”成为对立的两端。这一源于西方立场的时间意识内在地将同一文化的“今”与“古”视为对立的价值,而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则被表述为某种时代问题。“现代性”顺理成章地成了西方艺术独有的价值与传统。无论是康有为、梁启超等的“美术革命”论,抑或丰子恺、潘天寿等的“中国美术优胜”说,其中关捩在于赋予中国画以“现代”内涵。潘公凯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中西两代绘画体系互补并存、两端深入”[1]的主张概括了在现代性冲击下中国画发展的局面。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的传统”与“西方的现代”这种单一、机械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是否能够合理解释艺术“现代性”的真正内涵。
20世纪初,随着中国绘画理论在西方的广泛传播,成为西方现代主义自我建构的重要资源。尤其是中国传统的“写意”美学观念启发和支持了西方“表现”观对“再现”观的超越,使得西方艺术完成了由“传统”到“现代”的顺利过渡。正如美国学者包华石(Martin Powers)所言:
“唐宋理论家的‘形似’与‘写意’的对比是通过宾庸(Laurence Binyon)和弗莱(Roger Fry)直接影响到欧洲的现代主义理论而在现代形式主义理论的建构中起着关键作用。我并不是说现代主义原来是中国人的发明,不过我们应该承认,自从18世纪以来,‘现代性’在文化政治战场的修辞功能是将跨文化的现象重新建构为纯粹西方的成就。”[2]如果西方学者关于西方现代艺术吸收中国艺术成分的考察是合理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国的传统”与“西方的现代”并不能构成对立的两端,因为“西方的现代”中已经包含“中国的传统”,而“中国的传统”自身已具备走向“现代”的可能性。因此,对中国绘画的“现代性”反思首先要走出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魅影,在中西艺术的互动中重新审视和反思我们自身所具有的传统。
正如我们所谈论的那样,中国画有着根深蒂固的“尚古”传统。纵览古今中外艺术之发展,任何一个传统都有其惰性和弊端。中国画的发展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有过低潮和停滞。此时,画家所应做的,无非是走向艺术的本源。正本清源,吸收转化,传统出新。同时,“尚古”传统又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有着强大的消化、吸收能力,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机制。中国画所尚之“古”,非谓传统绘画“表相”的内容和样式。凡是表相的事物,都处于不断的运动变化之中,因人而变,因时代而变。因此,对待传统的绘画,并非一味地继承,亦有修正和扬弃。正如表相的王原祁和石涛大为不同:王画守旧,石涛新潮;王画更多的是让我们见到古人,石涛的画更多的是让我们见到他自己。但是,他们各自的艺术价值并未因这些表相而减价或增值,他们都在以各自的方式探讨中国画的根本规律,也就是中国画的“画道”。《中庸》谓:“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3]所谓画道,是对绘画形而上的认知,是绘画形成与发展中不变的存在。从本质上看,中国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艺术现象,它承载的是儒、释、道思想的价值观念。在中国传统观念中,绘画与宇宙本源相通。清人刘熙载谓:“艺者,道之形也。”[4]绘画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维持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如何才能在绘画创作中求“道”呢?《老子》谓:“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5]对于中国画来说,画法的精熟与学问的增长是必要的,但却并非求道的关键。求道恰恰相反,在现有的基础上作减法,减之又减,从而进入象征天地之始、无以名状的宇宙大道之中。正如尹沧海教授所言:
“‘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其对于绘画之法既应有在学的过程中的‘益’,也应该认识到绘画的终极不是单纯的法的增益,而应该在法度完备的情况下‘损之又损’,直至达到内心的纯粹表达,达到与自然的和谐,尤其在当代,各种奇巧淫技扰乱人心,让人不断在‘法’的变化中迷失自然之性,‘不识本心,学法无益’。”[6]“学”的是“法”,“悟”的是“道”。外在的“法”只有与内在的“道”融为一体,绘画才能直至纯粹的表达。倘若明悟“画道”,不仅可以自由创作和正确品鉴中国画,而且可以指导中国画的发展,使其趋于完善。中国画艺术的最高审美境界是遵循自然之道,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使人的身心归于率真、淡泊、平和的状态。《庄子》谓:“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7]因此,中国画所创造的美不是视觉上的新奇和艺术形式的新旧,而是与天地共有之大美。
时至今日,不少人将石涛视作“革新派”的代表,并将“创新”指认为艺术的灵魂。其实,对中国画来说,曰古曰新,皆属表相。正如石涛所说:“古者识之具也,化者识其具而弗为也。具古以化,未见夫人也。尝憾其泥古不化者,是识拘之也。识拘于似则不广,故君子惟借古以开今也。”[8]石涛所谓的“古”,即其“一画”之法所彰显的绘画根本之法——画道。不明乎此者,打着“笔墨当随时代”的旗号哗众取宠,怪力乱神,殊不知“泥古”和“创新”都是在表相上做文章,而与绘画的根本——画道——渐行渐远。
二、“外力作用”与“传统规范”
中国画在20世纪经历了由外在形态到内在价值的重大转捩,特别是在20世纪末的当代,随着西方现代艺术思潮的外部渗透和“传统再认识”的内部发掘,抽象水墨、实验水墨、观念水墨、水墨构成以及新文人画等形形色色的水墨艺术风起云涌,由此中国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压力。当代水墨艺术的各行其道压缩了中国画自律性发展的空间,虽然它们在材料媒介与观念手法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关联,但从本质上看它们已经走向了泾渭分明的两极。在20世纪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画在“经世致用”的西学背景下打起了“中西融合”的持久战。从世纪初的徐悲鸿、林风眠等人的筚路蓝缕到当代“新浙派”“学院派”的百花齐放,虽然也涌现出了颇有成就的大家和经典,但“中西融合”策略并未对中国画的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普适性经验。
在“外力”的作用下,当代中国画创作给人的感受大体可分为两类。一为“悦目”,即追求视觉效果的逼真和震撼;一为“炫技”,即探索水墨材料的表现可能和表现技法的标新立异。“悦目”的中国画作品为了强化视觉上的冲击力,常在素材的选择和气氛的渲染上寻求突破。为了在图式个性上取得新变,他们从自然时空的个性化特征切入,传统中国画所遮蔽的部分——光影、透视、空间、肌理这些与视觉形式密切相关的因素——成为其表达个性的重要媒介。此外,特定地域的审美特征成为其强调视觉、感受真实的主要依据。在他们看来,个性化笔墨语言以及地域画风的形成基于符合特定地貌特征的审美创造。实际上,这样的作品对传统中国画笔墨语汇和文化观念的借鉴甚少,为了突出特定审美客体的视觉效果,他们在语言中的视觉形式上做文章,其结果是对传统审美价值一定程度上的颠覆。而最大程度地发掘水墨材料的表现可能以及处理手法上的标新立异则制造出了多种颇具表现力的“新奇形式”。尤其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水墨肌理的制作一度风行画坛。肌理制作打着“科学”的旗号寻求物理或化学效果上的偶然性,而对笔墨本身的艺术价值却视而不见。其结果是将水墨降为工艺技法上的制作效果,从而缺失笔墨本身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可以说,将科学作为艺术探索的动力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艺术并不等同于科学,科学注重陈述意义,而艺术注重表现意义。如果科学过多地介入艺术,势必会以“创新精神”的名义追求“新奇形式”的开发,而对艺术本体的精神性阐发置之不顾,由此造成审美评判标准的畸变和艺术秩序的紊乱。因此,无论是“悦目”还是“炫技”,其所达到的成就站在传统中国画的立场判断只能归类于“能品”,缺失笔墨内涵和精神价值的中国画终究只是媒介材质上的借题发挥。原本承载“天人合一”思想以及从人文传统中“羽化”而出的中国画如今却在人与自然对立的关系中沦为一般意义上的风景画。在这样的作品中,“笔墨”等同于“笔触”,“气韵”被“气氛”取代,“境界”被“场景”遮蔽。更有甚者,有些水墨装置已经从二维走向了三维。这样的“新奇样式”不仅“移步换形”,甚至已经走出了“中国画”的边界。事实上这样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已不再适合冠以“中国画”之名了。

1.孙路 东方欲晓 140cm×235cm 2021年

2.孙路 黄山快雪 97cm×180cm 2020年
值得注意的是,将这些艺术形式请出中国画的范畴并非要忽视或者抹杀它们的价值。艺术发展的道路从来都是开放的、多元的,我们并不反对一部分画家对水墨语言的彻底变革以及建立新的语言体系的探索。只要他们坚持走下去,建立符合艺术规律的语汇系统,对艺术的发展未尝不是好事。但是任何学术研究都必须在确定的范围内做出讨论和价值判断,这是学术研究起码的限定,否则将失去研究的意义。因此我们谈论中国画,必须在中国画的语境下探讨它的历史沿革、高下优劣以及当代意义。中国画区别于其他艺术形态的原因首先在于它的艺术语汇。而从绘画角度考量,中国画不同于其他绘画题材,本质上亦是由其特有的笔墨语汇所决定的。从一定程度上看,笔墨是为了表述中国画特殊的语言结构方式而形成并且固定下来的。如果说谢赫的“六法”和荆浩的“六要”开启了中国画重笔墨的先声,宋代的文人画家以自身的学养、气质赋予笔墨精神上的内涵,那么明清两代的画家则对笔墨做出了理性化的全面探索与论证。因此,笔墨是中国画的基本要素,是中国画的艺术特征、形式特征和表现特征。它既是手段,亦是目的。因此,无论中国画在过去或者未来所表述的观念和传达的思想要跨越多少不同的时空与心灵的间隔,其基本语汇系统的选择与发展无疑是保持其固定面貌与特殊精神的前提。只有保持中国画这个最大的特色和总的趋势,中国画才能永葆民族之特色,与西方绘画拉开距离,以自己独特的面貌和优势结合现代审美意识,从而走向新的纪元。
如果说“外力”作用对中国画的当代发展价值有限,那么基于民族文化内部挖掘的笔墨表现对新环境的适应则少了些应变能力。总体上看,以传统笔墨为依据的当代中国画过于关注外在表相上的笔墨构成,而对笔墨内在品质的提升和画道的彰显则力不从心。他们在技法的运用与图式的安排上显示出深厚的传统修养,对中国画的基本元素构成与画理、画法有着较为清晰的认知。当代各类艺术思潮的广泛渗透并未阻止传统中国画自主发展的脚步。然而,当我们仔细审视这些作品时,并未感到过多的惊喜,对传统画道理解的偏差造成画法的舛误和品质的降低。他们只观照到了笔墨的“有无”,而忽略了笔墨的纯度,当代中国画“不耐看”的原因即在于此。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作品以似是而非的笔墨元素寻求技法的创新与风格的多面,作品尺寸越画越大。画家不厌其烦地执着于对局部的刻画和细节的描摹,将传统笔法等同于材料工具的熟练掌握,书法与人格方面的修养沦落为形式上的坐而论道。如果说当代人对传统文化的浅尝辄止丧失了传统中国画的“诗魂”的话,那么书法修养的缺失则将传统笔墨的意蕴降为一般性技巧的展现。缺失独立审美价值的笔墨只能将用笔勉强泛化为外轮廓线的勾描,将用墨简化为明暗调子的涂抹,由此当代中国画只停留于对物象的搬前挪后,成为徒具形式意义的“空架子”,而中国画所要传达的笔情墨趣和境界营构则成为记忆中的远古诱惑。
此外,“视觉冲击力”“展厅效应”等这些原本不属于中国绘画语言体系的“外来词汇”却成为评判作品优劣的重要指标。把心灵与眼光专注于“创造形象”之上,把所谓的“深入生活”轻易转化为“摹绘物样”,绘画价值的判断由此变得混乱不堪。因此,当代中国画虽然打破了传统画法的旧有格局,但却无力建立一个合乎画道的新秩序。换句话说,当代中国画已不完全遵从传统笔墨法则的规范来表现当下的审美感受,而更强调笔痕墨迹的相对独立性,从而在更广阔的范围内任意施展。然而,各类水墨艺术的“为所欲为”使得中国画笔墨价值和文化内涵的彰显失去意义,而境界的迷失则使“悦目”的作品呈现显得更加粗糙和乏味。当代的中国画家,显然面临着关怀传统的使命。对于中国画这一经典而成熟的文化样式的全面传承必须重视两个方面:其一是传统中国画所体现和包含的基本文化精神,其二是其所具有的各种文化手段。前者主要体现在画理与意境方面,后者主要表现为趣味与法式。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方面的基本判断准则必须是历史经典的文化共识。既然传承的目的和本质是文化样式和文化精神的延续,那么最危险的做法就是缺乏文化底蕴的“标新立异”。因此,表现的自由不能以减弱艺术品质为代价。在当代中国画探索中,重视传统文脉,纯化笔墨的精神内涵,这是提升中国画品质的必要条件。
三、回归与超越
如前所述,中国画是反映人与自然关系的一门学问,是艺术哲学在自然观上的体现。文化的健康发展必然伴随着对自然变化平和而普遍的适从。只有在平和与适度的比较、选择之中才能完成对“天人合一”的本源认识,进而达到人与自然关系在本质演进上的和谐统一。中国画只有遵循这样一种天然常规,才能在普遍的发展变化中反映出一种“笔墨当随时代”而又“万变不离其宗”的民族文化的精神追求。然而,在20世纪中国画的阶段性变革中,我们看到了张璪“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主、客关系论调经历了复杂的变化。由侧重“心源”的主观表达到注重“师造化”的客观表现,反映了中国画逐步走向为大众服务的世俗化倾向。中国画所承载的使命已经远远超出了古代文人“畅神”的主张,为祖国山河立传与对现代社会意识的表现迫使其功能发生转移。而对传统笔墨的回归又迫使画家对“造化”和“心源”关系进行重新认识与把握。这是一个痛苦且挣扎的过程,对传统笔墨的回归是否因此失去了自我个性与中国画的现代性关联则成为当代画坛争论的焦点。
对当代的中国画画家来说,能否以“超越”的视角审视中国画艺术与人类自然观的变化之间的关系,将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艺术作品要反映时代的精神特征固然没有错,但是“反映”并不是“等同”。伴随着当代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逐渐肢解与破碎,人们的心理也变得愈发躁动与扭曲。虽然人们试图通过现代文明的方式去弥补两者的关系,但缝合之后的关系与古人那种浑然一体的和谐境界已经相距甚远。在当代这种关系之上,如果依旧试图以古人的艺术手法和眼光再现传统的笔墨样式和审美趣味,势必造成一种徒具空壳而无内在生命的艺术存在。这样一种无病呻吟的矫情作风与那些矫揉造作的流行画风一样缺乏精神感染力,令人生厌。然而就中国画传统所探索和确立的基本规律和原理而言,却具有超越历史和时空局限的永恒价值。美的和谐便是与“道”相通的至高境界。在精神自由的状态之下,画家从万籁之中感悟宇宙和生命的意义,从心灵深处直觉天地精神与生命的律动。超越时间与空间的有限,让生命的真性自在彰显。这正是“尚古”传统的魅力所在,其所探索的普遍性规律在当代依然具有一种不可磨灭的艺术价值。因此,一个真正的画家不仅是敏感心灵的守护者,更是民族优秀文化的捍卫者。他必须永葆忧患意识,始终站在新时代的历史高度,关怀人类生存的终极命运。
中国画传统止于至善、画道至美,最大限度地维护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它是符合人类长远、根本利益的文化精髓。“尚古”传统将古典之美赋予新的精神内涵,从而使中国画在新的高度上复归其本原。它不是静态的、封闭的、保守的,而是动态的、开放的、与时俱进的。它联系着过去、现在和将来。它不仅是我们走到现在的原因所在,更指引着我们走向未来的正确方向。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的迅猛发展与巨大变迁而言,文化建设更应该保持坚定的民族精神,才不至于在传承之中失去方向。既然传统中国画是中华文化经典的艺术样式,便更需要坚定地按照文化传承的基本规律来进行。令人遗憾的是,当代中国画的发展所欠缺的正是对这方面的清醒认知。因此,时至今日我们依旧选择遵循这种普遍规律,继承和发扬中国画传统,并非出于狭隘的民族情结和民粹立场,而是符合艺术规律和众生利益的“正知见”。
结语
“尚古”传统所营构的理想境界,其基础是画家主体与宇宙大道之间和谐统一的关系。在工业科技高速发展而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新时代,人与自然和谐的关系被逐渐肢解。在这种现代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基础之上,如果强行恢复古人的笔墨形式与风格境界,势必造成一种徒具空架子的空洞艺术存在。而纠结于“创新”与“传统”这些表相问题,对艺术的探索也将不得其法。当代中国画的发展不仅要逸出主流文化、流行文化,而且要逸出传统绘画表相的束缚。在继承和创作过程中从“画道”切入,不执着于艺术的表相,对传统绘画的精华广泛继承,整合转化;对外来的文化细心吸收,丰富营养。由此派生出的中国画则是愉悦人生、澡雪精神的完美艺术。
注释
[1]林宸胄、潘公凯,《专访潘公凯:中国美术高等教育——“大美术”视野下的跨越式发展》,《美术观察》,2018年第11期。
[2]包华石,《中国为体西方用:罗杰·弗莱与现代主义的文化政治》,《文艺研究》,2007年第4期。
[3]王国轩译注,《中庸》,中华书局,2016年,第56页。
[4][清]刘熙载著,王气中笺注,《艺概笺注》,贵州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496页。
[5]陈鼓应译注,《老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250页。
[6]尹沧海,《复归于朴:写意花鸟画要旨》,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年,第129页。
[7]陈鼓应译注,《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650页。
[8][清]石涛著,窦亚杰编注,《石涛画语录》,西泠印社出版社,2006年,第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