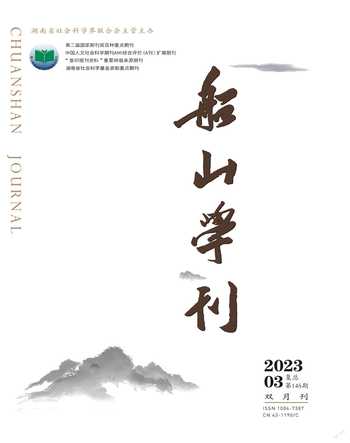性体理用关系论
摘要:性理是王夫之哲学的核心范畴,王夫之常常称理即性。人们通常据此以为二者相同,其实不尽然。王夫之以体用论解释事物及其存在,即以事物为体,以其生存或发用为用,事物及其生存为体用关系。以生存或存在解释事物,即以用释体,体即用。王夫之同样以体用论解释性理关系,即性在体中,理在用中。从意谓来看,体即用,性即理,二者同出而异名。但是,从意味来看,性指主体,理指行为,二者显然有别。即体即用体现了性理之间的转换,体用分别则突出了各自的重点。
关键词:王夫之性理体用理气
作者沈顺福,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暨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济南250100)。
性與理是宋明理学的两个核心概念,其中,理学之名便源于理的概念。关于性理关系,从程朱到陆王,乃至后来的王夫之等皆主张性即理。这一解释常常给现代学者造成一种错觉,以为理与性是同一的。如牟宗三认为朱熹所体会之理“是只存有而不活动者”,属于“静态的存在之理”,而“非是动态地创生之之‘使然者然”的理,[1]458从而忽略了性理区别。当前学术界也常常将性与理合称为“性理”[2]62-66,几乎无视二者之间的区别。然而,在笔者看来,性理关系绝非如此简单。本文将以王夫之学说为例,指出:性理具有体用关系,性存于体,理隐于用;从即体即用的角度来看,性即理,二者同出而异名,从体用分辨来看,性理不同,性为主体,理指行为,重点不同。
一、仁与理
儒学是做人的学问,最关注如何做人。如何做人即如何生存。中国传统哲学是一种气质生存论,即从气化流行的角度来理解人与万物的生存,认为生存即气化流行。王夫之曰:“天以二气成五行,人以二殊成五性。温气为仁,肃气为义,昌气为礼,晶气为智,人之气亦无不善矣。”[3]1054人的生存即行为便是二气五行的运转、发用与流行,生存即气动。通过气化流行,天地万物相贯通,而形成一体。这种贯通一体,理学家称之为仁。程子以日常生活为例,曰:“医书言手足痿痹为不仁,此言最善名状。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认得为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诸己,自不与己相干。”[4]15贯通便是仁,不通便是不仁即麻木不仁。仁即通而为一体。王阳明曰:“盖其心学纯明,而有以全其万物一体之仁,故其精神流贯,志气通达,而无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间。譬之一人之身,目视、耳听、手持、足行,以济一身之用。”[5]62自然界的万物,通过气质贯通,自然形成一个身体,人与他者如同手足,自然亲爱。这种自然亲爱的行为便是仁。王夫之曰:“气充满于天地之间,即仁义充满于天地之间。”[3]1056仁即气化流行。通过气化流行,万物贯通一体,相亲相爱而和睦。故“仁生气,义成气”[3]1056,仁是气质活动。这种气质活动之仁,王夫之称之为人道:“道也(修身以道),仁也,义也,礼也,此立人之道,人之所当修者。”[3]520人只能依据仁义之道而事而行而生存。仁义是正确的行为或活动,正确的行为便是人道。仁义行为,按照中国传统生存理论,乃是气化流行。
作为人道的仁义不仅是一种气化流行,而且内含某种特殊的性质。这种特殊的性质实体便是理。仁义之中有理。“仁义,一阴阳也。阴阳显是气,变合却亦是理。”[3]1057仁义气质的变化内含理,如“以知、仁行道者,功在存理。以勇行道者,功在遏欲”[3]491,仁知行为是理的具体表现。某种气质活动之所以是正确的,原因在于其符合理。理是一个行为的正当性的终极依据,是其“所以然”:“理者,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6]194理是正确行为即事的“所以然”者,是正确行为的依据。比如仁义之举,王夫之曰:“若夫人之实有其理以调剂夫气而效其阴阳之正者,则固有仁义礼智之德存于中,而为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所从出,此则气之实体,秉理以居,以流行于情而利导之于正者也。”[3]1055-1056只有遵循理的气质活动才是正确的行为。或者说,人的正确行为不仅是由气质之心所主导的活动,而且必定符合理,理在其中。理是“天地万物已然之条理”[3]718。理即条理,是万事万物存在的终极性依据。
理决定了万物生存的性质。王夫之接受了传统理学的生存观,曰:“质是人之形质,范围著者生理在内;形质之内,则气充之。而盈天地间,人身以内人身以外,无非气者,故亦无非理者。理,行乎气之中,而与气为主持分剂者也。”[3]859人生无非气与理,其中气质提供动力与载体,生存即气质流行,理行于气中。气中之理主导了气的活动:“以理御气,周遍于万事万物,而不以己私自屈挠,天之健,地之顺也。”[6]196理主宰气质活动。王夫之比喻道:“质如笛之有笛身、有笛孔相似,气则所以成声者,理则吹之而合于律者也。”[3]860理如音律,是音乐的主导力量。“气亦受之于天,而神为之御,理为之宰,非气之即为性也。”[6]368理是神理,能够主宰气的运行。理主导行为而为尊:“大德大贤宜为小德小贤之主,理所当尊,尊无歉也。”[3]992理因此是至尊的。
这种作为决定者的理是一种形而上的实体。形而上之理是无形体的实体:“天地间只是理与气,气载理而理以秩叙乎气。理无形,气则有象,象则有数。”[3]551理没有形体,因此无法被认知。理是未发之中:“盖吾之性,本天之理也,而天下之物理,亦同此理也。……吾心之理无不现,则虽喜怒哀乐之未发而中自立焉。”[3]1107理即未发之中。未发便是尚未显现,自然不可知。这种未发之理便是“形而上之理”:“盖孟子即于形而下处见形而上之理,则形色皆灵,全乎天道之诚,而不善者在形色之外。”[3]963理是形而上的实体。这种形而上之理具有绝对性。王夫之曰:“形而上者,亘生死、通昼夜而常伸,事近乎神。”[6]128理无时不在,具有永恒性。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理是“无穷之理”[3]1109,无法被完全认知。
二、理在于用
绝对的理的存在确保了气化流行的正当性。从人的生存来看,理确保了人类行为的正当性,使人的行为正确。王夫之曰:“唯人为有仁义礼之必修,在人之天道也,则亦人道也。知仁勇,所以至于善而诚其身也。所以能行此知之所知、仁之所守、勇之所作于五伦九经者,忠信也,人之道也。”[3]533此处的天道即天理。天理在人间便是人道,即人类的正确行为,如知、仁、勇等。这些正确行为的依据便是理。王夫之曰:“于内有主,于外不疑,条理既得,唯在决行之而已矣。行斯得矣。”[3]402条理之理内在于人,是人类行为的主导,决定了人的行为的性质,即理是一切道德行为的依据。作为依据,理蕴含于所有的道德行为之中。
理首先通过主导行为的心灵活动发挥作用。行为之事发于心。王夫之曰:“有其司则必有其事,抑必有其事而后有所司。”[3]1090司即主管如心灵,由心灵所主导的行为便是事。“今既云‘不思矣,则是无其事也,无其事而言司,则岂耳目以不思为所司之职?”[3]1090无心的行为便不是事。王夫之曰:“性为天德,不识不知,而合于帝则。心为思官,有发有征,而见于人事。天德远而人用迩,涉于用(非尽本体)而资乎气(不但为性),故谓之‘三近。”[3]524心灵所主导的活动必然表现为事。心是气质人心,故由心所发动的行为必定属于气质行为。故王夫之曰:“故好色、好斗、好得者,血役气也。而君子之戒此三者,则志帅气而气役血也。今以好色、好斗时验之,觉得全是血分管事。及至淫很之心戢退,则直忘此身之有血,而唯气为用事矣。”[3]849好色是血分管之事,戒色戒斗是气所引导之事。血所主导的行为是自然的、生物性的活动,体现了人的生物性与自然性;而气所主导的行为则高于此类自然性活动。
为了确保自然行为的合理性,理学家主张人的自然之心应该与理合一。王夫之曰:“性,道心也;情,人心也。恻隐、羞恶、辞让、是非,道心也;喜、怒、哀、乐,人心也。”[3]966喜怒哀乐之情乃是人心的活动,有了天理在心中,人心便有了合法性,从而能够产生恻隐、羞恶等仁的活动。含理之心乃是人类正确行为的基础或发动者。事是有意的、合理的活动,事出于理。王夫之曰:“理者,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6]194理乃是事的“所以然”者。如忠恕之事,“所以说忠恕是学者事。何也?未至于圣人之域,则不能从心所欲而皆天理,于是乎絜之于理而性尽焉,抑将絜之于情而欲推焉。两者交勘,得其合一,而推所无滞者亦尽所无歉,斯以行乎万事万物而无不可贯也”[3]639。忠恕是事,此事依据一定之理。理乃是正确行为的终极性依据。
这种由心所发动的、与理一致的活动,从气化流行的角度来说便是发用,简称“用”。用即事物的使用、运用、作用或存在。理存于用中。王夫之曰:“说制便是以心制事,(观朱子利斧劈将去之喻自见。利斧是体,劈将去便则是用。)如何不是用?说宜是用,说事之宜便是体。(事是天下固有之事。)”[3]896宜是从用上讲。宜即义,理在事上便为义。义是合理的行为,是用,用中有理。王夫之曰:“二气之动,交感而生,凝滞而成物我之万象,虽即太和不容已之大用,而与本体之虚湛异矣。”[6]40-41万物生生不息、气化流行,便是理气合一而形成的太和的、必然的大用。
从人的生存论来看,用便是心动。王夫之曰: “说性便是體,才说心已是用。说道便是体,才说德便已是用。说爱是用,说爱之理依旧是体。”[3]896心灵活动便是用,如志便是用,志即道心的活动或用。王夫之曰:“若吾心之虚灵不昧以有所发而善于所往者,志也,固性之所自含也。……则君子之有志,固以取向于理,而志之所往,欲成其始终条理之大用,则舍气言志,志亦无所得而无所成矣。”[3]925心中有理而为志。志是道心的发用。它引导人们向善:“气者,天化之撰;志者,人心之主;胜者,相为有功之谓。”[6]44志主导人类行为。这种志,与其说是观念,毋宁说是行为。王夫之曰:“故曰‘心者身之所主,主乎视听言动者也,则唯志而已矣。”[3]403理在心中的活动便是志。志是行为,是用。“道是志上事,义是气上事。”[3]932志之所动便是事,事便是行。“德者,己所有也,天授之人而人用以行也。……以德行道,而所以行之者必一焉,则敏之之事也。”[3]521事即以德行道,如仁、义等行为。由道心或志所引导的活动便是行。事即理之行,行即流行与发用。王夫之曰:“理,行乎气之中,而与气为主持分剂者也。……乃其既有质以居气,而气必有理,自人言之,则一人之生,一人之性;而其为天之流行者,初不以人故阻隔,而非复天之有。”[3]859-860行乎气中者便是理,理发用流行于存在中。故牟宗三称理为“实现之理”[7]80,理在实现之用中。
用分两类,即天道之用和人道之用。从人类生存之前来看,理自在于天道流行中。王夫之曰:“乃天为理之所自出,则以理言天,虽得用而遗体,而苟信天为理,亦以见天于己而得天之大用。是语虽有遗而意自正。”[3]1113在落实于人类行动之前,理属于天理,即自在之理,它是天道之流行大用。王夫之曰:“乃以理言天,亦推理之本而言之,故曰‘天者理之所自出。凡理皆天,固信然矣。”[3]1112这里的天并非苍天之天,而是天概念的一种具体用法,用来隐喻最初存在或第一本源。天理即自在之理。这种自在之理也是自然的:“天理之自然,为太和之气所体物不遗者为性;凝之于人而函于形中,因形发用以起知能者为心。”[6]124理是自然而固有的实体。从人、物的生存来看,理隐含于仁行之中。但是,在人物之生存之前,作为绝对实体的理依然存在。它存在于天道的气化流行之中。“天道之以用言,只在‘天字上见,不在‘道字上始显。道者天之大用所流行,其必由之路也。”[3]531-532天道必然发用。“(如吹火者,无火则吹亦不然。)唯本有此一实之体,自然成理,以元以亨,以利以贞,故一推一拽,‘动而愈出者皆妙。”[3]1057在天而言,气化流行,理在其中,这个气化流行便是天道大用。
从人物生存领域来看,理在仁行中。仁行是用,故理在用中。王夫之曰:“道以干物,物以行道,(道者化之实,物者化之用。)不曰道不杂二而生物不测也。”[3]562-563万物生生(“物”)便是用,其基础便是天理,理在生化之用中。王夫之曰:“‘用者,用之于天下也。……‘和者,以和顺于人心之谓也。用之中有和,而和非用礼者也。”[3]592作用于天下便是用,又叫和,和即和谐天下,它是合理的发用。从人的生存与实践角度来看,王夫之曰:“夫手足,体也;持行,用也。浅而言之,可云但言手足而未有持行之用;其可云方在持行,手足遂名为用而不名为体乎?”[3]454手足是体,行为是用。“《易》文言所云‘庸行‘庸言者,亦但谓有用之行、有用之言也。……道之见于事物者,日用而不穷,在常而常,在变而变,总此吾性所得之中以为之体而见乎用。”[3]454道现于事物的存在中,即道理在日用之中,理在用中。含理之用便为仁。王夫之曰:“仁之于父子,义之于君臣,用也;用者必有体而后可用,以此体为仁义之性。”[6]118仁义等道德行为是用,这些仁用内含天理。王夫之曰:“仁也者,所以行其直也。直也者,所以载夫仁也。……直为道,则在天而天道直也,直道以示人,天之事也。”[3]685天道即天理,表现为仁行。仁行是用,用中含理,理在用中。“理之则有理矣,故转为‘理义字,事之当然而行之顺也。……即玉即理,玉无不可为理也。”[8]352用含义理,故而合理。
三、性是体
既然理在用中,言理指向用,那么,什么是此用之体呢?王夫之接受了朱熹的生存论,将万物的存在视为一种生存。该生存包含三层,即气、质和理。王夫之曰:“盖性即理也,即此气质之理。主持此气,以有其健顺;分剂此气,以品节斯而利其流行;主持此质,以有其魂魄;分剂此质,以疏浚斯而发其光辉。即此为用,即此为体。”[3]865万物的存在离不开性、气和质。其中气、质是生物的自然材质:“气质者,气成质而质还生气也。气成质,则气凝滞而局于形,取资于物以滋其质;质生气,则同异攻取各从其类。”[6]127气管生机,质管形体,气质相依而万物生成。这种气质依然可以统称为气。自然的气质构成了体用之体的第一种形态即形体。王夫之曰:“夫手足,体也;持行,用也。浅而言之,可云但言手足而未有持行之用;其可云方在持行,手足遂名为用而不名为体乎?”[3]454手足是体,持行是用。自然形体是用的自然主体,也是必不可少的主体。体首先是气质的形体之体,它由气质构成。
与此同时,为了确保主体的行为的合法性,理学家赋予主体新的内涵,即以性为体。原始的气质形体加上性,便可以组成合理的新主体。王夫之曰:“仁之于父子,义之于君臣,用也;用者必有体而后可用,以此体为仁义之性。”[6]118体即性。以性为体,并与自然形体相结合,最终形成了有理、有气的主体。故王夫之曰:“在天者,命也;在人者,性也。命以气而理即寓焉,天也;性为心而仁义存焉,人也。”[3]1075自然存在着两种东西,即理与气。当这二者相结合而形成主体时,理便转变为性,成为性体,区别于气质形体。性体来源于理。王夫之曰:“若当其未函时,则且是天地之理气,盖未有人者是也。……而其为天之流行者,初不以人故阻隔,而非复天之有。是气质中之性,依然一本然之性也。”[3]860当理气未合而发用时,只是理与气。这是思辨的立场,即在经验的生存之前,理气分离而自流行。一旦理落实于人间或身体中时,理便转变为性。王夫之曰:“在天谓之理,在天之授人物也谓之命,在人受之于气质也谓之性。”[3]865超越之理落实在人便是性,这个性便是体。王夫之曰:“诚者天之用也,性之通也。性者天用之体也,诚之所干也。”[3]544性是天用之体。王夫之曰:“抑朱子以尽心为尽其妙用,尽性为尽其全体,以体言性,与愚说同。”[3]544以体言性,是王夫之与朱熹皆坚持的观点。
王夫之所说的性既指人性,也指物性。“人物有性”[9]1006,人和物皆有本性。王夫之曰:“天命之人者为人之性,天命之物者为物之性。”[3]457天命在人为人性,天命在物为物性。或者说,人性区别于物性。其中,人性乃是人类本质之性。王夫之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其本在性,而其灼然终始不相假借者,则才也。故恻隐、羞恶、恭敬、是非,唯人有之,而禽兽所无也;人之形色足以率其仁义礼智之性者,亦唯人则然,而禽兽不然也。”[3]1074人性别于禽兽之性,为人类所独有。与之相伴随,人还有独特之才。正是这些材质确保人类能够彰显自己的本性。王夫之曰:“总以人之有性,均也;而或能知性,或不能知性,则异。孟子自知其性,故一言以蔽之曰‘善,而以其知性者知天,则性或疑异而天必同,因以知天下之人性无不善,而曰‘道一而已矣。”[3]967这便是后天的知性。虽然人人天生都有此性,但是这种性却被遮蔽了。只有后天的学习与教化,才能将被遮蔽的人性彰显或呈现,否则天性在如不在。
因此,性有兩个来源。王夫之曰:“诚明皆性,亦皆教也。得之自然者性,复其自然者亦性,而教亦无非自然之理。明之所生者性,明之所丽者亦性(如仁义礼等),而教亦本乎天明之所生。特其相因之际,有继、有存,(成性存存,道义之门。)有通、有复。”[3]539人有自然禀赋之性,但是这种自然禀赋之性却被遮蔽了。只有经过后天的教化和努力,自然之性才能呈现。也就是说,单纯的天性并不足以让人成为圣贤,它仅仅提供了某种可能性。只有后天的努力相协助,天性才能澄明。成性即成就行为主体。王夫之曰:“以天理言之,以体用为本末。而初因于性之所近,终因乎习之所成。则俭与戚有所不极而尚因于性之不容已,用皆载体而天下之大本亦立。”[3]616所成就之性便是真正的主体。学习便是化理为性而成体。理在人心而为性。王夫之曰:“性,谓理之具于心者。”[6]198通过后天的学习,穷得天理在人心,理转化为性。王夫之曰:“就气化之流行于天壤,各有其当然者,曰道。就气化之成于人身,实有其当然者,则曰性。”[3]1113流行之理凝聚于身体之中便是性,理与气合而为性。
体不仅有形体,而且包含性体。性体依附于形体,离开了形体,便无性体。王夫之曰:“而君子因有形之耳目官骸,即物而尽其当然之则,进退、舒卷各有定经,体无形有象之性,以达天而存其清虚一大之神,故存心养性,保合太和,则参两相倚以起化,而道在其中矣。”[6]46君子以自然气质之体,在无形性体的主导下,才能行道于天下。道不仅需要理,而且离不开性体。王夫之曰:“惟性则无无不有,无虚不实,有而不拘,实而不滞。故仁义礼智,求其形体,皆无也,虚也;而定为体,发为用,则皆有也,实也。耳之聪,目之明,心之睿,丽于事物者,皆有也,实也;而用之不测,则无也,虚也。至诚者,无而有,虚而实者也。此性之体撰为然也。”[6]361形体与性体,虚实结合而统一为完整的主体,成就超越性行为。“情以性为干,则亦无不善;离性而自为情,则可以为不善矣。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固未尝不入于喜、怒、哀、乐之中而相为用,而要非一也。”[3]967情发于形体之心,同时得到了性的保障,最终成为合理之情。这种情,作为一种活动,符合理。体发而为用,情用之中含理。
王夫之秉持性气不离的立场,反对天地之性的说法。王夫之曰:“其化无形埒,无方体,如何得谓之性!‘天命之谓性,亦就人物上见得。”[3]866性气不离而相依,性只能是形体之性。天地无形体,便无性。对于朱熹的“天地之性”,王夫之予以批评,以为“一语乖谬。在天地直不可谓之性,故曰天道,曰天德。由天地无未生与死,则亦无生”[3]865-866。天地无形,故而无体、无性。天地只有理、道,而无性。这意味着王夫之不再将天地当作自然物体。天道并非苍天之道,而是自在的天理。
四、从指称理论来看
王夫之借用体用关系解释性理关系。体用论是中国传统哲学受到佛教影响而产生的一个特有的哲学体系,其中,体即形体,乃是感性直观到的自然存在,用即作用或使用,是事物的存在或生存状态。事物为体,其存在或生存便是用。体用论通过活动的用来解释自然形成的经验性物体,即以用释体。对万物来说,其用便是生存。从感性直观来看,万物生存表现为形体之体,其实质已然是生生不息之用。体用异名,所指同一,故体即用。王夫之曰:“当其有体,用已现;及其用之,无非体。盖用者用其体,而即以此体为用也。”[3]896万物生生不息,或者说,生存乃是万物存在的本真状态。体是变化的事物,用是事物的变化。变化的事物与事物的变化,便是体用之间,异名而同实。王夫之曰:“体用元不可分作两截,安见体上无者之贤于用上无耶?”[3]422体即用,体用不二。
王夫之以孔子的“川流”说来解释:“川流既与道为体,逝者即道体之本然。川流体道,有其逝者之不舍;道体之在人心,亦自有其逝者,不待以道为成型而法之。此逝者浩浩于两间,岂但水为然哉!”[3]738川流是道体,故而有不舍之形体,逝去为道用,故而有人心的遗忘。从空间来看,道表现为川流,从真实存在(其实还是经验性的时间角度)来看,道即万物的生生不息。从感性直观来看,“目刻刻有可视之明,耳刻刻有可听之聪,入即事父兄,出即事公卿,此皆逝者之‘不舍昼夜也”[3]738。生生不息的真实之用表现为视觉的形体。用必然表现为体,体即用。王夫之曰:“道体自然,如何障塞得?只人自间断,不能如道体何也。天地无心而成化,故其体道也,川流自然而不息。”[3]738生生不息是万物的真正存在,形体之物是不真实的,只有用才是真实存在。王夫之以用释体,从生生不息的存在论角度解释了事物的本质。存在并非物体,而是物体的存在。体即用,体用无二。
事物是体,生存是用,事物生存便是体用关系。在这种具体体用论中,体是具体之物,用是其生化流行。在具体体用论基础上,理学家们逐渐发展出抽象体用论。在抽象体用论中,体是抽象之性,具体之用为抽象之理。准确地说,性存于体,理含于用。性理所指同一,从体而言便是性,由用而言便为理,性理关系乃是体用关系。这便是王夫之的性理关系论。王夫之曰:“在天谓之理,在天之授人物也谓之命,在人受之于气质也谓之性。若非质,则直未有性,何论有寓无寓?若此理之日流行于两间,虽无人亦不忧其无所寓也。”[3]865自在流行中便是理,存于身体之中而为体者便是性。性在身中而成为体的一部分,这便是性体。它来源于流行发用之理,即理存身于发用之用中。王夫之曰:“未發之中,不偏不倚以为体,而君子之存养,乃至圣人之敦化,胥用也。已发之中,无过不及以为体,而君子之省察,乃至圣人之川流,胥用也。……浑然在中者,大而万理万化在焉,小而一事一物亦莫不在焉。”[3]453未发之性是体,而理便发用于事事物物中。性在体中,理在用中。
性体理用,性理关系表现为体用关系。体用论中的性理关系,二者既有相同之处,又有差异。从指称理论来看,二者意谓(meaning)相同,意味(sense)相异。所谓意谓即词或概念所指称的对象,如金星指称某颗星星,启明星也指称某颗星星,那颗星星便是金星、启明星等概念的意谓。从意谓来看,金星与启明星是一致的。所谓意味即词或概念在使用中所发挥的作用、产生的效果等。相同的词在不同句子中使用时,其意味常常是不同的,效果也会有差别。
从意味来看,性是体,理在用,二者指称重点不同,产生的作用与效果也有显著差异。前者在人,后者在事。王夫之曰:“所以明夫人之生也,皆天命流行之实,而以其神化之粹精为性,乃以为日用事物当然之理,无非阴阳变化自然之秩叙而不可违。”[6]351理是天命流行、日用行为之理。言理强调行为的合理性,重点在行为。言性突出行为的主体性,重点在人。言理在做事,言性在做人。从做人来看,“气之化而人生焉,人生而性成焉”[3]1112。人生而备性,但是此性并非已然或现成。天性仅仅是一种可能性,需要不断生成,这便是性日生日成说。“天之与人者,气无间断,则理亦无间断,故命不息而性日生。学者正好于此放失良心不求亦复处。”[3]1079生生不息之中蕴含着理,落实于身体之中便成为性。性来源于日用生存中,反过来说,只有在日常生存中,性才能出现。这便是气日生,性日成。没有生存,便无人性。从人类生存与实践的角度来说,我们既需要关注日常行为的合理性,也要确立行为主体的正当性。对理的关注体现了行为的合理性,对性的关注集中在行为主体上。性日生日成说意味着:主体的诞生并非一劳永逸的事件,而是不断的进程或系列性事件。言性关注于做人,言理关注于做事。尽管做人与做事其实是一回事,但是,关注点明显不同,意味也有差异。
但是,从意谓来看,体用不二、以用释体,性理关系也是相即不离,性即理。性理之间保持了指称的同一性。性与理,异名而同实,皆指称同一种存在。王夫之曰:“其所自者,性也;其能然者,理也。理全于性,性即理也。”[8]312性是主体或本源,所发之用中含理。性是源头,理在发用。性即理,性理所指同一。性理指称的一致性或同一性,确保了生存转化的关联性。王夫之曰:“盖性即理也,即此气质之理。主持此气,以有其健顺;分剂此气,以品节斯而利其流行;主持此质,以有其魂魄;分剂此质,以疏浚斯而发其光辉。即此为用,即此为体。不成一个性,一个气,一个质,脱然是三件物事,气质已立而性始入,气质常在而性时往来耶?”[3]865性即理。当理落实于气质身体中时,理转变为性,成为性体。性体主导了气质活动,最终表现为发用的合法性即理。即性体又转变为发用之理,发用之理呈现于气质流行的光辉中。相同的性理,在体中表现为性,在用中表现为理。从性体到理用的转化,以及从理用向性体的转换因此而成为可能。王夫之曰:“秉太虚和气健顺相涵之实,而合五行之秀以成乎人之秉夷,此人之所以有性也。原于天而顺乎道,凝于形气,而五常百行之理无不可知,无不可能,于此言之则谓之性。”[6]33在人之体便是性,处事之宜便是理。在体为性,在用为理。相同的性理,在不同存在中,表现为不同的存在形式。在不同形式的背后,贯通着相同的存在。这便是性即理:“盖以性知天者,性即理也,天一理也,本无不可合而知也。”[3]967自在之理,在人便是性。性理所指同一,“是理唯可以言性”[3]1112,性理相同。
【 参 考 文 献 】
[1]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下册.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3.
[2]陈来.王船山《论语》诠释中的理气观.文史哲,2003(4).
[3]读四书大全说∥王夫之.船山全书:第6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
[4]程颢,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
[5]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吴光,钱明,董平,等编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6]张子正蒙注∥王夫之.船山全书:第12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
[7]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册.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3.
[8]说文广义∥王夫之.船山全书:第9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
[9]周易外传∥王夫之.船山全书:第1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
(编校:祝美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