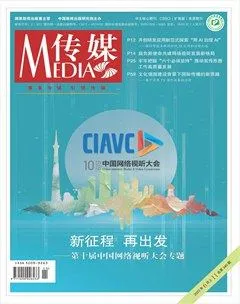从“界限沟通者”到“界限赋能者”
王亚莘 李祖康
摘要:构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话语体系,是国家高端智库建设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议题,是助力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建设、提升中国国际传播效能的关键一环。本文从“界限沟通者”出发,指出其当下的困境,并提出了从“界限沟通者”到“界限赋能者”的角色转换,是中国智库增加海外话语机会的可行路径。精准对话“关键定义者”、传播跨舆情周期的“韧性”话语、动态调适人-机对话关系、对话桥接社群、对话“无声”的“潜水者”,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实现“赋能”的核心要点。最后,本文聚焦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NCR),探讨了其构建中国特色新型媒体智库话语体系的主要经验与未来趋势。
关键词: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话语体系 NCR 界限沟通者 界限赋能者
近年来,我国媒体“走出去”的步伐不断加快,对提升国家影响力发挥了显著作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是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一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国智库如何更加积极有为地承担起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的历史重任是亟需讨论的重要议题。作为“我国国家高端智库方阵中唯一媒体型智库”,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简称NCR)兼具信息总汇与政策研究的双重优势,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中独树一帜。以其为典型分析样本,探讨在构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话语体系的过程中面临哪些挑战、拥有哪些机遇、进行了哪些有益探索,具有重要意义。
一、智库的“界限沟通”作用及其当下困境
放眼全球,重视高水平智库建设,早已形成共识:智库既是“思想库”(Think Tank),也是“旋转门”(Revolving Door);既是多元公共政策议题研究的“智囊团”,也是政策研究人才跨界流通的“中转站”。实践中,智库跨越组织边界、沟通信息观点,扮演着“界限沟通者”的重要角色。所谓“界限沟通者”,最早源于学者Adams,J.S.对组织内部功能结构的学术研究,是指与外部环境进行信息交换与资源交换的组织成员。“界限沟通者”往往发挥着交换信息、过滤信息、汇集信息、发布信息以及为组织建立信息“缓冲区”的功能。据此分析,质言之,智库组织本身就是社会运行系统中的“界限沟通者”:智库促进了“智力资本”的跨界流动,增益了环境间信息交换的机会;同时,在危机传播与冲突情境中,还发挥信息交换“缓冲区”的调节功能。
尽管如此,在全球信息环境日益复杂的今天,扮演“界限沟通者”角色的智库,正面临多重挑战。从话语体系角度出发进行分析,要点如下:
首先,近年来,随着社会组织的形态变迁与社交媒体崛起,智库发挥影响力的机制正在改变。传统组织形态外,包括网络意见领袖社群、非政府组织(NGO)等形态在内的自组织兴起;跨国组织、超国家组织也参与到全球治理中。多元、多轨与多变的“界限”,令“界限沟通者”难于发挥以往的效能。其次,全球发展环境的易变性(Volatility)、不确定性(Uncertainty)、复杂性(Complexity)与模糊性(Ambiguity)骤增,全球舆论光谱既“光影交错”,又“光怪陆离”,使得跨组织的“界限沟通”频频失效。全球发展环境巨变与全球思潮剧变互为表里。近年来,和平发展的主潮下,逆全球化思潮、政治极端主义、民粹主义抬头,国际舆论交锋激烈而频繁,意识形态斗争形势严峻而复杂。西方国家刻意制造对立、挑起纠纷,令智库发挥“二轨外交”的“界限沟通者”效能大打折扣。再次,智能技术的“双刃剑”效应,使得智库在提供“全球公共品” (Global Public Goods)时,面临复杂的供需环境。信息获取方面,新闻信息领域的智能推送技术,既让信息获取从标准化走向精准化;但也制造了诸如算法控制下的“信息茧房”“信息回音壁”效应。从个性化走向自我区隔,从开放性转向封闭性,折射出智能技术迅猛发展背后的信息失衡。
舆论生成方面,算法通过无数信息与观点的“过滤泡”(Filter Bubble),对用户进行着隐蔽的“操纵”。比如,研究显示,由算法支配的社交机器人(Social bots),已经具备了操纵舆论的能力。这其中介入政治传播议题的,就是“政治机器人(Political bots)”。计算宣传干预下,全球舆论场盛行“媒介化愤怒”、社会怨恨等在内的情绪极化现象,反映出智能技术“乐观主义”背后,被遮蔽的价值悖论。
二、“界限赋能”是媒体型智库的话语机会
“话语机会”(Discursive Opportunities)是指公共话语中,那些决定信息、观点能否以及如何走入媒体报道视野、调动公众注意力的传播机会。“话语机会”解释了为何某些信息、观点能够引发社会共鸣、跻身热点议题的话语空间博弈机制。增加话语机会主要有两种策略:原则性议题上坚定立场,在全球话语“竞技场”中,时刻维护自身话语正当性,保护自身话语机会的合法性,清除全球对话的“负能”;非原则议题上求同存异,规避话语间的“零和博弈”,创造话语间的“正和博弈”,为全球对话“赋能”。媒体型智库介入全球议题的话语机会得天独厚。媒体型智库既更加接近全球公共事务(Global Public Affairs)现场,又能保持研究者的观察距离。“记者+智库”有机协同的媒体型智库模式,有助于智库拓宽“声道”,释放“声量”。在面对大环境下智库“界限沟通”之困时,媒体型智库需要升级“界限沟通”思维,铺设“界限赋能”路径,用以增加话语机会。
1.精准对话“关键定义者”。如上所述,社会组织的形态变迁与社交媒体崛起,正使得沟通的“界限”多元、多轨与多变。但越是界限纷繁、甚至界限混沌,就越需要抓住其中的主要矛盾,清晰识别话语场中发挥关键舆论影响力的组织或个体。在媒介研究中,人们发现,存在所谓的“议程设置型媒体”。它们或依靠较高的公信力(如机构型媒体)、或依靠较强的情感效力(如自媒体),左右着社会的事实认知与价值判断。研究者也将其称为“关键定义者”(Primary Definer)。它们(他们)处于信息交换网络的中心节点,有力地影响着社会舆论的走向。这提示我们,影响有影响力的人(关键定义者),至关重要。与“关键定义者”对话中,议程设置、议程融合与反向议程设置,构成了议程“三角”。缺失对任何一环的关注,都可能导致对话的失败。有鉴于此,首先,依据重要(Significance)、相关(Relevance)、适用(Applicability)法则,设计议程清单。其次,激发数据的“势能”,通过数据挖掘(Data Mining)技术,刻画主题聚类、情感向度,寻求界限间对话的最大公约数,并注重双向、多向的议程融合。再次,需要妥善應对“反向议程设置”。针对“关键定义者”对我方设置议程的发难,若仅仅停留于回应式对话,极易丧失议程设置权;议程设置权的反转,便是舆论反转的前奏。
2.传播跨舆情周期的“韧性”话语。国际舆情瞬息万变、波诡云谲,这更加考验我国媒体型智库参与国际对话与话语交锋的智慧。面对变动不居的舆情热点,需要提供跨越舆情周期的“韧性”话语。如果说热点舆情是“快变量”,那么热点舆情背后的底层逻辑,则是“慢变量”。发掘短期热点舆情的底层逻辑,直击其核心关切,引入长久议题,从而实现赋能话语“韧性”。见证舆情周期、超越舆情周期,这是媒体型智库的显著特性。在快慢交替间,考验的是媒体型智库的话语“韧性”。
3.动态调适人-机对话关系。Boshmaf等人的研究显示,(社交)机器人对社会网络渗透的成功率可以达到80%。通过算法运行的社交机器人,在当今全球舆论场的议题扩散力远远超过人类。但是,算法不是万能的,社交机器人亦有其“阿克琉斯之踵”:研究证明,对非结构性数据的忽视、不确定性推理的累积、真实性核查的缺位,是人工智能技术参与信息传播全流程中的“痼疾”。算法的议题扩散能力强,但议题的回应能力弱。媒体型智库在发声过程中,动态调适人-机对话关系,有助于将新闻的议题扩散与专业的深层解析有机结合,实现媒体所擅长的“短平快”与智库所擅长的思想性的有机协同。
4.对话桥接社群。研究发现,跨文化传播中,具有文化双重身份的群体与组织,拥有“排他性”的传播资源。能够更好地穿透“文化”屏障,给跨文化传播带来不同话语间“浸入式”的收受体验。这带来的启示是:我国媒体型智库创新话语体系时,需要提升文化敏感度,注重“同声”与“转译”的结合。“同声”是指我国智库对不同文化间的智库,运用直接对话的方式,传播中国声音、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转译”是指充分吸纳、借助海外华侨、华人社群中的智库专家人士、媒体人士的多元发声渠道及其人脉资源、社会网络,建立外部形式松散、文化认同紧密的“桥接组织”,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更好传递本土声音、融汇全球“声部”,提供话语“接力站”,实现话语传播的路径转圜。
5.对话“无声”的“潜水者”。看似众声喧哗的全球舆论场喧嚣表象下,是“沉默的大多数”——无数的网络“潜水者”构建起的“潜舆论场”。然而,“潜水者”并非没有态度,他们“相机抉择”,极有可能在全球热点舆情事件激发下,出现大规模的舆情啸聚。一旦“爆发”,其舆论烈度不容小觑。在近年一系列引发全球关注的“连结性行动”(Connective Action)中,都伴随着“潜舆论”演变为“行为舆论”的过程。这提示我们,媒体型智库在聚焦“关键定义者”时,需要反顾、研判、引导全球互联网舆论场中那些“沉默”与“沉没”的声音。媒体型智库有着其他类型智库所不具备的舆情分析优势,又有着进行跨学科深度分析舆情成因的突出特点。这是媒体型智库介入全球舆论场的“隐形”话语机会。
三、NCR构建中国特色新型媒体智库话语体系的经验与展望
NCR既立足“界限沟通”,更向“界限赋能”积极转型,构建中国特色新型(媒体)智库话语体系,进行了有益探索。
1.贡献中国方案,对话“全球南方”。2021年,NCR向全球发布《中国减贫学——政治经济学视野下的中国减贫理论与实践》(Chinese Poverty Alleviation Studies: A Political Economy Perspective)的智库报告。通过传播中国特色反贫困之策,为全球社会的公共福祉建设赋能。《中国减贫学》既跨越中西语境、具有全球视野,更注重与全球舆论场中失语的“全球南方”国家进行积极对话。在全球发展深度不平等、传播权力严重失衡的现状中,通过对话“全球南方”这一国际舆论场中“无声”“沉默”的对话者,不仅为第三世界国家摆脱贫困,提供平等的对话平台、有益的方案镜鉴,更通过媒体型智库的传播力,提高了反贫困议题的全球可见度。此外,该智库报告,聚焦了中国方案中的关键议题,提出“中国减贫学”这一重要概念。借此概念,NCR成为全球舆论场此议题的“关键定义者”。
2.放眼长周期,与时间对话。从2014年至今,NCR连续以“中国经济的下一程”为议题,举办“思客年会”。与会者是来自政经、科技、文化等领域的著名专家学者,围绕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多元议题,展开思辨对话。以2021年第8届思客年会为例,会议邀请来自清华大学等高校的著名学者、来自全国政协等政府部门的专家领导、来自金融等行业的领军人物,与会嘉宾阵容充分体现NCR跨行业跨领域的对话功能;会议议题主要讨论新能源、元宇宙、公共卫生体系、城市数字化赋能、宏观经济调控等长周期议题,凸显对话内容的实践性与未来性。从对话的设计看,没有局限于“回眸”,更是重在展望。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特别需要有识之士,传播那些跨越全社会舆情热点周期的中国发展“韧性”话语。不为一时一事所局限,不被一得一失所牵绊,能够在放眼长周期、与时间对话的过程中,阐释好中国道路的全球价值。
3.立足理性话语,提升对话的可理解性。NCR作为媒体型智库,不仅注重以理性话语方式开展思想对话,還发挥“媒体”特性,提升对话的可理解性。比如,开设“思客云讲坛”“中国智策”等视频节目,更好适应传播的“视觉转向”所带来的新变化。NCR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进程中已有长足发展,通过体系建构、组织优化、融媒体改革等等方式,增强传播力与影响力,使思想对话在内容与载体的共同提升中实现可理解的广泛传播。NCR立足中国经验、推介中国方案,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国际传播话语体系,服务国家十三五、十四五战略规划,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NCR共建9个下属研究中心,形成有独特“智力资本”的、专业化水平较高的媒体型智库;NCR作为国家高端智库中唯一的媒体型智库,创新了智库组织理念与形式,注重智慧集思,更注重智慧传播,在多渠道中实现智库研究成果的融合媒介呈现。NCR在近两年陆续发布《人民标尺——从百年奋斗看中国共产党政治立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追求与探索——民主自由人权的中国实践》等重大智库报告,持续不断推出有深度、有影响、有标志的一流智慧成果,向“全球南方”推介具有丰富理论性与实践性的中国经验,在全球发展中国家的政经领域、学术界、媒体行业以及公民社会中得到了广泛的理解、认同与赞扬。
当然,比照国际一流新型全媒体机构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定位,NCR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比如,如何更好采纳智能技术,通过算法来增强议题的扩散度?如何更好对话桥接社群,打通全球传播的“最后一公里”?如何增加在诸如全球气候变化等全球治理议题中的话语机会?这些都是NCR在国家高端智库建设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亟待思考的课题。
作者王亚莘系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河北省城市传播研究院研究员
李祖康系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本文系河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青年基金项目)“战略传播视角中的河北省新型智库传播力研究”(项目编号:SQ2023249)、河北大学校长基金项目“互联网时代的中国共产党政论思想研究”(项目编号:2019HXZ018)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美]凯瑟琳·米勒.组织传播(第2版) [M].袁军,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2]史安斌,刘长宇.解码“乌卡时代”国际传播的中国问题——基于ACGT模式的分析[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2(03).
[3]杨帆,牛耀红.美国Twitter用户涉华态度及认知——基于政治光谱视角[J].国际新闻界,2022(06).
[4]曾持.“媒介化愤怒”的伦理审视——以互联网中的义愤为例[J].国际新闻界,2022(03).
[5]师文,陈昌凤.分布与互动模式:社交机器人操纵Twitter上的中国议题研究[J].国际新闻界,2020(05).
[6]陈昌凤,师文.智能化新闻核查技术:算法、逻辑与局限[J].新闻大学,2018(06).
[7]田浩,常江.桥接社群与跨文化传播:基于对西游记故事海外接受实践的考察[J].新闻与传播研究,2020(01).
【编辑:钱尔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