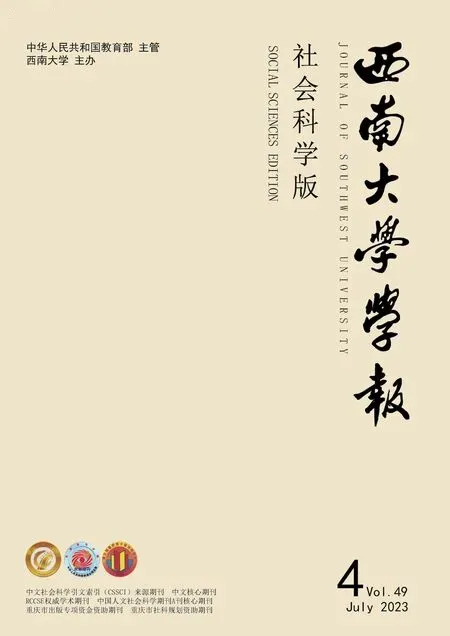“吴宓赠书”与吴宓的西方古典学知识①
郭 涛,陈 莹
(西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重庆 400715)
20世纪前半期中国的西方古典学知识是如何形成的?在灿若群星的先哲中,吴宓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位。近年来,很多学者注意到吴宓不仅是比较文学的开创者,而且也是近代中国研究西方古典学的先行者之一。有学者考察了吴宓对古希腊文学的研究与翻译,然而因为史料所限主要侧重于线索的勾勒,或者将其置放于“学衡派”这一较为宽泛的背景中[1-4];也有学者试图在世界古代史的框架下展开研究,但只局限于吴宓1953—1958年在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任教期间的零星材料,难以窥其全貌[5-6]。吴宓究竟读过哪些西方古典文本,他的古希腊语、拉丁语语言水平如何?吴宓又是如何用中国传统语汇表达西方古典文化,在翻译过程中遵循了怎样的原则?换言之,吴宓的西方古典学知识是何种面貌?对于这一宏大而又细致的问题,在西南一隅的小城北碚恰恰存有一套鲜被学界关注的文献,能够提供丰富的史料。吴宓在1956年将自己收藏的大部分外文书籍整体性捐赠给西南师范学院,现由西南大学图书馆以“吴宓赠书”专题收藏。这套文献不仅体量庞大,而且涵盖了1950年代之前吴宓不同的人生阶段。那么,我们能否从“吴宓赠书”的书籍中重构吴宓,进而管窥20世纪前半期中国知识精英探索西方古典学术的历程?
一、文献来源与概况
“吴宓赠书”主要来自吴宓入蜀之后留在北京的藏书,曾由其前妻陈心一女士保管。在迁居北碚后,吴宓在1955年底决定将藏书整体邮寄,并捐赠给西南师范学院,他在1956年9月14日的日记中写到:“宓捐送西师之书已达863册。由友生取去而损失者甚多。现存者,虽宓所极爱重之书,亦无所顾惜,一体捐赠。”[7]511[8-9]关于吴宓捐赠书籍的具体数目存在争议[9]150,经常被学者忽视的一点是,吴宓在1956年之后对这套文献进行过补充,他在《中世之心:欧洲中世思想感情发展史》(TheMediaevalMind)下册扉页题跋注曰:“今上册竟遗失,甚望学校能不苟配全也。”[10]然而,该书上册的扉页题跋中则写道:“此为欧洲中世史、欧洲文化史、世界文学史之极佳之参考书。共有上下二册,宓皆购藏多年。初谓上册遗失,乃1961年至北京竟取得之,喜可知矣。”[11]可见,“863册”仅是1956年大规模赠书结束时的数字。
经笔者新近对这套文献的全面整理和研究,西南大学图书馆题为“吴宓赠书”的专题藏书现有外文书约630册,另有全套的《学衡》《甲寅周刊》等少量中文书籍。所藏外文书籍主要是由欧美国家出版于19世纪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英语书为主,同时有法语、德语、意大利语、希腊语、拉丁语与和阗文。在藏书门类上,西方古典文明约127册、欧洲中世纪与圣经研究约13册,近现代部分可大致按国别与区域分为英美约154册、法国约262册、德国约9册、意大利约9册、西班牙约7册、俄罗斯1册、东方约11册;其它工具书、理论和通史类书籍约37册。由此可见,古希腊罗马、英美和法国是吴宓西学知识体系中的三个重心。
这套书籍的购置伴随了吴宓在清华读书、国外求学、国内工作等不同的人生阶段。吴宓本名“吴陀曼”,1910年改名“吴宓”[12],赠书中约4册印有“吴陀曼”印章,其中一册为《马考莱拟作(共四篇)古罗马英雄故事之民歌》(Macaulay’sLaysofAncientRome)[13],内容是英国历史学家马考莱(今译“麦考莱”)拟写的四篇古罗马英雄史诗,吴宓在扉页注释曰“(中学读本)”,这本书是19世纪英国中学的标准读本,应是吴宓在清华留美预备科学习外文的读本之一。吴宓赴美留学后,由于上课所需教材、参考书等原因,开始大规模购买外文书籍。吴宓在1892年版《威弗里小说集》(TheWaverleyNovels)第一卷扉页撰写题跋:“宓在美国哈佛大学肄业时1919年春始购置书籍。”[14]在《法国十七世纪文学选注读本》(SeventeenthCenturyFrenchReadings)一书的页边上,吴宓当年为应付考试而做的笔记仍依稀可见[15]。回国任教后,吴宓在清华大学、东南大学、武汉大学、西南联大等地教授《翻译术》《文学概论》《文学批评》《英国散文》等课程的外文教材也在这套赠书之中,这部分书籍很多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经由汉口、昆明的龙门书局翻印的版本。
在1956年3月至9月,吴宓一边对这套藏书进行整理,一边分批交付给图书馆。他用毛笔在大部分藏书的扉页注释了作者姓名、国籍和生卒年,将书名翻译成中文,并做题跋,对书的版本、内容进行介绍和评论,仅吴宓题写的汉译书名及扉页题跋两项,现存约1万6千字(2)此为经笔者整理、校勘后统计得出的数字。。所以,吴宓对这套赠书的整理,不仅是目录学、版本学意义上的整编,而且也是一次具有相当篇幅的、严谨的学术写作。与此同时,“吴宓赠书”中夹杂了吴宓求学和读书时的注释、笔记、摘抄、读书卡片等大量资料,不啻为一座研究吴宓学术思想如何形成的“图书馆”。很大程度上,吴宓对这套书籍的整理是抱着临终遗作的心态进行的。对于这位曾与“新文化运动”顽强抗争的老先生来说,进入五十年代新的学术场景同样是痛苦的。肖太云指出,吴宓具有某种殉道思想[16];张麒麟则强调当时挚友相继离散、家庭生活上的打击造成吴宓晚年避世、出世、厌世,甚至求死的态度[8]19。无论如何,爱书之人整体性地捐出毕生珍藏,这一行为本身意味着对过去的学术与人生,甚至是对当下生命的诀别。吴宓在日记中极富悲情地写到,“如1956春之运书来碚,捐赠西师”等事,皆所谓“完结此生之债者”[17]112。可以说,吴宓对这套赠书的整理实际上是对自己学术思想一次难得的整体性回顾,因而是研究吴宓西方古典学,乃至整个西学知识的珍贵史料。
二、文本阅读与研究
吴宓读过哪些西方古典文本,他的西方古典语言能力到底如何?吴宓深受白璧德等西方新人文主义学者的影响,认为古希腊罗马蕴含着对现代人的指引和规范;不仅如此,西方古典文化因其原典地位,是吴宓及“学衡派”与新文化运动争夺话语权的阵地[2]174。那么,吴宓对西方古典学是否有科学的严谨研究,抑或只是服务于对现实的关切?虽然“吴宓赠书”中的藏书并非吴宓阅读书籍的全部,比如他曾于1957年将留存南京的希腊文学史11册赠于郭斌和[17]72,但是约127册西方古典学书籍的庞大体量仍然为我们提供了较为充分的证据。
吴宓对荷马史诗颇有心得,这不仅体现在1923年《学衡》第13期发表的《荷马之史诗》一文,同时也反映于他阅读过的书籍。关于《荷马史诗》的文本,吴宓在《西洋文学精要书目》一文中提到麦克米伦出版社在1883、1879年出版由安德鲁·朗(Andrew Lang)等人英译的散文体《伊里亚特》《奥德赛》[18]1,“吴宓赠书”中藏有该英译本的节本2册[19-20](3)此处“安德鲁·朗”为笔者译名。,扉页均加盖西南师范学院的前身之一“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图书馆”印章,没有赠书中普遍加盖的“吴宓藏书”印章,但借书卡上写有吴宓1957年10月10日的借阅记录,因此至少可以说,麦克米伦出版社出版于1883、1879年的英译本,或者该译本的节本,是吴宓阅读荷马史诗曾经采用过的文本。除此之外,“吴宓赠书”中还藏有多部研究性专著,在1923年之前出版的有6册:《荷马研究手册》(HandbookofHomericStudy)[21]、《荷马与史诗》(HomerandtheEpic)[22]、《荷马同时论:荷马史诗之时与地研究》(HomericSynchronism:TimeandPlaceofHomer)[23]、《特洛耶城:荷马史诗之地理研究》(Troy:AStudyinHomericGeography)[24]、《荷马统一论》(TheUnityofHomer)[25]、《安诺德全集卷七:论古爱尔兰文学、论翻译荷马》(OntheStudyofCelticLiteratureandonTranslatingHomer)[26]。
在《荷马之史诗》一文中,吴宓明确指出曾参考安诺德《论荷马翻译》对荷马史诗行文风格的论述,上述其他几册书籍虽未明确提及,但内容基本涵盖了《荷马之史诗》一文所涉及的荷马史诗的语言、结构、创作过程、历史背景等问题,特别是对所谓“荷马问题”的讨论,吴宓列举的武鲁夫(F. A. Wolf,今译“沃尔夫”)等十位代表性学者的观点在上述参考书中都有涉及。其中,《荷马统一论》出版于1921年,属于西方古典学界久负盛名的“萨瑟古典讲座”(Sather Classical Lectures)丛书,遗憾的是,吴宓没有在《荷马之史诗》一文中提到该书作者斯科特(John A. Scott),(4)此处“萨瑟古典讲座”“斯科特”为笔者译名。但可以确认他曾认真阅读过,在扉页题跋中概括、评论其观点:“主张荷马实有其他人,而伊里亚特与奥德赛二史诗皆荷马一手作成,并指出荷马以海克多为‘道德之英雄’,其立意之正大。”因此可以推测,吴宓在1923年发表《荷马之史诗》一文后才研读该书。在“吴宓赠书”中,还藏有2册在1923年之后出版的研究专著:《伊里亚德之传统及计画》(TraditionandDesignintheIliad)[27]和《希腊史诗之起原》(TheRiseoftheGreekEpic)[28],吴宓在前书扉页题写的书籍中译名之前,追加标注了一个书目分类名称“荷马史诗研究”。因此,可以发现,吴宓在发表《荷马之史诗》一文后对荷马史诗及相关研究的思考并未停止。值得一提的是,吴宓在《西洋文学精要书目》一文提到《希腊史诗之起原》的1911年版[18]2,“吴宓赠书”现存版本是1924年版,没有裁页,所以对1924年版《希腊史诗之起原》没有通读,尽管如此,购置新的版本仍能说明,吴宓持续关注、追踪西方古典学界的新近研究成果。
相较于荷马,吴宓研究希霄德(Hesiod,今译“赫西俄德”)的参考书籍则非常明确,他在迈尔(A. W. Mair)所著《希霄德诗集》(Hesiod:ThePoemsandFragments)扉页撰写题跋:“宓1923撰希腊文学史中希霄德一章,载学衡杂志第十四期者,即本此书而演述之。”[29](5)此处“迈尔”为笔者译名。迈尔全书分为四章:导论、文本提要、英译文及附录,其中“导论”分为四节,第一节“希霄德的诗歌”,主要介绍其文体与史诗的区别、与希伯来智慧文学的对比和语言风格,第二、三节的标题分别为“希霄德的生平”和“归于希霄德的诗歌”。吴宓1923年在《学衡》第14期发表的《希霄德之训诗》一文分为四节:第一节“希霄德以前之训诗”、第二节“希霄德略传”、第三节“希霄德训诗之内容”、第四节“希霄德训诗之评论”。
如果将两份文本对比,会发现很多有趣的相似和不同。在迈尔的“导论”第一节,首先强调史诗与训诗的主要区别是:史诗重娱乐,而训诗重教诲;相较之下,吴宓《希霄德之训诗》的第一节则列举了与史诗的八条区别,只有第三条是对迈尔原书内容的概括,其他七条均为吴宓的思考和演绎;继而,迈尔将希霄德对希伯来智慧文学进行了对比,吴宓则将这部分内容改编至第四节的第三小节“希霄德训诗与希伯来圣书比较”;紧接着,迈尔从语文学的角度,指出希霄德经常使用隐喻性的语言,比如用“雅典娜的侍者”代替“木匠”,而吴宓则在第四节第二小节“希霄德诗才之特长”介绍了希霄德的语言风格,但没有采用迈尔的观点,而是归纳为“性情真挚”“文笔简洁”“描绘逼真”和“利用自然”,这四个方面在迈尔的书中均未提及。
迈尔“导论”第二节讨论希霄德的生平,从内证、外证两个方面列举西方古典文本证据,没有过多评述;而吴宓强调应该依据希霄德自身文本的记载,认为“以上皆希霄德于其诗中所自叙,要皆可凭信也”,指出“后人所作传,述希霄德之事迹者极多,然皆不可信”,继而对迈尔列举的“外证”史料的缺陷、谬误进行了洋洋洒洒地评述。最后,迈尔在“导论”第三节整理了提及希霄德及其作品的古典文本,列举归名于希霄德的作品名称,并做简介;吴宓则将这部分内容调整至自己文章的第三节,在介绍《田功与日占》(WorkandDays)、《诸神纪》(Theogony)的主要内容后予以罗列和简介。不难发现,吴宓的《希霄德之训诗》一文有明显模仿、改编迈尔《希霄德诗集》“导论”部分的痕迹,但同时在文章的论证结构、具体观点上有不少自己的思考和创见。
除了荷马和希霄德,吴宓对很多古希腊罗马经典作家都有阅读和研究。“吴宓赠书”中藏有:品达(Pindar)1册、爱斯克勒(Aeschylus)2册、苏福克里(Sophocles)2册、尤里披底(Euripides)5册、阿里斯多芬尼(Aristophanes)3册、芝诺芬(Xenophon)2册(有一册与柏拉图为同一本书)、德谟森尼(Demosthenes)1册、柏拉图(Plato)15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19册、海里奥道鲁斯(Heliodorus)1册、凯撒(Caesar)1册、西塞罗(Cicero)2册、布鲁塔克(Plutarch)7册、维吉尔(Virgil)3册、路克安(Lucian)4册,奥维德(Ovid)2册、阿普列乌斯(Apuleius)1册、朗吉努斯(Longinus)1册、卢克莱提斯(Lucretius)1册、彼得罗尼(Petronius)1册、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1册、隆古斯(Longus)1册、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2册。(6)此处“阿普列乌斯”“朗吉努斯”“隆古斯”是笔者译名。吴宓对这些古典作家有较为准确的了解,比如:他根据文本的内容将德谟森尼(今译“德谟斯提尼”)的演说辞《金冠辞》(UpontheCrown)译为《自辩辞》,并在扉页题跋中概括其内容为“自叙一生功业应受国家荣褒”,注释这篇演说辞发表的年代为“330BC”[30];将阿普列乌斯的《金驴记》(TheGoldenAss)译为《变驴记》,并在扉页题跋中解释到“此书在当时风行,故后人加‘金’字于上,言其书甚可宝贵,称曰金驴,实非本名也”[31]。对于残篇、轶文等不那么“经典”的文本,吴宓也很关注,不厌其烦地完整翻译了1851年版凯撒著作英译本的书名:《凯撒所作高卢战纪八卷 其第八卷乃部A. Hirtius所续内战纪三卷 附非洲西班牙战纪部将所作诗文集轶》[32]。
吴宓对西方古典文本的阅读、研究主要依据当时流行的英译本,但在“吴宓赠书”中保留了不少阅读古希腊语原文的笔迹。周轶群在《吴宓与世界文学》一文中认为,吴宓主要是在东南大学任教时随《学衡》同人郭斌和学过古希腊语[33]38-39,这一说法不准确,“吴宓赠书”中的题跋对此提供了更为详细的说明。吴宓在1921年牛津版《亚里斯多芬尼所作谐剧云》(TheCloudsofAristophanes)扉页题跋写道:“1923年夏英国香港大学副校长沃姆G. N. Orme先生力劝宓等学习希腊文(详见学衡杂志二十二期)。宓遂托先生回英国后代为选购希腊拉丁文学研究之精要书籍。其后先生函告宓曰,英国古典文学家李文斯敦先生特赠二书与君,今同寄上,望君能日进于所志之学业也。宓得读李文斯敦先生编著之书,殊深敬慕。是年秋始从南京英国教士Mather先生学希腊文,不久而辍,终于无成。”[34]



西方古典语言是通达古典学术的基础,吴宓曾勉励后辈在留学期间学习古希腊语和拉丁语,强调“研究古典文字即探求西洋文化之根源之工夫也”[47]。吴宓践行了自己的学术理念,尽管他在1956年为赠书撰写题跋时声称,自己的西方古典语言学习“不久而辍,终于无成”,但是我们根据吴宓读书时做的笔记、注释等痕迹,有理由认为他的古希腊语、拉丁语能力至少曾经达到文本细读的水平。1933年出版的郭斌和、景昌极合译《柏拉图五大对话集》的序言写到:“是书之译,吴雨僧先生实主张之。译后又取各英文译本与希腊文原本,详为之校。”[48]由上观之,此言诚非虚语。
三、翻译实践与理论
吴宓不仅有广泛的研读,而且致力于对西学古典文本的译介,在其主办的《学衡》杂志发表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的多篇原典。吴宓如何用中国传统语汇表达西方古典文本?他如何平衡西方古典文明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在已刊印发表的文献中,吴宓本人对西方古典文献原文的翻译并不多,因而相关研究往往被置放于“学衡派”这一较为宽泛的背景中考察。鲜被学者注意到的是,“吴宓赠书”中的题跋、页边注释记载了不少吴宓关于翻译的思考,那么,这些“犄角旮旯”里的文献对当前的相关研究结论是否有所补充,甚至是纠正?
首先,吴宓是如何翻译西方古典研究中的专有名词的?在“吴宓赠书”扉页题跋翻译的书名和题跋中,很多古典作家的译名在当代学界仍然使用,比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凯撒”“奥维德”等。他倾向于只音译人名的词干部分,而不译会因变格而发生变化的词尾,比如“Aeschylus”译为“爱斯克勒”而不是“爱斯克勒斯”,但偶尔也会全部译出,比如“Lucretius”译为“卢克莱提斯”。虽然“吴宓赠书”的题跋主要是在1956年3月至9月期间集中写作的,但一些译名没有统一,比如“爱斯克勒”又译为“爱斯克洛”,“尤里披底”又译为“幼里披底”,“阿里斯多芬尼”又译为“亚里斯多芬尼”,“布鲁塔克”又译为“布尔特奇”。这一现象在“吴宓赠书”其他门类书籍中同样存在,比如吴宓将《杂俎》(Variété)一书的作者“Paul Valéry” 译为“韦拉里”,同时注明梁宗岱的译名“梵乐希”[49]。吴宓没有像罗念生那样编订一份《希腊拉丁文译音表》,但他意识到翻译需要警惕方言的影响,吴宓为《孟德恩论文集》一书撰写的题跋可作参考:“此为法国十六世纪后半散文大作者孟德恩之论文集论文一体乃其所创,原‘尝试’之意,吾国梁宗岱君曾有介绍,译其名曰蒙田粤音。此英译本1603作于莎士比亚之时,亦古朴有名。共三册”,吴宓指出梁宗岱的译名“蒙田”根据粤语方言是不妥的[50]。
吴宓在阅读西方古典文献的过程中,针对一些短语、短句和段落在书籍的页边位置做了批注,对原文进行转写、概括或摘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是对原文的一种“翻译”,具有代表性的几例有:

吴宓读书页边注释举要(14)序号1—8所在书籍版本信息为Benjamin Jowett trans.,The Dialogues of Plato,vol. 1,New York:Scribner Armstrong and Co.,1873。序号9所在书籍版本信息为:A. D. Lindsay ed.,Plato and Xenophon:Socratic Discourses,London:J. M. Dent &Sons,1910。序号10所在书籍版本信息为:Theodore Alois Buckley trans.,The Tragedies of Aeschylus,London:George Bell &Sons,1901。序号11—17所在书籍版本信息为:J. E. C. Welldon trans.,The Rhetoric of Aristotle,London:Macmillan,1886,该书没有收藏于“吴宓赠书”之中,扉页未加盖“西南师范学院图书馆”钢印,但盖有和“吴宓赠书”所藏书籍相同的“吴宓藏书”印章,遗憾的是,这本书已被私人书商售卖,不知所踪,笔者只获得部分照片。
正如很多学者注意到的那样,吴宓热衷于用文言,而非白话翻译西方古典文献,比如表格第12例“the law of nature”,今译为“自然法”,而吴宓则译为“天道、公理”;吴宓总是寻找与中国古代典籍相互对应的表达,比如表格第5~8例,征引《论语》《孟子》《大学》中的语句来概括,或者说“意译”柏拉图的原文语句。吴宓批评郭斌和、景昌极的某些翻译受到了流行白话文的影响,在1873年版乔伊特(Benjamin Jowett)译《柏拉图对话录》第一卷扉页,粘贴有郭斌和、景昌极译《柏拉图五大对话集》的广告插页,吴宓在此写下评论:“此书原登学衡杂志,各篇均经吴宓校注。其书名应曰语录,不应从今俗曰对话,时宓在欧洲,乃迳出版,不从宓定名,可憾也。”[41]对于吴宓的翻译风格,施耐德(Axel Schneider)强调吴宓是一位“古典保守主义者”,同时混合了孔子和柏拉图的语言元素[51],姜筠则认为使用中国古典语言翻译西方古典文献的目的是强调两种文化之间的共性[1]199。需要注意的是,吴宓意识到中西古典语言之间存在无法对译的情况,比如表格第16例“在古希腊人中,又在古希腊文中,友与爱无别。”因此,刘津瑜的解释更引人深思,吴宓及“学衡派”并非简单地寻找中国与西方古典语言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文的意思进行增加或删减,比如:郭斌和用“礼”翻译柏拉图的“καλν”,强化了礼教的成分,而弱化或无视欢娱(pleasure)也是这一概念的重要内容[4]103。
如果可以接受这样的解释,那么吴宓及“学衡派”在翻译西方古典文本时遵循的标准是什么?吴宓在1923年发表的《论今日文学创造之正法》一文曾指出,翻译应依据严复的“信、达、雅”原则,但同时又指出翻译的具体方法以“意译(Paraphrase)最合中道”[52],这里的“意译”具体指什么原则?吴宓在阅读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第332—363行被学界称为“人颂”的合唱歌时,在原书第11页页边位置不无自豪地注释道:“已由宓译出,见学衡53期,又载吴宓诗集卷七9—10页,题曰人智之卓越”[53](15)此处“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为笔者译名。,然而,《吴宓诗集》刊印的只有文言诗体译文本身,没有解释为何如是翻译。对于吴宓及“学衡派”来说,对原文意思的增删与“信、达、雅”原则如何保持平衡?
在“吴宓赠书”中,藏有1册“人人文库”1907年版英国翻译理论家泰特勒(Alexander Fraser Tytler)的《翻译原理论》(EssayonthePrinciplesofTranslation)[54],为深层描绘吴宓的翻译原则提供了形象证据。吴宓对此书极为爱护,将其作为在清华大学教学的课本,在扉页题跋写道:“始自1925年,宓在清华授翻译术一课程,恒以此书为课本,用之多年,其书尚如新。”在第一章第9页,泰特勒提出了翻译的三原则:I.译文应完全复写原文的意思,II.译文应与原文具有相同的风格,III.译文应与原作一样流畅,吴宓在此页的页边注释曰:“严几道(复)先生(一)信(二)达(三)雅之说,似由此出。”紧接着,《翻译原理论》分章举例阐释了翻译的三原则,吴宓对每章列举的范文都做了数字标号,对第一部分关于“信”的讨论尤为关注,泰特勒认为,译者拥有增加或删减原文意思的自由,对此吴宓在页边做了多条注释。
对于增加原文意思,泰特勒主张译者可以追加从原文衍生出来的意涵,并在书中第22~23页以英国诗人谛克尔(T. Tickell)《死别》(ColinandLucy)一诗第四、五节的法译文为例。有趣的是,吴宓曾将这段诗译为中文,《吴宓诗集》刊印的版本为:“明日入婚筵,双双各整备。勖汝新鸳鸯,露西行亲莅。慎将吾遗体,往见俏郎君。羡郎着华服,怜妾覆素衾。”[55]然而,在《翻译原理论》第23页的页边位置,吴宓誊写了自己初期的译文“明日入婚筵,1彼时同戒备。2勖汝双新人,露西行亲莅。慎将吾遗体,往见俏郎君。3羡郎着华服,4怜妾覆素衾”,继而罗列了文中数字标号处的备选译法:“1双双各整备、2寄语新鸳鸯、3喜郎着华服、4君衾不同颜。”最后,吴宓在同一页边位置单独写下一句译文:“往别俏郎君,看郎着华服”,将其中的“别”“看”用红笔划线强调,并用英文注明泰特勒使用的术语“Superadded idea”,吴宓另将1925年翻译全诗的初稿字条粘贴在此处。字条和页边注极为生动地再现了依据泰特勒的理论翻译《死别》的全过程。

由此观之,吴宓在对荷马史诗具体文本的翻译上,与泰特勒有不同意见,尤其是对中西方经典文献中英雄形象的比较使他跳出、超越了泰特勒的研究视野。但总体而言,吴宓接受了泰特勒的翻译原则,不仅将这些原则贯彻于翻译实践中,而且将自己的译诗作为体现这种原则的范例。不难发现,吴宓(某种程度上包括“学衡派”)从泰特勒《翻译原理论》那里接受过来的“信”这一翻译原则与我们通常理解的“忠实原文”的意涵具有显而易见的差别,译者可以为保持所谓原文的“本意”对原文的意思进行添加或删减,究竟什么是“原文的本意”往往取决于译者自己的理解。事实上,在吴宓的观念中,“文学”的旨归乃是“救世”,他对只强调客观实证的考据之学是批评的。正如周轶群指出的那样,吴宓有着强烈的淑世之心[33]83,在“吴宓赠书”收藏的《亚里士多德全集撮要》(Aristotle)一书扉页题跋中,吴宓写道:“作者乃一考据之学者,思想及文笔无足称,所著道德权责论未能动人,有枯索之感。宓在牛津曾往谒聆教,亦无所得也。”[56]由此观之,“忠实原文”,抑或“准确”,并不是吴宓翻译西方古典文本时追求的首要目标,相反,吴宓及“学衡派” 通过借用泰特勒的翻译理论获得了“以新内容入旧格律”的方法,在标榜“信、达、雅”的同时,“重写”西方古典文本,将西方古典知识嵌入中国传统语言之中,进而实现其最终的文化理想:构建一种融合中西方古典文化,却又超越其上的新文化。
四、结 语
通过对“吴宓赠书”的研究,我们可以重构吴宓西方古典学知识的大致面貌:吴宓对西方古典文本有着较为广泛的研读,虽然以英译本为主,但他的古希腊语、拉丁语能力达到文本细读的水平;他对西方古典学界的研究成果有着持续的追踪与研读,对具体文本的研究既有模仿西方学者的痕迹,也有不少自己的创见;与此同时,在翻译西方古典文本的过程中,吴宓的目标不是实证性的考据,他秉承的翻译原则允许译者有增删原文的自由,进而“重写”西方古典文本,将西方古典文化融汇、嵌入中国的传统语汇之中。近年来,国内学界对如何建设中国的西方古典学科的路径存在不小争议,[57]一方面,如何科学、准确地通达西方古典学术,另一方面,如何平衡西方古典文明与中国文化,乃至现代中国社会的关系?这不仅是当代学者争论的焦点,也是20世纪前半期中国研习西学的先哲们曾经面对的问题。必须承认,我们无法从先哲那里照搬答案,然而,对吴宓西方古典学知识的考察仍然能够为我们重新审视20世纪前半期西方古典学知识在中国的形成提供了一个缩影,据此鞭策我们反思前辈们的探索历程和经验,并进一步思考:如何“让西方古典学真正成为最优秀的中国学术之一部分”?[58]
非常遗憾的是,吴宓的西方古典学知识在50年代之后的传承充满坎坷。他虽然对西方古典学术有不少了解和研究,但在历史系教授《世界古代史》课程期间仍发出“用宓之才学不当,且使本门课程受损也”的感叹[7]274。对于“吴宓赠书”这套当时国内不多见的外文文献,吴宓在1962年致李赋宁的信中写道:“……此间无人读此一批书也。其中有许多重要有用之书(如Du BellayDéfenseetIllustrationdelaLangueFrançaise1549)(19)此处原书校勘的作者名和书名有少许错误,在征引时纠正,现存“吴宓赠书”中没有找到这本书。,如北大杨周翰等诸公,编译外国文学,尽可利用……”[59]此处的“无人读此一批书”实际上是有所夸张的,但可以想象,这样的感叹源自他极度孤寂而又无奈的心境,社会与时代的巨变导致他孜孜以求的治学方法、学术理想不被认同,蜀中知音难觅,毕生所学无所用之。虽然斯人已去,但值得庆幸的是“吴宓赠书”事实上留下了不少印记,《荷马研究手册》一书贴有字条“此书插图及地图,甚可贵重。且为世界古代史课之必要参考书。故望能于1956年九月十五日以前,编目完成,可以借”[21],《特洛耶城:荷马史诗之地理研究》一书贴有字条“世界古代史必用之参考书(望早编目)”[24],这套文献中的很多书籍成为西南师范学院教授《世界古代史》课程的参考书,不仅如此,在《西塞罗演说集》(OrationsofMarcusTulliusCicero)[60]、《西塞罗道德论集》(Cicero’sThreeBooksofOffices,orMoralDuties;andhisCatoMajor,anEssayonOldAge;Laelius,anEssayonFriendship;Paradoxes;Scipio’sDream;andLettertoQuintusontheDutiesofaMagistrate)[61]、《布鲁塔克希腊罗马英雄传》(Plutarch’sLives)[62]、《剑桥中世纪史》(TheCambridgeMedievalHistory)[63-65](20)此处“《剑桥中世纪史》”为笔者译名。等书籍的借书卡片上留下世界古代史教研室教师孙培良、王兴运、陈济沧、喻小航等在1950—1980年代的借阅记录。随着历史的变迁,书籍不断被重新阅读,吴宓的西方古典学知识也随之被继承和重塑,而这则属于一个新时代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