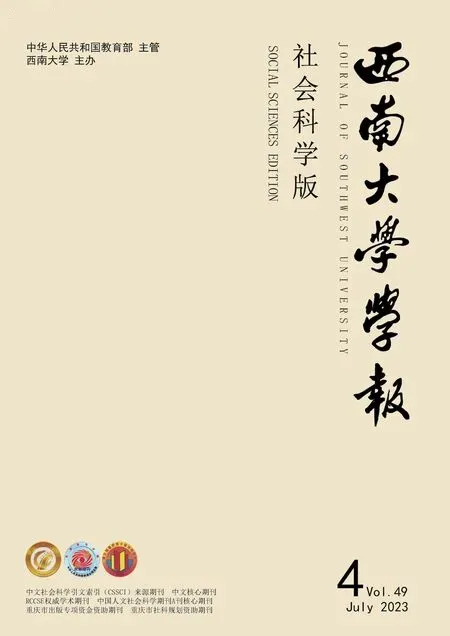唐代城市应对战争机制的历史考察
梁 克 敏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 文化与历史研究所,陕西 西安 710065)
战争作为政治延续的一种暴力手段,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生。由于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或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唐代频繁爆发了大大小小的战争。据《中国历代战争年表》统计,自唐高祖武德元年(618)至哀帝天祐三年(906)共发生过193次战争[1],这还只是规模较大的战争。实际上还有许多规模较小的战争,仅从天宝十四年至长庆四年(755—824)的70年时间就发生过大小内外战争228次,平均每年3.26次[2]。
战争是不同国家、民族或政治团体为了争夺财富、资源、人口而发生的一种激烈的暴力活动。“城镇聚集着财富和权力,因此引起征服者或掠夺者的注意”,而且城市还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中心,“占据城市中心,就能最好地从政治上和经济上控制地区”[3]。因此,城市往往成为战争中攻击的首要目标。在战争中,不仅城市的基础设施被直接破坏,财富遭受劫掠,人口被大量杀伤,而且城市周边的农业也会受到破坏,人口大量流失,城市发展的社会环境被破坏,使城市面临严重的危机。如安史之乱期间,安禄山攻陷陈留郡城后,“杀陈留降者万人以逞,血流成川”[4]卷191,《忠义上·张介然传》;尹子奇久围睢阳城,城中食尽,“括城中妇人食之,继以男子老弱”,城破之时城中数万人“所余才四百人”[5]卷220,唐肃宗至德二载十月壬子。安禄山占领长安,“取帝近属自霍国长公主、诸王妃妾、子孙姻婿等百余人害之”,“群臣从天子者,诛灭其宗”,因而“士人皆逃入山谷,东西骆驿二百里”,唐军与叛军在关中争夺郡县城市,“前后反覆十数,城邑墟矣”[4]卷225上,《逆臣上·安禄山传》;战争使城市周边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洛阳诸郡人相食,城邑榛墟”[4]卷225上,《逆臣上·史思明传》;回纥军在洛阳“放兵攘剽,人皆遁保圣善、白马二祠浮屠避之,回纥怒,火浮屠,杀万余人”[4]卷217上,《回鹘传上》;战争中,洛阳城“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城市人口锐减,不满千户,周边地区“井邑榛棘,豺狼所噑,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6]卷120,《郭子仪传》。安史之乱平定后,战乱并未停止,周边民族入寇和藩镇叛乱使城市常常惨遭兵燹。宪宗时,吴元济反叛,四处攻占城市,“屠舞阳,焚叶县,攻掠鲁山、襄城。汝州、许州及阳翟人多逃伏山谷荆棘间,为其杀伤驱剽者千里”[6]卷145,《吴少诚传附吴元济传》;太和三年(829),南诏袭取成都,“大掠,焚郛郭,残之,留数日去,蜀之宝货、工巧、子女尽矣”[4]卷96,《杜如晦传附杜元颖传》。唐末,农民起义及藩镇间的争战愈演愈烈,长安、洛阳、扬州、成都等古都名城都遭到严重的破坏。战争关系到城市的存亡、兴衰,是城市所面临的最严重危机,应对战争危机是城市管理的一项重要任务。
城市从诞生之时就具有明确的安全防御功能,面对频繁的战争及其对城市的严重破坏,唐王朝非常重视城市应对战争机制的完善,在战前和战时采取多种措施来减轻甚或消弭战争及其带来的危机,以保障城市在战争中的安全,战后也会采取一些措施以便城市能尽快从战争中恢复过来。目前,学术界对唐代战争与城市关系的研究虽已取得一些成果[7-9],关棨匀[10-11]、张清华[12]分别从军事防御技术的角度对隋唐五代城市的军事防御和城防技术进行了研究,探讨了唐代城市防御技术的发展,但关于唐代城市应对战争危机的机制还鲜有论及,缺乏对这一问题的系统研究。本文试图从城市危机管理的角度对唐代城市应对战争的具体措施进行考察,并藉以探讨唐代城市应对危机的机制。
一、唐代城市战前的防御措施
古语云: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忘战必危[13]卷64上,《主父偃传》。唐朝统治者具有强烈的居安思危意识,深知和平时期城市军事建设的重要性。唐太宗在《帝范》中说道:“夫兵甲者,国之凶器也。土地虽广,好战则人雕;邦国虽安,亟战则人殆。雕非保全之术,殆非拟寇之方。不可以全除,不可以常用……故知弧矢之威,以利天下。此用兵之机也。”[14]卷4,《阅武第十一》由于古代技术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唐代城市战前采取的防御措施主要有二:其一,“内严师兵之营卫”,即加强军队的建设和布防;其二,“外固沟池之垣翰,简阅以供时,使屯戍以防外虞,益缮戎器,增治战具”[15]卷124,《帝王部·修武备》,做好城市的军事防御工程建设和必要的物资储备。凭此二途,增强战争来临时城市应对危机的能力。
(一)城市军队力量的建设
人是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正所谓“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16]卷1,《权修第三》,军队是城市在战争中最重要的防卫力量,因此唐朝统治者非常重视军队的建设。唐前期的军队建设主要是继承和完善周隋以来的府兵制,高祖李渊晋阳起兵之初,仅有三万军队,在进军关中的过程中,又收编了沿途的反隋武装和旧隋降军,兵力增加到二十万人。建国后,置军府,以骠骑、车骑两将军府统领军队,并将当时唐朝所控制的关中分为十二道,析置十二军,军置将、副各一人,以督耕战,以车骑府统领;武德六年(623),改骠骑曰统军,车骑曰别将;贞观十年(636),唐太宗进一步完善府兵制,改统军为折冲都尉,别将为果毅都尉,诸府总称折冲府。军府的设置、布局也与城市的战争应对密切相关。唐代折冲府数量非常可观。《唐六典》记载天下置府五百九十四[17]卷5,《尚书兵部》。由于唐王朝奉行“关中本位”政策的缘故,这些军府的分布是极不平衡的[18-19],关中地区是军府的集中分布地。《新唐书》记载:“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号,而关内二百六十有一”[4]卷50,《兵志》,以达到“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的目的[20]卷72,《府兵》。然而,自高宗、武后开始,由于频繁对外用兵,府兵的兵役负担不断加重,加上土地兼并导致均田农民大量破产,府兵制逐渐寖坏,“番役更代多不以时,卫士稍稍亡匿,至是益耗散”。因此,到开元十一年(723),宰相张说奏请“一切募士宿卫”,“取京兆、蒲、同、岐、华府兵及白丁,而益以潞州长从兵”,共募得十二万人,号“长从宿卫”,后又改称“彍骑”,募兵制开始逐渐取代府兵制,“自是诸府士益多不补”,以彍骑分隶十二卫,总十二万[4]卷50,《兵志》。这就弥补了因府兵制的崩坏而导致京师长安城市防卫能力下降的不利局面,为都城长安应对战争提供了足够的兵力保障。
府兵之外,京师长安还有所谓的“天子禁军”。唐朝统一全国之后,高祖以天下已定,将大部分军队遣散罢归,只留“宿卫者三万人”,号“元从禁军”,这是唐代最早的中央禁军。贞观初,唐太宗简择善射者百人,分为二番于北门长上,称为“百骑”,又置北衙七营;贞观十二年(638),置左、右屯营于玄武门,领以诸卫将军,号曰“飞骑”;龙朔二年(662),唐高宗取府兵越骑、步射又设置左、右羽林军;武则天时,增补“百骑”人数至千人,改称“千骑”,中宗又改曰“万骑”,并分左、右营;玄宗时,改称左、右龙武军。至此,唐前期的禁军始至完备。府兵制崩坏的同时,唐中央禁军也开始废弛,至玄宗末年,“禁兵寖耗,及禄山反,天子西驾,禁军从者裁千人”,随肃宗赴灵武,“士不满百”。由于安史之乱时原有禁军已流散殆尽,至德二年(757)唐肃宗置左、右神武军,以元从、扈从官子弟补,不足则取它色,制如羽林军;又择便骑射者置衙前射生手千人,曰“供奉射生官”或“殿前射生”,分左、右厢,号“左、右英武军”。左、右神武军、英武军作为当时中央禁军,成为安史之乱期间唐王朝防守长安城的主要军事力量。代宗时,源自京师西北的神策军由于在皇帝的多次逃亡过程中护卫有功,再加上宦官鱼朝恩担任观军容使,监其军,“遂以军归禁中”[4]卷50,《兵志》,由一支地方武装而升为天子禁军。此后,神策军日渐强大,成为朝廷掌握的一支战斗力较强的军队,是长安城应对战争危机最主要的武装力量。
在唐前期,地方城市也设置有一定数量的折冲府[21]11-12,是它们应对战争危机的主要力量。安史之乱后,唐王朝中央集权受到极大的削弱,地方武装力量日渐增强,“刺史皆治军戎,遂有防御、团练、制置之名。要冲大郡,皆有节度之额”[6]卷38,《地理志一》。各地藩镇为了壮大自己的实力,都自行募兵,以致形成“大都通邑,无不有兵”的局面[6]卷17下,《文宗本纪下》,藩镇武装构成了所在城市应对战争危机的主要力量。
(二)城市防御设施的建设
除了加强军队建设和布防之外,完善军事防御设施也是提升城市应对战争危机能力的必要举措。京师长安是唐王朝最为核心的城市,唐代统治者非常重视长安的城防设施建设。
首先,长安城外围军事防御阵线的建设。在唐前期,长安城面临的战争威胁主要是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突厥。因此,唐统治者在长安城以北至阴山的广大区域构筑了三道阻挡突厥军队南下的防御战线[22]附篇一,《唐代河套地区军事防御系统》。如武德二年(619),唐高祖令关中州县“修治堡固,以备胡”;武德七年(624)又令长安北边诸州“修堡城,警烽候,以备胡”[15]卷990,《外臣部·备御三》。突厥入侵时,刘弘基奉命率步骑一万进行抵抗,遂“自豳州北界东拒子午岭,西接临泾,修营障塞”,将突厥军队抵挡在北部边境之外[6]卷58,《刘弘基传》;武德九年(626)九月,唐太宗即位后,突厥骑兵进抵至长安北渭河岸边,对长安构成直接的军事威胁,因而在突厥退兵后,太宗立即颁布《修缘边障塞诏》曰:
城彼朔方,周朝盛典;缮治河上,汉室宏规。所以作固京畿,设险边塞,式遏寇虐,隔碍华戎。自隋氏季年,中夏丧乱,黔黎凋尽,州域空虚,突厥因之,侵犯疆场,乘间幸衅,深入长驱,寇暴滋甚,莫能御制。皇运已来,东西征伐,兵车屡出,未遑北讨,遂令胡马再入,至于泾渭,蹂践禾稼,骇惧居民,丧失既多,亏废生业。……御以长算,利在修边。其北道诸州,所置城寨,粗已周遍,未能备悉。……其城寨镇戍,须有修补,审量远近,详计功力,所在军民,且共营办。所司具为条式,务使成功。[23]卷107,552
经过两代人的努力,唐王朝构筑了以突厥为防御对象,以关中为核心的北方防御网络[24]。突厥灭亡后,地处西北的吐蕃日渐强大,安史之乱中西北边军内调,唐朝西北边防线急剧内缩至关中凤翔、泾原一带,“平时安西万里疆,今日边防在凤翔”[25]卷427,《西凉伎》。吐蕃军队得以常深入关中腹地,逐渐成为长安城面临的主要战争威胁。为了防范吐蕃对长安城的侵扰,安史乱后,唐代宗开始着手重建京西北防线,经过德宗、宪宗至穆宗几代人的经营,形成了以神策军为主力的京西北八镇防御格局。《新唐书》记载:神策军成为天子禁军后,“京畿之西,多以神策军镇之,皆有屯营”,称为“神策行营”[4]卷50,《兵志》。在西南地区,晚唐时期南诏的崛起,成都等城市不断受到侵扰,唐朝中央和地方不断加强西南边防建设,增置军兵、修筑堡戍、优化政区建置等,尤其是防冬兵的增置是晚唐加强西南边防建设的重要手段。《资治通鉴》记载:峰州“旧有防冬兵六千”,胡三省注曰:“南方炎瘴,至冬,瘴轻。蛮乘此时为寇,故置防冬兵。”[5]卷249,唐宣宗大中十二年六月丙申同时,唐王朝也注意修筑城堡、障塞等防御工事。贞元三年(787),吐蕃军队毁盐州城,“自后塞外无保障,犬戎入寇”,九年(793)德宗诏“复筑盐州城”,“既城之后,边患顿息。”元和三年(808),泾源节度使段佑奏请修临泾城,“以扼犬戎之冲”,诏从之;长庆四年(824),夏州节度使李祐亦奏于塞外筑乌延、宥州、临塞、阴河、陶子等五城,“以备蕃寇”[20]卷86,《城郭》。为了防范南诏对成都的攻击,西川节度使李德裕奏请:“大度水北更筑一城,迤逦接黎州,以大兵守之方可”[5]卷244,唐文宗大和四年十月戊申,7995;后来,牛丛又在边境地区修筑新安城和遏戎州两座要塞[15]卷410,《将帅部·壁壘》,构成了成都外围的第一道防线;此外,还修建了清溪关、望星关、琉璃、仗义等关城和戍栅、驻防弩兵等第二道防线,构筑了大渡河南、北两层防线。同时,还不断对成都本身的防御设施进行增修完善。咸通十一年(870),南诏退军后,颜庆复“教蜀人筑壅门城”[5]卷252,唐懿宗咸通十一年二月庚子;乾符三年(876),西川节度使高骈又增筑成都罗城,“南北东西凡二十五里,拥门却敌之制复八里,其高下盖二丈有六尺,其广又如是,其上袤丈焉,陴四尺。斯所谓大为之防,俾人有泰山之安矣。而甃碧涂塈,既丽且坚,则制磁饰頳,又奚以异。其上建楼橹廊庑,凡五千六百八间。梠栉比,闉闍鳞次。……其外则缭以长堤,凡二十六里。或引江以为堑,或凿地以成濠”[26]卷793,《创筑罗城记》,从而大大提高了成都的军事防御能力。此外,唐王朝还在边境地区设置有众多的烽燧,“从缘边置烽,连于京邑,烽燧相应,以备非常”,《唐律》中规定:“诸烽候不警,令寇贼犯边;及应举烽燧而不举,应放多烽而放少烽者:各徒三年”[27]卷8,《卫禁律·烽火不警》,对不按规定放烽发出外敌入侵警报者给予严惩。不论唐朝前期针对突厥的北方防线,还是后期防御吐蕃的京西北防线和西南防线,都是以耕戍相兼的大小军城为支撑,由军城、遮虏障和边州行政城邑组成,构成了长安和成都等大城市外围应对战争危机的一道坚固军事防线。
此外,唐政府还注意增修城墙、城门、城隍,疏浚城壕、护城河,完善城市本身的工程防御设施。武德九年(626)正月,唐高祖“命州县修城隍,备突厥”[6]卷1,《高祖本纪》。永徽五年(654)、开元十八年(730),唐政府曾两次增筑长安外郭城;东都洛阳城在隋炀帝时仅修有短垣,长寿元年(692),武则天令凤阁侍郎李昭德“造定鼎、上东等城门,修筑外郭”;天宝二年(743),再次“筑神都罗城”,号曰“金城”[20]卷86,《城郭》。武周时期,河北州县常遭突厥袭扰,“时诸州闻突厥入寇,方秋,争发民修城”[5]卷206,唐则天后圣历元年八月戊子。天宝末,颜真卿任平原太守,察觉安禄山有意叛乱,遂以霖雨为托词“修城浚池,阴科丁壮,储廪实”[15]卷696,《牧守部·修武备》;安禄山起兵反叛,叛军一路南下,东都洛阳当其冲要,面临严峻的战争威胁,东京留守李憕与留台御史中丞卢弈、河南尹达奚珣“缮城垒,绥励士卒,将遏贼西锋”[4]卷191,《忠义上·李憕传》。安史之乱后,战争更加频繁,各地纷纷修城备战,加筑外郭城。建中初,术士桑道茂曾对唐德宗说:“国家不出三年,暂有离宫之象”,会发生战乱,因奏请修筑奉天城,“制度为垒,以备非常”,德宗“遂令京兆尹严郢充筑城使,具畚锸,抽六军之士督策之”[28]卷1。建中末,“天下方骚,北边数有警”,河东节度使马燧认为太原城“宜固险以示敌”,于是“引晋水架汾而属之城,潴为东隍,省守陴万人。又酾汾环城,树以固隄”[4]卷155,《马燧传》。从安史叛乱后,袁知泰、能元皓等相继对魏州城“缮完之,甚为坚峻”[6]卷111,《崔光远传》。贞元时,李元谅为陇右节度使,治良原城,其城“隍堞湮圮”,吐蕃常常入寇,元谅乃“培高浚渊,身执苦与士卒均,菑翳榛莽,辟美田数十里,劝士垦艺,岁入粟菽数十万斛,什具毕给。又筑连弩台,远烽侦,为守备,进据势胜,列新壁”,故此后“泾、陇以安,西戎惮之”[4]卷156,《李元谅传》。张建封为寿州刺史,李希烈派遣杜少诚攻寿州城,建封于“霍丘坚栅,严加守禁,少诚竟不能进”[15]卷696,《牧守部·修武备》。黄巢起义后,战争更加频繁,为了增强城郭的战争防御能力,各州县治所城市纷纷增修、扩展城郭。唐末,赵犨为陈州刺史,“完城堑,缮甲兵”,后黄巢军东攻项县,赵犨引兵击之[5]卷255,唐僖宗中和三年五月;晚唐时,南诏屡兵犯成都。咸通十一年(870),唐朝廷遣东川节度使颜庆复率军前往救援,南诏撤军后,颜庆复“教蜀人筑壅门城,穿堑引水满之,植鹿角,分营铺”,南诏得知成都已有防备,从此“不复犯成都”[5]卷252,唐懿宗咸通十一年二月庚子;后来,高骈继任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观察使,又增修成都城墙,“计每岁完葺之费,甃之以塼甓,雉堞由是完坚”;高骈转任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当时王仙芝、黄巢起义军正转战长江中下游各地,高骈“缮完城垒,招募军旅,土客之军七万”[6]卷182,《高骈传》。大顺元年(890),上元由县改为升州,冯宏铎任刺史,“遂增版筑,大其城为战守之备”[29]卷2,《冯宏铎传》。为“绝外寇窥觎之患,保一州生聚之安”,明州刺史黄晟修筑州城罗城,周回十八里[30]卷3,《叙郡下·城郭》。僖宗时,魏博节度使乐彦祯,征发所属魏、博、贝、相、澶、卫六州百姓“筑(魏州)罗城,方八十里”[5]卷257,唐僖宗文德元年二月庚寅;天祐三年(906),邓季筠出任登州刺史,登州旧无罗城,季筠到任后“率丁壮以筑之,民甚安之”[31]卷19,《邓季筠传》;同是汴将的杨师厚为襄州节度使,也为襄州修罗城,“兴板筑,周十余里,郛郭完壮”[31]卷22,《杨师厚传》。罗城的增修有利于扩大城市防御的纵深空间。此外,晚唐时期城市的防御设施也有新的发展,在一些重要的州府城市还普遍增修了甕城、羊马城和敌楼等城防设施。光启三年(887)十月,朱温攻陷濮州,刺史朱裕逃奔郓州,朱温遣将朱珍攻郓州,朱裕向珍诈降,“珍军已入瓮城而垂门发,郓人从城上磔石以投之,珍军皆死甕城中,珍仅以身免”[32]卷21,《朱珍传》。文德元年(888)五月,在朱温征讨蔡州秦宗权的战争中,汴军“进军蔡州,营其西南,既破羊马垣,遇雨班师”[31]卷19,《朱珍传》。光化三年(900),李克用将李嗣昭攻河阳城,已“坏其羊马城”,幸亏汴将阎宝率佑国军赶到救援,“河东兵乃退”[5]卷262,唐昭宗光化三年十月丙申。这从侧面反映了羊马城在阻碍敌军攻城、屏卫主城方面的作用。景福二年(893),钱镠征发民夫和兵士“筑杭州罗城,周七十里”[5]卷259,唐昭宗景福二年七月丁亥,城上“十步一楼,可以为固矣”[5]卷263,唐昭宗天复二年八月丁亥。这些城防设施的完善进一步增强了城市在战争中的防卫能力。
战时守城所需的各种物资也需要在和平时期做好充足的准备。粮食和军事器械的储备是城市守卫中最基本的物资准备。《通典》引《李卫公兵法》曰:“什物、五谷、糗糒、鱼盐、布帛、医药、功巧、戎具……长锥、长鎌、长梯、短梯、大钩、连锁、连枷、连棒、白棒、芦竹,为稕插以松桦,城上城下,咸先蓄积,缘人闲所要公私事物,一切修缉。”[33]卷152,《兵五·拒守法附》天宝末,颜真卿任平原太守,察觉到安禄山有叛乱的意图,遂以霖雨为托词“修城浚池,阴科丁壮,储廪实”;李皋为洪州刺史,时梁崇义反叛,他“缮甲兵,具战舰,将军二万”;王翃为东都留守,“开置二十余屯,复市劲筋、长铁,简练器械”;陈州刺史赵犨,在黄巢起义军进攻之前,除了增修城墙,深挖城壕外,还“实仓廪,积薪刍。凡四门之外,两舍之内,民有资粮者,悉令挽入郡中,缮甲利兵,剑矟弓弩矢石无不毕备。又招召劲勇,寘之麾下,以仲弟昶为防遏都指挥使,以季弟珝为亲从都知兵马使,长子麓、次子霖皆分领锐兵”,后黄巢军东攻项县,赵犨引兵击之,起义军大溃[15]卷696,《牧守部·修武备》;马璘为四镇北庭行营节度使,以吐蕃多次犯边,移镇泾州,至州“分建营伍,缮完战守之具”,在州八年,“城堡获全,虏亦不敢犯境”;李景略为丰州刺史、西受降城使,“廪诸备,器械具”,军声雄冠北边,回纥畏之而不敢犯边[15]卷429,《将帅部·守边》;冯宿任东川节度使,“完城郛,增兵械十余万”[4]卷177,《冯宿传》。其次,守城所用的一些其它物品也需要提前准备好。唐人李荃所撰的《神机制敌太白阴经》中记载的守城之具有悬门、突门、涂门、转关桥、凿门、积木、积石、楼橹、笓篱战格、布幔、木弩、燕尾炬等[34]卷4,《战具类·守城具篇》,这些物品在守城过程对于击退敌人的进攻都能发挥特殊的作用。
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城市应对战争危机的最佳效果。战前的充分准备,在一定程度上能使敌人知难而退,止兵革于未萌,使城市免遭兵燹。即便难以避免战祸,充分的准备也能提高城市抵御战争的能力,减少战争的破坏,使城市能够在战争中得以保存。
二、唐代城市战时的应对措施
在面对战争之时,戒严是唐代城市战时体制中的核心措施。通过实施戒严,城市管理者加强对城市的严格管控,以便能够集中城市资源抵御敌人的进攻,保全城市。
(一)城市戒严的实施
唐初,因突厥的侵扰,京师长安城经常会面临严重的战争危机,多次实施戒严加以应对。武德七年(624)八月戊辰,突厥入寇关中,京师戒严,壬午突厥退,乙未京师解严[6]卷1,《高祖本纪》;九年(626)八月,突厥趁太宗初即位再次入寇,其骑兵直抵渭水北岸,唐王朝刚刚经过“玄武门之变”,政局不稳,无力抵抗,长安城不得不再次宣布戒严[6]卷2,《太宗本纪上》,唐太宗一方面令“简较户部尚书裴矩等二十余人各陈御寇之策”,调集尉迟敬德等将进行防御,另一方面不得不亲自“出自玄武门与侍中高士廉、中书令房玄龄、将军周范驰六骑幸渭水之上”,隔河与突厥颉利可汗进行谈判,最终通过刑白马、重立盟约而使突厥撤军,解除危机[15]卷991,《外臣部·备御四》。
安史之乱后,关中地区又时常遭到吐蕃的侵扰,长安城因受到战争威胁而前后实施过五次戒严。广德二年(764)十月,仆固怀恩叛乱,引诱吐蕃军队侵入关中,丁卯“寇奉天,京师戒严”,直到十一月乙未,叛军与吐蕃军溃败,京师才解严[6]卷11,《代宗本纪》;永泰元年(765),又因吐蕃犯西陲,京师戒严[6]卷145,《李忠臣传》;大历二年(767)九月甲寅,吐蕃寇灵州、邠州,京师戒严,到十月戊寅,灵州奏破吐蕃二万,京师才解严[6]卷11,《代宗本纪》;三年(768)八月丁卯,吐蕃十万寇邠州,京师戒严,九月唐军进行反击,戊戌,灵武破吐蕃军六万,战争威胁才算解除,京师解严[6]卷11,《代宗本纪》。贞元二年(786)八月丙戌,吐蕃寇泾、陇、邠、宁等州,诸镇守闭壁自固,京师戒严;九月乙巳,吐蕃又进寇好畤,京师又戒严[6]卷12,《德宗本纪上》。可见,戒严已经成为唐后期长安城应对吐蕃入侵的主要措施。兴元元年(784),陆贽向唐德宗上疏中就提到:“自禄山搆乱,肃宗始撤边备,以靖中邦,借外威,宁内难,于是吐蕃乘衅……不能遏其侵。故小入则驱略,深入则戒严。”[4]卷157,《陆贽传》当然,除了吐蕃入寇之外,长安城在安史之乱期间和甘露之变时也因面临可能的战争威胁而实施过戒严[6]卷10,《肃宗本纪》[4]卷179,《郑注传》。
除京师长安以外,地方城市在战时也会实施戒严应对战争。安史之乱期间,安禄山遣史思明率军围攻平原郡城,太守颜真卿实施戒严[36]卷16,《颜鲁公集神道碑》;至德元载(756),潼关失守后,叛军攻入关中,其将安守忠及李归仁、安泰清至大和关,逼近凤翔,凤翔城因而实施戒严[6]卷110,《王思礼传》;泾原兵变发生后,唐德宗逃至奉天城,朱泚遣军围城,奉天城亦实行戒严以应对之[28]卷1;中和元年(881),诸道行营都监押衙何群在荥阳作乱,被都虞侯发现,都虞侯大惊失色,“驰出戒严”[35]1201,在荥阳城实施戒严,应对叛乱。

表1 唐代城市戒严事例统计表
(二)城市戒严的具体措施
尽管戒严是唐代城市战时应对战争危机的主要举措,但是由于历史文献的阙载,关于古代戒严我们了解的很少,只能根据零散的记载对唐代戒严的具体内容进行分析。
首先,当战争来临之时,城市管理者要做好战争动员,鼓舞人们的战斗士气。安禄山反叛,围攻饶阳,守将张兴“开张祸福,譬晓敌人”,鼓舞城内军民士气,因而“众心遂固”,饶阳最终守城一年[4]卷193,《忠义下·张兴传》。建中末,李希烈攻陈州,分兵劫掠诸县,项城县令李侃召集吏民,曰:“令诚若主也,然满岁则去,非如吏民生此土也,坟墓存焉,宜相与死守,忍失身北面奉贼乎?”城内士卒、百姓受到鼓舞,纷纷表示誓死守城,敌军久攻不下,“遂引去,县卒完”[4]卷205,《列女·杨烈妇传》。唐僖宗乾符中,黄巢从长安撤军东归,围攻陈州,陈人大惧,刺史赵犨恐众人离心,乃鼓舞众人曰:“忠武素称义勇,淮阳亦谓劲兵,是宜戮力同心,捍御强寇,建功立节,去危就安,愿君图之。况吾家食禄久矣。今贼众围逼,众寡不均,男子当死中求生,又何惧也!且死于为国,不犹愈于生为贼之伍耶?汝但观吾破贼,敢有异议者斩之。”于是众人“靡不踊跃”,积极防御,多次击退敌人的进攻,甚至主动出城攻敌[15]卷400,《将帅部·固守二》。
其次,增加城市的守军。一方面,征集、武装城中的青壮年人口,增加军队数量,补充城市防御力量。天宝十四载(755),安禄山叛乱,平原太守颜真卿实施戒严,征调郡中所集“静塞军屯丁三千余人”,又召境内武举人,并散财募义勇之士,很快召集万人[36]卷16,《颜鲁公集神道碑》;永泰元年(765),仆固怀恩引吐蕃军队入寇关中,京师戒严,唐代宗下令“括私马,京城男子悉皁衣团结”[6]卷11,《代宗本纪》。另一方面,向邻近地区求援,请求派兵增援。安史之乱期间,史思明兵围常山郡城,因城内兵少,太守颜杲卿“求救于河东”[4]卷192,《忠义中·颜杲卿传》;永泰元年(765),吐蕃入寇,京师长安进入戒严状态,唐代宗下诏征调“郭子仪自河中至,进屯泾阳,李忠臣屯东渭桥,李光进屯云阳,马璘、郝玉屯便桥,骆奉仙、李伯越屯盩厔,李抱玉屯凤翔,周智光屯同州,杜冕屯坊州”[6]卷11,《代宗本纪》,增强长安城的军事防御力量。
再次,要做好人员和物资的分配与调度。颜真卿守平原时,征集万人军队后“遣录事参军李择交统之,以刁万岁、和琳、徐浩、马相如、高抗朗等为将,分总部伍”[4]卷153,《颜真卿传》。至德初,叛将尹子琦率兵二十万围睢阳城,太守许远“自以材不及巡,请稟军事而居其下,巡受不辞,远专治军粮战具”[4]卷192,《忠义中·张巡传》。《神机制敌太白阴经》中也讲到:“夫守城之法,以城中壮男为一军,壮女为一军,男女老弱为一军。三军无使相遇,壮男遇壮女,则费力而奸生;壮女遇老弱,则老使壮悲,弱使强怜。悲怜在心,则使勇人更虑,壮夫不战。”[34]卷2,《人谋下·攻守篇》《拒守法》记载:守城过程中,“城上一步一甲卒,十步加五人,以备杂供之要。五步有伍长,十步有什长,五十步、百步皆有将长,文武相兼,量材受任,而统领精锐”[33]卷152,《兵五》。咸通时,南诏入寇成都,西川节度使卢耽“选将校,分职事,立战棚,具礮檑,造器备,严警逻”,同时,张牓招募骁勇之士,厚给粮赐,应募者云集,“列兵械于庭,使之各试所能,两两角胜,察其勇怯而进退之,得选兵三千人”[5]卷252,唐懿宗咸通十一年正月甲寅。战时,根据每个人自身才能,合理分配任务,各司其职,相互合作,有利于提高城内有限的粮食、军器等物资的使用效率。
此外,守城期间还要增加城市巡逻,加强城市治安管理,防止有人趁机扰乱城市秩序及敌人偷袭或间谍渗透。《拒守法》载:守城期间,守城人员分为“或十队、二十队、三十队,大将、副将各领队,巡城晓喻,激励赴救”,“城上立四队,别立四表,以为候视”,若有敌偷袭,则去城五六十步,即举一表;若敌人以橦梯逼城,则举二表;敌若登梯,举三表;欲攀女墙,举四表。夜即举火如表[33]卷152,《兵五》。泾原兵变后,德宗幸奉天,城内戒严,诏令右龙武大将军李观“都巡警训练诸军戍帅”,征集五千余兵,“列之通衢,整肃鼙鼓”[15]卷418,《将帅部·严整》,加强城内的治安管理。兴元元年(784),李希烈纵兵围攻宁陵城,宁陵两城都知镇遏使高彦昭、宣武军马步都虞候先锋救援兵马使刘昌、御史端公张昌等率众守城,“分番上城,更直巡探”,后随着人员减少“并皆上城”[28]卷3;《拒守法》还强调:守城时,要加强城市防火,以防止敌人纵火扰乱人心,“城内人家,咸令置水防火,先约失火者斩。火发之处多,恐奸人放火,但令便近主当八部官人,领老小丁女救之。火起,所部急白大将,大将领亲信人左右救火”,若城中因失火而有兵卒及杂人骚动,城上守城之人“不得辄离职掌,乱走街巷者斩”[33]卷152,《兵五》。咸通初,裘甫叛乱,攻越州城,义成军节度使王式守越州,有贼间谍潜入城中“窥虚实”,探听“城中密谋屏语”,王式察觉后,“悉捕索,斩之”,严惩将吏横猾者,并严门禁,规定“无验者不得出入,警夜周密”[5]卷250,唐懿宗咸通元年四月乙未。唐末,王建等攻成都,陈敬瑄征发城中丁壮,“昼则穿重壕,采竹木,运砖石,夜则登城,击柝巡警,无休息”[5]卷258,唐昭宗大顺元年正月乙巳。当然,唐代城市战时戒严的内容绝不止这些,各城市都会根据自身的特点及面临的形势作出具体部署。
三、唐代城市战后的恢复措施
战争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危机的结束。战争导致城市的基础设施破坏,人口大量减少,战后初期的城市依然面临着严峻的军事、经济危机。因此,唐朝政府战后采取一系列措施,以恢复城市的正常秩序和发展。
首先,重建城市的基础设施。安史之乱中,洛阳地区是主战场,洛阳城内的宫殿、水渠都遭到严重破坏。至大历初,张延赏出任河南尹,他施政简约,“轻傜赋,疏河渠,筑宫庙”,经过数年的重建,“都阙完雄”,唐代宗下诏褒奖[4]卷127,《张嘉贞传附张延赏传》。黄巢起义军占领长安,使长安城遭到严重破坏,“宫观焚残”,唐军收复长安后,唐僖宗任命王徽为大明宫留守、京畿安抚制置修奉使专门负责长安城市设施的重建,王徽在“外调兵食,内抚绥流亡”的同时,“兴复殿寝”[4]卷185,《王徽传》,使长安城得到初步修复。唐末,洛阳城再遭兵燹,张全义主政东都后“缮池垒,作第署”,使“城阙复完”[4]卷187,《李罕之传》。
其次,通过减免赋税来恢复城市经济。为了使城市经济尽快地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过来,唐政府常通过给复,蠲免遭受战争摧残的城市赋税。武德七年(724),唐军平定辅公祏,唐高祖颁敕“逆贼辅公祐驱扇凶丑,蚁聚蜂屯,侵虐黎民,摇动城邑……扬越之民,新沾大化,见在民户,给复一年”[15]卷83,《帝王部·赦宥二》。元和十二年(817),平定淮西之乱后,唐宪宗下诏:“淮西百姓等,陷此凶逆,久罹残伤,莫匪吾人,宁忘优恤。宜准元敕,给复二年,仍委州县长吏设法安抚。”[23]卷124,《平吴元济诏》会昌四年(844),平定李同捷叛乱后,唐武宗“念彼战争之地,况当凋瘵之余,租赋且蠲,征徭合减”下诏泽、潞等五州给复一年[23]卷125,《平潞州德音》。据笔者统计,唐代因战争给复共27次,特别是唐后期,因战争给复22次[37]。
此外,招徕人口也是战后城市缓解危机的重要举措。隋末唐初,洛阳城“逢丧乱,郛邑凋残”,唐朝收复洛阳后“爰降纶旨,令实三州”,下令移民,处士康元敬家族自相州安阳迁徙至洛州阳城[38]咸亨085,《唐故处士康元敬墓志》。建中时,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叛乱,邻近的陈、蔡二州居民“多逃窜他邑以避祸”,叛乱平定后,陈、许等州节度观察使曲环“赋税均平,政令宽简”,招徕流民,“不三二岁,襁负而归者相属”[6]卷122,《曲环传》。大和初,横海节度使李同捷反叛,“大兵之后,满目荆榛,遗骸蔽野,寂无人烟”,沧州城沦为“空城”,唐廷任命殷侑为沧齐德观察使,他招揽外来人口,恢复经济,“周岁之后,流民襁负而归”[6]卷165,《殷侑传》。光启末,洛阳城“遭巢、儒兵火之后,城邑残破,户不满百”,张全义任河南尹,“披荆棘,劝耕殖,躬载酒食,劳民畎亩之间,筑南、北二城以居之”,故而没过几年,“人物完盛,民甚赖之”[32]卷45,《张全义传》。人口是城市发展的主体,战后招徕人口,对于城市的重建和经济的恢复都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战后,唐政府采取的重建城市设施、减免赋税和招抚人口等措施,有助于城市尽快从战争破坏中恢复过来,也有利于提高城市应对未来战争的能力。
四、结 语
城市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数千年来世界各地诞生了无数名城大邑。然而,这些曾经繁华一时的城市往往遭罹兵燹,在战火的硝烟中毁于一旦。唐代是中国城市发展的繁荣时期,同时又是一个战争频仍的时代,统治阶级之间争权夺利、农民阶级反抗剥削的战争和民族之间的战争,此起彼伏,相互交织。在这些战争中,各地大小城市成为首要的攻击目标,遭受战争之祸。作为唐王朝各级政权的统治据点,城市应对战争与唐政权的安危密切相关,因而唐王朝具有强烈的危机意识,非常重视城市应对战争机制的完善,在战前和战时以及战后都采取了诸多应对措施。在战前,一方面,唐代统治者不断完善府兵制,顺应时势改行募兵制,集中大部分兵力于关中,前期在陕北建立数道防御突厥的军事防线,后期则在京西北建立抵御吐蕃的军事防御体系,同时不断扩充禁军,以此来增强长安城的兵卫防御力量,各地主要城市也都驻守有一定的兵力,以应对战争的威胁;另一方面,唐代城市也都注意修缮城墙、城池,储备军械、粮草等物资,以增强城市抵御战争的持久性,大大提高了城市应对战争的能力。在战争来临之时,唐代城市往往通过实施戒严加以应对,做好战争动员,鼓舞战斗士气,征集青壮年入伍,同时向外求援,合理调配人力和物资,严控城内秩序,防范敌方的间谍和破坏。战后,唐政府也会采取一些措施使城市尽快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过来。
唐代城市应对战争机制的完善,既折射出唐代战争之频,战祸之烈,又反映出唐人城市危机管理意识和应对能力的提高。战前措施是唐代城市应对战争的基础,战时措施是城市应对战争的关键,战后措施是城市走出战争创伤、恢复发展的必要措施。城市作为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唐代城市应对战争措施的实施和机制的完善,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城市的防御力量,提高了城市在战争中的生存能力,减轻了战争对城市的破坏,保持了唐王朝在各地的政权统治,保护了城市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战后措施的采取保障了城市经济和文化的可持续发展。